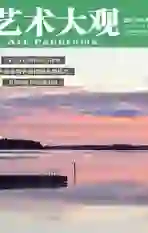《乐书要录》中的音乐美学思想
2024-02-15郑子依

摘 要:本文探讨了唐代乐律著作《乐书要录》中的音乐美学思想。通过分析《乐书要录》中关于音乐与自然的关系、音乐的教化作用以及音乐审美过程中的实践性与感知性,初步展现了书中蕴含的音乐美学理念。《乐书要录》不仅继承了历朝历代的音乐美学思想,还体现了唐代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乐书要录》;《美学》;音与自然;七音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357(2024)35-00-03
《乐书要录》是唐代的一部乐律著作,成书约公元689年之前,原书共十卷,现存三卷(五、六、七卷)。其书征引了大量的前人著作,如《礼记》《华谭论》《月令章句》等数十部,其中不乏含有已经佚失的古籍。就现存内容观之,《乐书要录》中不仅阐述了乐律学说,还蕴含一些音乐美学思想,尤以第五卷为甚。当前学界研究聚焦于其乐律理论层面,对其中表达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少有涉及。诚然,书中音乐美学之论述并未独立成章,而是散见于各章节的字里行间。但作为唐代官方钦定之书,《乐书要录》中的音乐美学思想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因而具备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唐代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它不仅继承并发展了历朝历代的音乐美学思想,而且在俗乐兴起的背景下,多种思想并蓄并存,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李西林在《唐代音乐文化研究》中指出:“多元化特征是唐代思想、文化、艺术多种派别类型并存合流的典型反映[1]。”书中与音乐美学有关的论述大多分散在第五卷的各个章节中,如论每均自立尊卑义、乐谱等。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音乐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古代艺术家深谙音乐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早在春秋时期,已有先贤提出音乐是源于自然的观点。《左传·昭公元年》卷十五载:“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2]。”也就是说,所谓“五声”(宫、商、角、徴、羽)皆来源于天之气,是天地之间本就存在的。同时期,虢文公的“省风”说,师旷的以乐听风说等都肯定了音乐与自然的联系。老庄的美学思想继承了此观点,将“气”与“风”联系在一起,倡导音乐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发展理念[3]。国学经典著作《老子》中有四章涉及音乐,蔡仲德先生把其中的音乐思想概括为“音声相和”“五音令人耳聋;乐与饵,过客止”“大音希声”三个部分,其中,“音声相和”中指出“声”乃人为之物,借器物而发;“音”则源自自然,未经雕琢。二者既相互对立,又和谐统一,二者之间存在矛盾的辩证关系。书中推崇无为而自然的声音,而音之所指的是自然之美,这正是老庄学派推崇的。这些思想在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李贽的《童心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乐书要录》中充分体现了音乐与自然的关系,认为音乐源于自然之气。卷五《辨音声 审声源》一章记载:“夫道生气,气生……然则形、气者,声之源也。”书中认为,“声”产生的源头源于自然,自然中产生“气”,“气”再通过一定的运动产生“声”,这表明声音的产生源自自然的流转和运动,是自然发生的现象,并不是我们人为获取的。书中自注解释:“无体无声者,道也。”其中,“无体”指的是没有规定的礼节,“无声”指的是不依托于人或乐器的音,也就是天道自然的思想。这一思想继承了前文所提到的有关老庄的音乐美学思想。后卷五《论二变义》也记:“夫七声者,兆于冥昧,出于自然。理乃天生,非有人造”,又为这一思想添加了佐证。另外,在《乐书要录》中也存在一些“音”与“声”之间关系的表述,第五卷《乐谱》记:“声者,音之质;音者,声之文。非质无以成文,非文无以成乐。”声是音的质地,音是声的文字,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这与《老子》中所谈论的“音声相和”有所呼应。在蔡仲德先生看来,“音”“声”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据其分析“音”是自然的,未经修饰的丑,而“声”是人为的,加工的美,美丑相和才得以协和之音。而在《乐书要录》中,显然“声”与“音”之间的关系已密不可分,而这种两者相和的背后体现出一种“和”的音乐美学思想。这种“和”思想从三国时期阮籍的《乐论》中“至于乐声,平和自若”,到明代徐上瀛的《溪山琴况》的“二十四况”都有所体现。
综上所述,《乐书要录》继承了春秋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书中认为,音乐源于自然之气,这一观点与老庄所推崇的“道法自然”思想一致。同时,也继承了关于“音声相和”的理论,探讨了“音”与“声”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体现了“和”的音乐美学思想。
二、音乐的教化作用
对于音乐教化功能的认识,在春秋时期已初见端倪。《国语·晋语八》中,师旷的言论:“修诗与咏之,修礼以节之”[4]便已揭示了音乐对社会风化的潜在影响。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乐教思想,体现教育最终落实到“乐”来实现,十分重视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他倡导的“礼乐合一”思想,不仅强调了音乐作为艺术表达的重要性,更突出了其作为教化手段的独特价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也凸显了音乐在塑造社会风气,提升民众品德方面的独特作用。孟子亦将音乐视为教化人心、弘扬仁义礼智的重要途径。他认为,音乐与人的品德修养紧密相连,通过音乐,人的“仁”和“义”得以彰显。与孔子稍有不同的是,孟子更加注重“与民同乐”,意在通过音乐实现更为广泛的社会教化效果。至汉代,五音(宫、商、角、徵、羽)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据《汉书》记载五音与五行(土、金、木、火、水),五常(仁、言、貌、视、聪),五事(思、言、貌、视、聪)相联系的[5]。但两汉后,由于国家动荡不安,这种思想便逐渐衰弱。直到唐代,经济繁荣发展,各类不同的思想观念才重新焕发生机。
《乐书要录》卷五第十一节《乐谱》对宫、商、角、徵、羽五音的教化功能进行了阐述。以书中论述“角”为例:“角音调则人道得,人道得则君有恻隐之心,好生恶杀,不夺人时,同其忧乐,人有仁施之行而无争夺之心,不隐山薮,竟游道艺,岁星修度,和风顺节,苍龙在沼,木并生。角乱则忧。”大致意为“角”调和谐,没有超过应有的限制,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协和,人们心中也不会有所歹念,繁荣安定。虽未直接有教化相关的词语出现,但其中表明了音乐对人的影响。如“人道得”,通过“角”的熏陶,人们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关系也会和谐有序,体现了“乐”具有道德教育的功能,即“以乐成德”的思想内涵。正如《荀子·乐论》中荀子所言:“君子乐得其道,可以善其民心”,这正是乐教思想的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乐书要录》中的观点与孔孟思想所倡导的“乐教”思想相契合,认为音乐能够引导人心向善、提升品德修养。这种思想在文人中得到了广泛接受。如白居易《沿革礼乐》中所言:“苟可以和人心,厚风俗,是得作乐之本情矣[6]。”即便李世民对孔孟思想中一些过于夸大音乐作用的部分有所异议,但他同样肯定了音乐在调和人心、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
三、“耳听心思”和“耳决之明”
《乐书要录》卷五第一节《辨音声 审声源》记载:“然象无形,难以文载,虽假以分寸之数,粗可存其大略,自非手操口咏、耳听心思,则音律之源未可穷也。……此识知音之至言,人妙之通论也。”此段文字大致意思是音乐是无形的,虽然假设以分寸的数理方法可以粗算其大概,但若不是自己亲自演奏演唱,聆听领悟,是不能完全领悟音乐的真谛的。用文字记载的方法只是更方便传播,终归不是精准的,用听觉记录才是最为准确的[5]。这一段中蕴含两点审美方向,即“耳听心思”与“耳决之明”,均凸显了音乐审美过程中的实践性与感知性的重要性。
其一,“耳听心思”强调多方感官的协同参与心灵的领悟,这与中国古代先贤美学思想对“心”之议题的侧重不谋而合。在中国古代美学体系中,“心”被视为连接外在客观世界与内在主观情感的桥梁,是审美体验得以发生和发展的核心所在。这一观点在诸多经典著作中均有体现,《庄子》中曾言:“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段话不仅阐述了在聆听音乐时,应超越耳朵这一单纯听觉器官的局限,还要以心去感受声音的韵味与意境;更进一步指出,即便是心的感受,也非终极目的,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去感悟那气韵相通、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最终达到一个“心斋”的境界[3]。这种状态,是心灵的一种极致的宁静与纯净,是审美体验的最高境界。
其二,“耳决之明”是音乐审美过程中的重要能力之一,“听”是最为精准的,而文字记载只是一种辅助工具。春秋时期的单穆公早已认识到音乐是一种听觉上的艺术,故而意识到人的听觉是有限的,需要一定的规则加以节制,如果超过此限度便不能欣赏到音乐的美[3]。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古代的音乐讲究平和、节制之美。这种美,既体现在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上,也体现在音乐的演奏和传承上。与其同时期的《乐府杂录》中,便有相关的论述。修海林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中,将其定义为“音乐审美中‘耳道’的作用”。《乐府杂录》中记载的唐玄宗命人“造谱”之事,以及乐伎张红红“记曲”的事宜,都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4]。它们表明,在古代音乐的传承过程中,听觉记忆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谱面虽然重要,但只是作为辅助工具存在。真正的音乐,是存在于演奏者的心中,是通过听觉记忆得以传承和发扬的。所以,中国古代的音乐讲究平和,节制之美。这种思想,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影响深远。它使得中国古代音乐的流传方式,惯于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即使有谱例存在,也并非事无巨细地体现所有细节。演奏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对音乐进行二度创作。这与西方遵循谱例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差异,也导致了中西两方在音乐传播、教学方式上的不同。
此外,《乐书要录》卷五第三节《论二变义》中论述了其认同的音乐审美形式,即七音。简单来说,是在五音的基础上,加入了两个变音,即变徵和变宫,形成了七声音阶。相较于五音,七音提供了更多的音高变化和音乐表现力。文中载道:“五声二变。经纬相成,未有不用变声能成音调者也。故知二变者,宫徴之润色、五音之盐梅也、变声之充赞五音,亦犹晕色之发挥五彩,不知音者,莫识其源。”此言论充分肯定了七音的不可或缺性,并且认为不用变宫、变徴便不能称之为音调,把其定义为乐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这一观点的形成正是和当时蓬勃发展的经济有关,随着外来音乐文化的积极融入,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蓬勃发展,而变音的使用能够增加其趣味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乐书要录》秉承着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外来文化并不排斥。实践中,七音的理念在唐朝的音乐作品中也得到了体现,如姜夔的《扬州慢》《杏花天影》等。从理论层面看,“八十四调”的提出者万宝常,以及赞同此理论的祖孝孙、张文收等人,可推敲出也是偏向于变音的使用[7]。然而,保守派对此却持不同意见,如陈旸《乐书》表示:“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
四、结束语
《乐书要录》在音乐美学方面既是先前音乐思想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其融合发展的产物。书中展现了其音乐的教化功能,又体现了唐人追求音乐自然和谐之美的审美追求;既注重传统音乐的传承,又展现出开放包容的音乐思想。这些特点不仅体现了《乐书要录》自身的独特价值,也反映了唐代音乐审美的倾向和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1]李西林.唐代音乐文化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
[2]洪亮吉,撰.春秋左传诂[M].李解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3]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4]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
[5]赵玉卿.《乐书要录》研究[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6]张小雨.白居易乐教思想述论[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2(06):98-104.
[7]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