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气与势
2024-02-04陈正宏
陈正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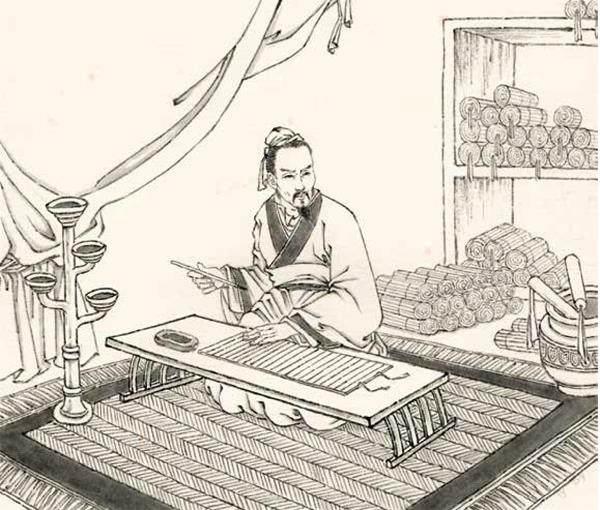
孟子对孔子的基本价值取向既有继承,也有推进和提升。(冯涛 / 绘)

陳正宏
说起孟子,今天的我们很容易把他跟孔子连在一块儿,孔孟仿佛是兄弟的感觉。其实两人虽然在儒家系统里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生活的时代却相差大约两百年,虽然都算是周王朝,孔子东奔西走的时代是春秋,孟子则已经到战国了。
关于孟子的生平,现存真正早期的文献其实很少。比较靠谱的,只有《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里的孟子传记部分。这篇孟子传,总共只有137个字,连孟子的名字都没记(今天我们知道孟子名轲,是据给《孟子》作注解的东汉学者赵岐的记录)。而这137个字中,还有40个字是写秦用商鞅、富国强兵之类历史背景的。剩下的97个字里,写孟子实际生平的,只有三点:第一,他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子思的再传弟子;第二,他到齐国和魏国推销自己的政治理论,都不受最高当局待见;第三,之所以不受待见,是因为当时各国都忙着合纵连横,以打胜仗为最高目标,而孟子却还在宣传他坚守的三代道德,不合潮流了。所以最后,他只好跟自己的学生一起,做没有国家资助的自选项目,写成了《孟子》七篇。
这七篇《孟子》,后来被各分上下,逐步演变,就成了今天我们见到的通行的十四卷本《孟子》。和记录孔子金句的《论语》相比,它字数上已经翻倍,形式上也多了战国时代流行的策士论事的精密逻辑和激情说理。但直到唐中叶,《孟子》至多只能算是《论语》的影子。我们看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像河北定州中山怀王刘修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那样高规格的西汉诸侯王墓葬里,都一再出土竹木简本的《论语》,就可知两千年前《论语》就红了。反观《孟子》,虽在东汉班固主纂的《汉书》里记录了西汉官方典藏有其书,但唐以前《孟子》的书本实物,无论是简帛还是纸本,到今天好像一片半叶都没有传下来。
所以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孟子和《孟子》的地位后来那么高,历史上一定发生过一次或多次时来运转的突变。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些突变之中,数唐宋两代接力而行的“孟子升格运动”最为著名:以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为先锋,诗人皮日休为策应,宋代大学者朱熹进一步推举,孟子在儒家名流的序列里,第一次被抬升至仅次于“至圣”孔夫子的“亚圣”地位;《孟子》一书,最终也跟《论语》一样名列经部经典。这场运动自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这里无法细说。但透过《孟子》一书,看看其中所言能跟《论语》比肩甚至超越的东西,大概就能理解唐宋以后的读书人,何以对孟子抱有如此高的热情。
首先是孟子对孔子的基本价值取向有不少继承。像他在《尽心上》篇里说的“君子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前面说的是行孝悌,中间说的是成君子,最后说的是做导师,都精准地踏在孔子的原有路径上。
当然也有推进和提升。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于个人立身处世提出了比孔子更严格的标准。他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这里的“大人”,与孔子所说的“君子”近似,而形象更显高大。葆有赤子之心的“大人”,在孟子看来,做人的底线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更高一级则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有意思的是,孟子还进一步为他心目中的大丈夫们设定了种种极端的情境,比如《告子下》篇里那段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为开头的话,由于被收入现代中学教科书里,是今日读者再熟悉不过的。而对于期待成大事的大丈夫们必须施以那样炼狱般的考验,背后的理据,是因为对于负有责任的君臣和士大夫而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正因此,在最棘手的生死问题上,孟子在《告子上》篇中进一步把“义”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位置: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舍生取义,意味着把道义的坚守和理想的实现,看得比个人肉身的存在更宝贵、更重要。这样的理念,作为一个人面对生死抉择时的一种不二决断,出现在距今两千三百年前礼崩乐坏、诈伪层出的战国时代,不能不说是一种异数。但它在中国后来漫长的历史中,尤其是历次反抗外来入侵者的战争中,成为千千万万烈士奋不顾身的精神来源和行动指南,又说明这一理念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真实分量。儒家的形象,在孟子的努力下,因此也由相对文弱的文质彬彬的君子,上升为不乏英雄气概的大丈夫了。
说到英雄气概,就不能不提孟子在自述修为境界时说过的一句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在《公孙丑上》篇中,当弟子以“何谓浩然之气”相问时,孟子还作了一大段解说,中心意思是这股“气”,是与“义”和“道”相互配合而存在的,当你用正义去培养它,它就会充塞于天地之间。“气”从一种自然的生态,演变为中国人文精神里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应该就是从孟子这里开始的。所谓“人活一口气”“做人要争气”,形容一位正派人经常用“一身正气”这样的词,诸如此类的说法,追溯上去,直接的源头就是孟子的“浩然之气”。而作为精神气质外化的“浩然之气”,从中国人的普遍意识里说,其实就是对于正义的一种持续不懈的追求和坚守。
舍生取义,意味着把道义的坚守和理想的实现,看得比个人肉身的存在更宝贵、更重要。儒家的形象,在孟子的努力下,因此也由相对文弱的文质彬彬的君子,上升为不乏英雄气概的大丈夫了。
此外,与“气”相关,在孟子笔下落墨不多却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势”。所谓“势”,就是情势、趋势和潮流。《孟子》里直接出现“势”这个字的地方,只有很少几处,但像“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公孙丑上》)之类的话,已经透露出孟子是比孔子更懂得用言语运势甚至造势的人。我们看书里,他不时给跟他聊天的对方挖坑,即使对方是一国之君,聊天聊到“王顾左右而言他”也不管,就知道这孟夫子对于辩论上的乘势追击,是如何地偏爱。但其实在他的内心,对人性的了解是相当透彻的。他教学生识人,说听人讲话的时候,要“观其眸子”,也就是注意看對方的眼睛,因为对方的心事,在眼睛里是藏不住的,即是一例。
而以对人性的透彻理解为基础,加上对“势”的把握,成就了孟子的另一种显著的能耐,就是推己及人的功夫。推己及人,在孔子那里,说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与我的边界感十分明晰;孟子则跨出边界,更富热忱,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用同理心把最大多数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所以与孔子比较强调个人的学养不同,孟子更多看到的,是作为群体的人的力量,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要实现“人和”,靠的就不单是读书人个人的修养了。当然,这方面孟子走得最远的,是在《尽心下》篇里提出的如下论断——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传统中国语境里,敢说这样的话,是足够惊世骇俗了。
惊世骇俗,当然逃不过命运起伏的宿命。即便借了唐宋以后科举考试必考题那般有利的“势”,孟子和《孟子》一书,在14世纪之后依然命运坎坷。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读了《孟子》,很不舒服,扬言这老头要是活在我大明朝,绝没有好结果。而有确证的史实,是这位出身贫寒的明太祖下令删除了《孟子》里八十五条“词气之间抑扬太过”的违碍文字,刊成《孟子节文》一书下发全国,下令:“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并把孟子配享孔庙的地位也取消了。而那让朱元璋不悦被删除的文字中,就有上述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孟子说的中心意思,脱去君君臣臣的旧外套,不就和我们今天用现代语言表述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非常接近了吗?
史载当时一位担任刑部尚书、名叫钱唐的高官,公然反对朱元璋贬低孟子,面对几乎送命的危险处境,钱尚书带着棺材上朝,声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神奇的是,钱氏这股得自孟子的浩然之气,最后不仅让朱元璋没敢痛下杀手,还间接地迫使官方恢复了孟子在孔庙配享的地位。而到了今天,明初刻本《孟子节文》已非常罕见,未经删节的《孟子》全本,却是家喻户晓的大众读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