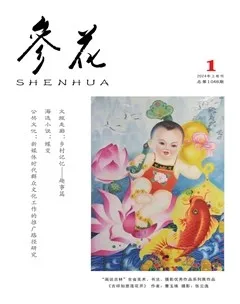燃烧的火凤凰(外一篇)
2024-01-31高俊香
高俊香
蓝天下,白云邊,它微微泛红的脸像一个羞怯的少女,修长的身材,包裹一身绿裙,肩头两片长长的叶子像垂着的绿飘带,它飘逸俊雅出尘若仙。
阳光俯下身轻轻地吻着它,风儿缠绵地拥住它,鸟儿也爱慕,轻轻地靠近它,喳喳地说着情话。它陶醉着,脸就更红更动人了。鸟儿忍耐不住猛地一吻,啄出它心头的一粒微火,这个得手的偷心贼逃跑一般无情离去,留下的疼颤落了叶尖上一颗硕大的泪珠。阳光吓得没稳住脚跌落尘埃,风儿也惊得四散。
这是我在杖子边上种的高粱糜子,不必派它们用场,只为此时的景致,此景让我迷离,恍惚中又被带到了房后的红高粱地。
九月是高粱糜子最美的时节,穗大红,叶和秆微黄。父亲和母亲挥舞着银镰把一颗颗红穗子从秫秸上掐下来,捆成一捆一捆的,我负责运回院里放在“烟囱桥子”上,红红的穗子上带着的细长的秫秸叫“箭秆”。
父亲说趁着还没开始秋收,抓紧扎几把笤帚去卖,这笤帚糜子不湿不干颜色还好。说干就干,先“刮糜子”。一把不太锋利的铁锹,一块青石,锹头脸朝下担在石头上,右脚踩住铁锹,右手倒攥着糜子,左手为掌把糜子牢牢地担在锹刃上,右手使劲拽,刺啦刺啦,珊瑚珠似的高粱粒蹦了一地,母亲把籽粒都收起来,她说,入冬后新媳妇结婚用得着。没了高粱粒的糜子,又叫“细糜”,半缸清水,细糜一头扎进去,只剩下一节箭秆露在缸外。
当父亲张罗着要扎笤帚的时候,母亲便先忙起来,她从仓房的棚顶扯下一团凿软的麻匹打经子。打经子的纺车是奶奶从山东拿来的,途中车子摔坏,只剩了风叶和轴承,和连接两头叶片的撑子,架子和底座完全坏掉。父亲找了一个带杈的圆木做了一个架子和底座。不知这纺车用了多少年了,它的几根撑子都已极其光滑油润,母亲把麻匹的一端系在纺车的撑子上,右手拇指与食指捏一小团棉花,棉花裹住麻匹,扽紧麻匹,摇动纺车,手里的麻匹在飞快的旋转中一点点上劲儿,越来越快,快得像一只飞转的轮子,再快,只看见一圈圈的涟漪从母亲胸前荡开。
随着麻匹上劲的速度,母亲的手一点一点地往后移动,身体也随着一寸一寸地往后倾仰,仰到她快要坐不稳的程度才停住纺车,把这段上好劲儿的经子缠到撑子上,续上麻匹再转起来。她像平时舞《东方红》一样,一俯一仰,一停一顿。
扎笤帚需要一把剪子,一把镰刀,一个拐子,一个钢油丝腰绳,一团经子。先把细糜三棵一组在箭秆处绑好,需要几组由笤帚的大小薄厚决定。腰绳勒在腰间,拐子踩在脚下,嘴里叼着经子,拿起一组细糜在油丝绳上绕,油丝绳缠住细糜,这时开始用力勒紧,一组一组按顺序排列,笤帚头形成了。再扎笤帚把,这是最费工也最讲究的,此时箭秆被勒得向四外怒张着,真像要射出的箭。削减它们的气势,就是剪掉中心多余的部分箭秆,再将剩余的箭秆攥到一起成胳膊粗细,不过此时它依旧带着不服,像一只握紧拳头血脉偾张的手臂。
一根根地摆弄,一根根地排列,抚摸是最好的温柔。
笤帚把像一只要变身的飞鸟,低头轻飞进油丝绳的底部,顺势一缠,交付自己的身体。父亲两手分别在油丝绳的两侧握住笤帚头和笤帚把,双脚使劲儿蹬住拐子,腰用力往后撑,身体如一张拉满的弓。双手赶着转动赶着使劲儿,让所有的箭秆都均匀地着力,着了力的箭秆服帖了。父亲从嘴上拿下经子在油丝绳勒的地方缠了几道,系好剪断,余出寸许来长的经子再压进箭秆里。勒好了开头的这一道,余下才是展示技艺的部分:扎“花把”。
他要雕琢,一板一眼地雕琢,用最粗糙的手雕琢一个最细腻的世界。
扎“花把”,就是把最外一圈的箭杆单数挑起,把下面双数的箭杆勒一圈,然后再把双数挑起勒单数的。如此反复,一个二尺来长的笤帚把要差不多一下午才能勒完。勒完的“花把”凹凸有序,看着精美,摸着舒服,勒“花把”的绳不能用经子,要用买来的很细的尼龙丝绳,绳细如刀,不小心便勒破他的指节。
笤帚疙瘩有魔法,而且是家家不一样的魔法。母亲的笤帚疙瘩喜荤不喜素,动不动便奔着我屁股上的肉来,我只能两手捂着往爷爷奶奶身后藏。邻居二妈手里的笤帚疙瘩总能让她男人笑,她总是攥着笤帚用疙瘩头笑嘻嘻磨蹭她男人的肩膀,然后软声说话:“给我抱柴火去!”她男人就笑嘻嘻地麻溜去了。小红她妈的笤帚疙瘩最厉害,会飞!冷不丁就飞出多老远,“吧唧”一声撞门框上或者撞杖子上……
有一回小红让我给父亲传话,让他再扎笤帚的时候别留笤帚把,父亲不听,他扎的笤帚细糜都使没了,笤帚把都不坏。
我九岁那年,家里的老房子很陈旧了,父亲张罗盖一座新房。
秋收之前新房子盖完,拉了两三千块钱饥荒,他置办了石磨与毛驴,准备做豆腐还债。
暮秋时候,父亲在去姑姑家的路上捡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男孩。
弟弟的奶粉实在赊不来的时候就喂些饭或糨糊,父亲除了做豆腐增加收入以外,就是在春季种地的时候,边边拉拉的地块和大块地的地头都种上高粱糜子,别人家地头地脑都是种一些苘麻籽或栽一些向日葵,这样种一是为了好辨认自己家的垄,二是阻挡猪呀牛呀的糟蹋地里的庄稼,我家的地头都种高粱糜子,只为了能多扎些笤帚,多换几个钱。
那个暑假,只有我哄着弟弟。他已有十来个月大,由于营养不良很瘦弱。我每天背着他,他穿一个背心,我穿一个大裤头和一件后背都是窟窿的背心。
直到要开学了,有一天父亲顶雨卖豆腐回来,打开藏在怀里的豆腐包,里面包着一个很漂亮的花裤衩和一件白底绿碎花的翻领背心,一摞本子,一捆铅笔,父亲嘱咐我要节省着用。
父亲每天半夜起来做豆腐,然后再出去卖豆腐,回来歘空儿(抽时间)扎笤帚。
那一年好像是我长那么大最遭罪的一年,大米饭捞不着吃,吃苞米面大饼子,上顿吃下顿吃。我最不愿意吃大饼子,早饭时揭一个饼子嘎嘎嚼着去上学了,白天在学校饿一天,晚上回家再吃一个饼子嘎嘎,还要帮着父亲卷豆腐布。晚上肚子饿得咕咕叫,父亲就在熬好豆浆之后,把我叫醒喝一碗。他会做好豆腐之后给我留一点,而我偏偏更不爱吃豆腐,比玉米饼子还不爱吃。我每天照旧一顿一个饼子嘎嘎,父亲又生气又心疼,就更不停地干活。平时他都穿得比较肥大,看不出他有多瘦削。有一次他扎笤帚往腰上勒油丝绳时才看到,原来他的腰比母亲的腰还细。油丝绳再紧紧地勒在腰上,就像门口的电线杆子。
他没日沒夜地干活,身上的力气似乎快用没了,他踩不紧勒笤帚的拐子了,为了能勒得有力量,他把门槛钻了一个小洞,拐子别在门槛外头,腰绳穿过小洞再勒到他的腰上,这样他在弓腰往后扽的时候能使得出力气。
腰绳好像勒进了皮肉,隔着衣服我能感觉到那种杀进肉里的疼,他每缠一道经子都是咬着牙用尽全力。
生活的困境就像这绳索狠狠地勒着他,他较着劲,咬着牙,不敢喊疼,也不敢停下。生活把困苦给了他,他把困苦转换成力量,还给生活一片阳光。
日子一年年的好了,不用再卖笤帚挣那几个钱。地头地脑的高粱糜子不用种那么多,够自家用就好了。自己家又能用多少,父亲的笤帚、盖帘大多都送了亲朋。母亲不许他种,他不听,他说他喜欢看红红火火的高粱穗子,像雪地里的炭火。
他扎笤帚扎了一辈子,村里人也都使惯了他扎的笤帚。老了他不想扎了,老兄弟们就商量他,再扎几把吧,扎几把够使上几年了。他就又绑上油丝腰绳。
大伙儿说扎成了能使就中,别太用力气,不比年轻,别干啥事都非得板板正正,糊弄糊弄能咋。父亲只是笑笑摇摇头。他这一辈子无论大事小事哪件事糊弄过呢!年轻时候铲地,人家都会糊弄,留夹垄,或者锄头拉长趟儿,用土把草抿住,别人一条垄轻轻松松铲到头,他则累得满头大汗才铲一半,不剩一棵草,不杀一棵苗。人家到地头歇息他在铲地,人家回家吃中午饭了他还在铲地。大伙儿背后说他,落下点草就落下点呗,还有下遍呢。
唉,奈何他不会糊弄。不论人前背后,不会糊弄也不会说假话,更不会玩心眼儿,就这样实打实的一辈子。
“粒粒珊瑚珠,节节琅玕玉。”每一棵秫秸就这样自然地摆着,便是顶级的艺术品。
西仓房像是一个小型的秫秸用具收藏馆。支起的木板上从南至北一溜儿排开,都是父亲用秫秸制成的各种生活用具。
我说扫炕的弯把笤帚像一张北斗,转动冬夏,转动花开花落。他点头。我说扫地的长把扫帚像一颗歇脚的流星,刷锅的刷帚像一只倒挂的丝瓜。他点头。我说大大小小的盖帘像天边或远或近的圆月,长长短短的弯帘像大大小小游水的小船。他摇头。他说他不喜欢小船,无根无基漂泊不定。
他扎不动笤帚了,还种高粱糜子。只在杖子边上种一溜儿,他把红穗子一缕一缕地挂在墙上。他说小时候上私塾先生给他们讲过,高粱糜子的穗子像火凤凰的羽毛,那是它燃烧重生时落下的星火,有着不灭的灵魂。
到哪里去
一锹,一筐,一人,到田野里去,小根蒜等在那里呢!
西风叟是个爱制造浪漫可爱的小老头儿,它把大地描成华贵厚重的金色,树叶染出赤橙黄绿的斑斓,云梳理得若羽毛轻盈,天幕洗得纤尘不染清透碧蓝,连阳光都揉成波浪的形状,铺满角角落落,铺进午后的时光。
南风君是好“色”之徒,偷偷潜回来在缤纷的叶子间流连缠绵。叶子也是情愿的,你看它们颤抖着的娇媚的身子就知此刻它们内心有多欢畅。
虽然霜降已过,但西风叟未催,南风君便赖着不走。我也被眼前的景象迷住,徘徊流连忘了初衷,南风这个家伙居然乱情,趁我不备跑来轻浮我的鬓发和额头,气得我一把推开它躲进田野。
推倒庄稼的田野有些落寞,一垛垛竖立在阳光里的玉米秸秆像一座座收容岁月的城堡,过往的虫声、鸟鸣、白云、星辰都在这里留下足迹。
无影无踪,小根蒜是都躲起来想逗我吗?弯下腰吧,或许是想要个见面的仪式感吧!目光一寸一寸认认真真在一堆一堆即将匍匐大地的蒿草里,浅浅见底的小溪畔寻找。
轻手轻脚,不敢弄疼蒿草倦了的脊背,它驮着日子里的风雨好不容易走到生命的这一站,更别踩碎脚下的枯叶,它们只剩一副脆弱的骨骼了,相拥着挤成一块厚被的形式盖住身边裸露的土地。大地给它一份养育的恩情,它反哺大地一份守护的爱。草木知道感恩,当它们用瑟瑟颤抖的身体里最后一点温度去温暖即将僵硬的土地的时候,我们则以粮食的名义在一步步无情地铲除它们。
顺着一缕倒在地上浅黄如线的叶子的指引,剥开失去油润而变得干涩的土层,大大小小的小根蒜暴露在眼前。它们惊诧地看着我,一个个脏了吧唧,沾着许多黑皮,有些瘦弱、干瘪的须子似几根乱线头一样纠缠着。我一直认为小根蒜的须子才是它的灵魂,白白粗壮的长须,灌满土地的精华,吃在嘴里有嚼头。蒜头大的如拇指肚,最小的跟一粒大米差不多,舍不得扔,摘得干干净净放入筐里。这要是父亲看到,准会指着我的脑门数落:你呀,这是吃命呢!它们可爱又可怜的模样惹得我总是低眸,用温柔至极的眼神去看,然而一个冷不防,被它们一把给我按回到童年,按回到那个在田野里奔跑攥着大把小根蒜花的女孩面前。
广袤的旷野里,小根蒜的花开了,众多的野花里数它最窈窕,淡紫色极小极小的花,像一个个小伞挤在一起,鲜艳且优雅,尤其那一条举着花冠的长茎,像一只美人的纤臂,修长有弹性。它的颜色从根部至顶部由浅变深一点点地变化着,又像一条温润的玉带。我们则会把它变成更精致的链子,戴在脖颈、手臂、耳朵和发辫上。
灵巧的小手指欢快地舞蹈一般,左一下右一下,把花茎掰成每段两厘米大小的长度,每段之间皮是不能扯断的。很快一条绿玉粒串成的链子搭在手上,紫色的花冠就成了这条链子的玛瑙坠。戴在脖颈是项链,戴在发辫上是头花,缠在腕上就是手镯,不小心弄断的就做耳环和戒指,再采各种野花编织一个美丽的花环。当一个小男孩为一个穿着天蓝色连衣裙梳两条小辫子的小姑娘做完这些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新娘就坐着小伙伴用手臂搭成的轿子出发了。
小根蒜有好几个名字,大名“薤白”。我们从来不叫它的大名,就像我们在家里的时候都喊小名,只有在学校里才喊大名。它有好几个小名,小根蒜、野蒜、大脑瓜。三老板一见挖小根蒜的小孩老远就唱:抢吧菜,大脑瓜,小孩吃了学习好,小媳妇吃了能当家,老太太吃了眼不花!还拦住我们把筐里最大的小根蒜拿出来比较,挖得又大又多的他就使劲儿地夸赞,还会擅自做主,把筐里最多的抓一把匀给最少的。
当饭桌上家人都抢着我挖的小根蒜蘸酱吃得香的时候,我就笑嘻嘻地唱:抢吧菜,大脑瓜,有人吃,没人挖!他们笑话我,除了能挖点菜还能干点啥,我不生气,还会拎着那个有点夸张的大筐继续和小伙伴们去挖。小伙伴们嘲笑我的大筐,说我每次挖的菜连个筐底都盖不住,还嫌弃我挖的菜不干净,带着干草棍儿。她们就不说自己都有姐妹帮忙,而我只有我自己,在那一大帮孩子中,最小的我自己。
有一次我真的挖了大半筐,是叶子绿油油的时候,而且是干净整齐地放在筐里。提回家父亲很开心,中午用它炒了菜,还做了“菜团子”的馅儿,老屋的时光里至今还留着一丝炒小根蒜的香气。
铲二遍地的时候,妇女们把铲出来的小蒜头都收起来,去梗去须只留脑瓜儿,放筐内挂于檐下或仓房通风处。风干外皮的小蒜头失了大部分水分,只剩了辣气,变成了紫黑色,晶莹透亮,像我棉袄上的玻璃纽襻。来年下新酱了,酱发缸之前,舀一碗稀稀的酱汤,抓把小蒜头在手里搓搓,搓下的皮用嘴使劲儿一吹,小蒜头往酱汤里一扔,一顿饭下来个个满头大汗。我不敢吃,但看着他们欢快流汗的样子,也感觉到了一种舒坦。
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翻遍了田间地头壕沟土埂,只挖了少半筐,真正能算上蒜头的寥寥。曾经的餐桌上它唱主角,现在它没这个实力了,它被庄稼逼出了田野,苟且着在边边拉拉的地方落脚生存,恐怕这种地方它们也住不长了。看看这几年水泥路的路基上,就那么一点土地都被勤劳的人种上苞米、豆子,栽上苏子,他们很精心侍弄这些庄稼,一棵杂草都不许长。
前两天村微信群里村主任宣布要在地头重修拉地的道,让家家把占的“抹牛地”给让出来。每块地头都留有宽绰的“抹牛地”,为了春种秋收走车走人所留,是不允许种的。
是该给庄稼拉一条警戒线了,不然风都没了下脚的地方,只能气急败坏地在庄稼地里横冲直撞。你的垄抵着我的垄,你的苗压着我的苗,人在打,苗也在打。当阡陌重现的时候,可不可以允许一些野草生存呢?
它们该去哪里呢?没了家园又没处流浪的野草,天气会越来越冷,它们只有使劲儿佝偻起身体,躲避这一次胜过一次的寒凉。让它们去哪里呢?夕阳无声,默默地歇脚山后,白云无声,轻轻地酣于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