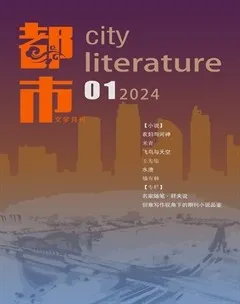生活和艺术的距离
2024-01-31李苇子
李苇子,2007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当代》《花城》《大家》《青年文学》《鸭绿江》《西湖》《山西文学》《黄河》《湖南文学》等纯文学刊物。有作品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海外文摘》《视野》《教师博览》等杂志转载。著有小说集《归址》。晋中信息学院创意写作教师。
生活就像一片片零散的叶子,艺术将这些叶子串联起来,攒成一棵摇曳多姿的树,树上有枝,有叶,有花,有鸟巢。对于小说来说,这个从叶片到树的过程,便是虚构。王安忆曾在《虚构与非虚构的》演讲中如是说:艺术还是应该到艺术里找,生活不会给你提供艺术,生活提供的只能是一个扫兴的结果,一个不完整的故事。
关于生活和艺术的距离,我们不妨借用《最后的晚餐》进一步阐明。抛开作品的宗教指涉性不谈,最基本的信息是:一群人在吃晚饭。画面中,一字排开的人皆坐在桌的同一侧,即,观众的正对面,除了c位的男性以正面示人,其余皆是侧面或半侧面。这根本不符合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在现实中,无论是长条桌还是方桌、圆桌,人们都是绕圈而坐。但是,假如完全照搬生活,按照一点透视的原理,c位的男性将成为离观看者最远的一个,相应地,他在画面中的占比最小,那就彻底违背了创作者的初衷,也影响了构图的和谐,艺术的主体性丧失殆尽,沦为生活的奴仆。
这便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生动的例子。
探讨这个问题的目的不是这个问题本身,而是想厘清长久以来困扰我的问题——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作家该如何处理生活和小说的关系?离生活太远,小说会变成奇观,靠过度扩张的情节会削弱作品的严肃性,而紧紧贴住生活(这似乎是当下倡导的一种创作态度),小说就变成生活的镜像还原,变得琐碎无聊,艺术性荡然无存。大概,正是因为后者的泛滥,才有了这样一种抱怨:看小说不如看非虚构。
相比书写当下经验的故事,我们更愿意看过去的事情,相比国内作家的作品,我们更愿意亲近国外作家的作品,这是不是恰恰说明了一点,陌生经验的重要性?在构成一个好故事的诸多必要条件中,猎奇到底有没有一席之地?也许,“猎奇”的表述太言重,我们不妨还是用陌生化吧。问题的关键在于陌生化的程度,我想起王祥夫老师的一个短篇小说,包工头想睡一年轻民工的女朋友,最后带着女人爬上了高耸入云的建筑工地的塔吊,在那间狭小的操作间里颠鸾倒凤。包工头、女朋友、工地和塔吊,这些素材本身没有任何陌生性,然而,组合在一起后却出现了陌生效果。尽管我们都知道这是虚构的故事,但我们依然深信不疑,知道虚构和深信不疑,会不会就是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
生活中,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但是,假如在小说中用到了吃饭这一素材,吃饭就不再和饱腹有关,而是为了引出别的东西,或遇见一個推进情节进展的人,或发生一件重要的事。卡夫卡为什么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而不是患病或工伤?大抵正是因为后者离生活太近,前者离生活较远,它像一枚大一号的针,更能刺激人们麻木的神经,人变成甲虫听上去过于奇观,但是接下去,作者用现实主义手法营造出一幕幕真实无比的生活场景,将二者之间的间隙做了弥合,让这一虚构具有了穿透现实的力量,而不是满足对生活的简单还原。
金晖的《在阁楼上唱歌》(《青年文学》2019年第2期)篇幅不长,大约只有六千多字,这个小说比较符合我心中好小说的标准。首先来说说作者的空间营造。故事发生地是一个江南小镇,对于我这个北方人来说,杏花烟雨江南几乎就是文学的代名词。“南方梅雨季节带来的水汽还没有完全褪尽,薄雾像轻烟一样在南方低矮的屋檐间若隐若现,偶尔一阵风吹来,轻盈得像鸟过枝头,一下就没影了。”这个描述让我想起苏童的“香椿树街”,潮湿和神秘,还带着一点儿腐烂的味道。《在阁楼上唱歌》里的街道有个极富诗意的名字“莲池巷”,可是,在这诗意的表象之下是一个凌乱、肮脏、治安很差的地方,“经常有警车呼呼地开进小巷来,抓了人后又呼呼地开走”。还有一群如嗜血动物般专门以刺探别人隐私取乐的可怕的当地人。这可真是对“出淤泥而不染”的莲的莫大讽刺。第三个空间是阁楼。我们总是在江南作家的笔下看到这一重要意象,狭窄的空间,晦暗不明的光线,樟脑的味道,木地板,旧家具,老物件,一个时髦的女人站在阁楼上听唱片。这大约是肮脏的“莲池巷”上唯一的净土。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莲池巷的人们似乎深谙其道,他们果然联手将这个女人的生活踩到了泥土中。“尽管知道秋喜和莲池巷的女人相处得很好,但后来看到她们像恶狗一样狠狠地向她进攻时,我并不感到意外。我说过,我们莲池巷的人是有欺负外乡人的习惯的,这也是他们日常的生活内容之一。”可怕的恰恰是那个“我并不感到意外”,这是比偶发的暴力事件更深层的暴力,是一种如皮癣般挥之不去的恶疾。
我先总结一下这个部分,我想说的还是艺术和生活的距离,江南小镇、莲池巷、阁楼三个空间让我陷入遥远的遐想,它们是陌生且极富诗意的,而填充材料的朴素又将我拽回到日常生活的真实,甚至是残酷。
莲池巷的生活本来是单调无聊且重复的,突然有一天,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突兀地出现在这块执拗而闭塞的”小镇上,这可真是朝饥饿的狼群中投掷出了羔羊。现在,一组对立关系出现了:本地人和外地人,土著和新人类,传统与现代,守旧与新鲜,不变与变。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一个永恒的、世代作家都在书写的历久弥新的主题,金晖能用一个篇幅极短的小说表现这一主题,是我喜欢这个小说的第二个原因。
女主角秋喜是个漂亮、时髦又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神秘之处主要集中在她有那么多漂亮衣服,却从来不出门工作。她的美和漂亮衣服让镇上的女人们疯狂。“虽然他们对外乡人心里总是隔隔的,但女人们天性总是爱美的,于是她们就去找秋喜取经。”这是一群实用主义至上的现实的人。但是,实用主义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便是用完即弃。当人们再也不能从祥林嫂那里消费到快乐时,祥林嫂便会被贴上不洁的标签打入遗忘的冷宫。秋喜则是另一极的祥林嫂。对一个女人最大的伤害莫过于骂她是个荡妇,而妓女则是荡妇里最淫荡的那类。于是,当地人用自己的阴暗给秋喜的“不寻常”找到了最心安理得的答案——她是个暗娼。这句话最终由一个小孩说出来,原本最纯洁无瑕的孩子,说出一句如此恶毒的话,我们当然知道孩童背后的操纵者是谁,总之,这是一把邪恶的钥匙,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将仇恨、嫉妒、罪恶统统释放出来,人性之恶像蝙蝠一样布满莲池巷的上空,让一个无辜的人找不到容身之所。刘庆邦在北师大的一次讲座中说,好的小说总是人性大于社会性,人性足够深刻,小说也就具有了社会性。这是我喜欢这篇小说的第三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