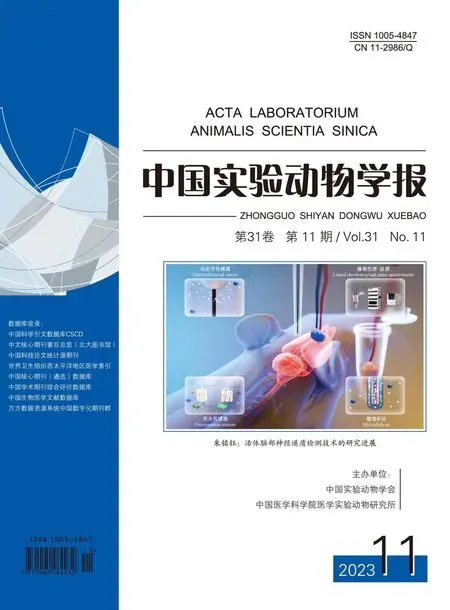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研究的小鼠和猴子动物模型
2024-01-29张博陈庭伟李孝琢李天晴董娥
张博陈庭伟李孝琢李天晴董娥*
(1. 云南中科灵长类生物医学重点实验室,昆明 650500;2. 昆明理工大学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院,省部共建非人灵长类生物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昆明 650500)
冠状病毒是单股正链的RNA 病毒,具有多种毒株,其中包括SARS-CoV-1(SARS-CoV) 和SARSCoV-2,这两种病毒均可导致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SARS-CoV-2 感染宿主细胞涉及病毒的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与宿主细胞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受体特异性结合,因此宿主细胞表达ACE2 是病毒感染的关键。 合适的动物模型对于研究SARS-CoV-2 的感染机制至关重要,也是药物和疫苗有效性评估的关键。 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与人ACE2 受体同源性相近的动物包括恒河猴、食蟹猴、非洲绿猴、仓鼠、水貂和猫等[1]。 近交小鼠由于在遗传背景上具有均一性,实验结果上有一致性等优点,因此被广泛用于研究基因功能或疾病机制。但是由于小鼠和人类ACE2 存在差异,传统的小鼠模型无法有效模拟SARS-CoV-2 病毒感染以及临床患者的症状和相关免疫反应。 因此,研究人员通过转基因、基因敲入、病毒递送等技术,构建能够感染SARS-CoV-2 病毒的关键动物模型,最终用于研究SARS-CoV-2 病毒的感染机制、评估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有效性,以及深入探究其致病机理。 本文综述了目前用于模拟SARS-CoV-2 感染的临床前动物模型以及构建这些动物模型的方法和策略。
1 小鼠模型
在许多病毒学研究中,小鼠模型被广泛采用。然而,由于SARS-CoV-2 感染宿主细胞主要通过人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human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hACE2)受体而非小鼠ACE2 受体,这导致野生型SARS-CoV-2 无法感染传统的标准实验小鼠。 鉴于此,针对缺乏新冠病毒易感染小鼠模型的现状,研究人员采取了多种策略来建立易感小鼠模型。 首先,从病毒角度出发,在小鼠体内通过连续传代新冠病毒的方式,筛选出能够有效感染标准实验小鼠的适应株,利用适应株建立易感模型。 其次,从小鼠角度来说,可构建ACE2 基因人源化的小鼠来实现这一目标。 由于转基因小鼠培育和繁殖周期较长,亦可通过气管接种腺病毒(adenovirus,AdV)或腺相关病毒(adeno-associated virus,AAV),使小鼠肺组织迅速表达人源ACE2(hACE2),从而促进SARS-CoV-2 对小鼠肺部的感染。 此外,为了更准确地研究新冠病毒攻击宿主后产生的免疫学反应,在小鼠肺组织人源化的基础上,还需将小鼠的免疫系统人源化,这将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SARS-CoV-2 感染人体后引发的免疫病理反应。 下面将详细介绍目前用于SARS-CoV-2 研究的小鼠模型,并讨论这些模型的致病特征。
1.1 稳定遗传的转基因小鼠模型
构建SARS-CoV-2 感染小鼠模型,表达人源的ACE2 基因是关键。 在早期,由于技术限制,通过将异源基因启动子驱动的hACE2 表达载体直接注射到胚胎中就可构建转基因小鼠。 涉及的启动子包括mACE2、hK18、hHFH4/FOXJ1、CAG[2-5]。 mACE2启动子驱动的hACE2 基因表达更接近于小鼠体内天然ACE2 的分布情况,但hACE2 基因表达较弱。而由hK18、 hHFH4/FOXJ1 人源启动子驱动的hACE2 基因的表达则更强,但改变了ACE2 在小鼠组织中的分布,从而改变病毒的组织嗜性。 总之,该方法的缺点在于外源性导入的hACE2 基因随机插入小鼠基因组中,可能干扰其他基因表达,同时无法兼顾hACE2 在体内的高表达以及表达分布接近体内的真实情况。 随着CRISPR/Cas9 技术不断成熟,这一技术也被用来构建转基因小鼠模型,并成功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研究人员利用CRISPR/Cas9 系统将hACE2 基因定点敲入至小鼠内源性ACE2 位点的2 号外显子中,这种方式不仅破坏了小鼠内源性mACE2 基因的表达,也保证了外源hACE2 基因表达分布与内源性ACE2 的表达具有一致[6]。 此外,将四倍体补偿技术和CRISPR/Cas9 胚胎干细胞基因编辑技术相结合,可以在35 d 内成功建立ACE2 人源化的近交系小鼠[7]。
SRAS-CoV-2 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转基因小鼠经鼻途径感染病毒后,除了出现相关的上呼吸道症状外,体重减轻是小鼠感染模型中最主要的临床症状[3-4]。 不同的毒株、感染途径、病毒感染剂量以及ACE2 在不同组织的分布差异,都可能会引起不同的临床表现和病理变化。 hACE2 小鼠经SARS-CoV-2 感染后会引发与人类患者高度相似的肺部疾病,包括弥散性肺泡损伤,间质性肺炎、炎症或淋巴细胞浸润以及肺血管损伤[2]。 人们发现,由于老年小鼠体内干扰素和抗体的产生明显受损,在感染病毒后,与年轻小鼠相比,病毒在其体内复制更加旺盛,从而导致症状加重[8-9]。 同时也发现,性别对于新冠患病严重程度也有影响,雄性小鼠比雌性小鼠的症状更加严重[10]。 目前K18-hACE2 小鼠被大多数研究人员作为SARS-CoV-2 免疫研究的对象,人们发现其感染病毒后,高表达与发病进程相关的趋化因子(如CCL2、CCL3、CCL4、CXCL1 和CXCL10)以及炎性细胞因子(TNFα、IL-6 和G-CSF)[11]。 这与人感染SARS-CoV-2 后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K18-hACE2 小鼠是目前研究新冠感染后机体免疫变化很理想的易感模型。
1.2 Ad5-hACE2 或AAV-hACE2 转导的小鼠模型
除了通过基因修饰的转基因小鼠过表达hACE2 基因之外,还可以通过病毒介导的基因递送方式在小鼠体内实现ACE2 的异位表达。 常用的病毒载体包括Adv 或AAV。 例如,通过鼻内或者气管接种的方式,使过表达hACE2 的腺病毒Ad5-hACE2感染大部分肺上皮细胞,促使SARS-CoV-2 在小鼠呼吸道内繁殖和复制,这一过程可以持续数天,导致小鼠体重下降约20%,在感染过程中,可以观察到肺部出现炎症浸润、出血以及肺泡水肿等病理变化,说明肺功能受到损害。 TNF-α 和IL-6 等炎症因子也显著上调[12]。 相较于腺病毒,腺相关病毒的免疫原性较低,通过AAV 介导hACE2 在小鼠肺部表达,再经SARS-CoV-2 感染,病毒同样可以在小鼠肺组织中复制,进而引发肺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的浸润增加,同时还诱导Ⅰ型干扰素和体液免疫反应[13]。 目前靶向小鼠肺组织常用的AAV血清型是AAV-6 和AAV-9,通过腹腔注射和气管接种AAV-ACE2 病毒,能够实现在小鼠肺部持续表达ACE2,时间可达28 周[14-16]。 感染AAV-ACE2 的野生型小鼠在SARS-CoV-2 病毒攻击后,病毒在hACE2 小鼠肺部的复制过程持续7 d 左右,出现了中度的间质性肺炎症状。 这些症状包括支气管周炎症、肺泡上皮弥散性感染、单核细胞以及衍生的巨噬细胞的浸润,不同品系小鼠免疫反应方面表现不一[17]。 免疫力强的小鼠能在1 周左右迅速清除病毒,而免疫缺陷小鼠,如IFNAR-/-和STAT1-/-小鼠,病毒清除的时间则较长[12-13]。 这种个体免疫差异能够很好地模拟临床上的重症症状。 值得注意的是,免疫缺陷小鼠被感染后,肺组织不再募集巨噬细胞,且CD4+、CD8+T 淋巴细胞以及NK 细胞的激活受到抑制,淋巴细胞数量减少,而中性粒细胞数量却显著增加,这一现象在SARS-CoV-2 患者的病理过程中相当常见[18-19],因此正向免疫反应对于抗病毒至关重要。 尽管AAV 或Adv 可快速获得新冠易感的动物模型,但与K18-hACE2 转基因小鼠相比,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能力降低,对应的临床症状也较轻,也就是说在模拟SARS-CoV-2 感染的病理特征方面存在一定限制,这可能主要归因于hACE的异位表达影响了病毒对细胞或者组织的亲嗜性。
1.3 新冠病毒鼠适应株筛选及其感染模型
为了应对缺乏适用于新冠病毒研究的小鼠模型,从病毒角度着手,采用SARS-CoV-2 在小鼠体内进行强制连续传代的方法,筛选能有效感染小鼠的新冠病毒适应株,即MASCp6。 经过对该毒株深度测序分析,发现与原始毒株相比,第一代(P0)的肺组织研磨液中,新冠病毒S 蛋白基因的受体结合域(receptor-binding domain, RBD) 已经出现了A23063T(N501Y)突变,该位点突变可有效增强病毒与小鼠ACE2 受体的亲和力。 随着传代至P36,获得了一株毒性更强的小鼠适应菌株MASCp36,其中涉及突变位点包括K417N、Q493H,该突变株感染小鼠后引起典型的呼吸道症状[20]。 同样,将SARSCoV-2-Hu-1 毒株在1 岁龄BALB/c 老年鼠中传代,病毒滴度达到峰值时处死老年小鼠,将收获的P1代病毒经鼻接种到幼鼠中连续传代,产生小鼠适应毒株WBP-1。 病毒序列分析显示,第一代出现了Q498H 突变,而Q493K 突变则发生在第五代,这些突变均发生在RBD 区域,增强了病毒与mACE2 的亲和力[21-22]。 使用TLR7/8 激动剂雷西莫德可以保护小鼠免受WBP-1 攻击,这种小鼠适应性毒株是研究SARS-CoV-2 和开发新疗法的有力工具[23]。 除了通过连续传代积累有利于病毒复制的突变外,还可采用反向遗传技术重塑S 蛋白抗原和mAce2 的结合部位,从而快速构建小鼠适应性毒株SARS-CoV-2 MA 重组病毒。 该病毒借助mAce2 受体感染宿主,产生的临床相关表型较hACE2 小鼠更为丰富,包括体重下降、肺功能受损、致死率和死亡率增加等[24]。并用SARS-CoV-2 MA 毒株在小鼠身上证明了新冠感染严重程度高度依赖于年龄大小的疾病特征,同时证实聚乙二醇化IFN-λ1a 在临床上可用于治疗SARS-CoV-2 引起的感染[25]。
1.4 植入人体组织或细胞的人源化小鼠模型
尽管可以通过基因人源化或筛选小鼠易感的SARS-CoV-2 毒株的方法建立新冠感染的小鼠模型,但是肺组织作为SARS-CoV-2 感染的主要靶组织,难以通过小鼠模型揭示人肺感染SARS-CoV-2 时的病理变化。 因此,拥有人肺成熟结构的组织对于模拟SARS-CoV-2 感染人体的过程至关重要。 通过手术将人胎儿肺组织移植到重症联合免疫缺陷小鼠(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SCID)的背部皮肤内,经过8 周的生长,建立了SCID-人肺小鼠模型,随后对该模型进行SARS-CoV-2 感染实验,结果显示病毒在肺组织中快速复制,引发了严重的肺损伤和强烈的炎症反应[26]。 但也有研究表明,将人胎儿肺移植到肾包膜下,更有利于人胎儿肺组织微血管的重塑。 无论是肾包膜移植还是皮下移植均支持病毒在移植肺组织中的感染和复制,借助该模型发现SARS-CoV-2 主要感染人Ⅱ型肺泡上皮细胞(human type Ⅱ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hAEC2s)以及气管中的纤毛细胞,并验证了口服EIDD-2801 这种广谱抗病毒药物能显著抑制SARS-CoV-2 在肺移植物中的复制[27]。
为了使人源化肺组织具备气体交换功能,从而更好地研究病毒传播,研究人员首先通过博来霉素破坏鼠源的肺细胞,随后通过静脉注射或者气管滴注的方式在原位嵌合人肺干细胞、人胎肺细胞、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ESCs)以及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iPSCs)定向分化来的肺样细胞,最终构建人肺嵌合小鼠模型[28]。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使用此模型来研究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报道。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模型中的人肺嵌合比例较低。
尽管人肺异种移植小鼠模型可以作为研究SARS-CoV-2 感染人肺部过程的有利工具,但要充分模拟SARS-CoV-2 病毒感染人类肺部引起的人类免疫反应过程仍然存在困难,主要原因是人肺小鼠模型缺乏人的免疫反应系统,因此在人肺小鼠模型基础上,通过移植人的骨髓将小鼠免疫系统人源化是探索临床中SARS-CoV-2 感染人体肺组织免疫反应的关键。 当SARS-CoV-2 感染该模型小鼠后,小鼠出现严重的炎症和SARS-CoV-2 相关的免疫病理学表型,这可能与巨噬细胞浸润和分化以及Ⅰ型干扰素上调有关[29]。 因此肺/免疫系统双人源化的小鼠不仅可以用于评估SARS-CoV-2 病毒感染早期引发的免疫反应[30],还可以作为评估抗体和类固醇疗法对新冠病毒早期感染影响的重要模型[31]。
2 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
与小鼠相比,非人灵长类动物(non-human primate,NHP),包括恒河猴、食蟹猴、非洲绿猴、狒狒和普通狨猴等,在生理特征和免疫调节等方面与人类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因此可以用于SARS-CoV-2感染的大动物模型。 ACE2 基因在多物种中的序列比对分析显示:恒河猴的ACE2 基因与人ACE2 基因的同源性为91%,且ACE2 与S 蛋白关键结合区域RBD 的氨基酸序列在人、食蟹猴和恒河猴中是保守的。 尽管如此,不同品种的猴子对SARS-CoV-2的易感性不一样,最敏感的是非洲绿猴、其次是恒河猴,最后是食蟹猴,这一现象表明有无ACE2 受体表达并不是评估新冠病毒感染与否的唯一指标,可能还与其他辅助受体的参与有关。 NHP 单细胞测序分析显示,Ⅱ型肺泡细胞、鼻杯状分泌细胞和吸收性肠细胞均同时表达ACE2 和Ⅱ型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transmembrane protease,erine 2,TMPRSS2),而这两种蛋白是SARS-CoV-2 感染宿主细胞的关键受体,这一结果表明这些类型的细胞很可能是SARS-CoV-2 感染的主要靶细胞[32]。
非洲绿猴在受到病毒攻击后,出现的临床症状包括短暂发烧、食欲下降、高碳酸血症、淋巴细胞和血小板减少症、肝转氨酶升高,单核细胞增加以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33-35]。 值得注意的是ARDS 在老年非洲绿猴身上可以持续观察到,这个症状在其他NHP 中很难模拟,因此老年非洲绿猴可能是模拟新冠重症非常重要的模型[35]。 感染病毒的猴观察到病毒性肺炎、胃肠道异常和广泛的肺部病变,包括:肺变色、浑浊、细支气管炎、充血和胸膜粘连[34]。
恒河猴则在感染病毒后出现轻度发烧、体重减轻、食欲下降和缺氧,偶有乏力、血小板减少、短暂中性粒细胞减少和淋巴细胞减少[36-37]。 尽管恒河猴表现出典型的人类患者的临床症状:肺部变色、充血、玻璃样浑浊、浸润、出血、坏死和间质性肺炎,但是无法重现临床上重症患者的症状,例如ARDS[36]。
当通过鼻内或气管内的方式感染SARS-CoV-2时,食蟹猴的肺出现实质病变,轻度发烧以及体重减轻,同时还观察到SARS-CoV-2 感染猴表现出另一种病理变化,即弥散性肺泡损伤(diffuse alveolar injury,DAI)[35]。
总的来说,三种NHP 均对SARS-CoV-2 易感,但症状不如临床上的严重。 序列分析显示:猴子ACE2 与RBD 的亲和力低于人,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NHP 能够感染SARS-CoV-2,但不会发展为重症。 因此通过AAV 病毒在猴子肺部实现异位表达hACE2,可能是模拟人类SARS-CoV-2 引起的重症临床症状的最佳手段。 此外,不同种类的NHP在病毒复制和清除方面存在差异。 而病毒的复制和清除除了与猴子品种有关,还与病毒感染宿主的途径有关。 单独鼻腔和鼻腔气管联合接种病毒,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病毒大量复制,并在感染后1 ~ 3 d 达到峰值,持续5 ~ 7 d 后下降[38-40]。 有研究报道,SARS-CoV-2 感染后5 d 会引起病毒在鼻腔组织中的第二波复制,病毒脱落期延长,可持续4 周[4]。 另一项研究显示,下呼吸道和肺组织中的病毒复制在感染3 d 后增加,并在感染9 d 时达到峰值[41]。 而气管内接种SARS-CoV-2 则不会引起病毒在鼻组织中复制,且病毒在肺组织中载量要低得多,表明上呼吸道病毒聚集是加剧下呼吸道的病毒传播和感染的重要前提,上呼吸道病毒聚集会出现更严重的新冠症状[42]。
SARS-CoV-2 感染后,先天免疫反应的激活发生在感染后1 ~ 3 d 内,感染早期诱导Ⅰ型IFN 反应,中晚期则诱导Th1/Th2 反应和获得性免疫反应[43-45]。 中和抗体最早在NHP 感染病毒后5 d 产生,并在感染后15 ~ 21 d 时达到峰值[41,46]。 当NHP 再次暴露于SARS-CoV-2 时,中和抗体和记忆免疫反应可有效防止病毒再次感染机体[47]。 当病毒诱导T 辅助细胞的Th0 亚型向Th1 亚型转变后,Th1 细胞协同巨噬细胞激活B 淋巴细胞,从而促进机体内病毒的清除。 此外,TNF-α 和IFN-γ 可直接作用于肺上皮表面的受体,诱导抗病毒反应。 Th2分泌的细胞因子IL-4、IL-5、IL-13 和IL-10 则抑制抗病毒反应并延迟清除病毒[45],总之,清除SARS-CoV-2 是一个受机体免疫调节的过程,针对病毒产生的中和抗体和适应性免疫反应会促进病毒的清除。
3 结语
小鼠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拟在SARS-CoV-2 患者上观察到的临床症状和特征。 K18-hACE2 和CAGhACE2 转基因小鼠能很好地模拟重症ARDS 患者的特征。 由于小鼠遗传背景比较清楚,因此在操作性和重复性上具有很大优势。 AAV 或Adv 异位表达则会改变病毒对组织或细胞的嗜性,且仅短暂表达。 而NHPs 与人类亲缘关系较近,在疫苗和抗体效果评估方面有很强的优势,但价格昂贵。 因此要想充分研究SARS-CoV-2 的致病机制以及感染后引起的免疫反应,需要综合评估不同动物模型的优势和劣势,更好地为新冠病毒疫苗开发和抗病毒方法的研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