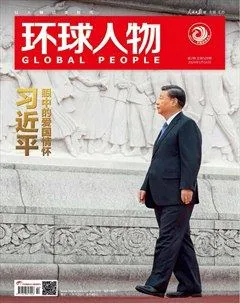青铜宝器,从两江总督府到大都会
2024-01-29徐婉玲
徐婉玲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故事不仅仅是过往的回声,它们仿佛成了时光的信使,横跨世纪,连接着迥异的文明和心灵。其中,西周青铜柉(音同凡)禁的存藏与流转,串联起晚清重臣端方和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的故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陕西凤翔府宝鸡县戴家湾斗鸡台附近村民王奎在村北坡地取土时,发现了30余件青铜器。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共14件祭祀青铜礼器,举世罕见。这套礼器由铜禁、鼎卣(音同有)一、鼎卣二、铜勺、鼎尊、父乙盉(音同和)、妣己觚(音同估)、子扫帚斝(音同甲)、父乙觯(音同至)、牺形爵、祖癸角、父甲觯、雷纹觯、亚形妣己觯和铜斗组成。西周是中国青铜文化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阶段,在青铜器上出现了大量铭文,这些铭文记载着周朝重要的事件。因此,这套青铜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
此套青铜礼器出土后,为当时湖北巡抚端方收藏。端方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担任过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等要职。在清末大臣之中,他思想开明,富有才干,锐意改革,推行新政。从政之余,还醉心金石书画,收藏颇丰,精品亦不少,最著名的,当数这套青铜礼器。
端方喜欢用当时最新的照相技术分享他的收藏。故宫博物院现藏一张1903年拍摄的照片,照片以“铜器全影”命名。画面中,端方与幕僚同好围合在铜器四周,青铜礼器陈设于桌案之上。端方居中,立于青铜礼器桌案之后;左侧端坐者为李葆恂、王闿运;右侧端坐者为黄绍箕、梁鼎芬。此外,端方还重金聘请技艺高超的拓工,制作了最具技术和艺术表现力的全角拓。这件拓片留存至今,拓片上器物繁多,纹饰繁复,器形准确,古意斑斓,堪称形神兼备。
端方作为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内心深处隐藏着对于文化、艺术乃至世界的深切好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踏入了位于纽约中央公园边缘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个坐落于繁华都市的艺术殿堂,仿佛是时光的港湾,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珍品。在这座宏伟的建筑中,西方的铜器、油画和塑像与中国的珍宝玉玩交相辉映,让人不禁陷入深深的沉思。端方的这次参观,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考察观摩,更是一次深刻的观念洗礼。博物馆中的每一件艺术品,都像是一面镜子,投射出他对未来的无限遐想。

陕西凤翔出土的青铜柉禁是一套完整的西周祭祀礼器,举世罕见。

“銅器全影”照片中,端方(中间站立者)与幕僚同好围合在这套珍贵的青铜器周围。
可能是这次参观,坚定了他在琉璃厂开设陶斋博物馆的决心,也激发了他编撰《陶斋吉金录》,用拓印技艺留下文物影像的设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编成《陶斋吉金录》,收录了此套青铜礼器,将之定名为“柉禁”。
在古代,“禁”特指一种几案形状的器物,中空无底,上放各种酒器。端方以“柉禁”一词指代这组成套的青铜礼器。
随后,一个名福开森、字茂生的美国传教士,走进了端方的府邸,多次参加了当时的文人雅集。他撰文记录了造访南京总督衙门的经历:
我经常在南京总督衙门与他共进晚餐。餐桌是一架大的诸葛铜鼓,我们坐在较小的铜鼓上。我还经常能看到他新收藏的青铜珍品,这又增加了这一场合的特殊性。他在《陶斋吉金录》中完整地记录了自己的藏品,每当我翻阅这套珍贵图书时,我都会想起他在把玩青铜器时那闪光的眼神和不安的动作。
福开森与端方的交流不限于表面的礼节与言辞,更深入到了文化、哲学的层面。福开森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宗教观念和艺术形式,端方则向他展示了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哲学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技艺。
1912年,福开森离开北京,前往华盛顿,获得了艺术代理人的身份,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买中国文物。
1915年,福开森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官方职务虽告一段落,但他与这家博物馆之间的深厚联系依然牢固如初。他的生活被艺术品市场所包围,他的目光始终聚焦于那些可能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珍稀艺术品。
真正的机会在1924年悄然降临。端方去世后,家族陷入困境,决定出售一批私人收藏维持生计。福开森顺利地成为家族委托的代理人。并且,凭借对中国社会习俗的熟稔,福开森选择在农历新年前的关键时刻与端方家族进行谈判。他深知那时是中国家庭清理债务、最需要资金的时刻。
1924年1月5日,福开森在天津成功说服了端方家族,使他们同意以约20万两白银(当时约合1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青铜柉禁。
福开森在信中描绘了这一刻的情景:“我把银行汇票交到他们手上,换来的是那些珍贵的铜器。”随后,他转头以约30万美元的价格将宝物卖给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仔细检查每件铜器,联系保险公司,确保这批珍宝得到全额保险。对于能够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购这些稀世奇珍,福开森感到异常欣喜,他感慨道:“17年未见,每一件铜器都在我的记忆中焕发新生。”
福开森短暂停留北京,请来了琉璃厂3位经验丰富的技工以及茹古斋的经理裴先生。这些古玩行的行家被请来协助制作铜器的拓片并打包装箱。见惯了珍奇之物,但面对这些古铜器时,他们仍然禁不住惊叹,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用了10天时间完成拓片和装箱工作。1月24日,这批铜器踏上了前往纽约的旅程。然而,福开森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路途中,部分铜器因非法撬箱而遭到损伤,好在大部分铜器仍然完好。

端方题“柉禁”全角拓片。
青铜柉禁远渡重洋而去,福开森与端方的故事并未在中国的土地上消失。1926年,福开森在《学衡》发表《陶斋旧藏古酒器考》,简明扼要地记录了这笔交易的起因经过: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秋革命军起,端方死于四川,遗产皆在北京,其后人以贫故,不能守,稍稍货其古器物以自给。近年贫益甚,遂以此二十器,归于我国(美国)纽约中央博物馆,此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春事也。
故宫博物院所藏“铜器全影”的照片题记,与福开森的文字可成对照。题记十分悲切地感叹端方收藏的流散:
陕西宝鸡县之斗鸡台,出土古禁及诸器,为长白端方陶斋所得,其时陶斋官湖北巡抚,集诸名士摄影,为玩古之图……并此禁器,其后人亦贫不能守,售诸美国中央博物馆,可慨也!
今天,青铜柉禁已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我们在展厅驻足沉思时,这些来自东方古国的艺术珍宝不只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世事沉浮和文化流转无声的讲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