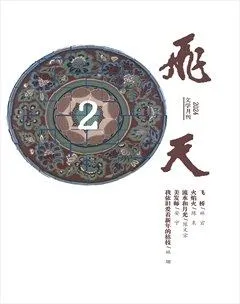黑河畔的流金岁月
2024-01-25吴晓明
吴晓明
黑河。弱水。同一条河流,别样的称谓。
依偎在黑河臂弯里的乌江村,隶属乌江镇,是一个很典雅的小村庄。乌江村周围的贾寨、敬依、元丰、大湾、小湾、东湖等村庄,都像是黑河的孩子一样,千百年前就被黑河滋养着,而乌江似乎格外受宠。她像是一粒贡米,温润中闪烁着岁月的光泽,触摸她,总是泛起丝丝缕缕记忆的清香。
乌江村,在我心底深处,一直是青春岁月里的诗意家园,最美好的时光跟那个枣花飘香的小村庄在一起,跟滚滚的稻浪在一起,跟那些朴实的孩子在一起,跟那些烟火的日子在一起。他们装点了我的岁月,我陪他们共度流年。多年之后,想起那个村庄,那些远去的日子像是一场春雨一样,瞬间会把我湿透,可是那湿漉漉的记忆里滋长的都是美好和诗意。
90年代初,乌江村有一所初级中学,即张掖市第六中学。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我第一次走进校园,就被那满校园的花花草草吸引了,我的脚步就为那些花草逗留了。那个六月,我如愿以偿走进了那个诗意的村庄,走进了那个开满鲜花的校园。当时学校高中和初中都有,我刚进校就带高一两个班的语文。两个班一百多个孩子,都是那片土地上的孩子,朴实得像是校园里那些花草一样,你可以叫不上他们的名字,可是他们的笑容却像是校门口的八角莲一样明艳。刚走出校门的我和那些学生看着相差无几,还没有学会怎么去爱他们,生命中那些沉睡的爱还是被他们一点一点唤醒的。
中学的对面是一所中心小学。小学里有一座魁星楼,就是乌江村的地标性建筑。魁星楼,是乌江村的一个制高点,不管是地域上还是精神上。当时的魁星楼破破旧旧的,看着很有岁月感,据说有300多年的历史。魁星楼夯土为基,青砖围砌,木构两层,雕梁画栋,四檐高挑,气势雄伟。里面的雕像、壁画清晰可见。魁星楼的周围长着高大的椿树,应该是臭椿,每到夏天的时候,椿树的味道几乎覆盖了枣花的清香,那个沧桑的亭子就在绿树掩映之中若隐若现,感觉很有诗情画意。我们站在高台之上,乌江村周围的美景尽收眼底,屋舍、庄稼、炊烟一览无余。当然,也可以看到周围其他村庄影影绰绰的模样。有时候我看着马路上人来人往,看对面我们校园里的孩子们奔跑吵闹,有时候我们也指点山河激扬文字。很多时候我们看着不远处的铁路上一列一列火车拖着笨重的身躯从容而过。
当然,提及乌江,似乎后面跟着的“大米”成了历史长河中一个醒目的标签。千年之前,依旧稻花飘香。乌江大米走进朝廷最早可追溯到唐朝。乌江镇位于黑河中游,自古以来,这里溪流密布、水量充足、土地肥沃,有着得天独厚的稻米生产条件。这里是昔日闻名遐迩的米粮仓,乌江贡米至今依然散发着馥郁米香;这里河水溪流纵横、清泉湿地遍布,因而虽处戈壁塞北,却胜似江南水乡,素有塞上“鱼米之乡”美誉。千年之后,乌江贡米依旧进入寻常百姓家。
每到春天,育苗、插秧依旧是农人们最重要的事儿。每年五月份,我们带着学生插秧,那是真正的勤工俭学。那些朴实的孩子们,可以算不出难的数学题,可以背不出英语单词,可是丈量土地、算自己的劳动所得,没有人能比上他们。五月的小镇依偎在黑河的臂弯里,做着绿油油的梦,等着金灿灿的秋,孩子们“手把秧苗插满田”,我蹲在地埂上“低头便见水中天”。农人们脸上汗珠子滚动,心中喜悦蔓延,那片土地,真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如今想想,我和这个村庄是有缘分的。我是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偶尔走进那个校园的,当时是盛夏,也是校园最美的时节。校园里花团锦簇,真是满校园的孩子,满校园的花朵,感觉孩子们就是奔跑的花朵,而花朵就是静止的孩子,我的脚步就是被那些花草牵绊了。
学校很开阔,一条小河穿学校而过,小河似乎把学校自然分成了生活区和教学区:一面是烟火日子,一面是诗意生活;一边书声琅琅,一边炊烟袅袅。到了黄昏的时候,有家的温暖,有校园的诗意。晚餐过后,小河的一边是背书的孩子,另外一边是我们闲散的日子,打牌的、下跳棋的、织毛衣的、喝酒的,真的是岁月静好。那时候不知道有诗和远方,如今,回头打量,那时候的日子就是诗和远方。
校园里都是平房,年轻人很多,我们都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单身宿舍,尽管只是一人、一桌、一床而已,可是毕竟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当时,学校有食堂,饭菜也不错。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多年轻人就开始自己做饭,宽松的工作环境很容易让人迷恋上烟火的日子。那是90年代初,还没有液化气,大家都用煤油炉子。
当时,住在我隔壁的是从另外一个学校调来的洲,她比我大不了几岁。她朴素又内敛,在喧嚣的人群里,她显得安静而又沉稳。那时候的她已经结婚,爱人不在身边。而当时我又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每天孤芳自赏郁郁寡欢,两个人不知不觉走得很近。后来,看到别的同事都相互搭伙做饭,我俩也开启了我们的烟火人生。
洲从家里拿来了煤油炉子,就那一簇火苗伴着尖锐的煤油味,让我开始品味生活中的苦辣酸咸,简单的一日三餐治愈着青春岁月里所受的伤。
每当下班之后,两个人走出校门,不遠处就是乡政府,走过乡政府所在地,就是一个小小的集市,那儿就是那个村子的心脏,一年四季都是喧嚣拥挤,非常热闹。周围有商场、裁缝店、理发店、农业银行、邮电局等,而街头卖菜的、卖肉的、卖酿皮的、卖油糕的都守着自己的摊点迎来送往。我们俩提着菜和肉走在街头,感觉我们就像是那个村庄长大的孩子一样,我似乎觉得那样的日子我们就一直过下去了。
那时候饭菜很简单,和面、擀面是我的工作,而洲的菜炒得很有滋味。简单的土豆丝、白菜粉条肉、西红柿炒鸡蛋等家常菜,她总能炒出不一样的味道。两个人各司其职,边做饭边聊天,从学生到家长,从文学到音乐,似乎有聊不完的话题。吃晚饭之后,我洗碗,她擦桌子,很默契。平淡的日子像水一样流过,每当她的婆婆来看我们的时候,日子便又泛起晶莹的浪花一朵。
那时候,洲的婆婆在距离乌江村不远的东湖村。那个村庄我是去过的,那是张掖市海拔最低的一个村庄,据说,只要在地上挖几米,就有地下水汩汩流淌。那时候各家各户都有压管井,也正是因为有水,才能有芦花飘雪,才有稻花飘香。黑河周围的村庄,似乎都是黑河养育的孩子,一样的村落屋舍,一样的花草树木,一样的炊烟袅袅。
老人很善良,一直都是面带微笑,笑容里都是慈爱,皱纹里都是笑意。每到端午节或者是中秋节,抑或老人闲暇的日子,老人的身影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学校。老人骑着自行车一脸的阳光,自行车上前面后面都是大包小包。那一天,就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我们俩不做饭,吃着老人做的糕卷儿或者月饼,那种幸福的滋味氤氲在身体的每个角落。
闲暇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到乌江街头去凑热闹,我们学校对面就是一个大操场,中小学的孩子在操场里跑步打闹。逢年过节,旁边的戏台上还会唱大戏,整个操场围得水泄不通。那是老百姓的精神大餐,也是庄户人家最好的时光。那一台大戏,就是对一年辛苦的最好治愈,似乎也是以那样隆重的方式进行了年终总结。
每到秋天的时候,似乎走远的诗句都像鸟儿一样飞来了,“甘州城北水云乡,每到秋深一望黄。穗老连畴多秀色,稻繁隔垄有余香。”这样美丽的诗句就是乌江的稻子成熟的季节。满眼金灿灿一片,似乎漫步在希望的田野上,农民们尽管脸上滚动着汗珠,可是眼里都是丰收的喜悦。
午饭过后,两人一起漫步在小村庄里,漫步在黑河之畔,漫步在铁路边上,看稻田里忙碌的身影,也看绿皮车慢腾腾地走过,车窗里人们匆匆而过的脸,看麦田里忙碌的身影,听稻田里蛙声一片。可是,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在迷茫的青春里活得多愁善感。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自己拘囿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通过读书、写日记化解着那些小情绪,我的日子过得并不是轻舞飞扬。
那时候洲的爱人看她的时候,她小鸟依人一样依偎在高大帅气的爱人身边。每当两人走在校园,感觉那就是最美的一道风景线,幸福像是一层釉一样镀在她青春的容颜上,感觉她整个人都熠熠生辉。
很多时候,依旧是我跟她在一起,两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她一笔一画练钢笔字,我写日记、看书。那时候的日记也是千篇一律,可是有很多时间都属于自己。我喜欢唐诗、宋词,尤其是那些伤春悲秋的诗词,似乎总是能够迎合我的心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写作似乎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也是我灵魂最好的出口。
那几年,学校分配的年轻人很多。90年代初,城里开始兴起舞厅、火锅,每到周末,一帮年轻人便结伴进城,吃自助火锅。自助火锅每人不到30元钱,花钱不多,能够满足我们蓬勃的食欲。尤其是各种饮料和酒水让我们感觉特别过瘾,感觉两个小时的光阴弹指一挥间。酒足饭饱之后,就去跳舞,去的最多的舞厅就是商贸大世界的歌舞厅,每次舞厅里都是人头攒动,激越的音乐,激动的尖叫声,到了蹦迪的时候简直就是群魔乱舞,真是青春燃烧激情飞扬,等到所有的激情都消耗完,我们像是一队出征的将士凯旋。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打扰看门的老人,便翻过校门,笑声唤醒了沉睡的校园,校园的路灯像是瞌睡人的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量那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那时候的日子有青春打底,怎么张扬都不为过,青春真是的就是一道阳光,明亮而又耀眼。
很多个周末,大家都各自回家了,那个空荡荡的校园是我一个人的。尤其是飘雪落雨的日子,我走在校园里,感觉那就是我一个人的天地。到了秋天黄叶翻飞的季节,我踩着落叶一个人走,似乎一直可以走到秋天的尽头,心中弥漫着无法言说的忧伤,文字成了我的感情的依托。回到屋子,一个人捧着书本,仔细咂摸诗句背后的情感,李清照、朱淑真、柳永、纳兰性德等似乎隔着时空来跟我约会,春天感受“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的惆怅,秋天承受“泪眼问花花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的凄凉,那些文字就伴着我的思绪飞扬抑或沉寂。那些日子,文字就是我心灵的知己,我也把青春的怅惘都安置在文字里,那是我一个人的山高水长,也是一个人的地老天荒。那时候没有手机,似乎我也忘了外面的世界,有时候读书,有时候饮酒,有时候发呆,不知道算不算是一场寂寞的盛宴,总之,那就是和自己的一场博弈。如今想来,我和文字一样寂寞,和文字一样踏实,那是青春岁月里最好的时光,也是我的光辉岁月。那真是一段举世无双的好时光,青春的岁月里只有文字,只有自己。偶尔有文字变成铅字,我拿着报纸走一路看一路,我的文字好像盛开的花朵,我总会嗅到岁月的芬芳。
后来,我在那儿成家,在那儿当上了母亲。庸常的日子被琐碎的事儿填得满满的,我没有时间伤感,日子一天跟着一天,在柴米油盐的交错中,在孩子的哭喊中,在别人眼里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成了一个烟火味十足的女人,感觉伴着孩子的呱呱坠地我似乎从半空跌入人间,满身的尘埃,甚至满心的沧桑。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知道有书籍相伴的日子是多么奢侈。
后来,每年有同事进城,我也蠢蠢欲动了,进城成了我们的诗和远方,奔赴城市是给孩子更好的交代,也是最好的歸宿。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小村庄,走进了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似乎青春也风卷残云一般,没有了和自己相伴的那样低调的奢华岁月,而是初为人母的慌乱,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的忙碌。洲也进入了城市的一所小学,那个村庄成了记忆中的一道风景线。
洲的婆婆,那个一脸笑意的老人,等到我再次见她的时候,她已经躺在殡仪馆了,滚动的照片上她依旧是暖暖的笑意,似乎这个薄凉的人间给她的从来都是温暖和美好。我想起我们站在阳光下,她从自行车上拿下面粉、大米、土豆、葱、蒜等,她的笑意里都是泥土和蔬菜的芬芳,我们烟火的日子里都是老人的味道,那是一个母亲的味道。
如今,那个学校放飞了很多孩子之后,曾经的同事也所剩无几,已经变成一所小学了。所幸,我的青春正好镶嵌在那个校园最蓬勃的岁月里。
黑河畔的那段日子,成了我记忆中的流金岁月。我像是黑河里一株水草抑或一颗鹅卵石,在那段温润的岁月里,寂然欢喜,暗自生香!
责任编辑 晨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