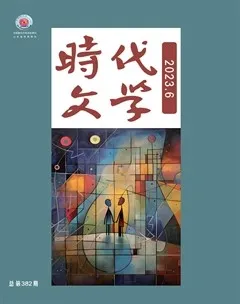另一种身影
2024-01-23李新文
李新文
直到目光完全被状若扇形的叶子所吸引,你才确信那是树——一棵高过屋脊、直指蓝天的大棕榈。不光褐黑色的树干挺得笔直,就连绿汪汪的叶掌也向上伸展着。这样子,好似抚摸一方天空,又像把精神飒爽的状貌交给扑面而来的时间。
等走近了,才发觉这树上了年纪,非但树干充满铁的质感,而且留下不少被刀刃切割的痕迹。看上去,很像排列整齐的褶皱。往深里想,怎又不是写在时间里的生命书?只不过,乌贼般的根系扎得很深,像是把天光、地气、水土的精华以及岁月的汁液一并汲进体内,以长出发达的年轮。我正这么想着,突然感到自己体内也长出一匝一匝的年轮,仿佛同树木一道生长。
四周全是稻田。稻田之上,流淌着透明的空气和分分秒秒的时间。当然,还有几只白鹭上下翻飞,把悠然自得的心情展示得一览无遗。想来,大概是跟我一样受不了棕榈的诱惑吧。
打心眼里讲,我见过的棕榈还真不少。大的,小的,高的,矮的,粗的,细的,一应俱全。甚至,我感觉它们在各自的坐标系上不停生长,把诸多憧憬、愿望、绿意表达出来,长成梦寐以求的貌样。只可惜,我对树干上的棕片是怎么切割下来又怎么变成蓑衣的过程一无所知。
不能不说,这是一段记忆的空白。
好在,我经常看见毛乎乎的蓑衣挂在堂屋的东墙上,哪怕随意扫一眼,也能感到一股热烘烘的气息扑闪而来,直抵人的内心。至今,我仍清楚记得爹说过这么一句话:“清明谷雨,犁耙蓑衣横着走。”仅一个“横”字,就给人十分的动感——似乎刹那间,把匆忙、急迫、干练、一往无前的姿态展现出来,有着无可替代的坚执与笃定。很自然地,你会想到风,想到雨,想到天地苍茫以及披蓑戴笠匆匆而行的情景。也许这个时候,天地间行走的除了人与蓑衣,还有如期而来的节气吧。
记忆中的雨,往往比人的目光跑得还快。一霎间,急切的,不蔓不枝的,清脆的,响亮的,坚硬的,柔软的,甚至带有江南小令式的……全是雨点发出的声音,全在稻田上翻涌、旋转、飞扬,融为气势不凡的声场。自然,一同进入的还有风。也许,那是“春眠不寒杨柳风”的风吧;又或许,是“二月春风似剪刀”的风。不管哪样的风,也不管夹杂着怎样的味道,一起在田野上集结,继而迈开脚步游移、蹦跶,以便对自个儿的生命有所交代。不经意间,把各自的精气神儿凸现出来,一如自由放达的大写意。与此同时,还将长长短短的线条舞得呼呼作响,疑是送给季节的礼物。我就想,假如这些风深谙处世之道,少不了来个抱拳施礼、自报家门。要不然,怎会表现得如此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稻田也不呆痴,马上用油菜花、燕子花、地米菜夹道相迎,一尽人间的礼数。确实,三月的风性情得不行——一忽儿扭腰弄肢,挥袖振臂;一忽儿呼呼烈烈,高低起伏,像跳着奇妙的舞蹈。要不兴趣来了,打个呼哨,以召唤犁铧蓑衣的到来。其实用不着客套,它们早已上路了。具体说来,是受不了花草的引诱,一步一步走向稻田的。
瞬间,汉子下到田里,将家伙什和耕牛料理停当后,大喊一嗓子:“起——嗨——”便开犁了。这声音响亮,雄浑,粗犷,如打在时间册页上的标点,更像必不可少的仪式。而我见到的光景是:爹裹着半新不旧的蓑衣,一手掌着木犁,一手捏着竹鞭,牙齿咬着,嘴巴抿着,摆开一副严肃认真的架势。恍惚,他的牙齿一咬,每块骨骼里的力气一齐涌向执掌木犁的手心,而后传到犁头,并直线般地钻进脚下的泥土,就像文学里讲的精神辐射。而这源源不断的力量,恰恰与耕牛的擎引达成一致,心照不宣。我搞不懂这是不是力与力的交融,只觉得双方那么和谐默契,就像遇上相交多年的老朋友。随之而来,你的视觉屏幕上呈现出一推一拉的动景,仿佛是古代壁画里的某种图案。不一会儿,气氛热烈起来,鲜活起来——牛在前面引路,酷似拉着一个季节在动。犁头,这尖锐的闪着寒光的家伙,兴冲冲地插入泥土,而后一路游走、穿越,俨如穿越一个接一个的时间。倏忽间,就将洁白的光芒和积蓄一冬的能量都释放出来。此时的农人、风雨、蓑衣、耕牛、木犁、泥土等相融相济,洋溢着酣畅淋漓的痛快。竹鞭一挥,便让耕牛找到奋力前行的理由;泥水“哗啦”一響,将人带入只可意会的妙境,就连时间也增了一抹亮色。顷刻,板结的泥土被打开来,像打开一扇春天的门。站在春意浩荡的门槛边,似乎随手一伸,就能抓到一把春天的语言。当然,还有不少生长的气息肆意弥漫,熏得耕牛大口喘气。这会儿,我清晰地看见,一串山歌从爹的喉咙里跑出来,那么悠闲自在,不着半丝尘埃。尤其叫竹鞭一甩,直抵那边的山崖。岂料“啪啦”一下撞在岩壁上,激起无数空空的回声,如岁月的余音一寸一寸地蔓延。
天空下,被翻卷过来的泥土很有秩序地排列着。乍看,好像层层叠叠的波浪。仔细一想,又像写在田野上的诗句。此刻,进入视觉范围的除了闪着光亮的泥带,更多的是发自天然的美,足可与书法里的朴拙和率真一较高下。我突发奇想,假如蓑衣长着一双眼睛,见到这种情形,大概会涌起不少激动吧。而泥土不管这些,铆着一股劲儿把它们的气味、色素和所包含的生命分子推送出来,随后传给花,传给草,传给蓑衣、雨水、空气以及人的知觉器官,像是告诉你季节已揭开崭新的一页,朝着春意盎然的目标迈进。燕子花、油菜花、地米菜等经不起犁铧的捣弄,干脆与泥水统一阵线,用鲜明的色泽照亮人与蓑衣行进的路。
我把瞳孔睁得老大,一眼瞥见爹正沿着花草指引的方向摆弄木犁。木犁仿佛得了某种神秘指令似的,使出浑身力气,试图开辟崭新的航道——每走一步,犁铧“咯吱”一响,宛如送给季节的问候;每走一步,油黑闪亮的泥土豁然分开,恍若打开土地的书页。由此我马上想到,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劳作,何尝不是在营造特殊的诗意?自然而然,赤裸的双脚被雨水、泥土的气味和花草的馨香全然浸透,如同受到一场彻头彻尾的润澈。换句话说,怎不是从生命的一道门进入另一道门,乃至一种精神涅槃?我傻傻地想,要是蓑衣也有思维,定会为眼前生发出的一切而欢欣鼓舞吧。
细细想来,棕线密织的蓑衣何尝不是诗意的存在?你看,此时的天空下,泥土在犁铧的牵引中哗哗流淌,未尝不是因蓑衣的到来而改变生命的样式——转瞬之间,整个稻田生动起来,快活起来——大块大块的泥土绕着耕牛与犁铧在动,耕牛与犁铧绕着时间在动,人和稻田绕着春天的路径在动,而蓑衣在风雨交织的大背景下徐徐转悠……似乎,所有与蓑衣有关的人、物都变得激情满满、热血沸腾,甚至人的思绪也进入妙不可言的场域。我想,若是天才诗人李白在时间里复活,面对此等情景,会不会再次发出“水闲明镜转,云绕画屏移”的感慨?此时此刻,进入视网膜里的何止是开犁的场景,更有众多物象纷纷交织、重叠、更迭、变幻,演绎出非同寻常的气场。一点没错,是气场。否则,那个躲在岁月深处的老子也不会发出“无物之象,是谓恍惚”的感叹了。“恍惚”到底是怎样的概念,一时半会儿我讲不清。倒分明瞧见大批的雨水,顺着蓑衣的棕毛一滴一滴地往下滑。稍不留神,拉成一个个白晃晃的线条。这模样,跟平面几何学里的辅助线相差无几。可我搞不懂这样的线条是蓑衣派生出的细节,还是在丈量土地与日子之间的距离?只觉得,它们拿摇头摆尾的风毫无办法,即使随便一阵风,也让好端端的线条变得七零八落,没了看相。果不其然,风变了招式,一改先前的优哉游哉,成了力道十足的鞭子,抽在人的脸上、脖子上,火辣辣地痛。我想象不出风抽在蓑衣上是何感觉?眼一瞟,发现一线线的风正朝着爹的身体冲锋陷阵、摇旗呐喊,似要将其纳入风的版图。爹头上散发着的热气与风的坚硬形成不小的反差,正如乳汁与匕首相遇,无法产生心灵的共鸣。我寻思着,难不成这反差是冲着美好的诗意而降临人间的吗?或者说,大千世界本就是一种相互矛盾而又辩证统一的哲学?此间,我没发现自己有多疑惑,却看见爹的嘴角边挂着一绺莫名其妙的笑。那笑时隐时现,一派安然,很容易让人想起唐朝张志和笔下“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句子。细雨当然是有的,风却一刀一刀地割,显得十分卖力。我猜这个时候,一如我爹的农人想不成为风雨的一部分也难。
当时,我戴着斗笠支在田埂上,看着爹披蓑而耕的情景甚是入迷——仿佛一招一式不是现场表演,而是魅力十足的画面,直接映入我的脑海,定格成一种永恒。讲良心话,我只想学着他的样子去稻田里犁一下泥土,哪怕一溜儿也行。可他就是不肯。不肯也罢,还眼珠子一鼓,硬邦邦地甩来一串:“屁伢儿没一蓑衣高,犁、犁、犁,犁个鬼……”说完,敞开喉咙哈哈大笑,将遏制不住的傲然与狡黠彰显得淋漓尽致。很明显,他把我看成比蓑衣不如的玩意了。笑也不打紧,还命令我在田埂上待着,倘若胡来,就给一鞭子。我当然吃不消一竹鞭,只好老老实实待着。但终于敌不过强烈的好奇心,只等他侧过身去,立马脱掉鞋袜,将一只脚尖伸向水里。不伸还好,一伸冷冰冰的,像触电般地痉挛。于是我赶紧把脚缩回,照旧支在田埂上。一晃眼,我发现爹的腿肚被冻得通红。不知怎的,通红的颜色在我眼前急剧放大开来,像要覆盖周遭的一切。迄此,我才明白看似诗意的乡土并不那么诗意缭绕。或许,历代文人墨客竞相咏唱的田园牧歌式的图景,是在一滴滴汗水和坚忍不拔的意志里熬出来的吧。转而又想,一边是寒风凛冽,一边是披蓑而作,难道这样的景象是农耕文化里不可或缺的生命元素?
我不知世间是否有“蓑衣文化”一说?掏心窝子讲,我更愿意把蓑衣看成农人的另一种身影或生命符码。想想看,经纬密织的蓑衣披在人身上,人贴在稻田上,人的身子一动,蓑衣跟着在晃,其间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蓑衣不用时,爹准会挂在堂屋东边的泥墙上,说是打眼,便于拿放。还说什么蓑衣往墙上一挂,五谷司神会悄然而来,绕着蓑衣来回走动。他说得神乎其神,好像亲眼见过一般。我当然不信。不过,有那么一回,我把眼睛瞪得状如箩筐,望着墙壁上的蓑衣发呆,只想看看五谷司神是怎么走过来的,又怎么在蓑衣旁来回走动……然而等了老半天不见动静,未免有些失望。倒是忽然间,蓑衣在我眼前呈十倍百倍千倍地放大开来,大得超出想象——仿然挂着的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具象,而是一个巨大的身影。这期间,我隐隐感到人的体温和汗沿着蓑衣的纹路冒出来,一下将堂屋填得爆满。经过此事,我认定从一棵棕榈出发的蓑衣不但吸纳了数不清的时光岁月,更是土地上不可多得的生命载体。
我正看得入神,爹突然从大门口走来,接着喉咙一滚,冲我大吼:“好好待在家里读书,别乱动。否则,当心老子一丁弓。”说完,手一挥做了个打击状。我吓得一搐,只好坐到木椅上,翻开那本读了无数次的语文书。
万万没想到,爹前脚一走,阳光从云层里拱出来,继而把晶亮的光芒射到东墙上,将蓑衣照得分明。我盯着它,想象这类似于人体的蓑衣里暗藏着什么。
傻傻待着不动是不行的。我的手和心都在发痒,特别是一探究竟的愿望相当强烈。恰恰这时,隔壁的猫伢跑来说,扮一下“蓑衣鬼”如何?我惊讶得两眼发直,老半天才弄明白:大约是一件蓑衣穿久了,人的精神元气融入其间,若是碰到雨天或月夜,会变成人的样子,跑到田地里继续干活。这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信口开河。只不过,我的理智完全被汹涌而至的好奇心打败。于是,书本一放,搬了木椅搁在墙脚根,随即跳上去将蓑衣取下,“呼啦啦”套在身上,全副武装。这一刹,我不知自己的灵魂是否与毛茸茸的物件融为一体,更猜测不了下雨天或有月光的晚上,我的灵魂是否与蓑衣一道在田野里走动,只是物件儿往身上一套,一股热烘烘的气息漫向全身,直逼每个细胞。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奇痒呼啦而至,潮水般地涌向内心。那感觉,活像无数只毛毛虫在拱,在向我大肆闼伐、攻城略地,如果当时有镜子,定会看见我无所适从、抓耳挠腮的丑态。转眼,猫伢拖出一条木凳要我坐上,说是可当犁铧与耕牛,学着大人的架势犁田。我當然没有反对,赶紧一屁股坐上去,随即大喊一声就算开犁了。恍恍惚惚中,眼前浮现出一帧极为生动的镜像:漫天的雨水在降落,一拨一拨风声在游走,还有宽展的稻田以及大片的油菜花、燕子花、地米菜等等,组成色彩斑斓的图画。这样的气氛让许多词语相形见绌,更让时间加快了脚步——似乎,天空下的每个生命分子都在起承转合、匆匆迈进,连同我的整个生命都处于鲜活状态。
我想,蓑衣带给人的何止是一个春天的方向,恐怕更多的是化入心魂的温暖罢。吸进肺叶里的,全是泥土的芳香和风雨无阻的味道……正当疯得一塌糊涂时,爹突然出现了。他一脚跨进大门,劈头盖脸朝我甩来一串:“化生子,尽干坏事,把蓑衣搞烂了,还想吃饭吗?”他的怒吼凌厉、斩截、刚劲,将屋子震得嗡嗡作响。接着,一块块空气哗然坠落,化作一地碎片。万般无奈,我只好把蓑衣脱下,赶紧放回原处,生怕挨他一丁弓。
第二天中午,忽而下起了暴雨。刹那间,远远近近的山峦、树木、瓦屋、田野成了雨的世界。我满以为哗啦啦的雨水是蓑衣给带来的,要不然,这个毛茸茸的家伙什怎么老是同我一样望着天空发呆,说不准早就渴盼大雨的到来吧。那天中午,爹在大门口朝不处的耪地望了一眼,接着埋怨地嘟囔:“这鬼天气老是下雨,下个不断纤,真可恼……”说罢,转身回到堂屋,将挂在泥墙上的物件飞快地取下,又飞快地穿好,随即搬上锄头出门。我问:“干啥?”他说:“去对门耪地看看……”话头刚落,一闪身冲进了雨幕。其实他不开口,我也晓得他要去的地方叫黎家冲。那儿不单草木发旺,还有大片大片的菜园。此刻,我家的耪地躺在天空下一言不发,任由风吹雨打。这架势,一点不输给高尔基笔下的那只海燕。一眼望去,地势东高西低,加之两边的山使出狠劲挤压,出落成不折不扣的簸箕造型。恰恰因了这种造型,这地歪打正着出奇地肥沃,种什么长什么,似乎哪怕插根筷子,也能生根发芽。瞬息,我看见爹裹着蓑衣在风雨里移动,扑闪扑闪的样儿,像极了披风破雨、展翅飞翔的老鹰。对,是老鹰。还别说,他当真像一只时间里飞来飞去的鹰,长年累月,用匆忙的动作打理他的农事和二十四个节气,收获的不仅仅是人间粮食,还有不可计数的汗水、疲累、欢笑和荣光。我下意识地想,倘使每个披蓑戴笠的农人都是一只鹰,我敢肯定,他们的世界里除了风雨、稻田、村言俚语与山歌子,还生长着密如繁星的禾稼和葱茏的绿意。或许,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精彩最诱人的诗意吧。不说别的,就拿我爹作比,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被蓑衣支配着,用鹰一样的方式打理他的日子。设若以此放大开来,亘古的华夏大地上,岂止生长风雨四季,恐怕更多的是一个接一个“蓑而耕,日昏不去”的生命镜像。如此,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农耕文化以及岁岁返青的农业,也便有了五谷丰登、长盛不衰的人间。正当我浮想联翩时,眼眶里扑入一个更为生动的镜头——爹将锄头高高举起,砸下;砸下,又举起……起起落落的动作与晃动的蓑衣形成绝妙的呼应,堪为非同寻常的视图。至此,我没有理由不相信貌似平常的蓑衣,实则隐含了太多生活细节和无法掂量的生命重量。万万没想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将爹的身子吹得摇摇晃晃,接着脚下一滑,连人带蓑衣一起摔倒在地,然后又打了个翻叉……这一刻,我的心几乎要蹦到口里,差点冲向雨幕。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传来一阵大大咧咧的咒骂。骂声汹涌澎湃,像无数的纠结泛滥成灾。种种迹象表明,爹除了烦躁不安,还被各种滋味包围着,险些不能自拔。哦,对了,你能说柴米油盐的现实世界,不是由一个个这样那样的滋味组成的吗?
爹一瘸一拐地回来,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与其说他被众多目光扫射着,倒不如说被腌臜的情绪围得水泄不通。而我,分明瞧见他的蓑衣成了两半:一半披在身上,一半拎在手里。这样子,像是把一个血气充盈的生命体硬生生地划开——一半写着沮丧,另一半写着憧憬。我闹不清此时的蓑衣是何感受,尤其面对突来的遭遇想说什么。我娘见了,却想也没想送上一串:“蠢货,好端端的蓑衣搞成这样,还想吃饭吗?”哦,明白了,从现实意义来看,蓑衣还真像我们的饭碗——仿佛蓑衣是另一种形式的稻田,盛产极为丰富的人间食粮。爹挨了骂,收洗一通后,坐在大门口用针线缝补那破烂的物件。瞟一眼他飞针走线的动作,格外从容、镇定,远比我阅读语文书上的课文来得细致,更像把一个日子的缺口给缝补起来。
那天晌午,爹一边缝补蓑衣,一边跟我闲聊。他满脸郑重地说:“很多年前,上屋场有个叫刘明生的老汉,在对门耪地上翻了好一陣地,累了,披着蓑衣坐在墈湾的一棵大棕榈下歇脚,歇着歇着,一口气没吁转,做梦般地去了……”我想,这个时间刻度上,老人的魂儿定然与高大的棕榈融为一体,组成无数个精神指向极为相似的“同心圆”。只可惜,我无法穿越时光的秘道亲临现场,感受一下人与棕榈相互影映的气氛,更揣摩不了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没脱下蓑衣的心理构成。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底是蓑衣给予人太多的恩赐,还是人与蓑衣之间有着血魂一体的关联?然而哪怕想破脑壳,也找不到准确的答案。谁知爹吸口烟后,接着又说,后来,老人的儿子披着那件蓑衣继续翻,可翻着翻着,不觉鼻子发酸,泪水汪汪,好伤心哪。那会儿,他看见身上的蓑衣,就像看见了他爹。迷幻中,老人散发出的气息好像在一遍遍抚摸儿子的身体以及每一条经络。如此,他便觉得不是自个儿在翻地,而是他爹捏着他的手教他翻。每走几步,喉管咕隆一下,呜咽——似乎千言万语化作无尽的哀伤,仿佛披着的蓑衣不再是简单的物件,而是他爹的魂魄……遂想,莫非老人一生中所经历的风雨、勤劳、坚韧、汗水、苦涩以及过往的一切,全化作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或者说一种独有的生命样式?这当儿,爹把每个字说得很慢很慢,似在讲述一个传奇或一段花白的往事。临了,还补上一句:“咱梅溪乡下,往往一件蓑衣父亲穿了儿子穿,要不打上补丁接着穿,只要不彻底破烂绝不轻易丢掉。”我搞不懂这是一脉相承的习俗,还是根深蒂固的生命范式?
透过雨幕,我不由自主地望了田畈里的大棕榈一眼,回头又望了爹一眼,蓦然觉得,二者之间有一种不可言喻的东西存在着。我猜,那是化入骨血和心魂的生命维系吧。于是就想,等我长大后,是否也穿上爹正打着补丁的蓑衣,继续在风雨里耕耘一个个日子或二十四个节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