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法律和社会想象*
——1772—1864年英属印度盎格鲁-印度教法建构中的文本翻译
2024-01-18杨清筠王立新
杨 清 筠 王 立 新
关于传统印度宗教、法律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王云霞认为:“古代印度是一个宗教社会,宗教的强烈光芒覆盖了一切。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宗教的附属物……”(1)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23年第7版,第38页。这种界定代表了当前中国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主流观点:历史上的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宗教社会,其传统法律和社会都奠基于它的传统宗教——印度教。高鸿钧也这样概括“传统印度法”的模式:“传统印度法中的宗教法是印度教的组成部分。印度教是古代印度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处于支配一切社会领域的地位。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宗教法,获得了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因而比世俗法具有更大的权威性。”(2)高鸿钧:《法律与宗教:宗教法在传统印度法中的核心地位》,《清华法学》2019年第1期,第16页。“法律与宗教密切关联,法律附属于宗教,宗教法是核心,世俗法是边缘。”(3)高鸿钧:《印度法研究与传统印度法的主要特征》,《清华法学》2022年第1期,第28页。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开始对在英印时期形成的、被中国学者所普遍接受的上述主流观点提出质疑。英国历史学家D.A.沃什布鲁克认为,印度教法的形成是英印时期英国殖民者和印度婆罗门阶级“密谋”的结果,他们合力把婆罗门阶级的意识形态塑造成印度的社会传统和法律秩序(4)D.A.沃什布鲁克:“印度殖民地时期的法律、国家和农业社会”(D.A.Washbrook,“Law,State and Agrarian Society in Colonial India”),《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15卷第3期(1981年7月),第653页。。美国印度宗教和法律史专家理查德·拉里维耶尔则将印度教和印度教法看作英国人对印度文化误读的产物,直截了当地指出:“直到英国人发明它之前,并不存在印度教法这种东西。”(5)理查德·拉里维耶尔:“法官与梵学家:当代印度教法律史解读中的一些反讽”(Richard Lariviere,“Justices and Pa Ironies in Contemporary Readings of the Hindu Legal Past ”),《亚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48卷第4期(1989年11月),第758页。美国当代人类学家伯纳德·科恩分析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法律实践,认为英国殖民当局出于在印度殖民地创建统治工具的目的,试图寻找和实施他们想象的印度本土的传统法律,但最终却只是“将印度教法完全变成了英国判例法的一种形式”,创造了一种在印度原本并不存在的法律传统,即“盎格鲁-印度教法”(Anglo-Hindu Law)(6)伯纳德·科恩:《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Bernard Cohn,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7~75页。。实际上,根据他们的观点,当前中国学界关于印度教法的流行观点不过是一种殖民主义知识遗产。
鉴于由英国殖民当局组织、英国东方学家们实施的本地法律文本(婆罗门梵语文献)的编译工程在英印时期盎格鲁-印度教法的实际形塑过程中发挥了基础作用,本文致力于对1772—1864年间盎格鲁-印度教法建构中文本翻译的历史进行深描(7)一般认为,殖民地时期所谓“盎格鲁-印度教法”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1772—1864年为盎格鲁-印度教法发展的第一阶段,1864—1947年为盎格鲁-印度教法发展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对一些古代印度文本的翻译以及由英国法庭任命的印度教潘迪特提供的文本解释构成了盎格鲁-印度教法律的基础。在第二阶段,通过了一部成文法典,印度教潘迪特因对法律文本的解释日益分歧和所谓的“腐败嫌疑”而被解职。在英印时期印度教法的发展历程中,1864年司法改革及其“假设”(即假定盎格鲁-印度教法已经对印度教伦理和法律拥有了足够的“知识”,从而不再需要求助于本地印度教潘迪特亦即梵学家们的法律解释)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意味着英印殖民当局主持的现代印度教法律文本编译工作的终结。。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殖民地时期印度宗教、法律和社会的实际形塑过程,也有助于我们在梳理和解析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英印殖民统治的知识遗产。诚然,当代著名印度裔学者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在《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与殖民语境》(Siting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ndtheColonialContex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一书中论述了“殖民统治下翻译‘发挥作用’的所有语域:哲学的、语言学的和政治的”,但是她的论述聚焦于“后殖民脉络”下对“当代欧美文学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反思,并未真正聚焦于“翻译的历史性问题”(8)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著,袁伟译:《语言:斗争之所》,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编:《重塑民族主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34~36页。。
一 前殖民地时代印度的“法律传统”与英国殖民者的印度教法想象
要谈论前殖民地时代印度的“法律传统”,不得不说有一些勉强,因为将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概念用于前现代印度并不是没有争议的,按照当代宾夕法尼亚大学梵语教授卢多·罗彻尔的说法,“在印度传统中没有一个表示法律(law)概念的术语,既无‘法’(ius)意义上的,也无‘律’(lex)意义上的”(9)卢多·罗彻尔:“印度教的法律概念”(Ludo Rocher,“Hindu Conceptions of Law”),《黑斯廷斯法律期刊》(Hastings Law Journal)第29卷第6期(1978年7月),第1283页。。的确,在梵语中,“法”或“达摩”(Dharma)一词的涵义与作为普遍的强制性行为规范的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有很大不同。“达摩”一词的原义为维持,可理解为在某种情境中维持平衡的方式,大到自然宇宙,小到微观世界,任何维持事物运行的规则都可看作“达摩”。在社会生活中,“达摩”还经常被描述成一种处世哲学或行事策略。总之,“达摩”一词的内涵包罗万象,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或许可以被囊括其中,但二者却不能完全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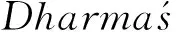
看来,印度前现代社会的确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印度人在处理诉讼争端时没有任何规则可依。印度大多数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与法律的性质相近,只是实际约束力有限。自然,这些以风俗习惯形式存在的“法律”规则是鲜有书面记录的。实际上,在印度,不只是地方的风俗习惯,甚至连宗教典籍在近代以前也多通过所谓的“口语传统”(oral tradition)流传下来。在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教育中,“吠陀知识”“被认为过于神圣而不能任其作为一种外部物体而存在,它必须作为人的一部分而活在他的记忆中,在他的心中受到珍视,而不是作为某种外在于他的东西”(13)拉达·库穆德·穆克吉:《古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教育》(Radha Kumud Mookerji,Ancient Indian Education Brahmanical and Buddhist),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212页。。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非成文法特别是习惯法就成为印度人处理争端的最普遍的“法律”依据。布谢特的通信证实了这一点:“印度人没有成文法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公道……判决的公平性完全建立在神圣的习俗和代代相传的惯例上。他们认为这些惯例清晰明了、无懈可击,不仅普通人用它解决纠纷,就连王族也不例外。”(14)卢多·罗彻尔:“布谢特神父关于印度教法管理的信件”,第675页。
由于地区传统或身份方面的差异,印度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尽相同,因此印度人的矛盾处理通常以群体(种姓、行会、村庄、宗教)为单位进行,著名的潘查亚特(Panchayat)是最广泛存在的“司法机构”。出现争端时,潘查亚特的长老们将依据公认的风俗习惯断案,裁决标准因时因地而异,具有鲜明的多元特征。这就是印度本土长期以来的主要“司法实践”模式,伊斯兰政权基本上未对非伊斯兰群体内部的司法过程进行干涉。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人才开始打破这个“法律传统”。
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莫卧儿皇帝手中获得迪万的职权,从一个纯粹的商业机构转变为统治孟加拉的殖民政府。虽然公司政府顶着莫卧儿皇帝授予的头衔,却并未遵循莫卧儿帝国的不干涉管理模式,而是直接介入孟加拉本地人的争端裁决。英国人自以为虽为外来者,却能做到“在保留土著传统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纠正其不公,弥补其缺陷”(15)M.E.蒙克顿·琼斯:《沃伦·黑斯廷斯在孟加拉(1772—1774)》(M.E.Monckton Jones,Warren Hastings in Bengal,1772—1774),伦敦:克拉伦登出版社1918年版,第311页。。
然而,事实上,英国人却是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社会观念来认识当地族群的。当时比较宗教学正在西方盛行,西方人热衷于按照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将非基督教世界的人们界定为各种宗教共同体(16)蒂莫西·卢宾、唐纳德·戴维斯、贾扬特·K.克里希南编:《印度教和法律:导论》(Timothy Lubin,Donald R.Davis Jr.and Jayanth K.Krishnan,eds.,Hinduism and Law,an Introductio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导言”,第2页。。于是,英国人也根据宗教信仰将印度的族群划分为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其中,伊斯兰教被认为是印度的外来宗教,印度教则是印度的本土宗教——但实际上,前现代印度的本土宗教并不是一个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的单一宗教体系。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是,虽然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在1817年出版的《英属印度史》一书中根据宗教信仰的差异明确把印度人划分为“穆罕默德(Mahomedan)种族”和“印度(Hindu)种族”,但在讨论印度宗教时并没有给出一个专有名称。《牛津英语词典》认为“印度教”(Hindooism)一词首先出现在1829年报刊《孟加拉人》(Bengalee)第45卷中,而且指出1858年德国著名的印度学家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也使用了这个词。不过,德莫特·基林利(Dermot Killingley)声称拉姆莫罕·罗易(Rammohan Roy)在1816年使用了“印度教”(Hindooism)一词。正如基林利所言,“拉姆莫罕可能是第一个使用‘印度教’(Hinduism)这个词的印度人”(17)理查德·金:“东方学与‘印度教’的现代神话”(Richard King,“Orientalism and the Modern Myth of ‘Hinduism’”),《神性》(Numen)第46卷第2期(1999年4月),第165页。。由是观之,实际上直到19世纪,在西方宗教观的影响下,印度人自己和欧洲人才开始把印度的本土宗教理解为一个类似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的单一宗教,并赋予它一个专有名称。
也同样是根据当时西方流行的宗教法观念,英国人认为印度教徒也拥有一套同伊斯兰教法类似的宗教法,即他们所谓的“印度教法”(Gentoo Law)。他们相信这个民族的一切思考都拘囿于自身宗教的狭隘范围,印度教法就是印度本土“自古代延续至今而未曾改变的”神圣法律,其内容“与宗教紧密相联,所以被奉为最高权威”,而英国人如能够掌握这套法律,便能“使英国政府的权威建立在当地古老法律的基础上,获得符合这个民族意愿的统治途径”(18)G.R.格莱戈:《沃伦·黑斯廷斯阁下:首任孟加拉总督的生活回忆录》(G.R.Gleig,Memoirs of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Warren Hastings:First Governor-General of Bengal)第1卷,伦敦:威廉·克劳斯父子出版公司1841年版,第400~403页。。那么,到底在哪里才能够找到他们想象中的印度教法呢?英国殖民者“合理地”推定,既然西方教会法的渊源是《圣经》,伊斯兰教法的渊源是《古兰经》,那么印度教法就应当存在于印度教徒的圣典即以《吠陀》为代表的各类梵文典籍中。他们相信只要能将那些包含了法律规范的梵文经典翻译成英文,便可获得对印度本土法律系统的充分了解。正是在这一信念的鼓舞下,1772年新任孟加拉省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年)首先将从印度梵文经典中编译印度教法文本的计划付诸实施。
二 创制文本:沃伦·黑斯廷斯和纳撒尼尔·哈尔海德的《印度教法典》
沃伦·黑斯廷斯上任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民事管理可谓一塌糊涂。按照莫卧儿帝国的规定,公司政府作为迪万理应承担税收和民事司法两项主要任务,但公司统治初期只热衷于收税敛财,对民事司法则不闻不问,竭泽而渔式的横征暴敛导致富庶的孟加拉遭遇了长达三年的大灾荒(19)默文·戴维斯:《沃伦·黑斯廷斯,英属印度的缔造者》(Mervyn Davies,Warren Hastings,Maker of British India),伦敦:艾弗·尼科尔森与沃森公司1935年版,第72页。。面对严峻形势,公司董事会不得不宣布“以‘迪万’的身份站出来”,整顿孟加拉的税收和司法(20)沃尔特·凯利·费尔明格编:《下议院特别委员会关于东印度公司事务的第五份报告》(Walter Kelly Firminger,ed.,The Fifth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the Affairs of the East-India Company)第1卷,加尔各答:R.坎布雷公司1917年版,“报告”,第5页。。黑斯廷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任孟加拉省督,肩负起管理当地司法行政的任务的。
黑斯廷斯早在17岁时便来到印度,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与大多数单纯贪求财富而来的英国人不同,他对印度的历史文化怀有极大的兴趣,一直致力于深入探悉印度本土的语言、风俗、法律和制度。长期的接触让黑斯廷斯自认为对印度社会有了足够的了解和充分的共情,反感欧洲人对印度蛮荒、专制、毫无法纪的刻板描述。在他看来,印度其实和西方一样,拥有自己的文明和法律。所以,在司法方面,黑斯廷斯对“古老印度教法”的存在坚信不疑,极力主张在英国人的管理下“让印度人遵循自己的法律”(21)G.R.格莱戈:《沃伦·黑斯廷斯阁下:首任孟加拉总督的生活回忆录》,第400、401、403页。。1772年8月,刚上任不久的黑斯廷斯便在孟加拉颁布了《司法行政计划》(PlanfortheAdministrationofJustice),其中第23条特别强调:“关于继承、婚姻、种姓的问题,必须按照《古兰经》或沙斯特(Shaster,即印度教法——引者注)之规定来解决。”(22)G.W.弗雷斯特编:《印度总督国家文件选集第2卷:沃伦·黑斯廷斯文件》(G.W.Forrest,ed.,Selections from the State Papers of the Governors-General of India,Vol.Ⅱ:Warren Hastings Documents),伦敦:康斯坦布尔公司1910年版,第295~296页。负责民事案件的迪万法庭还请了伊斯兰教徒法官以及梵学家协助,分别负责解释伊斯兰教法和印度教法的原则(23)G.R.格莱戈:《沃伦·黑斯廷斯阁下:首任孟加拉总督的生活回忆录》,第400、401、403页。。1772年8月,刚上任不久的黑斯廷斯便在孟加拉颁布了《司法行政计划》(PlanfortheAdministrationofJustice。
不过,对于当时民事法庭上的英国法官来说,“印度教法”还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他们从来没见过任何一部真正的印度教法典,更不用提据此审案了。于是,黑斯廷斯很快将编译印度教法典的想法付诸行动。他从孟加拉各地请来11位德高望重的梵学家(pundits),让他们以印度传统的梵文文献和自己头脑中的知识为基础,尽快提取出具有约束和规范性质的内容,并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进行适当修正和补充,再用纸笔记录下来,最终汇集成一部梵文法律文本。这部梵文法律文本先由一名懂梵语的伊斯兰教徒(Zaid ud-Din’Ali Rasa’i)根据一个孟加拉语口头版本翻译成波斯文,然后再由黑斯廷斯的政治盟友、英国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纳撒尼尔·哈尔海德(Nathaniel Halhed,1751—1830年)从波斯文转译成英文。尽管编译过程十分复杂,颇费周折,但黑斯廷斯和纳撒尼尔·哈尔海德都一再强调这部法典忠实于原文:“梵学家们……从原始梵语文献中逐字逐句筛选,未敢增减任何内容。筛选出的条款被原封不动地翻译成波斯文,翻译成果又被以同样谨慎和还原的态度转译为英文。”(24)纳撒尼尔·哈尔海德:《印度教法典:梵学家之规训》(Nathaniel Halhed,A Code of Gentoo Laws,or Ordinations of the Pundits),伦敦:[印刷者不详]1776年版,第x~xi页。在黑斯廷斯看来,印度古老的印度教法已经被成功转录到英国法官能够直接阅读的录本中⑦。
当然,并不是所有英国人都认同印度教法典的构想,特别是远在宗主国——英国——的绅士们,他们早就听说印度本土根本没有成文法,轻蔑地将这里称为“毫无法纪……统治者目不识丁”的野蛮之地(25)罗伯特·奥姆:《自1659年起的莫卧儿帝国、马拉塔人和英国人在印度的相关历史片段》(Robert Orme,Historical Fragments of the Mogul Empire,of the Morattoes,and of the English Concerns in Indostan;From the Year MDCLIX),伦敦:F.温加夫印刷1805年版,第437页。。因此,与黑斯廷斯相反,英国国内不少人都主张“用从国外引进的新式法院、法典和司法原则取代(印度)本土制度”,从而“拯救孟加拉贫穷愚昧又饱受压迫的人民”(26)默文·戴维斯:《沃伦·黑斯廷斯,英属印度的缔造者》,第94页。。1774年,黑斯廷斯听闻英国议会准备向孟加拉引入一套全英式司法系统。为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他立即将已完成的两章“法典”样本寄给英国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力图向国内异议人士证明印度存在本土法律:“印度没有成文法的说法……是多么荒谬……他们其实拥有一套亘古未变的法律……我现在有幸将前两章展示给阁下,由此证实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并未处于毫无正义的野蛮状态。”(27)G.R.格莱戈:《沃伦·黑斯廷斯阁下:首任孟加拉总督的生活回忆录》,第400~402、400页。
在附信中,黑斯廷斯极力强调英国政府保留印度本土法律的重要性:“一个帝国要维护公民自由,最基本的就是保证他们能够遵循自己的法律……剥夺人们受自己的法律保护无疑是一种不平之事,而强迫人民服从他们完全不知道、也不可能有了解途径的其他法律,则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暴政……伊斯兰教统治者尚未剥夺(本地人遵守自己法律)的权利,那么英国的基督教政府起码应该表现出同样的宽容。”(28)G.R.格莱戈:《沃伦·黑斯廷斯阁下:首任孟加拉总督的生活回忆录》,第400~402、400页。黑斯廷斯的信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部尚未完工的法典样本开始令英国人相信印度的确有完备的成文法来支持当地的司法行政,从而保留当地法律比引入英国法更为可取。
1775年3月27日,在黑斯廷斯和哈尔海德的共同推动和努力下,印度本土法律的首次编译工作终告完成。次年,东印度公司在伦敦将其成果付梓,即《印度教法典:梵学家之规训》(ACodeofGentooLawsorOrdinationsofthePundits)。这是一个内部版本,由东印度公司发行。1777年唐纳森翻印了这部《印度教法典》,1781年该法典还出现了另一个版本。不仅如此,到1778年这部法典还被译为法文和德文出版。作为英国殖民当局编译创制的第一部印度教法律文本,《印度教法典》在现代印度教法形成的历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在东印度公司的法庭上一直使用到19世纪早期。不过,尽管这部法典的编译和出版给黑斯廷斯和哈尔海德带来很大声誉,但这部法典本身却充满争议,因为这个英译本并不是由英译者据原始梵文文献直接翻译而来,它的准确性大受质疑,未能成为盎格鲁-印度司法系统中的权威文本。在英国殖民当局看来,要编译和创造一部“权威的”印度教法典,就需要由一个精通梵语、能够亲自阅读和翻译梵文典籍的英国人承担此项重任,以避免转译过程中的讹误和本地婆罗门梵学家有意无意的误导。随着1783年9月25日富有语言天赋、早前已被任命为孟加拉威廉堡最高法院陪席法官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年)抵达加尔各答,印度教法典的编纂迎来了一个看来更为合适的人选。事实证明,威廉·琼斯的确为英印殖民当局编纂“权威的”印度教法文本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 构建权威:威廉·琼斯的印度教法律汇纂和典籍翻译
威廉·琼斯是一个非凡的语言天才,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通晓东西方的十几种语言。依靠语言优势,他翻译了大量的东方文学作品,对东方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还在国内时就被认为是“英国首屈一指的东方学家”(29)富兰克林·埃杰顿:“威廉·琼斯爵士(1746—1794)”(Franklin Edgerton,“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美国东方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66卷第3期(1946年7—9月),第230页。。遗憾的是,当时威廉·琼斯对印度的了解只停留在书面上,还未亲自到过这个遥远的异域,切实了解这个东方国度。所以,主司法律的他很渴望能够得到一个孟加拉法院的职位,并为之花费了4年时间进行争取。1783年3月,威廉·琼斯终于如愿被任命为加尔各答最高法院法官。那时,他还不曾想到,他的印度之行最大的成就并不在司法,而在梵文文本的翻译。
起初,威廉·琼斯并没有对印度教法抱有太多兴趣,更未打算掌握梵语,因为他觉得自己年龄已大,很难对完全陌生且晦涩难懂的梵语从头学起。然而,当威廉·琼斯开始投身于加尔各答法院的工作后,他很快发现英属印度实际的司法状况与他预想的完全不同。黑斯廷斯主持编译的《印度教法典》内容并不详实,只是“偶尔才在法庭上被援引”(30)罗珊娜·罗彻尔:“盎格鲁-印度教法的发明”(Rosane Rocher,“The Creation of Anglo-Hindu Law”),蒂莫西·卢宾等编:《印度教和法律:导论》,第80页。。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大量裁决不得不依赖当地梵学家的帮助。按照威廉·琼斯自己的说法,这些梵学家对印度教法原则的解释几乎是“随心所欲”,甚至能“在找不到成文法律时酌情现造一个”(31)泰恩茅斯勋爵:《威廉·琼斯爵士的生平、著作和通信回忆录》(Lord Teignmouth,Memoirs of the Life,Writings and Correspondence,of Sir William Jones),伦敦:J.哈查德印刷1815年版,第330、382页。,而英国的法官则苦于不懂梵文,只能听凭摆布。威廉·琼斯对此感到既愤怒又忧虑。他说:“凭借多年经验,我认为我决不能轻易采纳本土专家所进呈的书面意见,因为哪怕有一丁点利益驱使都可能使他们误导法庭。无论我们多么小心,他们要蒙蔽我们都易如反掌。”(32)泰恩茅斯勋爵:《威廉·琼斯爵士的生平、著作和通信回忆录》(Lord Teignmouth,Memoirs of the Life,Writings and Correspondence,of Sir William Jones),伦敦:J.哈查德印刷1815年版,第330、382页。
威廉·琼斯和黑斯廷斯一样,坚信印度人拥有自己的法律,也极力主张殖民当局必须“谨慎地尊重他们的宗教情感和风俗习惯”(33)A.阿斯皮诺尔:《康沃利斯在孟加拉》(A.Aspinall,Cornwallis in Bengal),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31年版,第126页。。但是,他并不认为那些“易受蛊惑”又“糊里糊涂”的印度人自己有能力实施和解释自己的法律(34)加兰德·卡农编:《威廉·琼斯爵士的信件》(Garland Canon,ed.,The Letters of Sir William Jones)第2卷,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0年版,第847、795、796~799页。,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要由英国人来做。可是,“在英国人对印度的习惯和法律典籍充分掌握之前,给英属印度制定符合当地风俗观念之法的目标分明无法实现。”(35)A.阿斯皮诺尔:《康沃利斯在孟加拉》(A.Aspinall,Cornwallis in Bengal),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31年版,第126页。于是,威廉·琼斯决定亲自学习梵文,将“封锁在古老文本和梵学家头脑中”的印度教法律解放出来,通过英国人建立的现代司法系统真正实施这些法律(36)伯纳德·科恩:《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第69、70页。。
1785年夏末,威廉·琼斯正式开始接触梵语语法。不到一年,他便开始萌生出一个更具野心的想法,那就是重新编纂和翻译一部足够完备的印度教法典,用英国人熟悉的汇纂形式编排,从而用一部新的英文法律汇编取代黑斯廷斯和哈尔海德编译的《印度教法典》,使之成为首要的司法依据。威廉·琼斯计划与印度的梵学家们合作,将民法领域最具权威的原始文本全面筛选整理出来,以汇纂的形式分类排列,形成一部成熟实用的法典,再译成英文供英国人法官使用——这相当于把当地分散凌乱的“法律”文献整理为一套系统的专门法典,极大增强了英国人在法庭上的自主性。由于这种编写方式效仿了欧洲历史上的《查士丁尼法典》,威廉·琼斯因而兴奋地期望时任总督康沃利斯伯爵(Earl Cornwallis)成为“印度的查士丁尼”,而将自己暗比为《查士丁尼法典》的编纂者特里波尼安(Tribonian)(37)伯纳德·科恩:《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第69、70页。。
1788年3月,威廉·琼斯致信康沃利斯总督,向后者陈述目前印度民事法庭的困境:“绝大多数印度教法和伊斯兰教法的原则藏在梵语和阿拉伯语文献中,而能够解读这两种复杂语言的欧洲人却凤毛麟角……若我们一味依赖当地人的解释,很难保证不会被欺骗。”(38)加兰德·卡农编:《威廉·琼斯爵士的信件》(Garland Canon,ed.,The Letters of Sir William Jones)第2卷,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0年版,第847、795、796~799页。接下来,威廉·琼斯详细阐述了他解决这一问题的宏大计划:“如果能编修完整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法汇纂……并准确翻译成英文……供各地民事法庭参考,我们大概就可不再为案件适用的规则感到苦恼,且不再被梵学家或毛拉所欺骗。……我们只需(将汇纂)限于民事纠纷中最常用的合同法和继承法部分……(由)当地梵学家和伊斯兰毛拉来汇总,当地记录员抄录……还需要一个懂梵语和阿拉伯语的领导者,此人须熟知法理,甚或具备立法精神……从而承担事务部署、汇编督察、将成果转译为英文等关键性的工作。”(39)加兰德·卡农编:《威廉·琼斯爵士的信件》(Garland Canon,ed.,The Letters of Sir William Jones)第2卷,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0年版,第847、795、796~799页。威廉·琼斯表示自己愿意担任这一关键的领导者,并希望该建议能够被尽快采纳,并在资金方面得到政府的支持。
威廉·琼斯编写法律汇纂的构想很快获得殖民当局的认可,康沃利斯总督对他的主动请缨表示由衷的欣慰,并且毫不犹豫地承诺愿意提供该计划所需要的经费(40)查尔斯·罗斯:《康沃利斯侯爵的通信》(Charles Ross,Correspondence of Marquis Cornwallis)第1卷,伦敦:约翰·默里公司1859年版,第541~542页。。收到回复的威廉·琼斯迅速投入这项工作中。他首先将民法内容分门别类,再请当地的梵学家在每个类目下摘录最具权威的法律文献资料,备注原始作者姓名、作品出处、章节和字句等,最后由他亲自将这些内容译成英文,并勘定索引(41)加兰德·卡农编:《威廉·琼斯爵士的信件》第2卷,第721、928页。。从1788年起,威廉·琼斯开始在本职工作之余尽可能抽出时间参加汇纂的编译。他相信,新的印度教法汇纂出版越早,越有利于英国人对印度本土法律的掌握。到1794年3月,威廉·琼斯向东印度公司管制委员会主席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报告说,长达9卷的梵文法律汇编已经完成,翻译工作则预计在1796年前结束,而到那时,他将辞职引退,安然度日(42)加兰德·卡农编:《威廉·琼斯爵士的信件》第2卷,第721、928页。。然而,不幸的是,1794年4月威廉·琼斯就因病去世了,未能亲眼看到他规划和编修的印度教法汇纂的出版,后续翻译和出版工作由被誉为“欧洲第一个伟大的梵语学者”的亨利·科尔布鲁克(Henry Colebrooke,1765—1837年)接手完成(43)C.D.沃特斯顿、A.麦克米兰·希勒:《爱丁堡皇家学会前会员传记索引(1783—2002)》(C.D.Waterston and A.Macmillan Shearer,Biographical Index of Former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1783—2002)第1部分,爱丁堡:爱丁堡皇家学会2006年版,第194页。。尽管威廉·琼斯本人未能最终完成他规划的印度教法汇纂工程,但他在构建“权威的”印度教法文本方面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实际上,除了致力于编译印度教法汇纂,威廉·琼斯还凭借自己的语言天赋将一些重要的梵文典籍译成英文。对他来说,准确了解和理解作为印度教法渊源的印度教圣典和编纂现代法典本身一样重要。威廉·琼斯此类工作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接替印度学家查尔斯·威尔金斯(Charles Wilkins)翻译了《印度教法精义:摩奴之规训——据鸠鲁伽注本,论印度宗教和世俗义务体系》(InstitutesofHinduLaw:or,theOrdinancesofMenu,AccordingtotheGlossofCullúca.ComprisingtheIndianSystemofDuties,ReligiousandCivil,Calcutta,1794),即人们熟知的印度教法典籍《摩奴法典》(Dharma-shastraofManu/Manu-smriti)。这部译作最重要的价值可能并不在于其中呈现的具体的法律内容,而在于威廉·琼斯在为其撰写的“前言”中对印度教法的解释。威廉·琼斯称,印度民族本就是一个深信神之启示的群体,而《摩奴法典》正是传说中的神圣立法者摩奴颁布的法律,所以是最神圣的印度教法的基础(44)威廉·琼斯编译:《印度教法精义:摩奴之规训》(William Jones,trans.& ed.,Institutes of Hindu Law,Or,The Ordinances of Menu),加尔各答:印度政府1794年版,“前言”,第iii~iv、v~xvi、xvii~xix页。。随后,他借助西方文明历史的时间谱系分析了印度教法重要发展阶段可能对应的年代,并花费了大量笔墨来分析摩奴及其法律与西方文化的亲缘性(45)威廉·琼斯编译:《印度教法精义:摩奴之规训》(William Jones,trans.& ed.,Institutes of Hindu Law,Or,The Ordinances of Menu),加尔各答:印度政府1794年版,“前言”,第iii~iv、v~xvi、xvii~xix页。。在威廉·琼斯的描述下,印度教法呈现为一种充满宗教和迷信色彩的古老规范集,而且与西方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同源性。威廉·琼斯的描述无疑给印度教法赋予了重要的辨识度,使其从一个只能用“本地”和“宗教法”等简单标签来界定的模糊影子,成为有特征、有历史、可追溯的传统。作为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印度教法律典籍,《摩奴法典》的英译无疑也构成了印度教法权威文本建构中的重要一环。当然,威廉·琼斯始终都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他自豪地宣称自己的工作成果是“这个对欧洲政治和商业利益都意义非凡的国家的最受尊崇的法律”,其背后的意义则是“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教徒勤奋工作给英国带来的巨额财富”(46)威廉·琼斯编译:《印度教法精义:摩奴之规训》(William Jones,trans.& ed.,Institutes of Hindu Law,Or,The Ordinances of Menu),加尔各答:印度政府1794年版,“前言”,第iii~iv、v~xvi、xvii~xix页。。
四 盎格鲁化:亨利·科尔布鲁克的印度教法翻译与解释
在威廉·琼斯去世后,亨利·科尔布鲁克接手了印度教法汇纂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亨利·科尔布鲁克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乔治·科尔布鲁克爵士曾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受家庭影响,1783年年仅18岁的亨利·科尔布鲁克来到印度。他起初在加尔各答谋职,后被调往印度古典文化的圣地蒂尔胡特(Tirhut)任收税官。在那里,他出于对古印度代数知识的兴趣开始接触和学习梵语(47)T.E.科尔布鲁克:《H.T.科尔布鲁克的生活》(T.E.Colebrooke,The Life of H.T.Colebrooke)第1卷,伦敦:特吕布纳公司1873年版,第53、75页。。1794年,亨利·科尔布鲁克已在梵语学习方面获得了一定成效。当听说威廉·琼斯突然离世,编译印度教法汇纂的工作可能不得不戛然而止时,他便自告奋勇提出愿意接替威廉·琼斯的工作(48)T.E.科尔布鲁克:《H.T.科尔布鲁克的生活》(T.E.Colebrooke,The Life of H.T.Colebrooke)第1卷,伦敦:特吕布纳公司1873年版,第53、75页。。不过,在此之前,亨利·科尔布鲁克并未从事过多少专业的司法工作,语言技能是他进入英属印度司法部门的主要优势。
亨利·科尔布鲁克的加入让印度教法汇纂的编修工作再次顺利运转起来。经过4年紧张的工作,1798年完整的《印度教合同和继承法汇纂》(ADigestofHinduLawonContractsandSuccessions,以下简称《印度教法汇纂》)终于在加尔各答出版,供孟加拉司法部门参考。然而,威廉·琼斯和亨利·科尔布鲁克致力编译的这部“权威的”《印度教法汇纂》并非没有受到质疑。即使在亨利·科尔布鲁克自己看来,这部法律汇纂也显得冗长杂乱,“原始引文多来源于法经和法论,但此外也会引用往世书、史诗故事等其他文献资料……一些明显相互矛盾的解释被编者并置,要么毫无注解,要么编者自作主张地添上自己的想法。”(49)罗珊娜·罗彻尔、卢多·罗彻尔:《西方印度学的建立: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与东印度公司》(Rosane Rocher,Ludo Rocher,The Making of Western Indology:Henry Thomas Colebrooke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纽约:劳特里奇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37页。弗朗西斯·麦克纳格顿在其《孟加拉现行印度教法考鉴》中虽然称赞“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观点(与亨利·科尔布鲁克的相比)可以合乎情理地得到更大的尊重”,但也抱怨《印度教法汇纂》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不能在被认为拥有同等权威的文本中找到肯定或否定根据的印度教法问题”(50)弗朗西斯·麦克纳格顿:《孟加拉现行印度教法考鉴》(Francis MacNaghten,Considerations on the Hindoo Laws,As It Is Current in Bengal),塞兰坡:传教出版社1824年版,第317、iii页。。托马斯·斯特兰奇爵士尽管称它为“司法知识的宝藏”,却也同意当时殖民地法律界对它的普遍评价:“对律师是最好的法律书籍,对法官而言却是最糟糕的。”(51)托马斯·斯特兰奇:《印度教法大纲;英国在印度的司法判例参考》(Thomas Strange,Elements of Hindu Law;Referable to British Judicature in India)第1卷,伦敦:佩恩与福斯印刷1825年版,第xviii~xix页。这种评论反映了这部法律汇纂实际适用的糟糕状况:英国殖民统治者和东方学家的法律想象同印度的社会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归根结底,这是由于威廉·琼斯和亨利·科尔布鲁克根据西方的单一宗教和单一法律观念建构起来的这部《印度教法汇纂》并不符合印度本地复杂多变的多元化社会现实。因翻译《印度教法汇纂》而转入司法部门工作的亨利·科尔布鲁克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就已发觉,不同地方承认的经典文本往往迥然相异,要在司法实践中参考和适用同一部法典简直是困难重重(52)T.E.科尔布鲁克编:《H.T.科尔布鲁克的杂文及作者生平》(T.E.Colebrook,ed.,Miscellaneous Essays of H.T.Colebrooke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第1卷,伦敦:特吕布纳出版社1873年版,第85页。。不过,亨利·科尔布鲁克并没有对印度教法概念本身提出质疑,而是试图调和《印度教法汇纂》与印度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
亨利·科尔布鲁克的解决之道就是创造一套“关于印度教法性质的话语”(53)伯纳德·科恩:《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第72页。。他主张将印度教法典籍区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别:第一类是他所谓的“法经”(Dharma-sastra)(54)“Dharma-sastra”国内学界一般译为“法论”,区别于所谓的“法经”(Dharma-sutra)。不过,在亨利·科尔布鲁克的话语语境中,Dharma-sastra作为他理解的“神圣法典”(‘sacred code of law’)译为“法经”似乎更符合中文语义,而他所谓的“法论”则是指一类他称之为“本集”的梵文法律文献。,称为“所记”(smriti),区别于所谓的“所闻”(sruti);另一类则是数量庞杂的“本集”(sanhitas)。亨利·科尔布鲁克认为前者与欧洲人理解的实体法或法律规范较少相关,而与法证法(forensic law)有着更多的相关性,后者则是威廉·琼斯理解的“法律”(规定性规范),印度人认为这类规范是由“仙人”规定的。他进一步认为古代仙人创制了这些法论(treatises),后世的印度教法学家或梵学家则为之撰写注释(commentaries),这两者——原始法论和后世注释——共同构成了印度的法律典籍。此外,还有一类可称为“弥曼差”(Mimamasa)的文献,亨利·科尔布鲁克认为这类文献讨论的是法律逻辑问题和调和相互矛盾的法律解释的方法。在他看来,印度教法律“传统”中对同一法律文本经常存在着彼此矛盾的解释(亨利·科尔布鲁克认为这是印度各地存在历史和文化差异的结果)。他将这一事实看作印度教法中存在不同“学派”的反映。如同伊斯兰教法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派别一样,亨利·科尔布鲁克在1810年翻译出版的《印度教继承法二论》中也将印度教法律传统分为“达耶跋伽”(Dayabhaga)和“密塔娑罗”(Mitakshara)两大派别。前者的影响仅限于孟加拉,而后者的影响范围则包括了贝拿勒斯、迈塔拉(Mithala)、马哈拉施特拉和达罗毗荼等广大地区。根据亨利·科尔布鲁克的看法,每个学派都有确定的“教义”,因而英国法官需要寻求“那些可靠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每个学派的全部教义就可以根据支持它的理据作一通盘的综合性考量”(55)伯纳德·科恩:《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第74、72页。。
尽管伯纳德·科恩盛赞“亨利·科尔布鲁克在为歧义纷呈的法律文本提供将成为英国法庭标准的固定解释方面比任何一个英国人都做出了更多贡献”(56)伯纳德·科恩:《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第74、72页。,但对于亨利·科尔布鲁克主张的印度教法存在不同学派的观点,却不乏非议。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前所未有,难以考证,有人认为其对印度教法的划分与伊斯兰教法的派别模式太过相似,实有生搬硬套之嫌。法学家阿奇博尔德·加洛韦嘲笑“贝拿勒斯学派和孟加拉学派法律听起来就像鉴赏或艺术流派一样”(57)阿奇博尔德·加洛韦:《对印度法律、宪法和当前政府的看法》(Archibald Galloway,Observations on the Law and Constitution,and Present Government of India),伦敦:帕布里与艾伦公司1832年版,第287页。。梵语学家伯内尔则委婉地将亨利·科尔布鲁克的诠释称为“英国法学家演绎出来的一种结论”(58)A.C.伯内尔:《分产与继承法》(A.C.Burnell,The Law of Partition and Succession),芒格洛尔:斯托尔兹与希尔纳印刷1872年版,第v页。。马德拉斯法官詹姆斯·纳尔逊更对亨利·科尔布鲁克划分印度教法学派所依据的梵文文献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那篇备受尊重的论文(指亨利·科尔布鲁克所译《印度教继承法二论》中的《密塔娑罗》——引者注)毕竟只是对一部汇集了某些迈提拉(Maithila)哲学家教导和启示的作品的注释,难道就仅仅因为亨利·科尔布鲁克曾经喜欢它并在1810年出版了它的译文,马德拉斯高等刑事法院就得毫不犹豫地将其奉为马德拉斯省的法律吗?”(59)詹姆斯·纳尔逊:《马德拉斯高等刑事法院关于管理印度教法的观点》(James Nelson,A View of the Hindu Law as Administered by the High Court of Judicature at Madras),纳加帕蒂南:伊克利斯印刷1877年版,第96页。
不过,这些批评并未对亨利·科尔布鲁克在英印司法界的实际影响力产生多大损害。凭借在梵语法律文献翻译方面的独特贡献,亨利·科尔布鲁克成为英印殖民地首屈一指的印度教法专家,他关于印度教法学派的解释很快在英印司法界占据主导地位,哪怕亨利·科尔布鲁克自己也表示这些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60)亨利·科尔布鲁克:《印度教继承法二论》(Henry Colebrooke,Two Treatises on the Hindu Law of Inheritance),加尔各答:A.H.哈伯德印刷1810年版,第ii页。。《印度教继承法二论》甫一出版,便被送往所有民事法院作为参考,法庭随即开始改变之前在统一的印度教法典中寻找有关条文的做法,转而根据地区来查找相应法学派的规定。1868年,英国枢密院在一起上诉案件中明确表示:“执行印度教法法官的职责,并非查询争议性条款是否能由初始(梵文)文献推断出来,而是确定它是否为案发地所属的法学派认可。”(61)埃德蒙·摩尔编:《司法委员会和国王陛下最尊敬的枢密院审理和裁决的案件报告,东印度最高法院和高等迪万法院的上诉》(Edmund Moore,ed.,Reports of Cases Heard and Determined by the Judicial Committee and the Lords of His Majesty’s Most Honourable Privy Council,on Appeal from the Supreme and Sudder Dewanny Courts in the East Indies)第12卷,伦敦:史蒂文父子公司1873年版,第436页。
威廉·琼斯曾期待印度教法典的英译本能够取代当地梵学家的权威,亨利·科尔布鲁克让这一点变成了现实。亨利·科尔布鲁克本人也成为印度教法文本的权威解释者。他的一系列评论文章成为解释印度教法的公认标准。后来,不仅英国法官援引他的法律解释,就连印度本地的梵学家们也遵从他对印度教法的解释。若有新的法规发布,必须由亨利·科尔布鲁克判定是否符合印度教法才能登记在案,甚至作为法庭顾问的婆罗门也要由他进行认证才能上岗(62)罗珊娜·罗彻尔、卢多·罗彻尔:《西方印度学的建立: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与东印度公司》,第62页。。用当时一位英国中殿律师威廉·莫利(William Morley)的话说:“千数梵学家之语,不抵亨利·科尔布鲁克一言。”(63)威廉·莫利:《英属印度的司法管理:其历史与现状》(William Morley,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British India:Its Past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伦敦:威廉和诺盖特公司1858年版,第333页。
这种情况看似荒谬,却是英印殖民当局相当满意的结果,因为至此英国人终于取代印度人成为解释印度教法的最高权威。现在,英国殖民者不仅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意愿形塑了“权威的”“文本化的”印度教法,而且获得了告诉印度人他们自己的法律传统应该是怎样的资格。结果,印度人的印度教法变成了所谓的“盎格鲁-印度教法”,即英国人创制的盎格鲁风格的印度教法。这种英国人创制的“现代”印度教法逐渐打上了深深的英国判例法烙印:“在接下去的40年中,在威廉·琼斯宣布他将通过得到法庭任命的梵学家协助的英国法官为印度教徒提供他们自己的法律后,一种特别的判例法形成了。在基础部分,有某一作者的文本可供参考,该作者被认为代表了某个特别的地区学派的规范,但在诸如托马斯·斯特兰奇的《印度教法大纲》(ElementsofHinduLaw)之类的集解中,被尊为印度教法律的却是由英国法官们对判例所作的一系列解释。”(64)伯纳德·科恩:《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第74~75页。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令人意外的是,随着盎格鲁-印度教法的正式形成,印度本地的梵学家们最终在1864年司法改革中被排挤出英印司法系统。这就是沃什布鲁克所谓的盎格鲁-印度教法“假设”:“自1864年起,盎格鲁-印度教法便‘假设’其关于印度教伦理的知识已然足够而解雇了梵学家。解释由此固定下来了。”(65)D.A.沃什布鲁克:“印度殖民地时期的法律、国家和农业社会”,第673页。这样,原本仅为英国殖民者社会想象的印度教法最终转变为英印殖民地社会的法律现实:盎格鲁-印度教法。
五 结论:盎格鲁-印度教法和西方化东方的知识建构
美国埃默里大学南亚和伊斯兰教研究教授斯科特·库格尔曾在“构设、指摘和改名:南亚殖民地时期伊斯兰法学的重铸”一文中指出:“法律是权威文本、文化想象和统治之策在一定条件下的综合产物……它是一种经验解释,这种经验解释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能够依靠(统治者的)权力,将解释的内容转变为社会现实。”(66)斯科特·库格尔:“构设、指摘和改名:南亚殖民地时期伊斯兰法学的重铸”(Scott Kugle,“Framed,Blamed and Renamed:The Recasting of Islamic Jurisprudence in Colonial South Asia”),《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35卷第2期(2001年5月),第257页。这段描述用来形容盎格鲁-印度教法的诞生过程是再恰当不过了。通过收集和翻译古老的梵文典籍,英国人在印度创造出一种盎格鲁风格的宗教法典,它不仅将印度口头传统的权威转移给宗教法文本,使得当地原来主要依靠非成文的习惯法裁决争端的传统转变成西方主要依靠成文法典的司法实践,还用一套单一的法律体系取代了印度多元的法律和解释传统。更重要的是,英国人一方面把这种文本化了的印度教法介绍到西方,让西方人相信印度本土法律就记录在东方学家翻译的典籍中,另一方面又通过殖民权力让印度人自己同样接受了英译本中的印度法律。直到最近,国际法学界还将“印度教法”界定为“法论文献中描述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法律”,“根据这个定义,印度教法是一种可与犹太教法、伊斯兰教法和教会法等其他传统比拟的宗教法律体系”(67)蒂莫西·卢宾等编:《印度教和法律:导论》,第6页。。作为殖民主义知识遗产之一的盎格鲁-印度教法并没有随着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到来而烟消云散。
此外,英印时期印度教法文本编译的作用和意义并未局限于法律建构方面,而是扩展至宗教乃至整个社会领域。如前所述,19世纪之前,印度并不存在一种名为“印度教”的单一宗教体系。作为一种单一宗教体系的“印度教”概念来自英国殖民者对印度本土社会的想象。英国人对印度本土法律最初的定位即是“宗教的”和“神授的”(68)威廉·莫利:《英属印度的司法管理:其历史与现状》,第199页。,只要提及印度法律,就一定会强调其宗教背景。1772年之后,当英国殖民者和东方学家们企图从古代梵文文本中编纂印度教法典时,那些被作为法律渊源的古代梵文文本便成为印度本土宗教的圣典,东方学家在对其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又刻意为之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暗示出某种强烈的宗教属性。于是,在英国人通过文本翻译逐渐建构起盎格鲁-印度教法典的同时,一个古老、神圣、正统的文本化宗教也同时被创造出来了。
的确,直到19世纪30年代,现代印度教的概念才开始逐渐流行,它的核心要素就是英国人认可的典籍。1877年,莫尼尔·威廉姆斯爵士编写的《印度教》一书出版。该书通过介绍吠陀及其他梵文典籍来阐释印度教的思想与实践,明确指出:“欲知印度教的前世今生,领悟其精神内核,必得从研读梵文文献起步。”(69)莫尼尔·威廉姆斯:《印度教》(Monier Williams,Hinduism),伦敦: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印刷1877年版,第14页。尽管根据古老的吠陀传统,人自身的头脑和心灵(而非外在的书本)才是知识的适当容器,但英国人的印度教法典编译工作无疑大大促进了印度教的文本化。从此以后,就像《圣经》被视为西方基督教的基石一样,吠陀典籍也被看作印度宗教——印度教的基石,典籍、宗教和法律三者开始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不仅如此,通过法典编纂和宗教建构而形塑出来的印度社会也由此变成了一个“西方化的东方社会”,即一个按照西方人的社会想象来建构的东方社会,尽管这个社会被看作与现代西方社会迥异的他者社会。18和19世纪深受当时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影响的英国东方学家普遍对他们所看到和想象的神秘、灵性、遥远的印度文明抱有强烈的共情,将印度的现在视为欧洲失落了的过去。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在历史中为欧-印双方寻找相似性和亲缘性,另一方面又希望将印度描述为一个类于西方而亚于西方的文明和国度。在谈及印度本土的法律状况时,沃伦·黑斯廷斯就曾说道:“一个民族无论如何聪慧,如果它的研究局限于他们自己的宗教的狭小圈子,局限于以它的迷信为基础的法令,如果它在寻求真理过程中的讨论缺少那种灵性的辅助(that lively Aid)——这种辅助只能来自理解力的自由运用和反复辩难,那么,从这个民族的劳动中是不能指望产生一种完美的法学体系的。”(70)孟加拉省督和参事会:《威廉堡省督和参事会关于孟加拉土著人司法的议事录》(Bengal Governor and Council,Proceedings of the Governor and Council At Fort William,Respect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mongst the Natives in Bengal),伦敦:J.阿尔蒙印刷1775年版,第35页。在他们看来,英国人肩负的使命就是帮助印度人找回昔日的辉煌,正如威廉·琼斯在诗作《恒河颂》(HymntotheGanges)中假借印度人之口为英国定位的那样,“……终止咱们(被外来侵犯)的恐惧,恢复咱们的法律”(71)泰恩茅斯勋爵编:《威廉·琼斯爵士作品集》(Lord Teignmouth,ed.,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第13卷,伦敦:约翰·斯托克代尔出版公司1807年版,第333页。。这恰恰契合了英国浪漫主义者在异域寻找理想化了的过去的自我的心理需求。正如萨义德所说,“对西方人而言,东方总是与西方的某一方面相像”(72)爱德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89、8页。。
美国当代人类学家尼古拉斯·德克斯将此称为殖民主义者的一种“经典性的自我效仿(Self-mimesis)”(73)尼古拉斯·德克斯:“前言”(Nicholas Dirks,“ Foreword ”),伯纳德·科恩:《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第xv页。,即殖民主义者看似是要将他们的殖民地构建为一个与自己全然不同的他者,但事实上,这个他者不过是殖民者自身的倒影。印度教法译本中显露出来的印度社会其实只是一个西方自我定义中的东方。萨义德指出:“之所以说东方被‘东方化’了,不仅因为它是被……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而且因为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为——‘东方的’。”(74)爱德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89、8页。在盎格鲁-印度教法建构的过程中,文本编译的实践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制作或驯化的场所,它看似是一个透明转录的过程,但实际上带有深刻的目的性:印度教法典中的文本印度“被制作成”现代西方人想象的传统社会。传统性既是印度教法典编纂的前置预设,也是印度教法典编纂的直接结果。由此建构起来的印度社会事实上被置于西方的霸权性话语体系之下。直到今天,甚至印度官方还都习惯用“不可思议的印度”(Incredible India)和“奇异国度”(Exotic Land)之类的语词来形容自己,他们明显承袭了殖民地时期英国东方学家的印度社会想象和建构(75)参见印度旅游局官方网站http://www.incredibleindia-tourism.org/,[发布日期不详]/2023-11-02。。
这一由文本翻译开启的社会建构工程的殖民主义性质始终不易察觉,但它的确形塑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正如当代印度文化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所说,“翻译形塑了并具体化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等的权力关系”(76)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语言,斗争之所》,第32页。,而这种权力关系直接造成了一种长期实力悬殊的文化定局,企图让殖民主义状态在印度这样的前殖民地永不谢幕。殖民主义知识遗产影响深远,对殖民主义知识建构的一个片段的历史的重访,或许有助于我们厘清人们仍习以为常的某些“常识”的真实性质和隐藏于其中的权力关系。过去无法改变,但现在和未来却可以不被过去长久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