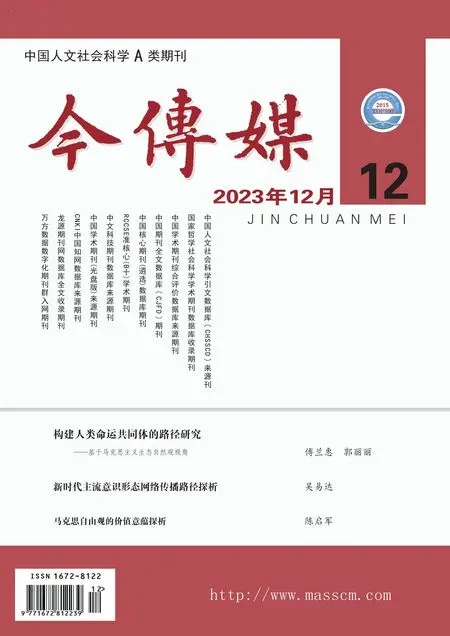风险传播中的媒体公共话语属性再思考
2024-01-17刘冰瑜
刘冰瑜
(西安报业传媒集团,陕西 西安 710068)
一、引 言
20世纪下半叶至今,近半个世纪,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在内的频繁的战争、瘟疫、恐袭、核扩散和生化污染等灾难频发,危机和风险传播成为新闻报道的显著风景。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借由新媒体传播被放大,媒介公共话语属性在风险传播视角下经受再次检视,如何守正媒体方向、增进新闻舆论“四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二、背景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弥漫全球,从政府机构到专业团队,从传播媒介到受众,由病毒引发的“危机”意识笼罩着人们,也使得“灾害传播”“危机传播”和“风险传播”成为热门话题。由于危机发生的区域、时间、强度和破坏程度的不确定性,加上媒体性质、立场甚至传播个体的认识等不同因素影响,风险传播报道极易出现偏差,媒体公共话语属性受到了严峻考验。
三、媒体公共话语属性定义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新闻媒体具有公共(公众,社会)属性,即媒体的公共话语属性。本文认为,媒体公共话语属性是指新闻媒体借由为公众传播信息而具有的社会引导、教化和批判功能,它是塑造文化认同、社会信仰和公共精神的有力工具。
媒体的公共话语属性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新闻媒体具有统一性。作为国家和政府的特殊资源,它通过所有权和监管权体现公共属性(即通常表述为“公众性”),而媒体具有的“公共性”,比如报纸、杂志、图书、网络信息、电子出版物的书号和刊号、广播电视电影的频率使用许可和批准文号均由国家管控,国家管控赋予了媒体全民与社会属性。另一方面,新闻媒体的公共话语属性还具有开放性和公益性。媒体面向所有人,寻求最大化影响力,受众权利均等、均享。媒体公共属性要求必须把维护公众共同利益视为媒体的基本诉求和最大目标,且必须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新闻媒体公共属性主要包含以下具体要求:1.保障满足公民知情权;2.保障媒体不得侵犯法律所保护的公众私人利益;3.保障媒体的普遍服务原则。媒体的公共属性定义了新闻生产、产品及其销售活动的“公共产品”性质。诸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言,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指: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或劳务显著不同)具有三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以及受益的非排他性[1]。
四、风险传播视野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播
我国学界对风险传播的定义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把风险传播和危机传播视为一体的“危机风险传播”,认为风险传播是危机传播四个阶段 (预防沟通、愤怒管理、危机沟通和利益相关方沟通)或五个阶段(前危机、初始、保持、解决和评估)的第一阶段;另一种观点认为,风险传播是一种独立、自成体系的传播模式[2]。一些专家认为,风险传播和普通传播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对正在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传播,前者是对未发生事实的预测报道。笔者认为,风险传播仍是一种对事实的传播,报道本身就是在各种事实基础上推理出来的,例如自然灾害、疫情走向等。所有作为风险提示指导的先验性、先导性传播,都首先来源于对既有事实的分析研判。也就是说,专家、权威人士或政府部门发出的参考、引导和指导性意见都是他们根据各自领域专长、根据现有技术手段以及实际情况,在已(往)发生的事实基础上的研究、判断和推理的结果,是多米诺骨牌式事实因果关系的反映[3]。
笔者以2019年12月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进行风险传播分析,发现大部分人出现了“疫情集体焦虑症”,如疫情的确证暴发、对疫情结束的预期、对莲花清瘟等中药和疫苗效果的疑虑等都是舆论场的关注重点。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于2020年1月20日晚接受央视采访时,证实了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的情况,消息一经发布就引爆舆论场,形成了新一波报道热潮。1月23日,超千万人口的武汉市宣布“封城”,进一步引发了人们的焦虑情绪。从潜伏期到暴发期,仅仅经过1个月,大众与媒体都经历了对新冠肺炎一波三折的疑惧感知过程。
五、疫情报道中的媒体公共属性表现
在我国,党管媒体是基本前提,新闻媒体按照自身规律运行是基本原则;前者保证了媒体的基本公共属性,后者确保了媒体的专业属性。在媒体管理机制与体制上,有管理权属(央媒和地方媒体)、地域分布(发达和非发达地区)和行业分类(地质、煤炭、铁道、旅游、文化、贸易等)的区分。在党和国家政府部门的统筹领导下,媒体实现了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优势互补、力量共聚。在这场持续了两年多的风险传播报道活动中,全国主流媒体圆满完成了任务,有力地发挥了主流媒体引导舆论、化解危机的公共担当作用。
(一)发挥公信力,凝聚共识
疫情暴发后,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奔赴疫情一线地区报道前线抗疫情况,例如《财经》 《新京报》 《澎湃新闻》《三联生活周刊》 《中国青年报》以及《中国新闻新周刊》等,出色的独家报道让人印象深刻。2020年1月21日,《人民网》发表了李泓冰《面对疫情,任何侥幸都可能夺人性命》一文,向人们传达了“遏制疫情蔓延,保障群众健康,任何‘耍大胆’‘不设防’的侥幸心态都是极其要不得的”的呼吁,起到了科学抗疫、稳定人心的作用。
(二)发挥权威性,稳定情绪
疫情期间,主流媒体采访一线人员和医疗专家,通过真实及时地报道和科普,稳定了人们的情绪,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例如,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连线采访钟南山院士、上海东方卫视采访张文宏教授、多家媒体记者深入武汉进行一线报道。《人民网》1月28日再发沈彬的评论《病毒必须隔离,人心不能疏离》,“要警惕,不能把群防群控概念偷换成极端狭隘的‘地方主义’,(呼吁不要)‘谈鄂变色’,把抗疫大业搞成‘地域黑’”。这些权威媒体的声音有力有效地填补了社会和群众之间的沟壑。
此外,2020年3月20日《湖北日报》刊发的消息《湖北新冠肺炎新增病例首次零报告》,以及4月8日新华社发布的《从“暂停”到“重启”: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 (两篇均为2020中国新闻一等奖作品),均起到了稳定社会、凝聚人心的作用,有效发挥了主流媒体的独特优势。
(三)发挥专业性,服务到家
2020年1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发布了《拒绝新型肺炎,你必须懂得的“口罩文化”》,2020年2月28日,《北京日报》客户端发布了《2月“科学”留言榜,榜单上果然都是TA》,均从受众关注的焦点出发,以科普形式破解了谣言。例如“吸烟能预防新冠病毒感染”“超市内的蔬菜、水果和肉类,很容易传播新冠病毒”“喝高度酒可抵抗新冠病毒”“气溶胶传播新冠病毒?还能否开窗户”等。总体而言,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宣传中,主流媒体的各种科普“提示”“链接”“贴士”和“手册”,都在第一时间解答了受众的疑虑。
(四)发挥融合力,互动到位
近年来的媒体融合发展,使得主流媒体在智媒化过程中有了长足进步。据不完全统计,在2021年底西安疫情严重时期,西安报业传媒集团全平台发布稿件达3.4万篇(条),总阅读量逾29.42亿次。全媒体矩阵平台“西安发布”“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和“西安新闻网”充分发挥集群性优势,全面覆盖“报网微端屏”多渠道全流程,及时有效地向大众传达了政府声音、反映了疫情期间民意诉求、准确传递了专家见解,倾力将真实及时的抗疫信息传递给大众。
六、风险传播中媒体社会属性表现反思
面对新冠肺炎这场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各类媒体应守土有责,坚守阵地,传递好有效、准确的信息。但是,在这场危机的报道中也呈现出以下几点不平衡性,如何发挥好媒体的社会舆论引导作用,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首先,央媒或全国性媒体与地方媒体之间不平衡。央媒或全国性媒体从切入报道开始就体现着报道的“直面危机”“直面问题”视角,更容易赢得受众认可。地方媒体的地域管辖属性使得它的报道更符合属地要求,舆论引导为主,正面报道较多,但是在突发问题面前部分地方媒体存在反应速度不够快、直面力度不够强等问题,容易引发受众负面情绪。
其次,地方媒体生产力和传播力不平衡。近年来,我国媒体生态发生了变化,媒体布局也在调整,少数地方媒体脱颖而出,媒体影响力呈现出不平衡等情况。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上,“澎湃新闻”“红星新闻”“界面新闻”“上游新闻”等媒体在“跨地域采访”“异地监督”方面呈现出诸多优势;部分本地媒体则相形见拙:正面报道切入角度困难、深入程度不够,受属地管理和舆情口径制约,“问题报道”和“监督报道”难以施展。此外,在疫情暴发初期,信息披露不畅和问题处理不当等现象较多,使得本地媒体在引导舆论方面稍显被动。
最后,地方媒体之间因属地利益而忽视公众利益造成不平衡。在激烈的媒体报道竞争中,部分地方媒体舆论导向存在“局限化”“狭隘化”“话语部门化”“地域化”等倾向,个别媒体“画地为牢”,为了属地利益设置出现“互怼”,忽视了媒体为公众利益发声的立场。
新闻媒体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媒体在风险传播活动中,要谨防信息传播的不真实、不准确、不客观、不及时、不全面和情绪化。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和地方媒体报道的分析情况来看,部分地方新闻媒体机构受个人专业素养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受众感受,或多或少发布了未经证实的信息,对专业医疗知识也似懂非懂,由此引发了一些争议。此外,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3月15日,与疫情相关的新闻、微博和微信文章共180余万篇(条),说明海量碎片化传播环境促使新闻传播整体提速,但新闻信息的茧房效应与过载效果也同时产生。疫情发生一年后,《中国日报》发文呼吁,“发挥社交媒体积极作用,为全民疫情防控助力”(2021年1月27日),标志着社会对自媒体在防疫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清醒意识。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报道与一般新闻事件传播不同,在这种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新闻媒体作为风险与危机的预警者,其专业传播活动对熨帖大众心灵、安抚大众情绪非常重要,故而信息内容应更加全面、及时、严谨、专业。
总而言之,新冠肺炎风险传播中公共 (机构)媒介在疫情报道的公共话语权弱化或缺失,根本源于当下社会话语结构对风险的“塑形”。原因至少有:1.疫情来势凶猛,应对与真相滞后;2.新传播场域助推;3.风险被放大;4.沟通管道不畅;5.制度建构障碍与污名化;6.视点分散与信任隔膜;7.个体情绪化与极化。
七、风险传播的思考结果与治理建议
面对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风险传播活动,媒体的影响力、公信力备受考验与拷问。一方面,风险传播视野中的新闻舆论活动,媒体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在保障执行新闻传播权利、新闻职业行为与遵行新闻法规、新闻伦理道德关系,新技术新传播环境下处理好主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自媒体关系方面,还有很多探索空间[4]。另一方面,要建立政府、管理机构、专业部门、受众之间的互信场景,建构科学高效的风险传播沟通机制,提升媒体公信力,促进媒体在引导舆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