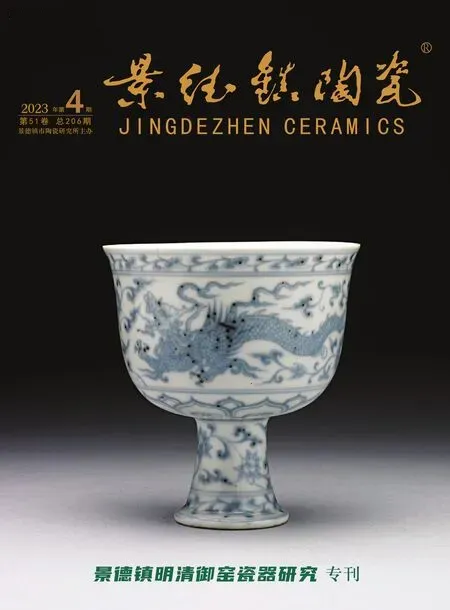明代宫廷对中、西亚的瓷器馈赠
——以陆路外交为中心的考察
2024-01-16陈洁
陈 洁
明代瓷器的对外输出一直是学界热点,但对于经由宫廷外交等特殊方式流通至海外的瓷器,却一直未见系统性研究。就器物而言,这类瓷器通常是输出海外瓷器中等级最高、质量最好的品类,其“外交礼物”属性也使相关讨论能够触及器物背后的宫廷外交史。可惜的是,囿于材料,以往的研究在时间上局限于永乐、宣德时期,在路径上集中于郑和下西洋的海路航线,对明代陆路交往中的材料关注不足[1]。事实上,明代陆路外交的范围、规模、延续时间及重要性皆不容小觑。本文于传统史籍之外,挖掘《回回馆译语》、《高昌馆课》等稀见史料,结合伊斯兰史书及中西亚出土、留存、仿制实物与图像材料,尝试还原明代宫廷在陆路对外交往中的瓷器馈赠,拓展以往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明代宫廷的外交及其变迁。
一、洪武时期明朝与中亚的陆路交往及贡赐往来
明朝建立之初,太祖便“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推翻蒙元政权而立的朱明王朝为了彰显正统,特别强调“夷夏之辨”“内外之限”,这一观念反映在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外交实践上,即成为倡导以“华夏”“大明”为中心,重建符合传统礼法“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朝贡体系的思想基础[2]。故明朝自建立伊始,就力图将元朝的对外关系与贸易网络纳入以大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中,重建亚洲区域内的华夷秩序。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来自中亚内陆区域的回应寥寥。直到明朝军队取得一系列对蒙元残余势力的胜利后,在中亚崛起的帖木儿王朝开始意识到与明交往的必要,于洪武二十年(1387)起遣使通贡,明代史书中以其国都撒马儿罕称之。洪武二十四年,别失八里(东察合台汗国)亦遣使赴明,遂开启明朝与帖木儿、东察合台汗国等中亚国家的正式交往。
当时的帖木儿正在中、西亚不断征战扩张,出于战略及刺探虚实等需要,向明朝遣使纳贡。其所贡献者多为马匹,如洪武二十年15 匹、二十一年300 匹、二十二年205 匹,二十五年84 匹加上驼六只、绒六匹、青梭幅九匹、红绿撒哈剌二匹及镔铁刀剑盔甲等物,最多的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献马1095 匹。而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明廷在这些年份给予的相应回赐分别为白金18 锭、白金每人60 两及钞有差、白金400 两及文绮钞锭(从者白金700 两文绮钞锭有差)、白金文绮有差、钞25190 锭[3]。从《实录》记载看,洪武朝廷给予中亚的回赠以钞币及丝织品为主,太祖虽然认为贡赐往来“薄来厚往可也”,但实际给赐品种、数量都不算丰富,颇为务实[4]。从行使往来的情况看,双方交往并不顺畅。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祖派出的宽彻使团为别失八里扣留,仅放回副使。洪武二十八年,太祖派遣的傅安使团又遭帖木儿扣留,洪武三十年帖木儿又扣押了北平按察使陈德文率领的使团。雄心勃勃的帖木儿其实并不甘居于明朝之下,洪武朝对西域的外交策略亦相对保守,双方交往有限。
作为对《明实录》记载的补充,伊斯兰史书中亦有涉及帖木儿与明交往的部分。歇里甫丁•阿里•雅兹迪的《帖木儿武功记》是记述帖木儿(1336 ~1405)生平事迹及征战武功的史书。书中记录了1396 年帖木儿在锡尔河畔乞那斯镇过冬时,明朝皇帝(Tangouz Can,emperor of Catai)派遣使团,携带珍奇礼物到达的情况[5],从时间判断,这应该是洪武二十八年派出的傅安使团。可惜书中并未记录具体的礼物清单。但书中记载了不少帖木儿时期的贵重礼品及宴饮器用,如帖木儿长子与花剌子模尤西夫•苏菲家族联姻时的礼品:“金币、红宝石、麝香、琥珀、天鹅绒、金银织锦、中国锦缎(China Satin),以及其它珍奇物品,镶嵌宝石的金器,以中国金制成(vessels of the gold of Catai,adorn’d with precious stones)、女奴、以及最好的马匹”[6],在伏尔加河畔举办宴会时“各种肉食及酒类盛放在宝石镶嵌的金质器皿中,由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亲手奉上”[7],另一场宴会中“大帐中喷洒了芬芳的蔷薇水,接着放置餐桌,各种肉类盛放在金盘中”[8],又或“餐盘放好之后,持杯的侍者上前,手里拿着水晶的酒瓶以及金杯”[9]。这些礼品及器用显示,帖木儿时代输入当地的中国贵重物品以丝织品及金银为主,与《明实录》的记载相吻合,而帖木儿宫廷宴会中的器皿也以金银器为主。在双方的文献中,目前都未见洪武时期帖木儿宫廷接受中国瓷器的明确记录。
另一项重要的观察记录来自15 世纪初西班牙卡斯蒂利亚使节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出使帖木儿帝国后撰写的《克拉维约东使记》,游记保存了对帖木儿帝国及宫廷的详细观察。使团于1403 年5 月出发,经君士坦丁堡、白玉路、小亚细亚特拉布宗,德黑兰、苏丹尼叶等地,于1404 年到达撒马尔罕,作者本人屡次谒见帖木儿,书中多处叙及帖木儿及其宫廷生活,按照中文译者杨兆钧的说法,其描绘“不厌繁琐,务求详尽,即其己身之种种遭遇,亦据实而录”[10],因此史料价值颇高。
在游记中,使团行至帖木儿的出生地开石(渴石)城时,参观了当地行宫,注意到宫殿及庑廊“以金色及蓝色的釉砖铺镶装饰(ornamented with gold and blue patterns on glazed tiles)”[11]。此时尚处永乐元年,洪武末明朝使团遭扣留双方断交后,永乐使团尚未到达。这里描绘的金色及蓝色釉砖,在洪武朝未见生产,应该是中、西亚一带较为普遍的锡釉陶砖。关于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克拉维约也有详细的记载 :“自俄罗斯及鞑靼境内运来之货物,为皮货及亚麻。自中国境运来世界上最华美的丝织品(尤其是锦缎)、麝香(只在中国出产)、红宝及钻石、珍珠、大黄和其它货品。”[12]这里提到的中国奢侈品是丝织品、麝香、珠宝及大黄,没有论及瓷器,与前述《帖木儿武功记》的记载互相印证,显示此时输入帖木儿的中国奢侈品面貌。
最重要的线索是《克拉维约东使记》中记载的多次帖木儿宫廷宴会。这些大约于1404年举办的宴会极为盛大。使团第一次受到帖木儿亲自接见时,克拉维约观察到了瓷盘的使用,“内侍将肉切成小块,放在金、银、陶器、玻璃及瓷盘中,瓷盘是非常稀少和珍贵的”[13]。在其余宴会中,所用器皿多为金银器,帖木儿赏赐的糖饯白果、杏仁及葡萄等“分别盛在有托银盘内”[14],使团数次应邀进入帖木儿大汗帐及诸位妻妾处所,大夫人举办宴会时,“帐幕之中央,置有巨柜,其上放置酒盏及盘碟之属”,而其“所有饮盏,皆贮此柜内,饮盏系纯金所制,外镶珠宝,或上嵌绿色翡翠”[15]。带着对于东方事物的好奇,克拉维约对帖木儿宫殿、服饰、器用的描绘皆详尽而细致。结合前述《帖木儿武功记》,我们可以知晓帖木儿的宫廷器用以金银为主,釉陶、瓷器的使用尚不普遍,唯一一次提及瓷器的场合,克拉维约强调“瓷盘是非常稀少和珍贵的”,可见其在当时罕见稀有。这些瓷盘应当是来自中国的瓷器,但从当地盛行的仿制品看,很可能是元青花瓷器。克拉维约曾提及当日帖木儿“为充实撒马儿罕城,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完整、最重要之名都起见,不惜用种种手段,招致商人,来此贸易。并于所征服各城市中,选拔最良善、最有才干以及有巧艺之工匠,送来此间。他在大马士革时,即将该处之珠宝商、丝织工匠、弓矢匠、战车制造家、以及制作琉璃及瓷器的陶工,一律送至此城”。[16]彼时当地有不少模仿中国青花的白釉蓝彩陶器,而其模仿对象,最多见的就是元代青花瓷器[17](图1),以及稍后的永宣官窑青花,可以证实元青花及永宣官窑在帖木儿帝国的流通,但目前尚未见对洪武官窑青花或釉里红的模仿。

图1 撒马儿罕出土白釉蓝彩仿元青花残片撒马儿罕国立历史博物馆
克拉维约使团在撒马儿罕时,还曾经遇见明朝使臣,使臣称帖木儿七年未纳贡,先前因大明国内“兄弟之间,举兵相争,大太子最后兵败,并就大帐中举火自焚”[18]而无暇顾及,但新天子即位后即遣使前来。这应该就是朱棣得位后于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遣使赍诏谕哈烈、撒马儿罕等处,并赐其酋长金织文绮”[19]的使团。克拉维约对中国使团在帖木儿宫廷的情形也有详细描述,但未提赍赠瓷器的情况。
事实上,在十五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的帖木儿细密画中,常见蓝白相间的陶瓷器与金银器组合使用,可见其受宫廷喜爱的程度,下文还将详细论述。但笔者未在十四世纪晚期至十五世纪最初几年的帖木儿画作中,看到中国瓷器的痕迹。这也许与这一时段的画作稀少有关,但综合前述文献记载,以及中亚一带的考古出土及仿制青花情况,我们只能肯定当时有元青花瓷器的输入及使用,目前尚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洪武官窑瓷器的输入。
二、永宣时期明朝与中、西亚的陆路交往与瓷器馈赠
克拉维约使团在撒马儿罕时,帖木儿已取得对北边金帐汗国、西边奥斯曼帝国和东南面德里苏丹国战争的节节胜利,野心膨胀,意欲恢复成吉思汗帝国的疆土,对于明朝“昔日帖木儿对中国称臣纳贡,现在则拒绝之矣”[20]。帖木儿遂于当年集结大军,意欲东征明朝,但随着帖木儿1405 年2 月死于东征途中,笼罩在当时两个东方最强大国家间的战争阴影消散了。
帖木儿死后,帝国分崩离析,继任的帖木儿之孙哈里于永乐五年(1407)遣人送回被扣留长达十三年之久的傅安、郭骥以及陈德文使团,以示与明朝和睦相处的愿望[21]。1409年,帖木儿幼子沙哈鲁夺取王位,将都城迁往赫拉特,明朝称其为哈烈,撒马尔罕后由沙哈鲁之子兀鲁伯管理,皆愿与明修好。
这一情形正与明成祖“锐意通四夷”的积极外交策略相呼应,永乐六年成祖即遣傅安护送撒马儿罕使臣回国,同时出使哈烈。此后,永乐帝一改洪武时期相对保守的对外政策,积极发展同西域诸国的关系,不断向西域派遣使臣,使团奔波于赍诏赏赐西域诸国及引领西域使团入明朝贡的路途中。在二十二年间派往西域的使团30 余次,将众多的西域国家、地区纳入大明的朝贡体系之中,其中尤以陈诚、李达四出西域最为著名。在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等地的带动下,永乐时期向明朝贡的西域国家和地区达到十八个,总计朝贡次数将近一百三十次,开启了明代陆路交往的黄金时期[22]。
就外交往来中的赏赐品而言,太祖虽强调贡赐往来“薄来厚往可也”,但在给赐时颇为务实,品种、数量等皆相对节俭。而得位不正的永乐帝更需要“万国来朝”的盛景以强化其正统性,对西域诸国的赏赐格外丰厚大方。在给予西域的赏赐品中,瓷器也明确成为其组成部分。
永乐十七年,以失剌思、亦思弗罕等处使臣辞还,遣中官鲁安叶先等送之,并赍勑往劳失剌思王亦不剌金,赐之绒锦金织文绮纱罗玉系腰磁器等物,凡安所经亦思弗罕等处其头目各有赐,及行亦思弗罕使臣马哈木等奏愿留居京师,从之,赐赍有加。[23]
从来贡国家看,此时陆路交往已达中东伊朗境内的设拉子(失剌思)、伊斯法罕(亦思弗罕)等处[24],而官方的瓷器赏赐亦通过陆上交通线路向西输送。
永乐二十二年,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一往拖西撒马儿罕失剌思等处买马等项及哈密取马者,悉皆停止,将去给赐段疋磁器等件就于所在官司入库。[25]
永乐帝驾崩后,新帝登基,按照惯例取消“不急之务”,特别提及将“给赐段疋磁器等件”收入库,可见这一时期瓷器在赍赐品中的分量不小。
明朝史书之外,伊斯兰文献中有更直接的记载。帖木儿帝国史臣阿卜答儿•剌扎黑•撒马儿罕地(1413-1438)在《两颗福星之升起及两海汇聚之地》中写道:
“回历八百二十年三月,中国大明汗复遣使至哈烈,其使为李,陈,等四大臣,马君三百人,赍赐品甚多,有鹰隼、文绮、红绫、磁瓶等物,并有御赐诸王子公主等件。携敕一道,中述两国旧好,冀望两朝亲善关系,永远不绝”。[26]
回历820 年3 月为公元1417 即永乐十五年,在《明实录》中,可以找到与之对应永乐十四年六月的遣使记载:
哈烈、撒马儿罕、失剌思、俺都淮等朝贡赐臣辞还,俺都淮等朝贡赐臣辞归,赐之钞币,命礼部谕所过州郡宴饯之,仍遣中官鲁安、郎中陈诚等赍敕偕行,赐哈烈王沙哈鲁等,及撒马儿罕头目兀鲁伯等,失剌思头目亦不剌金,俺都淮头目赛赤答,阿哈麻答罕等白金、纻丝、纱罗、绢布等物有差,并赐所经俺的干及亦思弗罕等处头目文绮。[27]
两相对照,这正是李达、陈诚在永乐间第二次出使西域的情形。《实录》仅记钞币文绮等物,但帖木儿的史书明确的永乐青花小碗残件(图3),而撒马儿罕博物馆的库房里,还有当地发掘出土的瓷片,其中可辨识出数片永宣青花残片(图4)。2017 年在布哈拉的考古发掘中,也出土了永宣青花的残片(图5)[29]。布哈拉即为明代史书中的卜花儿,陈诚使团曾经到过此次,在《西域番国志》中有记载。撒马儿罕和布哈拉出土的瓷片,见证了当日官窑瓷器由使臣经陆路赍赐的情形。

图3 撒马儿罕出土永宣青花碗残片撒马儿罕博物馆,展出于Amir Timur 博物馆

图4 撒马儿罕出土永宣青花残片撒马儿罕博物馆

图5 布哈拉出土永宣青花残片
直接考古证据之外,当地出土的本地陶瓷也进一步验证记载有“磁瓶”,印证官窑瓷器在永乐年间由陆路到达中西亚的频次显然高于《实录》记载。
与文献材料相呼应,在中亚一带的出土品中,也保存了珍贵的考古实物。首先是在撒马儿罕区域,阎焰先生发表了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萨布兹博物馆展出的明代永乐青花天球瓶残片(图2),此瓶出土于塔什干以南150 公里吉扎克附近靠近撒马儿罕的区域[28]。近年来,Valentina Bruccoleri 对中亚陆路留存官窑青花进行调查,有更重要的发现,Amir Timur 博物馆展出了撒马儿罕出土了永宣官窑在中亚的流布。沙赫里萨布兹博物馆展出了一件白釉蓝彩花果纹碗,其外壁饰缠枝,碗心绘石榴果实,器型纹样皆与永乐花果纹碗接近(图6)。约翰•卡斯维尔发表的撒马儿罕出土青花花卉纹盘(图7),板沿、弧腹,其盘沿花卉、盘壁折枝及盘心花纹,明显带有永乐青花的痕迹,同书中另一件花鸟纹盘则可见永乐花鸟纹大盘的影响(图8)。[30]

图6 沙赫里萨布兹出土中亚仿永宣青花碗沙赫里萨布兹博物馆

图7 撒马儿罕出土中亚仿永乐青花盘

图8 撒马儿罕出土中亚仿永乐青花盘
如前所述,《克拉维约东使记》中已记载当日帖木儿为充实撒马儿罕城,将大马士革等地制作的琉璃及瓷器的陶工,送至此城。《明史•哈烈传》中亦记载当地“田美多获,宜桑与蚕,纨绮细密,磁器精巧”[31]。可见撒马儿罕和哈烈所在的赫拉特都有陶瓷生产,前述当地出土的器物应该就是本地所产。这些器物对中国官窑青花的模仿,间接验证了当日类似瓷器曾由明朝使臣赍赐至此地。
帖木儿时期的细密画也同样说明问题。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波斯诗歌选集插图中的青花玉壶春瓶与酒盏同明初官窑式样极为类似(图9)。塞克勒藏《帖木儿庆祝征服德里》中的青花瓶也正是同款(图10)。两幅画中的瓷瓶似乎可以印证前述《两颗福星之升起》中提及的赏赐品“磁瓶”。克利夫兰《胡尚故事》中同样器型的瓶则很可能是赫拉特一带生产的白釉蓝彩陶器(图11),《庭院皇家宴会》所绘者亦以本地陶瓷居多(图12、13)。细密画中大量出现的青花陶瓷器是当时上层器用风尚的生动写照,显示十五世纪前半的帖木儿宫廷贵族已经养成了使用陶瓷器的习惯,间接显示当时的赍赐数量与风尚。

图9 波斯诗歌选集 十五世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图10 帖木儿庆祝征服德里设拉子,1436美国哈佛大学塞克勒博物馆

图11 胡尚的故事, Majma al-tavarikh of Hafiz-i Abru赫拉特 ,1425–50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

图12 庭院皇家宴会,Shahnama of Firdausi设拉子,1444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

图13 庭院皇家宴会,Shahnama of Firdausi设拉子,1444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
在现藏托普卡比宫的《行旅图》中(图14),可以看到十五世纪在中亚陆路沙漠山谷间车载移动的金银制品和青花瓷器。从图中各色人等的服装、佩饰以及面貌长相观察,可以判定其中多人来自中国,不排除即为当日之中国使团。倘若如此,画面展现的很可能正是中国使团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将明廷赏赐的高级瓷器和金银制品携至中西亚的场景。不排除在如今中东的藏品中,也存在部分经由陆路自中亚抵达至此的器物。

图14 行旅图托普卡比宫图书馆 H.2153,fols.130r
中国与伊斯兰文献、考古出土品、当地仿制品及图像材料都揭示出永宣时期明廷与中、西亚交往中的官窑瓷器赍赐盛况,与洪武朝有云泥之别。值得注意的是,撒马儿罕出土天球瓶的残片,其器型并非中国本土传统,很可能是模仿伊斯兰玻璃或金属器,在伊朗阿德比尔寺、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均有收藏,透露出此类器物系专为伊斯兰地区生产的讯息。更说明问题的是,传世品中所有天球瓶、扁瓶,一旦出现象征皇权的龙纹,则皆为三爪,无一例为五爪(图15-23)。对比永宣时期明代宫廷自用器上龙纹皆为五爪,而赏赐朝鲜大罐所绘龙纹为三爪的现象,我们可以判断,这类器物原本并非宫廷自用器皿,应当是专为赏赐伊斯兰地区而烧制的。这种充分考虑、照顾对方需求的做法,与明成祖积极的对外政策以及对外邦的特殊重视相呼应。永乐帝通过“万邦来朝”强化自身正统性的愿望强烈,故赏赐手笔极大,充分照顾不同需求,以笼络外邦,吸引各国来朝,彰显上国地位,其“大度雄风,为之敷被,太祖始未及矣。”而使用三爪龙纹,则是明廷“天下秩序”及等级观念的反映,五爪龙纹是“天子”身份的象征,赏用瓷器使用三爪龙纹,是对双方地位和等级的强化,瓷器纹饰亦成为强化身份与秩序的道具。

图15 景德镇青花龙纹扁瓶故宫博物院

图16 景德镇青花龙纹扁瓶故宫博物院

图17 景德镇青花龙纹扁瓶故宫博物院

图18 景德镇青花龙纹扁瓶土耳其托普卡比宫

图20 景德镇青花龙纹天球瓶伊朗阿德比尔寺

图21 景德镇青花龙纹天球瓶伊朗阿德比尔寺

图22 景德镇青花龙纹扁瓶天津博物馆

图23 景德镇青花龙纹扁瓶英国大维德基金会
三、明中后期的对外交往及文献所见对中、西亚瓷器赏赐
永乐、宣德时期是明代对外交往的最高峰,永宣以后,明朝国力渐显颓势,对于朝贡的巨大支出变得敏感。正统开始,明朝逐渐陷入内外交困的艰难时世,对外西北边疆不稳,正统十四年更发生“土木堡之变”,对内财政入不敷出,已无财力与热情支持频繁的大规模朝贡,遂于海路停罢下西洋计划,对外不再积极开拓。同时,朝廷对前来朝贡国家的招待、赏赐也都开始节制,不复永乐朝之阔绰优渥。
与此同时,海禁也逐渐松弛,15 世纪末开始,欧洲殖民者航向东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相继以武力占据了南亚、东南亚的重要港市,区域政治经济秩序受到巨大挑战。在上述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朝贡体制在明代中后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有鉴于此,学界对于明代中后期对外关系的研究,重心皆转向海外贸易、中西交涉等层面。
然而明代中后期的朝贡体系虽然急剧衰弱,但并未消亡,其范围缩小、规模萎缩,但依然维系。明廷在典型朝贡圈,如朝鲜、琉球、暹罗、安南、占城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朝贡往来。陆路对外交往亦维持着相当规模,包括撒马儿罕、哈密、吐鲁番、鲁迷、天方、捨刺思等。尽管所谓“亚洲内陆圈”并非典型朝贡国,与明廷亦非封贡宗藩关系,其中也可能包含商贾充任的伪使,但相较于海路外交在非典型朝贡圈的急剧萎缩,明代中后期陆路对外交往的重要性甚至还略有上升。下表依据《明史•外国传》对中后期的朝贡作初步统计,其统计不如《实录》详尽,但也基本反映了中后期朝贡外交往来的基本面貌(表一)。

表一 明中后期主要朝贡国一览表[32]
据上表可一窥明代中后期,明廷在海路、陆路的外交往来。这一时期的朝贡及外交已经不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较为寥落,对于此时对外交往中的瓷器,学界的研究更是几乎空白。但《明史》及《明实录》的记载已经透露出一些线索:
《明实录》载成化二十年:
赐火失阿儿等处羽奴思王虎斑绢、磁器,从其使臣请也。[33]
《明史》日落国条:
弘治元年,其王亦思罕答儿鲁密帖里牙复贡,使臣奏求纻丝、夏布、磁器、诏皆予之。[34]
此次赏赐在《实录》中有更详细的记录,弘治元年五月辛巳:
赐迤西地面锁鲁檀马哈木阿民斡子伯王,琵琶、银壶、金碗各一事,迤西阿黑麻曲儿干王、迤西日落国亦思刊荅儿、鲁密帖里牙王,纻丝、磁器、夏布等物从其请也。[35]
日落国的地望并不清晰,明史只记其永乐中来贡,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其与罗马教廷有关[36],至今未有公认的结论,但从迤西地面、迤西日落国的方位看,是西亚或以西的国度。虽然地望不明,但无疑都经陆路往来。
《明史》失剌思条:
嘉靖三年与旁近三十二部并遣使贡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襕、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却,量予之。[37]
此条同样见于嘉靖三年《实录》:
舍刺思等番使满刺捏只必丁等三十二种进贡马匹、方物,各奏讨蟒衣、膝襕、磁器、布帛等物,诏量与之。[38]
失刺思即设拉子,永宣时期在帖木儿治下与明廷往来密切,正统、成化、弘治、嘉靖间皆有遣使往来记录,此处特别提到其与旁近三十二部一起奏讨瓷器等物,明廷此次瓷器馈赠的范围应该不小。
《明史》与《明实录》中的记载仅此寥寥数语,但透露出重要讯息,即明中后期,瓷器仍然在宫廷外交中持续输出,且多缘自经陆路前来的使臣求讨。在基本史料的基础上,笔者透过挖掘研究者较少注意到的《回回馆译语》《高昌馆课》来文,发现了更为重要的线索。
为了处理对外交往中的语言和翻译问题,明代在元代基础上设立四夷馆,回回馆是其中负责处理、翻译回回文书的机构。为了培养翻译,四夷馆还负责编写各自语言与汉语对照的词汇表,即“杂字”,将所管地区、国家上呈大明皇帝的奏折写成汉文再附上民族语言译文,称为“来文”,两者合称“译语”。回回馆编有《回回馆译语》,其中有来文的版本主要保存在海外,日本东洋文库本存来文30 篇,去除重复后实有21 篇,柏林国家图书馆本存来文16 篇,内阁文库本存来文17 篇,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本存来文17 篇,以上各版本去除重复后大约共有24 篇左右来文存世[39]。《来文》中保留了各国讨要瓷器的材料:
天方国使臣塔主丁大明皇帝前进贡五有(玉石)一百五十斤,西马十匹,望乞收受。求讨罗段茶叶磁碗磁盘,望乞恩赐奏得圣旨道。[40]
撒马儿罕地面奴婢塔主丁皇帝前奏今照旧例赴金门下共进,贡玉石五十斤小刀五百把望乞收受朝廷前求讨织金段子磁碗磁盘等物,望乞恩赐奏得圣旨知道[41]
大明皇帝前,速坛阿黑麻王奏,我情愿与朝廷出气力,今奏讨金甲,金盔,金鞘刀,撒袋,箭描,金弓,各样颜色妆的车,各样颜色妆的磁瓶,琵琶,筝,笛,等件。今差使臣火只马黑麻副()阿力等,进贡阿鲁骨马二匹,鞑靼马二匹,骟马三匹,去了怎生恩赐,奏得圣旨知道[42]。
这些记录显示天方国、撒马儿罕等地曾向明廷讨要瓷器,从所贡物品仅有少量马匹及玉石等情况看,这显然是明代中后期的情形。对于讨要,往往是“天子不能却”而“量予之”的。天方国、撒马儿罕及速坛阿黑麻王讨要瓷器的情况,显然补充了《实录》及《明史》缺失,展现了明代中后期对外瓷器赏赐的更多细节。
对于《回回馆译语》来文作为史料的可靠程度,有学者曾因其波斯文法生硬而有所怀疑,然而已有学者指出这些来文不同于官方使臣携带的正式表文,它是使臣向明廷乞讨赏赐的请愿书,根据四夷馆考察自“番文底本内揭出一段”要求官生学习译写的要求,这些来文应自底本中揭出,并非捏造,仍具史料价值[43]。更说明问题的是,教习畏兀儿文,负责翻译吐鲁番、哈密等地包括黑娄(即帖木儿赫拉特)往来文书的《高昌馆课》来文也有众多求讨要瓷器记录,反映了同样的情形[44]:
第三篇:哈密地面差来使臣,都督佥事力伯颜答,仰望天皇帝洪福,奴婢每来京进贡,求讨回去,乞赐织金缎子二匹,青二匹,素二匹,磁碗、磁碟,乞赐与的,奏得圣旨知道。
第九篇:火州地面差来使臣罕完前来到京进贡,事完求讨赏赐回去。望赐与织金缎子、素青缎子,并磁碟等件,奏得圣旨知道。
第十一篇:哈密地面进贡使臣法虎儿丁,大明皇帝前叩头奏,奴婢每多受恩赐,今回本土,望赐与衣服表里、金绣胸背缎子,并磁壶等件,今乞赐与的,奏得圣旨知道。
第十五篇:速坛阿黑麻王差来使臣哈只马哈麻等奏,朝贡到京,求讨赏赐,乞赐银壶、金碗,及磁碗碟等件的缘故,怎生恩赐,奏得圣旨知道。
第十八篇:速坛阿黑麻王差来朝贡使臣火只法虎儿丁迭儿必失,求讨回还本土给赐蟒龙、并磁碗、磁碟等件,赏赐与的,奏得圣旨知道。
第二十篇:哈密地面差来进贡使臣把把格等奏,奴婢来京,求讨回去,仰望朝廷怜悯,赏赐衣服表里金壶、金碗、磁碟等件,怎生恩赐,奏得圣旨知道。
第二十二篇:亦力把力地面差头目拾剌马哈木舍等,朝贡回还,求讨赏赐。仰望朝廷怜悯,给赐胸背缎子,并磁碗、磁碟等件,奏得圣旨知道。
第二十七篇:火州地面差来使臣头目罕完等,奏朝廷,前求讨衣服胸背缎子素青缎子红绢,并磁碗、磁碟,恩赐远人的,奏得圣旨知道。
第四十三篇:阿速地面小奴婢阿把把吉儿叩头奏,我今仰赖天朝洪福,居边方一心遵守礼法,不敢违背。今差火只前去进贡:镔铁腰刀一把、骟马九匹。去了乞讨应用的物件:金瓶金碗、各色花素磁器等物。如蒙恩赐与的,奏得圣旨知道。
第五十二篇:哈密地面差来使臣火只奏,奴婢远居边方,来京朝贡,多受辛苦。望赐与衣服表里、汤瓶、磁器等件,怎生恩赐,奏得圣旨知道。
第五十九篇:曲先地面兀也思王奏,今仰望天皇帝洪福,地方安稳,人民快乐,奴婢每感戴不尽,今备土产方物,专差头目罕完赴金阙下,求讨衣服胸背缎子、素青缎子,并磁碗、磁碟等件,奏得圣旨知道。
《高昌馆课》所录的各函件未注明年、月、日等信息,但函件内容颇可对应史书记载,如《高昌馆课》第四十一函记速坛阿力王进贡事,提及“得了哈密城池印信,照例进贡”,与《明史•西域传》之“(成化)九年春,袭破其城,执王母,夺金印……阿力修贡如故,一岁中使来者三”相互印证。胡振华先生还将不少《高昌馆课》来文与明史印证,证实其史料价值[45]。而从《高昌馆课》来文的回鹘文看,其语法亦完全不符合阿尔泰语系语言SOV 型的语法规则,是由汉文逐字直译为回鹘文的[46],这与《回回馆》译语来文的情况相似。其中原因尚需语言学者研究,但并不影响其史料价值。
如果将《明史》《实录》的记载与前述两馆来文与比对,至少在赏赐器物层面来文与史实亦相当吻合,如:
《明史》失剌思条:
嘉靖三年与旁近三十二部并遣使贡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襕、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却,量予之。
《明史》天方条:
正德十三年,王写亦把剌克遣使贡马、驼、梭幅、珊瑚、宝石、鱼牙刀诸物,诏赐蟒龙金织衣及麝香、金银器。嘉靖四年,其王亦麻都儿等遣使贡马、驼、方物……所进玉石悉粗恶,而使臣所私货皆良。十一年遣使偕土鲁番、撒马儿罕、惟密诸国来贡,称王者至三十七人……天方及土鲁番使臣,其籍余玉石、锉刀诸货,固求准贡物给赏。礼官不得已,以正德间例为请,许之。
《殊域周咨录》天方条:
(嘉靖四年)天方国使臣火者马黑木等十六名赴京进贡……初来投进番文十一道,除进贡方物验收题赏外,又求讨蟒衣、金盔等项”[47]
《明实录》嘉靖二十二年十月:
土鲁蕃、天方国、鲁迷、撒马儿罕等夷奏乞中国币物,量以金段、茶、药、器物给之[48]
上述正史史料显示失剌思、撒马儿罕、天方、吐鲁番等西域国家往往结伴朝贡,贡玉石、刀、马等,求讨蟒衣、膝襕、磁器、布帛、茶、药等。
而回回馆来文:
撒马儿罕使臣哈非子,大明皇帝前进贡西马六匹、小刀一百把,望乞收受,求织金缎子茶叶,望乞恩赐,奏得圣旨知道。
撒马儿罕地面奴婢哈非子,大明皇帝前奏,今奴婢照旧例赴金门下叩头,进贡西马、达马,刚钻等物。望乞收受,朝廷前求讨织金花样段子,酒金笺纸等物。望乞恩赐,奏得圣旨知道[49]。
吐鲁番使臣阿力等,大明皇帝前奏,今奴婢照旧例赴金门下叩头,进贡阿鲁骨马五匹,玉石一百斤,望乞收受,朝廷前求讨织金段子,高丽布,各色绒线,茶叶等物。望乞恩赐,奏得圣旨知道[50]。高昌馆来文:
速坛阿黑麻王差来朝贡使臣火只法虎儿丁迭儿必失,求讨回还本土给赐蟒龙、并磁碗、磁碟等件,赏赐与的,奏得圣旨知道。
哈剌怀地面也先卜花王叩头奏,今仰慕朝廷好名声,特差头目皮儿马哈麻等进贡,珊瑚二枝,玛瑙二块,番红花五十斤,硇砂二十斤,就乞讨大红织金胸背缎子,通袖膝襕缎子,汤瓶,马革占等物,望赐与的,奏得圣旨知道。
来文显示这些国家、地区贡马、玉石、小刀等,求讨蟒龙及各色织金缎、膝襕、瓷器、金银器、布匹等,与明代史书中的记载完全吻合,可以验证来文作为史料的可靠性。极少数传统史书中未出现者,如撒马儿罕讨要的洒金笺纸,在存世帖木儿王朝书籍、细密画中,也可以找到书写于中国笺纸之上者(图24),时间、器物、物品皆相合,进一步证明来文记录不虚。

图24 哈菲兹诗集 帖木儿王朝1451 年 明洒金笺纸大英图书馆
退一步说,即便来文汉语可能有所截取,但其与正史在赏赐器物方面的高度吻合,也证明其显示的“需求”真实无误。《回回馆译语》、《高昌馆来文》中众多求讨瓷器的记录反映了西域国家和地区统治者对高等级瓷器的喜爱和索求。现存《高昌馆来文》89 条,其中涉及讨要瓷器的有11 条,现存《回回馆来文》约24 条,涉及求讨瓷器者3 条,显示出类似的索求频次。事实上,中、西亚伊斯兰地区文化、审美、习俗接近,朝贡往往结队前来,需索大体类似。撒马儿罕、天方、日落国、鲁迷等中亚、中东地区对瓷器的需求和喜好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养成”自永宣时期的慷慨馈赠,对瓷器的偏好在明中后期延续下来,现在中东留存的器物便是当地偏好中国瓷器的明证。
与永乐朝多次主动派遣使臣赴西域赍赐不同,中后期的交往及馈赠不及此前积极主动,多因使臣奏讨给赐。留存至今的来文相对实际数量只能是一鳞半爪,前文《明中后期主要朝贡国一览表》对撒马儿罕、鲁迷、天方、失剌思、日落国往来的统计也只是当时外交往来的一部分。明代中后期,文献中已明确记载有对日落国、失剌思、天方、撒马儿罕的瓷器赏赐,除此之外,根据来文讨要的规律,以及《明会典》中“求讨、请旨量与物件,到京者照名给散,在卫者,请敕开付差来人领去”的规定[51],尚另有一定数量的瓷器透过外交赏赐到达域外,这在以往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四、明中后期与西亚的陆路外交及当地留存官窑瓷器
从实物角度看,海外出土及旧藏的明代中晚期官窑其实也有一定数量,但以往对这一阶段的外交朝贡往来认识不足,因此一直仅从明后期官窑管理不严,器物透过私人贸易流入海外的角度加以认识。
明代中后期,御器厂管理不如早期严格,嘉靖朝官窑烧造更开始采取官搭民烧的方式,确实有部分器物流入市场。1556 年访问广州的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曾经记录“瓷器有极粗的,也有极细的;有的瓷器公开售卖是非法的,因为只许官员使用,那是红色的和绿色的,涂金的及黄色的。这类瓷器仅少量偷偷出售。”[52]克路士访问广州是在嘉靖三十五年,能够见到私下贩售的宫廷专属黄釉瓷器,可见确实有部分官窑瓷器私下贩售,进而透过葡萄牙及沿海私商的贸易网络流通至海外。
然而,前述历史及文献梳理已经显示了当时官窑瓷器透过外交赏赐流通至海外的通路,尤其是经陆路自中亚直至中东的交流路线。透过《明实录》的记载,明代中后期明廷与撒马儿罕、天方、失剌思、鲁迷的往来颇为密切。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故宫博物院新入藏之《丝路山水地图》(图25),以及嘉靖刻本《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图》与《西域土地人物略》,台北故宫藏《西域土地人物图》皆显示明代中后期出嘉峪关经新疆至中亚、中东的路线不容低估,后二图中天方至鲁迷段的描绘更显示与中东一带的交通(图26)。

右图29 景德镇窑正德孔雀蓝釉鱼藻纹青花盘伊朗阿德比尔寺

图25 《丝路山水地图》撒马儿罕段故宫博物院

图26 《西域土地人物图》天方至鲁迷段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27 十六世纪中亚、西亚地理图(部分)采自赵永复《明代<西域土地人物略>部分中亚、西亚地名考释》

左图28 景德镇窑成化白釉盘伊朗阿德比尔寺
结合文献记载与学界对前述地图地名的研究,可以基本明确撒马儿罕即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儿罕;天方《明史》中明载“一名天堂,又曰默伽,……相传回回设教之祖曰马哈麻者,首于此地行教”[53],显然是穆斯林教圣地麦加无疑;失剌思则早在洪武末傅安出使帖木儿被扣留期间,“其主与群下骄倨,欲夸其土地之广,遣人导安西至讨落思,安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剌思,还至黑鲁诸城,计万千余里。凡六年反其国”[54],为伊朗南部之名城设拉子,当然亦不排除可能是帖木儿在中亚萨控赫斯建立的同名之城;而鲁迷“去中国绝远”,出现在《西域土地人物图》中,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即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55]。
天方、鲁迷皆位于今中东地区,而集中显示当地瓷器收藏的伊朗阿德比尔寺及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有不少明代中后期官窑瓷器,包括白釉、黄釉、青花、孔雀蓝釉青花等品种,年代横跨成化至万历,甚至包含部分可能上溯至十五世纪中期的产品[56]。阿德比尔寺的白釉瓷盘底部书“大明成化年制”款(图28),另有五件“大明弘治年制”及一件“大明正德年制”同款瓷盘。正德青花盘内外书写阿拉伯文字,外沿书“大明正德年制”官款(图31),孔雀蓝釉青花则书“正德年制”四字楷书款(图29)。另有成化至万历的青花等官窑器物多件(图32、33)。托普卡比宫的官窑黄釉、白釉盘碗自弘治至嘉靖,官窑青花则包括盘、碗、瓶、罐乃至龙缸等器型(图34-41)。明代后期,礼制松弛,赐服中五爪蟒纹日渐增多,与龙纹难以区分。前述求讨来文中,不乏求讨蟒衣者,对五爪龙纹的禁忌亦不复严格。

图31 景德镇窑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盘伊朗阿德比尔寺

图32 景德镇窑万历青花碗伊朗阿德比尔寺

图33 景德镇窑万历青花龙纹缸伊朗阿德比尔寺

图34 景德镇窑弘治黄釉盘土耳其托普卡比宫

图35 景德镇窑弘治白釉碗土耳其托普卡比宫

图36 景德镇窑正德黄釉碗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图

图37 景德镇窑嘉靖黄釉碗土耳其托普卡比宫

图38 景德镇窑嘉靖青花花卉纹盘土耳其托普卡比宫

39 景德镇窑万历青花花卉纹盘土耳其托普卡比宫

图41 景德镇窑万历青花龙纹缸土耳其托普卡比宫
两地藏品中的明代中后期官窑,尤其是其中早于官搭民烧阶段,御器厂管控尚较严格的成化、弘治、正德朝产品,其流入渠道可能比以往的认识更为多元。笔者不否认其中部分器物可能积存至晚期后经私商流通出海,亦赞同两地明后期官窑中存在经海路转运而来的部分。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鉴于明中后期与中、西亚的交往,以及文献中明确的给赐记录,两地藏品中应当也保存了经由官方外交馈赠流通至此的部分,这是以往为学界忽视的情况。
梳理明代中后期明廷与天方、鲁迷、失剌思等地的往来,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的交往及贡赐物品流通情况(表二)。

表二 明中后期天方、鲁迷、失剌思与明廷往来[57]
据上表所示,鲁迷、天方、设拉子在明中后期同明廷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外交往来,除极少数由海路前来的特例外,他们往往与撒马儿罕、吐鲁番、哈密等共同经陆路前来。尽管明廷已察觉“番使多贾人,来辄挟重赀与中国市”,“西域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各国称王者百五十余,皆非本朝封爵……盖西域贾胡诡立名色,以侥赉予”[58],但并不禁绝。且因通事“皆以色目人为之,往往视彼为亲,视我为疏,在京则教其分外求讨,伴回则令其潜买禁物”,结合前述来文中的瓷器求讨记录,这些来华使臣对瓷器的求讨恐怕不少,上述两大旧藏中源自官方赏赐的部分也许不在少数。
土耳其托普卡比宫藏景泰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谕能进一步充实、补强我们对明廷与西亚外交往来的认识。敕谕由明朝颁给剌儿地面头目咩力儿吉,以汉、蒙两种文字书写:
皇帝敕谕“剌儿地面头目咩力儿吉,尔世居西土,敬顺天道,尊事朝廷,遣人远来朝贡,忠诚可嘉,特赐尔綵币表里……颁赐 纻丝:晴花骨朵云绿一匹、晴细花蓝一匹、暗细花绿一匹、暗细花红一匹、素青一匹、素红二匹、素绿一匹,綵绢:红四匹、蓝四匹”[59]。
发表这份敕谕的哈佛Cleaves 教授指出剌儿地面即今伊朗法尔斯省东南部的拉里斯坦(Capital of the district of Laristan, to the southeast of Fars),但他未能在《明实录》中找到对应记载。笔者查检后认为此即景泰三年十二月一日“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头目脱脱不花,亦力把里地面也先卜花王并妃……等一百二十一处地面头目俱遣使来朝,贡马,赐宴并彩币表里纻丝袭衣等物,仍命来使各赍敕书彩币表里,归赐其王及妃并头目有差”[60]。剌儿地面头目咩力儿吉是“一百二十一处地面头目”之一,此即赏赐中的一份。
《明实录》中的这条记录历来未引起学界注意,其地距离伊朗设拉子不远,与诏敕对应,可知明朝在中期与西亚仍保持着可观的陆路交往规模。诏书保存在托普卡比宫,反映了中东一带高等级物品向奥斯曼宫廷聚集的事实,亦进一步提示其藏品中部分高等级瓷器的来源。当然,这份诏敕也提示我们,不应过高估计当时对外赏赐瓷器的频次与数量,彩币缎匹是对外赏赐的主流与标准配置,中后期的瓷器赏赐可能多来自求讨及特赐,数量与频次应当有限。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是进一步梳理中、西亚的相关藏品及出土品,尤其是关注中亚出土明中晚期官窑及中东藏品上的刻铭与旧藏记号,这些材料蕴含着器物来源及流通的更多信息,相信梳理之后会有更多发现。
在明朝的对外交往中,官窑瓷器是重要的“国礼”之一,由使臣携往各地,成为笼络海外诸国、强化关系及秩序的道具。在输出线路上,我们不应只关注郑和下西洋的海路航线,在明廷与中、西亚的往来中,陆上线路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时间轴线上,我们也要对不同时段的情形有更精确地把控:对洪武朝的输出不应估计过高,不同于以往的模糊推断,目前的材料并不能证实此时明廷已经在与中亚的交往中使用官窑瓷器作为赍赐[61];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相呼应,陆路外交及瓷器馈赠同样呈现出明显的“爆发”态势,中国及伊斯兰文献、考古出土品、当地仿制品及帖木儿细密画共同拼合出这一盛景;对于明代中后期的情形,则不应估计过低,相较于海路外交的急剧萎缩,陆路交往延续了相当规模,而《回回馆译语》、《高昌馆课》等史料更显示这一时段明廷因中、西亚需索而不断持续的瓷器赍赐,因而有必要重新思考部分中东留存明代中后期官窑瓷器的输入途径。
注 释:
[1] 关于陆路交往中的瓷器馈赠,目前仅有少数研究者关注,见阎焰.从”帖木儿”时代出现在撒马儿罕附近的永乐青花看当地的窑事[M] // 明代生活美学论坛文集:中华文物学会四十周年纪念.台北,2019,以及Valentina Bruccoleri.Recent discovery of an early Ming blue-and-white porcelain shard from the citadel of Bukhara [J].Newsletter number 30 May 2022,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2022.而对于明代中晚期的情形,目前似未见正式研究。
[2]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1。
[3] 太祖高皇帝实录[A].卷一百八十五,洪武二十年九月壬辰条;卷一百九十三,洪武二十一年九月丙戌条;卷一百九十七,洪武二十二年九月乙未条;卷二百十七,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壬午条;卷二百四十五,洪武二十九年四月甲寅条。
[4] 关于洪武朝对外赏赐中的瓷器,笔者在博士论文《明清对外赏赐瓷器研究中》已有讨论,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详述,将另文讨论。
[5] Sharaf al-Dīn ʻAlī Yazdī.Translated by John Darby.The History of Timur-Bec: Known by the Name of Tamerlain the Great, Emperor of the Moguls and Tartars: Being an Historical Journal of His Conquests in Asia and Europe[M].1723:541.
[6] 同 前 注,页159,“女 奴”前 另 有magnificent habits,但其意不明。
[7] 同前注,页381。
[8] 同前注,页507。
[9] 同前注,页483。
[10] 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东使记[M].杨兆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
[11] Ruy González de Clavijo,Translated by Clements R.Markham, F.R.G.S.,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our at Samarcand, A.D.1403-6,London,Hakluyt society,p.124-125.
[12] 同前注,页171。
[13] 这一段在中译本中有所省略,但英译本及西班牙语原文中,均有瓷器的记载,西班牙原文称为“porcelanas”,区别于釉陶“barro vidriado”。英文版同前注,页134,西班牙全文检索:https://www.cervantesvirtual.com/obra-visor/viday-hazanas-del-gran-tamorlan-con-la-descripcionde-las-tierras-de-su-imperio-y-senorio--0/html/feed4b6c-82b1-11df-acc7-002185ce6064_2.htm#2。感谢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博士后王琳婷(Valentina Bruccoleri)提示西班牙语本中“porcelanas”与“barro vidriado”的区别。
[14] 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东使记[M].杨兆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37。
[15] 同前注,页148。
[16] 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东使记[M].杨兆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56-157。中文翻译为琉璃及瓷器,西班牙语原文为“y los que labran el vidrio y barro”,是玻璃和釉陶工匠。
[17] Valantina Bruccoleri, Porcelaine et influences chinoises,Splendeurs des oasis d'Ouzbékistan Sur les routes caravanières d’Asie centrale [M].2022:290.
[18] 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东使记[M].杨兆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58。
[19] 太宗文皇帝实录[A].卷十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条。
[20] 同前注,页127。
[21] 张连杰.试论明前期与中亚西亚诸国的交往[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
[22] 袁小湉.明代中后期宫廷涉外交往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
[23] 太宗文皇帝实录[A].卷二百十二,永乐十七年五月己巳条。
[24] 设拉子、伊斯法罕皆为伊朗境内的名城,傅安遭扣留期间,帖木儿曾安排傅安远赴大不里士、伊斯法罕、设拉子等地观览,以夸耀疆域之广。从稍后的《丝路山水图》、《西域土地人物图》等地理舆图上的标注看,明廷对这些地点都有清晰认识,因此《明史》中所指很可能即此。但与此同时,帖木儿为彰显帝国实力,也以历史名城之名在中亚建城,撒马儿罕西边萨拉赫斯亦有失剌思城,不排除这里的失剌思也可能指中亚的设拉子。
[25] 仁宗昭皇帝实录[A].卷一上,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己巳条。
[26] 邵循正.有关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M]//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7] 太宗文皇帝实录[A].卷一百七十七,永乐十四年六月己卯条。
[28] 阎焰.从”帖木儿”时代出现在撒马儿罕附近的永乐青花看当地的窑事[M]//明代生活美学论坛文集:中华文物学会四十周年纪念.台北:中华文物学会,2019。
[29] Valentina Bruccoleri.Recent discovery of an early Ming blue-and-white porcelain shard from the citadel of Bukhara [J].Newsletter No.30, May 2022,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2022; Valentina Bruccoleri.From Jingdezhen to Samarkand: Early Ming Porcelain in Timurid Cnetral Asia[J].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Vol.86,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2022.
[30] John Carswell.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nd its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 [M].British Museum Press, 2007.
[31]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20。
[32] 本表依据《明史•外国传》统计,《明实录》的记载较此详尽,但相关数据已能反映明中后期朝贡基本面貌。后文将根据《实录》详细统计重要国家.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明廷最忠实的藩属国,朝鲜逢圣节(皇帝生日)、正旦、冬至、千秋(太子生日)及因请封、庆慰、谢恩等事由频繁入贡,因往来繁多,故《明史》中并未加以详细记录,表格中未加反映。
[33] 宪宗纯皇帝实录[A].卷二百五十一,成化二十年四月赐火条。
[34] 张廷玉.明史[M].卷三百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20。
[35] 孝宗敬皇帝实录[A].卷十四,弘治元年五月赐迤条.
[36] 廖大珂.日落国”考证——兼论明代中国与罗马教廷的交往[J].厦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110-116。
[37] 张廷玉.明史[M].卷三百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20。
[38] 世宗肃皇帝实录[A].卷三十六,嘉靖三年二月戊申条。
[39] 胡振华.珍贵的回族文献:《回回馆译语》[J],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5(2):87-91。
[40] 胡振华,胡军.回回馆译语[M].中央民族大学东干学研究所,2005:241。
[41] 胡振华,胡军.回回馆译语[M].中央民族大学东干学研究所,2005:245-246。
[42] Graeme Ford.The Persian College Exemplary Letters in the Late Ming ‘Huayiyiyu’ Dictionary [M] // Persian translating at the Ming court,Macquarie University,2022.
[43] 张文德.明与中亚帖木儿王朝往来的语言问题[J].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十八辑),上海古籍,2006。
[44] 胡振华 黄润华.明代文献高昌馆课(拉丁字母转写本)[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45] 胡振华 黄润华.明代高昌馆来文及其历史价值[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1):47-52。
[46] 景治强,刘林.明代回鹘文文献《高昌馆课》的语言研究[J].现代语言学,2022,10(5):932-941。
[47]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M].卷十二:拂菻•天方国条.北京:中华书局,2009。
[48] 世宗肃皇帝实录[A].卷二百七十九,嘉靖二十二年十月朝鲜条。
[49] Graeme Ford.The Persian College Exemplary Letters in the Late Ming ‘Huayiyiyu’ Dictionary [M] // Persian translating at the Ming court,Macquarie University,2022.
[50] 同前注。
[51] 大明会典[A].卷一百一十一。
[52] 伯来拉•克路.南明行纪[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152。
[53] 张廷玉.明史[M].卷三百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20。
[5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上中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5] 赵永复.明代《西域土地人物略》部分中亚、西亚地名考释[J],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 周运中.明代《丝路山水地图》的新发现[J].;李之勤.《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01)。
[56] 关于十五世纪中期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官窑生产,香港中文大学、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都曾举办展览,揭示可能的生产情况。然而,关于部分产品的窑址地层、精确断代,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为谨慎起见,本文仍然采用十五世纪中期的笼统说法。
[57] 据《明史》及《明实录》统计。
[58] 世宗肃皇帝实录[A].卷一百九十六,嘉靖十六年正月礼部条。
[59] Francis Woodman Cleaves.The Sino-Mongolian Edict of 1453 in The Topkapi Sarayi Müzesị [J].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3, No.3/4 (Dec.,1950), 1950:431-446.
[60] 英宗睿皇帝实录[A].卷二百二十四,景泰三年十二月哈密条。
[61] 有关明代 “洪武”官窑瓷器及洪武朝对外交往中的瓷器馈赠与赏赐,有诸多新问题需要厘清,笔者将另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