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一个剧作家
2024-01-15玛乔丽·布雷姆纳
〔英国〕玛乔丽·布雷姆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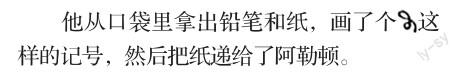
“谁会想杀一个剧作家呢?”戴克问。他是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的代称。——译注)的年轻巡警,黝黑,瘦削,此刻正在阿勒顿博士的书房里闲坐。阿勒顿是他的好友,很久以前短暂当过法医,为人和善,现已年过花甲,戴克经常和他讨论案件。装有镶板墙的书房灯火明亮,两人悠闲地喝着威士忌加苏打水,似乎已经将凶杀案抛诸脑后了。
阿勒顿咧着嘴笑了。“我会,我会想杀很多剧作家。一想起有几个晚上我看的那些戏剧,打杂的女佣竟然是大地母亲的化身,而且——”
“那些肯定不是出自刘易斯·梅纳德之手。他是个一流的剧作家。大家都喜欢他——不管是观众还是批评家。”
“你现在还想说什么?”
“基本没什么了。梅纳德住在切尔西,整晚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医生说他是晚上6点到8点间遇害的。他当时在酒柜取酒或者是拿酒杯,凶手趁机朝其脑后开了枪,距离很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指纹。”
“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烟灰缸里有两支烟。一支带过滤嘴,那是梅纳德的,因为梅纳德只吸带嘴的;另一支就是普通香烟。”
“如果上面没有口红,那说明凶手不是女人。”
“除非是一个不涂口红的女人。”
阿勒顿笑了。“那么,这是完美犯罪?”
“至少目前是这样。现在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入手调查。看不出来有谁会想置梅纳德于死地。”
“他的竞争对手。”
戴克哼哼一笑。“剧作家不会到处去杀比他们更成功的竞争对手。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不会因为世上少了一个作家,自己的作品就更有机会搬上舞台。”
“一个争风吃醋的女人,一个等着继承他财产的人,他的剧本导演,被他伤害的人,或者一个失去理智的窃贼。”
戴克叹了口气,“梅纳德人很好。他和妻子结婚十五年,生活很幸福,事发当晚,他妻子在瑞士,和父母待在一起;他的钱除了做慈善,都给了妻子和儿子;他的导演多年未换,两人是很好的朋友,而且事发当晚这个人正在参加一场派对,身边围着十来个人;说他伤害了别人也没什么根据,梅纳德的生活就像一本翻开的书,没有在南美隐姓埋名数年或诸如此类的事;最后——这个凶手认识他。没有强行入室的痕迹,肯定是梅纳德自己开的门。他不会邀请窃贼坐下抽烟喝酒吧。”
“那么答案很明显了。”
“什么?”
“没人杀他。”
戴克无奈地笑了笑。“不过,这并不好笑。梅纳德是个大人物,很受大众喜爱。如果我们不查清楚是谁杀了他,警察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你就知道说俏皮话。”
“好吧,但是根据你的描述,没人会去害他。我还能说什么呢?不对,我还有个想法:凶手杀他不是因为他做过什么事,而是因为他要做的事。”
“如果这就是你——”戴克突然停了下来,两人看着对方,然后阿勒顿说:“你看——俏皮话也是有用处的。”
“确实,”戴克若有所思地赞同道,“他遇害可能是因为他要做的事。”
一周后,戴克把调查情况告诉了阿勒顿。
“你的话是破案的关键,”戴克说,“你记得你之前说梅纳德遇害可能不是因为他做过什么事,而是因为他要做的事吗?嗯,一个剧作家总会计划要做什么,那就是写下一部剧。所以我又去找梅纳德夫人了……”
梅纳德夫人快四十了,依然美丽迷人。“嗯,是的,”她说,“刘易斯是准备写新剧,或者至少已经在构思了。但我第一次听他说起这部剧是在一个晚宴上,我去瑞士的前一晚……”
晚宴很愉快,是罗利夫妇举办的——唐纳德·罗利之前在外交部工作,他们在国外待了几年,刚回国。他们的房子在威斯敏斯特,餐厅宽敞,天花板高高的。银器和水晶玻璃杯在擦得锃亮的黑桌子上闪闪发光。背景是一面大镜子,映着男人的白衬衫和女人靓丽的衣服。聊天一直都很轻松愉快,不过后来刘易斯·梅纳德说起了亨利·沃特曼。这名年轻的新晋议员突然放弃了自己在下议院的职位,一年后在一场坠机事故中丧生。当时一共十二人遇难,其中包括他的妹妹和妹夫。“这肯定能写成一部好剧。”梅纳德说。
“但是这算不上一部剧吧,梅纳德。这顶多算一个小故事——当然,除非您从哲学角度大谈特谈他的抱负以及突然离世。”爱德华·林霍普说,他黑皮肤,鹰钩鼻,是最有影响力的晨报编辑之一。
梅纳德笑了笑。“不,”他说,“不对。没有人知道沃特曼为什么突然离开政界。这就可以写成剧本。”
“但确实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约翰·舍伍德说。他是内阁成员,跟林霍普一样,四十多岁,沉着稳重,声音温柔。“当然,您跟他是很好的朋友。或许他跟您说了什么?”
这个不经意的问题打破了轻松愉快的氛围。空气中弥漫着一丝焦虑,挥之不去。
梅纳德没有直接回答。他说:“这个嘛,我不是一个吃白饭的剧作家。您说得对,我跟他是好朋友,不过和其他人一样,我也不知道原因。但我可以发挥想象力——其实,如果您仔细想想,这种情况应该能激发任何一个作家的想象力。”
這个话题引起了晚宴女主人的注意。“那以您的想象力,他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呢,梅纳德先生?”她问。
“哦,有很多种可能。但是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对一部剧来说——沃特曼是遭人胁迫才离开政界的。”
“胁迫!”大家立马异口同声地说。
“是的。当然不是指钱,你们应该知道。可能是某个不喜欢沃特曼的人,比如政治上持异见的竞争对手。这个对手可能知道沃特曼的什么秘密,然后对他说,收拾东西走人,我就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否则,我就公之于众。沃特曼照做了。故事到此结束。”
短暂的沉默,但足以让之前紧张的气氛转向威胁这个话题。但罗杰·亚当斯轻描淡写地说:“不仅是故事结束,第一幕写完后,整个戏剧到这儿也结束了吧。”亚当斯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老板,能力很强。
梅纳德笑了笑。“别开玩笑了,这剧肯定不止一幕。”
“但是我了解沃特曼。他不像是那种人——他能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舍伍德反驳道。
“哦,可以是任何事。也许他辞职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救别人,他很在意的某个人,一个女人。”
“那么,我一定要看看你的剧,梅纳德——我一直都看你的剧。但我最想看的就是你会怎么结尾。”编辑林霍普说。
“很简单。”梅纳德俊俏的脸上洋溢着欢乐和智慧。“这个家伙——X——胁迫沃特曼离开政界,后来他一直在保护的女人死了。”
“那么,”女主人若有所思地说,“我想他保护的女人可能是他的妹妹。当然,她和沃特曼都在那场飞机事故中丧生了,但在一部剧里,可以不用完全按照事实来写,不是吗?如果真是那样,这个女人死了,那么他完全可以说出真相。”
“这只是一种可能,”梅纳德说,“假如沃特曼——或者我在剧中也可以用别的名字——保留了他被胁迫的证据,那么只要他的妹妹还活着,他就有顾忌。一旦他妹妹死了,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那就会成为另一部剧——复仇和复仇计划。但是说实话,我还没想那么多,也还没有决定好怎样结尾。”
戴克中断了叙述,对阿勒顿说:“当然,有件事很明显。”
“那就是梅納德知道沃特曼辞职的原因,而且他在那场晚宴上是在威胁某人。他肯定给出了很多暗示,不是吗?‘或许他是在保护某个女人。‘复仇和复仇计划。‘我还没有决定好怎样结尾。”
“是的——他已经说出了整个故事:有人胁迫沃特曼退出政界,为了保护妹妹,他照做了,而且他把整件事告诉了梅纳德。如果没什么特殊原因,梅纳德从不会那么随意地谈论自己才开始动笔的作品。他妻子也很吃惊,因为以前从来没见梅纳德这样做过。”
“但是这样做也太公开了,为什么不私下里威胁他呢?”
“不知道。我猜他是想让那个人紧张紧张。毕竟,沃特曼是他的朋友。他可能是想替沃特曼报仇,另外,他可能还想要一种诗一般的正义。我的意思是,把这件事写成剧本,让所有人猜到是谁胁迫了沃特曼,梅纳德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他赶出公众视野,就像之前的沃特曼被赶走一样。”
“很有戏剧性。但我想一名剧作家确实会做出这么戏剧性的事。那你之后做了什么呢?”
“哦,我先缩小了调查范围。当时在场的一共有六对夫妻,我排除了所有女人,因为她们都不参与公众事务;然后排除了梅纳德自己外的两个人:晚宴的主人,因为事发当晚他在国外;还有一个来访的加拿大人。”他停了一会儿,“那么只剩下三个人——亚当斯、林霍普和舍伍德。”
阿勒顿吹了声口哨,“国有企业的老板,有影响力的编辑,还有内阁部长——妥妥的三个嫌疑犯!”
“确实。我也不敢出什么差错,毕竟他们都是大人物。我觉得凶手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肯定是。但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展开行动。我正绞尽脑汁,梅纳德夫人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去见她……”
“很抱歉打扰您,”梅纳德夫人对戴克说,“因为这事可能帮助不大,但是您说过如果有任何不对劲的事情都尽快告诉您——”
“当然,您想起什么事了吗?”
“这个。”她拿出一份晚报,戴克接了过来,看了一眼上面的日期说:“这是您丈夫遇害那天的报纸。”
“是的。我当时在架子上整理一些文件——”她朝房间角落里的柳条架点了点头,“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
“是什么让您觉得这份报纸也许很重要呢?”
“因为我丈夫从来不买晚报。”
戴克很激动。虽然这不是什么大线索,但这是他第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线索。他问:“你们有女佣?”
“有一个钟点工,九点半来,两点半走。她从不看书看报,但我还是问了问她,想确认一下。她说不是她买的。她是在刘易斯遇害的第二天在书房里发现的,就把它放在了架子上。”
戴克在心里抱怨这个女仆也太勤快了,第一次检查这个房间时他就问过她,有没有碰过任何东西,她说没有。把报纸放在架子上显然不算碰过任何东西。
他小心翼翼地说:“好吧,当然,这可能就是某个不速之客留下的。”
梅纳德夫人摇了摇头。“不,刘易斯从来没有不速之客,他很讨厌工作时被打扰。如果要见别人,会提前约好。他从来不会放下手头工作去见不速之客。”
“我明白了。”
“我觉得这报纸不会有多大用处,”梅纳德夫人胆怯地说,“它们一天卖上百万份,但我想——”
“您说得很对,但说不定这个最后会对破案有帮助。这些事谁也说不准。”
“希望能帮上忙。您现在有什么进展吗?”
“我也不确定,”戴克说,“我还在想那个晚宴上发生的事,其中可能有破案线索。”
“您是指亨利·沃特曼吗?”
“是的。您很了解他吧?”
“很了解。当然,刘易斯更了解他。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
“您觉得在沃特曼想保护他妹妹这一点上,可能另有隐情吗?”
梅纳德夫人犹豫了一会儿。“我不是很确定。可能有吧。刘易斯没有直接跟我说过什么,但他之前确实提到过一两句,我觉得他指的可能是阿拉贝拉,也就是沃特曼的妹妹。”
“具体提到了什么呢?”
“哦,没什么很确切的事情。但我大概知道她之前在战争期间跟一个美国人有婚外情。”
戴克想了想。“但就算这件事被发现了,危害性有那么大吗?毕竟,很多人都会——”
梅纳德夫人淡淡地笑了笑,“但很多人都并没有嫁给阿拉贝拉的丈夫。他看上去一本正经,却很可怕。如果他听到一丝那样的风声,会立即遗弃她。而且她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可能会发疯,甚至自杀。”
“她情绪那么不稳定?”
“我想是的。他们家的人都这样。”
“我不知道居然这么严重,”戴克说,“不过我还是觉得——嗯,即便您说得对,但为了这种事情放弃职业生涯,是不是太感情用事了。”
“是的,但这不是普通的兄妹关系。阿拉贝拉和亨利在远房亲戚家长大,他们憎恶那些亲戚。他俩从小相依为命,为了妹妹,亨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明白了,但在我看来这还是太荒唐了。”
“嗯,是的。但这也是他的魅力,可能也是大家都那么喜欢他的一个原因。”
“有人不喜欢,”戴克严肃地说,“如果您的猜想是对的。您从来没见过有人讨厌他吗?”
“没有。”梅纳德夫人停了一会儿,“亨利是个很幸运的人,他英俊,有魅力,受人喜欢,人脉也广。没有他这种运气或者过得不那么好的人可能会心生怨恨,尤其是竞争对手。”
“如果是这样的话,”戴克缓缓说,“我能理解很可能有人会恨他。好了,非常感谢您,梅纳德夫人。您帮了大忙。我说的不仅是这份报纸。我会让您知道事情真相的。”
“我本来对这份报纸没抱太大希望,”戴克对阿勒顿说,“我把它带回办公室,逐行检查。上面当然是有指纹的,但是太模糊了,没什么用。不过我发现了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有人,就是拿过这份报纸的人,在一些报道上做过记号。他用的是绿色墨水和一支常规手稿笔。就是那种现在市场上卖的写字笔。”
“我知道,”阿勒顿说,“就像广告里说的那样,那些人想要写出祖先那样的漂亮笔迹。我呢,只要写出普通的笔迹就行啦。”
“除了药房里的人,没人指望能看懂医生的笔迹。”戴克笑着说。
“确实。哪些报道做了记号,是什么样的记号?”
“八卦专栏上关于国有企业的一篇文章,一篇关于生活成本上升的报道,还有一篇关于牛津和剑桥体育比赛的报道,这些报道上都画了一个圈,其中两个有这样的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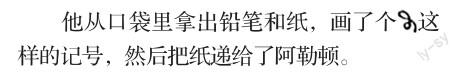
阿勒顿仔细研究了一会儿,然后说:“那这说明——”
“不一定。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那三个人的生活习惯。当然,我知道他们现在是做什么的,但我必须知道他们以前做过什么。《名人录》对我来说还不够。没人会在《名人录》里写他十九岁时在一家泡菜装瓶厂待了三个月,但这样的经历会让人养成一些生活习惯。看看那些当了一年海军的人吧,他们之后好几年都是用左手拿包裹,好腾出右手来敬礼的,尽管早就不需要了。”
“所以你得亲自跟他们聊聊?”
“是的,这其实不太好安排,但我还是去了。我先去拜访了舍伍德,他的办公室在白厅。他为人很谦和,他说局长告诉他这件事情很重要,和刘易斯·梅纳德有关……”
办公室很大很安静,有点简朴。舍伍德的桌子干净整洁,“收件”和“寄件”的托盘里几乎没有文件。舍伍德坐在桌子后面,沉着、稳重、有威严。在内阁成员里,他算很年轻了。
戴克说:“是的,是关于刘易斯·梅纳德的。更确切地说是关于那天晚宴,当时他说到了亨利·沃特曼。我想您应该记得吧?”
“当然记得。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梅纳德。但是您的意思是,您觉得那件事跟他的死有关?”
“说实话,阁下,我现在还不知道。梅纳德提到沃特曼什么特别的事了吗?”
“特别的事?我不觉得。当然,您可能也听说了,他推理说沃特曼是受人胁迫才結束了政治生涯——为了保护某个女人,我想他是这么说的。”
“是他的妹妹吗?”
“是的,有人猜测可能是这样。”
戴克掏出烟,给舍伍德递了一支。舍伍德把自己的和戴克的烟都点上了。戴克注意到这位内阁部长是左撇子。他盯着他那点燃的香烟,“您怎么看,阁下?”
“坦白说,我没什么太多想法。梅纳德是个很有想象力的人,他可以用这件事写出一部好剧。不过,至于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沃特曼又会不会听凭自己这样受人胁迫,这些我可真帮不了您太多!”
“我想您应该也不知道沃特曼为什么那样做吧,阁下?”
舍伍德停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吧,探长,这个不能外传:沃特曼家的人情绪都很不稳定。您知道国家肖像馆里那幅他祖父的画像吗?白白净净,身材修长,五官端正,看上去高度紧张。亨利就是那样——长得也像。我得顺便补充一句,阿拉贝拉情况更糟。我觉得亨利所做的只是这种不稳定情绪的表现之一。如果他之后又后悔,后悔自己出于某种奇怪的冲动而离职,我也不会惊讶。”
“我明白了,”戴克说,“这很有意思,阁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可以谈谈梅纳德这个人怎么样吗?”
“当然不介意。我很喜欢他。他人不错,很聪明,热情开朗,有自己的思想,但他不适合当公务员。”
两个人都笑了。戴克说:“我宁愿当剧作家,也不愿当公务员。”
“是吗?我可不愿意当剧作家。我讨厌文书工作和任何形式的写作,我甚至让妻子写所有的家信。美国人在这方面的想法很对——打字、口述、用录音机、找个秘书,就是要摆脱写作。”
戴克瞥了一眼“收件”和“寄件”的空托盘,还有干净的办公桌,“您在这方面似乎做得相当不错。”
“不算太差。”
戴克又回到了沃特曼的话题上。“您觉得他将来会有大好的前途吗?我是说,沃特曼的政治前途?”
“如果他能学会控制一下这种不稳定情绪,我想他前途光明。那时我们都在议会里,他、林霍普、亚当斯和我,他没理由混得比我们差。”
作为报社编辑,林霍普的办公室很不一样:大桌子上到处都是报纸,架子上也是乱堆的报纸。桌上还有三部电话,戴克和林霍普谈话时不一会儿就响一下。
林霍普和舍伍德迥然不同,林霍普更高,更瘦,给人活力四射的感觉。但是,作为一个年纪轻轻就取得如此成就的人,他也很有威慑力。他很乐意让戴克翻看报纸档案,查找有关沃特曼和梅纳德的报道,还微笑着补充说,关于这两个人的报道应该有很多。戴克递给他一支烟,注意到他惯用右手,于是谈起梅纳德的推理,说沃特曼是受胁迫才退出政界的。“您认为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先生?”
“不知道,”林霍普缓缓说道,“我想我不需要告诉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胁迫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当然,那些被胁迫的人应该报警。还是一样,不需要我费口舌和您说,他们通常都不会报警。”
“您说得很对。那么,您认为梅纳德也许真猜对了些什么吗?”
“很难说。这是件大事——屈服于他人的胁迫,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原以为他更有胆量,更像个战士。当然,可能是我错了。”
“如果只涉及他自己的话,他可能确实是个战士。但如果他是在保护别人——”
“哦,是的,有可能。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想让沃特曼退出政界。”
“可能有人讨厌他,或者觉得他是个竞争对手。”
林霍普神情疑惑。“我从来没发现有人讨厌他,甚至说不喜欢他。他人很好。说到竞争对手,大家都有啊,但我们不会去胁迫他们放弃自己的事业。”
“是的。当然,这只是梅纳德的推理。不过,在那次晚宴上,会有人当真吗?”
“我觉得没有。让我来仔细想想,沃特曼被人胁迫退出政界,梅纳德知道真相——”
“而且打算在他的剧里揭露这个人是谁,让他丢掉饭碗。这是一种很隐秘的伸张正义的方法。”
林霍普摇了摇头,“好吧,探长,这些事情还是您比较在行。我不了解。我只是个新闻编辑——一个蹩脚的作家。一直都是,还在议会时就是。但是,坦白讲,对我来说,这件事挺离谱的。”
“说实话,”戴克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但离谱的事情确实会发生,尤其是在谋杀案中。顺便问一句,既然您认识沃特曼,那您知道他辞职前有什么计划吗?”
“计划?”
“是的。我的意思是,他想继续从政,进入内阁,还是像您一样离开政界,去做编辑,或者像另一个那样去从事航空业?”
“哦,我明白了。我想他的主要兴趣是政治,但他对教育也很感兴趣。他可能想当一个红砖大学(指维多利亚时代创立于英格兰六大工业城市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得到英国皇家许可的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兹大学、布里斯托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和利物浦大学。——译注)的校长,诸如此类。”
“是吗?我之前没听说过。”
“哦,我们以前经常在酒吧聊天,他提到过一两次。”
“我明白了。很遗憾,不是吗?优秀的人本来就不多,这样的损失我们承受不起啊。”
“真的太遗憾了。”
亚当斯矮壮结实,曾经当过划船手和拳击手。戴克说明来意时,他的态度轻松友好。戴克递给他一支烟,他没有接,说他从来不抽烟,向前推了推一个大玻璃烟灰缸,让探长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嗯,我想知道您对罗利家举办的那次晚宴有什么看法,先生。您还记得他们提到过亨利·沃特曼吗?”
“当然记得,”亚当斯说,“但您的意思是这和梅纳德的死有关?”
“不知道,但我觉得有可能。不管怎样,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您能告诉我大家当时说了些什么吗?”
“当然。是梅纳德自己先提到亨利·沃特曼——”
“您了解他吗,先生?”
“沃特曼吗?很了解。我们那时是同班同学,虽然他总是赢过我,但他人确实不错,本来会有大好前途的。”
“政治上吗?”
亚当斯看起来很惊讶。“我想是的。没道理不會,毕竟那就是他的兴趣所在。”
“他对国有企业感兴趣吗?”
“您是说,他会喜欢我这样的工作吗?是的,可能会。而且他也会做得很好。”
戴克吸了一口烟。“我明白了。抱歉,先生,刚刚打断了您。刚才在说那次晚宴的谈话——”
“是的。但当时并没有说到什么要紧事。”他接着向戴克叙述了整个谈话过程,简洁准确。他讲完后,戴克钦佩道:“您记性真好,先生。”
亚当斯笑了。“我只对说过的话记得很清楚,别的事记性不行。我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复述一段对话,但对书面文字我是没什么记性。”
“既然您对说过的话过耳不忘,您也应该去写剧本——像梅纳德那样。”
“不。”亚当斯笑道,“我没有想象力。不过,我也许本会喜欢新闻。我中学时甚至想学新闻,但后来上大学之后,或多或少就忘了这件事。”
戴克点了点头。“舍伍德和林霍普跟您还有沃特曼不是同学吧?”
亚当斯摇了摇头。“不是。舍伍德应该是去了哈罗公学。林霍普——我不知道,我想他上的不是私立学校。”
“您认为这些还重要吗?”戴克好奇地问,“我是说,上什么学校?”
“哦,重要。”亚当斯笑了,“我觉得在这个国家,不管怎样,这一直很重要。改革家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观念,他们可能是对的。但事实还是现在这样,上什么学校很重要。”
“所以,”戴克对阿勒顿说,“从他们三个人跟我说的话来看,我知道是谁杀了梅纳德。”
“我知道。”阿勒顿严肃地说,“你很聪明——没有直接问一个问题,很了不起,但问题是你没有证据。”
“是的,只知道是谁。一个嫉妒沃特曼的人,惯用右手,抽烟——”
“那你之后做了什么呢?”
“嗯,我知道那份报纸是五点半到六点之间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售出的。我给一些人看了一张照片,然后去打了个电话。这样做有那么点不正规,但如果我们不想把丑事外扬,这似乎是唯一的办法。当然,从官方角度来说,局长并不知道……”
戴克去见了那个杀害梅纳德的人,那个在梅纳德剧本里被称为X的人。他热情地接待了戴克,递给他一杯酒和一支烟。戴克很清楚这个人有罪,也对他的配合感到惊讶,但还是不禁为这种人才和能力的浪费而悲哀。戴克耐心地跟他讲了自己对梅纳德之死的看法,他以同样的耐心听着。
“您看,”戴克说,“我从一开始就几乎可以肯定,梅纳德遇害是因为他在晚宴上说了那些话。他在公开威胁一个人。他会在他的剧本里揭露沃特曼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干的。”
“很有意思。”
“您一定还记得,当时在场的有六个人,我可以排除其中三人:梅纳德本人,晚宴的主人和来访的加拿大人。这样就把嫌疑人缩小到三个了。”
“三个,”那人很有礼貌地说,“那这个调查范围也不小了。”
“还有就是,”戴克说,“我有两条线索。凶手留下了一个烟头——现场有两个烟头,梅纳德的和另外一个人的;还留下了一份报纸,上面用绿色墨水的手稿笔做了记号。”
“您真像福尔摩斯。”那人笑着说。
“是吗?但这就是破案的关键。三个嫌疑人中有一个不抽烟,有一个是左撇子。”
“抽烟确实是个线索,”那人还是彬彬有礼地说,“但左撇子怎么算得一个线索呢?”
“嗯,您看,这些记号是用手稿笔画的。现在,您也知道,有专供左撇子使用的特殊手稿笔。如果他是个左撇子,还买了笔,说明他足够重视自己的书写,那他买笔时肯定会根据自己的情况买一支左撇子专用的。”
“这些都只是推测性的、不确定的东西。”X淡淡地说。
“也许是。不过,还不止这些。这三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真正有理由嫉妒沃特曼,或者说在他看来有些方面让他嫉妒了。只有一个人说不太了解他,但似乎很了解他。”
“是吗?”
“是的。最后,只有一个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人,才会在这份报纸上留下这样的记号。”
“别卖关子了。”他嘲讽道,“什么样的记号?”
戴克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所以我带了一张您的照片,”他说,“我把照片拿给在维多利亚车站或附近工作的人看了看。您应该记得,那是您买晚报的地方。”
“事实上,我并不记得。”
“这不要紧。我找到了那个卖报纸的人,他认为他记得您,说他认为您买过一份报纸,而且有可能就是在梅纳德遇害那天。”
X笑了。“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警察,您认为这是证据吗?”
“只有这个或许算不上,”戴克不紧不慢地说,“但有一个行李搬运工,他认为他记得您那天晚上经过维多利亚车站。还有一个邻居,他认为他在梅纳德住的那条街上看见了您。”
“是吗,探长——”
“那天您在维多利亚附近开会,”戴克补充说,“您很有可能是在那里买了报纸。”
“总而言之,”X又笑了,“您这还是捕风捉影。”
“我不是很确定,”戴克平静地说,“如果有更多的证据,我可能会直接起诉了。但即使我没有……”
戴克停下了。过了一会儿,那人问,话语有点犀利,“会怎样呢?”
“那么,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梅纳德的一个朋友去做他本想做的事了吧,不是吗?写梅纳德本来要写的剧本?我可以把情节告诉他。就算我不能以谋杀罪起诉您,也可以让您在社会生活中混不下去。”
“您应该也知道,”那人还是很犀利地说,“不是每一部写出来的剧都能搬上舞台。”
“这部可以。如果有必要的话,梅纳德夫人会花钱让人演出来。梅纳德的朋友们会看到这部剧引发讨论、在报纸上被评论,他们会帮忙的——您知道他有很多朋友。”
两人沉默了一阵。然后那人说:“您是个很决绝的人,探长。甚至有点猖狂。我想您知道这是一种勒索吧?”
“我当然知道。但您不会跟任何人说这件事的,对吧?我的意思是,综合考量,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办法。”
那人再开口时话语中少了犀利,听起来疲惫又无可奈何。“是的。我明白。您不僅很决绝,探长,您还很聪明。我知道了,我必须好好考虑一下。顺便问一句,既然您没什么证据,现在只有我们两个——我在那张纸上写了什么?”
戴克拿出一支笔和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个记号,然后递了过去。那人看了一眼,然后笑了。“一个删除的记号,”他说,“表示这里有一个多余的字母或单词。当然,我不自觉就画了这个记号,习惯了。我告诉过您,我只擅长做新闻编辑。”
爱德华·林霍普那天晚上死了,他的车在离多佛不远的地方坠崖。
(武肖林: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选自Murder by the Book First published 2021 by The British Library 96 Euston Road London NW1 2DB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22-79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