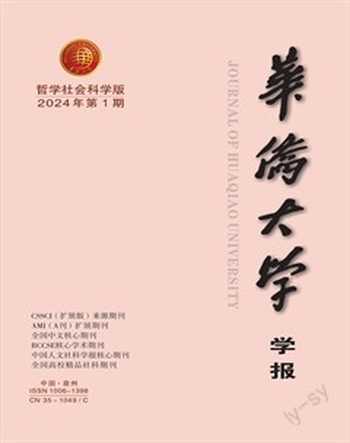性别地理:论美国加勒比裔小说中的跨国家园
2024-01-12陈天然
摘 要:
在美国加勒比裔小说中,“家”的空间表征体现为一种非同质性的跨国家园制作过程,它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划分与性别划分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跨国移民的家园概念发生在祖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社会场,并不断模糊化;另一方面,性别和地理的跨国缠绕催生了性别模式的变异,女性移民关于遗忘和记忆的家园叙事呈现出驳色的文本意义:其美国家园绘制彰显了开放性和前进性色调,却在有意无意间保留了加勒比家园底色;男性的家园怀旧叙事则关联家庭私域,呈现出封闭性和降维趋势,表达了主体性退隐或丧失的危机。由此,加勒比裔作家颠覆了男性/公共域和女性/私人域之间的齐整对立,动摇了传统的性别权力结构,再现了跨国空间中新的性别运作模式。
关键词:美国加勒比裔小说;跨国家园;性别运作
作者简介:陈天然,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族裔文学 (E-mail: 59412743@qq.com;福建 泉州 362021)。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美国拉美裔小说中的跨国物书写研究”(FJ2023B011);华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加勒比英语文学中的华人移民书写研究”(HQHRZX—202311)。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4)01-0128-09
一 引 言
21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跨国主义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跨国主义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们不应忽视美国文学自诞生之初就具有内在的跨国主义性质,而假设如今它进入了“跨国时代”。然而,虽然跨国主义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其当代时期“并不是旧的复制品,而是针对具体环境的重新配置”。Steven Vertovec.Transnationalism.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13-14.】热潮带来了美国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变。雪莱·费什金(Shelley F.Fishkin)在2004年美国研究协会的主席就职致辞中,强调了美国研究的跨国转变,认为对跨国批评的需求将成为变革美国研究的有效途径。【Shelley F.Fishkin.Crossroads of Cultures: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American Studies.American Quarterly, 2005, (57),pp.5-20.】2005年,施艾勒·洪斯(Sheila Hones)等提出了从“地域地理”到“关系地理”的概念转变,以挑战美国中心论。【Sheila Hones&Julia Leyda.Geographies of American Studies.American Quarterly, 2005, (57), p.1 021.】2009年,史蒂文·维阿托维克(Steven Vertovec)的《跨国主义》一书对跨国主义进行了界定:“跨国主义是指跨越国界的人或机构之间的多重联系和互动”,即“持续的跨境关系﹑交换模式﹑隶属关系和社会形态跨越了民族—国家”【Steven Vertovec.Transnationalism.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1-2.】。对跨国学者来说,地方特异性或民族框架将与互动网络中的其他特殊性一起存在,这些特征在全球化的美国研究中为跨越式和多向性的文化生产提供了便利。费什金的致辞主要围绕美国文学,所以她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转向的另一标志是“劳特利奇美国文学的跨界视角”系列书籍的出版。其中,保罗·杰伊(Paul Jay)的《全球事务: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认为,文学研究的跨国化是20世纪60年代学术体内外因素交织的结果。对内,跨国转向是对自19世纪以来阿诺德研究模式的否定,这种狭义的审美模式是一种理想的历史虚无主义;对外,它源于60年代初的民权/妇女/奇卡诺/同性恋权利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促进了种族、多元文化和后殖民主义研究,从而奠定了文学研究跨国转向的基础。【Paul Jay.Global Matters: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Literary Studies.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7.】笔者认为,裹挟在上述运动中不断壮大的族裔文学本质上就具有跨国书写的典型特征,这种跨国性集中体现在族裔文学的家园再现中,它使稳定﹑固化的家园神话分崩离析。
在美国加勒比裔文学中,“家”成了多种本土的﹑跨国主义为导向的移动家园,指向了家园概念的模糊化和变异性。在该领域,家园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Maia Butler,Lukasz Pawelek, 林文静,Elizabeth Hackshaw【Maia L Butler, Joanna Davis-Mcelligatt, Megan Feifer.Narrating History,Home, and Dyaspora: Critical Essays on EdwidgeDanticat.Jackson,Mississippi: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22.Lukasz Pawelek.The Role of Nostalgia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Caribbean Diasporas-Linking Memory, Globalization and Homemaking.Detroit, Michiga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2015.林文静:《飘泊中的求索:解读三位当代美国加勒比女作家作品中的家园重构》,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Elizabeth Walcott-Hackshaw.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Danticat’s Landscapes of Return.Small Axe,2008, (12).】等,盡管上述研究立足于族裔文学内在的跨国性,采用了双重视野,注意到家园书写的跨文化性,然而其分析或偏重移民对故国的想象或回归或聚焦于东道国家园建造,不自觉中使用了民族主义的分析逻辑,产生了新的二元对立倾向,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本中跨越国界来回穿梭的社会力如何构成双向流动的社会场。此外,研究也缺乏对跨国语境中与性别等具体变量相关的深层挖掘。帕奇希娅·佩瑟尔(Patricia Pessar)等建议,跨国研究应该“询问性别关系如何在跨越国界的移民妇女和男性之间进行谈判以及性别在跨国语境的衍变”【Patricia RPessar&Sarah J.Mahler.Transnational Migration: Bringing Gender in.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3, (37), p.815.】。以美国加勒比裔三部代表作《息,望,忆》《梦回古巴》和《褐色女孩,褐砖房》【选择这些作品有两重考量:首先,这些作家代表三代美国加勒比裔移民写作的文学传统,第一代是葆拉·马歇尔(1929—),第二代是克里斯蒂娜·加西亚(1958—),第三代是艾德维奇·丹蒂卡(1969—)。其次,她们的作品分别代表加勒比祖籍国三个重要地理文化区域——英语区﹑西语区和法语区。】为例,本文将重审家园再现表达的跨域互构特质,并将性别这种微观变量纳入阐释视野,进而思考:性别化的家园制作所处的跨国社会场体现出怎样的异质流动性?文本如何通过家园书写来挑战空间划分与性别划分?其呈现的新型性别运作模式具有怎样的指涉?
二 遗忘与记忆:加勒比女性跨国移民的家园制作
《无拘的国度》一书认为“移民”(immigrants)应被定义为“跨国移民”(transmigrants),当他们“发展和维持多种跨越国界的如家庭﹑经济﹑社会﹑组织﹑宗教和政治等关系时”【Linda Basch, Nina Glick Schiller, & Cristina Szanton Blanc.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and DeterritorializedNation-States.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8.】。“跨国移民”的概念挑战了将地理空间和社会认同捆绑的旧认知,揭示了移民本身如何被其跨国实践改变而生成了一种暧昧不明的认同。这种含混和不确定性在加勒比女性跨国移民“遗忘”与“记忆”的家园书写中得以集中呈现。一方面,女主人公选择逃离加勒比而体认美国文化,这使其有了冲破旧家园性别定势的动能,在打造后殖民自主家园时与失落的自我相遇;另一方面,她们通过远程交流或汇款或政治活动与旧家园保持联系,加勒比族裔社区环境也使其下意识地与根文化相联。维阿托维克指出,作为地方或本土性的重建,跨国主义通过人们与空间的关系以及在两个或更多国家创造跨国的“社会领域”或“社会场”的另类概念得到展示。【Steven Vertovec.Transnationalism.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12.】此时,女性的家园制作位于跨国社会场的撕扯中,表征着一种既遗忘又记忆的分裂性,体现在时空两个维度。空间上,她们经历了两种文化体制,必然会产生一种断裂,即与过去和传统的断裂,然而时间上,文化无意识又使其不自觉地埋首历史﹑打捞记忆,这种分裂性赋予了文本一种徘徊的张力和矛盾性审美。
《息,望,忆》是海地裔作家艾德维奇·丹蒂卡(Edwidge Danticat)的成名作,它的半自传体叙述反映了祖籍国海地的女性在男权社会所遭遇的后殖民压迫和禁锢。在臭名昭著的杜瓦利埃 (Francis Duvalier,1957—1986)独裁统治时期,创建同顿·马库特斯(Tonton Macoutes)军队用来维护极权统治,然而妇女却首当其害,惨遭蹂躏。主人公马汀正是国家“资助”的受害者之一,16岁时被一名蒙脸的马库特斯成员强奸。强奸案发生在甘蔗林,反映了海地奴隶制时代的性暴行与当代暴力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揭示了一种历史建构的父权制性别霸权气候。而“十根手指”的隐喻也反映了男权社会勾勒的女性图景:“做母亲、煮沸、关爱、烘焙、护理、煎炸、治疗、洗涤、熨烫、擦洗”【Edwidge Danticat.Breath, Eyes, Memory.New York: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4, p.151.】。海地妇女被牢牢锁定在关于责任、顺从和美德等母职经验的有形/无形的幽闭空间中,然而小说对性别认同的阐述超越了特定的海地家园,进入了跨国空间,这与跨国女性主义研究相呼应,“它涉及性别与跨越国界的地方和全球移民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Juanita Heredia.Transnational Latina Narrativ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6.】,这在小说中被解释为私人域/公共域与加勒比/美国地理家园的并置与交织。
小说中,童贞测试(virginity testing)被用来暴露跨国实践活动与父权制意识形态之间产生的矛盾,作为海地文化实践的一种暴力符号,它被移植入美国家园。虽然女性移民可能会在新家园建立新的角色和政治空间,但也“可能会重续父权制结构,这种结构时而赋权时而限制,因为她们继续以复杂的方式保持与家乡的联系”【BrendaYeoh,Katie Willis.Constructing masculinities in transnational space.in Transnational Spaces.edited by Peter Jackson, Crang Philip, & Claire Dwyer.New York: Routledge, 2004,pp.149-150.】。义无反顾地抵达美国彼岸表明马汀对海地父权体系的对抗,她要阻切过去﹑隔断世界。然而文化无意识已渗入马汀的精神肌理,驱动她持守海地习俗对女儿索菲进行多次的童贞测试。顾明栋认为,文化无意识“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教育、生活经历和意识形态教导而获得的教养无意识或教化無意识”【顾明栋:《论“文化无意识”——一个批评理论的概念性构建和实用性检验》,《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82页。】,“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无意识不是文化和无意识的简单叠加,而是文化和无意识通过历史、心理、话语等因素的互动而建立的文化心理机制和认识论”【顾明栋:《论“文化无意识”——一个批评理论的概念性构建和实用性检验》,《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80页。】。童贞测试正是在母国后殖民历史境况和父权话语等合谋中诞生的一种文化无意识的外化呈现,它联结着马汀被强暴失贞后遭受社会排斥的创伤体验,是父权社会驯化出的一种教养无意识,在跨国语境下,它转化为对母国传统和文化期待的倔强承继和艰难打破的矛盾过程。小说将童贞测试更精确地配置为旅行记忆和旅行历史,挑战了国界和国家记忆的地理固定性和不可渗透性,然而精神的震撼﹑领悟与转变也发生在跨国社会场,它内在的文化多向性引领女性步入新前景,获得了反观民族文化的必要距离,也获得了对话自我的契机和抵制父权话语捆绑的可能。意识到测试正将女儿推向精神崩溃的深渊,马汀挣脱了文化无意识的羁绊,寻女至海地并向她坦言:“你和我,一开始就错了……我们被允许重新开始”【Edwidge Danticat.Breath, Eyes, Memory.p.162.】。马汀最终跳出了男权“同谋”模式,揭开了被父权意识遮蔽的主体自我,和女儿达成了精神和解,重新界定了母职经验,从而指向女性获得超越性自由的希望所在。
在新家园,虽然仍处于移民的边缘化状态,但马汀通过职业选择创造了向上的生长空间,以一种主体性的内在逻辑走向新的社会形塑。一方面,她依靠自我开启了新家园的家庭制作。她用薪水在纽约购买公寓,后搬到拥有独户住宅的中产阶级社区,又将女儿接到美国,扩大了家庭制作。另一方面,她不仅通过电话和录音等通讯手段和海地家人交流,而且通过跨境汇款支持家人。来自国外的汇款可被视为“跨国主义的具体的、物质的表现形式”,并“对国内同胞产生深远的影响……汇款有助于维持国内的家庭和社区”【Nicholas VanHear.Sustaining societies under strain: Remittances as a form of transnational exchange in Sri Lanka and Ghana.in New Approaches to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me.edited by Nadje Al-Ali and Khalid Koser.New York: Routledge,2002, pp.202-221.】。马汀的汇款不仅为海地的女儿提供了学费,还让家人如上流阶层般享有宽敞的居所。移民妇女的消费行为“突出了一个强大的途径,劳工女性以此寻求新形式的自治和能动性以建立满意和有价值的社会身份”【B.M.Mills.Contesting the margins of modernity.Women, migration,and consumption in Thailand.American Ethnologist,1997,(24),p.41.】。尽管马汀作为移民妇女必须与其作为被剥削劳工的现状作斗争,但可以利用收入提升其在母国的社会地位,在边缘再造“中心”,她成功的移民形象也反映在她头戴墨镜、操着一口克里奥尔语时受到同胞钦佩的回归场景中。
为了摆脱殖民和父权制压迫,马汀试图抹去家国记忆以在边界外宣布独立。跨国动能带来了赋权和潜在的变革性,马汀以一种遗忘的姿态,打破性别规范的“紧箍咒”,参与自我激励的发展,从匮乏走向自足。虽十年间未曾回过海地,马汀仍潜意识地与家乡相联:经济和情感层面,她通过越洋汇款和电话﹑录音带等与家人保持密切来往;身体层面,她确实回家旅行,以修复与女儿的破裂关系,她的尸体后也被运往海地埋葬。小说既刻画了马汀新的性别身份,也描绘了她立足新家而遥望故园的悖论社会场,制造出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民族认同,是对跨国移民操作性别空间和地理空间的一种复杂再现。
性别和家园的跨国缠绕也反映在《梦回古巴》和《褐色女孩,褐砖房》中。如马汀一样,鲁迪丝和茜拉的祖籍国是对女性政治或经济压制的同义词,也是她们海外艰难旅程的起点,然而在美国家园,她们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参与者,被推向社区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的前台。
古巴裔作家克里斯蒂娜·加西亚(Cristina García)的名作《梦回古巴》以古巴革命为背景。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革命推翻了巴斯塔斯塔的腐败政权,然而,革命政府根据土地改革法大规模征用土地,没收私营企业以及不断增长的经济和个人限制,使许多古巴人流亡海外。鲁迪丝是小说中流亡群体的代表,在古巴革命中,夫家鲁非诺家族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鲁迪丝失去了特权阶层的舒适生活;她也被革命士兵强暴并痛失腹中胎儿。鲁迪丝的遭遇象征着失去权力、属性和对身体的控制。为了和古巴决裂,她举家流亡到纽约:“她不想要古巴的任何部分”【Cristina García.Dreaming in Cuban.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2, p.73.】,她的民族身份和性别身份在东道国得到重新协商与角力。移民后的鲁迪丝积极投入新家园的建造,试图在语言、文化习俗、商业和政治方面完全转型并拥有美国身份。她说英语而非西班牙语,庆祝美国节日如感恩节而非母国节日,支持美国的政治活动,成为附近的志愿协警,并在自家面包店组织流亡者参加政治讨论。更重要的是,她的創业技巧更适合在纽约发展。在跨国研究的“第二次浪潮”中,托马斯·拉克鲁易克斯(Thomas Lacroix)揭示了跨国进程与“世界秩序的新自由主义重新调整”之间的隐藏联系,其中“资本主义势力限制了国家能力,但为个人能动性提供了更多的空间”【Thomas Lacroix.Diasporic Identity,Transnational Agency,and the Neoliberal Recon guration of Global Migration.Diaspora,2007,(16),pp.410-411.】。鲁迪丝信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取得了面包生意的巨大成功,开办了连锁面包店。鲁迪丝以其多样化的存在解构了女性气质【女性气质泛指女性应有的心理/性格/行为特征以及兴趣爱好和活动方式等,如敏感、柔顺、被动、依赖等。女性气质通常被限制在家庭角色之中,与活动在社会公共领域的男性所体现出的具有主动性、影响力和领导者特征的男性气质相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一书指出女性/男性气质是父权制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这种气质说夸大了男女之间生物学的差异。玛丽·戴利(Mary Daly)的《超越父神》也否认男性气质(担任统治角色)和女性气质(担任从属角色)的说法,认为这都是父权制蒙蔽人心的产物,是男性制造的概念模式。】的神话,她的新家园制作活动表明,妇女如何在较少涉足的经济领域中可以拥有高光时刻,甚至在限制性政治舞台上起舞,从匿隐走向看见。
尽管鲁迪丝有意识地拒绝古巴,文化无意识使她仍与之紧密相联。她被古巴文化所包围:丈夫在家中建造了一个古巴世界以纪念失落的家园;女儿皮拉尔有强烈的归国愿望,甚至鲁迪丝自己也渴望吃糖果(这里的糖果暗指古巴最丰产的糖业)。她的无根和错位也暗嵌在她经过布鲁克林阿拉伯商店时的思忖:“他们的语言会发生什么变化?留下的温暖墓地又会怎样?他们那些僵硬的﹑未被翻译地躺在怀里的激情又去向何方”【Cristina García.Dreaming in Cuban.p.73.】?阿拉伯商店如镜像般反照现实,促使她反思自己的流亡﹑焦虑和失去,这实际上表明了她对古巴的复杂感情以及她和其他移民所共有的同化和流离失所。与历史和传统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使她无法完全抽身,古巴文化成了她缓释紧张和焦虑的一种手段,使她的精神之墙免于最后的剥离和坍塌。此外,与其他流亡者一样,对古巴政治的火热讨论成为她的主要政治活动之一。流亡者不断地讨论和评估国内政治局势,有助于形成密集的跨国政治社会场,它在祖籍国和东道国间延伸,撕裂了民族主义的统一性和同质性。鲁迪斯经营跨国家园的故事揭示了跨国社会场如何重建了女性的主体能动性和精神价值体系,也质疑了民族主义逻辑中的本质主义存在。
《褐色女孩,褐砖房》是巴巴多斯裔作家葆拉·马歇尔(Paule Marshall)的代表作。主人公茜拉在20世纪30年代从巴巴多斯迁移到纽约,决心在布鲁克林的褐砖房区拥有一座像样的房子,茜拉代表了海外巴巴多斯移民的精神。茜拉在美国再造家园,拒绝回到原乡,象征意义上,她必须切断与旧家园的联系才能过上和父权制和殖民压迫历史脱离的新生活。
像鲁迪丝一样,切断与祖国的纽带迫使她作为独立的女性和为家庭生计而奋斗的母亲向前看。为了实现在美国置家的梦想,她清洁房屋﹑在工厂工作(甚至在战争时期在危险的弹药厂工作)﹑在社区出售烘焙食品。新家的唯一装饰是全家福,不是来自她过去的岛屿,而是来自她在纽约生活的第一年。她的岛国被留在遥远的过去,而纽约则被视为永久的家园。除了女儿的加勒比银手镯外,她的其他物什都是纽约消费品。移民使她的生活向上流动,回到岛国,除了在收入不佳的甘蔗田里像机器一样工作外,别无他选。茜拉告诉女儿,她曾是家乡的第三阶层,这意味着无休止的工作和“在十岁的年龄比男人更努力”【Paule Marshall.Brown Girl, Brownstones.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1959, p.45.】。相比之下,纽约的工作是可以忍受的,并且她与受过高等教育的迪尔顿结了婚,这样的婚姻在阶级分层的巴巴多斯是无法想象的。此后茜拉加入巴巴多斯房主协会并占据了重要席位,她为之自豪并致力于社区公共事务,活跃在各种会议和论坛上。茜拉积极参与政治的行为表明妇女有能力获得代表权并以政治行为者的身份发表意见,这是女性自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实践,改变了她们在殖民和父权制压迫历史中的从属地位。茜拉决定永远不再回想母国,但她总是依赖于巴巴多斯社区获得必要的支持。与此同时,在女儿塞琳娜的银手镯中仍然有她的岛屿文化之痕,她的加勒比身份也反应在她那颇具加勒比特色的厨房里:“星期六,厨房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因为茜拉正在制作要兜售的巴巴多斯美食:黑布丁﹑还有酱制品……和椰子或甜面包”【Paule Marshall.Brown Girl, Brownstones.p.67.】。这些都象征着流散的巴巴多斯人与故国家园的文化联系,也时刻提醒着茜拉徘徊在巴巴多斯和美国之间的身份体认。
跨国女性主义研究承认,“实践总是在相互关联的特定冲突和矛盾领域中进行协商,女性主义议程必须被视为取决于历史具体情境下的构想和重构过程”【Caren Kaplan, I Grewal.Transnational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Beyond the Marxism/Poststructuralism/Feminism Divides.in Between Woman and Nation: Nationalisms, Transnational Feminisms, and the State.edited byCaren Kaplan, Norma Alarcón, and Minoo Moallem.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58.】。跨国女性的个体行为若没有真正有效的历史维度的建构,就不可能有真正富有意义和价值的生命实践。女主人公带着加勒比民族文化和特定的历史过往,在美国重建家园。她们在新家园的大都会中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女儿/妻子/同伴/母亲的预期角色,被都市中心的需求﹑分裂﹑陌生和流动所推翻,她们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新家园的匿名性有助于她们留下最糟糕的经历,从记忆中“抹去”祖籍国贫困﹑压迫﹑政治动荡的父权制社会,摆脱家国文化中的性别壁垒,打破母亲等于“母职”的迷思。然而在跨国空间中想象和实践性别时常会出现不一致的矛盾景观,虽然对决意购买单程票的跨国女性来说没有循环迁移,但她们并未被连根拔起,无论是汇款﹑探亲﹑还是政治活动或浸染在加勒比文化环境中,都构成了加勒比和美国之间的微观社会场和“记忆”互动网络。在这些家园叙事中,情节的连贯性被打破,“遗忘”和“记忆”的矛盾双重性并非是思想破碎的讯号,而是跨国性别实践的复杂再现,“遗忘”书写冲击了固化的两性伦理秩序,标志着对政治暴力和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对抗,而“记忆”书写则揭示了持续的跨民族—国家的交换模式﹑隶属关系和社会形态,进而将创伤的加勒比过往与充满生机的美国现在胶着在一起来重新定义女性和家园。
三 怀旧:加勒比男性跨国移民的家园构建
《草根跨国主义》一书指出,波兰人﹑犹太人和爱尔兰裔美国人所保留的祖籍国政治文化表明,跨国主义可以继续发展而与国土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而诉诸想象的家园构成了跨国主义的情感和象征形式。【Michael Peter Smith& Luis Eduardo Guarnizo.The Locations of Transnationlism.in 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edited by Michael Peter Smith& Luis Eduardo Guarnizo.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8, p.17.】对加勒比男性移民来说,他们可能无法维持较强的跨国实践形式,但保留着对加勒比的情感想象和象征性联系,这种跨国主义的痕迹体现的正是“情感跨国主义”。与汇款或参与东道国政治等女性移民的跨国实践相比,象征或情感跨国主义对男性移民尤为重要,这种跨国主义更具文化上的特色,这是一种包含在跨国社会场中的怀旧情愫。大多数情况下,跨国迁居并非是宣告男性气概的适当仪式,新土地上的定居削弱了对男性气质以及特权的肯定,而去权化孕育了男性移民的怀旧情绪。这种怀旧也多与私人和家庭场景相联,如品尝母国食品﹑保持旧家物什﹑回忆童年或怀揣母国筑居梦,而这传统上被归为女性特质。
在《息,望,忆》中,海地食物,作为海地文化的体现,成为怀旧的标志,并将男性角色与故国勾连。格劳瑞尔·安扎尔杜瓦(Gloria Anzaldúa)在《边疆》一书中提到“我们以更多微妙的方式内化认同,尤其是图像和情感的形式。对我来说,食物和某些气味把我的身份和祖国紧密相联”【Gloria Anzaldúa.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1987, p.61.】。安扎爾杜瓦强调食物和气味有助于形成归属感,对故国食品的消费是保存其族裔背景的一种方式,因为这种消费行为象征性地内嵌着个人的源出地。
食物﹑记忆和家园之间的关系在小说中赫然在目。坚持吃像芭蕉﹑大米和豆类这样的海地食物而不是典型的美国食品如水果拼盘和烤宽面条,揭示了老式海地人如马克在移民地对家乡的怀旧。多年来,马克一直生活在美国,但对海地文化心心系之,表现在他对海地食物的热爱:“马克是那些不吃妈妈的烹饪就会受不了的男人之一,如果他能让妈妈离开她的坟墓给他做饭,他就会这样做”【Edwidge Danticat.Breath, Eyes, Memory.p.53.】。为了吃到最好的海地食物,即使在费城和蒙特利尔等遥远的地方,他也会带着女友马汀在海地餐厅用餐。在一家名为Miracin’s的餐厅,马克加入了其他海地人对祖国政治的讨论。当食物被用作重要的情节或其他重要的叙事手段而成为文化冲突或融合的催化剂时,食物起着“意义食物”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海地餐馆重现了海地生活。海地食物作为文化调节剂,形成了双向社会场,刺激了人物对旧家园的记忆,也助其在新家园安居。
对马克来说,怀旧,不单是一种族裔起源丧失的失落感,而是一种超越种族认同﹑解除自我限制的途径。《当代小说中的伦理与怀旧》一书认为,怀旧并不一定代表着回归理想化过去的愿望,而实际上是在面对失望的现实时从伦理层面探索过去,这种伦理追求不能从美德和道德常识方面去理解,而是指“个人不同自我间的互动碰撞”【John J Su.Ethics and Nostalgia in the Contemporary Nove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2.】。这种互动在重审过去的过程中指向当前协商的状态,对流离失所的马克来说,饮食可以作为协商归属的工具,为他建立一种连续性。此外,食物记忆作为怀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用于和预设的女性/男性界限发生联系。食物在叙事中被确立为一种创造性语言,用于治愈或弥合移民后男女社会领域之间设定的鸿沟。与安扎尔杜瓦的女性烹饪经验不同,丹蒂卡将食物记忆与男性角色的怀旧联系在一起,动摇了女性/家庭与男性/公众之间的分界。
在《梦回古巴》中,与鲁迪丝的独立和足智多谋相反,她的丈夫鲁菲诺·普恩特在美国新家却因为流亡﹑被动和缺乏社会自主性而对故国家园产生怀旧情怀。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原籍国的分离使鲁菲诺产生了家国想象,故土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概念。他在新家的仓库中拟造了一个古巴世界:古巴雪茄﹑古巴朗姆酒﹑古巴音乐簇拥着他,他甚至在院子里种植水果﹑蔬菜和鲜花来回忆古巴农庄生活。“家”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理想,对怀旧的过去或乌托邦的未来的渴望。恰尔顿·映林(CharltonYingling)认为,“对流亡的研究往往强调流亡者与祖国的不连续性,相反,它应该被视为跨国建构的一个想象社区,目的是理解在流亡和归国过程中与原籍国和目的国都存在的脱离和重新融合”【Charlton W Ying ling.To the Reconciliation of All Dominicans: The Transnational Trials of Dominican Exiles in the Trujillo Era.in Crossing Boundaries:Ethnicity,Race,and National Belonging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edited by Brian D.B., and Simon W..U.K.:Lexington Books,2013,p.54.】。鲁菲诺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想象的古巴世界来解决失去故国家园的问题,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回归”,一种建立精神家园的努力,以缓解痛苦和困境并作为错位和无根的出路。女儿皮拉尔观察到,“只有当谈到过去和古巴的事情时,爸爸才看起来很活跃”【Cristina García.Dreaming in Cuban.p.138.】。鲁菲诺的怀旧也出于新家中性别权力的失衡。搬迁后,他的家长地位被撼动,因为现在妻子成了养家糊口的人。此外,鲁迪丝对鲁菲诺强势的性渴望也揭示了他在婚姻中的弱化和无力。鲁迪丝的赋权和鲁菲诺的无力表明婚姻中的权力动力并不总是有利于男性。不同于鲁迪丝的以务实精神为标志的跨国主义,鲁菲诺在新土地上重建想象家园的行为可视为一种由情感主导的概念性跨国主义,这通常是具有女性气质的跨国主义。因此,小说的怀旧书写也翻转了男性主导和女性被动的二元社会秩序。
在《褐色女孩,褐砖房》中,和茜拉对巴巴多斯作为剥削和苦役场所的痛苦回忆不同,她的丈夫迪顿·博伊斯将巴巴多斯视作童年天堂,并怀揣着筑房梦打算回归定居。迪顿的家庭概念常常和理想化的家园或某种程度的地方主义相连。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无知》中将怀旧描述为“由于渴望回归而造成的无法抚平的痛苦”【Milan Kundera.Ignorance.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0, p.5.】,昆德拉认为怀旧表明人物对失去的生活和文化以及甜蜜童年经历的渴望,这种渴望描述了一种不受现代性影响的感知景观。与昆德拉的怀旧观念相似,迪顿经常向女儿讲述童年故事。当塞琳娜问他:“家是什么样的?”他回答道:“巴巴多斯贫穷但足够甜蜜。这就是我要回去的原因”【Paule Marshall.Brown Girl, Brownstones.p.11.】。他的怀旧意味着对美国现代性带来的异化的拒斥与对原始家园的眷念。事实上,在各种低薪职业中挣扎的困境加强了迪顿的怀旧情绪。跨国学者认为,男性在东道国的定居往往面临失去性别特权的危险,因此渴望回国:“他们的低职业地位可能满足家庭内部的需求,但削弱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结果,男性希望回国以恢复因移民而受到威胁的地位和特权”【J.Itzigsohn & S.Giorguli-Saucedo Giorguli.Incorporation, transnationalism, and gender: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participation as gendered processes.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5, (39), p.897.】。迪顿亦然,作为无证非法移民外加黑皮肤的他遭受了一系列的职业失败,这种沮丧反过来强化了他回归故土体面生活的梦想。当得知他将继承祖国的一份土地时,他计划在这片土地上筑居。继承的土地意味着他在新家被剥夺的一切:社会地位﹑尊重以及诗意栖居。新家园改变了性别的社会动力结构,往往会给婚姻和性别关系带来紧张感。在迪顿阻碍妻子在美国筑家的行动时,妻子已悄然卖掉了他的土地,泯滅了他的希望之光。梦想破灭后,他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灵魂并走向死亡。小说揭示了弱势﹑非法和有色移民男性的家园建构是由他与祖籍国和东道国的内外社会场共同来定义的。象征意义上,家园梦的失落也解构了男权中心论,触及到男性群体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
在三部小说中,与东道国的疏远使男性角色产生了怀旧情结,过去与现在﹑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怀旧,作为反思﹑转化﹑生产和可能的治愈,体现了一种“情感跨国主义”【这里的“情感跨国主义”是指对于生活在美国的加勒比移民来说,他们可能无法维持较强的跨国实践形式,但仍然保留着对加勒比地区的情感想象和象征性联系,参看Wolf, Diane L.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Emotional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Struggles of Second-Generation Filipinos.in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edited by Peggy Levitt and Mary C.Waters, 2002, pp 255-294.】,因为它更多地关注如何在新旧家园叠加的背景下理解“存在”而不是成为“存在”。怀旧再现了一个时空空间,可以替代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作为回归的愿望,提供了目前通过想象重新审视过去的社会场,以避免和抵抗因流离失所造成的无法承受的精神负担。此外,怀旧被作家用作展示全球化性别意识形态的创造性手段,它通过男性在私人/私密空间中得到展开。在跨国社会场中对男性怀旧的再现推翻了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之间的明显区分,从本质上看,这是对理性与情感的社会区分的拒绝。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上,情感与理性是对立的,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生活活动的原则与动力受到推崇,而情感则被视为混乱,是人性中应该归顺于理性的部分。然而情感是判断的基础,也是认识的基础,如非德瑞克·伯瑟偌(Federico Besserer)所说:“女性本身不能动员情感来反对霸權性质的‘理性’,因为‘理性’无法与其所包含的情感体系区分开来。因此,一场理性的竞争总是包含着一种情感的斗争,而情感的斗争总是权力结构论争中固有的一部分”【Federico Besserer.Inappropriate/Appropriated Feelings: The Gendered Construction of 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in Gendered Citizenships.edited by Kia L.C.et al.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77.】。从男性角度来看,女性的情感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和非理性的,因为男性当权者声称理性统治世界。这种看似“客观”的权力方法“未能认识到权力在行使时内嵌的主观性”【Federico Besserer.Inappropriate/Appropriated Feelings: The Gendered Construction of 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p.77.】。实际上,理性和情感是互交互促的,因而作家得以手持理性的解剖刀,剖析情感,将其以逆向的方式与“客观的”男性形象相联。在这个意义上,怀旧作为一种情感,暗指男性群体的社会结构和精神气质的变化,成为全球化性别意识形态的一种“另类”象征。
四 结 语
根据性别地理学研究,琳达·麦克道威尔(Linda McDowell)描述了性别之社会建构的变化和程度,对此女性和男性经历的地方和空间各不相同。“通常,性别关系有明确的地理划分,因为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在妇女从属地位和相对自治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相应地,在男性权力和统治上也有较大差异; 在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别划分以及与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相关的象征意义上,也存在明显的多样性”【Linda McDowell.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12.】。琳达对自然化的性别划分提出了质疑,指出了性别关系在地理意义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她对性别划分和地理划分的阐释是基于国与国之间或国家内部,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仍然坐落于民族主义框架下,本文则以跨国主义为理论指导,基于对跨国移民家园制作的分析,对空间划分与性别划分的关系提出了进一步的质疑。与民族主义停滞的构图﹑有界或有型的配置﹑主体和过程不同,三位作家都强调了移民参与祖籍国和东道国社会之复杂和多样化的性别配置,超越了单一的性别主体性,把越界人物出入于不同文化﹑相互矛盾的各个方面呈现,以达其错综而不定的全貌,从而揭示跨国社会领域动态互构和多层交叉的特点:其一,跨国家园生产了一个双向流动的社会场,它具有开放性﹑创造性﹑适应当下的一面,也具有封闭性﹑想象性﹑回溯历史的一面。在这个社会场的穿梭往复中,女性移民在遗忘和记忆的博弈中获得了向上流动的生活姿态,从不在场走向在场;而男性移民在怀旧与现实的对峙中遭遇了男性气概的衰落,体现出下向流动的趋势,标示其主体性的退隐或丧失。其二,在跨国语境下,女性移民的家园建造多与公共领域有关,而男性移民的家园怀旧叙事更多地与私人和家庭场景相联,这也表明作家有意拆除男性/公共和女性/私人之间齐整的性别分工模式。再定居产生了一种新的性别意识,它溢出了决定男性/女性权利空间的地理边界,超越了主/仆﹑征服/被征服﹑男/女和夫/妻这些先入为主的关系,在跨国空间描绘了一条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替代轨迹。
从深层来看,美国加勒比裔小说蕴含欧、亚、非、美四大洲文化和历史,具有鲜明的跨国书写特征。性别作为跨国书写中家园维度的核心微观变量,所反映的移民历史、独裁政治、跨境经济、人口迁移等现象是重要的思想资源,纵深还原了族裔创伤历史、文化记忆及重建主体性的努力,提供了窥视加勒比性与美国性协商的窗口,对认识美国文化多元性/异质性具有重要意义,也提供了反思身份流动、多元认同、全球化等论题的切入点,打开了研究族裔文学的新视域。
Gender Geography:
On the Writing of Transnational Homeland
in Caribbean American Novels
CHEN Tian-ran
Abstract: In the Caribbean American novels,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home” reflects a heterogeneous process of transnational homes, which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division and gender division. On the one hand, the concept of home for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takes place in the social field between their old homeland and the new one, and is constantly blurr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nsnational entanglement of gender and geography has led to variations in gender patterns. The home narrative of female immigrants about forgetting and memory presents a contrasting textual significance: their American homeland painting shows the tone of open-mindedness and advancement, while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retaining the Caribbean home background color. The nostalgia narrative of men’s homes is related to the family private domain, showing a reducing trend of closed and dimensionality, expressing the crisis of retreat or loss of subjectivity. As a result, Caribbean American writers have overturned the neat opposition between the men/public domain and women/private domain, shaken up the traditional gender power structure and reproduced a new gender operation model in the transnational space.
Keywords: Caribbean American novels; transnational homeland; gender operation
【責任编辑:陈西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