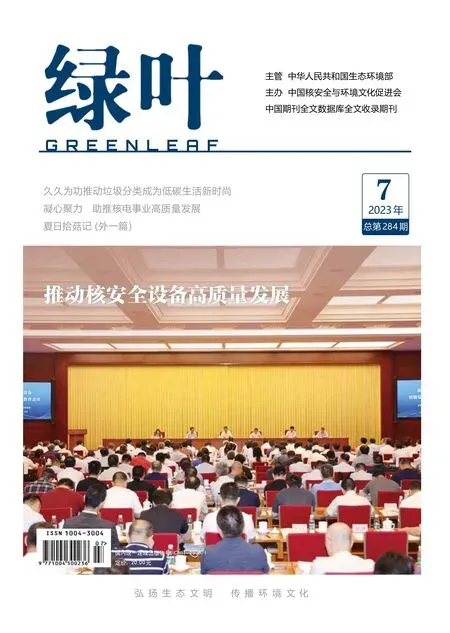家乡的鸟
2024-01-08彭宗怀
◎彭宗怀
我的家乡有很多种鸟。我认识的鸟儿也越来越多,不再仅限于乌鸦、喜鹊、麻雀之类了。这是荆山腹地的一个小县城,位于荆山之北。现在我所居之城,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鸟。鸟儿如人类一样,是自然界的一员。家乡的天空、大地、山谷、河流、树林、房舍,家乡的春光、秋色,显然是一个适宜鸟类生存的环境。在这里,鸟儿全然是任性的、纵情的,与人们融洽相处。如果鸟儿在某天猝然从林子消失了,我想,家乡的人们一定会感到非常寂寞。
一
县城虽小,街道上的香樟树却异常地高大繁茂,大多的树高超过五六层楼房。春分之际,天未亮,“啾——啾——啾”“咔——咔——咔”“叽——叽——叽”的鸟声便钻进屋子,如少年般清朗的声音,又如悠长的呼哨。细听,似小女孩细碎娇气的抱怨,又似老者的指责。这些声音像是很多鸟儿发出的,也像是一只鸟儿发出的。循声细看,是乌鸫立足于枝丫间鸣叫。乌鸫的身形并不美丽,全身黑色,只有嘴是黄色,眼圈也是黄色,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名字,经常把它误认为是乌鸦。其实,它的身形比乌鸦要小一半儿。乌鸦的叫声粗粝而又嘶哑,乌鸫就不一样了,叫声清脆婉转,百变多样,被称为“百舌鸟”。每个清晨,它总是用清澈而又花样百出的声音,慢慢地叫出云彩,叫出阳光。
自我在街道边的香樟树上发现乌鸫后,只要抬头在树间搜寻,总能见到它。乌鸫似乎已适应了城市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对于车水马龙的道路也不敏感,常单独在树间、草地上寻觅昆虫、浆果,见有人走近,才迅速飞到树上隐藏起来。乌鸫与人们有着极深的渊源,很早就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诗人王维曾专门创作一首《听百舌鸟》:“入春解作千般语,拂曙能先百鸟啼。万户千门应觉晓,建章何必听鸣鸡。”唐代诗人杜甫则挥笔写下《百舌》:“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知音兼众语,整翮岂多身。”刘禹锡的《百舌吟》堪称佳作,“笙簧百啭音韵多,黄鹂吞声燕无语”“舌端万变乘春晖,索漠无言蒿下飞”。这些诗人虽风格不同,却都提到乌鸫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婉转多变的叫声。生活中,有时难免疲惫不堪,甚至灰头土脸,但一觉醒来,听见乌鸫婉转动听的鸣叫,沉浸在它的声音里,就会感觉到清新的一天充满欢喜。
由乌鸫,我相继认识了红尾鸫、紫啸鸫、怀氏虎鸫、灰头鸫,还有中国特有的宝兴歌鸫。雨水时节的一天清晨,我在紫薇广场林中草地上看到一只鸟,这只鸟与众不同,不大不小,上体是橄榄褐色,眉纹是棕白色;下体是白色,密布圆形黑色斑点。穿梭在灌木丛中寻食,我小心翼翼地靠近观察,拿起相机正准备拍摄,它突然跃起,飞到一棵桂花树上。我猫着身子再次靠近。这只鸟落于侧枝上,双眼炯炯有神,盯着前方,一动不动。我一连拍了好几张照片。回家上网一查,原来是宝兴歌鸫。宝兴歌鸫竟然出现在家乡的山山水水间,实属罕见。我想,能在家乡的公园里拍到宝兴歌鸫,起码说明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鸟种越来越多。
身形较大的白颊噪鹛看上去,既有几分朴素,又有几分俏皮,更有几分机灵。一来就是好几只,动静大,在樟树间窜来窜去,或是落在草坪里,把枯叶翻得哗啦啦地响。它们专注地找吃食,根本没把周围的人放在眼里。
太阳从东山升起,光色嫩黄,如晨开的南瓜花,羞赧而明黄。起身出门,鸟儿影子多了起来,满眼的欢喜。大的、小的、黑的、白的,开始了工作前的运动。它们像清晨河边跑步、练剑、打太极的人群,有的在空中你追我赶,展翅翱翔;有的穿越街道,划过一道美丽的弧形;有的躲在树叶丛中,跳动不停。
清清亮亮的早晨,鸟声撕开蒙蒙薄雾,街道格外纯净,晨练的人步履轻盈,双臂舒展,像灵动的鸟儿奋起欲飞。
二
一棵果实累累的柿子树能够引来多少鸟儿?工作单位庭院这棵高大繁茂的柿子树上,从清晨到黄昏,无以计数的鸟儿来来往往,它们在树上吃柿子、小憩、抖被雨水打湿的羽毛、捕捉树上的小飞虫。
树上的常客是黄臀鹎,数量比麻雀还多。黄臀鹎常常栖于枝头的顶端,一落就是三五只。嫩枝似乎难以承受它的重量,摇摇晃晃。鸟儿如醉汉,悠悠荡荡唱着曲儿。一只鸟儿直冲天空,另一只鸟儿便紧随跟上,两只鸟儿在空中散开翅膀,追逐嬉闹,缠绕飞舞,刚回到枝头,另一对鸟儿又冲向了天空,很少看到它们进食,感觉它们就是来“秀恩爱”的。常有珠颈斑鸠藏于枝柯间,不细看,很难发现,拿相机拍照,拍上半天,人家就一个姿势,有些寡然无味。等到另一只斑鸠飞来,好像在一起嘀咕了几句,随之一起飞去。领雀嘴鹎和绿翅短脚鹎来得比较勤。领雀嘴鹎的羽色艳丽,鸣声婉转,在树上梳理羽毛,追逐打闹,翻飞跳跃,很是热闹。小满过后,柿子树叶子浓密宽展,柿果似围棋子,已密密麻麻从树枝里钻出,满树的绿色,几乎看不见枝干。有鸟声在枝间“啁啾”,仔细观察,原来是极小的黄腹山雀在枝间不停地跃动。鸟儿小叶片大,鸟身上的颜色淡,往往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只有它在跳动时,才能睹其真容,画面尤其美。有那么几天,金翅雀常常借柿子树歇息。它大小似麻雀,扇动着金灿灿的翅膀,站在树梢的高处鸣唱。嗓音甜美,歌声清脆动听,带着金属的质感,先是拉出一个高音节的长长的“吱……”音,跟随发出“嘀铃铃铃”的颤音,哨子般的歌声让人回味。盛夏之际,忽然发现金翅雀好似销声匿迹了一般,我一度怀疑它是冬候鸟,后来才发现它们都低调起来,隐于繁枝下安静地生活。
站在柿子树下一睹鸟儿真容是件不易的事。唯黄鹂鸟飞来歇息,耀眼醒目,总能看得见。“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读这首诗时,我尚年幼,便知有一种鸟名黄鹂。后来,我又读过很多关于黄鹂的诗,“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却从来没有见过黄鹂鸟。那天清晨,我早早地到了单位,跟往日一样,习惯地围绕着单位的庭院散步,柿子树上忽然来了一只鸟。它的翅尖和眼部为黑色,背部、腹部是鲜亮艳丽的黄,非常耀眼。看到它时,我并不知道它就是黄鹂,只觉得它就像一只从童话里飞出来的鸟,美得令人陶醉,似乎不像是一只鸟,却又实实在在是一只鸟。后来,我得知,那是一只黑枕黄鹂。它经常在林地、农田里捕捉昆虫。
俗话说:立秋胡桃白露梨,寒露柿子红了皮。熟透的柿子,泛红的树叶,远远望去,橙红一片。至隆冬,树叶落尽,树上柿子如一盏盏红灯笼,美不可言。冬日暖阳,柿红耀眼,各种鸟儿来来往往,热闹非凡。麻雀、喜鹊、画眉、山雀、白鹡鸰、松鸦、白颊噪鹛、啄木鸟等,纷纷登场。
最具观赏的鸟当数红嘴蓝鹊。
红嘴蓝鹊是一种体态美丽的林鸟,体背是蓝紫色,尾羽颀长,尾端白色,嘴红脚红,仪态端庄,雍容华贵。时不时地从周边树林里飞来,三五只在柿树枝间跳上跳下,寻得一枚熟透的柿子,张口叼上一大块,两翅平伸,尾羽展开,急速地向山中飞翔而去。
留几个柿子给鸟吃。庭院里柿子无人采摘,一个冬季,全部留给了鸟儿。这株柿子树,究竟住了多少鸟儿,除了柿子树,恐怕没有人知道。
柿子树下,园林呈阶梯状铺开。银杏树、樟树、桂树、石楠、茶花、月季、栀子栽植有序,亭台、木栏、步道掩映其中,如幽深的秘境。鸟儿藏在枝中、草地,忽而在树间,忽而在草地上寻找食物。
庭院里,鸟声盈耳,不扭捏,不嚣张,不牢骚,不敷衍。进进出出的人们,脸上漾着阳光般的温暖。
三
早晨,天空一片碧蓝,浓雾在河中缓缓流淌,平和的气氛混合着氤氲的水汽弥漫两岸。沿堤岸步道行走,是件很惬意的事。
河水被橡皮坝切断,形成梯级湖泊。白鹭成群,从浓雾里升起,在河谷上空不疾不徐地扇动着翅膀,来来回回。终于,在空中飞翔久了的白鹭,开始有意慢下来,遇有浅水处,停止扇动,落到石边,三只、五只,相继落下。随即,橡皮坝下的浅滩里,探出一排细长的脖子,耐心地守候着,静寂安闲,等待它们丰盛的早餐。白鹭临水最是好看。站立的白鹭倒映水中,实与虚的结合,具体与抽象的结合,两两对照,令人顿生无限遐想。
河道成湖,小䴙䴘便多了起来。起初,沿河两岸的人认为它是野鸭子,熟知的称之“水葫芦”,它身子滚圆,浮在水面上像个葫芦。我拍了几张照片,放到网上一搜,才知是小䴙䴘。初次接触“䴙䴘”这两个字,不知读啥,也太难写,总觉得怪怪的。后来才晓得“䴙䴘”一词用来形容走路不稳的样子,目睹了小䴙䴘上岸后那踉踉跄跄的怪样,便觉这名字起得实在是妙。小䴙䴘是捕鱼高手,看它漫不经心地游动,猛地潜入水中,起来时,嘴里含着一条小鱼,仰起脖子一口吞下,然后抖动羽毛,散去水珠。等待时机,再次扎入水中。小䴙䴘“凌波微步”堪称一绝。正当你仔细观察时,它竭力伸直脖子,抬起身子,扇动翅膀,双脚踏着水面,疾速奔跑,“噗噗噗”地漂去好远,身后只留一串水波。
白鹡鸰是河谷里最常见的鸟。它体形瘦长,嘴尖、尾长,羽毛是黑白两色,落在那儿,尾巴上下摇摆,飞行时一上一下地画着波浪线,发出“叽铃叽铃”的叫声,非常好辨认。白鹡鸰不太怕人,喜欢在水边浅滩处活动,疾速地跳跃、奔跑、摇动尾巴。河滩有了白鹡鸰,十分热闹。
溪水叮叮咚咚奏着小调,两岸杨树、柳树的枝条在溪流上搭起凉亭,枝条坠入水中,随水流摆动。岸边,蒲草、辣蓼子、水蒿葱绿。蒲草举着“蜡烛”,直挺挺地站立着,偶有翠鸟呆呆地立在上头,纹丝不动。一群小鸟站在枝条上,抖落水花又扎入水中。河谷里,看到最大的鸟当数苍鹭。它身高接近1米,嘴长、颈脖长,腿也很长,羽毛是苍灰色,立在河水中,很容易辨认。苍鹭喜欢独来独往,有时混在白鹭中,也总是与其他鸟儿保持一定距离,立在那儿,伸长脖子,目视前方,半天不动,雕塑般肃穆。那份孤傲,那份寂寞,总让我心生敬佩。立在水中一动不动的苍鹭究竟在做什么?我也一动不动地观察它。原来它是守株待兔的高手,在等候过往鱼群。猎物一旦出现,它便立刻伸颈捉了。当我大着胆子靠近它时,它也是不紧不慢地扇动着宽大的翅膀,脖子后缩,腿脚绷直,优雅地飞去。
鸟儿是大自然的精灵。在河溪里观鸟,许多鸟都认识了。白腰草鹬、长嘴剑鸻、褐河鸟、翠鸟、沙锥、黑水鸡、白冠燕尾等,都是在河溪里认识的。河溪里有这么多鸟儿,是我没有想到的。原来那种污水泛滥、沙石翻挖的景象不见了。两岸山中,草木葱茏,郁郁茂繁,蝉噪林静,鸟啼山幽。河边,一株大柳树上,坐满了珠颈斑鸠。
面对大自然,肃立河边的我,没觉得单调,没觉得孤单,融入其中,仿佛自己就是一棵树,一只鸟,只有敬畏。自然是书籍,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鸟来来去去,不知疲惫,我们知道的又有多少呢?我想,我所能回报的,只有洗净两耳,擦亮两眼,倾情谛听,仔细观瞻,行走在光阴深处。
四
荆山腹地,山垭上、坡埫下、林川里、河湾边,一个村百十户,散居其间。村子里,农户越来越少,草木越来越茂盛,鸟声越来越响亮。
农事中割麦插秧的时候是最忙的。麦子熟透,得赶紧收割,还得赶紧抢季节犁地插秧。越是忙,鸟儿叫得越是欢。“豌豆拔过,割麦插禾。”这鸟,清晨便鸣,好像在催促人们赶快下地干活;上午、下午依然连绵不绝,好像在提醒人们不要懈怠;到了晚上,它还在叫,“快快割禾”,生怕有人误了农事。大多的时候,叫着“布谷……布谷……”声音由远而近,像从悠远的山谷传来,而又由近及远,余音在天际间,久久回荡。婉转的声音里,沾着晨露,带着泥土的芳香,听了,似乎嗅到了风中那浓郁的麦香。童年,一到麦收,总跟着大人在田间捡麦穗。烈日当空,麦浪翻滚,勤劳的农民,头顶草帽,脖子上搭条毛巾,挥汗如雨。那丰收的场景,那远去的欢笑,只在记忆深处重逢。现在,村庄渐渐消失了,村子里的人也渐渐消失了,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耕牛换成了拖拉机,镰刀、簸箕、叉耙、石磙已派不上用场,唯布谷鸟依然嘹亮地叫着:“布谷、布谷”,声震八方。对于布谷鸟,我既熟悉又陌生。一次观鸟,听闻布谷鸟鸣叫,端起相机,拉长镜头,拍下图片,而后整理图片细看,其身形仍然模糊不清。想近距离观看布谷鸟,真的好难。布谷鸟又称杜鹃,与其相关的传说和诗文颇多,常见的有大杜鹃、小杜鹃和四声杜鹃。
小鸟依林而居,与人为邻。村庄周围,栽有果树,种有庄稼,兴有菜园,养有牲畜,百鸟竞相栖息,鸟声无处不在。常见的喜鹊、麻雀、乌鸦、燕子自不必说,难得一见的金翅雀、松鸦、灰椋鸟、黑颜凤鹛、斑姬啄木鸟渐渐多起来了,就连孤独的伯劳也时常遇见。
最早认识伯劳,是在乐府诗中:东飞伯劳西飞燕,皇姑织女时相见。每年都见到燕子,可伯劳没有见过,也许见了也不认识。去年秋,我开始用相机拍鸟,有天去上里等红腹锦鸡,红腹锦鸡没来。田边一株香椿树,树叶落尽,仅余枝干,光秃秃的枝头落有一鸟,头大尾长,背棕红色,黑色的翅膀搭配长尾,像穿了一件庄重的礼服,非常漂亮。用相机拉近镜头,眼睛又黑又亮,喙又粗又壮,脚爪有钩;嘴里含着一只蚱蜢,停在枝头不动。蚱蜢还在挣扎,过了片刻,待蚱蜢完全不动弹了,这只鸟才将蚱蜢吞进肚里。然后,快速地扇动两翅,向空中飞去,转了一圈,又落到原处,东张西望,搜寻猎物。查了资料,才知它叫棕背伯劳,有“小猛禽”之称。后来,又见了几次,对它的了解更深入。它总是孤零零地出现,或立于枝头,或站在电线上,也不喜欢鸣叫。听闻了一些关于棕背伯劳捕杀猎物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说如果猎物过大,它会将其挂在有刺的树枝上撕着吃。吃不完,晒成肉干,饿了再食。如此凶残的吃相,我没见过,真实与否,不得而知。除了棕背伯劳,我还遇见过红尾伯劳和牛头伯劳。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聒噪的蝉声从绿荫中传来,一波接一波,吱吱的长鸣盖过鸟声。鸟儿似乎都躲了起来,时常只有清晨和傍晚才可见到。狗尾巴草果熟籽实,穗儿摇曳不止。山麻雀钻入草丛,闹得更欢,啄得更响。人走近狗尾巴草,惊得成群的山麻雀从草丛中飞起,然后“簌”的一声如雨点般又落入远处的草丛中。
田野里频频出现的是俗称为“野鸡”的雉鸡或竹鸡。它们时常结伙,在田间地头,甚至在山路旁,在灌木丛间昂首巡视,或从坎边滑翔而过。在你窥视间,它似乎已发觉了你猎奇的目光,转身便隐入草丛里,或“呼啦啦”飞走。很多时候,你可以远远地看见,它们慢条斯理地行走在田野里,走一路,扒一路,一路走,一路吃。若在清晨,你总能听到“嘘叽叽,嘘叽叽”的叫声,洪亮悠长,气韵充沛,节奏不乱。寻声搜寻,竹鸡隐于草丛间,在求偶?在约会?始终是个谜。遇见“外敌”,雄鸡撒开翅膀,昂起头,憋着怒气,挺起前胸,顶过去,喙嘟嘟地啄下去,直到另一只竹鸡仓皇而逃。
自爱上拍鸟,立版的鸟儿我拍了上百种,飞版的鸟儿也拍下几十种。鸟的数量如此之多,为何我们很少看到鸟窝。有些鸟有窝,有些鸟不需要窝,大多的鸟只在繁殖期和育雏期才筑巢建窝。而我们人类,有的家庭购了一套又一套房子,深深地把自己束缚住。天高任鸟飞,鸟儿活得潇洒自在。
我的家乡,鸟儿实在多。尽管我是个“菜鸟”级别的观鸟人,当我将心贴近自然时,开始用新的视角看鸟类,周边的鸟,它们的名字、它们的生存智慧、它们之于人类的作用,便会勾起我凝思。面对自然界的万物,我依然保持一颗好奇心,走进真实的自然里、时光里、内心里,心里头总有一群鸟儿正展翅飞翔。它们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