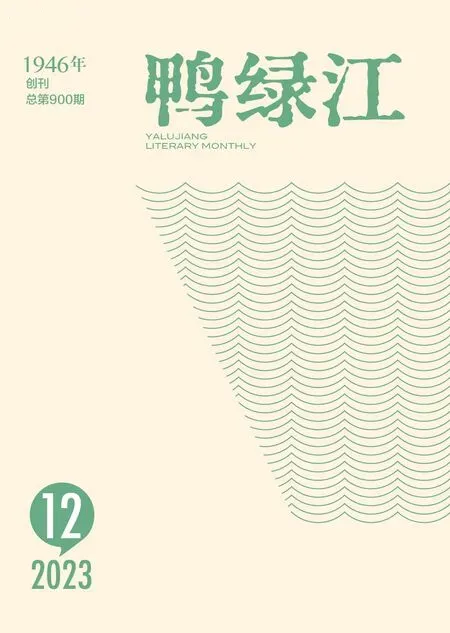在记忆里震荡,从现实中远行
——《鸭绿江》“海外华语小说速递”综述
2024-01-03戴瑶琴
戴瑶琴
2023年,夏周主持的《鸭绿江》新设栏目“海外华语小说速递”,集结了欧美亚不同代际的优秀华语小说家,既向海内外读者持续推介小说新作,又以集体力量打磨华语文学的独特性。夏周在开篇语中阐述母语写作对海外华人的意义:“小说的迷人之处不是简单还原一个故事,而是更深入地解剖世情和时代的肌理,与读者在更深层达成共鸣。从这个角度说,母语写作更容易实现准确表达,也更容易寻找到内心的归属。”①11篇作品以“世情”和“时代”为关键词,在作品—作者—读者之间架设共情的通路,从人物心灵向度探索能够抵达人性深处的小径。
陈永和的《贞姨》、唐颖的《生活与生活之间》、陆蔚青的《居酒屋》、沈乔生的《暴雨》、陈济舟的《背岛》、凤群的《暮春之雪》、江岚的《癫痫》、张惠雯的《痕迹》、王婷婷的《起点》、苏瑛的《末秋》、唐简的《漫长的一天》,这些小说触及生活的不同面向,在历史与当下的交错中,在梦境和现实的参差中,耐心地打开主人公埋设于时间丛的谜团。面对释疑的契机,他们放下重重顾虑索求一个答案,事实上也给自己提供直面情感缺失或人性弱点的机会,以便今后人生无须再负重前行。
栏目内部分作品直接跳出海外华人身份圈层,落地于写人,且又将写人落实于写情。陈永和《贞姨》是包裹时代、性别、家庭等论题的复合式故事,小说没有惯常地叙述一位“另类”女性的一生,而是别致地确立1983年——她的39岁。为什么是这样的数字?改革开放初期背景恰好为小说期待的传统/现代互渗提供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此时贞姨也处于青年向中年的转折。她独身,住在“公园里5号”红砖洋楼,平日化妆,蹬着高跟鞋,穿全色旗袍。装扮、年龄及生活方式都将她与周围的人群区隔开来,直到一只小狗娇娇闯入其私人领域。娇娇随即拉起贞姨与世界的纽带,娇娇产崽更是将她的闺房首次向公众敞开。“娇娇当母亲啦……贞姨的眼眶湿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慢慢地从脚底升上来,身体暖和起来。”贞姨见证着一次新生,她本人也由此获得重生。她开始不自觉地主动投入烟火日常,逐渐理解他人,也逐层化解个体孤独,她突然有能力领会生活给予她的善意。她骂赵三言语放浪,可此刻的骂,“已经是波涛翻滚之后的风平浪静,面上还抹着一缕阳光”。精心制作的带子掌控娇娇,虽能拴住它以防乱跑,但无法阻止两条狗的自然交配。贞姨从娇娇生育事件中,切实感知本性的力量,并借此修正其处世哲学,调整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洋楼成为隐喻,贞姨半生画地为牢,只有每天开窗换气的时刻,透露与外界的沟通,百叶窗半开半闭,娇娇的到来与相伴,才令她有勇气投奔现实。
如果说《贞姨》重点在人的经验,那么唐简的《漫长的一天》则跟踪人的心理。东方娜姿正绝望地潜水,以此缓释苦闷。“她在不断地进入并揭开一个个未知,她觉得自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静谧被吸纳进她的每一处毛孔,与此同时,自由发散开来,如水一样望不到边。”为了躲开常均和朱利莲,她独自潜水和攀岩,因受不了两人亲密态对其施加的情感撕咬,她只得从高强度运动消耗中获得心理疗愈。虽然东方也曾任性地与汪冰相恋,两人皆因爱被辜负而互相取暖,但她无论对常均还是汪冰,都无法启齿内心的真相。“她是如此地孤独,真的,孤独,不知在哪儿安放自己。”东方渴望陪伴,又不敢主动求取陪伴,转而通过不断地下潜和攀登,向自然求索,她恍然意识到人生困境“不过是在极限过后再撑一撑,原来这就是她今天命运的底牌,她先前自是预见不到”。小说给定了较为模式化的光明前景,东方在自然启示和个人努力的双重作用下顺利跃出情绪的谷底。
沈乔生的《暴雨》发掘深埋于特定年代的人性温情。小说主体是李石及其室友建构的人物侧面描写,从“他视角”还原李石与辛媚相识、相恋、相别离。令人难以释怀的并非辛媚的意外身亡,而是真挚恋爱尚未来得及公开,李石无法对人言说锥心之痛,只得将所有情感倾注于一块冰冷的墓碑。小说缭绕着年代、情感、伤痛的气息,从青春岁月切入解读人性的善恶,这是“新移民文学”成熟的写作模式。创作者基于记忆发掘其难以忘怀的人或事,借此,读者看到纯真爱情被戕害,美好的人陆续消逝。目睹即将握在手的幸福瞬间被不可抗力生硬夺走,而个人对此无力招架,这种痛苦是李石这代人最意难平的心灵创伤。李石的生命热力随同辛媚的死亡而暗淡残喘。
族群是海外华文小说的最核心论题之一。历史学家王明珂认为:“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他者的异己感以及对内部成员的根基性情感。族群成员间的根基性情感,来自‘共同祖源记忆’造成的血缘性共同体想象。”②爱尔兰华文作家颜歌曾以英文写作小说《一次地道的对话》,作品指向一个重要的族裔问题,即少数族裔存在无形的边界预设,一方面对话客体会给对话主体设限,另一方面,对话主体也不断自我设限。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及研究,一度专注前者,由此夯实以事例诠释中外文化比较,而忽视后者的事实存在。颜歌提示,主体的自我设限往往也是主客体无法顺利沟通的要因。凤群的《暮春之雪》是根植“根基性情感”、完全聚焦少数族裔的他国故事,它摆脱海外华文文学常见的构思和行文,以一种读者并不习惯的“翻译腔”文体记述加拿大的南美移民家庭。这部小说采取“新写实”写法,厄尔瓦多、玛利亚、胡塞尔,夫妻、父子缠绕的矛盾冲击着被集体努力经营多年的家。厄尔瓦多和玛利亚带着两个孩子,从哥伦比亚移民加拿大,结识了瓦伦蒂娜和老谭。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为了在加拿大生存,于法语班相遇,从此开始互相扶持的加国生活。厄尔瓦多和瓦伦蒂娜发生了婚外情,玛利亚隐忍二十多年后,终究决定告别猜忌和惶恐。小说令回忆和现实交错出入,以厄尔瓦多的心理为中心,令其明白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最看中的又是什么。他明确自己已对玛利亚及家庭产生深刻依赖,它无法被随意地、随时地抽取。作品具有典型的外国小说中国译本的语言格调,或许这是创作者的一次文学实验,以译介和原创并置的行文营造陌生化效果,但也引发了一些阅读的滞涩,小说滑入“讲故事”的类型小说写作范式。
华人群体在“落地”过程中需要处理婚姻和家庭问题。代际关系及由其延伸的教育,是海华写作的热点,其中既包裹着文化差异的张力,又折射强烈的当下性。近二十年美国华人小说中的代际书写,浮现一条主线,是代际沟通的无效→起效→有效,由此形成两项推论,即代际矛盾从冲突到化解、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从反抗到接纳。《起点》讲述“听妈妈的话”的过程、结果与效果。任丽娟是典型的中国母亲,小鹏自然地领受她的一切安排,密不透风的中国式家庭培养,都会以母爱为借口,一边给孩子穿上盔甲,他们由此可以自动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危机,因为始终有妈妈在;一边给孩子建造无菌房,一旦他们踏出房门,就丧失机体与心智抵抗力地在社会“裸泳”。母强子弱隐藏着母亲的敢想敢做、孩子的敢想不敢做。小说依然塑造母子间的默默对抗,抛出问题,即华裔移民家庭想选择与外国人联姻,进而巩固家族的在地。任丽娟要求小鹏执行,其根本目的并非自己生活得更好,而是认定儿子此后人生更为平坦。代际矛盾一再被推至新移民扎根进程的前沿,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即母亲确实都以孩子为出发点,规设其发展路径。我认为很有深意的一点是,“小鹏从小就能读出母亲细微表情里的各种她本人或许都未觉察到的内心活动”,如果顺着这条线索开发,那么代际主题可能被激发出更多新意。很多文学作品会将孩子直接归于弱,而略过其强,实际上,他们才是最了解母亲的人,出于对母亲的爱和自己心底的良善,从不揭穿这一点,默默替母亲收藏着或掩饰着她全部秘密。若从该视角重新审视小鹏的隐忍,他的平和与躲避实则源于其不愿意在外国继父面前表现他们母子存有矛盾,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母亲。我想,换位思考,反思儿子对母亲的付出,会引导代际关系的重构和重述。
苏瑛《末秋》也是教育题材,特色在于选取了海外华文小说很稀缺的海外辅导班话题,这是强烈混杂着中国特色和他国生活的当代故事。小说触及移民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盛辰在一家教育中心从事中介和补习的工作,她本人从父母家庭辅导和辅导班外力辅导双重补给下成长起来,而当前又投身教育业。她指导的丽兹、卡萝、奥塔娜,恰好是三个性格迥异的移民家庭女孩儿,她们正复制着“盛辰之路”。亨瑞因盛辰“不学那些拼命美国化的移民,有别于土生土长的亚洲女孩儿”而格外欣赏她,可教育机构的作用,却是培养合乎要求的美国化移民。父母皆希望孩子可以挤进好中学好大学,以此改变自身命运,获取上升通道。盛辰在严格家教中缺乏社交能力,也缺失爱人的能力,她甚至向学生夏琳请教,如何了解异性的想法。遇到私密性话题,她更会本能地用食指封住嘴巴,既不敢直面他人,又不敢袒露自我,步步为营的处世策略,已刻入“华二代”的骨血。
在技术层面分析,设定时空域,且进行文化比较是创作者熟练的写作手法。“比较的视野本质上是一种俯瞰的视野,从‘此时此地’抽离,来到多样性的‘上空’,从宏观开始领略,然后慢慢聚焦到微观,也就是从森林开始,慢慢聚焦到树木。”③唐颖的《生活与生活之间》的开篇是纽约中央车站42街与上海南京路的空间交错。生活与生活之间,是一个个日常生活态的交叠。正当“她”感叹安分守己的生活难度之大,老友吕鑫出现,并牵引出共同的朋友浩伟。“时间终究还是把我们腐蚀了。”“腐蚀”一词很精准,她、吕鑫、浩伟都在动态庸碌生活中慢性地耗尽生命力,他们变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无爱无恨又无趣的人,既循规蹈矩,又冷漠趋利。Lucy的自杀,曝光吕鑫和浩伟两人的秘密,他们都还爱着她,格外珍视她,一个是明线联系,一个是暗线惦记。小说深刻剖析了一代新移民的特质:“他们这代人太关注眼前的忧患、可以计算的利害得失。即使出了国,仍然带着国内的心理结构。”三个人之所以逐步陷入无望,皆因其权衡利弊后,一致做出了必要的舍弃,即放弃了理想,放弃了爱。生活与生活之间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想,表面上是人与人各自活着,实则是在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的中间地带,所有人被滞留此处,没有勇气冲破现实,又不甘心放弃理想,进而演绎出新移民的一种新型徘徊。自20世纪60年代“留学生文学”以来,海外华文文学一直强调夹在两种文化间的悬浮,它是较为抽象的,研究者也常常从宏大视角解读文化差异,而唐颖令悬浮具象化,回到个人,回到细节,从人性深处解剖新移民“缺氧”的痛苦,即沦陷于现实与理想夹缝中的了无生趣。
江岚的《癫痫》运用平行蒙太奇艺术处理,天晓居于时空中心,姑妈的故事(过去)与雇主的故事(当前)形成对比。虽然两人的背景与成长具有巨大差异,但都患有共同的隐疾,这严重干扰其正常生活,她们特别注意自我保护,担心因个人秘密泄露而遭受歧视。天晓和黄医生成为联结中外女人的纽带,一个知病一个治病。江岚从国族和种族视角表达人类命运的相似,确立信任与爱能消弭一切隔膜。比较视域掌控小说全篇的叙事走向,从大的方面看,是两个国家的人;从小的方面看,是两种处境的女性。弱者姑妈和强者露易丝,在疾病面前一样无助,小说导向共性结论:个人应该做的永远不是逃避,而是积极面对。
栏目中有三篇小说重视描摹“时刻”,作家从文学细部拓进海外华文小说的精致化向度。张惠雯的《痕迹》展开诉说痕迹—保护痕迹的叙事逻辑。小说以“我”为圆心,聚拢“痕迹”群。对“我”而言,痕迹是人生中一个个漠然状态,“我”“漠然地对待人与事,漠然地隐忍”。因“我”是被原生家庭抛弃的孩子,“我”的母亲实为“我”的姨妈,“我”承受纷至沓来的外界羞辱,无法消除情绪的分裂,故而离家是“我”的必然抉择。母亲(姨妈)病逝,“我”被动地回到人群中接受各方审视,生母家庭责怪“我”对他们的无情,养母亲戚埋怨“我”对他们的无义。只有当“我”独自守灵时,“我”才得到机会释放自己——“我”可以哭了。“我”撕开“漠然”的痕迹,触摸痛苦的遗迹:“最让我悲伤的并不是她死了,也不是我的遗憾,而是那种令人恐惧的空虚——一个对你来说曾那么重要的生命突然消逝、它留下的痕迹也会慢慢淡去直至全然消失的巨大的空虚。”“我”未料想到,这一刻“我”竟又触碰到母亲(姨妈)的情感痕迹。她曾经的恋人在灵堂外徘徊观望了两天,两人互为对方生命里无法抹除的痕迹。她曾经决定与他私奔,“很多年以后,那件事像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其实,我几乎不再想起曾有这么一段插曲存在。偶尔这件往事从心头掠过,也像一片无意义的陈旧信息,不再勾起任何情绪。”“我”明知道他是我们三口之家的破坏者,却不忍心驱赶他,他向“我”和盘托出母亲(姨妈)对“我”的爱,这仍是“我”根本不曾察觉的痕迹。小说的收束很有力,母亲(姨妈)火化前一晚,父亲悄悄来了,他非常仔细地擦拭相框,如同擦拭遗留在母亲(姨妈)生命里的某种痕迹。我想,作品最大的魅力在于每个人都知道那些沉默的真相,所以各怀目的地迫切除痕,但人力永远只能淡化其形迹,它的结构早已印刻于生命河床里。
陆蔚青《居酒屋》描述“我”和罗西的一次闺友私聚。音乐会后,我们来到井三的居酒屋。两人很自然地聊起各自家庭。罗西是叙述者,“我”是倾听者。她吐槽婚姻痛点,与丈夫老戴之间存有难以弥合的裂隙,转而追忆先前与阿生的一段虐恋。小说有一处重要情节,详述罗西微醺后泊车,“我站在路边,指挥她向左再向右,向右再向左,她还是泊不到路边。其间终于有一次,貌似泊好了,却离路边有三尺远,好像泊在路中央。于是罗西又上了车,努力再试。就这样,我们试了很久。终于泊好了,虽然看起来歪歪斜斜的,但总算是泊在路边。”泊车过程呼应罗西情感的起落。周边人围观泊车,如同观审我们的人生。谁都无法透彻了解他人,却又执拗地将个人想法附着他人。小冬必定也爱着阿生,可她只默默守候,同步阿生的悲喜。所有人都以为井三是日本人,可他实为中国西安人。闺友俩似乎参透了命运迷局,女人反复而艰难地努力就足够,因为旁观者的善意,“我们将生活中的某些酸涩的时刻都忘记了”。
陈济舟《背岛》从记忆枝丫中岔开一段未表的故事,文本洇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潮湿调性和暧昧文气。他(俊杰)要“寻”回出家多年的大哥,打听到俊宏可能栖居的山上寺庙。主人公家族虽有离家传统,习惯了漂泊,但“一辈子,他心里都在想着一个地方,想着一段时光。一辈子,都想回去,可就是弄不清楚究竟是犯了什么错,做了什么选择,才让他与那片土地和最初的信念渐行渐远。”俊杰探访佛寺,大殿上众多神佛照见其内心惶惑,直至遇到明海,他才得以从迷失中觉醒,旋即沉醉于一场白日里的梦。他去藏经阁拜访住持,一路如徜徉无穷宇宙,盘旋的白蚁,隐喻他蠢蠢欲动的欲望,而白蚁肆意侵蚀压在书堆下的人,则隐喻他受各种欲念的摆布和牵制。就在绝望和希望的煎熬中,若隐若现的大哥为其指点迷津,“路上有个人在吃力地攀登,不也正是自己?再高一点,要到云端了,于是便看见了整座山、整座岛,岛这边是村庄,岛那边是城市……”小说在清洗自我的同时,探究社会问题,即“一个人一辈子不下山,守着这寺,外面天大的动荡打过来都没事,最后却还是从里面坏出来”。一城一村一寺一人一像,《背岛》以古雅的意象群演绎中国水墨的抒情美学,呈现海外华文创作坚守的中国古典审美。
“海外华文小说速递”栏目,深耕海华文学的常设主题,即历史、年代、家族、人性,题材分布中国故事/他国故事,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语言。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应该可以从语言中捕捉住人物特性,换句话说,虽然由作者写出所有人物,但每个人应是自己在说话,有符合其生存处境与性格特质的语气语调,而不是所有人都表现为作者本人在说话。我们从阅读中感受作者揣摩每个人说话的方式,替他们说话。同样,小说在推进中,人物越扎实,就越容易脱离创作者既定的轨道,他们表现出对命运的表达欲和主导力。我们从栏目部分小说中看到一种隐隐的预设,作者受写作规划的一些约束,而用笔力圈定人物的自我成长,读者由此获取意料之中的阅读感受,作品给予阅读的新鲜度不够、冲击力不足。
《说文解字》解文,错画也,强调其纹理交错性。中外文化比较始终是海外华文小说的重点议题,创作者将“在地”书写放置于具体事例,从地域差异反映中外个人观和家庭观的异同,再导向两种文明伦理观和文化观的对比。我认为,这一创作思路曾支撑起海外华文小说于独特性,但又限制其持续发展。创作者着力于差异论,从故事性层面下功夫,以戏剧性演绎冲突论。纵然事件更为曲折、命运更为跌宕,创作者实质输出的发现仍是常识性论点,并未体现出来自不同代际创作群体的新实践与新思考。社会学者刘瑜指明现在进行时的“文明的冲突”之内涵,她认为亨廷顿描述的文明冲突,“指向一种全球性的、大规模的、最后很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的东西文明对垒,但是在现实中展开的文化冲突中,西方碎裂了,东方也碎裂了,相向而行的星球不但没有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因为内部的张力而不断分解。一场大的冲突分解成无数小的冲突,一场总决战分解成渗入日常生活的绵延斗争。”④这一观点很值得海外华文创作者反思。华人群体之所以总觉察自己与故乡、与他人确有隔,主因是其强调故乡/他乡之变,而略去自我之变,所持基本立场是以“己”不变应“他”百变,继而在单向认知过程中衍生出对现实的不满、对现状的不解。东西方文化都经历着聚变和裂变,文化因子溃散后游弋于世界,真正的文明冲突以日常生活为主战场,因而将中西文化冲突从概念化、预设性的宏大叙事中卸力,是突破华文小说模式化“在地性”书写的重要发展方向。
海外华文小说刻画“在地”与海外华文小说建构“在地性”指向相异的研究维度。前者,创作者从多视角描述移民在他国的生活,环境、场景、家庭、职场中饱含丰富的地域特质;后者要求创作者从融入进程中观审当地文化特性,这并非生硬地将中国文化设定为他者,华人移民在地化过程中,中外文化之间自然会形成交流态势,种族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等生发为建构在地性的维度。需要指出的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在地性”,不仅是作品对当地生活的传达、作者对当地生活的体验,而且也应纳入华文文学整体与所在国文学之间关系的思考。准确地说,文学作品和文学生态构成海外华文文学“在地性”的两翼。
注释:
①夏周:《另一个维度看世界——写在“海外华语小说速递”前面》,《鸭绿江》2023年第1期。
②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8-29页。
③刘瑜:《可能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3页。
④刘瑜:《可能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