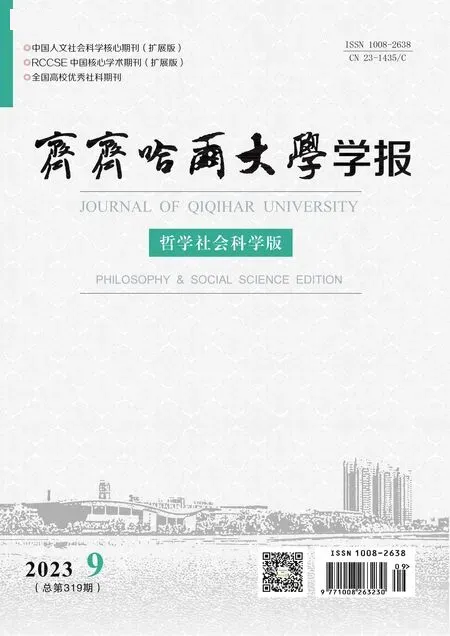传记文学《南京大屠杀》的中国抗战精神书写
2024-01-03汪顺来
汪顺来
(常州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民不能忘却的苦难史。2014年,中国政府将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永远铭记那段历史并警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勿忘历史、珍爱和平”。南京大屠杀已经载入历史档案,被列为“中国记忆遗产”和“世界记忆名录”。为了寻找二战中的“中国记忆”和恢复历史真相,让世代子孙勿忘国耻,并表达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坚强决心,美国华裔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 1968-2004)创作了《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1997)(以下简称《南京大屠杀》),将历史融入传记,以传记重写历史,揭示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暴行,讴歌中国人民和世界友华人士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维护人间正义,谱写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大作。“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1895-1967)的小说《大江东去》(1940)将历史、想象和记忆交织在一起,展示了南京沦陷前后和大屠杀发生时的南京想象,是反映南京大屠杀最早的一批文学作品[1]。语言能够展示文化的力量。英语国家的人们记住了二战历史上德国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对南京大屠杀却选择了集体失忆,甚至混淆视听。为了还历史以真相,告慰死去的同胞,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严歌苓、哈金选择用英语创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人民的创伤历史,从而让南京大屠杀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The Flowers of War, 2011)和哈金的《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 2011)分别聚焦于“国际安全区”中的圣玛丽教堂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本是人间净土的教堂和学校被侵略者践踏成人间地狱。前者塑造了一群面对暴行敢于赴死的妓女形象,上演了一场道德大义般的拯救;后者通过塑造院长明妮·魏特琳的西方圣母形象和高安玲、本顺等一群普通中国人形象,凸显其受难与拯救的核心主题[2]。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1997)超越了大屠杀文学叙事的创伤性审美意义,将日记、图片、回忆录、访谈等第一手资料杂糅到历史书写和文学叙事中,重构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为南京大屠杀中罹难同胞立传。《南京大屠杀》不是简单的大屠杀文学书写,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记,全面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精神,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奋勇向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一、《南京大屠杀》:中华民族的历史传记
张纯如是一位英年早逝的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生前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华人在美国的真实生活情有独钟,坚持以传记文学的形式再现华人的历史境遇。她的《蚕丝——钱学森传》(Thread of the Silkworm, 1996)记述了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平以及钱老在美国鲜为人知的遭遇,是科学家传记中的杰作;《南京大屠杀》(1997)是她用悲怆的历史和浓烈的民族情感为30万遇难同胞而作的集体传记;《华人在美国:一部叙述史》(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2003)中,她基于美国华人150年的移民史,揭示了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和华人的不公正待遇,是所有华裔美国人的历史传记。张纯如的创作穿行于文学与历史、历史与传记之间,集中展现了她高超的创作智慧。
(一)文学与历史的理性选择
张纯如的创作穿行于文学与历史之间,建立起文学与历史的整体观照。由于人们对历史的认知随着岁月的久远会逐渐淡漠,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需要对历史给予反思性批判。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南京大屠杀早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日军侵华罪行史。但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有意纵容导致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的甚嚣尘上,企图否认史实,混淆视听,还不断以文化渗透的形式悄然布局,妄图模糊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为此,张纯如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主义热情创作了《南京大屠杀》,重建中华民族的记忆共同体。张纯如在文学和历史间搭起一座桥梁,展现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的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
文学与历史的悖论关系表现在文学的虚构性和历史的真实性之间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但是新历史主义批评破解了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的对立,开启了文史互动和对话的渠道,重构文化语境。新历史主义批评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和历史书写的文学性,是一种“语境主义的文学研究方式。”[3]历史不仅仅是背景资料,还是被重新定位的阐释性文本。正如艾布拉姆斯指出:“历史本身并不是一系列固定不变的客观事实,而是像跟它互动的文学一样,本身是一个需要阐释的文本。任何文本(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历史文本)都是一个话语,虽然它可能旨在表现、反映外部的真实世界,但事实上是由所谓的‘表征’组成的。”[4]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与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路易·蒙特罗斯主张的“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一脉相承,共同阐释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文化诗学”。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践行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主旨,在文学与历史的悖论上作出了理性的选择。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需要借助于文学文本和语言、文化的力量,才能更好地保存和流传下去。通过阐释该文学文本,人们可以走进历史和感悟历史。同时,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更有效地发挥文本的历史价值。因此,《南京大屠杀》很好地体现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强调的“文本的历史性”。对于“历史的文本性”,张纯如坚持在历史的语境中寻找人性的真谛。为了恢复当时的历史语境,张纯如从大量的档案材料、日记、证词、照片等历史文本中获取第一手资料,重述那段创伤历史,将“大历史”分解成一个个叙述者的“小故事/小历史”,重塑历史人物形象。
(二)历史与传记的巧妙结合
张纯如是历史学家,也是传记作家。她善于将历史与传记巧妙结合,书写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人物传记和传记背后的历史。《南京大屠杀》融合了历史和传记之魂,一则为南京30万遇难者而作的民族传记,二则为中国人民不畏牺牲、反抗侵略而作的历史剪影。传记何以表现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提出以“传记”的写作方法引导“历史”叙述,谋求传记与历史间的某种平衡,达到道德说教目的[5]。普鲁塔克将传记与历史的关系归结为基于历史叙事的道德书写,目的为了弘扬传主的德行。然而,张纯如创作《南京大屠杀》并非道德说教,而是控诉罪恶和揭示真相,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她以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为主线,集中表现南京沦陷区和安全区遭日军凌虐的平民、战俘、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面对日军的暴行,他们表现出或慨然赴死,或舍命反抗的英雄气概;还突出了一群在华工作的外国友人发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南京大屠杀》的传主主要是普通中国民众,包括30万罹难者同胞,还有一群在华的外国商人、传教士、医生等,而不是德行泽被天下的历史伟人。
张纯如超越了为伟人或名人作传的传统,选择为南京大屠杀的亡魂作传,为国际人道主义者作传,将美国华裔传记文学推向一个新高度。华裔作家挤入美国文坛始于传记文学写作,多以自传或自传体小说形式书写华裔及其后代在美国的经历或在中国的生活,力求改善华人形象,以寻求在美国社会的一席之地[6]。张纯如的传记创作总是通过不断挖掘历史和重书历史,唤醒民众沉睡的历史记忆和集体无意识。她以传记来解释历史,促使传记与历史的交流沟通并达成共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既是反映中国抗战精神的历史教科书,又是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记书写。
二、《南京大屠杀》中的伟大抗战精神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中国精神。习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共同孕育出“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7]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抗战精神是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的升华和发展[8]。中华儿女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传统,爱国主义寄托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深厚情感。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自幼接受了家庭的爱国主义熏陶,怀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炎黄子孙的民族情结,以凝重的笔调揭示历史的真相[9]。《南京大屠杀》寄托了张纯如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主义感情,表现了一个有良知的华裔作家对中国抗战历史的关切、责任和胸怀,成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真实写照。
(一)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甘愿献出宝贵的生命。爱国主义是深藏在中华儿女心中不变的力量,激励着他们团结一致、忠于祖国、报效祖国,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10]。爱国主义体现了一种高尚的情怀,是理想、道德、情感和行为相统一的完整思想体系。美国华裔经历了长期的身份困惑,面临着同化与排斥的矛盾体验。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我们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远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11]霍尔的身份理论表明个人身份不是某时间点上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行进的构建过程。具有华人血统的张纯如对自己族裔身份的认识也是逐渐明晰的过程,在父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她对中国的印象从模糊到深刻。小时候,“她清楚地知道,她的先人来自那个神秘的古老国度。”[12]37长大后,她了解到祖国悲怆的历史,毅然选择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题材,既体现了一个青年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又表现出一位海外华裔后代的爱国情怀。
《南京大屠杀》是一座小型档案馆,以铁证如山的事实记载了日军的暴行,同时讴歌了中国人民顽强抗日的英勇事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野心不断膨胀,妄图占领东三省,进而控制全中国。但是,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也被点燃起来,普通民众的反日救国情绪不断高涨。193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南下进程,表现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日、忠贞爱国的大无畏精神。1937年8月开始的淞沪会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坚持三个月,彻底粉碎了日军速胜中国的美梦,展现了中国军队的抗战决心。
《南京大屠杀》的第一章“通往南京之路”详细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政策的起因,并且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张纯如感慨道:“中国——这个拥有淳朴民族的国家,尽管缺乏军事科学知识,也没有接受过多少军事训练,却顽强地遏制了强大的日军。”[12]17面对中日军事实力的悬殊,淳朴的中国百姓和弱势的中国军队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而支撑他们前行的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情怀。
回望二战时期的大屠杀历史,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被世人牢记,但是南京大屠杀有被遗忘的危险。张纯如曾向母亲表达自己创作《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想法:“这本书的最终目的是呼吁日本真诚地反省,力促日本对受害国家的人民道歉和赔偿。”[13]张纯如的创作实践充分表明一个华人作家对历史的道义和责任、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愤慨和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全世界的华人儿女一直牵挂着南京大屠杀的传播和教育活动,都自发行动起来,表达伸张正义的决心和爱心,全面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张纯如在“前言”中以热情洋溢的文字回顾了世界华人的爱国宣传活动:“许多华人积极分子通过组织各种会议和开展教育活动,宣传日军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在许多博物馆和学校播放或展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录像带和照片,并在互联网上传播相关事实和图片,甚至在《纽约时报》之类的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12]XXVII即便在异国他乡,洋装加身也改变不了华人的中国心。受爱国主义精神的洗礼,世界华人儿女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共同传播中华民族的声音。
(二)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
《南京大屠杀》的第二章“六周暴行”至第四章“恐怖的六星期”列举了大量史实和数据,对日军残杀中国军民的恐怖场景作了详细的陈述,引发读者“对战争背后人性和人类文明的思考。”[14]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妥协退让和国民党军队的军心涣散,日军很快占领南京,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日军的兽行令人发指,死亡人数令人不寒而栗:“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是,连日本人自己都相信,南京大屠杀死亡总人数可能高达30万。这个证据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是日本人自己的统计数据,而且是在南京大屠杀发生的第一个月统计的,那时日军对中国人的屠杀还远未结束。”[12]85大屠杀中死亡的统计数字就是一座纪念碑,铭刻了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遇难者30万也成了国耻的象征,激励着中国人民和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勿忘历史,永远不能宽恕日本军国主义的罪孽。
民族气节是维护民族尊严的精神品质。面对日军的暴行,南京沦陷区的各界民众誓死捍卫民族自尊,奋起反抗侵略,展现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1937年12月16日至17日发生在南京江边的草鞋峡暴动,数万名战俘和难民与日本刽子手进行了殊死搏斗。这是一次大规模集体性抗争,也是自发形成的惨烈暴动,英勇壮烈的人数和反抗的气势都令人震撼。草鞋峡暴动对重新阐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意义重大,弘扬和彰显了中华民族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特性[15]。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共赴国难,谱写了惊天泣地的雄壮史诗,是民族气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发展[16]。尤其是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不畏日军的屠刀,以个体的坚强意志和力量去救危难中的同胞和亲人。张纯如惊叹于普通百姓面临死亡威胁时的大义凛然:“并非所有在南京的中国人都轻易屈服于日军妄图斩尽杀绝的屠刀。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一个大规模的牺牲事件,其中也展现了个体的力量和勇气。靠着强烈的求生意志,有的人徒手挖开埋葬自己的坟坑逃出来……还有些妇女冲进大火熊熊燃烧的房屋去救自己的孩子。”[12]64-65张纯如以严肃的文字展示了中国人的力量和勇气,也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和泯灭人性。中国百姓并没有被日军的烧杀抢掠吓退,而是勇敢地面对死亡的挑战,以生命捍卫民族尊严。
大屠杀是人类历史的黑暗面,彻底暴露了侵略者丧失人性的恐怖。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书写不仅是对历史的昭示,也是对现实的警示。南京大屠杀的恐怖远超人类的想象力,它留下的创伤很难愈合。历史记忆需要不断书写,才能时刻提醒我们严防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张纯如以血淋淋的证据展示了日本侵华的真相,并慷慨激昂地表现了中国人民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三)血战到底的无畏精神
抗日战争中涌现出一大批民族英雄个人和集体,如左权、彭雪枫、杨靖宇、张自忠、狼牙山五壮士等。他们成为威武不屈的中华民族的脊梁,体现了伟大抗战精神之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面对强敌入侵,中华儿女挺身而出,为了民族大义,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显示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磅礴力量。
南京大屠杀期间还涌现出不少平民英雄和无名英雄,他们铁肩担道义,为拯救苦难同胞甘愿冒生命危险,付出血与泪的代价。南京沦陷区内的日军展开疯狂屠杀,江苏宝应人王恒山冒死救助多名中国军人和难民,谱写了一曲曲普通人的英雄赞歌[17]。南京安全区内,外籍友人担负起人道主义的救援责任,但中方人士仍是实施难民救助的主体。他们自愿担当难民收容所的管理者和志愿者,并协助红十字会等组织,开展粮食救济、医疗救助、遗体掩埋等工作,连姓名都未曾记载。这些无名英雄身上闪耀着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不畏强暴、患难与共的民族精神写照,是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18]。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些无名英雄和国际友人的守望相助精神也给予高度赞扬,指出他们的仁义之举“令人感动。”[19]正是这些平民英雄、无名英雄和国际英雄筑起了一道道精神防线,全国上下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团结抗日热潮,为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书写,张纯如以生命发出的呐喊引发了许多美国华裔作家的共情,让他们认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和使命[20]。以《南京大屠杀》为摹本,他们从不同视角展示了不畏强暴、勇于献身的英雄形象。严歌苓创作《金陵十三钗》时参照了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的史实,以“南京沦陷”和“恐怖的六星期”两章为背景,以一群秦淮河妓女替女学生受难为原型,塑造了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的平民“女英雄”形象。“十三钗”的遭遇和义举将她们从“堕落者”转变为“救赎者”,最后升华为感人肺腑、受人尊敬的民族英雄。哈金受益于《南京大屠杀》的启发,将“南京安全区”一章的史实改写为《南京安魂曲》,聚焦于明妮·魏特琳女士为代表的中外救援者的义行,塑造了一群伟大而平凡的“无名”英雄形象。
张纯如从国际视野诠释了人道主义的壮举,并讴歌守望相助精神哺育下国际主义者的英雄气概。《南京大屠杀》的第五章聚焦于“南京安全区”内欧美人士的仁义之举,张纯如称他们“如同光明的灯塔”[12]87,照亮了人间的黑暗。张纯如选择了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表明英雄的定义可跨越国别、党派和信仰的界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贝竟是个纳粹党员,以同盟国官员作为护身符救助受难的中国人;而威尔逊和魏特琳则是靠宗教信仰力量的支撑来扶危救困,赢得了难民的尊敬。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具有英雄本色和守望相助、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仁义善举,他们的事迹也一定被载入抗战英雄谱中。
(四)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的污点,留给了中国人民永久的创伤记忆。张纯如基于历史的追忆和大量的实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南京大屠杀》的第六章“世人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以铁证如山的态势揭示日军铁蹄下南京人民遭受的苦难,聚焦于中外媒体所展示的25张黑白照片,展示侵略者制造的惨绝人寰。第七章“日本占领下的南京”曝光了大屠杀后日军对南京人民的殖民统治,揭示日本侵略者的丑恶嘴脸。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为《南京大屠杀》作序中指出:“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把南京陷落看作一个截然不同的转折点。这座古城所遭受的劫难大大激发中国人收复南京、赶走侵略者的决心……日本侵略者用于无法迫使中国投降。”[12]XVII日军的暴行非但不能摧垮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反而增强了他们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的决心。支撑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就是中华民族永不言败的自信力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16],集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形势的科学研判,提出了持久战的科学论断。中国人民坚信正义必定得到伸张,罪恶定会受到审判。但是正义的伸张和罪恶的惩罚仍需进一步努力。张纯如在第八章“审判日”中详细评述了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指出:“许多南京大屠杀的主要罪犯,或者说那些原本可以运用皇家权威制止大屠杀的人,却从未出庭受审。”[12]159张纯如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批判了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审判中的绥靖政策,呼吁中国人民仍要坚持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战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在于中国人民具有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信念是钢,无坚不摧。中华人民正是凭着坚不可摧的信念,振奋了民族精神。《南京大屠杀》是张纯如再现南京浩劫的历史,以触目惊心的文字唤醒中国人民苦难记忆的力作。虽然她没有认识到中国抗战胜利的根本原因,但是她对待历史的态度,对待民族的情感以及替受难同胞代言的勇气和胆识着实令人敬佩。
综上所述,《南京大屠杀》是张纯如为30万遇难者同胞所作的集体传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85年,但是再现和审判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仍是当代华人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书写南京大屠杀不是传播民族仇恨,而是教育下一代正确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张纯如是一个道德良知和民族正义感的华裔后代,她的不朽之作《南京大屠杀》为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保存了那段历史记忆,并唤起了国人的情感共鸣,促进了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的构建。她将历史与传记巧妙融合,超越了文学的审美功能,促进了史实的传播,更加有效而可靠地揭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为遇难者同胞的亡魂作传。历史不容置疑,更不容篡改和抹杀。张纯如以负责任的态度和浓烈的民族情感,强烈抨击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传记文学《南京大屠杀》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精神,是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力量。回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艰难历程,当代国人更应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展望未来。当下西方主流媒体裹挟着文化渗透,正试图悄然抹去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而张纯如的创作恰当地再现了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共同传承,并传递了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的力量,进一步展现了当代华裔作家的历史责任和爱国情怀。现在中华民族正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国家的崛起在于精神的弘扬。弘扬抗战精神有利于凝聚各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彰显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张纯如的传记文学《南京大屠杀》既告慰了遇难者同胞的灵魂,还激发了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斗志,具有不可估量的史学价值和道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