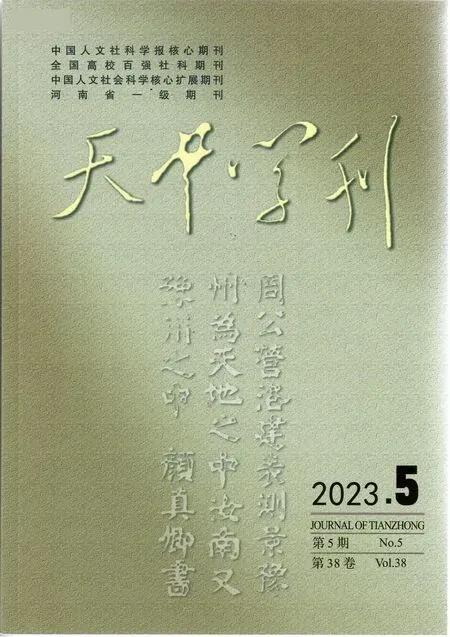“背德”内容与文学叙事
——以《莎乐美》与《金阁寺》为例
2024-01-03栗桢
栗 桢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文学作品时常会表现“背德”的内容或主题。比如法国作家萨德侯爵在《贞洁的厄运》中将美德与不幸进行形而上的连结,描绘了一位恪守美德的无辜少女遭受的种种凌虐。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所著小说《洛丽塔》描述了中年男性与自己未成年继女之间的不伦之恋,该作更是因其有“恋童癖”倾向的内容而广受批判。美国作家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的小说《美国精神病人》描绘了一名美国“社会精英”通过谋杀和残害他人缓解冷漠、空虚并寻求快感的故事。
当代西方学界,研究文学作品“背德”内容本身所可能具有的“认知价值”是相关领域的主要切入点,如依据英国学者马修·基兰在《禁忌的知识》一文中所做的评价,作品的“背德”内容通过探究犯罪者、心理异常者的“背德”行为,为人们展示了“背德”行为背后的心理成因和心理活动,展示了触碰道德底线的人们的生活轨迹和状态,所以其“背德”内容本身具有“认知价值”[1]56-73。
不同于上述以“认知价值”为目的的研究方法,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作品分析,探讨“背德”作为一种表达手段和叙事策略如何在特定作品中发挥作用,服务于“背德”内容之外的特定情感或主旨表达。另外,本文会阐释为何以“背德”作为叙事策略服务于核心表达的作品将无法逃避由道德主义文学批评所导致的价值贬损。
一、“背德”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基础:道德与行为规范力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背德”的涵义及其对文学叙事所能起到的作用,我们需要从道德哲学的研究中获得相关的学术基础。
在近代哲学界,康德对道德的本质进行了最为详细而深刻的描绘,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将道德描绘为理性对人们所下达的“命令”。道德不仅具有要求或者禁止人们特定行为的特性,其法则下的最高指令更是被称作无条件的“绝对命令”[2]xiii。换言之,道德规则是所有理性主体(包括人类在内)都应该遵守的无上法则。克里斯汀·科尔斯戈德也在《规范性的来源》一书中指出道德不仅是描述性的,更是具有规范性的[3]8-9。我们判断某件事如果在道德上是善的,便会随之产生一种规范性的力量促使道德主体去践行该事;如果判断某件事在道德上是恶的,道德的规范力便会促使道德主体回避该事。
其他范畴的概念也会产生规范力,比如在审美领域,画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不断对画作进行审美判断,并根据判断结果调整下一处落笔笔触的强弱以及颜色等,以求最终成品能够提供最大限度的审美价值。但是道德法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具有最高级别的规范力。换言之,当道德法则的要求与出于非道德理由的要求冲突时,道德法则永远有更强的约束力驱动人们放弃非道德的选择,并遵守道德的命令。道德最高级别的规范力来自康德所述的“理性”,因而任何理性主体都没有正当理由去做道德上错误的事。
明确了道德的内涵与其特殊之处,“背德”的涵义也随之明朗。“背德”作为对道德法则的僭越,是对道德所具有的最高级别规范力的对抗。依据道德拉斯·朴特莫尔在《道德与实践理性》一书中的描述,人们在实践中的决策是不同理由碰撞的结果[4]1。当一个人做出僭越道德法则的抉择时,与道德原则相对立的非道德理由必须在行为主体的认知中具有至少等同于道德规范力的力量,才有可能在该主体的决策中暂时“打败”道德理由,使得“背德”行为得以发生。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背德”行为的深层逻辑——即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决策中背弃道德法则的驱动力强烈到能够压倒道德动机之时,他才会做出“背德”的行为。不同的道德法则所具有的规范力也存在差异,比如“不能谋杀”的规范力显然要远大于“不能偷窃”的规范力。所以“背德”行为中所背弃的道德准则越重要,“背德”行为所需要的驱动力便越强。
文学总是以人类实践中的种种现象作为创作的重要依据和对象,而上述“背德”行为在实践中所具有的涵义及内在逻辑不仅可以解释特定文学作品中“背德”情节设置的效果,更可以作为强化特定表现力的叙事工具而发挥效用。更重要的是,文学可以在吸取道德哲学结论的养分后摆脱道德哲学结论真值的束缚,仅依靠某概念的“印象”进行创作。“人们不会在意历史上的拔示巴如何,而经常会刻板地将其作为诱惑与堕落的象征。”[5]486同理,假设某一天或在某个可能世界中,道德法则不再具有支撑其最大规范力的学术基础,它依然可以保有该级别规范力的“印象”而被艺术创作所运用。
二、“背德”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运用:以《莎乐美》与《金阁寺》为例
“背德”作为一种服务于作品核心表达的手段和情节设置,主要被运用于叙事性的文学作品中。下面笔者将以东西方文学作品中最能表现“背德”作为叙事策略与作品表达关联性的两部作品——《莎乐美》与《金阁寺》为例,对“背德”情节设置与作品主旨表达之间的正向关系进行分析。
(一)《莎乐美》的改编与爱欲的表现
《莎乐美》是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于1893 年创作的戏剧作品。该作品以《马太福音》中的人物莎乐美为原型进行了改编和再创作,但其故事架构和表达意旨与原型全然迥异。
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莎乐美的故事发生在希律王、希律王的妻子希罗底、希罗底的女儿莎乐美以及先知约翰这4 人之间。故事情节如下:先知约翰曾经对希律王迎娶希罗底表示非议,故而被希律王囚禁;希律王生日之时,莎乐美在众人面前起舞,希律王大喜,应允予其所求之物;莎乐美在母亲希罗底的授意下向希律王索要装在盘子中的先知约翰的头颅;希律王派人杀害约翰,取其头颅装于盘中,莎乐美将该物拿给了其母希罗底。在原版故事中可以看到,莎乐美自始至终都是主使人希罗底与希律王的工具,她被动地接受希律王的恩赐,被动地听信母亲的驱使。
在王尔德的戏剧《莎乐美》中,先知约翰被希律王囚禁,莎乐美慕名前去探望并疯狂地爱上了他。面对莎乐美的示爱,先知约翰以其是通奸之女为由表示了拒绝,但莎乐美却念念不忘。在希律王的生日宴上,莎乐美无视母亲希罗底“不要在宴会上跳舞”的劝诫,为希律王的宾客们献上了舞蹈。为了表示嘉奖,希律王许诺给莎乐美一件所求之物,莎乐美主动索要盛放于银制盘子上的先知头颅。希律王大为震惊,无奈之下将先知杀害,并按莎乐美的要求将其头颅盛于盘子之上。拿到先知头颅的莎乐美亲吻着丧失了生气沾染着血迹的先知嘴唇,被这一景象震惊的希律王最终下令将莎乐美处死。
王尔德的《莎乐美》对原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原作故事中希罗底与先知约翰之间的矛盾被完全淡化,造成先知约翰死亡的最大主谋希罗底甚至试图阻止女儿跳舞可能带来的悲剧,故事的主要矛盾转移并集中在了莎乐美与先知约翰之间。原作中被母亲当作工具的少女在戏剧《莎乐美》中所承担的恶与道德责任攀升到了一个巅峰,她从一个被动的传话者变成了出于主观意志而行动的谋杀者,做下了不可饶恕的“背德”之行。不仅如此,她又违背了“不可亵渎遗体”的道德法则,亲吻了先知的头颅。美国学者罗伯特·斯戴克曾在《捍卫艺术价值》一文中说,作品的好坏取决于作者能否运用多种艺术表现策略顺利实现其“艺术意图”[6]357。在《莎乐美》中,王尔德调整人物关系和动机,将上述双重“背德”行为施加在莎乐美身上,其目的便是为了更好的艺术表达,而加码“罪恶”与“背德”则是戏剧《莎乐美》实现其艺术意图和表达的最佳手段。
不同学者对莎乐美这一人物形象以及《莎乐美》作品艺术意图的阐释略有差异却又殊途同归,他们都认为莎乐美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是“原本处于男性凝视下被动弱势的女性倒转了主客体位置,成为观看的主体”,莎乐美“强烈疯狂地表达着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欲望,表现出甚至比男性更强大的主体意志”[7]54,而莎乐美对先知约翰的追求,体现出一种对肉体之美的强烈欲望:“在莎乐美的眼里,他的声音就是她要喝的酒,她所渴望的是他那迷人的肉体之美,所以,为了得到他的肉体之美,她想尽一切办法来征服先知。”[8]167“莎乐美对约翰的信仰并不关心,对他的宗教并不关心。她对他的欲望的终极,在于占有他的肉体。”[9]60学者对莎乐美人物内涵的解读不约而同地聚焦在莎乐美所表露出的对先知约翰色相之美的强烈渴望之上,而追求爱欲与感官刺激“正符合王尔德本人的唯美艺术的审美追求”[8]166。作为一部唯美主义艺术理念影响的文学作品,《莎乐美》的艺术意图便在于最大限度地表达爱欲与激情,而表达爱欲强烈的最好方法之一便是展现人物愿意为了爱欲做出何等行动,设置剧中人物在爱欲的裹挟下能够冲破何等阻碍。所以,道德因其至高的权威性及其伴生的无与伦比的规范力,在《莎乐美》中被设置成了爱欲的反面,《莎乐美》也因主人公对道德的背叛而得以烘托出人物的爱欲所具有的更胜于具有至高规范力的道德的力量。
为了更好地理解“背德”与“罪孽”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以及“罪孽”被不断加之于莎乐美之身时所带来的同等强烈的爱欲表现力,让我们来设想另一幅面貌的《莎乐美》:假设剧中莎乐美并非罔顾母亲的劝诫,主动献上舞蹈并大胆地提出要求,而是如原作一般借着母亲的驱使顺水推舟地提出要求,我们便不能感受莎乐美对约翰的爱欲所催生的主动性已经强烈到可以自发地创造出一整套“背德”的计谋,并且甘愿承担随之而来更为严重的道德谴责;假设剧中莎乐美在得到约翰的头颅之后,并没有狂热地亲吻沾染着血迹的嘴唇,而是如原作一般无动于衷,我们便无法认识到莎乐美对先知约翰的爱欲已经强烈到超越了生死、超越了灵魂的有无,使得她不惜亵渎尸体也要亲近所爱之人的肉体。
较之原作,王尔德笔下的莎乐美变得越发“罪孽深重”,正是因为莎乐美“罪行”的急剧加深,王尔德关于唯美、爱欲的表现才能如此鲜明、激烈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道德特殊而强大的规范力,“道德”的力量越强,“背德”所需要的反力便越强。道德的力量和“背德”的表现力在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奇妙的正相关联系。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由改编所强化和加深的“背德”作为辅助实现爱欲表现的叙事策略,为何能使《莎乐美》的艺术表达上升到一个高峰。
(二)焚烧《金阁寺》与自我改造
小说《金阁寺》不只是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代表作品,更是近代日本文学的代表性杰作之一。该小说的创作以1950 年的“金阁寺纵火事件”为契机,但三岛由纪夫为了实现作品的艺术表达,完全虚构了主要角色、动机以及整个故事脉络,仅将“焚烧金阁寺”作为故事的终点和高潮。在小说《金阁寺》中,“金阁寺”所代表的意象及其毁灭是整部作品的原点和焦点。真实的“金阁寺纵火事件”这一“罪孽”与“背德”的行为是小说《金阁寺》的灵感来源,三岛由纪夫也将这一“罪行”设置成小说中所有线索汇聚的终点以及所有矛盾爆发的高潮。而将“罪恶”置于全片高潮的聚光灯下的叙事策略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全篇的主旨表达。
《金阁寺》是一篇三岛由纪夫自身的精神史。作品对主人公沟口战时和战后两个阶段的精神变化进行了出色的描绘。战时阶段,沟口感受到自己理念中的金阁寺会与自身同在,并将与自己一同在毁灭中获得永恒,然而随着日本的战败,沟口与金阁寺共生的愿景化为泡影,此时的金阁寺是令人焦躁和煎熬的束缚。
与象征着绝对的美、绝对的超越者以及在毁灭中永恒的金阁寺相对照,小说中还存在另一个意象——女性。金阁寺和女性分别代表的意象之间的冲突,形成了沟口内心两股相互矛盾的力。沟口在面对女性的肉体之美时因脑中浮现出金阁寺绝对之美的画面而阳痿,表达的正是金阁寺所象征的绝对而虚幻的美对沟口“生之欲”的压倒。战后,行走在人世间、内心渴求着“生”的沟口却保留着金阁寺的烙印,所以他成了异常者。当虚无与生的矛盾到达高峰,他便不得不做出抉择。最终,沟口选择挣脱金阁寺的纠缠与束缚。
三岛由纪夫选择以主人公焚烧金阁寺这一对道德的背离行为作为全篇的高潮与结尾,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为了表达金阁寺所代表的“虚幻而绝对的美”对沟口的纠缠与禁锢之深。只有当金阁寺的禁锢对沟口造成极深的痛苦,他才会认识到只有不惜代价地将其毁灭焚烧才能挣脱这一旧日亡灵,哪怕要承担来自道德(与法律)的巨大罪责。假设沟口可以通过搬家或移居海外的方式从金阁寺的阴影中逃开,而不是非得将之付之一炬,那么所谓的金阁寺绝对而虚幻的美大概也终归只是外在之物,并没有内在而深入地进入主人公的意识,读者便也无法认识到金阁寺在沟口心中植根之深。如此,小说《金阁寺》的表达便会大为失色,所以唯有沟口与金阁寺正面对抗并将其焚毁的行为才能在文学表现上完美地契合作品的表达与主旨。其次,是为了表达“自我改造”的意愿之强烈。假如沟口只是将“自我改造”的字样刻在自己的手心,以时刻提醒自己拥抱“生”和摆脱旧日虚幻的美学意愿,那么读者便会认识到他虽然拥有“自我改造”的意识,但比起道德规范的“威压”和无视罪行带来的道德谴责,该意识并未足够强烈。因为如果沟口真的决意与过去的美学诀别,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便是一劳永逸地毁灭该美学所凝聚的对象——金阁寺。若非如此,等刻在手中的字迹渐渐消失而金阁寺仍然矗立着,那么便没有人能保证旧日的阴影不会死灰复燃,沟口也很可能会再度陷入金阁寺那“虚幻而美丽”的漩涡之中。只有打破一切顾虑与规范,不计后果地焚毁一切矛盾的根源——金阁寺,才是最为强烈的意愿所催生的行为,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背德”行为,小说人物那强烈到极致的“自我改造”的意愿才能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
(三)“背德”叙事与艺术表现力
《莎乐美》和《金阁寺》都讲述了“背德”的故事,且作品中人物的“背德”行为都被有意地安排成了叙事“装置”,用来承担作品艺术表现中最重要的部分。但“背德”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策略对作品的艺术表现有着其他叙事处理方法无法比拟的巨大增幅作用。
“背德”叙事所具有的强烈的艺术表现力来源于“道德”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特殊规范力。道德法则越重要,道德越具有权威性,则“背德”所需要的“力量”便越强烈。在康德理念中,根植于人类理性的“道德”就像阻挡一切冲动和感性疯狂外溢的堤坝,只有这堵大坝足够坚不可摧、足够宏伟壮观,它所阻拦的“洪水”决堤之时,我们才越能认识到冲击大坝的激流其力道是如此之强。由此,“背德”的表现力与“道德”的规范力形成了奇妙共生的正相关联系。“背德”也借由“道德”的规范力得以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策略,通过作者的情节设置而在一个虚构的情境中服务于作品的艺术表达。
三、“背德”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代价:道德主义与文学批评
虽然“背德”具有将特定感情与主旨的表现力推至极致的作用,但它作为艺术表达的一剂“猛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特定的副作用。“背德”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策略的最大代价便是会招致基于道德主义理论的批评。
(一)近代道德主义理论下的“背德”叙事
道德主义文艺批评源远流长,在近代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道德主义文艺批评之一便是休谟所下的断言:“当恶劣的行为被描写出来而没有被赋予恰当的谴责与否定,诗篇就会因此大为失色而变成真正的残缺品。”[10]227可以看到,以近代学界的评判标准,如《莎乐美》和《金阁寺》一般不仅描述恶行且不对其中人物所做的恶行予以谴责的作品,便会在道德主义理论的批评中折损掉一部分艺术价值。
(二)当代道德主义理论与作品态度的表达
西方道德主义理论在当代的最新形态是由分析美学家在20 世纪末至21 世纪初重新阐释的理论。学者们的共识便是道德主义批评的对象应该是作品所表达的态度,如贝里斯·高特认为艺术作品道德评论的对象是一种出于目的论意义上的“态度表达”,是作品对特定对象表达出的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11]183。A·W·伊顿也持类似看法:“艺术作品中的视点使得作品可以成为合理的道德评论对象,而这种视点是通过作品想要表达的态度来呈现出来的。”[12]282在学界最新的研究中,帕诺斯·帕里斯也将“不道德的作品”定义为“通过表现角色、事件等等艺术方式,以达到宽恕、灌输、支持以及使得观众接受某个不道德的态度的作品”[13]15。
道德主义理论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结果论的道德主义以及规范论的道德主义。结果论的道德主义以美国学者诺埃尔·卡罗尔的观点为基础,认为作品表达出的不道德的态度会在结果上阻碍特定艺术意图的实现[14]223-238,比如某个喜剧可能会因其不道德的态度表达而变得不好笑,而“不好笑”对于喜剧作品来说便意味着巨大的艺术失败。规范论的道德主义以英国学者贝里斯·高特的观点为基础,认为一部作品如果诱导或要求受众做出“不恰当”的反应则是艺术上的失败,而“不道德”的反应便属于“不恰当”的反应[10]233。根据美学与文艺评论学界最新的研究,规范论的道德主义理论因其内在存在诸多问题而广受诟病,因而结果论的道德主义理论成为当代道德主义理论的主要形态。
结果论的道德主义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莎乐美》和《金阁寺》受到的道德谴责,这是因为部分具有道德感受性的读者以及评论者会因为作品表现出“背德”的态度而无法很好地与作品人物共情,进而打破作品艺术价值实现所必须给予读者的“沉浸感”[14]232。《莎乐美》与《金阁寺》都表现了帕里斯所说的“宽恕”罪行的态度,因为“罪行”是实现作品核心艺术目的的必经之路,是可以被接受的代价,所以在欣赏《莎乐美》与《金阁寺》之时,部分接受道德主义文脉的评论者便会因作品“不道德”的态度而被动地跳脱出作品所设定的情景,无法继续融入作品叙事,并从作品中感到“病态”和“反胃”。作品艺术表达的意图在具有道德感受性的群体中也会因沉浸感的打破以及从叙事中的跳脱而无法实现。
在此之上,“不道德”态度的表现是作品将“背德”与艺术表达捆绑在一起,借由前者强化核心艺术表现力的必然产物,因为这种情况下作品将不可避免地展现对“背德”行为的理解、宽恕乃至认同的态度。只要作品将“背德”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用来强化作品的核心艺术表达,那么该作品便无法逃脱道德主义的批评。因为当“背德”行为与艺术主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便会形成正相关的密切关系,从而面临一损俱损的局面。而否定作为作品核心主旨表达“辅助”的“背德”行为,便意味着对作品主旨与表达本身的部分否定,致使作品陷入自我否定的窘境,并最终导致其艺术价值大幅贬损。让我们想象在《莎乐美》中,假如莎乐美在谋害了先知约翰之后为自己的罪行发自内心地向上帝忏悔自责,那么她那由爱欲所带来的激情是否依然会和王尔德的版本一样炽烈?那她对肉体之美的渴望是否会由此退化为可以被道德轻易浇灭的微弱火苗?《莎乐美》这部作品是否会因此丧失其原有身份,从一部颂扬激情、欲望和美的篇章转换为描述罪人迷途知返、渴求上帝宽恕的道德寓言?
因此,在当代道德主义理论的语境中,如果将“背德”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强化作品的核心表现力,作品便会因其对“背德”行径表达的“不道德”态度而受到批评。并且,因为“不道德”态度的表达与作品的核心主旨高度绑定,为了避免作品核心主旨受到牵连和扭曲,作品中一定程度“不道德”态度的表达将是必然,这也意味着基于道德主义的批评将不可避免。
总体而言,在虚构作品的叙事中,设置人物违背道德法则的“背德”行为比其他行为更能在特定情况下将作品的表现力推至极致。然而,采用“背德”策略强化作品核心主旨的表现力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它会阻碍作品在部分接受道德主义语境和具有道德感受性的评论家和读者中实现艺术表达的意图,导致该语境下作品艺术价值的贬损。因此,“背德”作为一柄艺术表达的双刃剑,在以其为叙事策略强化作品核心表现力的同时,将不得不承担来自道德主义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