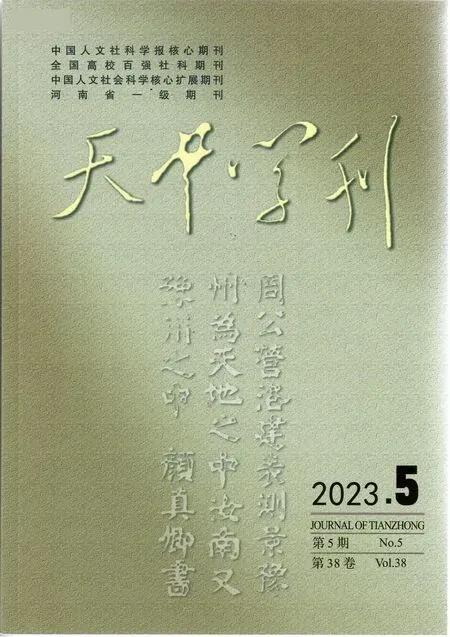颜真卿仙化故事的流变及其文化内涵
2024-01-03谭智
谭 智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人,唐代名臣、书法家。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因卢杞陷害,颜真卿奉诏宣抚叛军,兴元元年(784)被叛军首领李希烈缢杀。颜真卿死后不久,《戎幕闲谈》《玉堂闲话》《仙传拾遗》等中晚唐笔记小说中开始出现“颜鲁公尸解成仙”的故事。此后,该故事在小说、戏曲中广为流传,并在各个时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①。宋代,《洛中纪异录》《青琐高议》《续博物志》等笔记小说在延续和保留前代相关故事的志怪情节外,又对故事的详略进行了加工改造,将颜真卿进一步推向了神坛。到了元明时期,《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有象列仙全传》《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大全》等神仙传记则对他成仙后的去向做了具体的交代和说明,并正式将其纳入道教的神仙谱系之中。此外,以《昙花记》和《劝善金科》为代表的明清戏曲,也对该故事进行了重新剪裁和编排,将它穿插于教化剧之中,使其具有了新的面貌和意涵。本文试对颜真卿仙化故事的流变进行历时性梳理,并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结合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创作观念、创作手法以及各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宗教思想等要素,探究该故事流变的阶段性特点及其成因,并分析其在不同时期的文化意蕴。
一、唐五代笔记:“忠臣不死”的艺术化处理
唐五代是颜真卿仙化故事的起源期。这一时期,该故事多见于笔记小说,如《戎幕闲谈》《玉堂闲话》《仙传拾遗》等。从时间上看,最早记录颜真卿死后尸解成仙情节的是韦绚《戎幕闲谈》一书。韦绚自序其成书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根据《旧唐书》所载,李希烈“使阉奴与景臻等杀真卿”事则是在唐德宗兴元元年(784)[1]3596。也就是说,在颜真卿死后不到50 年的时间里,其死节事迹就被人们进行了传奇化地加工。
在韦绚《戎幕闲谈》之后,郑綮《开天传信记》、王仁裕《玉堂闲话》、杜光庭《仙传拾遗》等书均记载了这一故事。李昉在《太平广记》卷三二“颜真卿”下明确指出该条“出《仙传拾遗》及《戎幕闲谭》《玉堂闲话》”[2]208,实际上,《太平广记》中主要征引的是韦、王、杜等人笔记中带有志怪色彩的部分。从现有文本来看,该故事中的志怪情节主要有两处:第一处是在颜真卿的少年事迹中,出现了偶遇道士北山君授丹的情节:
真卿年十八九时,卧疾百余日,医不能愈。有道士过其家,自称北山君,出丹砂粟许救之,顷刻即愈,谓之曰:“子有清简之名,已志金台,可以度世,上补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摆脱尘网,去世之日,可以尔之形炼神阴景,然后得道也。”复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节辅主,勤俭致身,百年外,吾期尔于伊洛之间矣。”[2]205-206
另一处则是在颜真卿被李希烈杀害之后,出现了迁丧途中尸解成仙的情节:
贼平,真卿家迁丧上京。启殡视之,棺朽败而尸形俨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软,髭发青黑,握拳不开,爪透手背。远近惊异焉。行及中路,旅榇渐轻,后达葬所,空棺而已。[2]207
从效果上看,这两处情节遥相呼应。早期的“道士奇遇”既说明了颜真卿少年经历的传奇,同时又为后来“尸解成仙”等情节埋下了伏笔,而后期的“尸解成仙”则是对颜真卿早年奇遇经历的呼应。相较于正史的记载,这两处带有志怪色彩的情节不仅使得故事充满了传奇性,更让颜真卿形象具有了神秘性。
唐五代时期,颜真卿仙化故事中志怪情节的出现并不是文人凭空想象的结果,而是社会思想文化和小说创作观念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受唐代整体崇道氛围的影响。道教于唐代空前繁荣,在浓厚的崇道氛围下,文人普遍认同道教服食丹药、尸解成仙等理论和方法,因而影响到了文学创作,“道士奇遇”和“尸解成仙”情节在小说创作中屡见不鲜。因此,韦绚等人增加志怪情节的做法有其特殊的时代和社会原因。此外,颜真卿本人与道教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不仅创作了《魏夫人仙坛碑》《李含光碑》《麻姑仙坛记》等与道教有关的碑文,在抚州、湖州等任时,还大力修复和保护道教宫观,与吴筠、张志和、韦景昭等道门中人交游唱和,这些都为后世文人的创作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素材。
二是受唐五代笔记小说“资谈笑”创作观念的影响[3]。唐代文人士大夫的聚会闲谈成为一种娱乐方式,这样的社会风气对笔记小说的创作也有着影响。相聚闲谈之际,神仙鬼怪故事契合时人尚奇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小说的创作,为创作者提供了故事素材。《戎幕闲谈》一书即是韦绚专门记录李德裕闲谈的产物,书序云:
赞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语古今异事。当镇蜀时,宾佐宣吐,斖斖不知倦焉。乃谓绚曰:“能题而纪之,亦足以资于闻见。”绚遂操觚录之,号为《戎幕闲谈》。[4]
在序中,韦绚已预料所记之事将受“好事者”推重,因此他为了满足更多人的好奇心,将李德裕所谈古今奇异之事记录下来,以增长见闻,充实谈资。而颜真卿距离李、韦生活的时代仅过去不到50 年时间,在名人效应的推动下,有关颜真卿的奇闻逸事必定成为文人士大夫聚会闲谈时的热门话题。如《戎幕闲谈》《玉堂闲话》这些笔记小说便是闲谈、闲话的产物,之所以被记录、纂集成书,其目的主要还是娱乐[5]。“闲谈”“闲话”的命名方式不仅暗示了笔记的娱乐倾向,更显示其子部“丛残小语”的性质。
三是文人士大夫对“忠臣不死”结局的艺术化处理。《旧唐书》载,颜真卿被李希烈杀后,“德宗痛悼异常,废朝五日,谥曰文忠”,并下诏封赠。在诏书中,唐德宗高度赞扬颜真卿“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属贼臣扰乱,委以存谕,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1]3596-3597。颜真卿刚正不阿、忠君殉节的高尚品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而这也正是许多文人士大夫一生的追求。因此文人在处理颜真卿悲惨结局时,借用了道教尸解的笔法,既为其奇特经历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更表现了他们对一代名臣蹈节死义、与世长辞的遗憾与不忍。日本学者内山知也在论及该问题时,认为使用道教尸解的方法处理颜真卿之死是“史传和故事融合的失败”[6]。实质上,这是一种对颜真卿结局的艺术化处理。中晚唐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时代和人民渴望和呼唤忠臣的长期存在,不愿看到忠臣义士被排挤、杀害的悲惨下场,所以文人士大夫借助道教尸解成仙的方法,对颜真卿殉节后的去向进行了延展性的想象。正如宋人许永在《颜元祠记》中所说:“自古忠臣义士死必为神仙,如比干、屈原、伍子胥之徒皆为列仙,见于传记……旧说以鲁公为仙,以是知怀义秉忠之士虽死而实未尝死,无可疑者。”[7]人们以浪漫的笔调使得颜真卿能够以仙人的身份长存,表达的对“忠臣不死”的美好愿望。
二、宋代笔记:“天下鲁公”的神祇化崇拜
宋代进一步推进了对颜真卿神祇化崇拜的进程。这一时期的颜真卿仙化故事同样集中在笔记小说中,如北宋秦再思《洛中纪异录》、刘斧《青琐高议》、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和陈葆光《三洞群仙录》等均有记载。这些故事一方面直接来源于唐五代笔记,保留了其中的志怪情节[8];另一方面又在其基础上对故事详略进行了加工和改造。以刘斧《青琐高议》为例:
颜真卿问罪李希烈,内外知公不还,皆饯行于长乐坡。公醉,跳踯抚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以罗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缢杀之,瘗于城南。希烈败,家人启柩,见状貌如生,遍身金色,须发长数尺,归葬偃师北山。后有商人至罗浮山,见二道士树下弈棋,一曰:“何人至此?”对曰:“小客洛阳人。”道士笑曰:“幸寄一封书达吾家。”北山颜家子孙得书大惊曰:“先太师亲翰也。”发冢,棺已空矣。径往罗浮求觅,竟无踪迹。又曰:“先太师笔法,蚕头马尾之势,是真得仙也。”[9]
与唐五代相比,宋代对颜真卿仙化故事的改造主要展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缩减故事篇幅。宋代的笔记作者采用“横切”的手法[10],将颜真卿的生平、家世、宦迹等内容删去,截取“问罪李希烈”这一横断面进行精雕细琢,把原有长篇传记中的面面俱到式介绍变成了短暂片段中的重点突出式叙述。这样可以使叙述详略得当,集中叙述“问罪”“殉节”“仙化”等情节,把故事的矛盾冲突快速地推向高潮。
二是增加故事情节。虽然篇幅被缩减,但宋代的颜真卿仙化故事在情节方面却进行了增加。一处是在故事的开头,增加了长乐坡送别时颜真卿自言早年经历的情节;另一处则是在结尾处,增加了商人罗浮山奇遇、颜氏子孙发冢开棺的情节。宋代文人选取了颜真卿一生之中两段奇特的经历,并将其连缀成篇,既简要地展示了他的生活历程和殉节成仙的经过,同时也凸显了故事之“奇”、得仙之“真”。“横切”和“直缀”手法的使用,确保了结构的完整性和情节发展的波澜起伏。
三是细节的变化。如颜真卿早年所遇之道士从“北山君”变为了“陶八八”,道士预言的地点也从“百年外,吾期尔于伊洛之间”变为“他日待我以罗浮山”。这些细节的变化是宋代文人有意为之,其主要目的仍是增加故事的真实性。如罗浮山,从葛洪《抱朴子内篇》中的“二十八名山”到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和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的“洞天福地”,已成为仙人栖居之地的代名词。因此在宋代文人的笔下,罗浮山是颜真卿成仙后的最佳去向。
在缩减篇幅、增加情节和变化细节的合力作用下,颜真卿被进一步推向神坛。宋代文人对颜真卿仙化故事巧妙的艺术构思很大程度源于官方对颜真卿的推崇,正如牟巘在《重修颜鲁公祠堂记》中所说:“唐颜鲁公以名节著,人皆曰吾邦鲁公也。余则曰天下鲁公也。”[11]“天下鲁公”的概念准确地表达了宋人对颜真卿的顶礼膜拜。在宋代,全国各地修建了大量的颜鲁公祠,其中以江西抚州、山东费县、浙江湖州三地最具代表性,而它们被修建的原因基本上是“慕公之烈,以公之尝为此邦也,遂为堂而祠之”[12]。南宋绍兴元年(1131),汪藻知湖州时,又“以颜真卿尽忠唐室,尝守是邦,乞表章之,诏赐庙忠烈”[13]13131。颜鲁公庙祠的修建是颜真卿逐步被神祇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它既是宋代士人对颜真卿高度崇拜的体现,更是公共价值观和国家意志的集中表达。
此外,宋代还将颜真卿纳入官方祭祀的名单。如元祐中,费县知县杨元永在向朝廷建议重修费县颜鲁公庙时言:
鲁公守平原,时禄山逆状未萌,公能迹其端。及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与其从兄首倡大顺,河北诸郡倚之以为金城,可谓能捍大患矣。其后为奸臣所挤,临大节挺然不屈,竟殒贼手,可谓以死勤事矣。今庙宇不能庇风雨,愿闻诸朝,少加崇葺,俾有司得岁时奉祠。[14]
在杨元永看来,颜真卿平定安史之乱、为国殉节的行为符合儒家所言“能捍大患”“以死勤事”的入祀原则,自应被载入祀典,接受官方祭祀。他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元祐六年(1091),宋哲宗“诏相州商王河亶甲冢、沂州费县颜真卿墓并载祀典”[13]2560。这不仅意味着颜真卿拥有了被祭祀的合法性,更意味着他忠臣烈士的形象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也正是颜真卿忠君爱国的品质与精神,让其成为统治者宣扬教化的标杆。官方对他的崇祀,主要目的在于“表忠义,劝来世”,更好地为政治服务。
三、元明仙传:神仙观念的世俗化转变
元明时期是颜真卿仙化故事的宗教化巩固期。受南宋以来道教教派勃兴的影响,神仙传记不仅在取材上更加广泛,反映的道教思想也从遇仙感悟、劝善教化到修行得道,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因此这一时期的颜真卿仙化故事集中出现于仙传中,并且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如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明代王世贞《有象列仙全传》、罗懋登《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大全》等书中均有相关记载。
从故事框架来看,元明时期的颜真卿仙化故事延续了宋代笔记的做法。但值得注意的是,赵、王、罗三人笔下的故事都有相同的结尾:“白玉蟾云:颜真卿今为北极驱邪院左判官。”而在道教构建的宗教世界中,北极驱邪院“乃三界纠察之司,万邪总摄之所”[15]。这一带有宗教色彩的补充,一方面明确了颜真卿尸解成仙后的去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颜真卿在元明时已被纳入道教神仙谱系。其实,早在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神霄派道士朱执中注《火师汪真君雷霆奥旨》,就对颜真卿的仙化去向作了进一步充实,其注曰:
(汪子华)遂与颜真卿同师白云先生张约,再师赤城司马先生承桢,受清静之道……颜真卿后亦得道,为卢杞所陷,奉使淮西,为李希烈所缢,遂藁葬于蔡州。事定后,其子孙寻其墓迁葬焉,见真卿之尸如生,人皆以为尸解云。真君得道飞升之后,亦接引颜真卿居雷部,亦真君之力云。[16]
在注文中,颜真卿早年师从白云先生张约学道,在尸解飞升之时,火师真君汪子华将其接引至雷部,成为雷部神仙。受宋徽宗大力崇道的影响,道教天心派在南宋以后得以发展和繁荣,名为“五雷天心正法”的系列法术在民间尤其盛行[17]。随后白玉蟾对其进行了发展,将雷部雷法隶于“北极驱邪院”,自称“上清大洞宝箓弟子、五雷三司判官、知北极驱邪院事”[18],并将唐代褚遂良、李阳冰、白居易等人设为驱邪院中神灵,其中称颜真卿“为北极驱邪院左判官”。在朱执中、白玉蟾等人的推动下,颜真卿被正式纳入道教的神仙谱系之中。
颜真卿能够进入道教的神仙谱系,与此时的道教发展密不可分。宋元时期不仅是道教教派分化繁衍的兴盛期,同时也是道教神仙谱系的定型期。除传统的正一、上清派,还出现了神霄、天心等新道派。为传教的需要,在官方支持下,各派对斋醮科仪和神仙谱系进行了整理,如北宋王钦若和南宋金允中、留用光、宁全真等都曾编写过谱系。他们在整理编排道教神仙系统的过程中,既继承与吸收了原始信仰、神话传说中的神灵,对所选神灵进行必要的加工,又根据道教发展和信众的需求进行了新的创造。颜真卿尸解成仙故事由来已久,经过文人的加工后,流传甚为广泛,民间影响力也较大,因此在编排时即被纳入。
此外,宋元时期神仙观念的世俗化也间接促进了颜真卿被纳入道教神仙谱系。宋元时期的道教试图做到修仙的宗教目标与关注现实的世俗道德融合,如净明道强调“忠孝建功”[19]。而这也是当时道教其他教派共有的追求,体现了这一时期神仙观念普遍世俗化的特点。颜真卿“为臣死节”的品质恰恰符合宋元时期神仙观念的特征,将其纳入道教神仙体系,不仅反映了道教修仙伦理从“出世”到“入世”的变化,也是道教世俗化趋势的集中表现。
四、明清戏曲:因果报应的伦理化表达
明清之际,颜真卿仙化故事流传广泛,一些戏曲也开始对其进行重新创作。较之于笔记和仙传,戏曲的容量和篇幅较大,因此明清时期的戏曲对颜真卿仙化故事进行了扩充和敷演。同时,戏曲艺术所具有的表演性、宣传性和受众广泛的特点,使得因果报应的伦理表达在此阶段的颜真卿仙化故事中得以凸显,其中以明代屠隆的《昙花记》和清代张照的《劝善金科》最具代表性。
这两部戏并不以颜真卿为主要人物,而是将仙化故事穿插在其他故事之中。在描写颜真卿的相关情节时,也不再将焦点集中于仙化过程,而是详细交代了其前因后果。如《昙花记》第十四出“奸相造谋”,揭露颜真卿被害的原因,第三十一出“卓锡地府”交代卢杞陷害忠良而遭审判的结果,第四十四出“群仙会勘”是颜真卿等人清算卢杞罪行的详细过程,第四十五出“凶鬼自叹”则是会勘过后,卢杞面对结果时内心悔恨的独白。如此一来,就形成了看似形制松散却又内在联系紧密的剧目设置。
《劝善金科》中也有同样的剧目设置。《劝善金科》康熙旧本的第一本第十二出、乾隆内府刊本的第一本第十四出“卢杞用计害忠良”与《昙花记》第十四出“奸相造谋”如出一辙[20]。康熙旧本的第九本第十二出“敕忠贞阴曹勘罪”、乾隆内府刊本的第九本第四出“对神明巨奸俯首”与《昙花记》第四十四出“群仙会勘”情节类似。此外,康熙旧本的第九本第十一出“囚逆贼狱底知非”与《昙花记》第四十五出“凶鬼自叹”也一脉相承。
不难发现,这两部戏在对颜真卿仙化故事进行戏剧改造时,人物刻画和故事情节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在人物刻画方面,重点从颜真卿转移到了卢杞。明清以前的笔记和仙传基本上通篇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讲述颜真卿早年的见闻和尸解成仙的经历,多忽略了卢杞这一形象。而作为颜真卿被害的始作俑者,卢杞在明清戏曲中的戏份被大量增加,这一时期的剧作者甚至还为他设置了“独角戏”,如《昙花记》中的“奸相造谋”“凶鬼自叹”与《劝善金科》中的“卢杞用计害忠良”。以后者为例:
〔卢杞白〕颜真卿这厮,颇有名声,百官倚重。但这厮每事执拗,面折下官,首当剪除。〔作思科,白〕有计了。李希烈背反朝廷,法当征讨,我不免草成一表,只说真卿重望老臣,遣他去说希烈,可不烦兵而下。奏过官家,定差这厮,不怕他不去。希烈凶恶异常,真卿倔强犹昔,眼见得断送这老儿也。〔判官作书簿科,卢杞白〕其余文武官员,重则诬他谋逆,轻则坐以奸贪,或赤其九族,或去其首领,或削籍金门,或窜身荒裔。此时谁不落胆惊魂,谁不钳口结舌,好计!〔判官持簿呈采访使者看科,卢杞冷笑科,白〕诸公,不要道我太狠,争奈骑虎之势,也不得不然了。[21]187-188
这出戏对卢杞明处造谋时的心理活动进行了详细地刻画。剧作家借助卢杞的独白,一方面说明颜真卿“颇有名声,百官倚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将其陷害真卿和其余文武官员的原因、具体计划、前后过程详细地展现在观众和读者面前。一个“好计”、一句“诸公,不要道我太狠”将其奸诈阴险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
在故事情节方面,明清戏曲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增加。
一是仙化升天情节的设置。明清戏曲对颜真卿死后去向不仅进行了明确,还对他成仙之后的经历进行了再创作。如《昙花记》第四十四出“群仙会勘”中真卿自言其乃是“上帝优叙死事之忠,遂证神仙之位”[22]387。而《劝善金科》乾隆内务府刊本第四本第八出“众仙侣把臂天庭”以整出戏的篇幅对真卿成仙过程和成仙后的见闻进行了详细描写。颜真卿不仅“蒙玉帝收录仙曹,阎君差金童玉女相送,竟上天堂”,升天之后,又与众仙家相继会面。而在此期间,颜真卿的唱调多为正宫调和中吕宫调,如“正宫引·三叠引”“中吕宫正曲·千秋岁”,表现的是升天之后轻松、喜悦的情绪,唱词也多描绘的是“俯瞰尘寰世,看齐州九点,城郭依微”的壮阔画面和“云中奏风外吹,一派仙音沸,去瞻依玉座,朝参丹陛”的热闹场景,表现了成仙后惬意的生活。
二是勘罪情节的增加。明清戏曲中的颜真卿仙化故事还对卢杞进行了惩罚。由于卢杞生前之事已成定文,留给后人可创作的空间不大,因此只能在他死后借助阴司审判的形式对其进行清算。在《昙花记》第四十四出“群仙会勘”中,屠隆安排了颜真卿、李白、李泌3 人会勘卢杞,清算了他谋害文武官员300 余人的罪业。《劝善金科》中的勘罪情节在《昙花记》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动,审案的程序显得更加规范。在乾隆内务府刊本的第九本第四出“对神明巨奸俯首”中,会审卢杞一案的是房玄龄、杜如晦和阎君,房、杜二人先历数了卢杞犯下的滔天罪行,最后阎君就卢杞案会审的结果与房、杜二人进行了商议:
〔阎君白〕二位大人,这厮罪恶滔天,决难轻恕。前在东岳殿下,会审诸奸,将这厮问成腰斩之罪,今日复审无异,正当按律施行。〔房元龄、杜如晦白〕阎君所言极是,须用严刑处治,以彰报应便了。[23]44
“复审”“按律”等细节的处理,彰显的是勘罪的合理与公正。勘罪情节的增加,是剧作家用艺术化的手法让恶势力得到应有的惩罚,并以此告慰含冤而逝的忠贞之士,让其冤屈得以昭雪。而善者升天成仙与恶者堕入地狱接受严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质上表达的是一种“惩恶扬善”的社会情绪。这种情绪在戏曲中的集中展现,实质上是明清时期因果报应思想的伦理化表达。
屠隆和张照对戏曲的教化作用有着清晰的认识[24]。《昙花记》和《劝善金科》的序言和凡例中即清晰地说明了创作目的:“世人好歌舞,余随顺其欲而潜导之彻,其所谓导欲增悲者,而易以仙佛善恶,因果报应之说,拔赵帜插汉帜,众人不知也……”[22]549“此记广谭三教,极陈因果,专为劝化世人,不止供耳目娱玩”[22]550,“假借为唐季事,牵连及于颜鲁公、段司农辈,义在谈忠说孝”[21]13。可见,明清戏曲中的颜真卿仙化故事以教化民众、挽救世风为宗旨,通过对前代故事的创作和改造,利用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刻画、细节的处理来宣扬因果报应的思想,最终达到教化的目的,虽系宗教剧,然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明清戏曲将颜真卿仙化故事与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相结合,一方面在结构上采用因果叙述模式,增强了戏曲的故事性和逻辑性,在主题上将因果观念融入小说情节,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戏曲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借助故事文本的深远影响和戏曲舞台表演的功能,为宗教思想的传播提供了载体与平台。
纵观颜真卿仙化故事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可以得知,它在不同的文化土壤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故事形态。正如韦勒克、沃伦所说:“各种艺术(造型艺术、文学和音乐)都有自己独特的进化历程,有自己不同的发展速度与包含各种因素的不同的内在结构。”[25]颜真卿仙化故事的独特演变历程不仅反映了自唐至清各个时期的小说、戏曲创作观念,承载着不同阶段的特定功能,更说明了故事文本和人物形象无不受到社会思潮、文学观念、宗教思想的综合影响,是时代文化与文学发展共同决定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