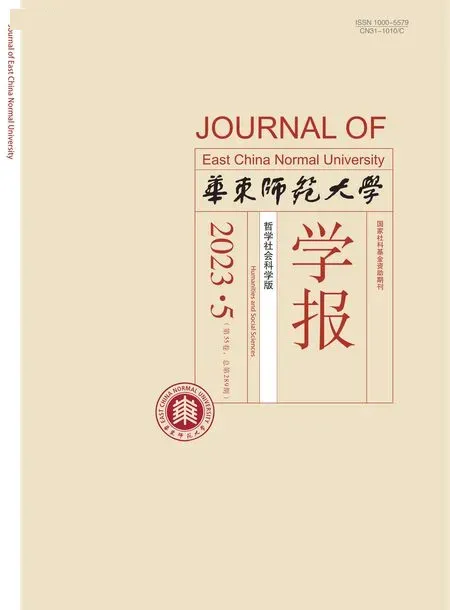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关系辨析
2024-01-03罗国强徐金兰
罗国强 徐金兰
一 关注战时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适用的紧迫性
由于战争是历史上最常见的社会现象,国与国之间应该和平相处的观念得到普遍接受,仍然需要经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①Hugo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libri tres, in English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J. Hill, M.Walter Dunne, publishing New York & London, 1901, p. 1.这正是普芬道夫以道德哲学为基础而构建的自然法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普芬道夫将人类视为道德共同体,共有的人性促使其成员对彼此负有责任,公民君主的主要责任是促进国家的安全和福利,自然法赋予他们对其他国家及其居民真正的道德责任;战争则是对人类自然状态的偏离,在自然自由的状态下的确存在一种必要的权利可以通过战争方式从食物的主人那里夺走食物,但这种权利只适用于所有者拥有超过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的时候。①Kari Saastamoinen, Pufendorf on the Law of Sociality and the Law of Nations, The Law of Nations and Natural Law 1 625-1 800,edited by Simone Zurbuchen (ed.),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9, pp. 107-129.这事实上反映了普芬道夫所阐述的自然法中最普遍和最必要的义务,即不伤害他人的义务。
普芬道夫将这种义务推论到国家关系和国际法规范中并总结道:只有自然法才能在法律上规范国际关系,国际法是由各国的自然法组成的,②Stephen Hall, The Persistent Spectre: Natural Law,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Limits of Legal Positiv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2, No.2, 2001, p. 274.直接约束处于自然状态的主权国家③Geoff Gordon, Natural Law in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Linear and Dialectical Presentation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e Orford, Florian Hoffmann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89-291.。他具体将国际法视为一套对他人的绝对自然义务,将国家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一种建立在道德履行和平义务与不受干扰地行使国家自然权利之间的相关性之上的道德关系,并认为这种和平义务必须适时地转化为国际关系的实践。④Vanda Fiorillo, States, as Ethico-Political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Samuel Pufendorf, System, Order,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Earl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egal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egel, Stefan Kadelbach (ed.) et 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00-215.而国际法领域逐渐发展出的各交战国或冲突各方在发生冲突时应当遵守的国际人道法规则,不仅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和平义务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巨大差距,尤其是在国际人道法某些部分内容含糊不清时,战斗人员应如何界定自己的道德义务。⑤Lisa Hecht, Law and Morality at War Adil Ahmad Haqu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100, Iss.907-909: 150 years of humanitarian reflection, 2018, p. 445.事实上,在国际人道法缺失的地方,战斗人员可以利用自然法为其提供行动指导。武装冲突方也应该在军事必要和人道考虑之间寻求平衡,履行对他人的自然义务,以促进国际和平。
笔者拟对武装冲突的不同局势下,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具体规范之间是否存在规范冲突以及存在规范冲突时能否予以解决进行深入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弥补国际人道法在武装冲突中的某些法律空白,解决理论上可能存在的具体规则之间的规范冲突,促进国际法律制度的“系统整合”⑥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inalized by Martti Koskenniemi, UN Doc A/CN.4/L.682, 13 April 2006, p. 206.和协调一致;也有利于判断在不同局势下武装冲突各方应受到何种法律规范的优先调整,同时为军事指挥者提供较为清晰的行为范式的选择指南。
二 对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关系的观点分歧和司法判例
在不同的国际法律制度中,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比较接近。国际人道法受到“人性原则”和马尔顿条款中“公共良知”的约束,国际人权法试图保护人类尊严。⑦Anthony E Cassimatis,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56, No.3, 2007, p. 628.随着当代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出现的融合趋势,两个法律体系的内容彼此影响。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战争时期,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和平时期。并且一些国际法院判例以及普遍和区域性的人权机构的判例基本已经认定国际人权法可以适用于武装冲突。①欧洲人权法院承认《欧洲人权公约》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占领局势及非国际武装冲突。参见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sayeva, Yusupova and Bazayeva v. Russia, Judgment of 24 February 2005, paras.166-167; Isayeva v. Russia, Judgment of 24 February 2005, paras.172-173; Noam Lubell, Challenges in Applying Human Rights Law to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87, No.860, 2005, pp.739-741。美洲国际间委员会和人权法院承认《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和《美洲人权公约》也适用于武装冲突。参见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Baˊmaca Velaˊsquez v. Guatemala, Judgment of 25 November 2000, Series C,No.70, para.209;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the Serrano Cruz Sisters v El Salvador, Serrano Cruz and Serrano Cruz v El Salvador, Preliminary objections, 23rd November 2004, para.112;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Juan Carlos Abella v. Argentina, Case 11.137, OEA/Ser/L/V/II.97, Doc. 38, October 30, 1997, para.158。目前普遍接受国际人权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观点,但欧洲人权法院在“格鲁吉亚诉俄罗斯”第2 号案件中指出《欧洲人权公约》不能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实际战斗阶段,拒绝审查俄罗斯的特定攻击是否符合《欧洲人权公约》。参见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se of GEORGIA v. RUSSIA (II), Application no.38263/08, Judgement of 21 January 2021, paras.138-139。因而,在武装冲突中,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有所重叠、补充或冲突。这种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十分突出。
多年来,两者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一直是政策辩论、司法判决和学术意见中备受关注的问题。对其产生的不同观点和认识差异也逐渐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类别。
在学术界,通过对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关系的讨论而引出的不同观点,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别:区分论、包含论、互补论。支持区分论的学者们认为,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当武装冲突爆发时,国际人道法将取代国际人权法的适用,因而其法律框架没有共同适用,两者不存在冲突。②G. Draper,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Reflections on Law and Armed Conflicts: The Selected Works on the Laws of War by the Late Professor Colonel G. I. A. D. Draper, OBE, Michael A. Meyer and Hilaire McCoubrey (eds.), Springer, 1998, p. 145,p. 149.包含论的主要观点是国际人道法仅是国际人权法的一部分。③一些学者认为国际人权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国际人道法属于“战争或武装冲突中的人权法”。参见徐显明主编:《国际人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年,第29 页。由于人权和人道原则促使国际人道法的人性化,两者之间合并趋势越发明显,而如果两者有所区分,则根据国际人权法的标准调整国际人道法的适用。但是,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国际人道法的独特作用,它与国际人权法在适用途径、宗旨目的、个人意愿选择等方面均存在差异。④朱文奇:《国际人道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453—460 页。
互补论认为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这两个法律体系基本互补,相互促进。它被认为是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最合理和最连贯的解决方案;它表明国际社会明确设想了两套彼此独立但本质上相辅相成的法律体系来解决国际实践中的现实问题,适用与特定情况最密切相关或者专门设计的规则,且为允许或者禁止的内容提供最详细的规则都是有意义的。⑤Terry D. Gill, Some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A Plea for Mutual Respect and a Common-Sense Approach, T.D. Gill et al. (e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16,2013, p. 256.“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被认为是有用的工具。互补论也强调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31 条第3 款第3 项所采用的解释方法,即在解释一项规范时,应该将“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与上下文一同考虑。
互补论的观点合理地认为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存在界限,也认识到两者之间兼容互补的可能。但是,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只是相互关系的最低限度。互补论实际并未真正指明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它单纯地认为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整个法律体系之间并不存在规范冲突。
国际法院的相关判例也相对支撑了互补论的核心观点。国际人权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首次表述出现在1996 年的“关于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以下简称“核武器案”)中。法院明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保护在战时并不停止,除非某些规定在国内紧急状态下可予以克减”,且“什么是任意剥夺生命的标准则由适用的特别法,即旨在规范敌对行为的适用由武装冲突的法律来确定”①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of 8 July 1996, ICJ Reports, para.25.。法院并未整体审查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两个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而是考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6 条所载的生命权与具体国际人道法规则之间的关系。
在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建造隔离墙的法律后果”(以下简称“隔离墙案”)的咨询意见中,法院认为“人权公约所提供的保护在武装冲突期间并不停止”,“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三种情形,即某些权利是国际人道法的专属事项,某些权利是人权法的专属事项,还有些权利是国际法两个分支的共同事项。”②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l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Advisory Opinion of 9 July 2004, ICJ Reports, para.106.法院在本案中认为,相对国际人权法而言,国际人道法是特别法。但是它将“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直接援引为解释性规范,却不解释这一原则在法律推理的过程中是如何导致了后续的法律后果。
在“刚果共和国诉乌干达”一案中,法院重申“国际人权法适用于一国在其本国领土之外,特别是在被占领土实施管辖权的行为。”③Case Concerning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DRC v. Uganda), Judgment of 19 December 2005, ICJ Reports,para.216.但是,法院只是简单地列举了乌干达违反的人权规定,却没有审查占领国在人权方面的立法权利。因而,各国仍然缺乏同时适用这两种法律体系的指南。④Tom Ruys and Sten Verhoeven, DRC v. Uganda: The Applic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Law in Occupied Territories,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Law: Towards a New Merger in International Law, N. Quenivet,R. Arnold (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8, p. 195.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争端”中,法院认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在武装冲突期间无论如何都适用,其也认定格鲁吉亚所指称的行为似乎可能违反该公约规定的权利,即使其中某些指称的行为也可能受到包括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其他规则的管辖。”⑤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Georgia v. Russian Federation), Order of 15 Oct. 2008, ICJ Reports, para.112.
从国际法院和某些人权机构对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关系的一般做法来看,它们通常将两者之间的关系描述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⑥国际法院在“隔离墙案”和“核武器案”中,将其视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在“刚果诉乌干达”一案中没有明确如此表达。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争端”中,国际法院面临着要求发布临时措施的请求,事情的紧急性导致法院采取了一种新方式阐释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关系,相较之前的案子,它并未将两套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区分为三个类别。国际法院的这些国际实践不具有连贯性。一方面,“特别法优先原则”作为解释性规范被直接援引,却不说明这一原则的适用如何导致了法律后果。⑦Case Loncerning Armed Activities on Territory of the Longo (DRC v. Uganda), Judgment of 19 December 2005, ICJ Reports,para.178.另一方面,这一法律原则也更多地作为法律结论发挥作用,即一旦进行了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分配,就不需要对具体事实进行深入的论证和分析,这种类型化的做法过于简化事实和法律背景,似乎引起对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两者之间关系的误解。①Bill Bowring, Fragmentation, Lex Specialis and the Tensions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Security Law, Vol.14, No.3, 2009, p. 485.总之,国际法院的这种推理过程类似一种自我参照,其对“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的考察仍停留在形式方面。它认为特别法本身就足以提供法律依据,从而忽视了对于事实特殊性、规则有效性等要素的考察。国际法院在后来的案件中参照先前判例直接援引这一原则,并得出了国际人道法在武装冲突中是特别法的结论,接着优先适用国际人道法。由此,这种法律推理过程在内部实现了逻辑循环。
这种做法潜在的后果可能是在武装冲突的每种情况下,国际人道法作为整体都将是更加具体的法律体系,甚至导出国际人权法将不适用于武装冲突的结论。这种结果也是十分危险的,例如保护关塔那摩被拘留者的国际人权法可能被作为特别法的国际人道法所取代,国际人权法最后没有为其赋予任何权利。②Françoise J. Hamps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Human Rights Treaty Bod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90, No.871, 2008, p. 550.但目前国际社会还未发展出专为武装冲突的综合性、专门性、全面性的法律制度,难以找到与实践完全对应的国际人道法规则,在武装冲突中国际人道法确有借鉴国际人权法的需要。
针对武装冲突中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关系辨析,以往的学者观点和司法判例基本上认为在武装冲突中国际人道法是特别法,国际人权法可以补充国际人道法。但是,可以想见,基于两套法律体系中的具体规则对不同情势的同时适用,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的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也表明“特殊性”才能决定哪个具体规则能够作为特别法得以优先适用。
因而,笔者将深入分析“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这一原则,分析这一原则所包含的对“特殊性”的衡量标准和考量要素,以明确这一原则在辨析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关系中的实际作用。
三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在辨析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关系中的适用条件和具体作用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lex specialis derogate legi generali,简称为“特别法优先原则”)源自罗马法法律体系,其内涵是在受到具体规则特别调整的场合,该具体规则将取代更为一般的规则发挥作用。对于这一原则,格劳秀斯认为:“应该优先考虑最具体和最接近手头事项的条款,因为特别规定通常比一般规定更加有效。”③Hugo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edited by James Brown Scott, 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25, p. 428.他提出了“特别法优先原则”的两个标准,即有效性和相关性。普芬道夫和瓦特尔也采取类似观点,认为应当考虑最接近实现目标的特殊法律,而且它比一般法有更少的例外,秩序更加精确。④Samuel Pufendorf, Le droit de la nature et des gens ou système général des principes les plus importants de la morale, de la jurisprudence, et de la politique, Translate by J. Barbeyrac, Basle: Thourneisen, 1732, Bk. V, Ch. XII, p. 139; Emmerich de Vattel, Le droit des gens ou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 appliqués à la conduite et aux affaires des nations et des Souverains, 2 vols, Londres, 1758, Tome I,Livre II, Ch. XVII, p. 511.尽管学者们对“特别法优先原则”的看法众说纷纭,但是他们都认为在不同规则可能存在冲突时,存在一规则相对另一规则得以优先适用的标准,即特别法之所以特别的标准。
“特别法优先原则”的适用条件并非规范冲突的存在,而是两套规则对同一事项同时有效且同时适用。而对规范冲突的认定大致上从有关条约必须有相同当事方、条约适用于相同实质事项、不同条约规定的义务相互排斥三个方面着手。①Report of the WTO Panel, Indonesia-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WT/DS54/R, WT/DS55/R,WT/DS59/R, WT/DS64/R, 2 July 1998, para.14. 28, p.335, footnote 649.其中,义务相互排斥是规范冲突认定的关键。规范冲突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分,本文拟采用狭义的规范冲突②狭义的规范冲突仅限于规则义务的冲突,即如果两套规范之间,其中一套规范所产生的义务使得承担义务者不能履行另一套规则所产生义务,两套规则不能并行不悖地适用,则认定两套规范之间存在冲突。广义的规范冲突包括义务之间的冲突、义务与权利之间的冲突等。参见廖诗评:《国际法中的特别法优先原则》,《法学研究》 2010 年第2 期,第187 页。,即仅限于规则义务的冲突。
判断两套规则之间是否存在规范冲突,首先要认识到“特别法优先原则”的性质,即“特别法优先原则”是属于条约解释的一部分还是属于规范冲突的解决工具。有学者认为“特别法优先原则”是“一整套完善的法律解释手段或系统的一部分,和在实际出现时调和法律文件和义务冲突的方法”。③Terry D. Gill, Some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A Plea for Mutual Respect and a Common-Sense Approach, T.D. Gill et al. (e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16,2013, p. 259.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特别法优先原则”具有双重作用:在没有规范冲突时,这一原则是法律体系解释的一部分,目的是强调平行的法律文书所产生的义务并对产生的所有义务予以充分考虑;在义务似乎有所冲突时,在解决具体冲突所必需的范围内,优先考虑更具体的规则。
另有学者认为在解决规范冲突时,特别规则可以被视为一般规则在特定情形下的运用或一般规则的例外。④Martti Koskenniemi, Study on the Function and Scope of the Lex Specialis Rule and the Question of “self-contained regimes”:preliminary report by Martti Koskenniemi, Chairman of the Study Group, [ A/CN.4/ ] ILC(LVI)/SG/FIL/CRD.1, 2004, pp. 31-33.例如,国际人道法被视为和平法完全适用的例外。⑤Orna Ben-Naftali and Yuval Shany, Living in Denial: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srael Law Review, Vol.37, No.1, 2003, p. 42.这种观点认为“特别法优先原则”是法律技术或方法,其并不直接阐释规则的含义。
本文比较赞同“特别法优先原则”具有双重作用的观点。不可否认的是,明确规则的详细内容在先,分析规则的特别法地位在后。条约的解释大致规定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的第31-32 条中,解释条约时所援引的依据包括以上条款提到的通常含义、上下文、宗旨和目的、嗣后实践等要素。通过各种解释规则和公认的解释方法,如文本法、历史法或目的论等,可以相对明确一项国际法规则的内涵和外延。另外,第31 条的精神,即为约文必须被推定为各条约当事国的意思的权威性的表示,其解释的出发点也是阐明约文的意义。⑥李浩培:《条约法概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351 页。尽管在此公约中没有明确载有“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但是这一原则根据第31-32 条作为条约的解释方法得到了广泛适用,其作为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的地位有所巩固。⑦Conor McCarthy, Legal Conclusion or Interpretative Process? Lex Specialis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Law: Towards A New Merger in International Law, N. Quenivet, R. Arnold(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8, p. 104.“特别法优先原则”所包含的有效性、相关性等标准也已经囊括了明确规则内容这一步骤。
接着,这一原则将规范之间可以兼容的部分交由条约解释方法予以解决,包括《维也纳条约法》第31 条第3 款所采用的解释方法,这与互补论的观点类似,此时两套法律规则之间并不存在规范冲突。它限缩了规范冲突的范围,反对将规范冲突无限泛化的观点,对规范冲突采取严格的界定。另一方面,在可能出现规范冲突时,它考虑“特殊性”的标准,先审查条款所规定的内容,并考虑当事方的意图,利用一切相关的解释工具、原则、方法,总结所有事实情况,以协调一致和合乎逻辑的方式调和可能产生的义务冲突。
“特别法优先原则”不是任何一个法律体系的专有领域,从其适用的前提和条件,可以认识到具体事实情况决定着两个法律体系的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以往司法判例中出现的类型化的做法,掩盖住了一套规则具有特殊性的原因,忽视了不同规则所体现出的缔约国意图等因素,由此导致了对“特别法优先原则”的混乱认识。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特别法的有效性、相关性、针对性等标准,对于在武装冲突中需要及时做出选择或做出判断的主体而言,仍然有些抽象。例如,国际法委员会曾经列举了特别法的某些参考因素:“对具体情况的敏感性、反映国家意志的能力、具体性、清晰性、明确性。”①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inalized by Martti Koskenniemi, UN Doc A/CN.4/L.682, 13 Apr. 2006, p. 64.还有学者认为,需要结合具体规则,不同法律体系下的规则可能相互冲突,但在必须决定何者优先适用时,最重要的因素是规则的准确性、清晰性以及对特殊情形的适应性。②Andrea Gioia,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Monitoring Compliance with Humanitarian Law in Armed Conflict, in Orna Ben- Naftali (e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p. 214.以上这些标准对不同局势中的冲突方所发挥的指导作用并不显著,难以为武装冲突中的军事决策者提供更加稳定而具体的行为范式的参照标准。这也产生了进一步细化特别法衡量标准的需要。
总之,将对“特别法优先原则”的认识,推论到对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关系辨析时,“是否存在冲突以及如何处理表面冲突取决于对相关规则的解释方式”③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inalized by Martti Koskenniemi, UN Doc A/CN.4/L.682, 13 Apr. 2006, p. 207.。对“特殊性”的考虑则是重要内容。在武装冲突中,要阐明“特别法优先原则”在法律推理中如何适用,“仅仅认定一套原则为特别法并不足以实现对可适用的法律标准和特别规则之间关系的性质的充分理解”。④Conor McCarthy, Legal Conclusion or Interpretative Process? Lex Specialis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Law: Towards A New Merger in International Law, N. Quenivet, R. Arnold(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8, p. 103.特别法的优先地位应当根据武装冲突中的不同事实情况予以个案分析。
因而,笔者将结合武装冲突的不同局势下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中关于使用武力的具体规则,分析冲突方应采取什么行为范式或者采取的行为范式是否具有正当性,以总结出特别法分析框架所需要的较为明确的法律标准和事实要素。
四 不同武装冲突局势下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之范式与适用
在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中,使用武力的规则并不相同,这种差异也反映在敌对行为范式和执法范式上。在武装冲突的不同局势下,如非占领的国际性武装冲突、占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冲突方所采取的使用武力的行为范式应当在综合具体事实情况的各种要素后做出选择。反之,这些法律标准和事实要素也是判断特别法优先地位的重要内容。
(一)受国际人道法调整的敌对行为范式和主要源于国际人权法的执法范式
国际人道法只适用于武装冲突,①Alexander Orakhelashvili,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Fragmentation, Conflict, Parallelism, or Converg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9, No.1, 2008, p. 162.包括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所有当事方,其权利义务是横向的。一般而言,国际人权法的适用范围是在一个国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有效控制内的地区或人员②例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2 条第1 款明确“国家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欧洲人权公约》第1 条认为“应当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个人”;《禁止酷刑公约》第2 条载明“在其管辖之下的任何领土内”;以及许多国家认为人权条约的管辖范围是指在该国权力或有效控制范围内的人员。,其基本上是以“有效控制”这一事实标准来确定适用的。并且,根据《日内瓦四公约》 共同的第三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 的序言,在非国际武装冲突中,保障人权的义务也受到对其领土行使“有效控制”的约束。③由于人权法在战争时期仍然适用,并且适用于国家行使“有效控制”的领土,因此有学者提倡制定“有效控制”的标准,如克服对手抵抗、军队可以在另一国家的特定领土不受阻碍地执行任务、普通的公共秩序体系已被消除、军队对领土及领空行使主权;且他认为达到标准后人权法的规定应当适用,并且应根据“有效控制”的水平适用人权法的标准,不能指望一个国家在失去对发生侵权行为的领土部分控制时保护其国民免遭叛乱分子或占领军侵犯人权的行为。参见Patrick Knäb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The New Zealand Postgraduate Law, e-Journal, No. 4, p. 18。它的权利义务方式是纵向的。
尽管两套法律体系在武装冲突中均可适用,但是它们对于使用武力的规定有所差异。国际人道法设定作战规则,限制武装冲突带来的人身、财产等损害。使用武力需要遵循国际人道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军事必要原则以及避免不必要痛苦原则等。例如,军事必要性是指在行动中使用武力的种类和手段,对于以最小的时间、生命和物质资源的消耗实现敌人屈服的目的而言是合理必要的。国际人道法中的必要性的标准更加自由。而且,在国际人道法中,比例原则不是对目标和平民之间生命权的判断而是对军事利益和附带损害的评估。
相比而言,国际人权法对使用武力的实体和程序限制较多,其基本要求是将使用致命武力作为最后的手段。一方面,主要人权条约均规定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欧洲人权公约》 则进一步指出使用武力剥夺生命的三个例外条件④《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 条第1 款、《美洲人权公约》第4 条第1 款、《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4 条,均规定了生命权的内容。而《欧洲人权公约》第2 条第2 款规定了剥夺生命的例外条件,该公约的第15 条第2 款也规定了紧急状态下的克减条件,即“因战争行为引起的死亡”。。人权条约表明使用武力的前提是存在迫在眉睫的严重违法行为,且除了使用武力以外别无他法。⑤参见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第9、10 条。并且第9 条是一个任择性条款,并不要求这些使用武力的条件同时满足。“麦卡恩诉英国案”也表明“绝对危急情况”是指“确定国家行动在民主社会中是否是必要的时候所通常适用的必要性检验”⑥McCann v.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of 5 September 1995,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para.149.,国际人权法对必要性的标准更加严格,规定了使用武力的“严格”或“绝对”必要性标准。人权机构在相关案件中对这些条款进行解释时,也会确认使用武力的主体是否已经采取了充分的预防措施,以避免造成平民伤亡。⑦在“居莱奇诉土耳其”案中,法院认为“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2 条第2 款第c 项的规定,使用武力必须在目的和手段之间权衡”。Güleç v.Turkey, Judgment of 27 July 1998,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para.67. “纳霍娃诉保加利亚案”中,法院认为“实施合法逮捕的合法目的只能证明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将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是正当的,即使不使用致命武力可能导致有机会逮捕逃犯而使其失踪。”Nachova v. Bulgaria, Judgment of 6 July 2005,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para.95。另外,在国际人权法中,比例原则要求必须适当考虑目标人员的生命权,以便在剥夺其生命时与执法人员或附近其他人的生命或肢体受到具体和直接的威胁相平衡。
对应地,在武装冲突的国际实践中,出现了两种较为常见的行为范式,即敌对行为范式和执法范式。①关于“敌对行为范式”和“执法范式”的称谓,参见W. Hays Parks, Part IX of the ICRC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Hostilities”study: no mandate, no expertise, and legally incorre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 42, No. 3, 2010, p. 812。在武装冲突的局势中,武装部队和军事官员对致命或潜在致命武力的使用受到两种不同范式调整:源自国际人道法的敌对行为范式②虽然敌对行动模式是任何武装冲突的固有模式,但它绝不是与武装冲突的整个法律制度同名。构成任何武装冲突一部分的许多活动和局势,例如对个人或领土行使权力、维持公共秩序以及拘留等,并不构成敌对行动范式的一部分。与主要源自国际人权法的执法范式。
“敌对行为和执法范式并不构成新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框架,而是相对于对分别属于人道法和人权法并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中使用武力情形的不同规范的描述。”③格洛丽亚·加焦利主编:《武装冲突中的武力使用:敌对行为范式与执法范式间的相互影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专家会议报告,2012 年1 月,第8 页。具体而言,敌对行为范式推定可以使用合法手段对战斗员和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使用武力,避免非必要的损害,而执法范式将使用武力作为保护生命的最后手段,任何受执法范式约束的行动都必须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以便减少诉诸致命武力。④Terry D. Gill, Dieter Fleck, Conceptual Distinction and Overlaps between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Conduct of Hostilities, th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Military Operations, Terry D. Gill and Dieter Fleck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71.敌对行为范式和执法范式,在必要性、比例性、预防性等方面存在着与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类似的差异。因此,两种行为范式受到不同法律体系调整而有所差异,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有所不同。
另外,武装冲突的存在是适用敌对行为范式和执法范式的先决条件。一旦判断武装冲突存在,在这两种行为范式之间做出选择意味着如何根据不同的局势决定以最适当的方式适用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
(二)在武装冲突的不同局势下敌对行为范式和执法范式的选择
在利用“特别法优先原则”辨析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关系时,通过判断冲突一方在某种具体局势下应该采取什么行为范式或者评估该冲突方在这种局势下所采取的行为范式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总结出有哪些法律标准或者事实要素对具体规则的优先适用施加了影响。
1.非占领的国际性武装冲突
目前,将武装冲突区分为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的二元法比较普遍,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 也在共同的第二条和第三条阐释了它们的内涵。⑤《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的第二条定义了国际武装冲突,而共同的第三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定义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目前对武装冲突的这种二元分类得到了普遍接受。参见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How is the Term “Armed Conflict”Defined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Opinion Paper, March 2008, p.1. Available at:https://www.icrc.org/data/rx/en/assets/files/other/opinion-paper-armed-conflict.pdf; Dapo Akande, Classification of Armed Conflicts, The Oxford Guide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Ben Saul and Dapo Akande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29。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国际性武装冲突分为两种类型加以讨论,即非占领的国际性武装冲突和占领,前者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武装部队之间的冲突,后者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占领。在非占领的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敌对行为范式和执法范式的区分度较大。而在占领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随着国际社会实践的发展,抵抗运动、反叛运动等新趋势使得执法范式和敌对范式之间的区分不甚明显,这也为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关系辨析增加了困难。
一般而言,由于国际人道法的规则适应了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基本现实,体现了各国对敌对行动的意图,涉及个人作为战斗人员或平民的地位、某人的官方职责或某人是否属于某一特定团体等问题,因而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国际人道法为与武装冲突有直接相关的所有行动提供了敌对行为范式。①法院认为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背景导致俘虏战俘和拘留对安全构成威胁的平民,是国际人道法适用的特征。参见Hassan v.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of 16 September 2014,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para.104. 上诉分庭认为肇事者的行动与武装冲突密切相关,对战争罪和纯粹的国内犯罪进行区分。参见Prosecutor v. Kunarac et al., IT-96-23 & 23/1, Appeals Chamber, 12 June 2002, paras.55-58。例如,国际人道法允许对合法目标使用致命武力,但需符合国际人道法对使用武力的原则和规则,其中合法目标包括国家正规武装部队的成员、属于冲突之一方的非正规武装部队以及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②尼尔斯·梅尔泽:《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定义的解释性指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09 年,第25 页。同时,对于盗窃或谋杀这类与武装冲突没有联系,在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中同样存在的问题,执法范式优先适用。可见,在非占领性的国际武装冲突中,敌对行为范式和执法范式的区分较为明显,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相分离的,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与特别法的优先地位并无直接联系。
此外,还有一种执法范式占据上风的情况。敌对行为本身意味着对任何人和领土缺乏有效控制,冲突方未能或者尚未成功地击退某一地区的特定的有组织的抵抗,不再行使公共权利,或者失去对领土的控制,都是缺乏控制的情况。但“如果一国实际上对个人行使权力或权威,尽管有关行动是在领土控制之外进行的,其仍属于该国的属人管辖范围。”③Terry D. Gill, Dieter Fleck, Conceptual Distinction and Overlaps between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Conduct of Hostilities, th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Military Operations, Terry D. Gill and Dieter Fleck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67.例如,一国对武装冲突中的被俘军事人员行使管辖权,其并不以存在属地管辖权为前提,而只是依据实际行使的权力或权威。此时使用武力则受到执法范式的影响。
总之,在非占领的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在与武装冲突直接相关的行动中,敌对行为范式是常见行为范式,国际人权法仅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得以适用,正如上述的对被俘军事人员行使的属人管辖权。
2.军事占领
在军事占领局势中,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的同时适用的情形更为复杂,敌对行为范式和执法范式的区分更为困难。
1907 年《海牙章程》 第42 条为占领设定了法律标准,“领土如实际上被置于敌军当局的权力之下,即被视为被占领的领土。占领只适用于该当局建立并行使其权力的地域。”从这一条款中可以发现,占领的成立意味着敌方当局替代了被占领土上的主权政府而行使其权力。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著作、军事手册、国际判例将有效控制的概念作为占领成立的核心要素,④尽管无法在国际人道法条约中找到“有效控制”的概念,但这一概念与占领成立的条件紧密相关。领土在其实际处于占领者的控制或管理之下时才是被占领的。参见Daniel Thürer and Malcolm MacLaren, “Ius Post Bellum” in Iraq: A Challenge to the Applicability and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p. 8. Available at: https://www.ivr.uzh.ch/dam/jcr:00000000-528e-0b9e-ffffffff93869fca/FSDelbrueck.pdf; United Kingdom, Ministry of Defence, The Manual of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2004, paras.11.1-11.3. See Prosecutor v. Tadic, Judgment, No. IT-94-1-T, ICTY, Trial Chamber, 7 May 1997, Judgement, para.580.认为有效控制以事实说明了占领定义中的“权力”的内涵。
尽管《海牙章程》 并未规定如何评估有效控制的程度,以及什么程度的有效控制才能实现占领,但是有效控制意味着事实上或法律上的管辖权。在武装冲突中有效控制的概念指向了一种法律事实。其中,“控制”意味着在其控制的部分国家领土的范围内行使局部管辖。①罗国强:《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的界定与原则》,《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5 期,第84 页。实现对外国领土的某种程度的有效控制即可导致占领法的适用。有学者甚至认为占领是一个有效控制程度的问题。②Yoram Dinste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Belligerent Occu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2.
具体而言,尽管在有效控制的构成要素上存在着观点分歧,但仍然可以从中总结出对有效控制标准的一般理解。在“刚果诉乌干达”一案中,国际法院在分析“一国是否构成战时法意义上的占领国时,需要收集足够的证据证明干涉国在有关地区建立并行使权力”,即乌干达是否“已经用自己的权力取代了刚果政府的权力。”③Case Concerning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DRC v. Uganda), Judgment of 19 December 2005, ICJ Reports,para.173.前南庭在“纳莱蒂利奇”案中也认为确定占领需要满足占领国取代原政府当局、足够的军事部署、临时的行政管理机构、向平民执行命令等条件。④Prosecutor v. M. Naletilić and V. Martinović, International Residual Mechanism for Criminal Tribunals, Judgment, Case No. IT-98-34-T, Trial Chamber, 31 March 2003, para.217.《英国军事手册》 提出“审查有关地区,并确定是否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前政府已丧失在该区域公开行使其权力的能力;第二,占领国能够用自己的权力取代前政府的权威。”⑤United Kingdom, Ministry of Defence, The Manual of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2004, para.11.3.可以将构成有效控制需要满足的要素大致总结为:占领方已经取代被占领地政府当局的公权力、被占领土的政府当局无法对该地区行使自己的公权力、占领方持续在被占领土部署军队。⑥Tristan Ferraro, Determining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an Occup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94, No.885, 2012, p. 143.确立占领后,国际人道法中关于占领的规则可以适用,占领方也需要承担占领法项下的法律义务和相应权利,例如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能。⑦根据第43 条占领国的主要义务之一是采取一切措施,在可能的范围内恢复和确保公共秩序和安全,这一条款对占领当局课以执法义务。这一义务也反映在第64 条中。
那么,占领中的有效控制与国际人权法的适用所要求的控制有什么区别吗?占领状态是否自动导致可以域外适用人权的“有效控制”?国际法院在“刚果诉乌干达”一案中认为《海牙章程》 的第43条规定占领方的义务包括“确保对适用的国际人权法规则的尊重的义务”。⑧Case Concerning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DRC v. Uganda), Judgment of 19 December 2005, ICJ Reports,para.178.这也意味着占领国为了达到国际人权法的目的的有效控制。占领国和国际人权法适用于被占领土的有效控制的标准大致相似,即实质的有效控制。占领国与被占领土的政府处于相似位置,因而占领国,至少在占领成立之后,能够通过有效控制承担相应的人权义务。本文也主要分析占领成立后,占领国同时承担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义务的情况。
军事占领是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状态。构成军事占领法的相关规则主要调整占领国与被占领领土的居民之间这种独特的关系。⑨See Kenneth Watkin, Use of Force during Occupation: Law Enforcement and Conduct of Hostiliti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94, No.885, 2012, p. 277.与此对应,占领国可以对与武装冲突明显相关的问题适用敌对行为范式,而对于盗窃、犯罪等与冲突无关的问题适用执法范式。此外,由于在实践中,执法范式的前提是占领国因其对领土的有效控制而有义务维持公共安全、法律和秩序,这种权威足够强大而稳定,因此可以认为“执法范式具有默认适用性”。①Terry D. Gill, Dieter Fleck, Conceptual Distinction and Overlaps between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Conduct of Hostilities, th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Military Operations, edited by Terry D. Gill and Dieter Flec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76-77.对于占领国而言,叛乱活动以及武装抵抗运动不仅构成对公共秩序的威胁,也构成军事威胁,因而,执法范式原本是为了应对被占领土内的平民,后来也可以扩展成旨在打击叛乱团体实施的犯罪行为和构成反叛乱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
暴力烈度和有效控制影响了占领局势中行为范式的选择和转变。一方面,如果武装抵抗团体具有组织性,将武装团体成员视为战斗员,由于其在被占领土中所组织的活动具有极端暴力性,那么仅仅适用执法范式可能无法对这些有组织的武装抵抗活动进行规范。认识到此时的复杂情况,可以采取平行适用的方法,对于具有持续作战职能的有组织的武装团体的成员或者直接并正在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适用敌对行为范式;而对没有从事敌对行为、但参与了暴动、孤立而不时发生的暴力行为和其他类似性质的行为的平民,适用执法范式。在实践中,不同行为范式的平行适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在警察部队和军队各自的理论、训练和装备中。②See David H. Bayley and Robert M. Perito, The Police in War: Fighting Insurgency, Terrorism, and Violent Crime,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0, p. 53.
另一方面,原本不构成武装冲突的暴力活动随着持续时间的加长或者暴力烈度的增加,行为范式也会根据行动的可能性而发生转变。暴动、孤立和不时发生的暴力行为原本并不构成武装冲突,但一定程度反抗活动可累积成为国际性武装冲突。换言之,本来对其抵抗活动可以适用执法范式,但随着严重程度、时间的持续,在其他手段无效或者没有实现预期结果时,占领国也可能对其适用敌对行为范式。这种武力升级程序在占领局势中更加明显。
执法范式到敌对行为范式的转变,原因可能在于执法范式的内在要求,因为执法范式需要占领方对某一领土具有较高的控制程度。如果适用执法范式无法对需要处理的威胁形势进行打击,敌对行为范式可能是占领国在实践中更有倾向性的选择,这也是适用特别法的“有效性”和“具体性”等标准的需要。但是,有效控制程度不是使得执法范式优先适用的唯一因素,还需要与暴力烈度、目标潜在身份、使用非致命手段的可行性等因素结合考虑。例如,在“以色列反酷刑公共委员会诉以色列政府”案中,以色列最高法院确认了可能影响逮捕、调查和审判优先性的因素,但也指出,虽然采取以上措施的可能性有时根本不存在或者存在较大风险,但是它是一种应当一直考虑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交战占领的条件下,采取这些执法措施可能是实际的。③Public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in Israel v. Government of Israel, HCJ 769/02, Judgment of 11 December 2005, the Israeli High Court of Justice, para.40.
与军队的有效控制相关,还应考虑到是否有必要采取致命武力而不采用逮捕之类非致命性的手段。例如,出现在被占领土内的武装叛军成员,此时脱离了武装抵抗活动而做一些与其职务并不相关的事,在正常情况下,因其敌对势力的身份,可以对其使用武力,但由于政府军的有效控制,以及不必诉诸作战手段和方法的可行性,可以对其逮捕。这也表明对行为范式的选择,不是哪套法律体系优于另一个的问题,而是对最适合具体事实的法律规则的适用。
总之,在占领局势中,由于占领国的有效控制,执法范式基本上是使用武力的默认行为范式。但是,当武装抵抗运动或者叛乱活动的持续时间和暴力烈度的增加,采取执法范式不具有可行性或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时,或者武装冲突恢复或者继续进行时,敌对行为范式将占据上风。此时,特别法框架尤其考虑到了有效控制和暴力烈度作为事实要素对行为范式的选择的影响。
3.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武装冲突的性质不同,所适用的国际人道法规则也不相同。《日内瓦四公约》 共同第三条和1977 年的《第二附加议定书》 是规范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规则,但其内容都没有涉及“战斗员”。并且,对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或行使持续战斗职能的个人是否应视为平民以及哪种情况下不应被视为平民,存在较大争议。因此,在缺乏针对这种局势的明确的国际法规则的情况下,急切需要寻找与具体情势联系更为密切的特别规则。
尽管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以条约为基础的国际人道法规则十分有限,但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关于敌对行为的习惯法大多源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即使这些规则的适用范围和精确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因而,对于暴力烈度高的战斗局势应适用敌对行为范式,其适用的空间范围集中于实际发生敌对行为的地区。在“伊萨耶娃案”中,这一点得到印证。鉴于该案中涉及持续和协调的军事行动的背景,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局势要求国家采取例外措施以便重新控制共和国和镇压非法武装叛乱”,“部署配备作战武器的部队”。①法院事实上认为冲突背景下的积极抵抗执法机构的持续性暴力行动导致国家可以使用武力。参见 Isayeva v. Russia,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Judgment of 24 February 2005, para.180。法院实际在执行和计划攻击的方法和手段上采用了国际人道法的某些术语。在“伊萨耶娃、尤苏波娃和巴扎耶娃案”中,法院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②类似地,法院认为车臣当时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采取例外措施以便重新控制国家和镇压非法武装叛乱,但应当谨慎检验袭击的计划和执行。参见Isayeva, Yusupova and Bazayeva v. Russia,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Judgment of 24 February 2005,para.178。:它没有利用“麦卡恩案”等案③在“麦卡恩案”“居尔案”“奥乌尔案”“卡普兰案”中,尽管使用武力的对象被认为是恐怖分子或恐怖嫌疑人或者非法武装叛乱成员,法院也仍然要求采取执法范式的严格要求,这些手段包括避免适用致命武力、进行鸣枪示警、预先计划减少对致命武力的使用、对致命和非致命的武器进行充分区分等,以维护国际人权法所保护的生命权。参见McCann v.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of 5 September 1995,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para.194; Gül v. Turkey, Judgment of 14 December 2000,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para.84; Ogur v. Turkey, Judgment of 20 May 1999,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eports 1999-III, para.82; Hamiyet Kaplan v.Turkey, Judgment of 13 September 2005,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para.50。中的观点,反而排除了对武装叛乱分子生命权的考虑,注重平民的生命权,并在对平民的附带损害和行动的目的之间取得平衡,实质上适用了国际人道法的比例原则。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敌对行为范式适用于一国武装部队并未行使有效领土控制的情况。由于缺乏有效的领土控制,国家和武装团体在这些领土上的冲突较为激烈,此时利用执法范式对此种战斗局势进行规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敌对行为范式尤其涉及武装团体实施排他管辖的地区以及交战方进行激烈争夺的地区。欧洲人权法院的一些判例支持了对一国有效控制领土以外的情况适用敌对行为范式的做法,其主要采用国际人道法判断行为范式的正当与否。例如,在“哈姆扎耶夫诉俄罗斯案”中,法院从攻击的计划与执行的角度,认为对武装团体的空袭可能是夺取该镇的最适当的措施,并认为敌方攻击可能导致不合理的伤亡,而且法院认为俄罗斯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高度杀伤性武器与当局保护生命免受非法暴力的目的形成鲜明对比。④Khamzayev v. Russian, Judgment of 3 May 2011,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paras.177-180, para.185.法院的判断和结论主要考虑了国际人道法的约束作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专家们曾经在一个情景设计中,将有效控制程度、暴力烈度、潜在目标的地理位置都作为辨析使用武力的行为范式的关键。他们设定“一国政府与一个有组织的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发生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该团体的一名武装分子正在政府控制区的家中与家人一起睡觉”,①格洛丽亚·加焦利主编:《武装冲突中的武力使用:敌对行为范式与执法范式间的相互影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专家会议报告,2012 年1 月,第11 页。对其采取的军事行动应当采取何种行为范式。大多数专家认为由于其作为武装团体成员,属于合法目标,对其使用武力可以适用敌对行为范式。也有学者认为,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实施人权标准需要考虑非国际冲突的特点,并且在人权原则下,需要保证以正当程序的执法范式为基础,因而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有理由使用致命武力保护人们免受非法暴力。②David Kretzmer, Targeted Killing of Suspected Terrorists: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or Legitimate Means of Def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6, No.2, 2005, p. 202.
这些观点进一步从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根本区别的角度认为,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执法范式是默认的行为范式,除非在具体的情况下,有组织的武装暴力的范围和烈度如此大,以至于维持执法的法律范式显然不恰当。③David Kretzmer, Aviad Ben-Yehuda and Meirav Furth, Thou Shall Not Kill: The Use of Lethal Force in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Israel Law Review, Vol. 47, No. 2, 2014, p. 195.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认识到了执法范式与敌对行为范式就合法目标推定使用致命武力的差异。执法范式推定使用致命武力不合法,但在绝对必要和严格必要等例外情况下可以使用,而就合法目标而言,敌对范式推定可以对其使用致命武力。另外,这些观点也认识到可以对其使用武力的合法身份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不同。
然而,上述观点并未将军事占领局势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进行区分,也没有阐释发生在两个武装团体之间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这种类别。一方面,一国武装部队对领土的有效控制是军事占领的显著特点,执法范式是军事占领的默认范式,但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政府军与武装团体以及不同的武装团体之间的有效控制程度存在较大差别,④有学者将国际人权法的义务分配给武装团体以补充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人权保护制度下的国家义务,并将武装团体分为三大类,在特定领土上行使准政府权力的武装团体、对领土和人口实行实际控制的国家安全武装团体、不控制领土和人口的团体,并以有效控制程度和有效性原则确定了不同武装团体的人权义务。相关内容参见Tilman Rodenhäuser, Organizing Rebellion, Non-State Armed Group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Human Rights Law,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pp. 116-117。所承担的人权义务也相应地有所区分。尽管国际人道法规定了非国际武装冲突中冲突各方的相对平等的义务,但是根据国际人权法它们的义务并不平等。政府军受到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双重约束,而作为冲突一方的武装团体原则上不承担人权义务,其人权义务限于在其控制区域内的人所实施的特定行为。⑤要求非国际武装冲突中的非国家行为体,诸如武装反对派团体,承担人权义务,还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学界一般倾向于让非国家行为体承担人权保障义务,并且认为这一做法并不会自动赋予合法或者准政府地位。相关内容参见Andrew Clapham,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of Non-state Actors in Conflict Situa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88, No. 863, 2006, pp. 522-523。政府军对武装团体除了适用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以外,还可以适用国内刑法,它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可能与其承担的人权义务实现了相对弥合。
而且,政府军能够在自身领土上进行攻击的有效控制要素是人权法得以优先适用的主要事实要素,但并非影响特别法适用的唯一事实要素。暴力烈度与有效控制程度是相互关联的,在一国政府军实行较高有效控制的地区,适用敌对行为范式要求军事行动的烈度很高,而在一国政府军对领土的有效控制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适用敌对行为范式的要求变低。
另一方面,如果是发生在不同武装团体之间的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由于对武装团体是否承担人权义务以及通过何种法律依据承担人权义务的争议更大,执法范式和敌对行为范式的选择更加复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仍然需要结合具体情况予以个案分析,不同的局势、目标身份、有效控制的程度、暴力的烈度是影响行为范式的重要因素,逮捕的可能性、地理范围等事实则指示了有效控制程度的高低。要判断采取何种行为范式,应当综合考量各种事实要素。作为使用武力的合法对象是导向敌对行为范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其他事实要素,诸如领土有效控制程度、暴力烈度等,如果全部支持了执法范式,此时采取执法范式更加合理。
综合而言,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武装冲突中的关系可以总结为:在非占领性的国际武装冲突中,与武装冲突直接相关的行动基本上应当适用敌对行为范式,除此之外可由执法范式调整,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各自适用,互相分离;在占领中,执法范式是使用武力的默认行为范式,但考虑到有效控制程度、暴力烈度等因素的影响,占领国可以对叛乱、抵抗运动或在冲突恢复时,采取敌对行为范式;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如果一国不行使有效控制并且面临暴力烈度较高的战斗情形,敌对行为范式将占据上风。在后两种局势中,行为范式的选择仍需要结合目标身份、有效控制、暴力烈度等要素综合判断。同时注意到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政府军与有组织的武装团体之间的行为范式对暴力行为发生的地理范围更加重视,而两个或多个武装团体之间的武装冲突首先需要考虑武装团体承担的人权义务的法律依据和限制范围。
五 特别法分析框架及中国因应之策
在武装冲突中,通过对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关于使用武力的具体规则的考察,可以发现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的特别法的地位并不固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并不存在规范冲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地适用。①在“对战俘的预防性拘禁的合法性的司法审查”这一问题上,也有学者提出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存在规范冲突,并认为政策选择取代了特别法优先框架而成为解决规范冲突的方法。相关内容可参见Marko Milanovic, A Norm Conflict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Law, Journal of Conflict & Security Law, Vol. 14, No. 3, 2010,p. 477。但是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关系辨析仍然需要综合法律标准和事实要素。
“特别法优先原则”并非创造了规则的层级结构,更多的是一种关于法律、事实、价值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以“特别法优先原则”为基础,以武装冲突的不同局势为背景,以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适用性为前提,以综合考量各种事实要素为内容,以执法范式和敌对行为范式的选择或者正当与否为目的,为在具体情势下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具体规则之间可能存在的规范冲突提供了解决方法,也为需要进行价值权衡和政策选择的军事指挥者提供一个具有操作性、客观性的行为指南。
“人们彻底消除战争的美好愿望与战争将继续存在的残酷现实之间尚存在一大段距离。”②盛红生、肖凤城、杨泽伟:《21 世纪前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339 页。国际人道法在保护战争的受害者方面也存在许多法律真空地带,这不仅有赖于对国际人权法中具体规则的解释和适用,也需要战斗人员将自然法作为其行动指导,以更好地保护战争的受害者。中国作为大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以及相关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适用问题上,势必需要表明一个符合国际法的立场,并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才能令国际社会信服、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推动适应于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的国际法体系的构建。为此,从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关系辨析的角度,中国在提出相关主张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武装冲突各方均应遵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则。冲突一方所采取的敌对行为范式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事实,并不能成为另一方违反旨在保护失去战斗力的人员的国际人道法规则的借口。
其二,责任追究是加强对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以及国际刑法的遵守与实施的有利途径。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可以同时适用于同一事项,反之,一个行为也可以导致对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同时违反的法律后果。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等规则的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的追究,有利于促进对国际法的遵守和实施。
其三,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可能存在规范冲突,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价值冲突。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共同点在于对人道原则的追求。在两个法律体系中均规定了“免受任意逮捕或拘禁的自由、免遭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自由、禁止歧视”等权利。①Orna Ben-Naftali and Yuval Shany, Living in Denial: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srael Law Review, Vol. 37, No. 1, 2003, p. 52.这些都体现了人类尊严等核心权利和核心价值。因此,中国应在规则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主动性,权衡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引导构建适应于武装冲突发展趋势的国际人道法的规则体系,从而更加合理地应对武装冲突所带来的人道后果。
总之,中国应通过准确辨析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及其在武装冲突中的关系等问题,提出合法合理的主张,积极维护实在国际法,充分运用国际法原理,倡导发展国际法理论,在国际社会上争取主动权和提升国家话语权,引领国际法潮流与动向,进一步将中国的国际法治思维从 “第三世界”层次提升到 “领袖型国家”层次,②参见罗国强:《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治思维的革新与中国共产党之历史使命》,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 年第1 期,第33 页。在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完善中逐渐成长为具有公信力并获得广泛国际认同的“领袖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