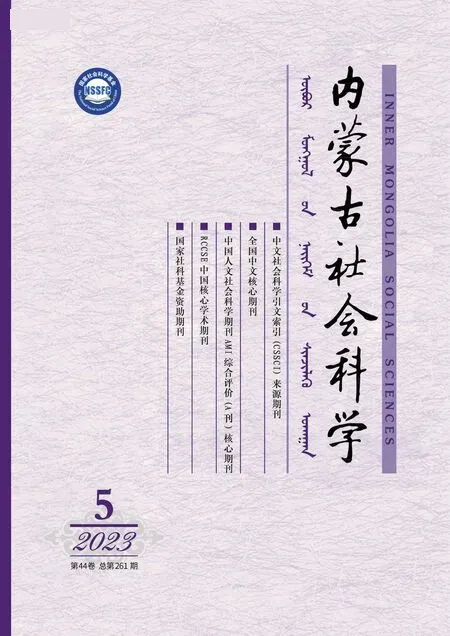自我与人生、社会、文明的现代守望
——中国现代游记的审美之思
2024-01-03陈邑华
陈邑华
(闽江学院 人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中国古代游记是文人寄情感怀的一种文体,多为山水游记,主要是描绘自然风景、名胜古迹、田园生活。相较于古代游记,现代游记内容大为拓展,不仅流连山水、寻幽访胜,更关注国内外的风土人情、社会现状以及人的现代思绪。不仅如此,现代游记的作者更为广泛,除作家之外,科学家、艺术家、翻译家、新闻记者等纷纷加入其中。“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为了工作和生活,他们旅食四方,更广泛地同通都大邑、名胜古迹、灵山秀水、风土人情接触,不同感兴,各为文章。这样,就造成游记、旅行记的繁荣。”[1](P.57)他们走出国门,放眼世界,以生动的笔触描摹异国风光,热心传播国外新思潮,展示异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刻画异国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与此同时,他们还描述自己独特的经验与感受,在本土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的对比思考中,表达着对国家命运与人类前途的思考和追求。相较而言,现代游记不仅视野开阔,对自然、人生和社会都有更为深入的思考,或以物境见长,或以情境著称,或以意境取胜。与古代游记相较,现代游记不仅拓展了书写的地理空间和审视领域,而且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对自然、人生和社会都有新的发现和表达。现代游记因人而异,各具风采。
一、现代自然的发现
自然历来是游记表现的主要对象。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决定了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人们与自然有着天然的亲近。人类早期,自然以无穷的威力左右着人类的一切,人们敬畏自然,对之顶礼膜拜。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孔子提出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即“比德说”的自然观成为中国自然审美的重要流派。魏晋以降,“畅神”的自然山水观念即玄学自然观盛行,亲近自然山水成为游者获得精神超越的主要途径。唐代游记家们常常于自然山水之中融入自身的情感、体验,人与自然浑然合一。宋至明中期,游记家们以精神超越的哲理高度与自然山水相契合,形成了在理学思想浸润下的理性自然观。晚明时期,游记家将自然山水人化,弘扬人的性灵,人与自然呈现出较为纯粹的审美关系。
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诸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其中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自然观对现代作家的影响尤为显著。许多游记家开始以现代观念审视自然,倡扬自然人性观,并且深刻认识到自然对人生、对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五四”以来,随着“人的发现”,个性解放成为时代的呼声。现代作家们尽管也流连于大自然,在自然中寻求性灵的解放,倡扬自然人性观,但已经不再是古人那种游目骋怀的寻胜,而是置入了现代人独有的文明忧思。如沈从文于湘西游记中赞赏健康、完善的人性,追求人性美、人情美;徐志摩笔下的自然界,凡物各尽其性;冰心描绘的自然诗意、圣洁,博爱、宽容,在自然中,人人自由、平等,解放性灵,实现自我价值。“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长处,一人有一人的价值。”(冰心《寄小读者》)显然,现代人文主义的思想视野让这些自然风光不再仅仅是“自然”,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下,基于现代人性意识的觉醒,是对现代人类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批判的意味彰显其中。
现代游记的自然依托的背景往往是人与社会、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思量。这与古代游记中人与山水自然的关系结构大相径庭。现代人的生活来去匆匆,喧嚣繁忙,难得清闲。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常常在喧杂的世间迷失自己,因而苦痛、烦闷。当人得以空闲、静心面对大自然时,往往会有惊喜的发现,“只有你单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单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单就呼吸单就走道单就张眼看耸耳听的幸福是怎样的”(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闲话》)。宁静清新的自然让人全身心放松,获得简单纯粹的快乐,这正是现代人的向往与渴求。徐志摩崇拜自然,热情讴歌自然,将自然作为疗治时代病症、恢复健全人性的理想途径。朱自清《春晖的一月》赞美自然,陶醉于乡村宁静闲适的生活。他批判现代都市“狭的笼的”的生活环境,希望用乡村的生活调剂都市烦嚣的生活方式。现代游记对自然充满了热切的向往与崇拜,对自然的抒写往往寄寓着对喧嚣都市、黑暗社会的批判。
有鉴于此,现代游记的自然书写往往是一种隐喻与象征,背后多有深意在焉。现代游记对于社会批判、文明忧思、人生境遇的多元探索,前所未有地拓展了现代游记的发现空间和情感内涵。现代游记对自然的书写不同于古人“从前的散文,写自然就专写自然”[2](P.450)。古代归隐田园的文人与自然朝夕相处,寄情山水,抒写怡然自得的美好心境,或藉此排忧遣怀,更多的是追求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现代作家承传、书写着古人对于自然的欣赏、陶醉之情,也“从一角新的角度而发见了自然”[2](P.450)。现代作家在自然的抒写中融入鲜明的个性特点、丰富精细的情感以及现代的人生体验,表达着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憎恶,对病态生活的批判与反省,对健康人性的倡导与追求,充分发掘了自然的审美价值及其对人生、社会的积极作用。
二、现代人生的新抒写
“五四”以来,现代交通业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旅游的繁荣,休闲成为人们生活放松、娱乐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的出游更多的是为了生计或国家命运。“旅游在人们观念中不再仅仅是游山玩水,出国镀金,而是关系到一个人的经验、知识和精神状态,直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3](P.253)现代游记抒写现代人生,现代人生的探索却关联着更为密切广泛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这种深广度是古代游记单一的人与自然、个人与人生的况味感慨所无法比拟的。
现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中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巨大差异,为了寻求新的学识以及振救国家和民众的道路,他们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或留学、或考察、或游历、或避难。郁达夫、郭沫若留学日本,孙福熙、李健吾赴法学习,冰心留学美国,徐志摩先后留学美国和英国,朱自清留学英伦,漫游了法、德、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家,刘思慕留学德国和奥地利,瞿秋白、郭沫若、茅盾赴苏联考察。郑振铎于大革命失败后,避祸出国,因而有了欧洲之行。王统照因小说被政府查禁,赴欧考察。邹韬奋流亡海外,漂泊于西欧、苏联,后来还赴美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萧乾作为驻欧特派记者在西欧度过了七个春秋。他们满怀着爱国热情,将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汇成一篇篇纪游之作,现代域外游记得以空前发展。
此外,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开发也催生了大量的旅行记、考察记,如冰心的《平绥沿线旅行记》、郑振铎的《西行书简》等。抗战时期,广大知识分子背井离乡,走上逃难之路,经受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一时期同样创作了许多流亡记、旅行记,如茅盾的《见闻杂记》、巴金的《旅途杂记》、丰子恺的“避难五记”等。这一时期的现代游记呈现出多元化、个人化的出游形态与心态,对人生有了新的抒写。从其情感表现来看,主要体现在悲情感伤、闲情逸趣两个方面,前者以情境见长,常常是触景生情,情景交融,后者多以思境见长,常常于“思与境浑”中抵达浑然忘我的境界。
“五四”以来,政局混乱、社会黑暗、经济凋敝。由于人生经历了种种不幸,奋斗中一再遭遇挫折,现代知识分子在游历中抒怀释愤,激愤地针砭现实,抒发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情绪,通过游记排解种种彷徨、感伤、悲苦的情感。郁达夫在《归航》《还乡记》《一个人在途上》《感伤的行旅》等游记中,尽情疏泄心中的悲愤感伤,将自己人生遭遇的困境、窘相,自爱自怜而又可怜可悲的心态,反抗现实却又无力改变现实的痛苦抑郁的心情淋漓尽致地抒写出来。倪贻德《东海之滨》、陈学昭《倦旅》等游记亦叙写了现代青年在黑暗社会流浪飘零、四处碰壁的人生遭遇及不满现实的种种感伤情绪。在《烟霞余影》中,石评梅漫步在龙潭之滨,看着周遭的风景,总怀想起自己悲苦的人生经历,她直抒胸臆,抒发悲痛之情以及压抑情感的苦楚。“真愿在这般月夜深山里尽兴痛哭;只恨我连这都不能,依然和在人间一样要压着泪倒流回去。蓬勃的悲痛,还让它埋葬心坎中去展转低吟!而这颗心恰和林梢月色,一样的迷离惨淡,悲情荡漾!”萧红在《长安寺》中也发出悲情的呼喊,直抒命运辗转之苦。庐隐在《月夜孤舟》《异国秋思》《秋光中的西湖》等游记中尽情倾泻感伤、愤懑之情。不同于古人的愁思悲苦,现代游记中的种种悲情伤感源于接受了现代个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对自我、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源于现代知识分子个人基本的生活权利与要求受到黑暗社会的压制和剥夺,个性不能自由发展、理想不能实现引发的苦闷与抗议。“他们对个人不幸遭遇的感伤,是与对人的合理生活的追求、对压迫人的黑暗社会的抗议、对个人不与丑恶现实妥协的独立人格的自信等思想感情联系在一起的。”[4](P.98)现代游记的悲情感伤具有了不同于古人的新意涵。
现代游记对闲情逸趣的抒写表面上以欣赏而非实用的审美态度对待生活,实质上却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人性化、合理的生命形态的曲折追求。“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正是不满于现实极端枯燥单调的生活,周作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喝茶》),觉得“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北京的茶食》)。周作人、俞平伯的游记以“艺术的态度”细细玩味生活中的日常物事,或欣赏乌篷船的构造、大明湖船夫手中的篙、玩味乘船游览的妙处、回味济南沿途的小吃,或观赏清旷的雪野、眠月观花、咏诗饮酒,优游自在,陶然忘我。不同于古代天人合一的逍遥境界,现代游记对审美境界的追求不为外物所役,独立于政治之外,独立于主流思想之外,以曲折表达的形式追求人格的独立自主,追求内心的自在自由,彰显了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生命形态的追求。
无论如何,现代游记对自然、对人生的抒写总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折射着现实社会的种种光影色调。现代游记对社会的抒写视域广阔,个人和社会与国家唇齿相依,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类游记多以物境、情境见长。“五四”以来,内忧外患的中国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现代知识分子深知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无论行走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关注社会状态、时事要闻,审视现实,所见所闻总能激起心中深挚的家国情怀。这一家国情怀继承和发扬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传统,从亡国灭种的生死存亡危机中激发出的爱国热情不同于古人的忠君报国传统,蕴含着现代人的现代民族和国家意识。这一家国情怀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有着不屈的抗争精神和坚定的信念。
三、现代意识:现代游记的精神内核
现代意识是现代游记与以往游记作品的根本差异之所在,是现代游记的精神内核。何谓现代意识?一言以蔽之,就是现代社会、现代文明语境下的现代人对现代思想情感的现代书写。
现代游记是现代人的现代书写,核心在于有现代的“我”。正如郁达夫所说,这个现代的“我”,“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2](P.451)。现代游记富于特色的精神追求,体现于自然、自我、社会三者内在关系的审美探求中。“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2](P.446)现代游记中的“自我”富于个性,显然已不同于古代游记中的“我”,亦不同于晚明游记小品中的“我”,其精神追求富于现代意识。古代游记中的“我”受“忠君”“卫道”意识的钳制,总出离不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古典审美观念的束缚。即便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提倡的“性灵说”倡导直接抒发真性情,也仅仅局限于人作为自然人的性情欲望的解放。正如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所指出的,明代这批悠闲人物逃避了世俗间的繁忙,注重表现自己心境上的灵感。当“达则兼济天下”的使命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无法实现时,晚明文人则退到“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地,转向内心,专注于个人情感,追求世俗的享乐。因此,晚明游记小品在冲破了“载道”及理学的束缚后,强调性灵写作,表现凡常生活,或逃逸山林,或随世浮沉,看似扩大了题材范围,实则将文学作为消闲的一种方式,在自我解脱的同时,也消泯了文学所承载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担当。
现代游记抒写的自我汲取的是文艺复兴以来近现代人学思想的精神资源,具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精神的现代个体意识,富于鲜明的个性特点,往往由自我出发,与自然、社会息息相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就首先就在于“人”的发现。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2](PP.445~446)这一论述精辟地道出了“人”的发现,“人”从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启蒙与影响,具有先进的“民主”与“科学”意识。“人”的解放对创作的个性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郁达夫指出:“‘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个性强烈的我们现代青年,哪一个没有这种自我扩张的信念?”[5]“人”的发现成为一面旗帜,“人”的发现是在寻求民族与国家的生存之路的背景下发生的,因而,这一觉醒的人不同于晚明士人始终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走向了社会、走向了时代,蕴含着现代启蒙色彩。“一种是‘出于自我而终归于自我’,始终以自我为中心,以表现自己、娱乐自己而自足;另一种是‘出发于自我,却终归于社会,’由‘小我的泄露而进于大我的调和’。”[6](P.109)晚明士人属于前者,专注于个人情趣的玩味,以自我为中心,现代游记中的“自我”属于后者,富于现代意识,个性鲜明,注重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出发于自我,终归于社会。
漫步于月下荷塘、陶醉于秦淮河的朱自清,终究难以排遣心中的哀愁和烦闷;原本想尽情消遣,以平和的心情漫步于“松堂”,其间总夹杂着丝丝怅怅,最后竟是压抑,一片漫天弥地的黑暗。在朱自清的游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直诚恳、温和朴实、充满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无论是早期“感伤的行旅”,还是中年阶段“奉宪”旅游;无论是赏“故都的秋”,还是观“江南的冬景”,郁达夫的游记都形神兼具,情感丰富,既有古代名士隐逸的情愫,又有现代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深情厚谊,率性风趣。现代游记善于捕捉各处风物景观的特点,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在描情绘景时,常常“旁涉一笔”,讽古喻今,针砭时弊。周作人于《乌篷船》《济南道中》等游记中,流露的是冲淡平和、随遇而安的性情,出世又不忘讽世,闲适情调中书写“艺术化的生活”,其间寄寓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寄小读者》呈现了一个真挚善良、满怀爱心的现代知识女性形象。冰心礼赞大自然、母爱、友情、童心,构建了一个“爱的世界”。这是一种富于现代意识的“爱”,承认人与人平等、承认个人主体价值,且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寄小读者》摹写异国他乡的风光民情,字里行间流淌着真挚动人的爱国思乡之情。《巴黎的鳞爪》中的徐志摩陶醉于自然,在自然中寻求生命的真谛,张扬性灵的解放,寻求爱、自由、美的实现,展现了一个真率浪漫、才华横溢、热情洒脱的现代青年知识分子形象。
现代游记的自我是现代人,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是现代人的精神底色,情感的抒写自然呈现出率真行诚的特点,这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以理节情、尚理致用的创作态度。徐志摩、冰心、瞿秋白、郁达夫等人的游记对情感的抒写皆呈现出率性抒怀、真挚坦白、不拘格套的新风貌。郁达夫《苏州烟雨记》《感伤的行旅》《还乡记》《一个人在旅途》等游记,以自己的情感为行文线索,随着情感的变化,交错叙写不同时空的经历,恣意任情地宣泄心头的苦闷、悲愤,纾解社会重压下痛苦的灵魂,他是“用感情统一风景与心理”[7](P.111);情感奔放,富于浓烈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笔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情绪是一种富于感染性的东西,用美妙的文字写下来的美妙的情绪,尤其富于感染性。”[8](P.221)在游记中,郁达夫还运用了场景描写、对话独白、心理刻画等小说笔法,丰富了游记的内容与艺术。这种率性抒怀、自由不拘的表现方式,“体现现代人思想感情的解放,自我个性的张扬,审美观念的变革,使散文突破了传统规范,扩大了表现功能”[4](P.121)。
纵观现代游记中的自我,现代意识鲜明,个性显豁。无论是倾心于描摹逼真如画的物境、沉醉于诗情画意的情境,还是处于物我同化的意境,抒情主人公的“自我”都是接受新思潮洗礼的自我,是觉醒的独立的自我。置身于内忧外患、西方各种现代思潮争相涌入的社会,游记的创作者似乎总处于“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境地,情感不再单一,即使置身于宁静的大自然,也难掩心头丝丝缕缕的愁绪。可以说,现代文明的人类忧患意识、现代社会的个体责任担当、现代人精神情感的深度心理开掘都或隐或显地成为现代游记的情感基调。尽管现代作家以敏感的心灵感受着大自然,但他们是以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人的身份关怀人生,关注社会,思考人类,探索文明,这种在现代游记中充分表达出来的、富于现代意识的精神追求,这种抒写对自然、对人生、对社会的现代人的新体验、新发现、新思考,显然是古代游记单向度、平面化、个体化的观看所无法比拟的。有心理深度的自我、与文明相望的自然、与个人对峙的社会、与野蛮相对的文明,在现代游记中如影随形,交织交融。因此,现代游记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审美之思和独有的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