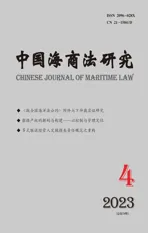数字法治的法理解析:形式、实质与程序
2024-01-02李忠操
李忠操
(大连大学人文学部法学院,辽宁大连 116622)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曾有国外学者预言,在未来的数十年中,互联网将演变成全世界用户均可参与的开放系统。借助这种开放系统,世界最终将实现“万物互联”。(1)Ana Paula Oliveira Avila &Andre Luis Woloszyn, Legal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in the Digital Era: Doctrine, Legislation and Jurisprudence, Revista de Investigacoes Constitucionais, Vol.4: 167, p.168(2017).事实上,伴随数字技术的持续进步,这一预言如今已经成为了现实,甚至“万物互联”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日常状态。数字技术中的互联网、数据信息、人工智能、算法和区块链的极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已然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时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27日,第1版。数字技术引发的革命,不仅席卷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引起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理论变革,而法治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或者说,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社会治理本身也在呼唤与之相配的“数字法治”。
然而,数字时代为法学“创造了许多”,也“同样毁灭了许多”。(3)[美]安德鲁V. 爱德华:《数字法则——机器人、大数据和算法如何重塑未来》,鲜于静、宋长来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数字时代为法治社会带来了许多深层次的悖论,如数智赋权悖论、数智参与悖论、数智规制悖论和数智人文悖论等。(4)参见马长山:《数智治理的法治悖论》,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4期,第66-71页。面对数字时代的“超现代性”,无论是法教义学抑或社科法学,均受到了新的挑战。面对迎面而来的数字时代,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现有的法治理论是否能够继续指导、规范数字时代的法治实践,并获得自身的存在意义。对此,笔者将从法治的三个维度,即形式维度、实质维度与程序维度,针对数字时代的法治现状——“数字法治”,从司法与社会两个层面加以审视,以期寻找数字法治的真正价值,并提炼出能适应数字中国建设需求的全新论断。
一、形式维度下数字法治认知的局限
数字法治的形式维度,即数字法治的形式合理性。(5)参见江必新:《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关系》,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4期,第4页。从当前数字法治的发展现状来看,数字法治似乎已经极为契合形式法治的要求。
首先,从司法层面来看,数字法治能够辅助司法决策。形式法治的首要要求是制定出形式化或程序化的一般规则来处理具体问题。但此套规则只是单纯地预设了全套法律于形式抑或程序方面应达到的标准,却不涉及具体法律处置问题时的实体价值取向。例如,纯粹法学代表人物凯尔森就曾试图从实证法中分离出政治、道德等因素,主张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之间泾渭分明;(6)参见伊卫风:《形式法治的迷思及启示》,载邵博文主编:《北大法律评论(2019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页。法律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也认为法治与道德之间并无必然之联系,其认为合法性的问题并非法哲学的议题,至少是在严格意义上的法的框架内所无法论证的议题,而应是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所关注的课题。(7)Jeremy Waldron, Hart and the Principles of Legality ,in Mathew H.Krameretal eds., The Legacy of H. L. A. Hart: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70.形式法治同样要求制定出的规则,其所内含的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标准,能够预防或阻止某些实体上不正义的法律或法律行为的出现。例如,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当权者制定不合理的法律。
数字法治的核心,甚至于数字时代的核心,是遵循“算法”分析社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例如,参与公共决策、法治实践以及影响商业决策。(8)参见郑玉双:《计算正义:算法与法律之关系的法理建构》,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1期,第98页。算法指用于达成特定目标的一系列清晰、准确、有限的指令,(9)参见[美]Thomas H.Cormen、 Charles E.Leiserson等:《算法导论》(原书第3版),殷建平、徐云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或者说,是“是一组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些过程在遵循时会产生一定的输出”。(10)Woodrow Barfiel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Law of Algorith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4.算法和数字法治的另一个基础要素——“数据”之间可谓相辅相成:数据是算法运行的前提,而“算法与数据结构密切相关——用于组织数据的方案,使它们能够通过算法进行有效处理”。(11)Robert Sedgewick &Kevin Wayne, Algorithms(4th Edition), Addison-Wesley, 2011, p.3.何邦武教授将“数字法治”和“算法”之间的关系形容为“无算法,数字无价值;无数字,算法无意义”。(12)何邦武:《数字法学视野下的网络空间治理》,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4期,第76页。而国外有学者认为,数字法治的绝大部分研究的目标是开发出能够提出法律论据并使用它们来预测法律纠纷结果的法律推理计算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s of Legal Reasoning,简称CMLR),以此来实现自动化的法律推理。借助先进的深度学习模型,计算机能够实现对问题输入文本的深入理解,并生成具有高度说服力的支持或反对特定结果的论点。这种预测的准确性已经在一部分社会公众内获得认可,因为它们是基于对大量数据和复杂算法的深入分析。支持者们认为,计算机生成的论点不仅富有逻辑性,而且能够针对特定问题提供具有清晰定义的推理过程,使法律专业人士能够准确地评估和认可这些论点。这种技术不仅可以提高法律专业人士的工作效率,而且可以为案件的结果提供更加准确和可靠的预测。(13)Kevin D. Ashle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Analytics: New Tools for Law Practice in the Digital 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4.
其次,数字法治有助于在社会治理中形成中立的“数字逻辑”。形式数字法治有其独立的判断标准。形式法治观学者认为,法治自有其内在道德(inner morality of law),(14)例如,富勒提出了一个规则体系所应追求的八种优越品质,即法律的一般性、法律的公开性、法律非溯及既往、法律的明晰性、法律不相互矛盾、法律的可行性、法律的稳定性、官员行为与已宣布的规则相符合。Lon L.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33-34;同样地,拉兹提出了法治的八项原则:法律必须是可预期的、公开的和明确的,法律必须是相对稳定的,特别法应当在公开的、稳定的、明确的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司法独立应予以保障,自然正义的原则必须遵守,法院应对各项原则的实施享有审查权,法院之门应当容易进入,刑事执法机构不能利用自由裁量权歪曲法律。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14-219.以区别于规则所服务的实体目标,即外在道德(external morality of law)。(15)富勒认为,所谓法的外在道德,是指法律所欲实现的实体目的或理想。Lon L. 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4;黄文艺教授将法律的外在道德解释为实体自然法,是指法律的实体目的或理想,如正义、自由、平等。参见黄文艺:《为形式法治理论辩护——兼评〈法治:理念与制度〉》,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第176页。形式法治论仅仅将法的内在道德纳为法治的构成要素,要求法治将法律和制度公允无偏和前后一致地适用于全体规制对象,(16)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Original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58.以此来寻求稳定。“法治简单地指‘公共秩序的存在’,它的意思是通过法律指挥的各种工具和渠道而运行的有组织的政府。”(17)W. Fiednamn,Law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Stevens,1951,p.281. 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的外在道德是被排除在外的。也就是说,形式法治要求重视法律的普遍性、稳定性和逻辑一致性等形式要件,这种形式化的法治要件论,“是价值无涉的”。(18)陈林林:《法治的三度:形式、实质与程序》,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9-12页。
对于形式法治而言,一套可以自主运行、不受外界因素(如政治、道德)影响的系统,似乎是其最为需要的。而数字法治恰恰就能够提供这一系统,原因在于:一来,数字法治即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法治工作,推行法治进程。而数字技术的应用单位为数据。“数据是‘对可以记录、分析和重组的事物的描述’”;(19)Viktor Mayer-Schonberger &Kenneth Cukier,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Eamon Dola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p.78.而数字技术是将数字整理后数据化,(20)“数据化”和“数字化”并不相同。“数据化”是指一种把现象转变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的过程。“数字化”指的是把模拟数据转换成用0和1表示的二进制码,这样电脑就可以处理这些数据了。可以说,“数字化”带来了“数据化”,但是“数字化”无法取代“数据化”。即将现象转化为数据的过程。(21)Jamie Susskind, Future Politics: Living Together in a World Transformed by Te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62.二来,在转化过程中,会先后产生“测量的数据”“记录的数据”和“计算的数据”三种类型的数据。(22)涂子沛老师在《数据之巅》一书中把数据的来源总结为三方面:测量、记录和计算。“测量的数据”,就是所谓“有根据的数字”,是指数据是对客观世界测量结果的记录。文本、音频、视频本身就是信息,其不是来源于对世界的测量,而是对世界的一种记录,因此称之为“记录的数据”。有了“测量的数据”和“记录的数据”,便可以进一步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处理,由此产生“计算的数据”。参见徐子沛:《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与未来》,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97、307、315页。理论上,前两种数据均是对客观世界的记录,因为这些事件的“个人在真实世界的活动和社会状态被前所未有地记录下来,这种记录的粒度很高,频度也在不断增加,为社会领域的计算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数据”。(23)参见徐子沛:《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与未来》,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316页。而前两种数据在经过算法的计算后,产生的“计算的数据”,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减少主观性最好的方法的结果”。(24)参见徐子沛:《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与未来》,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早在2012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太阳哨兵报》的记者凯斯汀(Kestin)就通过对上百万条数据精细地对比、分析和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当地的3 900辆警车在短短13个月内发生了高达5 100宗的超速事件。这些超速事件,绝大部分是在工作时间之外发生的,表明这些事件中的警车并非因工作需要而紧急超速行驶。这一发现引发了凯斯汀的深入思考。她开始质疑,这些频繁的超速事件是否暗示着当地警员可能存在滥用职权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揭示现象的本质,凯斯汀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并开始研究相关的法律和规定,以确定这种超速行为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之便滥用职权的行为。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她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而是普遍存在于警察群体中的一种习惯性做法。因此,她认为:当地警员存在利用职务之便滥用职权的行为,使得开快车成了警察群体的普遍习惯。此结论一出,舆论为之哗然,因为警察一直以来都被社会公众奉为“法律的执行者”,而凯斯汀冰冷的数据无疑宣告了当地警察知法犯法。其后,她又利用同样的数据分析方式继续对当地警员是否采取了改进措施进行了跟踪。(25)参见徐子沛:《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与未来》,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318-319页。由此可知,如果是合理地运用数据分析的方式,的确有可能摒弃经验、道德等其他因素的干扰,得出较为公正的结论,甚至可能是与社会公众认知大相径庭的结论。
数字法治与形式法治之间似乎是相辅相成的。那么试想,如果前文提及的CMLR在不久的将来真的被设计并应用于法治实践中,是否就意味着数字法治的最终形态得以实现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虽然数字法治符合形式法治的规则体系的完备性与确定性等要求,但单单以形式维度考察数字法治,极有可能使法治媾和专制政权,违背“法治和专制是根本对立的”这一基本底线。(26)参见卓泽渊:《中国现代法治的反思》,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3期,第122页。

诚然,数字技术在辅助处理案件上,有着人类法官和律师所无法比拟的效率优势。问题在于,现阶段的数字技术只能在司法诉讼中承担部分辅助程序工作,如法律检索(38)Ross Intelligence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律师,部分受到IBM的认知计算机Watson支撑,它可以理解自然语言,并提供特定的、分析性的回答,这接近于和人类律师一起工作的体验,甚至已经有超过10家主流律所“雇佣了”Ross Intelligence。参见曹建锋:《人工智能法律服务的前景与挑战》,载搜狐网2017年4月1日,https://www.sohu.com/a/131560668_170807。、文件审阅(39)预测性编程和利用机器学习算法的软件可以为相关法律文件检索电子信息。硅谷的一家电子取证公司Blackstone Discovery可以不超过10万美元的代价在几天之内分析150万份法律文件。参见周大伟:《人工智能可以取代律师吗?》,载新浪网2021年1月22日,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1-22/doc-ikftssan9495903.shtml。、咨询服务(40)法律咨询以Do Not Pay最为典型,它在线帮助用户挑战交通罚单。用户只需要访问其网站,同其发消息进行交流,其就可以利用用户提供的信息形成一份文件,用于挑战罚单。Do Not Pay在纽约、伦敦和西雅图已经成功挑战了超过20万个罚单,成功率是60%。Do Not Pay还在不断扩大其法律服务类型,已经涵盖了航班延误补偿金请求、政府住房申请等。在国内,号称中国第一个机器人律师的“小梨”,目前可以提供签证、离婚咨询等服务。参见曹建锋:《人工智能法律服务的前景与挑战》,载搜狐网2017年4月1日,https://www.sohu.com/a/131560668_170807。,甚至案件预测(41)伦敦律所Hodge Jones &Allen早已利用一个“案件结果的预测模型”来评估人身伤害案件的胜诉可能性。这直接导致了2013年的Jackson民事诉讼改革,使得人身伤害案件的诉讼成本大大降低。参见曹建锋:《人工智能法律服务的前景与挑战》,载搜狐网2017年4月1日,https://www.sohu.com/a/131560668_170807。等。但是,法官或律师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对诉讼文件进行整理,而是要在不同的案件中发现其中的细微差别。“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4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页。反观数字技术,其核心是基于既有的司法大数据来展开测算,进而推送“显影建议”,但这时法律和案例已有的系统偏误很可能会被大数据处理固定化。虽然从形式上来看,数字法治能够实现案件审理的“同案同判”,但是这种“机械式”的“同案同判”很可能牺牲当事人的权利,即牺牲实质的正义。对此,为了检测数字技术是否能够像人类法官或律师般分析问题,2017年,法国司法系统选取了雷恩与杜埃两地上诉法院作为司法人工智能判决结果预测软件Predictice系统的测试单位。通过测试,法国司法系统认为,Predictice系统无法区分具体案件中的些微差别,亦难以考量案外因素对案件带来的影响。在此之后,法国立法机关颁布禁止使用“法官画像”的禁令,禁止基于法官身份的数据分析、对比、评价与预测,借此将判决书大数据应用限制在相对有限的领域。(43)参见王禄生:《司法大数据应用的法理冲突与价值平衡——从法国司法大数据禁令展开》,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2期,第133页。
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在司法实践中片面地追求数字化,能否体现司法的实质正义。从前文来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司法实践中片面地追求数字化,可能会导致对于司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法律解释和法律议论的空洞化乃至消亡。众所周知,司法公正的关键是正当程序以及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进行的理由论证。但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算法独裁,势必使通过法庭公开辩论进行法律推理的环节变得不太重要、不太可能,甚至逐步形同虚设。尤其是现阶段的司法人工智能系统并没有以关于法律推理的算法研究以及相关软件程序设计为前提,对于法律议论与智能化审理之间关系的考虑不太充分,那就更容易出现压抑乃至扼杀法庭辩论的严重后果。如果听之任之,数字技术下的司法人工智能很容易蜕变为电子计算机系统加简易审判这样一种庸俗形态。因此,在推广司法人工智能之际,必须认真考虑法律的推理、解释、议论等语言行为适当反映到算法之中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现阶段的数字法治框架内,仍旧难以解决。
在司法实践中片面地追求数字化,将无法体现司法审判者的价值判断。实际上,法官的价值判断不仅在法律推理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且是这一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4)参见姜永伟:《论价值判断作为裁判依据的二阶性》,载《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60页。如果用数字技术或者司法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判断,那就必须把包括案情、经验、感觉、知觉、常识在内的所有信息都转化为计算机语言,均要进行编程计算。这意味着,必须为司法人工智能系统构建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库和知识图谱。对人类来说,常识性判断或许是非常直观简单的问题,但要将其转换成计算机系统的计算程序就极为困难。甚至可以说,数据库构建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程。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常识库,司法人工智能系统对很多问题就无法进行适当的判断。(45)参见季卫东:《司法人工智能开发的原则与政策》,载搜狐网2020年12月12日,https://www.sohu.com/a/690630044_121687424。
退一步讲,即使从技术层面能够建立这样的数据库,但仍不能从理论上证明“AI律师”或“AI法官”能够真正实现法治的实质正义。仍以前述的“同案同判”为例,法学理论中所追求的“同案同判”,绝不是两个案件的数个甚至全部的单列特征相同,而是在可被涵摄于相同法律规则之下的案件中实现法律要点上的相同评价。对此雷磊教授解释为,法律不仅是一个词汇系统,更是一个意义系统,(46)参见雷磊:《司法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司法公正?》,载《政法论丛》2022年第4期,第74-76页。是基于人类自由意志上的认知和理解能力才得以建立,而这种认知和理解能力正是“AI律师”及“AI法官”所欠缺的。尽管“AI律师”及“AI法官”可能实现数据的最优关联匹配,但却无法产生人类自由意志,进而走出整体性判断和“理解”所处理的语句意思。如果对实质正义加以漠视,单单追求条文的一致性,无异于掩耳盗铃,最终会损害社会的公正和公平。董必武先生对此早有过类似的警示:“没有法,做事情很不便。有了法,如果不去了解法律条文的精神实质,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又不去深入研究案件的具体情况,只是机械地搬用条文,也是不能把事情办好的。”(47)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521页。笔者认为,数字技术创造的所谓的“AI律师”和“AI法官”与真正的律师和法官相去甚远。
作为数字法治构建的基础支撑,算法和数据已经融入亿万数字公民日常交流的各个环节。然而,任何一种法律秩序倘若无视公民基本权利或普世的价值观,都将沦落为少数者的作恶工具,数字法治自然也不例外。有鉴于此,对于数字法治的理解与认知,绝不能限于形式维度,数字技术仍然需要为数字法治赋予实质性的内容。
二、实质维度下数字法治认知的失衡
数字法治的实质维度,即是从实质法治角度看待数字法治。与形式法治不同的是,实质法治更为关注的是法律的社会效果,(48)参见陈金钊:《实质法治思维路径的风险及其矫正》,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第66-89页。要求法律本身应基于对人的个性的至高价值的尊重,(49)Geoffrey de Q. Walker, The Rule of Law: 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6-7. 转引自高鸿钧等:《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这种尊重“不仅保障和促进个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且应确保个人的合法期望与尊严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50)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he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and Definitions, Geneve, 1966, p.68-70. 转引自高鸿钧等:《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包括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基本权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等。(51)参见陈林林:《法治的三度:形式、实质与程序》,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10页。数字法治于实质维度层面同样面临质疑。质疑来自于法治的社会层面——算法带来的法治绝对可信吗?或者说,在全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数字技术所依赖的算法是否能实现真正的实质法治呢?
随着数字技术中的算法在社会中的普及,立法者、司法者和法学家均开始关注算法引发的相关问题,例如算法是否会对部分公民造成歧视;(52)参见洪丹娜:《算法歧视的宪法价值调适:基于人的尊严》,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8期,第29页。或者因信赖算法而造成的各类事故的责任划分,涉及自动驾驶汽车造成的交通事故(53)Sven A. Beiker,Legal Aspects of Autonomous Driving, Santa Clara Law Review, Vol.52: 1145, p.1152(2012).及因使用医疗用外科机器人造成的医疗事故等;(54)例如,美国的“Taylor v. Intuitive Surgical案”中,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实施手术的最大推荐BMI(Body Mass Index,身体质量指数)是30,而记录显示患者的BMI已达到39,并不适合使用达芬奇机器人进行手术,但医生仍然选择使用,最终导致损害发生,法庭认定医生存在明显过失。参见李润生:《论医疗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从近期方案到远期设想》,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53页。或是基于算法产生的文学创作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等问题。(55)参见徐小奔:《论算法创作物的可版权性与著作权归属》,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3期,第52-53页。这些问题,目前虽然散见于不同的法律部门的实践当中,但是不难发现,看似公平、公正、独立的算法,其实并非如其标榜般的纯粹中立,而是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是在算法的设计之初就已经埋下的。
因此,从表面上来看,这一问题是在讨论算法的可行性,但其隐藏的实质问题却是算法的设计者可信吗?或者说,人工智能及其设计者们是如何将抽象的哲学和法律原则或价值观转化为工程师可以在设计中理解和规划的设计要求?尽管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嵌入并影响社会,例如通用设计(56)Ljilja Ruzic &Jon A. Sanfod, Universal Design Mobile Interface Guidelines (UDMIG) for an Aging Population, in Hannah R. Marston, Shannon Freeman &Charles Musselwhite eds., Mobile E-Health, Springer, 2017, p.17-37.、包容性设计、可持续设计(57)Till Winkler &Sarah Spiekermann, Human Values as the Basis for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ystem Design, IEE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Magazine,Vol.38: 34, p.35(2019).和价值敏感设计(58)Steven Umbrello, Imaginative Value Sensitive Design: Using Moral Imagination Theory to Inform Responsible Technology Desig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Vol.26: 575, p.577(2020).等。但是,纵然算法的设计者总是标榜其设计是遵循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59)Geerten van de Kaa &Jafar Rezaei, et al., How to Weigh Values in Value Sensitive Design: A Best Worst Method Approach for the Case of Smart Meter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Vol.26: 475, p.479(2020).然而,自从数字技术于人机交互领域广泛应用后,其遵循的前提就是“技术的价值性”而不是“价值的中立性”。与之相反,这些算法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极其敏感,无论他们是用户和设计师等直接利益相关者,还是环境等间接利益相关者,(60)Batya Friedman, David G. Hendry &Alan Borning, A Survey of Value Sensitive Design Methods, 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Vol.11:63, p.81-82(2017).这就导致算法在运用的过程中具有了价值倾向性,甚至会产生社会价值理念和算法设计者价值理念之间的冲突。
在设计者识别潜在的价值冲突时,价值冲突通常并非被解读为“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是被解读为不同理念之间的张力和束缚。(61)Jeroen van den Hoven, Pieter E. Vermaas &Ibo van de Poel, Handbook of Ethics, Values, and Technological Design: Sources, Theory, Values and Application Domains,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5, p.3.典型的价值冲突包括问责制与隐私、信任与安全、环境可持续性与经济发展、隐私与安全、等级控制与民主化等。(62)Jeroen Van den Hoven, Gert-Jan Lokhorst &Ibo Van de Poel, Engineering and the Problem of Moral Overloa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Vol.18:143, p.143(2012).以个人隐私保护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7条明确规定,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负有明确的告知义务。(6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7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下列事项:(一)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和联系方式;(二)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三)个人行使本法规定权利的方式和程序;(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告知的其他事项。前款规定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将变更部分告知个人。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制定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方式告知第一款规定事项的,处理规则应当公开,并且便于查阅和保存。”但是,平台时常利用本身掌握的数字技术,对平台用户进行追踪,并激励、诱导用户持续性地、经常性地使用平台。然而,在享受算法决策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用户很可能盲目地放任自身的惰性,过度依赖算法并将所有的决策权力交给算法。(64)参见冯月季:《符号学视角下智能算法对人类主体性的消解及其反思》,载《东南学术》2022年第5期,第56页。当用户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失去自我时,其行为也势必受到相关算法决策结果的深远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技术下的算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能够完全取代人们的决策能力,导致用户在进行决策时,高度依赖于算法程序的设计与开发,使得自我创造、发展、提升的能力逐渐停滞不前。这种不去深入思考和判断便得出结论的信息传递方式,不仅加剧了人们在事物判断上的偏见与喜好,还影响了用户自身主动接受异质化信息的能力。(65)参见侯东德、张可法:《算法自动化决策的属性、场域与风险规制》,载《学术研究》2022年第8期,第42页。而在这一过程中,平台用户可能并不知道自身的网络行为正在被追踪与分析。即便部分用户了解平台的做法,却通常不具有改变或阻止平台行为的技术能力,除非平台用户有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回避全部的数据收集。(66)Tarleton Gillespie, The Relevance of Algorithms, in Tarleton Gillespie, Pablo J. Boczkowski &Kirsten A. Foot eds., Media Technologies, MIT Press, 2014, p.185.例如,外卖平台算法系统既建构了复杂的劳动秩序,同时形成压迫式索取。这种算法导致外卖平台在压缩配送时间上永不满足,总在不断试探外卖员的生理与心理极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数字控制”。(67)参见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133页。
与此同时,算法价值观的控制权实际上是垄断在设计者手中的。表面上,数字算法的设计者仅仅参与算法制定中的设计流程。然而,“利益相关者的启发、价值观和分析可以影响技术和政策”,这就使得数字技术内部存在了一定程度的“技术官僚”。(68)Steven John Thompson, Machine Law, Ethics, and Morality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GI Global, 2020, p.117.算法的价值观设计一般基于三个不同但迭代的调查组成,分别为概念调查、实证调查以及技术调查。概念调查指设计师查阅可能与所考虑的技术相关的哲学文献,以确定可能涉及设计程序的一些初步价值。正是在这一点上,设计人员可以进行初步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以确定可能受到技术部署影响的直接和间接利益相关者。(69)Alan Borning &Michael Muller, Next Steps for Value Sensitive Design, in 30th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CHI, 2012, p.4.实证调查采取概念性工作并引出各种利益相关者群体,通过采用调查、半结构化访谈、设想卡、价值草图和情景等科学手段从而将利益相关者们纳入设计计划。(70)Batya Friedman, David G. Hendry &Alan Borning, A Survey of Value Sensitive Design Methods, 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Vol.11:63, p.73-76(2017).此时的目标是深化对支持或制约技术发展的潜在的相关利益方的价值观的理解,反之亦然。技术调查着眼于设计对象本身的架构是否足以支持或约束价值。“为了能够灵活地应对意料之外的后果和价值冲突,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底层技术架构中增加设计灵活性以支持部署后的修改。”(71)Steven John Thompson, Machine Law, Ethics, and Morality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GI Global, 2021, p.116.由此看来,似乎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应该是设计范式的中心,但实际上设计师和设计团队才对设计本身和最终产品拥有终极的控制权。这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即公民可以参与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并不能决定最终结果。数字技术下的算法设计也采取了一种“代议制”,不过是由设计师代替公众选择价值观,这就形成了设计者对算法,甚至对数字技术、数字法治的价值观设计的专断权。
或许,数据收集者以及部分乐观者认为,算法并不等同于数据收集,即使算法可能因设计者存在偏见而形成专断,但数据的收集技术可以基于中立的流程与操作。(72)例如,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坚定地捍卫技术中立论,他主张技术是完全中立的,其仅仅是工具而已,被人类所使用,被用来实现或善或恶的目的,然而善恶美丑和利害是非并不是由技术决定的。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认为技术拥有自主性,是自我主宰的力量,不受人类设定的任何技术目的所左右。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对技术决定论的技术中立观点进行了归纳梳理: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一经发明就会以不可阻挡的势头重塑社会;技术专家治国论主张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技术专家才能管理和控制技术;技术结果意外论将技术故障和技术灾难视为偶发的和意外的。这三种技术观都认为技术是中立的,将技术进步视为理所当然和不可阻挡的。参见刘兴华:《数字全球化时代的技术中立:幻象与现实》,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2期,第35页。然而,这种想法过于理想化。基于前述,算法和数据二者之间相伴而存。在早期的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中,既无算法亦无数据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二者是相伴而生的,“犹如一对孪生兄弟”。(73)殷继国:《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垄断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载《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5期,第187页。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的观点如出一辙,“失去数据的算法将变得毫无意义,失去算法处理的数据将毫无价值”,(74)Jack M. Balkin, The Three Laws of Robo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Ohio State Law Journal, Vol.78: 1217, p.1220(2017).它们共同构成数字技术的“左膀右臂”。因此,纵然数据收集起初的目的是价值无涉的,但基于数据的算法行为绝非价值中立的,而“设计者在运用算法选择、组织数据时,早已隐藏了歧视与不公”。(75)Jack M. Balkin, The Three Laws of Robo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Ohio State Law Journal, Vol.78: 1217, p.1217-1241(2017).甚至于,看似中立的数据收集行为,在收集行为开始前就已经明确指向了行为者的个人动机。“收集个人数据的目的应不晚于收集数据时指定,随后的使用仅限于实现这些目的或与这些目的不相矛盾的其他目的,并在每次目的变更时进行说明。”(76)Robert Walters,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national Data Flows Regulation, Wolters Kluwer, 2022, p.39.
今天,数据已经成为基础性的生产要素与社会资源,“数据既是算法社会运行的燃料;亦是其运营的产品”,(77)Jack M. Balkin, The Three Laws of Robo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Ohio State Law Journal, Vol,78: 1217, p.1219(2017).是“新时代的石油”。(78)齐爱民:《数据法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随着数字技术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数字应用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法治在实质维度上,不仅能够帮助法学研究者理解数据作为资源的重要性和价值,也会帮助法官判断数据作为资产的合法性。(79)例如,在“腾讯公司诉祺韵公司、优视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腾讯公司以著作权侵权、不正当竞争为由,将“5G芝麻”云游戏平台所在的祺韵公司以及提供“5G芝麻”云游戏平台的下载和分发服务的优视公司告上法院,要求两家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920万元等。该案中,被告两家公司认为其提供的是信息存储空间、链接等中立的网络服务或中立的技术支持服务,开发者可自主发布、运营、推广其应用等,其不进行人工干预、排名、编辑等,并不会收集、截取、修改、储存用户的数据。但是,广州互联网法院指出,祺韵公司未经腾讯公司许可,在网络上下载案涉五款网络游戏软件并上传到“5G芝麻”云游戏平台,以云计算为基础,通过交互性的在线视频流,使游戏在云端服务器上运行,并将渲染完毕后的游戏画面或指令压缩后通过网络传送给用户,致使社会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上获得并运行案涉五款网络游戏,侵犯了腾讯公司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后判决:祺韵公司赔偿腾讯公司的经济损失8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8万元。参见广州互联网法院(2020)粤0192民初20405号民事判决书。然而,对于数字新领域、新技术带来的价值观冲突,数字法治是否都能作出正确的解释与评判呢?例如,当前部分企业出于企业发展的目的,达成了算法合谋,引发了新的监管风险。(80)算法合谋的形式:算法从根本上影响市场状况,导致价格高度透明和高频交易,使公司能够快速、积极地作出反应。数字市场的变化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可能会使串通策略在几乎任何市场结构中都保持稳定;或者,通过为公司提供强大的自动化机制来监控价格、实施共同政策、发送市场信号或利用深度学习技术优化共同利润,可能使公司能够通过默契共谋实现与垄断相同的结果。正因为“在经济领域,如果立法机构不关注平等竞争,而支持在市场中违反古典经济学所珍视的平等原则垄断,则是荒谬的”。(81)Franz L. Neumann, The Rule of Law: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Modern Society, Berg Publisher Ltd., 1986, p.275.因此,对于算法掌控者运用算法分析大数据后进行的“黑市数据交易”“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中国已有相关文件予以禁止。(82)《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切实贯彻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严厉打击平台企业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超权限调用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从严管控非必要采集数据行为,依法依规打击黑市数据交易、大数据杀熟等数据滥用行为。”然而,算法的运用以及自动化的数据收集方式的出现,使得参与合谋的企业可以通过更为复杂的算法,轻易与有效地监控竞争对手的价格,以此来提高合谋效率以及监管的难度。(83)参见钱颜:《企业须警惕算法合谋反垄断风险》,载《中国贸易报》2022年2月23日,第6版。“我们已经不再有能力完全理解我们创建的算法所给出的结果。”(84)[瑞典]大卫·萨普特:《被算法操控的生活:重新定义精准广告、大数据和AI》,易文波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版,第33页。那么,是否意味着,数字法治不仅在形式维度存在着一些固有的通病,亦无法满足实质维度的需求呢?又或者说,数字法治是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又一次矛盾冲突,只能二择其一呢?笔者认为,数字法治可以在形式与实质、封闭与开放之间寻得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体现于数字法治的第三重维度,即程序维度。
三、程序维度下数字法治认知的匡正
如果说法治是一杆天平,那么在形式维度下,数字法治仅关注天平本身的性质、设计和准确度,而不关心天平所承载的事物和其价值。而在实质维度下,数字法治关心天平所承载的事物的价值,但可能只关注天平的一端,并且只涉及少数人。对此,一种中立的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机制的配置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程序性解决方案,它可以避免法律成为偏袒某些特殊利益的工具。法治需预先设定公正的法律程序以及合理的论辩规则,以引导相关当事人进行程序性的民主协商和论辩,或表达其意愿和需求,或主张其受侵害的利益。(85)参见陈林林:《法治的三度:形式、实质与程序》,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11页。与此同时,法治需要根据“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原则,来澄清和解决存在争议的法律标准和规范。相应地,法治角色也将发生转变:法律不再对特定行为提供实质性指导,而是组织参与、设计程序和规定权力,逐步成为决策程序的提供者。这种角色转变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有所体现,例如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立法者已经逐渐将焦点从技术、科学和责任问题判断转移到审查实际决策者的程序和行为上,并且也更倾向于利用程序手段来保护法律权利。
这就进入了数字法治的程序维度,即讨论程序法治于数字法治中的意义。程序法治是法治发展的最新发展动向,作为数字法治的第三个维度,程序法治主要表现为在遵行固定的顺序、方式与步骤的基础上作出法治化决定的全过程。(86)参见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83页。不同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程序法治并不赞成任何终极性价值设定,(87)参见高鸿钧:《现代西方法治的冲突与整合》,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或者说,程序法治并没有提前预设的真理标准,而是主张议论、决定过程的反思性整合,使当事人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需要与主张,从而确定争议化解的原则。“那些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只有获得所有相关人们——在理性沟通中作为参加者——的同意,才是有效的。”(88)Jurgen Habermas &William Rehg,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MIT Press, 1998, p.107.
遵行程序法治的结果,既可以消减甚至祛除形式法治的功能麻痹问题,也能避免实质法治的过度开放问题,形成一种独立于实体法的规范依据来源。(89)参见陈林林:《法治的三度:形式、实质与程序》,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12页。“程序的正当过程”这一用语,就是要强调程序中的价值问题。(90)参见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86页。与此同时,程序具有开放的结构和紧缩的过程,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然而程序参加者极难改变其结果,因此在效应上却是高度确定化的。(91)参见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83页。很多学者强调,法的发展是通过程序体系的严密化而实现的。(92)E. Adamson Hoebel, The Law of Primitive Ma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Legal Dynam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33.
对于数字法治这一“他者”,现有的法学理论流派仅有的共识是:数字法治与现代法治之间存在一种“次序性”更新迭代。而对于数字法治的程序维度,当前主要有三种认知模式。(93)浙江大学胡铭教授亦提出四种范式,分别为学科论、对象论、工程论和方法论。但笔者认为,这四种关系论亦可按照后文提到的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和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加以认知。参见胡铭、周翔:《看得见的“数字法学”》,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1日,第8版。第一种为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此种理解将数字法治看作现代法治研究方法论的一种拓展,或者说,是法学研究方法与数字技术研究方法的结合,例如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举例来说,一般而言,使用武力意味着对个人人身或财产进行非法暴力威胁或实施。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拓宽了军事法学对于武装暴力的研究范畴,最为明显的是网络武力如今已经被视为一种暴力形式。虽然可能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武装力量”,但其涉及对目标设施迅速的、有害的影响,甚至可以对其他国家产生某些有害或强制性的影响。(94)Lianne J. M. Boer, International Law as We Know It: Cyberwar Discour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Legal Scholarshi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63.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实际上是强调了数字法治的工具性作用。第二种为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此种理解将数字法治看作是现代法治理解范式的迭代,具体而言,将数字技术中的算法认知看作是继“经验认知—理论认知—计算认知”后的第四种认知范式。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实际上是将数字法治看作是法学分析方式的升级。
不难发现,无论是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抑或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对于数字法治的认识均更看重数字技术对于原有法学实践体系的一些改变和优化。诚然,在数字技术发展的早期,以上两种认识模式有其合理性,例如,对于数据隐私权的理解,必然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隐私权的相关规定,而如果想在数字时代寻求对隐私权的切实保护,必然要采用数字技术。(95)参见申卫星:《数字权利体系再造:迈向隐私、信息与数据的差序格局》,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100页。然而,法治本就是在“在历史环境的流变中产生的”。(96)[英]保罗·维诺格拉多夫:《历史法学导论》,徐震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165页。在过往,数字法治确实与现代法治之间存在基础理论的借鉴与研究方法的交叉。但是,数字法治如今已有其独立的涵义。2021年3月12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设立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专篇,并对“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生态”均设立了专章。广东省、浙江省开展了“数字广东”(97)《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中“重点建设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的八大载体”的第3项为“建设‘数字广东’”,其内容如下:“建设全省基础传输网络和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络,实现粤港澳网络一体化;建设网络民生、网络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在线化三大工程,实施数字家庭普及计划,实现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政务、商务、生产、生活中的普及应用,推进‘信息兴农’工程,实现‘泛珠’区域信息共享;大力建设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国家级产业园,形成优势信息产业集群。经过5年努力,全省经济社会全面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主要信息化指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珠三角地区信息化水平初步迈入全球信息化水平先进行列。”参见詹天庠、潘丽珍主编:《广东民营经济发展蓝皮书》(2007—2008)》,广东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438页。“数字浙江”(98)《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有相关表述:“数字产业竞争力全球领先,数字赋能产业发展全面变革,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全面形成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高水平建成网络强省和数字浙江,成为全球数字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理念创新重要策源地,为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和高水平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参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载浙江省人民政府网站2021年6月29日,https://www.zj.gov.cn/art/2021/6/29/art_1229620642_2409216.html。的建设工作。由此可见,作为社会理想化的治理形态,法治理应与经济运行、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及生态可持续发展等牵涉,因此有其独立的思考与体系,这也更契合国家的发展策略。(99)参见黄文艺:《迈向法学的中国时代——中国法学70年回顾与前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第8页。
因此,对于数字法治的程序维度又有了第三种认知模式,即本位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正确理解数字法治的前提,是要将数字法治视为现代法治为适应数字时代发展而进行的本体重建和代际转型,是法学总体发展的新阶段。(100)参见马长山:《数字法学的理论表达》,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第122页。正如拉伦茨在《法学方法论》中所说,发现个别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脉络,并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乃法学最重要的任务。(101)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6页。该理论并非质疑或否定前两种认识模式,但认为“只是功能、范围和认识方法的拓展,对信息革命带来的法学变革作用的认识仍不够深刻”。(102)张清俐:《创新数字时代法学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14日,第2版。正如农业文明升级为工业文明时,地域限制的打破使得以罗马法为基础的、以国内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现代法学无法在本体论上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多样化要求,(103)例如,经济全球化、气候变化和冠状病毒大流行等复杂问题已不是前现代法学所能应对与解决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社交网络会遇到不同的事情”。(104)Mike Hulme, Why We Disagree About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25.这就导致现代法治在吸纳借鉴前现代法治的基础上,逐渐替代前现代法治成为当时的法治主导形态。从法学理论的历史迭代来看,就形成了“古典法学理论—中世纪法学理论—近现代法学理论”的理论更替,而这种更替是基于法学理论对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和规则表达。在工业文明升级为数字信息文明的今天,面对数字空间出现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基于物理空间的现代法学同样于本体论上不再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105)参见马长山主编:《数字法治概论》,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425页。数字法治已经开始成为法治的主导形态。在此基础上,马长山教授提出本体论意义上数字法治理论构想。换言之,数字时代要求不能单纯利用物理逻辑来解释数字信息社会出现的现象和行为,因此对于数字法治的程序维度也不应将此限定在工具主义的框架内。例如,“网络法”(106)例如,郑成思先生认为,“网络法”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因国际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及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法学概念,是“解决因互联网络而带来的新的问题”的有关法律的一个总称。参见郑成思:《“网络法”的研究与完善》,载《法制日报》2000年2月20日,第3版。“人工智能法”(107)例如,刘艳红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法学是根据国家有关人工智能技术指向明确、政策导向直接的纲领性文件的规定,由“人工智能+法学”交叉融合而成的独立新型学科。参见刘艳红:《人工智能法学的“时代三问”》,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5期,第35页。“网络空间法”(108)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电子商务法教授克里斯·里德(Chris Reed)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法学教授安德鲁·默里(Andrew Murray)均认为,网络空间法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民族国家法律体系产生的法律不具有高于其他规则的特殊性或绝对权威。民族国家法律仅对该民族国家社区的成员具有权威性;二是民族国家法律并不是网络空间权威规则的唯一来源。非国家的规则体系不仅存在,而且在其运作范围内,似乎产生的规则对网络空间用户来说比民族国家的法律更具权威性。Chris Reed &Andrew Murray, Rethinking the Jurisprudence of Cyberspace, Edwrard Elgar Publishing, 2018, p.78.等。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概念,是基于研究者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理论以及各自知识储备等的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者的创见,但也将数字法治研究演变成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应急式研究。数字法治是进入数字时代后,法治程序本体的再次转型与升级。(109)参见马长山:《数字法学的理论表达》,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第123页。对于中国而言,数字法治在程序维度带来了司法和社会两个层面的变革。
一是来自司法程序的变革。“程序公正性的实质是排除恣意因素,保证决定的客观正确。”(110)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85页。而数字法治的应用,为司法由“接近正义”向“可视化正义”转变带来了新的动力与契机。如前所述,数字技术能够大幅度提升司法的纠纷处理能力,降低解决纠纷的成本。例如,2021年至2022年上半年,广州互联网法院新收各类案件73 143件,审结71 007件,一审服判息诉率98.42%,(111)数据来源于2022年8月18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在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发布的《关于发挥司法职能作用服务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工作情况的报告》。参见张璐瑶:《广州互联网法院去年至今年上半年新收各类案件73 143件》,载金羊网2022年8月21日,https://news.ycwb.com/2022-08/21/content_40993959.htm。远高于国内法院的平均水平。(112)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大会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指出,2021年,全国法官人均办案238件,一审服判息诉率88.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摘要)》,载《人民日报》2022年3月9日,第3版。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纠纷解决的自动化程度。其中,在存证方面,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了证据存储的可视化、自动化和固定化。(113)参见胡铭:《区块链司法存证的应用及其规制》,载《现代法学》2022年第4期,第166页。以北京互联网法院天平链为例,截至2023年9月18日,天平链共在线采集数据数239 305 101条,在线证据验证数32 236条,主链链接区块数量46 636 404个。(114)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天平链”》,载北京互联网法院网站2023年9月18日,https://tpl.bjinternetcourt.gov.cn/tpl。在辅助案件审理方面,以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又称“206工程”)为例,其包含智慧传译系统、金融案件审判的智能化诉讼服务系统、智慧保全服务平台以及诉讼风险评估系统等高品质应用。截至2019年底,上海刑事案件办理实现了立案、侦查、报捕、起诉、审判均在“206工程”内运行,且成效显著。(115)自2019年1月至2021年11月,“206工程”辅助公安机关累计录入案件123 894件;检察院受理逮捕案件54 365件;检察院受理公诉案件69 791件;法院受理案件59 661件;法院审结案件53 864件。累计录入证据材料43 883 431页、提供证据指引179 589次(依系统点击量统计)、提供知识索引1 580次、提示证据瑕疵24 679个。参见《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载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平台经济创新专委会网站2022年7月3日,http://www.cciaitic.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8&id=967。因此,依据中央政法委的部署,“206工程”开始逐步在全国推广。(116)“206工程”已在安徽、山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贵州、云南、吉林、青海、深圳、海南、拉萨、河南等多地开展试点应用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参见《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载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平台经济创新专委会网站2022年7月3日,http://www.cciaitic.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8&id=967。
如果说,上述数字技术于司法领域的运用更多体现在对诉讼成本的节约,也就是对司法效率的追求上,那么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数字法治对于司法程序的价值实现,甚至于对司法权的合理运用而言,则有其特殊的价值。
司法程序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升效率,更在于追求公正。(117)参见雷磊:《司法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司法公正?》,载《政法论丛》2022年第4期,第72页。因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118)参见《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4年10月30日,https://www.gov.cn/xinwen/zb_xwb40/content_2772626.htm。“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11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1版。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公正、合理地运用司法权。司法权以判断为本质内容,是一种判断权,(120)参见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载《法学》1998年第8期,第34页。而这种判断权又极其依赖于司法的亲历性。此源于,法庭所审理的纠纷问题通常具有微观性和复杂性,因此法官在形成对证据的采信和证据链判断的心证时,往往需要与当事人进行密切接触,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案情和证据。有鉴于此,司法程序极为重视司法人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亲历性,(121)参见游劝荣、姚莉:《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司法模式探究》,载《法学评论》2022年第5期,第14页。即司法人员必须亲身经历案件审理的全部程序,包括亲历事实质辩、亲历证据证明、亲历案件审理、亲历结果判断等。(122)参见朱孝清:《司法的亲历性》,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第919页。然而,疫情的暴发一度阻碍了司法亲历性。对此,数字在线技术于司法中运用,尤其是在线诉讼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司法人员即使“零接触”亦可参与诉讼的各个环节。(123)《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1条规定:“人民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可以依托电子诉讼平台(以下简称“诉讼平台”),通过互联网或者专用网络在线完成立案、调解、证据交换、询问、庭审、送达等全部或者部分诉讼环节。在线诉讼活动与线下诉讼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那么,类似于在线诉讼的数字技术,是否可以保证司法的亲历性呢?
从理论上来看,首先必须予以承认的是,在线诉讼与线下诉讼于司法亲历性的表现形式上的确有所不同。因此部分学者认为,在线诉讼中法官的司法亲历性受到了减损,具体表现为因法官缺少关于证据或事实的直接印象而造成对心证的影响,因此有损法官对于事实的认知。(124)参见高通:《在线诉讼对刑事诉讼的冲击与协调——以刑事审判程序为切入点》,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27页。然而,在线诉讼与线下诉讼于司法亲历性的本质上并无二致。司法亲历性的核心并不在于诉讼场所是线下的物理空间亦或线上的网络空间,而是在于是否以案件的事实认定为重点,进而能否确保案件事实在法庭上得到查证、诉讼证据在法庭上经过质证、辩诉意见在法庭上得以陈述以及裁判结果在法庭上得以形成,最终于法官心中形成一种“同理心正义”。(125)参见杜宴林:《司法公正与同理心正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10页。而事实上,于在线诉讼程序中,法官完全具备通过网络法庭对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进行细致观察的能力,理解其情感表达,并对电子化证据材料进行清晰、详尽的审视,进而形成独立的内心确认。也就是说,在线诉讼并不构成对司法亲历性的减损,二者之间并不矛盾。(126)参见左卫民:《中国在线诉讼:实证研究与发展展望》,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169页。究其根本,运用数字技术的在线诉讼实际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项程序性选择权。(127)参见肖建国:《在线诉讼的定位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33页。公民无论选择线下法庭抑或智慧法院的线上法庭,二者均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或网络空间,而是依据司法程序的目标设计的特定的审判平台,二者在功能上均作为承载司法程序的“场所”,并无不同。对在线诉讼的偏见,并不是来自对数字技术的担忧,而是来自“主观认识上的障碍”。(128)参见田圣庭:《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在线表达》,载《社会科学家》2023年第7期,第104页。也就是说,这种偏见所涉及的问题仅仅是个人认知领域的问题,完全可以伴随时代观念的更新迎刃而解。
从实践来看,运用数字技术的在线诉讼与审理亦已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人民法院大力推进互联网司法和智慧法院建设……形成了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的智慧法院信息系统”,(129)张晨:《互联网“最大变量”成“最大增量”》,载《法治日报》2022年9月8日,第6版。实现了跨域立案服务全覆盖和跨境网上立案。截至2023年3月,全国法院网上立案2 996万件、开庭504万场、证据交换819万件次、异地执行593万件次、接访15万件次。(13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人民法院报》2023年3月18日,第3版。
二是来自社会治理层面的变革。传统的社会治理以科层制为治理模式,治理的基础是行政级别和地域关系,同时以物理空间作为治理的场域。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为人类在物理空间生活的同时,塑造了虚实同构的“在线生活”,形成了一套“法规的/自愿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国家的/超国家的、等级制的/分散的”全新治理模式。(131)参见[英]詹姆斯·柯兰、娜塔莉·芬顿、德斯·弗里德曼:《互联网的误读》,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页。在这个全新的模式下,传统的行业和地理限制被揭去,导致基层结构的扁平化和瓦解,致使行政能力的应对效果略显不足,取而代之的是“代码就是法律”。(132)参见[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因此,数字法治必须能够涵盖数字技术运用的整体过程,即从数据的收集、存储、运用与流通,到作为生产、社交、文娱中心的数字平台,再到繁多的、具体的数字产品使用场景。然而,需要予以审慎的是,数字技术虽然能够促使政府在社会治理层面减负增效,但无论从形式维度抑或实质维度对数字政府加以认知,都可能导致出现政府工作趋向效能至上主义或者数字官僚主义的误区。
数字政府的初衷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实现业务和技术的深度融合,提升政府履职效能”。(133)王益民:《加强数字政府建设 全面提升政府履职能力》,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2年8月2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8/26/content_5706940.htm。如果从形式维度对其加以理解,数字技术的运用使得政府治理结构从“碎片化”向“整体化”转变,(134)参见蒋敏娟、黄璜:《数字政府:概念界说、价值蕴含与治理框架——基于西方国家的文献与经验》,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第177页。缓和科层制下行政资源的有限性与行政任务的无限扩展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135)参见展鹏贺:《数字化行政方式的权力正当性检视》,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第114页。进而提升政府的治理效能。但“效能”是“法治”的追求,却并非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法治建设侧重于对国家权力的掌控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而效能的追求则更注重对成本与效益的分析,对一些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存在着一定的纵容或使之合法化的倾向。(136)参见范柏乃、林哲杨:《政府治理的“法治—效能”张力及其化解》,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170页。“一旦数字政府建设以提升治理效能为中心,就容易忽视人的主体地位,导致人权价值被漠视。”(137)刘权:《数字政府建设中数字化与法治化的融合》,载《当代法学》2023年第6期,第16页。加之出于功利主义、追求政绩等复杂因素,形式维度下的数字政府治理会陷入工具主义的悖论之中。(138)参见马长山:《数智治理的法治悖论》,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4期,第71页。例如,某些地方政府出于维护地方稳定或提供公共服务等目的,借助大数据分析开展预测性治理并获得了极大成功。但这种预测性治理并不关注大数据的精确性,即摒弃了对数据来源因果关系的追求,(139)参见[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从实践层面颠覆了人类理性本身对因果关系的认知,(140)参见王天思:《大数据中的因果关系及其哲学内涵》,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第23页。“代替了人民群众具体而复杂的现实需求以及问题处理”,(141)张柏林:《数字治理中的政府权力约束和权力释放探析——基于统筹治理的视角》,载《领导科学》2023年第5期,第112页。甚至将导致政府治理目的与治理手段之间的本末倒置。(142)参见李云新、韩伊静:《国外智慧治理研究述评》,载《电子政务》2017年第7期,第60页。
同样,如果从实质维度加以审视,将数字技术视为政府职能或者权力的组成部分,可能会为政府带来缺乏同理心的挑战。与形式维度的工具主义不同的是,数字化行政已经从最初的程序性的“服务功能”向实体化的“决策功能”发展。(143)参见展鹏贺:《数字化行政方式的权力正当性检视》,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第1121页。一些行政行为的实体性决定,如行政审批工作,已经可以脱离人工转变为由算法主导的“智能审批”。(144)例如,陕西自贸试验区已经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行政审批全过程“智慧办”。参见崔春华:《陕西自贸试验区行政审批全过程“智慧办”》,载《陕西日报》2023年8月31日,第7版;又如,昆明市西山区引入专业的流程自动化智能机器人,确定一批适合采用AI“智能审批”的事项,做到办件“秒办秒批”。参见孙潇:《西山区启用AI“智能审批”》,载《昆明日报》2023年9月20日,第A02版。但有学者指出:“当政府开始放弃了人类的智力和专长,转而支持那些自动给予或拒绝利益与权利的体系时,灾难就会悄然而至。”(145)Ryan Calo &Danielle Keats Citron, The Automated Administrative State: A Crisis of Legitimacy, Emory Law Journal, Vol.70:797, p.838(2021).因为数字技术毕竟“缺乏同理心”。(146)Cary Coglianese,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Automated State, Daedalus, Vol.150:104, p.113(2021).如果算法决策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对人的行为进行驱动、引导、刺激、控制、限制,算法的接受者无疑陷入了“算法铁笼”之中。(147)参见段哲哲:《控制算法官僚:困境与路径》,载《电子政务》2021年第12期,第6页。还有学者指出,算法使得公民权利同时处于赋权与失权的矛盾状态之中。一方面,个人感受到科技进步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利,因为他们能更方便地获取信息、进行交流、组织活动,从而丰富他们参与公民生活的方式和方法;但另一方面,个体、民间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及地方社区日益感到自己被传统决策程序排斥,丧失有效参与的能力,其影响力与话语权被主导机构忽视,国家与地方治理权力日渐弱化。(148)参见[德]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李菁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97-98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数字官僚”阶层,而公众在面对数字政府时表现出的无力感恐造成更为严峻的“法治悖论”。(149)参见马长山:《数智治理的法治悖论》,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4期,第69页。
当从程序维度来审视数字政府抑或数字法治时,又会有以下发现。一方面,数字技术之于政府治理,不应仅仅看作是政府治理的一种工具,而应当看到其有自身的程序价值。政府治理是政府部门以功能为中心进行的,而行政法治注重的是“整体适用”,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既要对社会的需要作出充分的反应,又要在应用上坚持平等性、一致性等原则,这就需要充分理解并响应群众的诉求。而现代化政府治理中,要求重塑一种以“需求”为核心的、符合民众需要的、提高政府公信力的行政程序,实现由“政府中心”向“用户中心”转变的国家治理模式。数字技术对公众参与具有某种推动或限制作用,数字化政府的构建使得政府机构可以根据公众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需求来提供区别化的服务,甚至于“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服务也已经不再遥远。(150)Helen Margetts &Cosmina Dorobantu, Rethink Government with AI, Nature, Vol.568: 163, p.163-165(2019).与此同时,公众参与本身也能够反作用于数字化政务程序的提升,(151)参见常多粉、郑伟海:《网络问政时代政府回应如何驱动公众参与——基于领导留言板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载《社会发展研究》2023年第2期,第152页。从而使得政府的决策更具有民主性基础,这是数字技术之于政府治理的价值所在,(152)Eyal Peer &Serge Egelman, et al., Nudge Me Right: Personalizing Online Security Nudges to People’s Decision-Making Styl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109: 1, p.1-9(2020).也更符合数字政府的运作逻辑。(153)Karen Yeung, Algorithmic Regulation: A Critical Interrogation, Regulation &Governance, Vol.12: 505, p.517(2018).另一方面,政府部门是否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或者如何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决策,本质上仍属于政府治理方式的自主程序选择权的范畴。从程序角度出发,治理规则是否具有公开透明的程序是数字政府的核心问题。(154)Mireille Hildebrandt, Algorithmic Regul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Vol.367: 1, p.9(2018).即使是“自动决策”,隐藏其后的决策基准依然是由政府部门预先设定,将政府的意志以前置的形式嵌入到具体行政程序的启动之前,数字技术只是负责执行这一程序。(155)参见高秦伟:《数字政府背景下行政法治的发展及其课题》,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2期,第179页。因此,“自动决策”并未完全脱离政府的掌控。甚至可以说,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够在程序上更好地保障“政府—公众”之间信息传递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尽管数字技术减少了行政程序的人为控制,但是通过对特定决策步骤的执行和对外部执行行政权的影响,行政机关仍然可以控制其行政决定。
更为重要的是,较之于西方,中国的数字法治更有其独有特色,即始终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156)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第2版。数字化建设已经进一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重要发展方向,将数字法治运用于普惠包容的数字社会也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有鉴于此,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数字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数字法治在构建数字社会治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社会治理的全民共建必然要求社会公共利益和治理成果的全民共享。数字法治有助于妥善解决数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城市社会生态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实现公共资源的公正分配,消除城乡间数字鸿沟,从而让更多人分享到数字化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推动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
与此同时,数字法治覆盖社会法治所关注的众多领域,将过往碎片化的治理方式进行统合。爱因斯坦曾说:“科学是这样一种企图,它要把我们杂乱无章的感觉经验同一种逻辑上贯彻一致的思想体系对应起来。”(157)[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1卷)》,许良英、李宝恒等编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27页。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例,通过司法大数据的运用,2021年4月至2022年5月18日,国家反诈中心直接推送全国预警指令4 067万条,各地利用公安大数据产出预警线索4 170万条,成功避免6 178万名群众受骗。(158)参见张天培:《预防为先,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载《人民日报》2022年5月18日,第11版。再以疫情防控为例,中国现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是在现代科层制的基础之上,要求行政机关实现责、权、利的合理配置与动态平衡,以此提升责任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协同性,(159)参见李金龙、武俊伟:《京津冀府际协同治理动力机制的多元分析》,载《江淮论坛》2017年第1期,第73页。从而降低政府各层级与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打破政府信息“孤岛”,擢升行动效率。为此,中国已经自上而下成立了中央、省、市、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建了全球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疾病信息网络直报系统。(160)参见王红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及其评价体系研究进展》,载《卫生软科学》2020年第11期,第4页。数字平台作为“城市大脑”,能够实现“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在保障重大风险监管、辨别、预警、跟踪与处理能力的同时,实现了多极化治理主体之间的横向联通与纵向贯通,数据顺畅的传输、信息系统的兼容、数字安全的协作与专业人员的支持,合力提高了城市的整体行动能力。(161)参见于水、杨杨:《重大风险应对中的城市复合韧性建设——基于上海疫情防控行动的考察》,载《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第69页。甚至于,许多日常个人运用软件亦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162)例如,百度地图启动各类场景强提示,实时上线道路封闭信息,并推出公众场所人流密度大数据,引导公众提前避开;通过大数据分析推送、“头条寻人”整理更新有关信息,联合各地发布寻找与确诊患者同乘交通工具的乘客;美团App、大众点评App等推出全国定点医院与发热门诊实时在线查询服务,涵盖全国103个城市发热门诊信息。参见新华社:《用好大数据 加强疫情防控精准施策》,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0年1月27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1/27/content_5472436.htm。“数字科技”能够整合、统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算法等,数字法学能够统一目前相对分散与孤立的有关数字科技的法律研究。(163)参见《“数字法学三大体系建设研讨会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数字法学教研中心成立仪式”在京举行》,载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2022年4月2日,http://www.gzpopss.gov.cn/n185/20220402/i2451.html。
总而言之,从程序维度而言,数字法治“为更加接近正义奠定了现实基础”。(164)[美]伊森·凯什、[以色列]奥娜·拉比诺维奇·艾尼:《数字正义:当纠纷解决遇见互联网科技》,赵蕾、赵精武、曹建峰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64页。从程序维度理解数字法治,相对于形式维度而言,能够保障法治过程的实质公正性;相对于实质维度而言,亦能够确保程序的正义性,因此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165)参见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法治程序正义的“可视性”将愈发清晰,社会治理体系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将更加公正、公平、公开与人性化。
四、结语
随着数字技术应用领域的逐步拓展,人类已经开始迈入数字时代。对于数字时代的法治形态,必将有新的理解与模式。(166)参见李占国:《“全域数字法院”的构建与实现》,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1期,第6页。
对于数字法治的解析,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探讨,包括数字化建设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数字化技术的安全保障、数字化技术与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结合、数字化建设的普及率和认可度等。笔者认为,对于数字法治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数字法治的研究,理应形成一种共识,即对研究数字法治、发展数字法治理论的真正目标形成共识。当前,中国的数字法治实践已悄然走在世界前列,数字法治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前所述,无论是人民法院主动为之的数字化建设,还是新冠疫情暴发背景下政府被动运用的数字化技术,均为未来积淀了发展数字法治的绝佳的经验。然而,之所以选择数字法治,难道单单是为了提高法院或政府的工作效率吗?答案绝非如此简单。
研究数字法治,可以说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高度数字化的时代。数字法治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既保障个体权利,又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数字社会。研究数字法治,也可以说是为了推动社会的法治进步。数字技术的发展给法治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深入研究和探讨数字法治,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并利用这些机遇推动社会进步。研究数字法治,还可以说是为了寻求更高效、更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数字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通过研究数字法治,可以找到新的方法,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和公正性。以笔者之见,研究数字法治的真正意义在于如何根据中国当前社会治理进程妥善运用数字技术,进一步推动与实现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或许才是中国法学界孜孜不倦的探寻数字法治背后真意的根本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