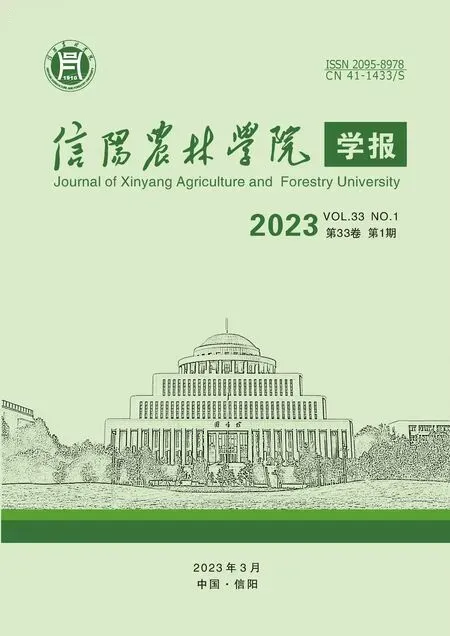论马克思“生态人”生成的历史演进
2024-01-02鲁桐君
鲁桐君
(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信阳464000)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在多部论著中对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给予了详尽的阐释,本文将处于这种辩证关系构境中的“人”称为“生态人”。从生存范式和价值意蕴来看,马克思“生态人”的生成经历了从“自然人”生存范式到“主体人”生存范式再到“生态人”生存范式的转换。从逻辑生成的微观层面来看,“生态人”概念是在与“自然人”和“主体人”的总体叙事框架中呈现出来,是在与“自然人”和“主体人”的双重差异中得到确证并在“主体人”成就的历史局限性中被建构。马克思的“生态人”是指具有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念和承担充分生态保护责任的道德人,这种道德人是在“自由人的联合体”(生命共同体)中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总体性维度去实践生命活动的价值旨涉,更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向度在社会有机体里整体性构成的具体实现。
1 从“自然人”到“主体人”的生存范式转换及其价值意蕴
就自然的先在性而言,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类最本源的创造者,人类物种的诞生肇始于自然。“人在肉体上只要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1]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人类生存的母体或“底片”。另一方面,从人类发生学来看,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一种有意识、有生命活动的自然,是一种“特殊”的自然,是可以赋予自然以人类学意义的客观存在。正是自然的进化发展才创造了人的肉身、基本意识和人的道德理性。
1.1 “自然人”的生存范式及其价值意蕴
在早期原始人类社会时期,人作为大自然之子尚处于襁褓之中,于自然的漫长孕育之中随着阵阵啼哭而呱呱坠地,大自然是神圣不可冒犯的天威,而人则是作为大自然的“奴仆”而生存,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处于一种“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的混沌未凿的蒙昧性和谐。自然人在意识层面造出万能的神灵或上帝,企图让自己不可理解的自然事物变得合理化,给自己的生命活动注入现实意义,乞怜神灵庇佑自己的生活。在这种阶段“人的生产技能不过在狭小的领域内和隔离的位置上发展着”[2],虽然也有“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征服和改造大自然的远古神话,但是敬畏崇拜自然是蛮荒时期人们别无他法的选择。
自然人的自然观实则是“自然给人立法”。自然在自然人眼中作为创生万物的源泉,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性和统摄一切的权威,雷霆万钧、绵绵细雨等自然现象成为神灵带给人类活动的启示,自然人以神灵的“隐喻”或“梦呓”为准绳调节自身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活动。描绘着动物或植物的图腾文化成为他们的信仰,他们跪拜在这样的图腾下,虔诚地祈求神灵能够赐予他们美好与幸福的生活。自然人秉持原始和纯真的心态,把直接体认到的东西视为珍贵的东西,在这种原始的“天人合一”的认识过程中,还没有明确出主观和客观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都是浑然一体的。在这样的意识中,人类相较于自然的主体性地位只是在虚幻的观念中进行表现,“自我应该沉没在虽说是另外一个自我里,不过是一个远在彼岸的自我里;只有在它里面自我才应该有它自己的价值”[3],自然人的主体性意识就这样消融进神灵的绝对逻各斯之中了。
自然人的生存范式即“自然化生存”。处于这种生存范式中的自然人感受到的实体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他们把看得见的事物与看不见的事物合二为一,把自然神灵人格化,“诗性思维”占据主导地位,尚未有理性思维的觉醒。在自然人的运思理路中,自然界仅仅停驻在直观的感受和朦胧的神秘这一度,人类以动物的本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的环境变化。自然人“把劳动的自然前提看作属于他所有这种关系的前提,但是,这种‘属于’是由他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作中介的”[4]470。自然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仅仅只能依赖于自然环境所提供的自然资源,采集、狩猎、金属的冶炼、农桑的耕耘等生产方式都以人的生存需要和使用价值为目的进行生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血缘亲近、宗法谱系为标准的直接依赖性关系,此时建立的属于自然人的经济、政治、军事关系一方面受限于直接依赖性关系,另一方面臣服于自然经济强大的异质性力量下,也必然伴随直接的附属和强制属性。
自然人的价值意蕴实质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赫斯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看重的所谓人类本真的“尼德兰图画”。首先,自然人的价值意蕴在某种程度上与黑格尔眼中的自然相暗合,自然人先把自己设定为与自然对立的存在物,然后在意识的照映下把自身同化成自然。实体自然与人本身实现身心交感的过程不过是意识的“画圈之旅”。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5]45其次,自然人的价值意蕴又在某种程度上与费尔巴哈眼中的自然相暗合,自然人过分在意人与自然的同质性,又被自然神秘主义的阴霾所笼罩,所以不了解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的辩证关系,不明白人类史与自然史是依靠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呈现出相互交织的璧合状态,甚至将人类等同于跳蚤等自然之物,将自身幸福的实现寄托于神秘的自然力量之中。试问没有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然谈何是现实的自然?没有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自然谈何是属人的自然?没有人的需要和改造发挥作用的自然谈何是历史的自然?自然人所期盼的幸福与美好注定是堂吉柯德式的精神幻想。
1.2 从“自然人”生存范式向“主体人”生存范式的转换
随着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历时性发展,人对自然的看法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在人的境遇的不同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现实样态。正是实践的历时性决定了“自然人”的生存范式向“主体人”生存范式的转换。马克思曾指出在人类史上由物质实践构成的人的生存范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态:第一,是以血缘氏族聚集在一起的生存性交往阶段,这一阶段是使人类社会从动物集群中分化出来的关键,即自然人的生存范式;第二,是建基于以交换价值为圭臬的一切劳动与财富的交换性交往阶段,这一阶段是人的主体性高昂的阶段,即主体人的生存范式;第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人的个性自由交往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实现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即生态人的生存范式。每一种人的生存范式都以前一种生存范式为发生学前提而依次嬗递。
事实上,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旦可以生产出剩余产品,就会进步为原始共同体之间分工和交换的商业活动行为,接踵而来的便是对原始共同体即自然人组成的原始社会的矇昧性、混沌性的否弃。在这样的分工、协作、交换的物质生产过程中,个人的实践能力愈发增强,原始的自然人的生存范式越来越难以禁锢人活动的空间范围和思想界限,人的观念定在和物质积累打破其边界的同时并不断延展,产生了阶级和私有制,从而构建了阶级共同体和观念共同体即国家。同时,在人的思维世界中,个人的主体意识绽放,自我的展露撕破了原始的“集体表象”,凝结出多极个体。语言和文字的出现使得主体的精神产品得以在不同时空中被另一主体所体悟、占有,各种思想和技术才能在不同主体间快速传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人分离的情境下也开始疏远乃至对立,早先那种原初“天人合一”的生存范式在人与人分离的催化下也逐渐分崩离析。在这种主体人创造的世界或自然界,是有别于自然人生活的原始世界,是一个真正的以人为中心的人化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6]86
2 从“主体人”到“生态人”的生存范式转换及价值意蕴
费尔巴哈把自然界视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即“无理性的人身”,他相信通过维持人类生存机能的自身能量的释放,人才能让大自然的存在物进入人的躯体成为人的本质,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与费尔巴哈旧的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不仅从自然客体方面,而且从人的“主体地位”、从人的对象化活动维度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去把握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2.1 “主体人”的生存范式及价值意蕴
自人类走出原始的氏族社会和黑暗中世纪后,哲学也由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转向认识论哲学。笛卡尔的心灵哲学和自我概念的提出如闪电般照亮被神学统治的万古长夜,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开始重视自我的价值和自我的地位。笛卡尔相信,通过怀疑能够被怀疑的一切,一个不受神性蒙蔽的,能够打破经院哲学的新的哲学思想定会喷涌而出,从而把人类从面对自然时的弱小无力和面对上帝的盲从迷信的精神囚笼中解放出来。这种怀疑论正如马克思所说,“是摧毁陈腐教条的极为有力的武器”[7]。因此,人类在怀疑论之后便以理性为地基,一路把真理大厦盖起来,实现对世界的充分理解和充分探索。人作为独立的自觉自为主体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意味着原始的完整的世界分裂为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两极,原来世界的浑然一体性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以主体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开始生成,于是整个客体世界不断退缩为主体人的历史注脚。“近代哲学的原则并不是淳朴的思维,而是面对着思维与自然的对立”[8],在这种哲学意义的背景下,本来偏居一隅的自然人由此获得了主体性的意义。
“主体人”生存范式的第一个特点是马克思所说的“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4]107。在这样空前发达的社会联系之中,个人超越以往的“自然联系”,超越以往作为族长或领主附属物的命运,真正作为独立的个人而存在。自工业文明伊始对资本的渴求俨然压倒一切对自然的敬畏,技术理性如同是被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吞噬着人的纯真本性,金钱至上的理念使每个人都陷入一种极端的疯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被异化为客体商品和金钱之间的交换关系。“主体人”生存范式的第二个特点是对自然的掌控能力大大增强。主体人在“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下向着自然界发起前所未有的攻势,自然界在主体人眼中也不再是不可捉摸的“黑箱”而是僵死的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自然内在的完整意义被淹没在主体人对自然的功利性渴求之中。自然物按照对人类的价值大小被由近到远的排序,人们根据价值大小来决定对自然物掌控的疆域,主体人成为自然物价值存在的预设前提,奴役、剥削自然界也就成为主体人世界的通行规则。“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等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6]119在主体人肆意掠夺自然物的过程中,由于人对自然的越位,本应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大自然不断被人类竭泽而渔,逐渐耗散于人的饕餮之欲中。
主体人的价值意蕴在自然观领域内揭橥为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对象性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本质上成为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一言以蔽之,“主体人”的价值内涵实则就是传统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主体与客体都在科学精神的内在规定下被运算、解构、重演乃至吞噬,科学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祛魅实质是一种促逼,正是这种促逼助产了世界成为图景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历史进程。这一科学技术的“解蔽”和神话崩坏的“弃神”的动态图景也就是“主体人”统治地球的现实图景。人在征服奴役自然的同时也奴役了人自身,在另一种程度上陷入了更深的自然的束缚。为此,“主体人”演化的历史进程本身就是沾染悲剧色彩的矛盾运动过程。它的本意是要使人成为自己完善自己、超越自己的积极力量,并打破笼罩在人身上神话和迷信的无形枷锁,但其结果却又使自身变为一种新的桎梏人、奴役人的更大的束缚。
2.2 从“主体人”生存范式向“生态人”生存范式的转换
近代的笛卡尔主客二分哲学与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是“主体人”生存范式的理论背景,这种哲学意涵虽然极大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却也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态危机。为了突破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以人现实的感性活动为枢纽,将主体的能动性和客体的先在性融为一体,并认为全部的人类活动(包括思想理论活动)不仅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去理解,更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理解,因为人的本质不仅具有自然性更具有社会性,倘若只从自然性向度去理解人的本质,那么将永远也达不到现实性、具体性的重要命义。
主体人在主客二分思想的指引下对自然任意亵渎与宰割,成为其思想的显性症候,演绎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生态腐败图并可能最终导致人类文明遭受灭顶之灾。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313生态危机正是“主体人”的主体性得不到全面、充分与健康的发挥而造成的,是部分人的主体性恣肆发挥而对另一部分人的主体性的无情掠夺造成的,是科学技术被资本异化之后造成的,同时,也是人的异化在自然界的现实延伸。“生态人”作为超越主客二分哲学范畴的人性假设是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构境中出场的,“生态人”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功利性价值论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价值论所扬弃,“主体人”对自然界的掌控和破坏将会在“生态人”中得到修复和保护,“生态人”所处的自然界将会在更加丰富多彩的完整性中获得一种全新的意涵。在这种意涵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强势支配,而是在双向生成中绽放出自然的美丽和人性的美好,“生态人”不仅仅只是生态的人,更是生态的社会,只有在生态的社会中人才会具有生态意义。
3 马克思的“生态人”的价值意蕴及其评价
马克思视阈下的自然既不是形而上的抽象物,也不是脱离人类世俗活动的伊甸园,而是浸透了人的类生活色彩并反作用于人的现实存在。“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的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6]104在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人类不断地向自然生成,使人趋近于物。自然也不断向人类生成,使物趋近于人。因此,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对自身以及对他人对社会的态度。
3.1 马克思的“生态人”及其价值意蕴
马克思视阈中的“生态人”是指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将合理的对象性活动作用于自然的,富有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道德人。这一道德人从属于自然界,但又生活于社会之中,以感性活动为炉鼎熔铸自然因子与社会因子于一体。这种道德人其内涵是“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52。“生态人”就是要从人与自然的双向压迫中获得双向解脱,人的本质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与占有,“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之间的矛盾冲突得到前所未有的和解,人本质的异化及劳动的异化在不断扬弃中实现历史性的回溯与超越,是在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双重辩证过程中达到“总体性”的对立统一。马克思认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是“生态人”真正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共产主义的实现同时也宣告人类“史前时代”的终结,人类真正进入属于“自然的人类史”与属于“人类的自然史”。“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6]78“生态人”也就是在人化自然的自为辩证过程中实现人类本质的充分展现和全面自由自觉的劳动生产实践方式。
“生态人”的价值在于成就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使之共同到达了辩证的历史的统一境界。这种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双重蕴涵,采用了全新的向度和方法,克服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利益为圆心规定人的症结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把人降格为普通生物的弊病。在“生态人”的视域内,人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体现出自己是能动与受动的双重存在物。“自然界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6]116,人在与自然的辩证对话中,自在自然融入人类因子与社会因子,渐渐摆脱原始的青涩的状况,人类也超脱了被资本侵蚀下的粗鄙的工具性价值圭臬和功利主义原则来对待作为属人身体的自然,以美的规律,按照“种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精心雕琢、再塑造整个自然界,使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超拔于自然必然性之轭,人类作为自然最得意的作品完美镶嵌在自然的宝冠上。在人与自然的双向生成中,“生态人”并不是脱离自然跃然空中的翩跹精灵,也不是顺从自然必然性摆置的提线木偶,而是融能动性与受动性、“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之物,正是这种能动与受动、“自律”与“他律”的契合显露了从事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人“自觉”的状态以及皈依之上的“自由”。这种“自由”“自觉”表明“生态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6]78。
“生态人”经过对主体的积极扬弃,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之前对峙的两极转换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的共生关系。此种共生关系并非原始的“天人合一”关系,而是“美”(合规律性)与“善”(合目的性)的历史统一。人类的自由总是嵌入自然的自由之中,人类要行使自己的自由,就必须要首先尊重自然的自由。“生态人”价值生成的历史履程绝不是人类私欲肆虐泛滥的溃烂图景,而是主体价值与客体价值在人、自然、实践三维立体坐标系中复合生成的动态景况,在这样的生态之境里自然与人显现了完满的意蕴相洽。在人与自然的相互联动与协同进化中,作为生成价值经纬的实践使自然内在的固有特性由抽象价值蜕变为现实价值,但自然的固有价值总是通过各种感性的具体的表象及各种偶然性表征出来,而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和利用这些生态价值也是人理性地对待理性主义本身应有的态度和方法——须知理性本身恰恰需要理性地对待,盲目的理性恰恰是一种非理性。
3.2 对马克思“生态人”的评价
从理论意义上来看,“生态人”作为自然和社会存在物在现实活动中眷注了深厚的生态关怀,生态性作为内在参数被写入社会运作的底层逻辑之中。“生态人”在运用“理性思维”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的生存,在实践过程中完成自己理想生命的升华和重构。同时,“生态人”通过实践使自然成为“社会的自然”,继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自然与社会合为一体的人类世界。在此种哲学意蕴上来说,实践既是“生态人”生存的本体,又是现存社会的本体。面对“主体人”留下来的人存在的虚无深渊及失落了生活的本真意义,“生态人”通过对象性活动逐步填补着“应然”与“实然”的巨大鸿沟。在“生态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既不同于“自然人”部落的联合,也不同于“主体人”阶级对抗的虚假共同体,人与人之间消灭了剥削与被剥削的残酷现实并摆脱“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对人的精神统治,人与人之间动物式的生存斗争也偃旗息鼓。
马克思的“生态人”思想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的“无止境的侵占”进行无情的揭批,“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在犹太人的宗教中,自然界虽然存在,但只是存在于想象中”[9]。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陷入了一种“无止境”的幻觉,人们误以为自己的“生存”就等同于对自然进行“无止境的侵占”,我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奴役、改造自然”,结果却使自然界遭到越来越多的破坏,“征服自然界的欲望”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敌视自然界。这种征服自然界的欲望不仅使自然环境日趋恶化,人类越来越无法在日益减少的自然对象中确证自己的本质及存在,沦为“生态贫民”。因此,资本主义盲目逐利的生产方式与实践的生态向度缺失,便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所在。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终结土地、劳动力等自然要素被作为商品的悲惨命运,才能彻底终结资本主义私有制分配对自然的破坏和伤害。
从实践意义上来看,目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已然成为当下人类亟待解决的最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生态危机外在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其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利益分配的矛盾在自然界的具体映射和逻辑延伸。马克思“生态人”思想认为生态危机绝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因为在资本统摄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被异化为资本与自然的关系,资本僭妄于人类之上,抹杀了人纯真的善的本质,窒息了具体的人的独立人格,在资本宰制下产生的机械论自然观、还原论自然观迫使从事社会劳动的主体人只见个体的自然、遗忘了整体的自然。资本主义社会不仅造成了资本家和劳动工人之间的对立,更造成了人与生态环境的对立。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也严重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破坏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0]。资本生产出的大量物质财富已为共产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可能,共产主义的桅杆已然出现在未来的海平面之上。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在公有制条件下,个人对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将实现真正的驾驭,自然资源将会处于人们共同的自觉的控制之下,并“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符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当下中国正处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攻坚阶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人类站在生命共同体的维度,重新辨析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真切转换工业时代毫无节制地消耗大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努力保护“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景物生生不息的自然诗意。马克思“生态人”思想完美契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旨向,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视为泽被当代人民与子孙后代的践履过程,全然阐扬人民群众筑就生命共同体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之在生态之境的保护和改善中走向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征程。马克思“生态人”根据历史经纬对人与自然二元分离思维图式进行系统反思,以信奉人与自然共存共荣为鹄的,在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揭批中寻求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向奔赴,从而实现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