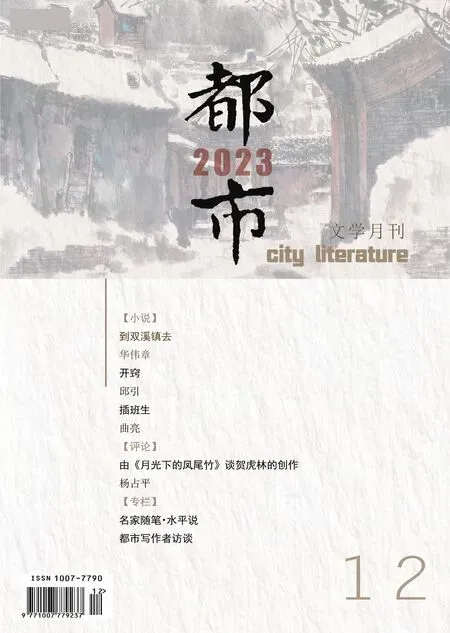张世勤:深究下去,方有意味
2024-01-02
张世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时代文学》主编。作品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等文学期刊,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多次选载并入选多种年度选本。著有长篇小说《爱若微火》、中短篇小说集《牛背山情话》《人体课》、散文集《落叶飞花》《龙年笔记》、诗集《情到深处》《旧时光》等多部。曾获泰山文学奖、刘勰散文奖、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济南城头,儒风浩荡
主持人:张老师好!泉城济南“一城山色,半城湖水”,美不胜收,您是“老济南”,济南是您写作、工作、生活的背景,您心中的济南是什么样的?
张世勤:昌鹏多次到过济南,济南视觉方面的美已被昌鹏捕获。济南有历史、有文化,这些更是我写作、工作、生活的济南背景,多年来我浸润其间。如果剥去城市面孔,济南的独到之处很容易便能显现出来。千佛山齐烟九点,暮鼓晨钟;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垂柳;趵突、黑虎、五龙、珍珠四大泉群,甘水淋漓,空明澄澈。不过对一座有着厚重历史的城市来说,凡此种种仍不过是一个个符号,还不能达其内里。一切须深究下去,方有意味。比如,虞舜帝早年躬耕历山,才有舜耕山之说。至隋佛教兴起,则呈千佛景象。今天的我们虽然已闻不见隋唐繁盛的香火,看不到宋时的富饶兴盛,想象不出金时的盐运集散,描绘不出元时的园林湖泉,听不到清时的曲声艺鸣,但穿越历史的烟云,我们是否可以感知济南城曾有的辉煌过往?比如,清冽的泉水它虽然没能把城市洗得晶莹剔透,但却洗亮了“二安”的诗词妙语。李清照的词,比泉水更清冽柔软,比柳丝更幽怨多思。辛弃疾的词,有着山风一样的粗犷豪放,有着黄河一样的恢宏气势。正所谓“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正是这些,让一座城市有了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高度。
主持人:济南文化厚重,街道命名却“不科学”,东西经,南北纬,与地球仪上的经纬线恰好相反,但以经纬命名确实挺有新意。
张世勤:关于济南的街道为何这样命名,说法众多。坊间所谓的韩复榘命名说,更像是敷衍出的一场娱乐,应不足取。与纺织有关说,则颇多契合。这又得回到济南的历史,清末时济南的纺织业已经非常发达,而在织布机上,通常长线为经,短线为纬。济南在黄河与千佛山之间,夹道而行,东西长、南北短,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其所称经纬与地球仪相反。但我更愿意把这种命名看作是与济南人文化性格上的一种暗合。齐鲁大地是孔孟之乡,儒家文化长久地浸润着这片土地,这使得每一个子民头脑中“仁义礼智信”的概念根深蒂固,处事交往崇仁尚义,重客好礼,推智言信,忠之诚之。其行为准则,一如经与纬一样,自己为自己划就明确的坐标,遵循有加,不越雷池。它的好,就是宽容厚道、仁爱忠义、好客诚信,带来的不好就是固守颇多,创新上束缚了手脚。这些征象,不仅表现在济南人身上,推而广之,整个山东人亦大致如此。
主持人:历史和文化是以什么方式投注在济南人身上的呢?
张世勤:济南的历史和文化是活的。比如,济南人习惯的称谓就很值得研究,那就是“老师”。在济南大街上,随处可听到“老师”之声,陌生人之间的交集大抵以“老师”起首,后面问路也好,咨事也罢,就基本有了保障。这是否也是两千多年儒风浩荡的结果呢?济南人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方言就是“愣赛咧”(好厉害或很优秀)。说起来,济南的确“愣赛”!济南人厚道、和气,中庸,很少有暴脾气的人。路上没有飙车的,很少加塞的,关键是车速都不快。我想,这是因为这里儒家文化深厚,大家规规矩矩,恪守本分。
主持人:张老师,您和济南的缘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世勤:我与济南的缘分,要从我到山东师范大学求学算起。我记得一入校,一院子十八九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却都以老张、老王、老李等相称,我一时不大适应。久了,不仅习惯了,而且也体会出了其中不少的味道。我想,这可能与济南人出门之后开口就叫“老师”一样,或许两者异曲而同工。我有一个同学,离开济南后“老刘”立马变成了“小刘”,到现在还没混回到“老刘”。我调侃他,还是回济南吧。老刘说,看来还是济南好,它能把每一个人的起点都给你抬得那么高。
我与济南相识已经四十年了。时间太窄,指缝太宽,四十年的光阴,流水一样浑然不觉,统统从指缝中漏完。四十年前,我像那列载着我的火车一样,昂首长鸣,无知者无畏,牛哄哄地一头拱进了济南,而多年之后,我背上简单的行囊,重返济南,与这座城市一起,寻找我曾经的过往。济南,不管是我爱她还是恨她,她都已经成为一座与我生命有缘的城市。“一城山色,半城湖水”,曾让我的青春豁然开朗。如今我再次登临千佛山顶,观望这座热气腾腾的城市,一条条街道泾渭分明,也经纬分明。我看到明湖似镜,黄河如带,青山绿水美,齐鲁青未了。
自行创造一套逻辑
主持人:张老师,您是《时代文学》主编,作为主编您怎么看待作家的写作?最近您比较关注哪些年轻作家的创作?
张世勤:文学写作和文学创作,可以看作是一件事,也可以看作是两件事。我以为,文学重在一个“创”字。东方卫视的《欢乐喜剧人》节目,有一期开心麻花团队推出了一个《善恶终有报》的小品,说的是武大发现家里种植的红杏出墙了,老往西门方向长。天上电闪雷鸣。第一次遭雷劈时,武大与潘金莲灵魂互换,然后说了一番台词;第二次遭雷劈时,武大与西门灵魂互换,然后又说了一番台词;第三次遭雷劈时,武大与武二灵魂互换,然后说了一番台词;第四次遭雷劈时,西门庆与老虎灵魂互换,然后说了一番台词。我不知道开心麻花团队读没读过卡夫卡,但他们这小品却很得其道。有的视频号让一些帝王画像开口高唱:江山笑,烟雨遥,红尘世俗知多少?我把它也归入这一类。法国作品《反常》,写同一架飞机,同一个航班,却一次是三月正常降落,一次是六月申请紧急降落。这样,每一个人都成了两个人。结尾页呈沙漏形,一行比一行短,最后三行是:end。福建作家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也进行了这类有益的实践。内蒙古青年作家渡澜以及东北作家班宇、双雪涛、郑执,他们的作品也都呈现出了不俗的创造力。
主持人:您心中的好作家是什么样的?
张世勤:王安忆有很多谈艺术的文章,这些文章经常围绕“常识”和“逻辑”展开,当然这话也不只她在讲。在知识和学科不断向深处开掘的年代,专门把常识拎出来进行反向提示,极具重要性。逻辑是一个通用词,生活有生活的逻辑,艺术有艺术的逻辑。它们可以交叉叠加,也可以“磁悬浮”。也就是说它们可以是相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对常识,大家都不会有疑义,但逻辑,无论是艺术逻辑还是文学逻辑,特别是小说逻辑,并不止一种。但凡好的作家都会自行创造一套逻辑。
主持人:王安忆、谢有顺、毕飞宇在谈论小说时都比较在乎“常识”和“逻辑”。您启发了我,我想了想,同意您“自行创造一套逻辑”的说法。逻辑的建立依靠的是因果关系,“创造”是在两件事之间建立特定因果关系,通过这种特定因果关系征服读者,同时也在这种特定因果关系中呈现世道人心。王安忆曾提出在小说中如何处置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我觉得这确实是小说写作的一大难题。您提到王安忆,我马上想到了这个问题。您思考过在小说中如何处置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吗?
张世勤:我思考过。1999 年,在我再次深度阅读《红楼梦》时,写下了一组红楼随笔,其中一篇是《与曹雪芹梦谈〈红楼梦〉》。有感于红楼研究的纷扰和对一些死结的争论,于是我干脆选择直接与曹雪芹对话。这种“对话”给我带来了益处,它引发了我对“时空”的思考,“时间”到底可以不可以折叠?“空间”到底可以不可以置换?由此延展,我还思考过,文体之间到底有没有边界?李修文可以用小说笔法写《山河袈裟》,莫言可以把断行的《饺子歌》当作小说发表;《人类简史》《北纬40 度》一类书籍到底算历史著作还是算文学著作?《时间简史》到底算文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写人记事的笔记体,到底算散文还是算小说?
主持人:萧红曾自称自己的小说是文章。陈平原有一个观点,大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在根子上只有两种:一种是诗歌,一种是文章。诗歌一直也有叙事、抒情、言志、哲思、探美等多种类型。叙事也是诗歌的正宗传统,《诗经》《楚辞》里面就有叙事诗,诗歌的叙事传统几千年来未曾断绝,延绵至今。杜甫的“三吏三别”是诗歌,也完全可以当作小说看。当代作家确实是“守正创新”,“守正”和“创新”这两点做得都算出色,这也是“胸怀”和“远见”的体现。
张世勤:儒风浩荡,齐鲁人“守正”,“创新”要能做得更好,那将更加蔚为大观。莫言肯定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莫言创造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上的地理坐标,这也体现出了他的“胸怀”和“远见”。随后,他把天南地北的故事,全部往高密东北乡里去装,这是他在实施“调虎离山之计”和“菜篮子工程”。在空间和时间的处置上,还有一个作家刘亮程,我也比较关注。刘亮程以新疆比内地晚两小时天黑的自然现象,开启了他的时间意识,写出了长篇《本巴》。我以为,作家本来就应该是时间魔术师,可以让时间快速前进,也可以让时间停止不动。
求变悟道,苦练内功
主持人:通过作品,我认识的作家张世勤也是一位“守正创新”的写作者。您写过许多城市题材的小说,比如刊于《收获》2016 年第2 期头题的中篇小说《英雪》以及曾被《小说月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选载过的中短篇作品《聂小倩》《靠山夜话》等,我想请您谈谈您的这些作品。
张世勤:《英雪》我在结构和题目上下了些功夫;《聂小倩》我在名著名篇借用上下了些功夫;《靠山夜话》我在人事物景全部变形上下了些功夫。此外,《远山》我在语言上下了些功夫;《婪岸》我在故事上下了些功夫;《穿越那片密林》通篇使用的是第二人称;《你们那儿有河吗》通篇是几乎重复的对话……这也就是说,我一直试求改变。在变中求生,也在变中得乐趣,并从中悟道。
主持人:孔子曰“君子不器”,张老师的小说也“不器”,不固化。
张世勤:我一直主张或试图打通边界。古与今,虚与实,长与短,上与下。界与无界,时与无时,动与不动,变与不变,静与不静,飞与不飞,一齐来。我的《大青山一夜》,有论者认为是用奇特的手法把红色题材的写法推向了一个新境界;在《我的时间书房》里,我把苏洵一家和班固一家六人,包括历史上并不一定真有其人的苏小妹,一并请到了我的书房;我的另一篇小说《和古人一起看桃花》,读者看题目就知道,时空完全纠合到一起。时间本来就是一个虚无的概念,有没有是一个哲学问题,即便有,其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哲学时间、小说时间等也都不一样。所以,不能被时空框住,不能被前人的写法框住。我一向崇尚文学创作应打破边界,转换有无,超越新旧,放大美丑,生发理趣。
主持人:请问求变悟道拒绝固化的张老师,小说创作中有没有不能变的要素呢?
张世勤:只有人格独立,才有精神的空间。有了精神的空间,才有独与天地相往来的自由文本和文字。作品站不起来,是因为作家站不起来。作家站不起来,是因为作家还未能把自身和外界真正打通。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不能变的要素是创作者需要人格独立。
主持人:创作者是创作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具有主观能动性。对创作者自身提出要求,就是对作家的“内功”提出要求。除了人格独立,张老师觉得创作者还要朝哪些方向“练功”?
张世勤:我很在意爆发力。刘邦的《大风歌》,曹操的《短歌行》,岳飞的《满江红》,苏轼的《赤壁怀古》,李白的《将进酒》……我喜欢这种作品给予我的冲击。一个创作者,首先要保证做到,让自己的心灵能够自由舞蹈,然后就是拿起笔来,翅膀卷着风暴,心生呼啸。没有基本的爆发力,就不要奢谈气度。要获得“爆发力”,作家还是得练内功。
主持人:爆发力确实源自作家自身,价值首先还是得向内求,文学价值也得作者向内求。您觉得一件作品,怎么样才算有文学价值?
张世勤:我觉得文学价值有三层。最高一层,首推美学价值,先不考察它实用价值几何,思想意义几许,先看它“美不美”;其次,要看作品对母语的深厚承继和颠覆创新,查验语言是否产生引领性,是否具备黏合度,是否富有穿透力;最后,才是看作品对人心的挖掘和揭示,对社会的启蒙和引领,对未来的信仰和预言。
“美”是第一原则,适用于一切艺术,比如书法之美、绘画之美、音乐之美、舞蹈之美、戏曲之美等等。文学是“人”学,但也是“美”学。文学要的就是对“美”的发现和对“美”的表达,形式、情感、语言、对话、韵味、意境、理蕴、节奏等等这一切,都必须是美的。一个建立不起“美的坐标”的人,是无法从事文学写作的。所谓的创作作品,其实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美学。
主持人:建立美学坐标,创造新的美学,这些依旧是对作家内功的要求。您觉得作家能通过苦练内功,成为好作家吗?
张世勤:好的作家有“四性”。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先后追踪了贾平凹、阿来、刘震云、毕飞宇、莫言、迟子建这六位优秀作家,通过寻找这五个“地瓜蛋”和一片“雪花”与文学相遇的原点,梳理他们所激发出的能量,这从中至少给了我们四点启示:好作家具有先天性,这并非唯心,而是文学作为一项极具灵性事业的必然要求;好作家都具有野生性,他要有旺盛成长的能力;好作家都有独立性,能保持沉默,在孤独中独自思考;好作家都能保持纯粹性,坚守自己对文学的看法。苦练内功对作家而言是必要的,但不一定能练出好作家。
心里没建立这些框
主持人:您对文学有深入的思考,您又写过许多城市题材的作品,您怎么看待“城市文学”?
张世勤:“乡土文学”这个概念用得久、用得多,在概念上文学界似已有共识。“城市文学”这个概念怎么界定?我至今还未接触到权威说法。对我来说,我心里没建立这些框框,我熟悉什么就写什么,一会儿写城里,一会儿写乡村,但写的都是我熟悉的生活。我的小说《拾月光的小女孩》,写了一个城里的孩子和一个乡下的孩子,我写她们之间的交往。这篇小说算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它算是儿童文学还是成人文学?这样的问题,我是回答不上来的。我在一篇作品里写城里的农民工,那这篇作品算“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城市文学”属于未来,城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城市文学”作品在未来可能会比比皆是。
主持人: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大部分作家出生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写城市题材的作品会变得相对容易?
张世勤:这倒未必。城市最大的问题是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集中,一个人要把握城市是困难的,身处城市的人并不敢说自己了解城市。此外,城市变化快,让人眼花缭乱,新经济形态、新就业人群,不断产生的套路等等。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作家能全程跟得上城市的全方位变化,作家消化不了自己要写的对象,要写出好东西那就太难了。
主持人:的确如此,正如“不识庐山真面目”一般,身在城市,或许更难看清城市。只能看到局部的城市,而难以参破局部背后,庞大的城市机器的运行规律。最后,感谢张老师为我们提供如此丰富的极具思辨性的视角,相信也会带给更多读者、写作者以深层次的思考感悟。感谢您接受此次访谈!
张世勤:也谢谢昌鹏,这样的聊天令人感到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