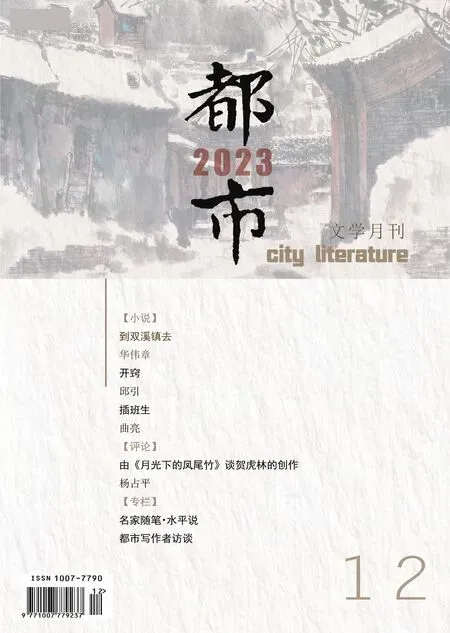时间煮雨,岁月缝花
2024-01-02葛水平
文 葛水平
有一句名言说:忘记昨天就意味着背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忘记昨天,才能心安理得地活在今天。
1
一座寺庙,其实就是一段时光、一些人事和永远承载的历史物证。
准备去晋城泽州府城玉皇庙时,再次翻阅一本名为《唐风宋雨》的书,这是一本知识和感官动人相融的书。那些华彩影像铺就的道路给了我进入玉皇庙另一个理由和入口。书的作者赵学梅对我来说是充满了才华、热情和能量的集合体,也是我此刻近在咫尺可靠的存在。生活对我们彼此都做了极大的修改,只是我们始终还留在历史的纠缠点上。说到她对晋城地方文化的贡献,在我时不时翻阅她的微信朋友圈时总会看到令我安慰的踪迹。
人与人之间也许并不需要时时往来,需要的只是彼此之间长久的默契和支撑。
此刻,站立在深秋的风中,我的心是郁悒的,历史从纵深处一闪而过,容颜漫漶而又清晰。现代化的高楼以物质的形式早已遍布城市的角角落落,四纵八横的道路,人走过,鸟雀很少飞起。旧是千万百姓的智慧、希望、辛苦和泪水,旧的消失,不知道还会让多少今人面对日新月异时蒙上一层愧疚的颜色?
梁思成曾经讲过:所有的建筑都是人造出来的,可它们一旦屹立在大地上,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夫人林徽因则说:世界上所有能载入史册的建筑都是权力和意志的体现,最能体现意志的除了皇权就是神权,所以,这样的建筑不是宫殿就是庙宇。
站在城市的边缘,已是黄昏,华灯初上。这是一座庞杂而陌生的城市,雨开始下大了,能感觉到整座城市血流趋缓。赵学梅算不算守寺人?
端量这个雨夜,审视与揣测我接下来要做的采访任务。雨夜打搅?不由自主地望而却步、犹豫不定。陌生有时又具有更致命的诱惑力和先入为主感。不想过多考虑,打过去电话,自报家门后,她欣然接受。
我对城市充满了抵触和否定,雨是对一个朋友妄断和偏见的最好消解。一路上,尽量快速提升对晋城泽州府城玉皇庙二十八星宿浅俗的认知。
大概是2009 年的夏天,空气要干燥清爽透明些,周边的庄稼地有几分丰收的迹象,天空渗蓝浸紫,地上的牛粪有一坨没一坨地散乱在泥路上,那时的府城玉皇庙四周全是庄稼地。我对古建筑怀有一种朴素的认知,不轻信什么,尤其不敢主观,更反感单一地绝对地极端地说好。我用世俗的眼光走近,满庙脊烧制的孔雀蓝琉璃,那上面是二十八星宿,呈现人类社会的真实情形,人的理想愿望。
我很清晰地记得离开府城玉皇庙后,我查阅了《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6.元明清雕塑》,其中概述部分有这样一段话:“元代道教造像中最为生动的是晋城玉皇庙二十八宿泥塑像,它是全国元代泥塑之冠。”
也就是说坐落在泽州县金村镇府城村北卧龙山岗上的晋城玉皇庙——当地人习惯称其为“府城玉皇庙”——是晋城境内现存创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寺庙。庙内,人和动物相结合产生的二十八星宿彩塑为“海内孤品”,专家说它是元代的。
宋和元是相邻最近的两个朝代,从考古的角度讲,对一件文物艺术品鉴定断代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事情,要综合多方面的依据。断代在文物鉴定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一旦确定了文物的年代,就可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研究。如果对文物艺术品的时代判定错了,其研究结论也必然是错误的。
关于上述问题,《唐风宋雨》中有赵学梅的解读:晋城泽州府城玉皇庙二十八星宿是宋塑。
没有一个守寺人像她一样,会为一座寺庙的塑像年代据理力争,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发现蛛丝马迹,就像寻找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胎记,因此,我迫切想在接下来对她的采访中触及时间流走般的遗失。
2
一本书上有这样一则寓言,一只蜈蚣因为被一只好奇的蚂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而陷入困境。蚂蚱见蜈蚣长着数不清的腿就煞有介事地问:“当你左边第一条腿移动时,右边第一条腿在干什么?左边第二条腿在干什么?左边第三条腿在干什么……”蜈蚣被这个庞大复杂的问题难住了,它停下脚步仔细想了想,突然就僵在原地走不动了。
人类世界的“腿”不仅远远多过蜈蚣,而且步伐更加纷乱,难理头绪。
为了活着,会有人劝告说:切不要过于为难自己而忘记了简单生活的本真。进入赵学梅住的院子,雨被隔在了门外。生命中支撑人灵魂的激情是一个人生存的理由,从院子和屋内的布置能看出女主人是常年埋在书堆的人。满壁书橱,我们坐在她读书的桌子前,暖色的灯光下,在屋外雨脚的节奏中神驰八荒,开聊眼里的往昔岁月。
赵学梅说:“对二十八星宿塑像,对它的关注理解,没有觉悟,只有一种怜悯,这是不是宗教?我认为不是。我只是把彩塑当作人。春夏秋冬,我都去看。它孤独在庙宇里。很多东西都活在短命的年代,它们留存下来,是历史久远的记忆符号。我的审美来自一切事物的外表,我喜欢美丽外表下蕴含的与众不同的心。原谅我将它们拟人化了,我去庙宇里看它们,就像去看给我精神引领的先圣先师。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每一次。”
重复肯定。哲人说,今天所看到的一朵花就是最后的美丽,今生已不能和眼前的这一朵花再次相逢。掀动衣襟的风,不会再有此时的温柔,因为,明天吹起衣襟的是明天的风,那么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重复,重复只是形式,而生活的实质是,生命里的每一天,以前没有,今后不会再有。不可重复中,每一次谋面都值得回味和留恋。春夏秋冬,三十多年的探望?历史并不常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让一切发生改变,唯有知道民族财富之人,才能体悟被磨损的庸常生活需要一种精神欢愉来修正。
赵学梅翻阅桌子上的摄影作品《唐风宋雨》:“这本《唐风宋雨》是2001 年出版,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大部分争论还是在于彩塑产生于什么时代。有人说是元代彩塑大家刘元的,有人说是刘銮的。有一本书叫《刘元研究》,他批评了《唐风宋雨》书中的观点。可以批评但我不接受。”
明亮的灯光下,赵学梅不刻意回避,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她的笑容感染了我。
元代雕塑奇人刘元的塑像是什么风格?我们今天的人没有见过。《元史·卷十九》《元代雕塑奇人——刘元》中讲述刘元是阿尼哥的弟子。在元大都和上都等地寺庙中,许多铜铸和泥塑的佛像都出自阿尼哥之手。阿尼哥塑造的是一种梵式佛像,也称藏式佛像,与中原的汉唐式佛像有明显的不同。他是中国藏式佛像的创始人,自元代起藏式佛像就逐渐取代了汉唐式佛像。刘元是阿尼哥的徒弟,他从师傅阿尼哥处学得了西天梵相,得其神妙,遂为绝艺,成为元代仅次其师的著名的塑像工艺家。清代乾隆时期《日下旧闻考》中有载:“刘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监卿。传其艺非一,而独长于塑,天下无与比。”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刘元是元代的著名塑像家,其作品甚多,但是,刘元的作品在清乾隆时期消失得无影无踪。时间可以把什么都改变,似乎这样才足够承载悲喜。
难道刘元曾经得了政治上的肿瘤?
天下精巧建筑,一定要托名于鲁班;天下神奇绘画,一定要署名“吴道子”。鉴于这样一种状况,就连梁思成先生对于刘元故里之宝坻区的精美塑像,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认定其就是刘元作品,刘元塑像彻底湮灭了。
晋城府城玉皇庙内的二十八尊星宿神像,被当今相当数量的人誉为刘元传世作品。关于此种说法,让我们来看看玉皇庙内说明牌的介绍:“刘元的造像风格:腰部细长,希腊鼻子,面部表情丰富而深刻,将密教雕法与中国风格相结合。本庙修时曾召请外地工匠,刘元有可能应召而来。二十八宿与刘元的造像风格非常相似,故大胆探讨,作此假设。”
赵学梅对府城玉皇庙的研究,则是根据现存于庙中的碑刻,用传统的逻辑反证法,将二十八宿的成塑年代确定为宋熙宁年间,进而推及塑像为泽州当地工匠作品。
生命既不可选择也不可期待,我们可选择的仅仅是如何对待这似乎可以无限延伸、不断重复的情境。丢失一定是缘于不再被珍视,懂得欣赏的人也一定是单个的灵魂。
赵学梅接着叙述:
“过于美的东西,人们会喜欢探究,会暗生莫名其妙的疼痛。我最早从阳城县调回晋城市是2001 年,在市里的职务是分管文化的副市长。晋城几乎每一处古寺庙中,都会有相关艺术形象的塑绘作品,以加深巩固其对民间社会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这些塑绘,无疑都是十分生动的美学、理学、哲学,或者宗教的实体教材,一代又一代人通过向其观瞻、膜拜,聆听长者讲述、劝谕,渐渐理解何为公平正义,何为因果相循,何为天理昭彰,从而树立起最原初、最基础、最朴素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但在如今,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古文化场所已荡然无存,它们的鲜活影像,便只存在于、盘旋于曾与之密切接触过的人们脑中。或许我们还有能力将它们重修再塑,但具备能力不代表能够还原意义,甚至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如果能力运用得不够审慎,或许还可能对既有意义造成割裂和剥离。我在市政府工作时,曾动员将府城玉皇庙二十八宿像用玻璃加罩,以利存护,回顾这一举措,未必不生叹惑——神祇配享香火,慰藉凡尘,这是一个闪动着神圣和虔敬色彩的俯仰循环,但被冰冷坚硬的玻璃这么一隔,这层色彩便似乎衰减了许多,这些神祇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也似乎黯淡了不少,很难说是否令它们的形而上价值受到了无形的损伤——尽管客观上它们确实因这一举措而改善了处境。”
满满的是回首时眼里的岁月和对时间惋叹的刻骨之痛。
“在《唐风宋雨》中,我之所以将玉皇庙的二十八宿塑像的成像年代前推了二百年左右,由元代世祖至元年间,上溯到了宋代的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做出了其缔造者并非元代宫廷雕塑家刘元的结论。整个考证过程,大致经历了发现、寻找、怀疑、定论四个阶段。20 世纪90 年代,晋城首任市长薛荣哲先生与考古科班出身的郭一峰先生在《泽州古代文化荟萃》一书中提到:‘据有关专家推断,玉皇庙的二十八宿彩塑和十二辰彩塑,均成塑于元代,并且可能出自同一匠师之手,有人认为是元代著名雕塑家刘元的作品,但迄今仍未找到真凭实据。’我注意到了这一记录中的严谨审慎之处,并由此产生了为二十八宿追本溯源的意愿;嗣后观览时,在二十八宿殿北门外的一通《二十八宿重妆记》碑文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旧有二十八宿行殿,创自宋熙宁间……’明确点出二十八宿的成像年代是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在此,我发现了同以往主流定论不同的信息逗漏。
“时日推移至2010 年3 月,《太行日报》有一篇文章披露指出,刘元塑像说最初倡言者是已故晋城籍学者原石民先生(1900—1966)。我辗转寻访到了提供这一信息的李家琪先生,向他求证,李先生表示,他是听原晋城县文化局李和平先生提及此节,并不见于文字记录。然而,口耳相传是不足立信的,我将考证重点重新转向了玉皇庙内的碑刻记载,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包括需要甄别汰滤数量庞大的无意义信息,需要对相关的地域、人物、事迹反复查证推敲,还需要训诂分解形形色色不见于今的繁文冗字。翻阅二十四史,《宋史》中,对泽州的记载还有数笔,特别是对北宋泽州天文学家刘羲叟有三百字的记载,刘羲叟的村子与府城距离很近,这对府城玉皇庙的建筑布局是有很大影响力的。这位伟大的古人给我提供了证据,指明了研究的路径。
“三十多通碑刻记载逐一考证下来,可知玉皇庙共经历过四次重要修缮,前两次以及最后一次同公认的刘元生卒时段不存在重合,基本可以排除他参与的可能。刘元唯一有机会参与的,只能是碑刻记载中至元二年(1265)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的这次修缮,根据史料记载,至元二年,刘元还只有十四岁,到了至元八年(1270),元世祖忽必烈昭告天下,广征能工巧匠入京修建仁王寺,年方弱冠的刘元便于此时赶赴大都,跟随来自尼泊尔的大雕塑家阿尼哥学艺,此后直至艺成出师,长年活跃奔波于大都、上都两地之间,时间纵然吻合,从空间上来说也无法分身来到晋城为二十八宿塑像。此外,至元三十一年玉皇庙修缮完毕之后,曾立有两通碑刻,详细记载了修缮过程及为之捐资添力的八十多位功德主姓名,其中上自将帅翰林、下至黎民百姓,各色人等俱全,对刘元之名却只字未提。
“这在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监卿的他来说,是绝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只能由此怀疑,乃至进一步推断:刘元的确未曾参与玉皇庙的修缮工程。即便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而特意忽略了刘元这位雕塑大家的功德,在朝代更迭之后,此事也不应被彻底埋没,然而我们考察元之后的四通明碑、二十四通清碑,同样也没有任何提及刘元的文字记载。”
结果不一定是解码,因为只是赵学梅自己的一厢情愿。翻阅时光,一些情境再次滋生了幻觉,女性本能的较真有些时候是天真烂漫的,曾经的现实已经消亡,论及重新被发现的可能——有限的生命怎么能盖棺论定那些永远活在历史上的事呢?
我笑着说:“在与时间漫长的较量中,天地无言,让人不能知晓和穷尽它的全部,真实其实从来就不曾有过改变。退而眺望,我们的起点也许就是终点。”
赵学梅停顿了一下,朝着书柜的方向望了望,似乎在寻找一本书,又似乎是歇下来回想她做过的某一件事,没有更多的表情,我想着她的容颜,从童稚变为沧桑。
突然她打破沉默说了一句话:“人生总得有一件事一往情深。”
黑暗洇染了许多往事的边缘,一些事物有了关联和共性,一往情深是多么美好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又是一句多么疏离而感伤的话,在雨夜变得清晰、浓郁,缠绵不息。
3
2006 年赵学梅由分管文化转为分管农业。一个月后,二十八星宿失盗,最生动的角木蛟的头被盗窃犯拿走了。
它的丢失也许和时间没有关系。
但是它的丢失让赵学梅十分心痛,因为它丢失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犯罪行为似乎都将人拉回野蛮的时代,每一时刻的邪恶欲念、冲动发怒,似乎都在与那条界限搏斗着。一个技术发达、文明秩序不断完善的社会,更需要人们完善心灵。文明不仅仅包括地面上的理性之物,还包括非理性的、野蛮的一面。野蛮一直都在。
飞光无痕,神祇无言。
庆幸有照片为证。发生的一切让赵学梅试图用抢救式的拍摄方式来留住它们,让美好变得更清晰、更清醒。当光影锁住并拓下时间一瞬的步履,我们真要感谢影像胜任了人类视觉对客观事物最稳定、最真实的记录,让现实充满了不尽的神奇与梦想。
一个用光描绘的伟大发明,使人类能够定格一个时光的瞬间。
拍摄二十八星宿,不仅仅是一个承诺,更多的是想从细部发现宋代印记。反复拍照,从多个角度理解它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些千年的记忆续接起来,把古人送来的香火延续下去。她无法述说内心怀着怎样的敬畏,世间精彩都需要亮相,独知独享的绚烂,终究只是昏暗和消失的意味,美需要感染人间。
每一次拍摄结束,站在玉皇庙外望着高天流云,她在想,宗教曾经温柔软润过人间,除去迷信,我们是否珍爱过这些塑像眼波流转的神情?
一切都像从前,一切都在改变,怀恋和感喟的情感寄托皆有因果。
赵学梅的孩提时代,是在一个只有六百多人口的小村庄中度过的,但就是这么一个小村庄,却拥有七处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场所。有应许受祷、行云布雨的道教龙王庙;有诫导人们成仁守义的关帝庙;有教化人们好善嫉恶的白衣堂;有演绎虚灵、托寓常世的佛教小西堂;有逸立傲雪、异质奇葩的梅树堂。几乎每一处古文化场所中,都会有相关艺术形象的塑绘作品。正如她所说,这些塑绘,无疑都是十分生动的美学、理学、哲学、宗教文化的实体教材,一代又一代人通过向其观瞻、膜拜,聆听长者讲述、劝谕,渐渐理解何为公平正义,何为因果相循,何为天理昭彰,从而树立起最原初、最基础、最朴素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与每一个出生在那个时代的人所经历的没有什么两样,那些缠绵悱恻、血脉偾张和涕泪滂沱的往昔留在被掩埋的尘埃里,一切永远不会再有。是什么让如此庞大的时间单位和情感因素被过度挥霍?当思维搁浅在她对不经意发现的乡村的一块匾额“一犁万卷”四个字的想象中时,“一犁万卷”的意境竟然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她涌来。
“我是看见过它悬挂在农家的门额上,后来它不见了。深情让人饥饿。想象总是辽阔的、美好的,北宋诗人杨公远善词工画,终身未仕,一生有记录的五百二十九篇诗文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其中《次程国舍》中的‘欲会春风欠宿缘,识荆琳宇忆当年。初逢脱略知心地,再见从容值暑天。万卷诗书君有种,一犁烟雨我无田。晓来喜报檐前鹊,忽得珠玑璨两篇。’这五十多字的七律中最让我喜欢的是‘万卷诗书君有种,一犁烟雨我无田’。但与故乡的‘一犁万卷’比却少了点广阔意境。”
对往事倾情,遗憾使语言贫血,能感觉到赵学梅一瞬间眼里噙满莫名难辨的泪水。时光年复一年这样消逝、这样呈现,我们丢失得太多了。她开始珍惜往昔,珍惜旧事、旧影、旧文化。童年时村庄的文化场所均已荡然无存,它们的鲜活影像,便只存在于、盘旋于曾与之密切接触过的人们的脑海中。
在中国的农耕时代,人们总是对未知的生活充满了期盼,由此形成了庙宇的两个主题——辟邪与祈福。如泥土让种子发芽抽穗,长成葱郁的植物,寺庙把民间的喜爱和感恩之念养得蓬勃芳香。然而,许多寺庙不知不觉中少了香火,那些缠绵悱恻、血脉偾张和涕泪滂沱的往昔消失成永远。
正如《唐风宋雨》书中的最后一句话:“它们需要关怀。”关怀它们就是关怀我们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无论如何,那一簇曾经灿烂的文明之火不应当在我们手中熄灭。
如冯骥才所说:我们无法阻止一个时代的变化,但是,文化,我们必须挽留。因为,文化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精神功能,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文明与全民素质。
4
赵学梅同我再一次前往府城玉皇庙,是在一个大好的晴天。太阳普照,光芒的颗粒均匀地分布天下。站在庙门前,对应历史与现实的思绪、场景、物件、形态,创造不过是复杂的生命本身与复杂的人类社会存在时相互作用、日日潜在积累的一个“神示”出口。
美是那些人世间永不回来的好岁月。
打开殿门,赵学梅说:“它们像是一幅长轴,塑造有七尊北宋年间骁勇闻名、消灭割据的英雄人物;九尊处江湖之远忧君、居庙堂之高忧民的北宋文士;九尊不妖不媚、不骄不卑的女士。中国的彩塑以侍女见长,二十八星宿有皇母君临天下的感觉。北宋的皇帝大都死得比较早,由皇母尽心竭力扶持小皇帝,没有内亲外戚干政。九尊女士彩塑颠覆了中国彩塑侍女卑微的形象,特别显示出一种气势。彩塑中的三尊老者,简朴恬淡,有乡村老农般的生动趣味,是社会生活再现。一尊像不是故事,一个群体才是故事。我没有从宗教方面研究,是从社会方面表达对北宋的理解。北宋的文人经历几多褒贬,或上或下,但他们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有一种‘忧士’精神,有一种承担天下的精神气质,他们对国家的关爱不变。”
一个激情四溢的解说者,她的声音吸引人恍若归家一般往前走,一部北宋的历史在叩问中慢慢展开。在赵学梅掌握的知识与思想世界中,有了她自己的经典和注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不仅仅是宋儒远大理想的象征性话语,而且恰恰也是宋代理学重建思想秩序的全面表述。就宋雕而言,一般宋代作品尤其是北宋时代的作品,往往缺乏先秦的狞厉、两汉的浑穆、魏晋六朝的激越悲慨以及隋唐之世的雄伟英气,而是以柔美细腻的风格见长,但它的雅致、它的技巧的圆熟以及它的造型样式的独特风格,更能体现道家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由意识,佛禅的“明心见性”“即心是佛”的思想,重视内心静虑,重视精神境界的开拓。
被感染,被说服,居然也遵从了我自己内心的理解:它们就是宋雕!
历史上元朝统治者看不惯汉民族的文化,他们对汉民族的哲学、宗教、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服饰打扮、风俗习惯等等相当隔膜,取之弃之都疑虑重重,因此,盲目排斥似乎是唯一可供选择的文化态度。宋雕有世俗化、平民化倾向,不再崇尚高大雄伟。实际上自宋开始,关于“神”的观念与信仰的淡化,乃至神和人等高。这并非表明中国人对神之崇拜三心二意,实在是由于中国人在面对神与人、此岸与彼岸时生发出一种随意、达观的人生处事态度。假如看过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与善化寺大雄宝殿里的塑像,会发现它们完全不是宋式建筑雕像那般秀逸、轻灵的模样。这是因为,辽金元虽重“汉法”,而因当时朝代更迭对峙,仍难以接受宋雕文化之影响。从唐末至五代,中国北方陷入割据局面,有宋一朝又陷入辽、宋战争,分裂和战争也是少数民族拒绝宋式文化之影响的重要历史原因。
脑海中走马灯般以图像的形式还原历史的真实与幻觉,喜悦、惊悸、兴奋,我们是人间最短促的过客,也许它们从来就不为了一个答案而存在。
赵学梅侃侃而谈:
“古代劳动人民为认知、辨别、尊崇星宿,将二十八宿塑成二十八位性别、年龄、性格、身份不同的人物,拉近了神与人的距离,使二十八宿塑像贴近生活,便于传承。《太上洞神五星诸宿日月混常经》有对二十八宿状貌之描述:‘角星之精,常以立春后寅卯日游于寺观中,形少髭鬓’‘亢、氐、房三星之精,常以寅卯日同行,衣青苍衣’‘角星神……姓宾名远生,衣绿玄单衣’‘亢星神姓扶名司马,马头赤身,衣赤缇单衣,带剑。’以‘心月狐’为例,他面向左侧,张嘴高吼,怒目凸眼,头发随着转身的力度向后飘动,上身及腿脚袒露于外,肌肉暴起,左手向左出击,右手手指张开,左腿盘起,右腿前蹬,表现出武士雄健和无穷的内在力量。
“在九尊女神像中,其一采用发怒形式,飞动的头发向上冲起,带动两个大耳环在虚拟中大幅度晃动,与胸前的璎珞和胸花碰撞。脸部五官肌肉拉动,嘴巴形成喊叫状,凤眼因怒而吊、炯炯有神,随着面部情绪的加重,身体向右转去,左手用力挥向右边,拉动红色深衣大幅度摆动,无意识地露出了里边的白色单衣。雕塑师把握了生活中的精彩一怒,用夸张的浪漫主义手法表达了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增加了塑像的体量和结构的力度。二十八宿中大部分女神高髻花冠,领子开得较低,出露颈部,衣服色彩华丽……
“据载,宋代在元丰六年(1083)就在(治府)成都之东,建立锦院,募军将五百人织造,到南宋初又织造锦绫被褥等。宋代文化注重细节、局部。宋代的织绣染色技术大发展,当时的织锦花样繁多。神像衣着以褐红、绿色和石榴红为主,千重万叠,风飘袂起,展现了中华民族襦裙礼衣的魅力。头巾、冠、帽在二十八宿彩塑造像中出现较多。‘妇女花冠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宋代花冠则用罗帛仿真花做成。宋人尚高髻,上高直耸,高及三尺。’九尊女像,七尊为高髻花冠。十九尊男神,七尊为武士,两尊戴东坡巾,一尊戴风帽,其他男神头戴高冠,冠缨飞动,配以宽袖襦袍,脚下露出高头屐……
“星日马绿色长袍庄重潇洒,奎木狼皂白长袍衣冠楚楚,张月鹿乳白色长袍文静谦和。胃土雉、毕月乌、女士蝠是老者形象,面部干瘪下垂、肌肤松弛、长髯飘胸,如同晋东南地区的乡村老翁,天真达观,生性快乐。胃土雉神衣饰简洁,追求朴素而丰富的平民生活,头戴风帽,手抚卧于腿上的雉鸟,和蔼善良,随意盘起一条腿,带起了襦袍的下摆。雕塑生动写实,刻画出人物的精神面貌,体现了宋代雕塑人性化、世俗化的特点。”
和我以往认识的赵学梅判若两人。她活在倒流的时间中,晚霞点燃了她眼里的闪光。
被太阳笼罩了一天的庙宇,渐渐拉长了影子,在满目的晚霞中,尘土毛茸茸的颗粒在不停地飞舞中也已经蜷伏了。靠天吃饭,年成的好坏,不在于今年和去年下气力有多少差别,而在于天候,这是民众不可转捩的。干旱曾经如此地抽打人心,造就朴素的忧患。一座为农耕者建的神庙,令我除了目欲上满足于彩塑七色图泽之外,第一次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冷暖阴晴、沉浮荣辱。
不舍离开的状态缘于另一扇打开的殿门。在十三耀星殿与东岳殿里,我见到了有确凿特征的元代塑像。圆圆的帽子呈圆顶型,顶部有算盘结,拖着飘带,帽口以上四指翻边。在面部特征方面,塑像呈圆脸,下巴宽,眼睛细小,额宽而鼻平。长长的袍子,扎着腰带,挎着特别讲究的皮包,脚蹬黑靴,长长的左袖垂过膝盖。可爱的元代塑像,不知道这位大师是汉人还是蒙古人,但他留下了元代塑像的影子。元朝统治者对汉民族的哲学、宗教、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服饰打扮、风俗习惯等等相当隔膜,在神权的世界里顽强地保留了本民族的特征。
两个时代的作品在一庙之中对垒,这种差异性文化,尤其能够让人感受到民族精神的指向。
我突然理解了赵学梅,她愿意耗尽自己的精力和热情寻找一个证明,细想一下,多少人对身边的景物麻木不仁,又有多少人患有“文化冷感症”?
讲述者的神采飞扬,皆因她面对的是一个生命场。
5
“爱不动,我颤抖的双手拿不稳机架,拍出的照片都要虚化,昏花的眼睛只能在取景器里辨别物体的细部。相机的肩带换了又换,摸着老相机,忆起与它一起爬过多少山、蹚过多少河、越过多少村庄。我曾携着它寻找太行山晋城地区的古树、蚕桑与石窟造像。时光年复一年这样消逝、这样呈现,日子过老了一代又一代人。可我太想隐在照相机后边去感受那‘咔嚓’的快门声,这或许是一份无法放弃的情怀。我常常想起清雍正年间泽州知府朱樟用典故调侃自己:‘问年何止退三舍,喻战犹堪张一军。’《淮南子·览冥》记述:‘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撝(挥)之,日为之反三舍。’用今天的话解释,‘日为之反三舍’谓太阳倒退过三个星宿的位置。而泽州知府朱樟表达的意思就是:论年龄我可以退回三十年,还很年轻,因此决定在泽州做一番事业。这是一个五十七岁依然豪情万丈的古代知府。按朱知府的算法,我退回三十年也才而立之年。可昂贵的欲望不再呈现,我梦想着能够再和二十八星宿对话,但是,年龄让我力不从心,我真的回不到从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多给喜爱它们的人们做做讲解。”
热爱是生存的一种方式,是活着的一个必要证据,是存在的基本理由。摄影照片像散开的珠玑一样,照亮过往岁月的暗淡行程。老去的年华,拿稳相机的手,依旧期待一个静谧出口的最后温情。我被感染,同时想和她认真仔细观察分析二十八星宿的一些具体特点,来推导二十八宿成像的真正年代。
宋代,道教的神祇谱系已大致成型,是一个综括了众多先天尊神、后天得道仙真、人鬼、星君、地衹、幽冥官吏以及各类召役神将仙吏,等级森严的庞大体系。其中玉皇大帝作为一位统摄天、地、人三界的核心神祇,便如同世间帝皇,自有百官朝拜,万众拱卫,玉皇庙塑于两庑的二十八宿,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玉皇庙的宋代碑刻曾数次提到,围绕中央玉皇殿的廊庑中,彩绘漆饰技艺都十分精湛。试想一下,有宋之时,玉皇便高居中殿,莫非周遭廊庑却空空如也,直到百年之后才将二十八星宿塑成?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合情理的。
从玉皇庙的一通《创建庙门屏志》碑刻记载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隋时居民聚之北阜,建庙宇三楹……迨宋熙宁丙辰……于旧庙稍西,度地为阳相形土岗,创建庙宇三院……”对照史料就会发现,当时的泽州曾涌现出了一次修观建庙的高潮,在熙宁短短十数年间,便集中建造、修缮了包括冶底岱庙、青莲寺上寺地藏殿、小南村二仙庙等一大批宗教、祭祀建筑。这同样可为二十八星宿的产生年代提供有力旁证。观赏二十八宿时,会发现它们不论文臣武将、男女老少,从袂裾袍袖到冠盖铠胄,尽皆惟妙惟肖,体现了北宋时期典雅、精致、从容的妆饰风格,以及精妙绝伦的织造艺术。比如胃土雉风帽上纤毫毕现的绣边,比如柳土獐额前轻盈若雾的丝巾,比如箕水豹头顶繁复华丽的发髻。
对比《唐风宋雨》中后半部青莲寺的塑像摄影,可看到唐代(也包括唐代之前)的神祇塑像大都十分安详端庄,神情淡逸。但在玉皇庙的二十八宿塑像脸上,就有了明显的喜怒哀乐,这一人格化的转变似乎剥离了它们玄漠空寥的神性,令其走下了神坛。
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击人心!
赵学梅让我看她拍下的一位被毁的供养人头像,经过修复后,原来的神韵消失,变得呆板拘谨。好端端,硬是把不可能的事做成了可能。人的妄想症和胆子令我难过,曾经的时间煮雨,岁月缝花,漫度日子的虔敬心丢失得无影无踪。
“我拍《唐风宋雨》中的神祇塑像,就曾详细考证了它们的用料干湿、泥土来源、颜料生产等诸多方面,你可能认为这些同摄影似乎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但却能够在细节层面上更为有力地支撑摄影。比如青莲寺下寺弥勒殿中的供养菩萨像头部严重残损,内在的木架、禾秆、麻绳全部暴露,我拍摄记录下了这一幕,并驳回了印刷方认为它毫无美感而力主放弃的建议,使其得以亮相,在青莲寺下寺弥勒殿阿南的袈裟底边上我惊喜地发现了约四十厘米的唐锦纹样,为该塑像为唐塑的推论取得了更加有力的证据。”
透过这些相片,我们可以领略时光变迁的威能。
“光是可以千变万化的,比如青莲寺的弥勒佛我已经拍摄了二三十次,每次总会有不同的体悟和收获。因此摄影的表现形式不一而足,具体到新锐摄影的激进、狂乱、叛逆,也只不过是它渴盼传递交流的外在呈现,在内核上,摄影仍是孜孜于剖析和反映事物的本质。形式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作品能否成为作者与观者心灵对答的载体,所以任何单纯为了炫奇逞异而无病呻吟的摄影行为都毫无意义。时间是流动的,摄影采撷空间,而空间是广袤的,因此摄影是一种瞬息万变、纵横开阖的艺术。不同的镜头语境下,用相机所记录的同一点,会产生诸多区别;不同的观者在欣赏同一幅摄影作品时,同样会因自身各异的状态而获得不同的体验。在试图为摄影的本质定性时,我们首先须要充分理解它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摄影迄今为止仅有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但在客观精确地反映物事这一意义上,要远超绘画、雕塑等摹拟艺术,然而当摄影师的意志藏身于镜头之后,影像的昭示力量也难免会有所压抑。常有人邀请赵学梅游览和拍摄外地的名山胜川、风物人情,她都婉言谢绝了,只将镜头聚焦于晋城辖区,这才是她谋生的好地方。
1946 年晋城解放,县长杨辛克,在荒草中发现这堂塑像的珍贵,带民兵随陈赓部队远征豫西时都不忘派专人看管。从此有了府城庙文物管理所,20 世纪60 年代山西省政府列其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 世纪80 年代列为国家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府城玉皇庙二十八星宿彩塑是中国文物的经典,人们在崇拜与欣赏之时发现了其脚下的三百亩土地更有吸引力。不与神争地,放弃价值达十一个亿的土地收益,决定建成绿地以保护这座艺术圣殿,在利益与文物中选择与放弃更需要眼界与情怀。
沧桑巨变,冬一更,夏一更,黄土一层又一层,无论古人、今人,人文情怀总闪烁着难掩的光芒。宋代的建庙者府城村村民秦翌、杜惟熙,元代维修庙宇者刘宽,新中国的县长杨辛克,无论跨越多少代,他们都有着一样的执念。
赵学梅想起《唐风宋雨》一版的拍摄工作结束之后,曾有阵子她总觉得若有所缺,未竟全功,在将影文都送去印刷后,到底按捺不住,重新背起相机,赶赴青莲寺,审查缺憾,终于发现原来未曾拍摄南殿。因为年久失修,倾圮严重,岌岌可危,南殿关闭已久,她说服了寺中工作人员,孤身入殿,在燠热潮闷、蚊虫纷舞的南殿中流连盘桓了整整一日。就在再次结束拍摄,即将转身步出的一刹那,神至心灵地回眸而顾,正同普贤菩萨视线交接。千年的风雨沧桑,已将他的另一只眼睛剥蚀殆尽,但仅存的这枚明眸却依然清湛如水、涟漪不生。冥冥之中,似乎有种深邃的力量由他的视线传递而来,一直送入赵学梅的心田,于是在《唐风宋雨》的后记之中,就有了这句话:“They also need warmth.”(他们需要温暖。)
“月亮月亮跟我走。”一个出生在穷苦人家的女孩,后来成了管文化的副市长,用她的余生证明一座寺庙里的塑像年代比元要远一些,远到宋,重复一个痴人的呓语。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神话中,人们对“痛失”无动于衷,忘掉了执念、悠久和永恒的意义。
夜色是最好的修饰品,夜色中的大地宽容而纵深。
离开庙宇时,我想到曾经那些不计其数的乡亲们,他们的生命像尘埃一般默默无闻充斥和填埋在时光中。而他们走进寺庙,虔敬地跪拜,也许对生存的实质没有任何意义,但他们的日常却是为着这个走近而存在。民间微弱和快乐的盼望,是我选择写守寺人赵学梅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