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训练“目光”,如何观看
2024-01-01唐卫萍
【摘 要】 贡布里希撰写的《艺术的故事》是艺术史家为普通读者所写的艺术入门读物的典范,让作品“可见”是其历史写作的核心要义。该书反映了贡布里希的艺术史观,也从一个艺术史家的视角沉淀出了训练“目光”、观看作品的基本原则:接触作品。“接触”作品不仅包含视觉接触,即观看,也包括触觉、嗅觉、听觉在内的其他感官接触。“接触”作品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观看的训练是在无数次“接触”作品的过程中发生的。
【关键词】 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可见”的作品;观看之道;艺术训练
“目光”是眼睛向对象投射的一束光,是聚焦、摆放和安置。艺术史研究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不断对过去和当代的艺术作品,包括对周遭的自然和社会投射“目光”。学者们可以在展厅、故纸堆、画册、研讨会会场甚至在梦境中“观看”,在匆匆一瞥或持续的注视之中,在对作品的反复咀嚼和回溯之中磨练“眼力”,在无数次投射中积累与作品互动的经验和知识。在此过程中,“目光”的准星也不断被调整。艺术史学者就是一个个生动的样本:他们通过持续地研究和写作,展示投射“目光”的过程和观看方法,并将所投射的全部内容转化为一种可资保存和传达的知识形态。
从受众的角度看,艺术史的写作可以笼统地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面向专业同行的写作;二是面向专业以外的、对艺术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的写作。前者是专业研究者的本色当行,后者并非学者写作的必选项。迈克尔·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曾在《意图的模式》中谈到他对艺术史学者及其写作的困惑:“的确,当我们遇到艺术史家时,总会看到他们是一种视觉敏锐,机智活跃,心胸开放,饶有兴致的人。但令人迷惑的是,这些优点在他们所写的艺术史著作中并未能充分反映出来。”[1]即使是非常成熟的艺术史写作者,要做到自如地转换笔调,熟练驾驭上述两种写作类型也并非易事。可见,不管面对的是哪一类读者,好的写作仍然是稀缺的。这两种写作的目标不同,写作方式有别,但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尤其是为普通读者写作的价值常常受到专业研究者的低估。
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艺术史学者为普通读者写作的经典案例。该书被奉为视觉艺术的经典入门书,至今仍畅销不衰[2],不仅对贡布里希个人的生活和学术影响深远,也为他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据贡布里希描述,这部书的成功让他处于一种“奇特的双重生活”之中:
有趣的是,我现在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对很多人来说,我是《艺术的故事》的作者,他们在学校里读这本书,他们的姑姑、阿姨送给他们这本书,他们知道我是《艺术的故事》的作者,却从不知道我是一位学者;另一方面,我的很多同事从未读过这本书,他们可能读过我关于普森或莱奥纳尔多的论文,但没读过这本书。这是一种奇特的双重生活。[3]
《艺术的故事》虽然是面对普通读者的写作,其学术分量却并未因此而降低,“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历史观念构成了其内在支撑[4]。如果要追溯贡布里希艺术史思想的发展,《艺术的故事》可谓一个决定性的起点。贡布里希当然还是“同一个”,然而实际的情形是,因为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他被分裂为“两个”,在两个平行的维度或被忽视、或被广泛阅读。这种“双重性”一方面反映的是艺术史学者与爱好艺术的公众之间的相互隔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者们对两种不同写作类型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当下的艺术交流环境比贡布里希所处的时代要好得多,艺术史学者除了通过著作、讲演、纪录片等传统的交流渠道之外,也在自媒体、展厅等各种场合直接与公众交流;尤其是近年来,有更多开放的线上资源可被获取,艺术史的成果面向公众扩散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与此同时,人们也能看到更多面向大众的艺术普及著作和新媒体资源。然而,更多的接触机会并不会让隔膜自动消失,就像我们手头有各种造桥的工具和原材料,但桥梁不会自动搭建一样,那个懂得如何建桥并已经着手的人所做的工作仍然是最关键的,值得一再探究。
一、“可见”的作品
贡布里希是有意识地打破隔膜并取得成功的艺术史学者。面向普通读者的写作为他提供了重新审视自身研究工作的机会—从严谨的专业名词和术语当中抽身,拉开一段距离,向研究对象投去自由的一瞥(艺术史家也需要不断地克服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思考惯性,“自由的一瞥”并非天然地随时随地就能获取),并对艺术发展的总体历史进行重新打量、整理和描述。这样的写作一方面使他能将艺术史研究积累的成果以一种更为精炼和概括的方式向专业之外的领域辐射,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回到艺术的基本常识来思考问题。
贡布里希写作《艺术的故事》的方式是:根据家里的藏书,主要从《柱廊版艺术史》(Propylaen Kunstgeschichte)中选出插图[1],并依据这些插图口述整篇文稿;打字员每周登门3次,记录并打印贡布里希口述材料的文稿[2]。可见的“图像—艺术作品”是贡布里希组织艺术历史的基本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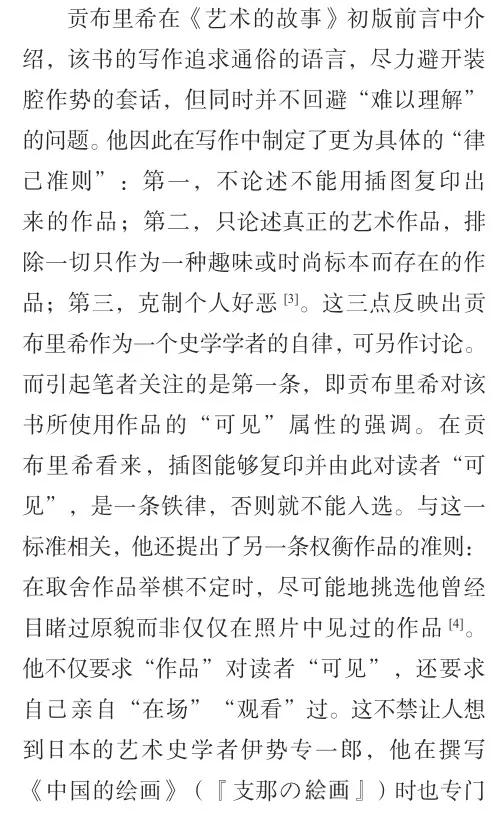

设定挑选作品的高标准往往意味着写作者对材料的掌握程度非常高,也意味着“作品”在历史叙述和写作中处于核心地位。艺术史家对图像的“可见性”“品质”及本人的“在场”如此执着,并非出于强迫症或者虚张声势,而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职业驱动,也可以说是对研究精度的极致追求使然:希望离原作越近越好,最好能够亲自观察、充分采集作品的原始信息,因为这是所有欣赏和研究得以进行的源头活水,是写作得以展开的立足点。对于贡布里希和伊势专一郎来说,作品的“挑选”和“呈现”是其著作的精华所在。而能够让读者,无论其专业与否,在阅读文字的同时“看见”这些作品就变得非常重要。贡布里希不仅在挑选插图上大费周章,而且在排版上也费尽心思,他力求让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眼前”就看到插图,让文字和插图相互提示、彰显和深化。而让读者沿着作者搭建的文字阶梯聚精会神地“观看”和“体会”作品,恐怕才是艺术史家想要传递给读者的“阅读之道”。对于一个艺术史家而言,如果其写作激发了读者从“阅读”书本到亲临展厅“观看”作品的冲动和行动,这无疑是对其研究工作的一种肯定和褒奖。
贡布里希在写作《艺术的故事》时所秉持的态度和原则,反映了其作为艺术史家的学术标准和品味,其中也蕴含着他的历史观念;同时他也撇开了各种细枝末节,从一个艺术史家的研究视角沉淀出了基本的艺术教育法则,这一点可谓艺术史研究的基本常识,即“观看”作品。
因此,在贡布里希这里,“可见”的作品是真正将艺术史家与普通读者的“观看”连接起来的桥梁。这也促使艺术史家在写作时回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许还涉及研究者对自我观看历程的追溯:一个想要欣赏作品的人,该如何展开自己的观看之旅?如何训练投向作品的“目光”?
艺术史学者海因里希·迪利(Heinrich Dilly)从学科的角度专门提到了艺术史的“观看”训练问题:
一个最常被提到的规定可能就是:“你必须学习观看,必须发展、训练出一种图像记忆!”于是相应地,人们会在讨论课以及学术会议上反复提出一个令人讶异的问题:“一个人又在哪里学习过观看呢?”观看训练的缺陷在学习阶段还有望弥补,在职业生涯中就只能花大代价去消除了。这里所说的观看在学院中一般是通过在当地博物馆参观原作或到欧美的艺术景点游览来训练的。最常见的训练形式是对绘画、雕塑、建筑进行比较性的观察和描述。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 lff lin)一直是比较性观看的大师。[1]
迪利的描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他让我们意识到,就如何学习观看作品这一点而言,艺术史家进入艺术这个领域所遭遇的困惑和普通爱好者毫无二致,否则研究者们不会在讨论课和学术会议上反复触及这个似乎本应信心十足的问题—“一个人又在哪里学习过观看呢?”艺术史家们似乎很少在文章中谈及这一点。艺术史家和普通爱好者的目光在作品之中交汇,艺术史家似乎应该反思是否过快地进入了“专业”的惯性,而普通读者则应该打消“专业”与否的疑虑,更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眼睛。那么,是否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观看技术可供人们效仿?答案是否定的。观看的训练似乎是永无止境的。迪利提到学院的训练方式是通过观看博物馆的原作、游览艺术景点来训练眼睛的敏感性,培育“目光”,而这种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发展出观看技术的训练方式,对普通爱好者也同样适用。
然而艺术史家与普通爱好者的观看目标又有着天然的区别。艺术史家需要为自己的观看建立一套解释性的术语,并在这些术语中安置作品。这种技术规定对普通读者来说并非必要,他/她只需汲取适合自己的经验,摸索出一条能够持续积累观看经验的道路,而无需过快、过度卷入专业话语生产的漩涡,也无身份的束缚,更无需忧虑观看的训练是否有缺陷,由此可以充分领略观看的乐趣和自由。在一定的条件下,轻松自由的心灵似乎更容易接近作品如其所是的面貌,这几乎和经过严格训练的眼睛一样重要。
二、观看之道:“接触”作品
眼睛是在“观看”的过程中受到训练的。更准确地说,是作品在训练眼睛,是作品在调整着人投射向作品的目光。在贡布里希看来,伟大的“作品”就如同活生生的人一样高深莫测,难以预言。诚哉斯言!他描述过眼睛的“看”逐渐走向深入的过程,“而我们越看就越能发现以前忽视的地方。我们的能力就会逐渐增长,逐渐感受到历代艺术家所追求的那种和谐。我们对那些和谐感受越深,就越能欣赏它们”[1]。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验描述,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无法直接向他人证明。观看的技术可以学习、模仿,眼睛的敏感性却不能直接通过知识的传授获得,需要在观看实践中积累经验。
我们有很多途径可以“接触”作品,直接接触原作当然是令人梦寐以求的,但原作的稀缺属性决定了它更多只能依靠“分身”出现在大众面前,下真迹一等的复制品和真迹一样珍贵。一般的欣赏者对原作价值的认知有一个过程,最便利的接触作品的方式还是观看复制品。
贡布里希曾遇到过一位当过小学教员的C. R. 韦布(C. R. Webb)先生,并对他引导学生进入艺术欣赏之门的做法极为赞赏:“他只是简单地把一些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品的复制品在教室里挂上两个星期,等到学生们都知道并记住了它们,他才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讨论这些作品。然后他在教室换上一批新的复制品。”[2]韦布先生的艺术教育方法很有启发性:他在孩子们每天上课的教室挂上作品,在这两个星期中,只要孩子们待在教室,有意无意间,肯定会“看见”这些墙上的艺术复制品。两个星期足够累积看的“印象”了,然后韦布才开始用“语言”介入。实际上,与这些画有关的“教育”在他开始讨论之前就已经在发生作用了。傅益瑶女士在回忆她的父亲傅抱石时,也提到他使用了与韦布类似的教育方法,“父亲的教育方法,是从来不让教育对象走进死胡同。父亲认为挂对子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常常让小孩子过过眼睛,时间长了就会看进去”[3]。傅抱石在这里挂的“对子”有双重功能,它既是书法艺术—熏陶眼睛,也是格言警句—涵养心灵。类似的做法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有很经典的例子。李成晴发表了一篇很有启发性的文章《壁帖:一种文本性与物质性交织的文献传统》,他梳理了宋儒及之后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壁帖”作为一种“图示化”的修身方法的历史[4],他在文章中征引了一则将“壁帖”实行于童蒙教育之中的材料,非常准确地道明了眼睛的“观览”在启蒙教育中的效用:
伊川先生亦尝曰:“读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盖读书不能力行,只是说话也。然学者趋向末端,欲体认力行,莫若常触于目以警于心。今《养正编》所载,大抵皆古人嘉言懿行,足以起发童蒙。为蒙师者,宜于每日功课之余,令幼童各书一条,贴于壁上,以便观览。一月三十条完,则令写于课本。下月复然。一年之内,共得三百六十条。食息起居,举目即是。不但记诵之熟,将从容默会,久而自化,其所以观感而兴起者多矣。不宁惟是。学者凡读他书,亦依此法,日无间断,朱子所谓“不知不觉,自然相触发”者也。[1]
这则材料很有代表性,“观览”这个行为实际上是一项综合性的智力活动,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可以让观览者在一定的时间长度内达到“记诵之熟”“从容默会”“观感而兴起”的效果。这不仅适用于童蒙教育,也几乎适用于所有的“观看”活动。可以看到,作为小学教员的韦布先生和作为画家、艺术史家的傅抱石所采用的教育方式与传统的童蒙教育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即让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作品,熟悉它们,通过无声的“目染”达到引导和教育的目的。“目染”是“润物细无声”式的、“从容”的,诉诸“眼睛”而非“语言”的,所谓“不知不觉,自然相触发”,即日积月累,自然达成。
这个过程本身并不玄奥,实质上就是通过人为设定一个“可见”的情境,增加接触和观看作品的次数。“观看”的行为在这个情境中既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随机的、偶然的。观看次数的增加意味着加深了视觉的体验、记忆和理解,也意味着增加了观看者获得观看灵感的机会。
这些例子提醒我们,观看作品从来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需要反复多次观看,并形成可调动的视觉记忆,这样的观看才能真正起到“累积”的作用。对于绘画而言,观看次数的增加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可能性,眼睛天然地会在作品中寻找不同的视角和感受,多层次地浸入作品。不同的时空情境也会对观看者产生微妙的影响。举一个例子,笔者所供职的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图1),走廊左边的墙壁上有一批精选的丰子恺漫画作品,这些作品是用石刻的方式呈现的,较之于纸上的漫画作品,更显线条劲挺,刀味十足。走过这条走廊的人几乎都会注意到左边墙壁上的作品,第一幅漫画就是丰子恺的经典名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图2)。

尽管笔者对这幅画已经非常熟悉,但经过这个走廊依然会抬头观看,每次观看时,触发点都有所不同:对绘画细节的重新品味,想象朋友聚会的场景,散场之后的寂静,饱含情绪的笔触,绘画的材质、制作方式,还有与时间、月亮有关的联想,甚至在夜晚推开窗户看到弦月时,也会想到这幅画。在无数次经过这个走廊,无数次地观看之后,作为观看者的“我”,不仅对这幅画形成了视觉记忆,还会在持续观看中加深对这幅画、对丰子恺的理解,乃至把这种理解带到日常生活中。这恐怕就是经典作品的力量—能够经受住无数次的观看而不让人感到厌倦,而且能够不断地对观看者产生影响。“观看”次数的增加无形之中磨练了眼睛的锐度和深度。这种观看的累积是无形的,对人的精神的陶冶也是无形的。无论是艺术史家、艺术家,还是希望进入艺术堂奥的爱好者,最基本的接触首先当然是“观看”,眼睛需要熟悉作品,熟悉那些已经创造出来的形式语言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独立的“观看”才有可能发生。
三、多感官的“接触”:你听,你看,你尝,你闻,但不要问
“接触”作品并不仅仅限于视觉层面,还可以包括视觉以外的其他感官。尤其是当下艺术的发展早已突破了单纯用眼睛“观看”的范畴,而强调多感官的互通和身体的全面沉浸。眼睛当然仍是非常重要的,但由眼睛指向身体的体验潜能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
当代艺术家王公懿有一件非常有意味的大型装置作品《你听,你看,你尝,你闻,但不要问》(图3、图4)。这件作品尺幅巨大,画册中的照片削弱了实物尺寸对人的感官的冲击力,在展厅观看沉浸效果更佳。这是艺术家到法国之后,因语言文化的隔阂,故借助艺术对自身身心状态的一种呈现,艺术家本人将其视为一件“表现禅宗思想的装置作品”[1]。撇开作品创作的背景不谈,这件作品在呈现“观看”这一行为的复杂性上,无论是在观念层面还是在作品的物质层面,都是一件极具张力的作品。

从标题来看,艺术家显然有意识地要悬置“语言”这一日常交流方式,而将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的能量加以充分释放。作者用了“你”这个称谓,既指向作者本人,也可以指向任何观看者,这个标题对所有的观看者提出了一个要求:关闭语言的通道。
作品是如何做到的呢?木条围合的边框像一道门,又像一个可穿越的、透明的镜屏,它既是平面的边框—画布的线条,又是空间的分割线—为画布拉开了一个身体可进入的立体空间。从正面观察它的形态(图3),立体性消失,立体的木条变成了画布的一个平面的围合线条,黑色粗边延伸到地面,画布、地面与木制框架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平面、新的画布。在这块新的平面上,画布的三维立体空间是由延伸的黑色粗边提示的。作品的焦点——文字符号,既提示线条,又提示颜色:可见的字的形体一方面与浓重的块面的黑色背景、明亮光滑的地面形成了点、线、面的节奏;另一方面,文字在明明灭灭之间,如同密林之中闪烁的光点,又在点、线、面的分布之中形成了颜色的分布,给人十分丰富的感官体验。
更有意思的是,文字在这里不仅是形式要素,也是表意的符号。标题提示“不要问”,而“问”出现在作品的内部,这是文字发出的“声音”。这要求观看者走得更近才能看—辨识清楚。我们从图像中能够辨识出的有意义的文字(这些文字显然是画家精心安排的)是:
为什么?因为……所以……但是……而且……你明白吗?这不可能!这不合逻辑!好好想想!实践证明……必须再确切一些!这确实是个真理。我觉得……我认为……我们如何证明它?为什么?因为……所以……但是……而且……你明白吗?这不可能!这不合逻辑!好好想想!
从问“为什么”开始,到“好好想想”结束,这个语法结构的循环像一条衔尾蛇,可以随着画布向地面的延展而无限延伸、无限循环下去。这个句式不指向答案,只提供“好好想想”的契机,“答案”或者说判断和选择的权力被交给观看者。这是指向观看者的“问”。所以,这个装置似乎在玩一个思维反转的游戏,通过不断地反转,向观众的常规认知发起挑战。
当眼睛结束观看,或者说身心经历了一番在作品中的历险之后,再从木质的框架中跨出来,从侧面观看整个作品(图4),木质框架恢复成作品“内”“外”空间的分割线,这是这幅作品结构上非常有活力的部分。观看角度发生变化,木框甚至把展厅也纳入作品之中,恢复了展厅的存在感,让“框进来”的外部空间和存在物也变成了建构作品的积极要素。对于观看者来说,除了视觉的兴奋点之外,这条分割线带来的观看的“仪式性”体验一定要身体跨过才能真正显现。人的身体进入这个边框,就如同进入画布,参与了画面内部的节奏,不仅眼睛在看、耳朵在听,身体也在感受,这是非常奇妙的体验。面对这样的作品,“眼睛”是不够用的。
《你听,你看,你尝,你闻,但不要问》的妙处在于,它更像是一则普遍的“接触”作品的隐喻,而作品本身的形式又鲜明地呈现了这个隐喻,作者的个人经验变成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普遍经验:你听,你看,你尝,你闻,但不要问。眼睛的“看”并非孤立的视觉活动,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心灵和身体互动的活动。
实际上,邀请观看者“接触”作品,在中国古典作品中也有非常精彩的例子,如书画当中的手卷就非常典型。眼睛在观看手卷时配合的是手的舒卷动作,这些动作将观者的注意力收束在这个微型的空间之中,也给观者设定了一个欣赏的情境:没有手的舒卷动作就没有观看,手是眼的先导。对于手卷这种作品形制来说,“手”和“眼”的作用几乎同样重要。手卷带给人的观赏体验十分特别,因为手的动作为眼睛的移动规定了节奏。虽然手卷在展厅中只能以平铺的方式展陈,但观众依然可以借助复制品来体会手眼配合、视线游移的乐趣。除了手卷之外,挂轴、横披、册页等传统装裱形式,实际上都在无形之中设定了作品与观看者互动的方式和节奏,观看者一旦体察到这种形式感的存在,它们对观看的调整及其所带来的微妙的审美感受才会真正被打开。
而从眼睛漫无目的的“看”到身心参与其中的“看”,不仅仅是由观看的“能力”带来的,作品的“打开”能力同样非常重要,上文提到的王公懿的作品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打开力”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抓住了观看者的“眼睛”,吸引人反复地观看、体验、思考。所以,“观看”活动本身,从最微观的层面来讲,首先仍是发生在“作品”与“观众”之间的一项复杂的交流活动,而且这种交流不是一次性的。
结语
“作品”总是在时代之中发展、变化,相应地,人们观看作品的方式也要随之调整。贡布里希在遴选《艺术的故事》的作品时还有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即克制个人的好恶,这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专业自觉,有助于人们了解艺术传统运作的方式,并尝试在个人和历史之间尽量保持一种平衡。但对于艺术爱好者而言,他们有一种天然的身份优势,无需受到这条规则的束缚。因为对作品的欣赏并不需要依照历史编年的顺序进行,人们可以依凭个人的好恶自由进出。艺术史有很多种路径供人们选择和摸索,尤其是观看的经验和方法,但欣赏艺术却注定是一条需要独自历险的道路。“独自历险”对于所有的观看者而言都是适用的。不妨以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中一段经典表述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想帮助读者打开眼界,不想帮助读者解放唇舌。妙趣横生地谈论艺术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评论家使用的词语已经泛滥无归,毫无精确性了。但是,用崭新的眼光去观看一幅画,大胆地到画中去寻幽探胜却是远为困难而又远为有益的工作。人们在这种探险旅行中,可能带回什么收获来,则是无法预料的。[1]
[1] [英]巴克森德尔:《意图的模式》,曹意强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2] 据统计,截至2023年,《艺术的故事》的英文版已经出版到第16版,并被译成42种文字,全球销量超过800万册。参见[英]E. H. 贡布里希、[法]迪迪埃·埃里邦:《贡布里希谈话录:贡布里希文集》,杨思梁、范景中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23年版,第47页。
[3] [英]E. H. 贡布里希、[法]迪迪埃·埃里邦:《贡布里希谈话录:贡布里希文集》,杨思梁、范景中译,第47页。
[4] [英]E. H. 贡布里希:《艺术与科学:贡布里希谈话录和回忆录》,杨思梁等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1] [英]E. H. 贡布里希:《艺术与科学:贡布里希谈话录和回忆录》,杨思梁等译,第276页。
[2] [英]E. H. 贡布里希、[法]迪迪埃·埃里邦:《贡布里希谈话录:贡布里希文集》,杨思梁、范景中译,第46页。
[3] [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2页。
[4] [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第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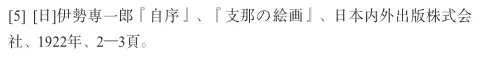
[1] [德]汉斯·贝尔廷等:《艺术史导论》,贺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1] [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第36页。
[2] [英]E. H. 贡布里希:《艺术与科学:贡布里希谈话录和回忆录》,杨思梁等译,第205页。
[3] 傅益瑶:《我的父亲傅抱石》,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4] 李成晴:《壁帖:一种文本性与物质性交织的文献传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1] 陈弘谋撰,苏丽娟点校:《五种遗规》,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笔者根据李成晴教授的文献指引使用了这则文献。
[1] 居振容、王公懿:《王公懿作品及艺术对谈》,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1] [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第37页。
责任编辑:秦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