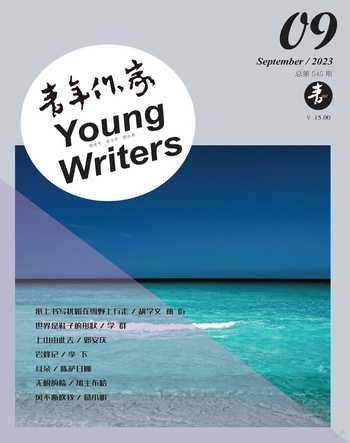风不断吹我
2024-01-01葛小明
一
风从陈年的铝合金制的窗户缝挤进来,它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什么年纪,不管你是贫贱还是富有,不管你此刻是开心还是沮丧,它迎面就来。哪里柔软,哪里好欺负,就先到哪里。腊月刚至,风就使劲地吹,使劲地伤害,极力地向你证明,它来了。
这个所谓的两室两厅一卫的房子,实际上只有一室一卫,剩下的空间或冷或旧已不能使用。阴面的卧室,永远见不到太阳,加上里面陈旧的灰从未清扫过,早已不能进入。厨房没有任何设备,没有厨具,没有餐具,没有天然气,没有能自然流出的自来水,没有人烟。恐怕连房东都不知道,因为天气太冷的缘故,处于厨房位置的水龙头早已冻住,流不出一丁点水了。客厅的沙发,无论怎么擦拭,都无法除掉布满的灰尘与油渍,没法坐人,没有人坐。有一张跟房子同样陈旧的玻璃茶几,勉强站在客厅里,没日没夜地接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尘埃与消息。沙发上有几张报纸,是《中国国土资源报》,年份大概是2017年。再往上是一本本各色的期刊杂志,多是我的作品发表后赠送的样刊,它们安静地蜷缩在一起,用尽自己的办法度过这个寒冬。
这堆书一度是我的困扰,想扔掉不太舍得,想留下,又实在放不开。这堆书太多了,大多是各地的内部刊物,加起来有近千本。这让本就矮小又凌乱的屋子,显得格外不雅。有一次,日照电视台新闻频道联系我,要来我的住处采访,经百般拒绝无果后,我首先想到要处理的就是这些书。尽管是因为获得文学奖受邀采访,但这些并不能成为我引以为豪的东西。在这样一个陈旧的出租屋里,任何稍微“高雅”点的修饰物,都不值一提,并且充满了违和感。
这里是县城最老的一片住宅区,因为过于老旧和杂乱,它竟然没有一个名字,甚至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它的标记。由于小区外围的马路边有一家很小的诊所——北斗门诊,人们往往喜欢称这一片居民区为“北斗门诊”。这家诊所的医生特别有原则,他从不按盒开药,每次给病人的药都是从药盒里拆分出来的,包在一个个很小的专用纸袋里,袋子上写着服用的方法。来寻医的人花最少的钱治好了病,大家对他都非常放心,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渐渐地,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当然大病他是治不了的,也不接收。有一次,我目睹了路边前来求助的一位母亲,她的小孩子在怀里休克了,救护车尚未赶来,是他跑着赶来紧急抢救了孩子。因为事出突然,没有围观的群众,事后这位医生也从没有在人前提起过。由此,我对这家门诊肃然起敬,以至于后来离开这片区域,仍旧会回来买药。
继续说一下我的出租屋吧。朝阳的卧室,是最暖和的,加上两床较厚的被子,熬过冬天不成问题。一张床,一个门已破损的衣柜,一个蜷缩在被窝的人,就构成了这个屋子、这所房子、这个世界的全部。由于拉上窗帘会遮挡稀有的阳光,我便在玻璃上贴上了一层半透明的窗纸,这样既能保证隐私也能获取大部分的光。尤其是在冬天,光的进入使这间屋子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寒冷,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光的心理学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光能让处在困厄中的人获得逃生的路径。
阳台是值得一提的地方,尽管它有三分之一的空间堆满了房东的杂物。有一棵高大的剑麻,在最东侧的一角立着,底部的叶片因为缺水已经枯死,但是顶部的叶子依旧鲜活。看得出上一任租客与我之间可能间隔了好几个月,不知道它受了多少苦。我来到的第一天就给它浇足了水,看到硬邦邦的土變为湿润的水田,心里顿时生出了满满的成就感,仿佛自己刚刚拯救了世界。周末的时候,除了睡觉时间,我大都站在剑麻的一旁,看着它在仅有的土壤里生长壮大。这让我想起川端康成凌晨四点钟发现海棠花未眠,不由地想到,要活下去。也让我想到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男主里昂怀抱的银皇后。它们是植物,是光,是寄托,是信仰,是三千世界。这株剑麻,在我刚毕业的那两年时光里,一度成为陪伴我时间最长的朋友。直到后来离开这所房子的时候,我忍不住与之作了隆重的告别。之后的每一年我都会挑一个时间回去看看,尽管迈不进屋子里,但在外面的小胡同里就能远远地看见它的梢头。它还在,一直都在,这让我心安。
风却不管这些。风不断吹我,伤我,杀我。那两年,风把最冷最无情的部分留给了我,毫不顾及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农村孩子,不顾及我为了省几百块钱的房租住进县城最脏最破的小区,不顾及我做着一份收入微薄的工作,它只管吹,只管伤,只管肆虐,只管杀。从每一扇漏风的门窗,从没有做任何保温的楼宇外墙,从贫穷底部,从勉强温饱,从众人的轻视中,一阵一阵地吹来,无休无止。隔着仅有的玻璃,我能清楚地听到胡同里走来走去的人。这个小区里住的最多的是老人和孤苦伶仃者,他们脚步迟缓,节奏感差,时常拖着地,稍微留点神甚至可以分辨出他们脚底的是粗沙子还是细砂砾。
他们在风中行走,在腊月严冬行走,在只有四层楼高的破旧小区里行走,在暮年衰弱无力的夕阳中行走,在儿女不在身边的孤独与寂寞中行走。他们有时候能从风中顺利回家,有时候迷失在风里,再也回不去。在风中,他们的感受或许是相同的,冷而不至于绝望,坚持一下尚且能获得下一个春天。
在我百般婉拒无果后,电视台的记者还是来了,两位男士一位女士,主要从四个场地取景:单位,母校,田野,住所。前三个很好解决,最大的困难就是住所,这个勉强可以称为家的地方。我实在不好意思让一位女士光临“寒舍”,这个寒冷的四面进风的地方,曾让我一度蒙羞。
好在采访比较顺利,只用了一天时间就结束了。几天后母亲从老家打来电话,说邻居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她接连看了好几天电视,也没有发现我的影子。话语间,她情绪激动,分贝比往日高了很多,好像获得了莫大的肯定。
二
“是谁报的警?”
“我。”
“你叫什么名字?把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葛小明。我没带身份证。这个人诈骗,收了我们的中介费,却不按照合同上的内容履行。”
“他是骗子!”
“他忽悠我们,现在我们无处可去了。”
“他在大学城里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人面兽心!”
“我连回去的车票都没有了。请警察同志制裁他!”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连穷学生都骗。”
“你们一个个来,不要搞事情。”
我冲在了最前面,跟正在记录的警察反映情况:我们三个人跟他签了合同的,上面有他盖的章。说着我便把一张纸拿了出来。
警察认真看了二十几秒钟,说道,“这是在日照签的合同,你们需要回去解决。打日照的报警电话吧,加上区号,0633110。不要搞事情。”
我把那个三十岁左右的中介拉到一旁,小声说道:“你把我们三人的中介费退还给我们,别的事我就不参与了,这一群人中只有我们仨有纸质合同,其他人我也不认识。”
中介态度坚决,“不可能”,并且掏了掏自己的口袋给我看,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的大一假期,本欲打一个月的工赚取下半年的生活费。通过日照大学城一家中介找到了这份工作,出于谨慎,我,还有我的两位同学,宋凯、王云庆与之签了纸质合同。在我的百般要求下,中介盖了一个红章,他说:“每年送去那么多人,你们是独一份。”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不同的城市聚集到了青岛。这是一个离海边非常近的地方,每年都要在此舉办国际啤酒节,我们的职责是安保。对方承诺每天工资不低于一百元,时间从七月十八到八月底。七月十号的时候,中介突然打来电话,让我们提前到达,不然后面的工作将不会安排给我们。我问,提前去的工钱怎么算?他不作正面回答,直说来了再说。我犹豫了半天,最终决定提前动身,因为二百八十元的中介费在我手里不是小数。这是我的第一次出门远行。从老家的小山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到日照汽车站,然后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大巴来到了青岛汽车站。最后三个人在汽车站集合,凑钱叫了一个出租车,四十多分钟后来到青岛国际啤酒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青岛,第一次见到大海。
途中一直陪伴我的是一个塞得满满的蛇皮袋子,里面有我的铺盖和洗漱用品,还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它们和我一样,在汽车里晃呀晃,经过一幢幢高楼大厦,经过一条条从未走过的道路,最终来到这里,这个人烟密布的地方。我所见过的海风,一定不是你见过的,它不温柔,不会只吹坚硬的石头以及沉默之物。它反常规地吹,吹贫穷的乡村大学生,吹外来陌生的稚嫩的面孔,吹连公交都没学会怎么乘坐的迷途者,吹一个个曾用来装化肥而现在装着被褥的蛇皮袋子,吹在水泥地上用篷布临时支起的巨大的帐篷。
我们的抵触情绪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之前承诺的一切,都被临时篡改,工作不是安保,而是服务员,且工资每天只有七十元。老板很直白地说,没有安保或者保安这回事,这份工作是自始至终的,不会发生变化,要么不干,要么一干到底。第二个原因便是住所,一个大约能装一百人的巨大帐篷,头顶是一块大篷布,勉强可以抵御风雨。床下是巨大的可以连接到海边的水泥地,一张张老旧的铁床站在那里,上铺下铺都挤满了人。
警察问中介:“你是什么单位的?”
那人低头没有底气地说了几个字:“大学生兼职委员会。”
“这明显是个伪组织,与盖的章内容也不相符。”我们三个人满脸的愤怒。
我又冲到警察面前,想继续辩解,试图陈述一下事情经过。警察似乎不太关心这个,一把制止住我,说:“你先闭嘴,不要搞事情。”他记录完他说的单位,就离开了,最后一句话是:不要搞事情。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小汽车,突然一阵失落,这车与其他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的车辆,本没有太大区别,一样释放尾气,一样铁面无私,一样无法治愈伤心的人。
天很快就黑了,本想着去旁边的石老人景区转一转,在海边的沙滩上坐一会吹吹海风,没想到什么兴致都没了。我们当即决定离开这里,但是已错过了最后一班回日照的车,事实上就算赶上了最后的车,也没有办法赶上日照汽车站回乡下的公交。可是,我们没有勇气去住旅馆,连问一问价格的勇气都没有。这个城市对我们来说,太大了,它足以吞没我们所有的不能、不甘、不堪、不愿。宋凯,这个我高中的同班同学,现在的济南大学的理科生,沉默了好几分钟后,决定问一问他在青岛打工的多年未见的老乡。
晚饭是那位老乡请的,在一个狭长且隐蔽的胡同里,我们三个不速之客与他互相寒暄。鲜酿的扎啤,第一次喝到。深夜大城市的月亮,第一次见到。青岛的市井与烟火气息,第一次沾染到。夏天由凉爽到逐渐刺骨的海风,第一次吹到。后半场,我们的酒喝得差不多了,人的话也就多了起来,不再像刚开始那样拘谨。从简单的寒暄到日常的工作生活,从一道菜的味道到外来打工者背后的不易,从美丽的石老人景区到幽深潮湿的胡同过道,我们无所不谈。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啤酒的鲜美,也终于在一张简陋的铁床上获得了消释悲伤的力量。
是夜,我们三个人加上原来就有的三个人挤在了一间出租屋里,床是上下两层那种,最原始的铁加上一点亮蓝色的油漆,此刻变成了我们最温暖的避风港湾。某个瞬间,我甚至以为自己睡在一艘船上,晃晃悠悠,惬意而优雅。这虽然是一间阴面的屋子,常年见不到阳光,但在夏天却格外凉爽。窗户没有全开,却可以明显感受到风。它细细的,密密的,就像山间一股温柔的小溪,轻缓流过,不划伤河床的皮肤,也不带走一粒沙子。它吹呀吹,让每一个疲惫的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这些梦,这些风,时常胶着在一起,让人分不清。
次日清晨,我们早早地离开了那个城市,回去后也没有继续报警。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好像没有悲伤。
三
他似乎是用尽了一生的气力攥紧那只拳头,我在床沿的一侧,没有看到他另外那只拳头是否也如此。但我明显感觉到他皱起的眉头和紧咬的牙关,那可能是一种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疼痛,大于被采石场的巨石砸中脚趾,大于老板拖欠了半年的工资迟迟要不回,大于骑了一年多摩托车轮胎被矿上掉落的石块刺破的心疼,也大于在外打工半年多不回家唯一提前回来的原因是肠胃疼到吐血。
他的恐惧更多来自于内心,作为一个极少走进县城的人,面对一群身着白衣的操刀者,他心有恐惧,看起来那刀比任何凶器都锋利。更深的恐惧是,他担心自己患了治不好的病,连累家庭。他的收入全都在银行卡里,钱只要存进去,就不会取出来,除非有生死的大事,或者全部给子女,一分不留。他就是这样,六十多年来一贯如此,不舍得吃穿,总是在有限的能力内把最无限的爱给予妻子和孩子。手术的时间被他无限拉长,这是一个熬人的过程,那漫长的时间里,他考虑最多的可能是孩子还没完全成才,他还需要继续照顾家人,继续养家,他还要为家里再多赚一点钱,让妻子有生存下去的底气。他想,如果这是不治之症,会不会一下子把家里的积蓄花完,甚至拖垮两个儿子。
尽管只有一米六八的身高,但这毫不影响他是家里乃至整个家族的顶梁柱。小小的身子,能够轻松地搬运百斤重的麦子和水泥,这一度让哥哥和我羞愧不已。在我们的世界里,父亲永远都是力大无穷的、万能的、不可战胜的。哪怕哥哥已经年过四十,我已近而立之年,仍旧觉得父亲没有变老,不会因为什么事情倒下。遇到问题和困难,我们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那是依靠,是高山,是精神支柱,是天。可是,现在他倒下了,躺在急救中心的病房里,目前处于半麻醉的状态。
他看到的天花板大概是白色的,死灰式的白,所有躺在病床上的人看到的都一样。那是一种极其冷漠的颜色,在这个宽敞的屋子里,这种冷漠被无限放大。你感受不到窗外吹来的风,但是手术刀的冷,铁床的无情,从身体内部散发的疼痛,这些足以让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内心冰凉。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也不敢看锋利的手术刀和专注于某种“仪式”的大夫,我只能把视线凝聚到他的拳头上。
那是一双极其粗糙的手,汗毛黝黑却无精打采,密密麻麻地斜立在手背上,就像是刚刚栽种便枯萎的茄子幼苗。有几根血管凸起,明顯高于皮肤,显得冲动而有力,好像能够战胜世间所有的苦难。他的每段指节都有厚厚的老茧,高出皮肤很多。这些茧,不知道为他抵挡了多少次危险,包括锋利石头棱角,切割机飞速转动的齿轮,蚊虫密密麻麻的叮咬和啃噬,凑不齐学费的窘迫、讨债无门的愤恨,这些它们都曾努力包裹好了,抵御住了。可是这一次它们似乎没有成功。
他忍着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事实上这一生他都没有发出过,所有的苦与痛、悲与情,都在一次次的隐忍中淡了下去。我试图去握一握他的拳头,让他心安一些,手伸到一半停了下来。我想他大概会觉得难为情吧,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就这么随便地倒下,他会觉得羞愧和不知所措。十几分钟后,他睡着了,可能是麻醉药起作用,也可能是真的太累了,这几十年我从没有见过他如此虚弱的样子。一些暗红色的液体从透明的软管中流到了另一个透明的容器中,天生晕血的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去观察那些流动的物质。那是他半生的委屈与辛苦,是永远无法言明的脆弱,是一个男人最柔软的部分,我心疼极了。
他是从一个临时搭建的木架子上摔落下来的,途中腰部恰巧撞到了一把站立的椅子的脊背上。起身后,继续为邻居帮工,砌起了新房子的围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想到的是,两天后他突然倒在田地里,翻不了身。救护车上,我们心里猜测着各种最坏的可能,哥哥在前面驾驶私家车,我坐在救护车里,不知如何是好。我尽可能地跟车上的医生陈述他以前的病史,医生干脆而果决地,点头,反复地说“嗯”。我看到车窗的缝隙里有风吹来,窗帘起起落落,有些吹在了他苍白的脸上,也有些使得他的头发越发凌乱了。我用力拉了一下车窗,无果,可能是经年不关,已经不听使唤了。我半蹲下来,再次用力,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那么无用,拿一个小小的车窗都没有办法。那些风啊,那些摧残人的流动之物,一个劲地扑在我受伤的父亲身上。
我后悔没有带一个被子之类的遮挡物,哪怕是一件薄薄的外套也好,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风一遍一遍地扑在他的身上。或许,那风于他并不冷。或许,那风正好能够减缓一点他的疼痛,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三十分钟的救护车,足以让一个躺在车里的人的恐惧加深,加到最深、最满、最无助,他始终闭着眼睛,我知道那是在躲避。一个再伟岸的人,一旦进了救护车,便瞬间成为世上最弱不禁风的人。
救护车应该是承载希望和绝望最多的容器了,它知道躺着的人内心的恐惧,也知道即将被救护的心安和如释重负,它救回了一些人,也送走了一些人。每个曾在这辆救护车里暂待的人,都会看到有风从窗户缝吹过,急匆匆的树影和摇晃的窗帘,以及忽明忽暗的生机。希望世上的救护车都装满了善意,希望每一阵吹来的风,都能够绕开那些躺在车里的苦命人。
父亲没有上过学,但是在有限的“夜校”学习期间,认识了一些字,也算是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不同于母亲的认识。他认得最多的几个字,不是白菜、猪肉、酱油、哈德门之类的,而是二甲双胍、格列喹酮、消渴丸、达格列净、缬沙坦氨氯地平片这些母亲常用的药物。他那双老年远视眼,最认真地盯着一件东西看的时候,就是为母亲辨认药物的时候。他甚至比母亲更清楚,哪种药每天服用多少片。而母亲辨认药物的方式更为特别,她不识字,对外包装类似的药物,她通过摇晃药瓶产生的声音来区分,总也没有出过差错。
当天晚上,他醒了过来,身体极度虚弱,几乎难以挪身。我试图和他交流,他首先关心的是,“这趟得花不少钱吧”“我感觉没事了,明天回家吧”。想都别想,我们太了解他了,这时候,我们必须替他做主。他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又坚持要出院。无果。五天之后,他极力要出院,说自己完全好了,就是个微创手术,还没有上次砸伤脚趾严重。
几番争执后,我和哥哥决定带他去医院西边的河边走走,看看他的状态之后再做决定。一个常年劳作的人,无法接受躺在床上无所事事还要别人照顾。为了证明自己已康复,他走得格外卖力,一路上尽可能地提高说话的分贝,就像一个喜欢表现的孩子。在河边,我们讨论的是地里的庄稼、河里的鱼、山上的马蜂窝和野兔,好像从来没有住院这回事。
水边的柳树长得很健康,枝条从天空垂到地面,路过的人总是小心翼翼地拨开它们。人们谈论的事情,我们无从得知,通常是住院的人接近康复状态才会走到这里。他们看到的水,一定很美。看到的树,一定很健康。河边时常有风吹来,窸窸窣窣的,它们粗粝的部分已主动留在了柳条之外。柳树下的人,迎风扑面,一点也不冷。风知道,这种柔软来得多么不易。
【作者简介】 葛小明,山东五莲人,出生于1990年3月,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作品发表于在《人民文学》《钟山》《天涯》《散文》等刊,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香港青年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等,著有《集体失传》;现居山东日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