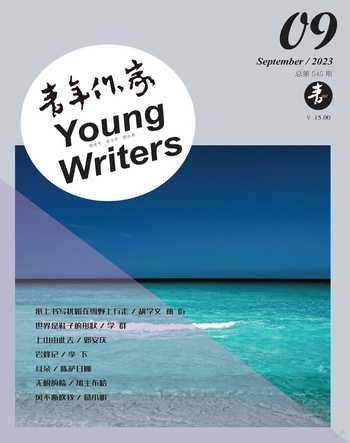“无根”是我们所有人的悲伤
2024-01-01宗永平
抒情
“他伸了个懒腰,漫无目的地走到半山坡上,在一棵枯萎的野梨树上坐下,耷拉着双眼望向山顶的云雾,他的手从枯梨树的肌理中,仿佛摸到了自己皱皱巴巴的余生,他觉得更悲伤了。”普诺其实只有七岁,无论是“肌理”的用词,抑或对自己“余生”的思索,都有失真的担忧——但是没有。抒情的基础,是对情感的忠诚和信任;如果单纯和持久变成奢望,情感的真实就将受到质疑。令人好奇的是:在几乎失去抒情能力的现在,加主布哈饱含深情的叙述和文字选择,为什么能被独特地感受?除了文字中单向流动的情感的饱满,当读到“普诺的姐姐戈玛,正收着晾晒在院子里的荞麦籽,她吹着细长的口哨召唤风”的细节,我们就会明白:小说里的世界,更贴近原初的生活,并且信仰它。单纯、原初和信仰,这是《无根的脸》的前提逻辑,也是它明朗抒情风格的源头。
家族
《无根的脸》形式上很容易被认为是一部家族小说。但是深藏的和最终的目的,却是瓦解它。它提供了传统家族小说中必备的亲情和爱情的式样,甚至也有对家族责任的承担(背叛,也是一种承担模式):这种承担带来的对家族温情的保持或破坏,让小说看起来要走向道德训诫的老路。但是作家的反动随处都在:小家庭遭受一次灾难,直系的叔叔抛弃了普诺和姐姐,反倒是舅舅达野收留了他们,并负担起养育的重任;但是舅妈的不满渗透进生活的每个细节。当然,“刀子嘴豆腐心”的事实,在他们跟着母亲离开时,挽救了亲情的温馨。但这只是为了映照后来自己父母的冷漠——这是另一重反动。
舅舅达野和科莫阿果的爱情模式显然更符合传统,它的基础是舅妈对舅舅绝对的痴情。代价就是女性无条件的付出,以致丈夫偶尔的体贴,都成了特殊的恩惠。至少,它确实稳固、可靠——当然,很难揣测最后的揭秘,对它冲击的力度。奶吉镇是四通八达的一座交通要塞,“外面的世界”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母亲和父亲鸠阿垛的感情受各种因素影响:伦理、欲望,物质、追求,生计、责任等。所以,当独占性受到挑战,他们也会有嫉妒和愤怒,但“殉情”的热情,最终演变成一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现代喜剧。不过,这样的爱情,无疑更有韧性,也更具侵略的锋芒。
姐姐戈玛不仅是普诺的看护人,也是感同身受的共同经验体验者,实际上也是某种意义的另一个普诺——一个选择不同、更加包容的普诺。
生命
在菓俄村,贴近自然就贴近了生命。一条等死的狗,不知来处,也不知去处,却成了普诺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见证者。在神话和传说漂浮的菓俄村,它不但能把悲伤传染给普诺,显然也是不祥的象征。当然,读完小说,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它蕴含的信息,甚至,它原本就是父亲的一个重叠影像。
生命在菓俄村表现得最磅礴澎湃的,是那场火——旧的死亡,是新的生命蓬勃焕发的条件。所以,死亡,是一种最真切的生命表达形式。被焚烧的树木花草如此,老狗如此,父亲也如此。而整个生活的偶然、意外,以及不可把握,就是命运。
告别
告别是《无根的脸》的主要情节,每次告别既是生活的结果,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真正的问题是:普诺总是被告别带来的怀念萦绕、纠缠。如果告别家到菓俄村舅舅家,普诺无法选择,或者说没有选择的话,这次告别只能是姐弟俩成长的背景。但告别菓俄,首先不是普诺的选择,更加重要的是,此时舅舅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点,而就是普诺的成长,也就是普诺自己。他不但融入了舅舅的家庭,而且接受了传统的生活理念,甚至,舅舅的音乐,以及由此而来的忧愁气质。这也注定了,普诺不会属于更现代的奶吉镇,当然也就不属于父母在奶吉镇的家和他们的价值观。所以,当面临婚姻的逼迫和恋爱的空虚,只能逃回菓俄村——一个存放自我和传统的所在。但是父亲和舅舅残酷的秘密,让一切灰飞烟灭。
悲伤
最后来考察贯穿始终的悲伤,结果就非常明确:《无根的脸》是一部瓦解家族,丧失家园和回忆,因而也丧失自我的小说。甚至还可以说,这样一个单独的人丧失自我,一个像菓俄村这样的村子失去可以凭借的传统,一个像彝族这样古老的民族失却自己的文化和信念,因为我们的生活,正在被现代文明“腐蚀”。如果说彝族就像奶吉镇,正在受到现代文化的侵蚀,那么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外面的世界”,已经在现代文明的海洋中弄潮。延續几千年的乡村生活消失殆尽,已经没有能力产生传统文化新的模式,也就丧失了对现实生活回应的能力。所以,我们正在彻底地告别传统,比所有文学或文化革命,都彻底。“无根”不仅仅是普诺的悲伤,也是我们所有人的。
【作者简介】宗永平,作家、文学编辑;江西新余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时光的隐寓》、长篇小说《炫耀》等;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