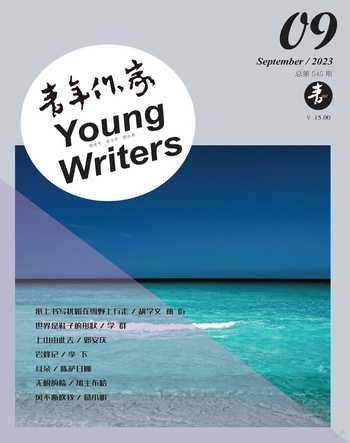上山由此去
2024-01-01邓安庆
一
拐到风华路时,坐在副驾驶的瞿麦说:“到路边停一下,我去去就来。”我问:“要买水吗?后备箱里有。”瞿麦语气坚决地回:“停一下。”我刚停好车,瞿麦随即打开车门,往路边那一排店铺跑过去。开始我以为她要去卫生间,谁知她跑进一家五金店里去了。我解开安全带,刚准备下车跟过去,她已经折返回来了,气喘吁吁地说:“走吧!”我只得又坐回去,启动车子时,瞥了她一眼,她手上多了一把短柄小铁铲。“这是要干嘛?”瞿麦把铲子放在腿上,眼睛直直地盯向前方,“有用。”我本来还想追问下去,看她若有所思的神情,又把话咽了下去。这一次出行,不能惹她不高兴。毕竟她能够答应出来跟我一起爬青阳山,已经是意外之喜了。我用讨好的语气问:“晚上睡得怎么样?”她没搭理我。我自讨没趣,讪讪地咳嗽了两声。她这时才回过神来说:“你问我什么?”我说:“青阳山景区快到了。”
正逢周末,又加上难得的晴天,我们到时,景区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瞿麦背着双肩包,手上拿着铲子,迟疑了一下,递给我,“能不能装到你的包里?”我接过来,打开背包正好能放进去,“你是要挖笋子啊?这个季节是不是有点老了?”瞿麦难得地笑起来,“埋你的,你信不信?”见她语气松快,我笑嘻嘻地回:“怎么?还让我自己挖坑自己躺下去?”瞿麦手轻轻地打在我肩头,“就会油嘴滑舌!”我从背包里掏出相机,“合个影。”瞿麦配合地贴着我站在一起,来了一张自拍。真是一个不错的开头。一想到待会儿去山上还能够牵她的手,心情不由得雀跃起来。
但我想错了。进了景区后,我们沿着木栈道随着人群慢慢往山上走。我尝试地碰了碰瞿麦的手,她明显地缩了回去。这让我有点沮丧。她双手抓住背包带,神情肃穆地往上走。走到一片竹林前面,我喊她:“你转过来,我给拍张照。”她没好气地回:“走啦!”我说:“时间还早呀。”她又一次语气坚决地说:“走。”我只好跟上她,因为心里有气,连话也不想说了。她没有察觉,或者可以说,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就像这次爬山,是她一个人的事情,而我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我决定不搭理她,看看山景也比看她好。兩侧山峦叠翠,粗壮的侧柏笔直地刺向天空,泉水从木栈道侧边潺潺流下,时不时从这里那里传来“哩——哩——”的鸟鸣声,深深地呼吸一口,清冽的空中甚至带着一丝甜。我“啊”了一声,马上要跟瞿麦表达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之情,但我憋住了。瞿麦早已经把我甩出好远了。
我还不怎么能摸得清她的脾性,也不敢贸然地发脾气,毕竟平时她不会这样。七个月前,她来公司上班,正好坐我对面。我每天抬起头就能看见她。她喜欢把头发盘成发髻,露出整张脸和脖子,会化一点淡妆,旁边的女同事找她说话,她会聚精会神地盯着对方看,然后忽地一下笑开,那一刻让人分外心动。后来有事没事,我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她,比如说组队做项目时拉她进组,开会时坐在她旁边跟她搭话,下班时故意掐点和她搭乘同一部电梯……渐渐地,我们熟络起来。几次大的活动,我帮她解决了几个技术问题,让她得以顺利转正,为此她还请我吃过饭。我没有直接跟她表白过,但她应该明白我的心思。我总觉得贸然地捅破这层纸,会有失去她的风险。另外我总觉得她有心事,虽然在外人看来她活泼开朗,但当她一个人时,又会流露出落寞的沉默神情。这一次爬山,我就想好好跟她聊聊,趁机也想把我们的关系挑明。成败在此一举,我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好觉。而现在这个局面,瞿麦心思显然没有在我身上,我喊了她好几声,她都没有停的意思。
到了青阳禅寺,我才撵上她。她等在山门处,双手还是紧抓这双肩包的背带,像是有人要抢她的东西似的。门旁立着一个木牌子,上面用毛笔字写着“上山由此去”。我叉着腰喘了一会儿气,埋怨道:“你听不见么?”瞿麦“嘘”地一声,跨进山门,往大雄宝殿慢慢走去。游客络绎不绝,庭院中央的桂花树每一根枝丫上都系了小小的红丝带,上面写着人们祈祷的内容。我也想在上面挂上一条,上面写什么好呢?我还没有想出来,回头看瞿麦,她已经进到大殿里。看到我,她转身说:“我们上山去吧。”我问她:“不再逛逛了?”她摇头道:“还有要紧事要做。”我问她什么事,她像是没听见似地往前去了。我忽然想她不会是想要跟我表白吧,这种可能性虽然不大,但还是不由得让我心生期待。
二
穿过青阳禅寺后,山显见地陡峭起来,一级级台阶往上曲折延伸,爬了不到十分钟,我开始腿打颤,气直喘。瞿麦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一手扶着山石,一手叉着腰,我跟上去递水给她,她接过。我说:“你包给我背着吧。”她摇手说:“不重。走!”我想跟她并排走,她猛地拽了我一下,脸色都变了,“你别这样!”我吓了一跳,“怎样?”她像是意识到什么,松开手,低头说:“对不起。”我追问道:“你怎么了?”她又抬起头,认真地说:“你别在边上走,下面是悬崖,很危险。”我“哦哦”两声,走到她身后,学她扶着山石。她回头瞥了我一眼,继续往上走。我问她:“以前来爬过吗?”她停住,又回头看我,想了想才说:“有想来过……但没有来成。”见我还在等着她说下去,她抿抿嘴,“说来话长。”叹了一口气,她转身继续往上爬。
说来话长。说来话长。我反复咂摸着这个词。但她显然没想说下去,真是有点百爪挠心的感觉。到了悠然亭,我们坐下来歇息。我递给她小面包,她小口小口地吃着。我又给她水,她连喝了几口。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几个大妈,她们兴致盎然地打量着我们。我想在她们的眼中,我们是今天来来往往的情侣中的一对儿吧。我尝试着靠近瞿麦,她没有做出反应,眼睛也没往我这边看。我的手臂贴着她的手臂,她没有推开,但显然也没有迎合,更直白地说是心不在焉。我的兴致低落了下去。大妈们起身往山上走,等她们拐了一个弯,消失在林间时,瞿麦突然站起来,“我们换条路走。”我讶异地问:“往哪里走?”她指向旁边的杂树林,“这里。”我说:“这里没有路。”瞿麦坚持道:“走。”说完,她已经起身往那里去了。
林间很难走,无数的灌木,扎人的小树杈,蹦起来的小虫子,我甚至想到会不会不小心踩到蛇,但瞿麦毫无畏惧,一个劲儿地往前钻。我拉住她的手,“太危险了,我们回去吧!”瞿麦回头看我,想了想:“那你把铲子给我。你先回去。”我说:“不行。你也要回。”瞿麦把手从我的手中抽了回去,“我不回。我还有事情要做。”我有点生气了,大声地问:“什么事情嘛?非要到这里来。”瞿麦脸色冷了下来,转身就往前走。我跟了上去,“你回答我啊。”瞿麦说:“跟你没关系!你别跟过来了!”我说:“你觉得我会让你一个人在这里吗?”瞿麦忽然停住了,“这话我也说过。”我“嗯”地一声,不知她在想些什么。我们的争论莫名地没有了。还是继续往前走,她在前面,有树枝会弹过来时,她还会抓住让我躲开。
好不容易走到一块稍微空旷的地方,她吁了一口气停下说:“就这里吧。”说着她伸出手,“铲子给我吧。”我取出铲子递给她。她接过来掂了掂,蹲下来尝试着在地上挖了几下。可能是草根太多,抑或是地太硬,挖了一分钟,只挖出浅浅的一个坑。她一屁股坐下来,叹气道:“太难了。”我靠过去,拿过铲子,使劲儿往下戳,作用不大。瞿麦摆摆手,“看来要换个地方。”我问她:“你现在能告诉我你打算做什么吗?”瞿麦抿嘴看我半晌,像是在盘算什么,忽然间又好似想通了什么,伸手拿过双肩包打开,从里面掏出了一件浅灰色男士夹克衫,还有一张照片,递给我,“我要把它们埋了。”
我仔细端详那照片,上面是一对男女站在青阳山景区门口的合影,跟今天我和瞿麦站在差不多的位置。照片上的女子一看就知道是瞿麦,比现在的更年轻,齐肩长发,笑得很开心;而搂着瞿麦肩头的男子,高挑消瘦,面色沉重,眼神死死地盯着镜头。我不由得打了寒噤,“他是谁?”瞿麦把照片拿过去,愣愣地看了半天,眼睛慢慢地湿润了,进而凝聚成泪水滑落出来。她像是扔掉烫手的东西一般,把照片扔到浅坑里。我尝试着问她:“他是你前男友吗?”她点点头。我感觉喉咙发紧,又问:“你们怎么了?”瞿麦坐下来,夹克衫搭在腿上,“我们说来话长。”我也靠着她坐下来,“没关系。反正时间还早。我想听你说说。”瞿麦问:“你真的想听?”我点头道:“我想知道更多的你。”
三
就叫他高高吧,因为你也看到了他比我高一个头。三年前我在另外一家公司上班,有一次公司派我去参加培训,住在一家靠近湖边的宾馆,环境非常不错,培训内容也很轻松,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放松机会。第一天早上,我去一楼吃自助餐,看见一个高个子男生坐在窗边吃饭。这本来没什么,吃完后他没有走开,反而是拿出一本书默默地看起来。那天来吃早餐的人特别多,餐厅里到处都是喧闹的说话声,而他丝毫不受影响,全身心地沉浸在阅读中。这让我有点吃惊。他不是一个很帅的人,搁到其他人眼中,可能就是一个不善言笑的瘦高个,但在我眼中他身上有一种迥异于人的沉静气质。培训课上,我特意坐在他身后。台上的讲师讲什么我没有心思听,一直瞟见他在白纸上耐心地给画的鱼勾勒鳞片。下了课后,他起身走开,我趁人不注意偷偷把那幅画藏了起来。
直到晚上回到房间,我才敢把那幅画拿出来仔细端详。他的画功不错,那条精心画上了鳞片的鱼,游弋在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里,再仔细看,每一朵浪花都是无数小鱼构成的。第二天一早,我又一次在自助餐厅看到他,他这一次换到靠近最里面的位置。我不好坐得离他太近,便选择了他昨天那个靠窗的位置。窗外下着雨,雨水顺着玻璃滑落下来,路上没有一个人。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我抬头看向他那边,忽然发现他也在看我。我忙低下头,再抬起头时,他还在看我。这让我十分吃惊,同时又莫名地有点兴奋。培训开始时,我还是坐在我昨天的位置上,而他的位置却坐的不是他。我忍不住环顾会场找他,扭头看到后面,他就坐在我身后。我“呀”了一声,他抬头笑了一下,我慌忙转过身去。那一整堂课我都有点儿魂不守舍,总忍不住想他在我后面会在做什么。我的耳朵捕捉着后面的细微动静,偶尔有咳嗽、椅子滑动、杯盖磕碰到杯子的种种声音,却分不清哪一个是由他发出的。
下课后,坐我旁边的同事问我要不要去上卫生间,我说好。起身时,我故意没往后面看。等我再次回来时,我的桌子上多了一张纸,翻过来一看,是一个女孩的背部,头发披洒下来,在发梢处画了一朵朵精细的小花。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这是他在一节课中坐在我后面的成果。我转身想要谢谢他,可他的位置却是空的。课上了一半,我假意要去上卫生间,偷偷地溜了出去。我沿着昏暗的走廊慢慢往宴席厅逛过去,清洁阿姨推着吸尘器打扫地毯,发出刺耳的轰鸣声。走到玻璃墙那里,雨依然下个不停。对面的一楼就是自助餐厅,我看到他就坐在那个靠窗的位置,还是在看书,面前还多了一杯水。看来他是不打算来听课了。想了想会场一百多号人,少了一两个人无人会在意。那我也不打算回去了。
走到他桌子前,他抬头看我时露出讶异的神情。我坐在他对面,说:“你画得不错啊。”他脸微微一红,“瞎画的。”我又问他:“你怎么不去上课?”他反问:“你不也没去么?”我笑了起来,他也跟着笑起来。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聊天,却感觉认识了很多年似的。一番交谈下来,我知道他是另外一个区的,目前在一家公司做着和我差不多的工作,再一聊,发现我们居然有很多共同认识的朋友。这不奇怪,毕竟同一个行业,圈子又小,我的同事是他的前同事,他的前上司是我们隔壁组的组长,总之一说都很熟,很多八卦消息也心领神会。如此一来,我们聊得非常火热。聊着聊着,他忽然看向窗外,“雨停了。”我也看过去,“是啊。”他提议出去走走,我说没问题。从宾馆大门走出去,包含雨气的风吹过来,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他说:“去湖边走走?”我说好。到湖边时,又下起了丝丝细雨,可我们走在雨中,谁也不介意。刚才在自助餐厅还聊得起劲,到了这里,却都沉默了下来。谁也没有觉得尴尬,反倒是很自然地看着雨点落在湖面,荡起一小圈一小圈涟漪,荷叶上的水珠随着轻风来回滚落,远处的楼群隐没在雾气中。看了半晌,他低声说:“回去吧。雨大了。”雨珠果然大颗大颗地落下,我们慌忙往宾馆跑。到了会场,他说:“你先进去。我随后。”我悄悄地从后门进去,讲师还在继续讲,没有人留意我。坐下来后,过了两分钟,听到后面拉开椅子的声音,我偷偷笑了。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他的脚触碰到我的椅脚,一下又一下轻轻地叩。
四
高高。麦麦。麦麦。高高。我们习惯这样称呼对方。培训结束过后没多久,我们就确定了关系。平日因为上班的缘故,我们住在离各自公司近的住处。我虽然住在市中心,但是是合租,他过来不方便,所以到了周五晚上,我就去他在郊区买的房子。从十号线倒到九号线,再转三号线,耗时一个多钟头才到,一出地铁口,他毫无例外地就会等在那里,那一刻积压一周的疲累似乎瞬间没有了。回他住的小区路上,我们一起去凉菜店买夫妻肺片、猪耳朵,到水果摊称上两斤时令水果,路过小超市顺带买两包瓜子和一大瓶冰可乐,方便晚上看视频。到了他家,发现高高在我来之前已经把饭焖好了,玉米排骨汤也熬得差不多了。一開始我想着搭把手,但高高不让,“你就踏踏实实地追你的剧。”我也渐渐适应做一个甩手掌柜,一手搂着我们一起养的小黑猫珍珠,一手拿起瓜子一粒粒嗑着。他炒完菜了,才从厨房探头出来说:“帮我端下菜。”我这才懒懒地起身过去帮忙。
高高这个房子不大,四十多平,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还有一个跟客厅相连的小阳台,种满了植物。他喜欢一边浇水一边跟我说:“这是银边绣球,这个呢是龟背竹,你看看这个叶片是不是很好玩?这个叫清香木,那个是花叶蝇子草……”从阳台望出去是铁路,房子不隔音,时常能听到火车开过去的震动声。有时候,高高会拿出两罐冰镇啤酒,我们一人一罐,坐在阳台上,晚风吹过来,也不必说话,就这么看着车来车去,紧接着楼轻微地震动一下,仿佛在召唤着我们也要去远方。
我们的确想去很多地方,在阳台上的那些夜晚,我们说好要去很多地方。泰山、苏州、厦门、东京、巴黎、清迈、奥克兰、纽约、波士顿、青阳山……“那些地方我们短时间内去不了,青阳山离我们这么近,我们倒是可以去一趟。听说那里的青阳寺求签很灵的。”高高说。说走就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往青阳山奔去。他那天穿的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件夹克衫。我们是坐大巴去的,一开始还好,有说有笑的,到了半途,他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微信,脸色随即不好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把手机塞到了口袋里。过一会儿,手机铃声响起,他再次拿出手机,脸色更难看了。我再次问他怎么了,他还是说没事,然后把手机扔到背包里。后面我再跟他说话,他尽量地回应我几个字,但显然兴致不高,我也就没有再说下去了。
到了景区门口,高高闷头要往前面走,我拽住他,提议来个合影留念。拍照时我让他笑笑,不要绷着,他勉强咧嘴笑了一下,随即又垮下脸。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事情惹他生气了,还是工作上上司责难了他,总之进了景区后两边的风景他都没有看一眼,一个劲儿地往前走。我喊他,他停下,等我赶上,他又径直往前走。快到青阳禅寺时,他站在我们刚才路过的那个“上山由此去”的牌子那里与人通电话。因为隔得远,又加上他在说他们老家的方言,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光看激动的手势和拧在一起的脸部表情,我知道他正在跟电话那头的人在吵架。我慢慢靠近他时,他忽然身体立直,挂了电话,脸上恢复成平静的表情。等我站在对面时,他说:“很抱歉,我得回去了。”我问为什么,他回:“我妈过来了。”一时间我呆住了,“啊……那我们回吧。”说着我刚要转身,高高拉住我:“你继续往山上走。我自己回去就行。”
终究还是我们一起回的,高高没有拗过我。坐在回去的大巴上,高高沉默地看向窗外,他很少讲自己的家事,我只知道他是在单亲家庭长大,他爸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是他妈妈带大他的。车子进了市区,我开始有点紧张起来。高高妈并不知道我的存在,为此我跟高高发过脾气的。我一恋爱,第一时间告诉我的爸妈,他们还在视频里跟高高打过招呼。而高高这边,我始终感受不到他家人的存在,他也从未主动提及过。待会儿就要见到高高妈了,我穿成现在这样可以吗?她是什么性格,容易交流吗?我是不是要准备一点见面礼?这些疑问我都需要抛向高高,而他一直冷着脸,浑身散发出“不要跟我说话”的气息。我只能生闷气。快到地铁口时,他忽然开口说话了:“麦麦,你今天先回去吧。我这边的事情有点复杂了,等我处理好了再跟你说,好不好?”我一时间松了一口气,同时又莫名地有点失落。没等我回话,他推我,“你快下!车子要开过去了。”我慌乱地背起包跑下去。我再一次转了多趟地铁回到自己住处,给他发了条微信报了平安,他没有回我。
五
第一天。第二天。无论我发多少微信,都没有一个字回过来。打电话、打视频,都没有人接。我着实生气了。既然他这样不理我,那我何苦去理他呢?第三天,我忍住没有联系他。第四天,坐在地铁上回家时无聊刷手机刷到一些入室偷窃的短视频,心猛地揪紧,“他不会出什么事情吧?”车祸?抢劫?生病?各种不祥的猜想同时涌上心头。尝试打他电话,已经是关机状态了。现在能做的就是直接奔他家去,反正我有钥匙。一番折腾到了他家楼下,抬头看去,每家每户都亮着灯,唯独他家是黑的,我的心沉了下去。走到他家门口,掏出钥匙,就已经听到了珍珠的叫唤声,一推开门,珍珠迫不及待地蹭着我的脚。我一看就知道它肯定是饿了。开灯后,给猫粮盆倒了猫粮,珍珠早已等不及了,埋头吃了起来,也不知道是饿了几天。我叫了几声“高高”,没有任何回应。客厅、厨房、阳台一如既往地干净,等我推开卧室门,一打开灯,随即看到床上躺着一个人,吓得我叫了起来:“谁?”那人缓缓转过身来,我一看,是高高。他一脸胡子拉碴,嘴唇起皮,头发蓬乱得不成样子。我忙过去问他怎么了,他哑着声音说:“关灯。”
虽然拉上了窗帘,屋外路边的灯光还是能隐隐地透过来。我躺了下来,他伸手把我手搭在他的腰上,我明白他的意思,随即抱紧贴着他。火车过去了三趟,屋子也轻微地震动了三次。一路上的火急火燎,此刻都消散了。珍珠吃饱喝足后,也进了房间跳上来,盘在我们的头顶。不知躺了多久,几乎快要睡着的时候,高高慢慢起身说:“你饿了吧?”我“嗯”了一声,他往床边挪去,“我去做饭。”我拉住他,“我去吧。”高高拍拍我的脸,起身出了卧室。我继续躺在床上,珍珠挪到我的手边,我一边摸着它的头一边听着火车开过。两大碗阳春面,我和高高一人一碗,通通都吃完,连汤都不剩。收拾完后,我们一起追剧。该笑的地方他会笑,无聊的地方他也会打呵欠,一切又回到了我熟悉的模样,可是失联的这几天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他都躲避了过去,要么说去上厕所,要么就是叫珍珠别乱跑。我也就明白了他不想说。这个我认为熟得不能再熟的男人,还有一个我完全进不去的陌生世界。对此,我暂时毫无办法。
必须说,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阴影。第二天是周五,我赶回去上班,在地铁上我给他发了微信,“你以后不许这样无缘无故地消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要跟我说。你要答应我。”他很快就回复了我,“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这样了。”当晚,他来到公司楼下等我,我问他怎么过来了,他笑笑说:“今天就别再跑那么远了,怪累的。”我们一起去美食一条街吃了烤鱼,又去看了一场电影,晚上就到我的租房睡。到了半夜,迷迷糊糊间感觉到他辗转反侧,我起来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咕哝道:“有件事想跟你说。”我开了台灯坐了起来,他也坐了起来,“我要不搬过来住吧?或者我们再一起在市区另外租个单间。”我问:“你不住自己家了?”他沉默了片刻,才说:“那不是我家。”见我露出讶异的神情,他声音小小地解释道:“那是我妈在我读大学时就给我买好的房子,她出的钱,所以那是她的房子。”我一時间有点糊涂,“既然是给你买的,不就是你的房子么?”他略显烦躁地皱了皱眉头,“我不想住那里了。我想搬出来。”我接着问:“可是你要是住我这里,上班就远了呀。”他躺下来,“我一周没去上班,他们也联系不上我,已经把我辞退了。”
很快,他就回去收拾好东西搬了过来,连带珍珠也一并带来。我的房间太小了,我的东西,加上他的东西,没办法住得舒坦,又加上其他室友对我们养猫的事情不是很欢迎。高高又另外在离我公司更近的地方整租了一个房子,搬家,搞清洁,安热水器,购买书架,添置锅碗瓢盆,全是他一个人搞定的。搬过去后,每天他都早起做好早餐,中午做好一桌子菜等我,晚上更丰盛,他总是能掐好点等我一进门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我喜欢看他系着奶黄色卡通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场景,喜欢灯光落在他浓密的头发上,喜欢他端菜时眉开眼笑的模样。我对我们的未来生活有了切实的向往。有时候我加班到很晚,他会带夜宵过来给我吃,还会细心地给跟我一起加班的组员带来点心。等我忙完下楼,我会习惯性地搂着他的手臂沿著河边步道慢慢地往家里走去。
他没有急着找工作,我出门上班时,他就在家里看书,接一些写稿子的碎活。有一次下午三点多我发现有一份要紧的文件放在家里了,本来想让他送过来一下,又担心打扰他写稿,便自己跑回去了。一开门就吓一跳,他站在鞋架面前发呆,我问他怎么了,他抬头见是我,慢慢地说:“我想下去买菜。”我又问:“那你怎么不穿鞋?”他转身往客厅走,“我不去了。冰箱里还有菜。”见他神色如常地坐在电脑前面又开始写稿,我虽然有点说不出来哪里有点不对劲,可还是上班开会要紧,就匆匆离开了。另一次是公司团建结束,我提前回家,饭桌上有剥了一半的豌豆,地面上的快递盒也罕见地没有收拾起来,手机躺在地上,我捡起来一看,手机屏幕已经裂开了。我叫他,没有回应。去推卧室房门,已经反锁。我担心得喉咙发紧,大声叫他,还是没有回应。没办法,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把门撞开,由于窗帘拉上了,室内一片黑,床上没有他,我又推开衣橱门,还是没有,结果在床与窗户之间狭小的空地上发现他躺在那里。我把窗帘拉开,阳光猛烈地涌进来,我打量他全身,没有受伤的痕迹,呼吸也是正常的,这才松了一口气。我拉起他,他睁开眼,红肿肿的,愣愣地看我半天才回过神来,勉强地笑了一下:“回来了?”接着又陷入呆滞的状态中。
如果我没有这两次的突然回家,那我对高高的印象就是那个下班后等我回家的贤良男朋友,温柔体贴,阳光开朗,而对他另外一面毫无察觉。我甚至觉得他一直一个人在对抗着什么,为了不让我担心,他从不告诉我。可我是他最亲的那个人,如果不把他从那个看起来很可怕的世界拽回来,我就会失去他。我没有办法想象没有他,我该如何度过未来的日子。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才很不情愿地跟我去了安定医院。等叫号时,他突然站起往外走,我拉住他,他叫道:“我没病!我知道我的原因!”任我如何劝说,他都不愿再返回医院。回去的路上,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你可以跟我说吗?”他头侧向一边,不看我,“说了也没用。你们帮不了我。”我被“你们”这个词刺激到了,气得眼泪都出来了。他冷冷地绷着脸,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我生气时抱我的动作。我们一路沉默地回到了家,他又一次恢复到我熟悉的那个高高,系了围裙,开火做饭,仿佛之前的不愉快根本没有发生过。
六
手机摔坏了,高高给自己换了一个新手机,手机号码也一并换了。我说:“你不怕别人联系不上你么?”他回:“也没有什么人联系我,我也不想联系别人。”他往新手机里熟练地输入我的手机号码,“我只记住你的就好。”我白了他一眼,嫌他油嘴滑舌,心里又莫名地开心。不过我已经没有过去的安全感了,总感觉太阳穴突突跳,有时候担心得不行,趁上班的间隙溜回家看他,每次他都好好地坐在那里写东西,我只得假装回来拿个东西灰溜溜地回公司。晚上睡觉半夜醒来,睁眼去看他,他正在看着我,这让我吓得不轻。我问他怎么不睡,他说睡不着。有时候醒过来,他那边是空的。下床去找他,他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有一瞬间,我怀疑他会跳下去,随即我整个身体动弹不得,生怕发出一丁点声音,害怕会刺激到他。等他回转身来看到我并走进来时,我才松弛下来,蹲在地上大口地喘气。他也蹲下来,双手环绕住我的脖子,“你哭了?”我没有力气站起来,身体发软。他柔声说:“我只是出来透个气。”我拽住他的胳膊,十分严肃地说:“你要答应我,不可以做傻事。”他声音更小了,“我答应你。”
我请了年假,策划了一次云南行,订好了路线和住宿,买好了机票,拽着高高冲到了机场。飞机起飞时,他紧张得闭上眼睛,一只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我笑他居然还有恐高症。等上了平流层,他才完全松弛下来,一路上都在睡觉。这是这么久以来他第一个安稳觉。空姐来送飞机餐,我没有叫醒他。瘦削的脸庞,淡淡的眉毛,薄薄的嘴唇,因为长期失眠导致的黑眼圈,他的手软软地搭在我的手上,有时候手指会微颤几下,兴许是梦中遭遇到过什么。我进不去他的梦,也进不去他的世界,为此沮丧过,也生气过,而此刻,唯有心疼。下了飞机,我精心安排的计划一项项都实现了。去大理骑着电动车环绕了洱海一周,到苍山上的寺庙吃了一顿美味的素斋,在丽江的酒吧一边喝白啤酒一边听乐队弹唱,在腾冲的乡间小路骑着自行车吹风,沿着普者黑热门电视剧拍摄地的湖边拍各种照片……高高也渐渐从那种要死不活的状态慢慢地“活”过来了。我们从一地玩到另一地,累了就在民宿里待着喝茶,歇息够了游山玩水直到天黑。直到旅行的最后一天,我们沿着木栈道爬上了山巅,高高亲了我一下,“谢谢你。”我笑着问他:“就这些?”他又亲我一下,“我爱你。”
晚上回去时为了方便赶第二天早上的飞机,我们订了一家离机场近的快捷酒店。高高负责拖着行李箱,我负责导航。街口大排档有四五个人在那里喝啤酒吃烤串,高高问我:“想不想来两串?”我嫌那里脏,“还是快点到酒店早点休息吧!”沿着街边走了五十米,再拐上另外一条路灯坏掉的暗街,穿过臭气熏天的胡同,到了导航所说的位置,却没有发现酒店,只有一排拉上闸门的小饭店。高高问:“是不是定位错了?”我把手机递给他,“没错啊,就是这里。”高高拿出自己的手机打开导航,显示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随即往那里走,又一次经过大排档,还是那几个人在喝啤酒吃烤串,然后拐到另外一条小路上,走着走着到了导航的目的地,又是第一次那一排小饭店,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方向。再一次导航,再一次经过大排档,还是那几个人,再一次走到小饭店……就像是陷入一场迷魂阵一般,怎么都走不出去。站在小饭店门口,我握住高高的手,他在发抖。我说:“我们再试试。”高高声音都在哆嗦,“我总觉得今晚这些早就在我梦里发生过,无论我怎么逃跑,最后都还是回到了原地。简直是一模一样……”我感觉一阵骇然,拽住他,“不管酒店了!我们走!”高高问:“去哪儿?”我说:“反正赶紧离开这里。”
再一次走到街口,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大排档那一桌人已经走掉了,老板正在收拾桌子。我也不看导航了,径直往马路对面走去。高高喊着我,“我们要往哪里走?”我回头环顾了我们盘绕了好几个小时的街道,“我们是鬼打墙了,不要再待在这里了。”高高乖乖地说好。我们径直往前,一直找到一条灯火辉煌的大路才略微松了一口气。没有出租车经过,手机软件上也叫不到车,我们只能往机场的方向徒步。高高拖着的行李箱,在空空荡荡的马路上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我当时只顾着往前导航,他忽然跑上来牵住我的手。我问他:“怎么还怕呢?”他咕哝道:“哪有?”我笑道:“手心上全是汗。”他要把手收回,我一把捏住,“别跑。”他小声地回:“我没想跑。”我朝他瞥了一眼,他脸颊消瘦,胡子没刮干净,鼻尖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我心忽然莫名疼了一下,忍不住伸手摸摸他的脸。他把脸的另一边也转过来,“这边也要。”我笑着推他,“不要得寸进尺!”
回到家后,高高的状态明显好了很多,睡眠也好了,笑容也多了。我松了一口气,上班时也不用再找借口往家里跑了。一个月,两个月……时间就这么平淡如水地流下去,直到我生日的前一天。还是一如既往地下班回家,打开门时,高高坐在沙发上,我问:“今天检查煤气的人来过了吗?”他绷着脸坐在那里没有动,也没有往我这边看,双手紧紧地抓着膝盖。我走过去,见他右边脸上红肿一片,“这是怎么了?”他说:“我妈打的。”我起身环顾四周,“她来过了?”他回:“她走了。”我拿冰袋让他拿着敷上,他听话地接过去,“她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你不是没告诉过她吗?”虽然高高很少谈起他家人,我大概也知道他一直以来是想躲避他家人的。高高想了半晌,“她肯定是盘问过我舅舅,才一路找过来的。我把我们的事情告诉过舅舅。他从小对我就特别好,我很亲他。”经过一番询问,我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高高妈妈找过来时,高高正好在家,他妈一见他就狠狠地打了他一耳光,很可能是生气他躲了这么长时间的缘故。两人在家里大吵了一架,直到他妈妈气得哭起来,说不认这个儿子了。高高说那正好,正好一刀两断,大家都不要再有联系了。他妈妈一听这话,气走了……他一边断断续续讲着,一边簌簌落泪。我搂着他,给他递纸巾,他也不接,只是紧紧地攥着我的手。
过了两天,我正在上班,他忽然发微信给我,说他要回老家一趟。我问原因,他说:“我舅说我妈住院了。”我立马打电话过去,他正在收拾东西,我让他等我,“我跟你一起回。”他死活不同意,我只好作罢。他走了一周,除了飞机落地时给我发了一条报平安的微信之后,就杳无音讯了。我又一次回到抓狂的状态,发了很多微信和语音都没有回应,给他打电话没有人接,到后面甚至关机了。我没有心思工作,晚上睡着会忽然惊醒,头发也开始大把大把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想去他家看看,可他从未告诉我他家的具体地址。说来真是好笑,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我没见过他家人。我想让他见我家人,他也拒绝了,说没有准备好。为此我跟他吵过几次,他都会露出小动物受伤般的无辜神情,让我吵不下去。我预想过很多种可能:他忙于照料他妈所以没空理我,他的手机被偷了,他生病了……夜里睡不着时,我把衣柜打开,里面挂着他的衬衣,是我送他的生日礼物,他穿过几次去应聘面试,我贴着衣服深深闻了一下,没有捕捉到任何一丝熟悉的气味。
七
第十天下午,我正在上班,忽然有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对方自称是高高的舅舅,问高高有没有联系我,语气听起来非常着急。我立即起身,对组长说家里有点事情得回去一下,连包都来不及拿就往家里跑。高高舅舅在电话里告诉我,高高妈妈确实生病了,高高回去后发现没有住院,跟他妈妈大吵了一架,这一吵他妈妈真的气得住院了,高高也深受刺激,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谁都不见,谁敲他门,他都说不要烦他。高高舅舅没办法,只好两头跑动。今天他打算给高高送点吃的,敲了半天还是没有回应,他忽然感觉有点不对劲,想办法把门撬开,高高却不在里面了。也没办法打电话,因为高高手机就在房间里,且是关机的。他很担心高高会想不开,因为之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还好发现及时救了过来,所以想到给我这边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到家后,我一边叫着高高,一边跑到厨房、卧室、阳台,甚至卫生间,都没有高高回来过的痕迹。我想立马买票赶到高高的城市,高高舅舅让我别急,“没准他这几天就回去了。”说的也是,我只好等在家里,哪里也不敢去。我加上了高高舅舅的微信,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都没有等到高高的消息。第三天,高高舅舅发来一段语音,“小瞿,高高找到了……派出所的人调了监控看,他跳河了……今天我去看了,是他……”后面是哽咽的声音。我没有回复他,只是坐在沙发上,珍珠过来躺在我的大腿上,我摸着它温热的身子,心里没有任何波动。阳光照过来,玻璃桌子像是一汪闪着金光的湖面。街上的鸣笛声,楼下孩子弹古筝的声音,窗帘随风拍在墙壁上的噗噗声,每一种声音都如此真切地灌到我的耳中。而我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人坐在这里,一个人飘浮在半空中看着自己,懈怠的、麻木的、无知无觉的,发呆。
很奇怪,我又回去上班了,下班后跟几个相好的同事去聚餐喝酒。她们问高高人呢,我也毫无波澜地说高高回家照料他妈妈去了,甚至还兴奋地提及高高写完的几篇文章都在杂志上发表了,等他拿到稿费一定请大家吃饭。大家都说好哇好哇。聚会散后,我回到家中,喝得晕晕乎乎的,倒頭就睡,第二天爬起来又开始新的一天。到了周末,趁着太阳正好,把冬天的衣服都拿出来晒,高高的高领毛衣、驼色风衣和羽绒服挂在晾衣杆上,等他回来再给他添置一点新衣服,这些都旧了。是的,我觉得他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毕竟他的电脑还在书桌上,他的三双拖鞋在鞋柜的中间一层整整齐齐地摆着,阳台上的花花草草长得可好了,冰箱里他买的冻牛肉还没开包……第七天,高高舅舅发了一段话过来,“葬礼在后天,你要是想过来的话,这是地址。”
夜色一点点淹没我,我像在深幽的水底较劲地往前行走,一直走到江边,没有路可走了,这才止住。我趴在栏杆上,看着江水浩瀚无声地流动,从上游漂来的枯树枝在江中央打着旋,忽然想起刚认识他时他画的那幅画,那条精心画上了鳞片的大鱼,游弋在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激起无数小鱼构成的浪花……但我忍住不去想,极力地把要冲开的心闸合上。高高舅舅已经被我甩到一边去了,我唯有把这憎恨抛给那个不肯露面的高高。他没有留一个字,发一个语音,打一个电话,决绝地要把自己抹掉,去做一条鱼?我不接受,也不相信。带着这一腔憎恨,我回到了家,倒头就睡,一沾枕头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之中感觉到有一只手从我的腰间滑过,小心地搂着我,脖子处有呼出的气息萦绕,慢慢地身体贴了过来,暖暖的,软软的,我没有转过身,而是任由这熟得不能再熟的搂抱持续下去,我心底滋生出一阵阵甜蜜感,甚至想着明天早上的早餐可以做什么。不知何时睡着的,睁开眼时,还是黑夜,房间里寂静得能听到自己猛烈的心跳声。“高高。”我喊了一声,“高高,高高,高高……”我一连串地喊起来。声音迅疾被夜色吞没了。我莫名地害怕起来,缩成一团,靠在床板上。
我知道,高高真的走了。
尾声
我们真得走了。天色暗了下来,景区恐怕也快要关门了。瞿麦站起来时,腿软了一下,我赶紧扶住她。看着她手上的夹克衫,我说:“算了,还是留着做个念想吧。”她想了片刻,慢慢地把衣服叠好重新放入背包,小铲子也不要了。好不容易从树林里钻出来,站在悠然亭,我大大地吸了一口气。瞿麦讲的这些,像一块大石头一般沉沉地压在我的心头。陆续有下山的游客从我们身边经过,他们说着笑着,拄着登山杖往山下去。我感激他们的出现,让我得以回到现实世界。我跟瞿麦说:“咱们也下去吧。”瞿麦往山上看了一眼,“来了两次,没有一次上去过。”我说:“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刚一说完,我觉得自己有点冒失,但瞿麦没有在意,或者说她的心根本不在这里。说了太久太多的话,她现在沉默不语,我递水给她,她摆摆手。走到一个开阔处,游人们纷纷止步,拿出手机和相机拍照。远处的山峰浸润在绯红的霞光中,一枚浅浅的新月浮了上来。我兴奋地想让瞿麦快来看,她早已静立在旁边,双手抱胸,眼眶蓄泪。我想也没想,搂住她。她没有推开。
穿过青阳禅寺,再一次经过“上山由此去”的牌子,瞿麦停住脚步,轻柔地摸着木牌说,“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高高妈妈打过来的。她想要过来,把高高的东西收拾一下带回家。我说我可以打包好寄给她。她半晌没有说话,但我听得到她在那边哭。我想安慰她几句,她突然说高高就是一个自私自利、残酷无情的人,她决不原谅。我那一刻特别想跟她吵架。她不觉得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吧?高高那么努力地想要逃离出来,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她拽进黑洞。我没见过她,但我见过高高接她电话时浑身发抖的场景。我没有能力把高高救出来,他……也没有给我这个机会。高高妈妈还在继续骂,但我不想再听了,挂了电话,直接拉黑。我把高高的衣服、书籍和各种杂物收拾好,向高高舅舅要了郵寄地址,唯独留下了这件夹克衫。我也退了租,辞了职,搬离了那个地方,直到找了新的工作……”我接口道:“后面的我就知道了。”她看我一眼,淡淡地一笑,“我们快点下山吧。天黑了。”
【作者简介】 邓安庆,生于1984年,湖北武穴人,毕业于襄樊学院;曾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读库》等刊发表作品,著有《纸上王国》《柔软的距离》《山中的糖果》《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天边一星子》《永隔一江水》等书,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意、西班牙、丹麦等多种语言;现居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