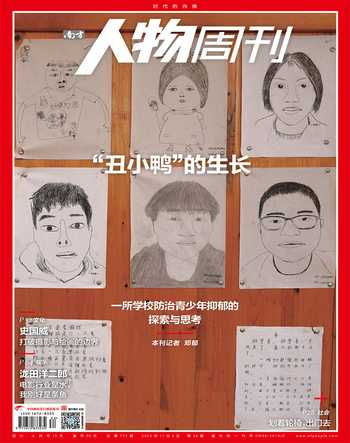走,去大自然
2023-12-29杨楠
这两年,我时常怀念一个或许并不存在的昨日世界。就好像茨威格形容他的父辈,被理想主义蒙蔽的一代人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坚信宽容和友好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真诚地认为各个国家及各个教派之间的界限和信仰的分歧,将会在人们的友善中逐渐化解,整个人类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和平与安全。
种种原因,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群,了解各式各样的思想,在沟通、靠近、了解、解释。而就像我的同事M所形容的,时常会想“即时退出人类社会”。每当此时,我就会做一些和人类无关的选题,动物或植物,大河或高山。无论大象出走还是洪水泛滥,无论冰川消融还是山林火灾,这些都折射出人类的渺小和愚蠢,人类的退让与自救。
这便是我想报道珠峰科考、冰川消融的最初动机。简单地说,连珠峰都能测出DDT(有机氯类杀虫剂)了,连东绒布冰川都在节节败退了,对于喜马拉雅这座横跨五国的年轻山脉,人类难道不该搁置偏见与分歧,互相信任合作么?也确实,在采访中,冰川研究者普遍把世界视为一体,面对自然,面对宇宙,争端与冲突都失去了意义。
尽管,全球变暖不仅关乎环境,也关乎公平。最脆弱人群和生态系统遭受的损失和损害尤为严重,也正在承受与自身责任不相称的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如同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张“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大讨论,意图在文学中剥离立场本就是一种立场,意图超越意识偏见去记录科学工作,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意识的选择。
兰州和西藏的采访,在我面前展开的是开阔的世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些在中国西部从事冰川研究的科学家热爱野外科考,部分原因就是热爱自由,追求潇洒的生活,他们能够忍受在珠峰脚下驻扎十年的艰苦,也是他们不吝啬时间,有能感知到地球脉动和珠峰壮阔的幸运。
有回晚上采访,我们坐在兰州大学的操场上,受访者跟我说,有时候还挺同情你们大城市人,那么多压力,永远走不出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我突然想到印象派的诞生:经历了工业革命的都市人,开始厌弃弥漫着工业雾霾的伦敦,向往田园与大自然。而后脱胎于印象派,又诞生了更为自由的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中国也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今天的国人,是否也向往自然与田园?向往离开小环境或大环境里的冲突与争斗?这是否会催生新的文化形态?
说回对全球变暖、冰川消融的关注。我心里过不去的愧疚是,记录一些研究冰川、感知地球脉动的人以科学证实人类活动剧烈地伤害了环境,好像谈不上是关注环境变化。
但最近,我读到了一段金国威的创作阐述,感到有所安慰甚至自洽。他是以拍摄《徒手攀岩》、《泰国洞穴救援》享誉全球的纪录片导演,他说:“我喜欢拍摄人性积极的那一面,那些能激励我们变得更好的品质。我有很多朋友拍摄人性的另一面,战争、冲突、争议。很显然,我还没有拍过这种主题的作品。世界上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灰心的事,让人悲伤,让人愤怒,我希望试着制作能与之抗衡的作品,我想这是我能为世界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