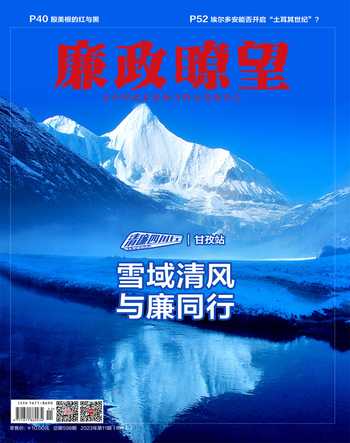梁中和:“爱,美与死亡”教育,让生命找到着落
2023-12-29王巧捧
“今天你们看天了吗?”
梁中和上课,喜欢问学生这种“题外话”。
这样的“题外话”在他看来,暗藏着生命哲学教育的理念。
作为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梁中和与团队开设的“爱,美与死亡”生命教育通识课,最近颇为出圈,课题内容映照进当下诸多现实和精神话题。
近日,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深度对话梁中和,一溯生命教育的内涵以及在当下的意义。
个体化时代,内倾严重
廉政瞭望·官察室:请问梁教授,你们的生命哲学教育课,为什么选择“爱,美与死亡”的主题?
梁中和:我们这门课,是川大百门通识教育课中的一门。我和团队的老师认为,生命教育不是单一的内容,我们选了爱的教育、美的教育和死亡教育这三个重要方面,希望引导大家在爱的行为中,去找到生命的动力。这爱,不是普泛意义上的爱,而是对于美好事物、对真理的追寻。
孔子强调,没有必要去谈论死亡,是因为我们不可能获得关于死亡的任何确切知识,这是我们先民的洞见之一,但是我们可以追问死亡,从而迫使大家思考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美、什么是爱,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在美的阶梯理论上,美从个体的美、群体的美、美的行为、美的学问到美本身,有五个阶梯。在这样的阶梯攀爬过程中,去爱、去拥抱美的、好的,能让我们发现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意义、对美好的感知等等,从而获得共在感,发现生命并不孤单,让生命找到着落。
廉政瞭望·官察室:为什么想要做生命哲学教育工作?在当下社会环境下,生命哲学教育的意义有哪些??
梁中和:现代性的危机下,以前那种高度熟人化的传统社会,逐渐在消失,个体化趋势增强,人和人之间直接的沟通变少;自我理解、自我认同加强,对他人的理解变少;对生命意义的挖掘,内倾更重,外向更弱。个体主义使得人们强调个人空间,追逐个人权益,在乎个人感受,这种倾向导致很多问题。
我听一个男生讲过一件令我惊讶的事。他们寝室4个男生,入校第一个月互相没有说话,他们在相互观察,观察室友喜欢打什么游戏,喜欢哪个明星,几点睡觉,甚至是洗澡频率、挤牙膏的习惯,默默地观察,然后才慢慢相互说话。
这其实是个体化精神进一步演化的结果,个人心理空间的需求随之放大,心理保护机制越来越强,造成内在化的自我愈发严重。
廉政瞭望·官察室:个体化的发展,主要受哪些方面影响?
梁中和:现代社会发展中家庭关系的演变,以及网络的推动,对个体化趋势都影响较大。
现在的父母之爱到什么程度?我还曾担心学生是否经常和父母联系,有次早上8点的课,我问一个学生最近一次跟父母打电话是什么时候。我还想找个例子“批评”一下,但是,学生的回答让我意外了,他说就刚才。“我一醒,我妈就给我打电话,说宝贝今天天气怎么样?冷不冷?你今天吃的什么?心情好吗?”这种电话,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另外一个学生,每天下午5点固定时间跟爸妈通话,汇报当天所有的学业内容、人际交往情况。
还有一个学生跟我抱怨,奶奶去世的时候,他在高二,父母说你好好学习,不用去参加奶奶葬礼了,我们会办好的。硬生生被切断了这份亲情,他感觉自己好像除了学习,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去做。

网络对人的异化更显而易见。
听学生反映,寝室室友不再是亲密的朋友。我向一个读社会学的学生求证,她说,她们室友之间非常客气,但是不交心。那心事向谁倾诉?网友。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不知道高矮胖瘦,但一切苦恼、心里话,什么都聊。所有一切在匿名下,可以放开聊。
包括现在的视频,你一打开手机,“好帅、好美,好好笑,故事曲折离奇”,什么都不用干,不用动,就能获得多巴胺快乐。“上瘾机制”把人吸引在手机上,对外的交流、人际的接触变少,人性的部分,被机器化了。
廉政瞭望·官察室:个体化对个体的生命认知有影响吗?
梁中和:个人的喜怒哀乐,发在网上,变成很小的一个数据条,淹没在浩瀚的数据海洋中,泡都不会冒一个。人的情绪不再是具体可感的,没有人承托,得不到很好的安抚,人的价值感、存在感会强吗?
还有,如果父母关怀备至,包办一切,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孩子的情感需求,那他就没有什么空间去承载别的感情。另一方面,父母付出的越多,年轻人看在眼里,越不想过父母那样的生活,不愿意结婚生子。
现在很多学生甚至不愿意谈恋爱,觉得费事。即使恋爱,时间也非常短,谈两周、谈几天的,很多;超过几个月的都不容易。有个学生还跟我讲,恋爱这个事情你不能主动,一主动,陷入恋爱脑你就输了。
爱情是输赢的事吗?这种思维还是自我、小我在作祟。社会个体化的结果,每个人权利义务的单位都是个人,让个体更关注自己的利益、得失。这方面还有一些让我很意外的情况。
有次上课,我请一个同学发言,然后我说的时候,他补充了一句。下课以后学生突然跑过来,给我90度鞠躬,他说:“对不起,老师,您刚才讲的时候我插嘴了。”另外一个同学回答问题后,下课找我说:“不好意思,老师,刚才我是不是惹你生气了?”
他们都回答得很好,不需要道歉,我也没有生气。孩子们担心老师的情绪会影响对他们的评价。
打破边界,走出自我世界
廉政瞭望·官察室:个体化是一个时代趋势,那我们的生命哲学教育对此能做什么?
梁中和:个体化的结果,让人的边界感非常强。我们上课的内容、包括组织的观影,围绕爱、美与死亡的主题,就是试图打破这种僵硬的边界感,让人体会到更重要的是人与他人、与这个世界的连接,去发现我们和他人共通的东西,去发现给我们带来更多感动的是人,而不是物品。几万块钱的包再精美,你就天天抱着睡又怎么样?那种快感很短的。真正耐人回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美好。
但是也有人困于人际的一些麻烦,不敢付出真心。最终的原因还是“小我”在作祟。过度的自我认同,容易造成根基的缺失感,所谓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在哲学上看来,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容易导致抑郁。当人完全陷入在自己的世界里,又没有办法成为意义的源泉时,抑郁就容易产生。
廉政瞭望·官察室:那个人如何突破这种困境,突破“小我”,找到人生的意义呢?
梁中和:意义的源泉,不应该限定在自己的“小我”里。有两条路可以去发现,一条向外的,接通自然万物,感受万物共生的状态。另一条是向内挖,但是不能只挖自己的小我,而是通过“我”的灵魂认识到他人的灵魂,人共同的灵魂。我们中国人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但是,有些年轻人认知范围非常局限,生活体验缺乏到什么程度?有次给大一新生上课,我问他们坐公交的体验,作答的学生挺笃定的,他说:“我坐过,高考完以后我体验生活去坐了一次。”
很多孩子没有尝过人间艰辛,甚至没有见过。我带学生赏析《三峡好人》电影,请一名本科生——19、20岁的样子,谈下观影感受。这个男生站起来,说,这个电影好,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我问魔幻在哪?他说光着膀子砸墙那些,很魔幻,现实里哪有这样的?
他们也不习惯人和人近距离接触,特别是疫情这三年来,00后这批学生,他们不喜欢任何身体接触。以前男生之间拍打嬉闹、勾肩搭背,现在的他们很介意。
这个其实就是缺乏向外的、和万物间的联系。天天钻在自己的世界里,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容易走不出来。
所以,鼓励他们看天,其实就是在跟万物建立联系,让自我放大。我们这门课,集合了13门学科,除哲学以外,还有社会学、政治学、法医学、动画专业等方面的专业老师,从各个学科的视角,带大家展开视野,多方面启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做激发人性的教育
廉政瞭望·官察室:你说要做激发人性的教育,为什么觉得需要激发人性?
梁中和:在学生中我发现,现在的他们可以很好地完成一项任务,但很少有人知道自己要干嘛。本来有一些孩子有自己的梦想,但是被家长掐灭了。
有次课上,我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被抽到作答的,是个工科专业女生。出乎意料,女生站起来,直接哭了。平复好心情,女生擦了擦眼泪说,自己其实喜欢画画,但是父母说工科才好找工作,她没办法,现在学的东西不喜欢,喜欢的东西没时间做。达不成自己精神上的追求,内心分裂,是最痛苦的。
还有个学生,他在高中时候曾经讨厌费孝通,因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教材内容,有各种对应的题,有标准化的答案,你得按照条条框框写。但是到了大学之后,不需要考试了,重新再读费孝通的书,他却喜欢上了。
在工具人的意义上学习,根本无法感受知识的魅力、内在价值。
有一天我在江安校区上课,大玻璃窗外,一个橙黄色的落日悬在那。我请同学们看夕阳,抽了一名同学说说晚霞有几种颜色。刚好这位同学是学艺术的,说得很细,其他同学跟着一起看,发现还真有紫色、蓝色、黄色、粉色、灰色,很佩服他。
但这名同学叹息学艺术没什么出路。
“你能回想起当年为什么学美术吗?”我问他。
他学美术的初心,是感受这类美,但是被工具化了以后,忘记了当初对这门专业动心的原因。
意义的源泉,不应该限定在自己的“小我”里。有两条路可以去发现,一条向外的,接通自然万物,感受万物共生的状态。另一条是向内挖,但是不能只挖自己的小我,而是通过“我”的灵魂认识到他人的灵魂,人共同的灵魂。
这也是整个社会的现实。当下的人们,困于功利思维,不想或没空去探索生命意义的方方面面,精神力长期处于耗损状态而缺乏补充,内心焦虑、不安,无处安放。
廉政瞭望·官察室:在激发人性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梁中和:课堂上,我们会潜移默化地去影响他们。我给华西的学生上中华文化课时,跟他们半开玩笑说,我以后去医院,你们要把我当个人看待,不能把我当数据、当机器。这是我的忧虑,也是趁机激发他们人性的一面。
我们也组织一些对社会开放的读书会、观影会,在家庭教育方面,做一些培养社会柔性良知的工作。
我们有读书会“亲亲与爱人”。古人说,“亲亲为大”,我们与亲人的亲密关系是最大的,是所有爱的源头,这个读书会就是针对家庭教育的问题,组织川大一些老师带着小朋友和家长共读儿童书,提升亲子关系。
还有亲子观影会,观影结束我会采访小朋友,小朋友会说很多真相出来,他们父母就在现场坐着,有时候还有点尴尬。这也是借机让家长听一听孩子的心声,希望能影响家庭教育,少一些功利性,软化亲子关系。
这些活动,也是用各种方式来促进人和人之间的直接交流,而不是线上的交流,对培植原本的人性的东西会有好处。
发现和赋予生命意义
廉政瞭望·官察室:你在课上强调,生命哲学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讲授知识,那在知识之外,还讲授什么?
梁中和:我以前上中华文化课,有个学生在大四最后一节课,专门过来感谢我。他是经济学院的,他说,这4年来这门中华文化课对他影响最大。为什么?“因为,”他说,“您这个课是唯一一门提到让我做好人的课。”
我在课上说,你们要做个好人。他很感激这句话。但是他做个好人的选择,是我给他种下的吗?不是。是他心底有这个呼声,想做个好人,本来就有向上的力量,但没有得到外在的呼应,他在这个课上得到了,他的良知在这儿得到认可,“原来我想做个好人不傻不笨不错,是对的。”
因为大学的专业课都是讲授知识,所以我说我们这门课,不仅仅是为了讲授知识,更重要的在于引导大家对美的热爱,发现生命的意义,从而热爱生命。

廉政瞭望·官察室:你们的生命哲学教育,不仅局限于学校范围,也在社会上多方推动,那生命教育对当下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梁中和:当下社会上的焦虑情绪比较严重,想寻找确定性但是又没有办法的那种焦灼,没着没落。最近热播的网剧《漫长的季节》里那句诗,“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也给我这种感觉。
从根本上说,如果生命的价值建立不起来,那么外在的物质、钱财、权力,都没有意义。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但生命的意义不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向外面找,而是自我赋予的。我们的生命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发现和自我赋予意义。
我收到毕业几年后的学生写的信,匿名的,感谢我当年讲的内容。工作之后,回味当年所学,他感激的是激发他价值感和信念感的人。
这就是我们生命教育的意义,激发人们的价值感、信念感,呼应人们心中的良知、善念,激发他寻求意义的冲动。在各种喧嚣中,我们哪怕只发出一小点声音,总比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