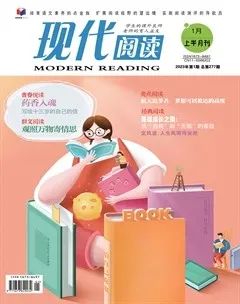一蓑烟雨 任平生
2023-12-29方慧颖
美文赏读
有人曾说,苏轼的一生,不是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
可无论他被贬谪到哪里,他的诗文中永恒不变的基调,是豁达。
写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苏轼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可在那低沉中不乏昂扬、悲凉中却饱含达观的诗句里,我们已能看出他一生的处世态度。
去小城密州做太守,他写《超然台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被贬海南岛时,他已经六十多岁,眼睛花了,看不清东西,可他说:“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
人生缘何不快乐?我特别喜欢苏轼的那首《东栏梨花》:“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苏轼的一生起起伏伏,颠沛流离。元丰二年(1079年),他因为“乌台诗案”被羁押,那是一场可怕的政治风暴。即使一生洒脱的他,也写出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这样凄惨的诗句。被贬黄州之后,他惊悸的魂魄才慢慢地平定下来,并且慢慢地寻回了生命中的那份淡泊。
大概是在黄州三年之中的一个春天,他与朋友相约踏青,却在途中遇到大雨,一行人都没有随身携带雨具,自然是被淋得狼狈不堪。在众人的埋怨声中,唯有苏轼气定神闲,且行且赏,一人在雨中享受着春雨、春景、春情。人生的疾风骤雨都没有将他摧垮,这样的天气又能耐他何?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他选择了《定风波》这一个词牌,简直是再合适不过。
词前小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多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一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舒朗轻狂的心境,溢于言表,颇有点“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意味。根本不像是经历过政治浩劫之人所抒发出的情绪。也许正因为有了“乌台诗案”的磨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才能够有这般旷达超脱的襟怀。
因为被这场文字劫难所牵连,苏轼的好友王巩甚至比他更加凄惨落拓。黄州虽远,荆楚大地到底还算得中原,王巩则是直接被贬谪到了岭南宾州,相当于今天的广西宾阳一带,崇山峻岭,烟瘴重重,委实受尽了折磨。苏轼对此深为内疚,常常寄信慰藉。他倒也没有一味低头道歉,而是总会找一些有趣的小话题来调节气氛,比如抵御瘴气的偏方、养生安神的道理等。他甚至毫不客气地说:“要是方便的话,麻烦帮我捎十两丹砂过来。”所谓“人以群分”,天性乐观的苏轼交友总不会太过小家子气,这两人的书信在今天看来虽显得漫无边际,仿佛最寻常的聊天记录,但却一点也没有因为山高路远、通信艰难而吝惜笔墨。多年后,当他重蹈王巩的岭南迁谪之路,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一直在耳畔回响,让他有些浮躁的心平静下来,就此决定“不辞长作岭南人”。
仿佛“乌台诗案”带来的政治风波注定是需要《定风波》来平定似的。与苏轼并称“苏黄”的黄庭坚也是受牵连者之一,被贬黔中。在天阴湿冷的边陲之地,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也写下了一首《定风波》:
自断此生休问天,白头波上泛孤船。老去文章无气味。憔悴,不堪驱使菊花前。闻道使君携将吏,高会,参军吹帽晚风颠。千骑插花秋色暮,归去,翠娥扶入醉时肩。
一曲又一曲的《定风波》,定了穿林打叶的山间急雨,定了风景浪高的人生狂澜,定了惊心动魄时的谈笑若定,安然了千百年的时光,铸就了一瞬间的永恒。(来源:现代出版社《枕上诗书》,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