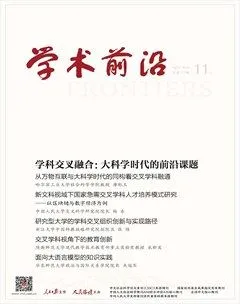大众性与科学性:实验哲学的跨学科特征
2023-12-29梅剑华
【摘要】实验哲学是以哲学问题为主要对象,以实验为基本研究方法的新型跨学科研究。实验哲学具有大众性和科学性的特征,即:哲学的问题和立场应该来自大众,这是实验哲学的大众性特征;哲学的方法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概念分析,而应该运用科学方法,尤其是心理学调查方法以及脑科学方法。因其在立场上和方法上的革新,实验哲学为当代跨学科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并在当代哲学中成为一股强劲的新思潮。实验哲学的大众性和科学性相互促进,以老百姓的视角、经验的视角、实验的视角,加深了我们对人类文明的真实认知。
【关键词】实验哲学 直觉 大众 科学 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1.007
廓清实验哲学的边界
作为21世纪的新哲学,实验哲学具有大众性和科学性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实验哲学是大众性的哲学。所谓大众性就是其问题和立场要从精英转向大众,哲学家要行动起来,走进实验室、走到田野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实验哲学具有革命意义。另一方面,实验哲学是科学化的哲学。所谓科学性就是实验哲学高度重视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拒斥纯粹的思辨和直观,认识客观世界的真实规律。如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于劳动人民的实践,实验哲学的大众性与科学性也统一于老百姓的实践。
从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理解,实验哲学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实验哲学从哲学跨越到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把不同领域的观点和方法联系起来。具体而言,就是把传统上和哲学相联系的那些问题、理论,与传统上认为和心理学、认知科学相联系的实验方法相结合。我们知道,心灵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心灵现象,语言哲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现象,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的本质。然而,与其他哲学门类有所不同,实验哲学既不是以实验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室哲学,也不是面向某个具体对象、领域的哲学,而是以实验为方法的哲学。
从科学哲学角度来理解,实验哲学是一种新型科学哲学。实验哲学领军人物诺布(Joshua Knobe)认为,实验哲学就是认知科学。经典科学哲学中的科学模型、科学说明和科学定律都是以物理学为范式的。科学哲学的传统模型是由物理学给定的,而实验哲学是以人为对象的科学哲学。近年来,一种研究人类认知结构的认知科学逐渐兴起,同时生物学也为科学哲学提供了不同于物理学范式的科学模型。物理学、认知科学和生物学是三种非常不同的科学范式,认知科学的兴起和对生物学的再审视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另辟蹊径。
从哲学方法的角度来理解,实验哲学是一种元哲学。通常,我们把探究哲学的本质、方法、思潮的哲学领域称作元哲学。实验哲学以方法的革新为哲学研究开疆拓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验哲学也属于元哲学,其研究对象涵盖了所有哲学领域。诺布认为,实验哲学包含三个主要领域(参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实验哲学”词条):一是否定性计划。实验哲学运用实验方法批判哲学理论的前提所依赖的直觉,认为传统的、以直觉为证据的方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哲学前提源自对客观世界或研究对象的直觉,批评直觉就是在质疑传统哲学的理论基础。实验哲学的一个旗帜性口号是“烧掉扶手椅(burning the armchair)”,传统哲学是一种思辨哲学,哲学家更擅长坐在椅子上喝着下午茶沉思哲学问题,而不会离开扶手椅动手做实验。实验哲学则烧掉了传统哲学家喝茶沉思的“扶手椅”,扮演了颠覆传统哲学的角色。这相当于逻辑经验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摧毁,逻辑经验主义者用逻辑手段摧毁了传统哲学问题,所有的命题要么根据意义为真,要么根据科学事实或日常经验事实为真,除此之外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实验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摧毁性则体现在对传统哲学理论基础的质疑。二是肯定性计划或修正性计划。否定性计划和肯定性计划是一体两面的,即:如果通过实验方法得出了与直觉相同的结论,则对其予以肯定;反之,则仍然是否定性计划。某种意义上,肯定性计划也可被称作修正性计划,即承认直觉在哲学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并在实验方法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直觉作进一步区分研究,从而为哲学理论提供局部证据。三是心理学计划或认知计划(笔者称之为“老百姓计划”)。如果说否定性计划和肯定性计划都是针对传统哲学框架而言的,那么心理学计划,或曰“老百姓计划”就是为了建构一种平民哲学。从大众性视角来分析诺布对实验哲学的区分,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否定性计划和肯定性计划对哲学问题的探讨路径之外,还可以通过实验研究所吸纳的大众立场来探讨哲学;另一方面,之所以说心理学计划或认知计划是老百姓计划,是因为它的问题来自老百姓,立场也来自老百姓。
实验哲学的“友军”有两支。一支是方法论上的“友军”,用认知科学方法去研究世界万物的现象。例如,道德心理学研究道德的心理机制,社会心理学研究人的社会行为,文化心理学研究文化背后的心理特征,宗教认知科学研究宗教背后的认知特征,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和实验哲学是类似的。认知科学的研究都是跟人有关的,而实验哲学根本上是研究人的直觉、理由、观念、判断,所以两者的研究方法存在互通的可能性。另一支是立场上的“友军”。传统的哲学关注道、理、心、性或者实体、属性、同一,总之都是非常抽象且思辨性强的问题。而实验哲学是一种立场的转向,回归真实的人类日常生活。在真实的生活里有性别的差异、人与动物的差异、成人与儿童的差异、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等,所以女性主义哲学、动物哲学、儿童哲学、机器哲学都是实验哲学的“友军”。那些存在人生困惑,甚至在心智上没有那么强健的人需要一种来自哲学的帮助,与此直接相关的哲学就是哲学咨询和哲学治疗,以前的哲学并不特别关心这些领域。
真实性哲学与哲学理论为真的标准
不管是实验哲学还是传统哲学,不管是哲学还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根本目的都是要获得对世界的真实认知。因此,不管是哲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求真是其根本旨趣之一。科学理论可以通过可重复实验检测结论的真假。那么,哲学理论为真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是描述性理论,就需要看世界实际情况,需要经验考查;如果是规范性理论,就需要问为什么必须如此,也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寻找根据。理论为真的根据应该首先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因此,一种哲学理论能否称其为真,既要有解释力,能够解释很多现象,也要与我们的直觉相吻合。然而实际情况是,针对特定的问题存在不同的立场。例如,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心学和理学之争、方法论的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知识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指称的描述论与因果历史论之争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等。哲学家都宣称自己的立场符合人类的普遍看法或直觉。然而,不同的哲学立场都仅仅捕捉到人类观念的某个面向,哲学家常常把自己所理解的某个面向当作唯一正确的面向。哲学家一方面为自己笃信的面向争论不休,从而产生了哲学史上纷繁复杂的哲学争论;另一方面他们自认为是“人民哲学的代言人”“人类灵魂的设计师”,并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更高的位置上。
实验哲学就是要针对这种哲学争论给出一种全新的系统的回应。如果直觉成为哲学理论的一种根据,那么我们应该去研究这种直觉是否普遍适用。但是,哲学在这里止步不前了,无法为直觉提供进一步的辩护。因为对于哲学研究者来说,直觉是哲学论证的前提、是最后的根据。我们只能对直觉进行一种间接辩护。例如,某种直觉支持的哲学理论甲要比哲学理论乙与其他哲学理论更为一致,或者这种直觉支持的哲学理论本身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但是,我们应该寻求一种直接研究直觉的办法,而哲学止步的地方需要科学。一种来自心理学研究的思路指出,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调查方法来研究概念论证的前提所依赖的直觉,调查人们的直觉到底是不是普遍的或同一的。这些调查使得实验哲学成为一种方法论,普遍应用于传统哲学的所有领域。
因此,实验哲学既批判传统哲学的概念思辨方法,也批判高高在上的精英立场,是一种新的批判哲学。相较而言,以论证为核心的分析哲学既无法摆脱论证的前提引发的争论,也无法保证真假悬而未决的前提是否能通过一般逻辑推理得到为真的结论。正如赵汀阳在《方法与问题》一书中指出:
“哲学的难处在于没有必然‘保真’,或至少‘保值’的方法。数学和逻辑有其保真方法,但哲学真的没有。当然,哲学运用了许多试图增强其有效性的方法,首先必用逻辑,但逻辑并不是专属哲学的方法,而是任何思想和知识的一般通用方法,逻辑虽有保证命题关系的形式保真性,但管不了前提或假设,而思想争议多半与前提和假设有关,因此逻辑只能为哲学助力却无法为哲学作保。”[1]
这个前提根据什么而真?大部分前提根据直觉而真,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们如此明显,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一书中指出:
“有些哲学家认为,某些事物具有直观内容这一点对支持这个事物来说并不是某种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而我自己却认为直观内容是有利于任何事物的重要证据。归根结底,我确实不知道对于任何事情来说,究竟还能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了。”[2]
在实验哲学的视阈中,直觉是一种不反思的、直接的、非推理的当下的倾向和反应。那么这种直觉与我们在科学研究中谈到的科学家突如其来的灵感和直觉有什么不同呢?哲学的直觉对哲学理论具有一种内在的辩护作用,因此哲学直觉和哲学家(或人类的)的直觉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但是,科学直觉和科学家的直觉可以没有关系。直觉可以帮助一个科学家发现一个理论,但辩护这个理论则不需要科学家的直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科学哲学里面关于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的区分来理解:在发现语境里,科学家需要非常好的直觉;发现科学理论之后,对科学理论的辩护就不需要科学家的直觉。相反,哲学直觉为哲学理论提供辩护。我们的哲学思考大多源自生活,越贴近生活的理论越需要直觉,越靠近科学的理论越不需要直觉。在语言哲学和伦理学中,语言直觉和伦理直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发现对于自然律的直觉,科学家要更可靠,哲学家也可靠,但是大众却不一定可靠。这是因为科学理论不直接根据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一个人对日常生活的感受不会影响他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可以通过重复实验获得真的标准,而对于哲学来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重复实验去考察不同的群体或个人的直觉到底有什么差异。
综上所述,实验哲学认为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被形式化为一个演绎论证(argument),即从前提推导出结论。我们也可以把一个演绎论证改造为一个故事、一个思想实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演绎论证和思想实验是同一的。但思想实验和逻辑论证的关系则有所不同:思想实验是将逻辑论证具象化,逻辑论证是将思想实验形式化。然而,不管表达什么主张,论证和思想实验都是依赖直觉的。[3]
对真实性哲学和哲学理论为真的标准作一系统阐释之后,我们就要进一步考察实验哲学如何批判传统哲学真之标准。为此,我们可以通过语言认知和因果观来讨论实验哲学如何通过批判和修正传统哲学而成为一种新的哲学。
否定性计划:以语言直觉为例
“五四”时期的思想家敏锐地观察到了中西方文明的实质差异,但缺乏科学手段进行系统研究。如今,我们可以运用实验哲学,对世界文明与中华文明之差异进行系统的跨文化实验探索,在对东西方文化心理、推理模式、理论直觉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的同时,在世界文明背景下探讨中华文明思维机制的特殊性与一般性。其中,语言直觉的差异就是一个典型的研究方向。在语言哲学中,命名理论处于核心位置。关于命名通常有两种理论。
第一种是命名的描述理论:名字的意义由和名字相关的描述所表达,根据描述可以决定名字的指称。例如,程广云教授,“程广云”相关联的描述包括:“首师大哲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这些描述构成了“程广云”这个名字的意义。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描述确定“程广云”所指称的那个人。1970年以前,大部分哲学家接受描述论,描述可能是一簇也可能是唯一的。我们对“程广云”这个名字的认知,就是一簇描述。一个反例是:我们知道“哥德尔”这个名字,但是对他并没有具体的了解,只知道他是不完全性定理的发现者,那么我们对“哥德尔”这个名字就是唯一描述。在《哲学问题》一书第五章中,罗素区分了亲知的知识和描述的知识。所以,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就有两种,要么根据亲知,要么根据描述,听别人讲,从书本上学、在电视上看。因此,命名理论具有认识论的意义。
第二种是命名的因果历史理论,克里普克认为名字的意义不是那些描述,而是指称对象本身。所有那些描述在被描述的对象身上可能不会被发现。“程广云”可以不是“首师大哲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但“程广云”还是程广云本人。正是利用这样一种直觉,克里普克批判了命名的描述论,并树起了命名的因果历史论的大旗。
在命名理论中,描述论和因果历史论就是两个彼此竞争的理论,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普遍为真的,理论所依赖的直觉是普遍的。2004年,实验哲学家从克里普克关于哥德尔的一则案例中,设计了一个调查问卷,去测试大众的直觉。问卷结果显示,这两种理论所依赖的直觉都不是普遍的,东方人更倾向于描述直觉,西方人更倾向于因果历史直觉。[4]问卷调查设计者让受试者阅读以下故事并回答问题。
假设约翰知道哥德尔是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的人。约翰擅长数学,能够复述不完全性定理的全部步骤,而且他认为哥德尔就是这个定理的发现者。现在让我们假设哥德尔并不是这个定理的发现者,而是一个叫“施密特”的人实际上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他的朋友哥德尔窃取了证明手稿,并公布了这个证明,大家因此认为不完全性定理的发现者是哥德尔。大部分人对“哥德尔”这个名字的了解和约翰类似。他们知道关于哥德尔的全部事实就是他发现了不完全性定理。那么,当约翰使用“哥德尔”这个名字的时候,他是在谈论(talking about):
A:实际上(really)发现不完全性定理的人;
B:获取手稿并宣称自己发现不完全性定理的人。
A预设了描述论直觉,B预设了因果历史直觉。
调查发现中国人大部分选择了A,而美国人大部分选择了B。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数据统计,而是按照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进行测验。这个问卷选择的主要调查对象是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后来这个研究在各个国家进行了重复实验,结论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2018年,语言学者李金彩与她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合作团队针对儿童的命名系统作了一个原创性研究和重复实验。在此之前,所有研究都仅限于不同文化传统的成年人。但是,李金彩的研究第一次关注到儿童的语言认知。一个人的语言直觉从小时候到长大成人会不会发生变化?通过哲学思考去讨论这个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李金彩等学者针对6~8岁的儿童采用了一个符合他们认知的超级狗赛跑的故事来进行调查。问卷如下:
这是一个关于一场超级狗赛跑的故事。超级狗赛跑发生在很多年以前——1900年。赛程穿越荒野,全长5000里,比赛终点在美丽的湖畔。一只叫虎子的小狗跑得很快,它参加了1900年超级狗赛跑。布丁和欢欢也参加了这场赛跑。一位记者去比赛的终点报道谁是赢家。虎子和布丁跑得特别快。比赛一开始,它们就冲在最前边。它们穿越荒野,一直在奔跑,而其他狗远远落在后面。大家都以为狗狗需要一周时间才能跑到终点。虎子和布丁只用三天就跑到了终点。同时,报道这次赛事的记者睡了一个长觉。没想到虎子最先到达终点,赢了比赛。但是,虎子实在是太兴奋了,根本停不下来,所以一直奔北极去了。从此,没有任何人看见过虎子。布丁第二个到达终点,它停了下来,望着虎子跑向远方。就在这时,记者终于醒了,他从小屋里走了出来。令他吃惊的是,布丁正站在终点,而且欢欢也从远处跑来了,但是他没有看到虎子。记者想着布丁赢了这场比赛,因此他大声呼喊:“恭喜你,布丁!你赢了这场比赛!”布丁不过是一只狗狗,它不会说话,因此也没法告诉记者发生的事情。记者将布丁赢了超级狗赛跑的消息发给了世界各地的报纸。他在报道中还提到了欢欢,虽然它的腿很短,但是跑得也很快。由于比赛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所有参赛狗以及知道这些狗狗的人们已经都不在世了。但是,人们依然可以从报纸上读到那个记者发的超级狗赛跑的报道。他们都知道布丁赢了比赛,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其他任何关于布丁的事情。一天,芳芳和冬冬的历史老师拿出一份很旧的报纸。报纸上有那个记者写的超级狗赛跑的故事。她把故事读给同学们听,她告诉同学们布丁赢了比赛。所以,这是芳芳、冬冬和同学们知道的关于布丁的全部事情,他们不知道关于虎子的任何事情。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芳芳的爸爸问道:孩子们,你们知道谁赢了1900年的超级狗赛跑吗?
冬冬说:赢了超级狗赛跑的那只狗狗是欢欢。
问题1:冬冬的话正确吗?
A.正确 B.错误
芳芳说:赢了超级狗赛跑的那只狗狗是布丁。
问题2:芳芳的话正确吗?
A.正确 B.错误
显然,问题1是一个对照组,东东的话是错误的,因为欢欢是第三名。关键是问题2,如果受试者回答是A,那就表明回答的儿童具有描述论的直觉,因为“布丁”的描述是“赢了超级狗赛跑的那只狗狗”。如果回答B,那就表明回答的儿童具有因果历史直觉,因为“布丁”的描述可以不是“赢了超级狗赛跑的那只狗狗”,但它就是这个名字的承担者。结果表明,在儿童层次也具有东西方的系统性语言认知差异,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和成人的差异保持一致。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这个发现是一个心理学发现、一个语言学发现,属于科学研究;第二,这个发现对语言哲学有帮助,作为研究语言哲学的人,直觉并非因果历史论普遍为真的有力证据。[5]因此,关于语言直觉的研究,包含了语言哲学、语言学和心理学三个领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由于对传统的因果历史论提出了批判,语言直觉被划分在否定性计划之中。
肯定性计划或修正性计划:以日常生活的因果推断为例
因果推断研究是一项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在传统哲学、人工智能、心理学和方法论中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传统哲学研究为因果推断提出各种不同的哲学理论,如规则论、倾向论、反事实理论、干预理论等。笔者曾结合珀尔在人工智能中的因果推断研究,指出因果推断是人的一种基本能力。[6]笔者认为,关于因果推断的实验研究是修正性计划与老百姓计划的结合。首先,这种研究并不否认直觉在因果推断中的作用,而是承认老百姓的直觉,并进行系统研究,所以其属于修正性计划,而非否定性计划。其次,这种研究关心老百姓的问题,探究日常生活中的因果究责,因此这种研究是一种修正性计划与老百姓计划的结合。
人的推理是受日常规范影响的。在日常生活中,引发某一结果的原因与社会或个人认可的规范密切相关。我家的花死了,没有浇花是原因。你可以编造各种反事实条件句:“如果克林顿没浇花,那么我家的花会死”“如果孔子没浇花,那么我家的花会死”“如果我没有教浇花,那么我家的花会死”等,真正的原因必然是“我没有浇花”。可见,日常生活中的因果推断就是从反事实条件中选择现实情境、从众多原因中选择正确的原因,是具有选择性的。既然是有选择的,那就意味着存在对众多原因和条件的认知偏见。对于哲学家来说,这种认知偏见并不重要,例如,刘易斯说:
“有时,我们会从某个事件的所有原因中找出一个原因,并将其称为‘原因’,就好像没有其他原因一样。或者,我们只列举一些原因,将其称为‘因果关系’或‘因果条件’……我无意谈到这些歧视性原则。”[7]
首先,考虑教授/助理的案例,这个案例反映了传统哲学家不重视的因果歧视原则。这一案例表述如下:规定在哲学系只有助理可以取用免费的笔,教授不能用。周一的早晨最后两支笔同时被助理和教授取走了。从纯粹因果推理看,两个人取笔的行为都是原因。调查结果表明:在阅读完上述故事之后,大部分受试者认为是教授而非助理才是笔被用完的原因。可见,一种潜在的规范是可以影响人们的因果判断的。而实验哲学的研究所要揭示的,正是这种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以科学主义之名、行道德主义之实的真相。[8]
其次,考虑医生/药剂师案例[9]。一名实习生在医院照顾病人。实习生注意到病人有肾脏问题。最近,实习生阅读了一系列有关可以缓解此类病症的新药的研究成果,他决定对该病人使用这种新药。在实习生使用药物之前,需要获得药剂师(以确认医院有足够的库存)和主治医生(以确认该药物适合该患者)的签名。因此,他向药剂师和主治医生发送了请求。药剂师收到请求后,检查库存足够,然后立即签名。而主治医生收到请求后,立即意识到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尽管一些研究成果表明该药物可以帮助患有肾脏疾病的人,但也有许多研究成果表明该药物具有非常危险的副作用。因此,医院有一项政策禁止使用这种药物治疗肾脏疾病。尽管如此,医生还是决定签名。得到两个签名的实习生将新药给予患者。碰巧的是,患者很快康复了,而且药物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副作用。
A.药剂师的决定帮助患者康复。
B.主治医生的决定帮助患者康复。
调查结果表明:在阅读完上述故事后,受试者更倾向于认为医生而不是药剂师的决定帮助患者康复。可见,人们的因果直觉并非受到究责判断的影响,而是受到违反规范判断的影响。受调查者会自觉地接受“医生就是治病的”这个常识性判断。设想一个相反的案例。如果服药导致患者死亡。责任是谁的?是药剂师还是医生呢?直觉上还是医生。无论结果如何,责任都在医生,但实际上责任应该由药剂师和医生共同承担,甚至开发新药的企业、批准使用新药的相关部门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医患矛盾更多追责到医生而非其他环节。
最后,考虑一个红线/黑线的案例。[10]在设置机器时,如果黑线和红线同时接触电池,将造成机器短路。如果只有其中一根电线碰到电池,机器将不会短路。黑线被指定为应该与电池接触的电线,而红线应保留在机器的其他部分。有一天,黑线和红线同时接触电池,发生短路。
A.红线碰到电池的事实造成机器短路。
B.黑线接触电池的事实造成机器短路。
案例中的规则是约定俗成的,而非道德判断。但是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受试者依旧认为是红线造成了机器短路。可见,人们的因果直觉并非受到究责判断的影响,而是受到违反规范判断的影响。综合三个案例来看,在教授/助理案例、医生/药剂师案例、红线/黑线案例中,行动者的角色逐渐消失,从一个行动者变成多个行动者再变成无行动者。影响人们判断的始终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规范。规范影响判断带来一个问题,机器人会作出怎样的因果推断?原因是教授还是行政助理?是药剂师还是医生?是红线还是黑线?如何教给机器人因果推断的背景知识?同理,人工智能要具有像人一样的因果推断能力,不仅要会作反事实因果推理,还要获得一定的规范认知,同时也要消除一些不适当的规范认知,这样才能对原因进行恰当的捡选。例如,在自动驾驶场景下,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的选择是恰当且安全的,就涉及我们上述案例所讨论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受到不同规范的影响,需要非常系统的科学调查。这种调查可能会修正、丰富我们既有的因果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日常生活问题。例如,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去纠正政策可能导致的偏见。实验哲学的因果直觉和传统哲学的语言学直觉研究不同,因果直觉的研究有益于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实验哲学是一种老百姓的哲学。
老百姓计划:大众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在哲学研究中,立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立场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证。哲学的主要工作就是作论证。例如,时间的三维主义和四维主义谁高谁低?功利主义和道义论谁高谁低?这都要看论证、看论据。从这个角度出发,实验哲学可以被看作一种祛魅,即去掉了一些所谓立场的高低之别,去掉专家和大众的区别,最终达到哲学立场上的“无分别心”。很多人认为哲学需要的直觉是专家直觉,因为专家经过训练,其直觉是可靠的,而大众的直觉不可靠。但是,专家和大众的区分不在于此,专家的直觉和大众的直觉都来自生活,直觉本身并无高下,不过是代表了不同的前理论立场而已。在概念分析、逻辑论证、知识训练背景方面,哲学家要比老百姓在行,正如在如何除草、育种、耕地、施肥方面,农民要比哲学家更为在行一样,无非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领域罢了。每个人在自己所处领域内都是行家,同时也是其他领域的外行。因此,我们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
哲学立场本身来自人类的直觉,来自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基本认知图景。如果把直觉跟哲学结合在一起,直觉就是人在生活中通过漫长的个体发展、社会交往、人类演化,对世界形成的一种不假思索的反应,与其相关的哲学讨论和哲学研究就需要这种直觉。例如,对于解答“什么是自然类?”“什么是科学解释?”之类的问题,直觉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但是,对于如何解答“什么是好生活?”“什么是谎言?”“什么是平等?”等问题,直觉显然不存在专家和大众的区别。同时,我们不仅要考虑直觉,还要考虑理由。哲学研究者不仅应该去实验室做实验,还应该深入田野做访谈,把理由和直觉相结合。[11]
哲学是生长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的,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哲学。每个人都是人民群众的一份子,哲学家并不比老百姓(大众)高明多少。实验哲学运用统计学方法和调查研究的方法去研究不同群体关于哲学理论的前理论直觉,这就使其成为一种老百姓的哲学。实验哲学就具体的哲学理论调查大众的前理论直觉,为某一哲学立场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可以说,实验哲学的基本立场就是千百年来大多数人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实验哲学体现了人民性,是真正的大众哲学。
作为老百姓的哲学,实验哲学是大众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实验哲学认为哲学理论的直觉就是老百姓的直觉。即从老百姓立场出发,在日常生活中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哲学思考的立场和问题都要来自老百姓。那么,在实验哲学的语境下,哲学家的意义何在?对于哲学家来说,逻辑分析、概念分析、文本阐释是重要的哲学方法,但更重要的是学会设计实验、统计分析、运用实验方法去研究哲学。因此,实验哲学所坚持的人民立场,需要靠科学方法来保障,即:人民性依赖于科学性。当我们不再依靠某一个或某一类哲学家的分析、思辨和想象,而是基于真实生活中的人民群体的实践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之时,就需要运用统计调查的方法来考察老百姓(大众)的直觉。(这些方法包括设计问卷、选择样本、统计分析等在当代认知科学、心理学广泛使用的调查方法,也包括在当代神经科学中广泛使用的脑电技术等。)
实验哲学的对象是人民大众的直觉、因果推断或大脑活动,实验哲学的方法是调查统计、脑电技术等。实验哲学以人类的日常生活场景为实验室,以老百姓(大众)的直觉为实验对象,以调查统计和脑电技术为实验方法,以验证某一理论的普遍性为目的。与此相对,传统哲学理论框架下的分析哲学构造了一个“脱离人类生活”的思想场景。同时,分析哲学的理论逻辑起点和进路都诉诸哲学家的哲学直觉,并以概念分析为方法、以证明某一理论的普遍性为目的。此外,实验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区别还在于:实验哲学诉诸自然科学方法,是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当代形式;分析哲学诉诸逻辑论证,是理性主义的当代形式。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实验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的争论看作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争论的一个新阶段。
实验哲学的大众性和科学性互相促进,加深了我们对人类文明的真实认知。传统哲学视角是精英的视角、逻辑的视角或语言的视角;实验哲学的视角则是老百姓的视角、经验的视角、实验的视角。当然,实验哲学也不会取代传统哲学,它只是为我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视角。我们已经看到现在很多哲学研究,如知识论、伦理学,开始逐渐具有实验的面向。就像当初逻辑分析、语言分析重新规划了哲学的议题和方法一样,实验哲学也将以老百姓的视角,塑造大众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新的哲学。
(本文系笔者于2023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哲学研究室的一次报告的主题,在此感谢段伟文研究员的邀请、程广云教授的评论和在场同学们的提问)
注释
[1]赵汀阳:《方法与问题》,长沙:岳麓书社,2023年,第8页。
[2]索尔·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3]梅剑华:《实验哲学的四重证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4]Edouard Machery, Ron Mallon, Shaun Nichols and Stephen Stich, "Semantics, Cross-Cultural Style," Cognition, 2004, 92(3), pp. 1-12;梅剑华:《实验哲学、语义学直觉与文化风格》,《哲学研究》,2011年第12期。梅剑华:《理由的缺席:实验语义学的一个根本性谬误》,《世界哲学》,2013年第3期。
[5]Jincai Li, The Referential Mechanism of Proper Names: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s into Referential Intutions, Routledge, 2022; Jincai Li, Longgen Liu, Elizabeth Chalmers and Jesse Snedeker, "What Is in a Name?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Referential Intuitions," Cognition, 2018, 171, pp. 108-111;李金彩、刘龙根:《实验语言哲学:革故鼎新抑或陈陈相因?》,《当代语言学》,2015年第3期。
[6]梅剑华:《人工智能与因果推断——兼论奇点问题》,《哲学研究》,2019年第5期。
[7]Lewis David,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Ⅱ,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1986, p. 162.
[8]具体讨论见梅剑华:《因果追责与疫情叙事》,《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Christopher Hitchcock and Joshua Knobe, "Cause and Norm,"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9, 106(11), p. 594.
[9][10]Christopher Hitchcock and Joshua Knobe, "Cause and Norm,"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9, 106(11), pp. 603-604, p. 604.
[11]梅剑华:《直觉与理由:实验语言哲学的批判性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
责 编∕韩 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