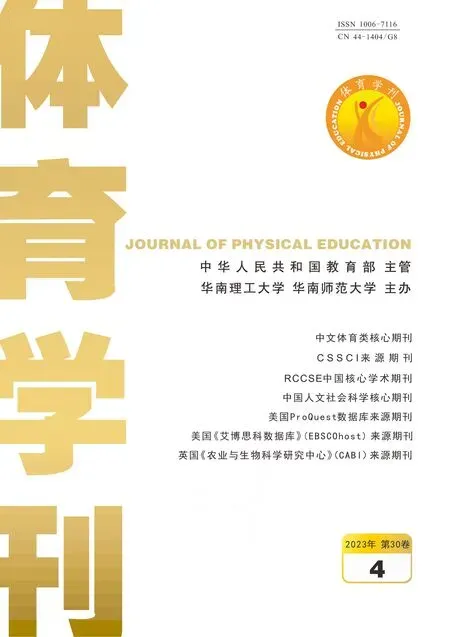溯源、解构与当代形塑:民族健身操身体动作之研究
——基于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个案分析
2023-12-29朱晓红
朱晓红
(吉首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民族健身操概念出现以前,体育与舞蹈联姻的健身操舞流行于健身行业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21 世纪初国家民委协同业内专家把这种项目正式命名为民族健身操,列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成为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崛起的创新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质疑,民族健身操到底是“操”还是“舞”,落脚在“舞蹈”还是“体育”?我国人类学专家对民族传统体育原始身体动作与文字、原始宗教舞蹈、身体文化形成的人类学分析等方面取得重要的突破,但在原始体育与原始宗教舞蹈身体动作文化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不多,致使当前社会仍存在“操”“舞”归属问题的争辩。哈拉尔德·韦尔策[1]曾指出:“不同历史时代沉积下来的记忆材料并存于社会记忆实践之中。”身体作为表述实践,传达和维系着过去的意向、知识和记忆,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2]。人类的身体动作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身体动作,文化赋予其外显形式和内在蕴意[3]。探究民族健身操身体动作原形,目的是希望厘清文化变迁的具体事相,为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求形塑民族健身操身体形态。在现代语境下,如何追溯民族健身操身体动作的雏形?如何形塑民族健身操身体动作的当代适应?鉴于这些问题,以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为个案分析,进行身体动作原生文化的历史追踪与田野实证,借助体育人类学身体动作分析法,探寻土家族“肉连响”身体动作原生形态,揭示民族健身操身体动作原生形态背后的文化事相,并从体制、文化、教育等方面探析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身体外在形态和内在文化的规训、塑造。
1 民族健身操的概述及社会发生
1.1 民族健身操的概述
解析民族健身操的内涵,实际就是在了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国本土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创新发展。目前,国内很多专家对民族健身操的概念给出了见解,最具代表的有中央民族大学李俊怡教授的观点:民族健身操动作一定要在其中包含民族的舞蹈成分与健身健美操的元素[4];寸亚玲[5]认为:民族健身操是在民族舞蹈、健美操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黄咏[6]提出:伴有民族特色音乐下结合民族舞蹈特点和表演的身体练习,具有多种功能的少数民族运动项目。综合专家们的见解,认为民族健身操的内涵应包括几点:一要把“民族特点”视为标志性文化,这里的民族特点主要指能代表各民族典型特色的舞蹈、运动、器械等身体动作;二要有当代体育健身的文化元素,包括动作技术、思想观念、精神认识等;三要有独特的民族音乐伴奏,包含典型的民族乐曲且同时具备动感的节律;四要有民族与现代健身文化的融合创造,包括与国内外一切现代健身产物的融合创新。那么,民族健身操是一种身体运动,是人们借助典型民族特色身体动作操化结构后进行的健身、表演、娱乐、教育为目的运动,它包涵多民族健身操和单一民族健身操的表现形式,其动作元素的构成大都来源于各族人民生产生活中对物化动作的身体塑造。
1.2 民族健身操的社会发生
“民族健身操”概念是21 世纪70—80 年代才开始提出,但健身舞在我国古代就有。1972 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代《导引图》勾画了身体运动姿态,有伸展、屈膝、体侧、转体、舞蹈等肢体动作,主用于宣气血筋骨的医疗体育[7]。在近代,以“五禽戏”为代表的成套养生导引健身法是健身操的源头和基础[8]。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角度思考,健身舞是通过一系列肢体的舞动来达到强身健体的身体塑造。在古代,人们很早就开始注重有意识的健身操练,其主要目的是为更好地面对生存问题而进行强身健体的身体练习,如生活中的狩猎、战争中的“武艺”、祭祀中的“巫”舞、医者的医疗操养等。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国外文化思想传入我国,中国儒家文化受国外文化思想的影响,产生了东西文化结合的观念,形成了民族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我国涌现一批以健康身心为目的的健身舞蹈,如迪斯科、秧歌舞、安代舞等,民族健身操初见雏形。1982 年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民族健身歌舞以韵律操的表演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如白族霸王鞭、彝族阿细跳月、纳西族东巴跳等,展现了我国民族体育健身舞蹈的多彩文化与独特魅力,民族民间体育舞蹈、民族健身舞逐现大众视野。2007 年国家民委组织业内专家,经过多次研讨与论证,最终把具有典型民族身体舞动特点创编的韵律操健身运动统称为“民族健身操”。经历多年磨砺,2015 年“民族健身操”被列为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民族健身操的社会发生,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当代转型的典型代表,实现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
2 追本溯源: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身体动作的探究
人类学专家李菲教授曾指出:无文字族群更注重以身体本身来进行文化表述,以人体对姿势的记忆、操演来加以铭刻,将“自我感”融入到每个个体的血液和骨肉中[2]。在无文字记载的原始人类历史发展中,身体动作文化符号是解开动作形态之间关联的重要链接和密码[9]。当前,土家族“肉连响”是民族健身操身体动作原生形态的活态代表,将其作为案例,借助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从历史文献及田野作业追踪“肉连响”身体动作的原形及蕴含意义,由此思考民族健身操身体动作之源起。
2.1 土家族“肉连响”概略
“肉连响”又称肉莲湘、肉莲香、肉年宵、泥神道等,是土家族人最具奇特的民间技艺,主要流传于鄂西利川市。肉连响的身体动作以拍打、夹击、跺脚、技击为主,集中在身体额头、肩、臂、肘、腰、腿等各部位进行动作的展示。主要动作有“鸭子步”“滚罐子”“秧歌步”“颤步”“双打”“三响”“七响”“十响”等。其动作特点是裸露上身用手拍打身体各穴位,身体自发噼啪声,加上舌头和手指弹动声响伴奏,舞风粗犷勇猛且古朴洒脱,具有强身健体、娱乐表演的功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需求,后加入了手铃、足铃、环铃、鼓,还有唱腔来使表演更加出彩,节奏也愈加明快、有力,身体动作逐渐增加了表演性、娱乐性的文化价值,满足参与人群的社会需求,项目的发展路径更加宽广。2008 年土家族“肉连响”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曾表代表湖北省参加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得表演项目的金奖。据当地87 岁非遗专家谭宗派先生阐述,“肉连响”就是泥神道(叫花子舞),在解放前经常有人在街上,裸露上体涂抹稀泥,手掌在身体各部位有节奏的拍打唱跳,目的意为讨钱。谭老说:“已故的第一代肉连响传承人吴修福老人的师傅——陈正福、潘招成,过去都是卖过草药、行走江湖的老艺人,拍打身体各个穴位肯定是具有一定的医用价值,也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健身价值。”“肉连响”身体动作的表现形式较完整地保留了土家族的地域特色,是一项族群身体文化典型特色遗留下的活化石。
2.2 “肉连响”身体动作的源流
“肉连响”的起源尚无文学记载,但民间传说不少。相传明世宗嘉靖年间,土王与客王打仗,客王把土王赶到猴儿寨,重重包围。客王兵多将广,土王则兵少粮缺,眼看年关逼近,土王预在腊月三十,待客王过年,疏于提防,土王军队杀倒正在猜拳灌酒的客王兵将,大胜而归。为欢庆胜利,土王将士们不择场地,赤膊上阵,狂舞猛跳,并以手击身,发出有节奏而又动听的声响。士兵因衣裤在打仗时,被荆棘抓烂,巾挂巾,绺连绺,随风起舞,因而,后来人们在打“肉连响”时,表演者上体裸露,多穿短裤,头戴须帕,腰吊飘带,身缠须套等[10]。从土家族的历史考古和传说中也可以佐证,“肉连响”粗犷威武的风格神韵有巴人武舞的历史遗迹[11]。
土家族是古代巴人后裔,巴人依山而居,在人与自然及部落族群的斗争中,衍生出独特的巴人文化。巴人文化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巫鬼文化兴盛发达,二是传统武舞喜闻乐见。相关历史文籍多有记载,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郭璞“巴西阆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11];《夏龠》中有为禹请功之舞,至周代仍很流行,表演时上身裸露,下着素裙[12];《山海经·中次五经》也有巴人宗教祭祀歌舞的记载[13]。原始巴人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视作鬼神作祟,他们需要通过图腾神物与祭祀仪式获得庇护与恩惠。《释名·释言语》记载:“武,舞也,征伐行动,如物鼓舞也。”[14]这些文献记载族人狩猎或是出征前的一些身体动作,是宗教仪式的一种精神意念,推敲其“武”意指拿着兵器舞动身体的人,是为战争服务的身体仪式。在楚汉年间,从崖墓和石棺中的古代青铜器、壁画、建筑物等器物上有“巴人乐舞图”的印记[15],巴人乐舞早期的出现扮演着巫神交流的工具,具有召唤神灵或祭祀祈福的重要作用。西汉初年,汉高祖重祭巴族“歌舞以凌人”这一法宝,对敌军“不战而屈之兵”的战术大获全胜,后将此歌舞记录存放,并命名为“巴渝舞”[16],这在《后汉书·南蛮传》《华阳国志·巴志》等史籍中多有记载。魏晋六朝时代,巴渝舞为适应军队需求进行改造加工,又名“昭武舞”;《行辞》以述魏德,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及晋,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16]。唐宋时期巴渝舞的创作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巴渝舞的曲名发展有《剑俞》《矛俞》《弩俞》,凡三章[16],之后宫廷巴渝舞便不见有文献记载。在历史中巴渝舞有两分支:一支是宫廷燕乐大雅之舞,另一支为民间祭祀之舞。从汉代到唐宋,巴渝舞在宫廷延续千年,从民间到宫廷曾辉煌鼎盛,北宋以后消失于各类文献[17]。当宫廷巴渝舞逐渐消弭,民间巴渝舞却逐渐形化成各种表演形式和流派,其神韵在土家族多个舞种中变通性的遗存,有土家族舞蹈文化开鼻之祖的称号。从历史背景及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巴渝舞的动作特征:一男性裸露上体,二有鼓乐助威,三刚劲勇猛,与“肉连响”动作特征有着非常显著的相同之处。由此认为:“肉连响”是民间巴渝舞的演化,分化于土家族传统舞蹈,在后人的传演中逐渐形成。
近代以来,该项目成为一种身体技艺在民间流传。据第2 代“肉连响”传承人刘守红介绍,民国时期“肉连响”便作为乞丐乞讨的身体表演,行走在土家族一脉族群中。改革开放以后,“肉连响”被艺术专家挖掘整编成土家族舞蹈,参与电视台及民俗活动的文艺展演。现代社会,为服务社会的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需求,土家族“肉连响”已成为一种在学校、社区、办公区域等健身诉求中,以刺激肌肉、调节心率、提高身体运动为目的的操化健身运动,其身体动作的表现形式及动作结构已脱离以表演为主要目的的身体舞动,“肉连响”的动作特征配合有节律的伸展、跳动是族群闲暇之余健身娱乐重要的运动项目。利川市非遗专家孙绘老师评价“肉连响”:“它是传统艺术和传统体育融合的结晶。”当前“肉连响”健身操保持着健康活泼的态势,彰显着生机与活力。
在古代,“舞”既“武”[18]具有相通之意,他们通过“巫”文化孕育发生[19],是人类用身体模拟世界的一种宗教仪式。“操”最初是指军事演练、体育技能的练习,后演变为一种身体康养的节律运动。美学家苏珊·朗格[20]认为:“舞蹈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第一种真正的艺术。”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历史记忆形式,体育是适应人类生产、军事和健康需要的一项身体活动,“舞”与“操”从当代学科归属层面理解,“舞”属于艺术范畴,“操”归属于体育范畴。德国艺术史家、社会家格罗塞曾把原始舞蹈分为“摹拟性舞蹈”和“操练性舞蹈”两大类[21],认为摹拟性舞蹈是模仿野兽或自己生活的舞蹈;操练性舞蹈是表达人类某种仪式、战场、演习的身体训练。格罗塞所阐述的操练性舞蹈,其实就是体操最初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存在于身体各仪式活动中。在现代,从不少民族体育表演项目的展演中可以隐约发现,身体表达大都呈现“舞中带操、操中有舞”的动素结构,他们之间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当代社会,人类对生活的追求从满足于物质生活到精神富足,在这样的文化需求下,“肉连响”身体动作璧合珠联,表现出以健身为目的舞操结合的身体动作,不再仅限于以表演为目的的身体舞动,更多的服务于人们大众健身需求。本研究认为,民族健身“舞”“操”的界定在于参与者身体动作的价值取向,以健身为目的的身体表达即为操,以表演为目的的身体塑造即为舞,民族健身是一种表达健康行为的身体操化运动属体育范畴,应称之为“操”。
综上所述,土家族“肉连响”身体动作的形成经历了原始宗教文化的母体分化,根据社会需求服务于宗教祭祀、军事战争、宫廷乐舞等,最后到民间技艺至健身的演变。这种身体活动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满足某个族群的社会性需求而产生[22],并在各自关联的网状结构中,形成较为稳固的制度文化。在现代社会,外来文化的入侵与社会结构层面的彻底翻新,长期形成的社会网状结构被打破,传统生态链的破裂,人类依赖于自然的社会现象逐渐消弭,文化活动场域的结构形式发生改变,身体动作从宗教仪式文化中解放出来,摒弃封建礼教的神秘意蕴,在各自文化领地发生发展。从文化进化论逻辑分析,人类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一样都要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阶段逐渐发展,造成普遍性的最终原因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23]。通过上述探究与分析认为,“肉连响”身体动作的原生应为“舞”“武”与“巫”文化结合的身体形态,在社会发展的历史熔炉中孕育衍生,历经原始宗教祭祀—巴人军舞—宫廷燕乐—民间技艺—舞艺表演—健身运动等一系列文化的变迁,在社会文化适应中、在社会需求下不断演变,现已成为一种在学校、社区等大众视野中开展的以健身为目的操化运动。
3 田野探究与质性分析:土家族“肉连响”身体动作的解构
利川市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地处鄂渝边界,上古为廪君地,周属巴国,古称“蛮獠杂处”“蛮夷杂处”,是神秘的古巴蜀地。境内万山重叠,沟壑纵横,道路崎岖,关隘四塞,历为楚蜀屏障、军事重地[24]。新中国成立前,利川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常年举行各种宗教祭祀活动,承载万物显灵、图腾崇拜、祖先保佑等深厚的多元宗教文化因子,许多民俗活动的身体运动都根植于原始宗教仪式而存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及相对封闭的地域特色,至今仍保留祭祖拜神的民间信仰。当前,“肉连响”不仅与利川县土家族民俗生活密不可分,还深嵌于社区、学校、旅游区等处,有着强健的传承路径。冀望通过实证研究了解文化背后的具体事相,课题组于2021 年3—9 月多次深入利川市,调研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访谈当地传承人、传习者、文艺前辈等。
田野调研共收集“肉连响”基本动作16 个:十二响、十响、九响、七响、四响、三响、对打、穿花、跪地拜打、鸭子步、秧歌步、穿肘吸腿跳、吸腿跳拍胸、吸腿跳拍(击)手、绕八字围身击(打)、徒手十拍双人对舞。经过与相关专家商榷,本研究选定土家族“肉连响”第2 代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守红及利川非遗中心珍藏的已故第一代传承人吴修富老人的身体动作为研究对象,借以体育人类学的研究视觉,解构身体动作文化符号,影像记录刘守红动作素材,直观分析身体动作的文化特征并阐释其深层意义。通过专家商议把“肉连响”动作符号分为生活形化、战争操练、宗教祭拜、动物模仿四大类。课题组根据分类重点筛选:十响、对打、跪地拜打、鸭子步4 组身体动作进行文化符号分析。
“肉连响”上肢动作主要靠拍打身体各部位、对抗、跳起击掌、俯身拍地等文化符号组成;下肢动作的马步蹲立、弓步屈膝、蹲腿起跳、跪地等文化符号,重心下沉力度稳健,踩步豪迈剽悍,动作粗旷古朴。从着装及动作的跳动神似原始人类在展示身体的强壮及表达作战的士气。综合本土资深专家及业内专家的认识与课题组的深入探析,归纳出4 组动作的功能、特征及背后隐喻意义(见表1)。
从解构的4 组动作可以清晰看出,土家族“肉连响”身体动作的当代呈现,依然记忆着大量原始文化的足迹。“肉连响”身体动作文化符号所隐喻的意义,与当地社会环境、民俗习惯有着密切关联:在潮湿窘迫的环境中人类采用身体的形化拍打来缓解寒气与蚊虫叮咬;在战争中用身体的粗犷彪悍来形化战斗的士气;在文化落后的背景下用身体表达图腾崇拜获得庇护与恩惠;在狩猎中用身体表象刚强勇猛擒获猎物等。这些隐喻的深层意义与文献记载的巴渝舞的文化背景有着较高的相似之处,既是对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身体塑造,也是对社会环境的一种文化创造。由此,也进一步验证民族体育类的身体动作与民族舞蹈身体动作的形成有密切的关联。
4 当代形塑: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的社会适应
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认为:身体作为自然物是被社会力量塑造的,那么身体动作是反映社会力量无声的语言,被社会需求形塑[25]。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的当代形塑应根据社会需求,从国家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等多因素,综合思考文化的社会适应。通过竞赛制度、传统节日文化、学校教育、健身美学社会服务4 个维度进行身体动作的形塑。其中,竞赛制度是项目发展的有效保障,传统节日是延续历史、增强民族文化软实力的精神支撑,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健身美学社会服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他们之间构成了民族健身操当代社会适应的重要链接。
4.1 当代竞赛制度下身体动作的规训、操纵及塑造
近些年,我国民族健身操通过各种竞赛形式登上世界舞台,在项目的国内普及与扩大国际影响力方面成绩显著。当代竞赛制度,对民族健身操身动作的形塑起着规范、导向和推动的作用。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竞赛制度中的构造,应注重外在竞赛规则和内在竞赛精神文化的形塑。首先,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要从赛事的规则需求,对身体动作的构成进行综合分析,根据赛事主题重构身体表达。例如:在民运会竞赛项目中,要保留土家族“肉连响”原生态身体动作风格和特点,结合竞赛规则中场地空间的运用、动作变化方向及身体姿态的操控等,重构宗教祭拜、战争、狩猎等原始的身体形化,融合现代健康动感节律进行身体动作的规训。其次,要根据评分准则对“肉连响”身体动作的表现形式进行操纵,如:“肉连响”的“九响”不能以单纯展现原生态身体穴位的拍打,要通过评分细则来创编身体动作,融合现代体育健身跑、跳、提、拉等动作元素,改造与规训身体动作的肢体表达。然后,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竞赛精神的内在形塑,要通过音乐背景的渲染及身体动作的内涵展示,来表达一种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从而展现出奋勇拼搏、挑战自我、热爱祖国的内在品质与精神面貌。竞赛体制下民族健身操身体动作的形塑,要在规则的执行中操纵身体动作,要有个性化的垦荒、耕耘和创新,也需注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之魂。
4.2 传统节日文化活动中身体动作的当代形塑
身体是体育与社会文化的中介,也是体育活动的主体[26]。在古代,传统节日中身体的舞动是为获得神灵恩赐与祖先庇佑的一种仪式文化,其身体动作是以特定社会环境为根基,在祖先崇拜及文化认知中被形塑。在当代,传统节日文化活动通过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展示营造一种“普天同庆”的节日气氛,身体表达具有重现历史、祭奠先祖的文化蕴意,又有热闹气氛、欢庆鼓舞、促进民族团结等价值。在契合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文化背景下,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身体动作的当代形塑,首先,契合传统节日主题重构身体表达。挖掘整理土家族“肉连响”身体动作的相关文化符号,捕捉最具代表性的身体动作来展示传统文化,如跳拜、穿花、绕八字等,开采由内至外精神表达,结合文化内涵与社会需求重构身体动作,通过有意义的身体操演展现符合节日主题的需求。其次,共同体意识形塑身体动作的多元表达。巧妙运用土家族“肉连响”族群认同的动作符号,融合当代中华民族熟稔的身体表达,塑造身体同源文化,凝聚族群民族认同,建构身体文化共同体归属感。最后,形塑民族文化自信。以传统节日为交流媒介,从“新、特、美”的视角融合创编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身体动作的文化符号,如“九响”“对打”“拜打”等特色动作符号与现代流行的健康动律元素融合创新,展示出一种浸润原生态且时尚的身体表达,从而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豪感。传统节日活动中身体的操演是建构族群文化记忆、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凝聚民族精神重要的文化符号。
4.3 学校教育视域下身体动作的当代形塑
2015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7]。在学校教育中引入民族健身操项目既能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又能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传导文化认同、增进身心健康等价值。学校教育要把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纳入体制建设中,通过筛选、重塑、加工、创新,建设民族文化的记忆与传承。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在当代学校教育中身体动作的当代形塑,首先,以育人为本的动作技艺雕琢。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在学校教育体制下身体动作的技艺塑造主要以锻炼身心健康、育化校园文化生活等,将原生形身体动作进行规范化、科学化、教育化动作形态雕琢,在加工改造中注重保留民族典型的动作遗迹,同时融合现代科学化教育的身体动作形态。其次,民族文化内涵教育的当代形塑。深挖土家族“肉连响”民族文化内涵,以教化育人为目的,过滤民族文化知识,沉淀文化精髓,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进行民族文化的塑造,培养学生对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增强凝聚力、产生影响力。最后,基于民族文化之魂形塑思政教育。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蕴涵优秀的民族精神,在教育中经过动态解读,积极思辨,形塑青年一辈的民族情怀、凝心聚力、人文素养等,在学校展示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将民族传统文化根植于受教者的思维意识。
4.4 健身美学社会服务中身体动作的当代形塑
为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的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全民健身条例》提出“推动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鼓励各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服务于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在全民健身背景下,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身体动作的形塑不仅要针对于身体机能的健康促进,同时还要注重视觉美、精神美的身体塑造。首先,形塑满足于人们健身养心的社会服务需求。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作为满足人体身心健康的身体运动,要将具有典型民族特点的动作元素,通过强身健心的形塑,结合运动处方,伴随独特动感的民族乐曲,进行刚柔并进、提拉韵体等科学化身体动作的规训与形态雕琢,满足人们健身养心的需求。其次,打造视觉美的身体形态。从动作美、气质美、健康美的美学特征,对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的身体动作加以艺术修饰,重构野蛮、狂野等纯原生态身体文化符号,展现力学美感与民族神韵相融合的身体动作,满足人们塑造外形美的追求,激发群众健身塑体的参与欲。最后,把民族体育文化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土家族“肉连响”健身操身体动作外在形态的构造,要结合蕴含民族体育文化的精神内涵,从身体文化符号的形态中塑造展示一种健康向上、积极进取行为上的归化,这是一种由内至外精神与身体文化的解体重组,在身体的运动中形塑知行合一。民族健身操的原生形与现代健身元素辨证融合,在健身美学的需求中解析、提炼和衍生传统文化,尊重发展规律,塑造具有时代精神的民族健身操新样态,是民族文化自我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路径与打开方式。
费孝通[28]曾在类型概念中指出:“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发生相同类型的事物。”把民族健身操看成一个文化复合体,由多民族文化交融组合,其身体文化在经历原始社会到当代社会的不断演变中存在文化共性,即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活动中形成的自然崇拜、宗教信仰、战事纷争、生活劳作等身体实践活动。从文化进化论视角分析,这些身体实践活动在中华大地所经历的历史变革和社会制度之间具有概括性的共同规律,呈现出文化本质的一致性和形式上的差别。在大环境下,各民族在自然环境与生活习俗的异行中,形变为具有地域特征的身体文化,这类文化的发展都是从蒙昧到野蛮再趋向文明。民族健身操动作元素的形成大都来源于各族人民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身体塑造,土家族“肉连响”是最为典型的单一民族健身操,与其他民族健身操动作元素虽有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性,但动作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文化共性和概括性的共同规律。对其进行身体动作的溯源及解构,是民族健身操较为典型的实例研究,反映了民族健身操身体动作演变的历史规律,揭示了特殊环境下身体动作的独特意义及社会功能,也为传统身体运动与原始宗教舞蹈,在同源异构文化形态中的离合分化和交融发展提供了实证案例,是人类在现实社会需求中对身体符号表征记忆的不同改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民族健身操是“古为今用”中国本土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当代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其未来发展要扎根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在当代社会文化的需求中创造与创新,在保留原真性身体文化记忆的同时形塑当代社会的文化适应,让民族健身操在新时代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号角的征程下不断焕发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