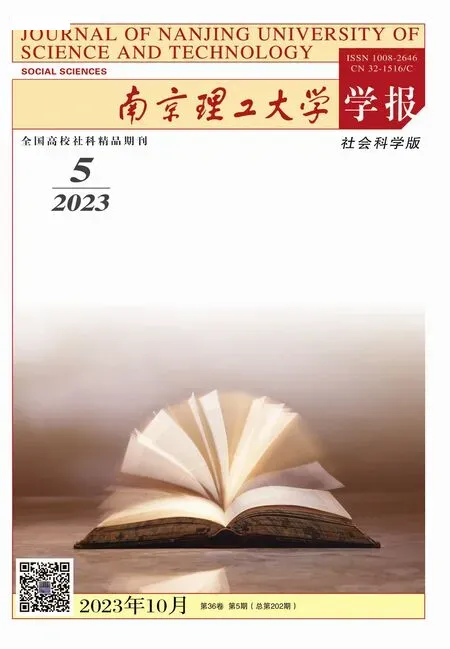恻隐之心为人立德
——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原型”及其现代意义
2023-12-28彭文超
彭文超,马 贺
(1.安庆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2.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23)
中国素有“道德文明古国”之称,堪称道德文化最为丰富和发达的文明国家。然而,道德文化的丰富和发达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的道德品质普遍高尚,在漫长的中国文化长河中固然不乏仁人义士,却也产生了很多的道德败坏者。正如鲁迅所批判的,在满纸“仁义道德”的字缝之中,隐藏着“吃人”二字,人们或吃着蘸满人血的馒头,或充当麻木不仁的看客。鲁迅一百年前的辛辣批判至今仍常常被人想起,因为类似的问题远未消失——近年甚为流行的“道德滑坡”论和引发广泛关注的诸多“道德冷漠”现象,乃至发生在校园中的“校园欺凌”事件等,都在提示当下我国道德问题依然不容忽视。究竟如何为人立德?教育如何方能立德树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和教育在“打倒孔家店”运动中被否定了,以致很长时间内我们都在求助西方文化中的道德筹划,希望借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结果不尽如人意,是因为以西方世界为主体的现代道德筹划本身就是失败的,将之勉强嫁接而来不可能取得成功。那么从何处寻找为人立德之道?近年来,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道路上取得长足进步,使得我们逐渐摆脱西方文化的笼罩,可以自信地重新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魅力。本文认为,回到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回归中国传统以恻隐之心为“原型”的立德之道,可能是一个富有价值的为人立德思路。
一、现代道德筹划的失败:何以为人立德?
为人立德,亦即为人类的道德确立根基,使人作为道德存在能够挺立起来成为“道德人”。古往今来人们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贡献出诸多道德筹划思路。归结起来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道德筹划思路:其一,道德源自超验的存在者,诸如各类宗教中的神,人只需听从神的指引行动便可确立道德;其二,道德源自人的先验理性,依据理性的命令行动便可确立道德;其三,道德源自人的经验建构,人在生活中依据情感、体验、习惯、功用等因素确立道德。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道德筹划基本抛弃了第一类宗教形而上学的筹划方式,主要采用了第二类理性主义的和第三类经验主义的筹划方式。那么,现代道德筹划是否成功?
1.现代道德筹划的失败及其原因
麦金泰尔明确判定了现代道德筹划的失败。在《追寻美德》一书中,麦金泰尔重点分析了三位最具代表性的启蒙哲学家的道德筹划:康德诉诸理性、休谟诉诸激情、克尔凯郭尔诉诸选择。[1]50-64康德将人类理性的先验预设发挥到了极致,认为理性能够遵从道德律,依据绝对命令而行动。理性为人确立的道德法则是作为先天综合命题强加给人的,与任何主观经验都毫无关系。休谟则首先假设道德要么源于理性,要么源于激情。在论证了道德不可能源于理性之后,他理所当然地认为道德是激情的产物。而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既不是理性也不是激情产生了道德,而是选择。人需要在审美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的生活方式之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想在此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又必须选择一个据以选择的第一原理。这种对第一原理的选择被称为根本选择,人就是在根本选择中确立道德。
在对以上三位哲学家的道德筹划思路做出分析之后,麦金泰尔发现,如果他们各自的论证是充分有效的,那么恰恰必将导致彼此的失败。“恰如休谟由于自己的论证已排除了将道德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可能性,就力图将它建立在激情的基础之上;康德也由于他的论证已经排除了将道德建立在激情基础之上的可能性,就将它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而克尔凯郭尔则将道德建立在无标准的根本选择的基础之上,因为他认为那同时排除了理性与激情的考虑具有一种强制性质。”[1]63每一种思路的成立都以对另一种思路的否定为前提,那么三种思路各自的有效论证也就意味着三者全部失败。据此,麦金泰尔判定现代道德筹划失败了。
那么,现代道德筹划失败的根源何在?麦金泰尔的分析指向这些道德筹划思路的共同特点。尽管启蒙哲学家们的思路各不相同乃至互相反对,他们却有一个高度一致的前提:“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拒斥任何目的论的人性观、任何认为人具有规定其真正目的的本质的看法。”[1]69这便是启蒙哲学家的道德筹划失败的根源。根据麦金泰尔的分析,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伦理学筹划展开为一个三重构架,这一三重构架分别由“未受教化的人性概念”“道德训诫”和“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性概念”三个要素构成。[1]67启蒙哲学家的道德筹划不论彼此有何差异,都放弃了第三个要素即“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性概念”,仅仅保留了前面两个要素。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一致出现在启蒙哲学家的人性概念和道德训诫之间,因为丧失了目的论内涵的人性与道德训诫无法构成合理的联结。未经教化的人性为何需要又何以能够遵循道德训诫?失落了目的论内涵的人性概念无法为此提供有效论证,无法跨过人性与道德之间割裂出的鸿沟。据此,麦金泰尔将休谟提出的“是(事实)推不出应当(价值)”亦即“没有任何有效论证能够从全然事实性的前提推出任何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结论”[1]71这一原则看作启蒙道德筹划失败的墓志铭,也是现代道德筹划思路与古典传统最终决裂的信号。从此,道德不再具有人所共有的基础,何以为人立德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麦金泰尔从纯粹学理的角度分析了现代道德筹划的失败及其原因,却没有描述这种失败带来了怎样的现实道德后果。笔者认为,现代道德筹划失败之后最为严重的现实道德后果在阿伦特笔下得到了最精微的揭示。在阿伦特看来,二十世纪的两次道德秩序大崩溃(一战和二战)所造成的真正的道德难题“不是在罪犯那里,而是在普通人那里,道德瓦解为一套孤立的风俗——一些可随意改变的风格、习俗、传统。”[2]正因为现代道德筹划的失败,道德哲学失去了像古典时代那样为人确立坚实可靠的道德基础的功能,道德才会“瓦解为一套孤立的风俗”。普通人才会在纳粹统治期间放弃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转而默认、遵从纳粹思想体系,将其接纳为新的“道德风俗”。在这种道德风俗之下,普通人对无辜犹太人遭受的苦难无动于衷、冷漠旁观,成为人类道德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2.为人立德:追随何种古典传统?
既然现代道德筹划如麦金泰尔所揭示的那样失败了,那么何以为人立德?基于对现代道德筹划失败根源的分析,麦金泰尔选择了追寻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如前文所言,现代道德筹划中的人性概念失落了目的论内涵,无法跨过人性与道德之间割裂出的鸿沟。据此,麦金泰尔认为只要寻回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目的论人性概念,将“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性”归还给人,便可解决人性与道德之间的割裂难题,重新为人立德。
当下中国人何以立德?是否应该追随麦金泰尔的脚步?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以来,“孔家店”被打倒,传统文化遭到否定,我国便一直在追随西方现代文化,以至于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道德筹划思路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国思想界接受。如此一来,西方现代道德筹划的失败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我国现代道德筹划的失败。现代道德筹划失败之后,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向何处去?像麦金泰尔那样追随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传统?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只有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才是解决人性与道德之间的割裂难题以为人立德的唯一或最优思路?我国的古典传统是否同样包含着在现代道德筹划失败之后重新为人立德的内在思路?
回答是肯定的。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孟子提出的“恻隐之心”为“原型”,展开一条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立德之道,某种意义上能够比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更好地解决现代道德筹划失败所留下的人性与道德之间的割裂难题。
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立德思路:作为“原型”的恻隐之心及其立德之道
关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立德之道,学界已有非常丰富的研究和阐述。不论是孔、孟、荀的仁、义、礼,还是朱、王的天理、良知,如此等等修身立德之道都已成为共识。问题是,他们的立德思路能否解决现代道德筹划失败所遗留的难题?笔者在此引入荣格的文化心理学概念“原型”,认为孟子的恻隐之心即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原型,这一原型从根本上打通了人性与道德的断裂隔离状态,给予人以立德的现实可能性。
1.“原型”:一种先天直觉形式
荣格在其“集体无意识”理论背景下提出“原型”概念。荣格创立集体无意识理论,以对应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理论。后者研究心理形成的个体后天根源,前者则旨在探寻普遍一致的、与个体后天经验无关的先天深层心理结构。原型就是这种先天深层心理结构亦即集体无意识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我们在无意识中发现了那些不是个人后天获得而是经由遗传具有的性质……发现了一些先天的固有的直觉形式,也即直觉与领悟的原型。它们是一切心理过程的必不可少的先天要素。”[3]5荣格的文化心理学正是基于先天固有的直觉形式来揭示和解释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
那么,原型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形成的?荣格认为原型是“一种记忆蕴藏,一种印痕或者记忆痕迹,它来源于同一种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缩。在这方面它是某些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沉淀,并因而是他们的典型的基本形式。”[3]5在此已经可见文化心理“积淀说”的影子。中国学者李泽厚受此启发,提出“经验变先验”[4]的命题以解释人类先验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机制,可以说是对荣格原型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作为心理的先天直觉形式,原型本身没有具体内容,“原型本身是空洞的、纯形式的,只不过是一种先天的能力,一种被认为是先验的表达的可能性。”[3]7
根据以上引述分析,荣格的原型概念可以概括为:原型是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先天直觉形式,由历史积淀而来,不包含任何具体内容,却能够为人的具体文化心理内容提供可能性。将原型概念引入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那个作为人的先天直觉形式、由中国历史文化积淀而来、不包含具体道德内容(如善恶观念、具体德目等)却又能够为具体道德内容奠定基础并提供现实可能性的原型是什么?笔者将在下文尝试论证,孟子所提出的恻隐之心正是这一原型。
2.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原型的恻隐之心:直觉形式与感觉能力
孟子以“见孺子入井”为例,揭示“恻隐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何为“怵惕恻隐”?朱熹解释说:“怵惕,惊动貌;恻,伤之切也;隐,痛之深也。”[5]239由此可见,恻隐是指人心受到惊动,为所见之事感到伤痛。在孟子的例子里,人突然看见孩童将要掉到井里,立即受到惊动,感到伤痛,并将毫不犹豫施以援手。这个例子已经充分标画出恻隐之心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原型的条件。
第一,恻隐之心是人的先天直觉形式。孟子否定了“见孺子入井”情境中恻隐之心的产生可能具有的后天经验理由,即,恻隐之心的产生不是为了交好于孩童的父母,也不是为了在邻里间留下良好声誉,同样不是出于厌恶孩童掉落水井的哭叫声。此三者都是后天经验给予人出手救人的理由,但恻隐之心的产生与他们无关。恻隐之心是人先天具备的,它是一种直觉形式,一种感觉能力,它“随见而发”“非思而得,非勉而中”[5]239,一见他人遭受苦难便立即受到惊动而自然发动。
第二,恻隐之心是人之为人普遍具有的。在孟子看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5]239,人之为人必定拥有恻隐之心,这也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内在理由。当然,经验中存在许多反例,许多人见到他人遭受苦难困厄而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但这并不构成对孟子恻隐之心乃人所普遍共有观念的有力反对,因为孟子已经将“无恻隐之心”的人划为“非人”,而“异于禽兽”的人仍然普遍拥有恻隐之心。对他人苦难麻木不仁者,如朱熹所言,是“物欲蔽之”[5]239,外在的利益考量遮蔽了本来具有的恻隐之心。
第三,恻隐之心由历史积淀而来。这一点在孟子的文本当中未有申述,却可以综观中国历史文化分析得之。尽管中国历史上同样发生过诸多战乱、争斗、冲突与分裂,中国人对待同胞和天地万物的态度始终是趋向于关心和爱护的。中国文化向往“天人合一”的境界,古代先民崇尚自然并向自然天地汲取生活智慧。在历史的长期演化和生活的迭代展开过程中,中国人“摸清了其(自然)亘古不衰的规律是合并而不是分离,是融合而不是离散,是联合而不是分裂。”[6]这种连续性的自然观决定了中国人在文化心理结构深处始终把自己与同胞连在一起,构成“民胞物与”的共生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恻隐之心正是中国人在五千年乃至更久的共同生活历史中逐渐积淀下来的文化心理形式。
第四,恻隐之心不包含任何具体的道德内容。从孟子文本来看,恻隐之心不就是“仁”吗?而“仁”便是具体的道德内容了。的确,孟子有时称恻隐之心是“仁之端”[5]239,有时又直接称“恻隐之心,仁也”[5]334,似乎都把恻隐之心当成了特定道德内容“仁(之端)”。然而,孟子其实是在说,恻隐之心得到扩充伸发之后才成为具体道德“仁”。直接说“恻隐之心,仁也”,其实是省略了其中的扩充过程。一如朱熹对“怵惕恻隐”的解释是惊动和伤痛之感,在得到扩充而成为仁之前,最初的恻隐之心只是先天直觉形式和感觉能力,尚且不包含任何的道德内容。既无任何善恶观念——凡人见孺子入井而生恻隐之心,不以任何善恶判断为前提,不存在先于恻隐之心的“救孩子的行为是善”的道德判断;也无任何德目——见孺子入井而产生恻隐之心不是基于“仁”或其他任何道德法则或规范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恻隐之心是先于道德的,也唯有先于一切道德内容,才能够作为道德文化的原型而存在。
第五,恻隐之心能够为一切道德内容奠定基础并提供现实可能性。恻隐之心本身虽不包含任何具体道德内容,却内蕴一切道德内容的种子。正因为人之为人拥有恻隐之心,才能够感觉到他人的苦难,在惊动和伤痛的直觉中关心他人并付诸行动,由此衍生出一切仁义礼智和相应的具体规范。与恻隐之心相比,孟子“四心”中的其他三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已经包含道德内容了,羞恶之心内蕴善恶判断,辞让之心内蕴关系差别,是非之心内蕴是非界线。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可以从恻隐之心衍生出来:既然人能够对他人的苦难境遇产生惊动伤痛的感觉并付诸行动,那么普遍意义上的善意(仁)和善行(义)便呼之欲出;有了善意和善行的观念,便对不符合仁义的行为感到羞恶;普遍意义的善意和善行具体到人际关系当中,便产生了对于长者、尊者的辞让之心;与此同时,行善为是、作恶为非的是非观念也将自然形成。质言之,只要人拥有最初的对他人当下境遇的感觉能力,便奠定了道德的坚实基础,一切道德内容都可以由此衍生发展而成,道德也就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在此意义上,恻隐之心犹如一颗种子,种子本身不是树,却拥有长成参天大树的可能性,而大树也只可能由种子生长而成。如朱熹引程颐的话说:“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5]340人能成为道德人,皆因此心有成仁之本性,而这种本性正是蕴含在“恻隐”的感觉能力之中。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归结如下:恻隐之心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原型,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文化活动中积淀而成的、人之为人先天普遍具有的对他人境遇的直觉形式和感觉能力,它不包含任何具体道德内容,却为中国传统以仁义礼智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赋予它们现实可能性。
3.恻隐之心的立德之道:基于人性与道德的连续性
上文已经说明恻隐之心为道德奠定了基础并赋予道德以现实可能性,那么,这一立德之道具体是如何展开的?笔者认为,恻隐之心的立德之道建立于人性与道德的连续性基础上,在社会道德文化层面展开为“恻隐—仁—道德系统”的生成过程,在个人道德挺立层面展开为“恻隐—扩充—成人”的成德过程。
人性与道德的连续性是恻隐之心原型内在蕴含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特征。麦金泰尔诉诸“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亚里士多德目的论或功能论预设以打通人性与道德的割裂分离状态,这一思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相比之下,恻隐之心却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人性事实,在此事实基础上解决人性与道德的割裂难题似乎更为可靠。以恻隐之心这一人性事实为起点,道德逐渐生长出来并得以完成,这种连续性打破了被麦金泰尔称为现代道德筹划墓志铭的休谟“是(事实)推不出应当(价值)”原则。恻隐之心作为人性事实,内在蕴含了充分的道德可能性,只要顺着恻隐之心加以扩充发展,便可生成完备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恻隐之心原型在社会道德文化层面展开为“恻隐—仁—道德系统”的生成过程。在孟子之前,孔子将孝这一子女对父母的情感作为包括仁在内一切道德的基础,即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5]48。孔子的“孝—仁—礼”结构是中国传统血亲伦理的表现,本身自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孔子所说的孝其实只是仁在亲子关系中的具体表现,只不过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宗法制体系从社会结构层面给予了孝以无可比拟的地位。从普遍的立德理路来看,孝并不先于仁;相反,仁是先于孝的,只有具备普遍的爱人之心,人才会在亲子关系中孝敬父母。而普遍爱人之心的基础又在于恻隐之心。只有恻隐之心发动,才会敏锐地感觉到他人的境遇,在惊动伤痛中付诸关爱之情和帮助行动。所以,相比于孟子的“恻隐—仁—道德系统”结构,孔子的“孝—仁—礼”结构是浮于表面的,未能发现深藏于孝和仁之下的真正根基亦即他们的原型恻隐之心。孟子发现了恻隐之心,尽管有时他又不断强调孝的极端重要性从而造成其道德哲学中的“仁—孝”深度悖论,[注]参见刘清平.论孟子恻隐说的深度悖论[J].齐鲁学刊,2004(2):12-15.在该文中作者认为“孟子的恻隐说在思想实质上与儒家以血缘亲情作为惟一本根的基本精神正相对立,因此在儒家理论架构内无法成立。”但是,孟子并非要在孔子的理论框架内另辟蹊径,而是在孔子理论框架之下找到了更深的道德根基,因此并不妨碍儒家道德哲学体系的自洽,只是填补了孔子在道德原型层面的空缺而已。但他在家族血亲伦理的包围下发现并阐发了恻隐之心,不得不说是伟大的人性发现。
恻隐之心在个人道德挺立层面展开为“恻隐—扩充—成人”的成德过程。这一层面的展开过程其实与上一层面彼此呼应,恻隐之心扩充的过程也就是“人而仁”的过程,而从扩充走向成人的过程也就是人对整个道德系统的自觉内化过程。作为恻隐原型所形成的核心道德内容,仁在个体成人过程中至关重要,可以说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语境下的“成人”实质便是“成仁”。“仁”在概念语义上便是对恻隐之心的进一步阐发:“仁”在中医里表示人体保有感觉能力,“不仁”则表示身体麻痹,失去了感觉能力。所以,麻木不仁是恻隐之心丧失的标识,而“人而仁”则是恻隐之心得到良好展开的表现。恻隐之心持续不断的扩充过程亦即人的道德挺立过程,“成仁”便标志着人的完成。个人道德挺立过程的关键便在于是否保有感觉能力,是否远离“不仁”而始终保持“仁”的敏感状态。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根本命题可以表述为:我仁故我在。[注]此命题的表达形式乃参照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而来。笛卡尔的命题高度概括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文化,其中的道德文化也以康德为显著代表充满了理性主义色彩;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此截然不同,表现为重视感觉能力的“我仁故我在”。
根据以上分析,恻隐之心为人立德的思路有力地解决了现代道德筹划失败所遗留下的人性与道德相互割裂的难题,为人的道德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也为我国当下的“立德树人”提供了来自古典传统的思想资源。
三、恻隐之心为人立德的现代意义:保存并扩充人之感觉能力
恻隐之心为人立德思路的基础和关键都在于保存人的这份恻隐之心而不失,并加以扩充,最终实现人的道德挺立。这在孟子的道德教育哲学里被概括为“尽心”。恻隐之心为人立德思路的教育意蕴和它对当下的意义也在于指引我们力求保存并扩充人的感觉能力,以生成普遍的善意和相应的善行,使人成为道德的人。
需要说明的是,恻隐之心意义上的感觉能力不同于设身处地意义上的同情能力。恻隐之心常常被理解为同情、怜悯的情感,这种理解虽未切中肯綮——恻隐之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对他人当下境遇的感觉能力,怜悯情感的产生包含在感觉能力之中——却也没有脱离本义。由亚当·斯密提出的设身处地意义上的同情却与此不同。亚当·斯密说:“由于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经验,所以除了设身处地地想象外,我们无法知道别人的感受。”[7]这种设身处地实则需要一个较为复杂的思维过程,需要经由想象才能感受他人的感受。与此不同,恻隐之心是一种直觉触发式的感觉能力,不需经过任何设身处地的想象程序。
所以,在恻隐之心为人立德的思路中,关键不是培养人设身处地的道德想象力,而是帮助人保持心灵的柔软度和鲜活度,不要放任它变得刚硬、冷漠或自我封闭。“为角色、地位、利益等等所分化的社会成员,常常是在共同的道德理想与原则影响与制约下,才以一种不同于紧张、排斥、对峙等等的方式,走到一起,共同生活。”[8]当下这种分化愈演愈烈,在此情况之下如何为人确立保证共同生活的道德理想与原则?我们常常从“道德何以必要”出发思考这个问题,殊不知诉诸必要性仍是一种功利思维,无法为道德的确立提供绝对的担保,而只有解决道德何以具有现实可能的问题,才能有力地为人立德,构建和谐、融洽、美好的群体生活图景。而这正是恻隐之心为人立德的思路:保有一颗活泼泼的心灵,人心自然拥有敏锐的感觉能力,从而对他人的苦难困厄感到伤痛并施以援手,对他人的快乐幸福感到愉快并成人之美,对他人的一切境遇都敏感且恰当应对。在当下这个人与人之间分化愈加严重的时代,保存并扩充人心的这种感觉能力,重新唤回已经丧失恻隐之心者的这种感觉能力,不论对于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化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