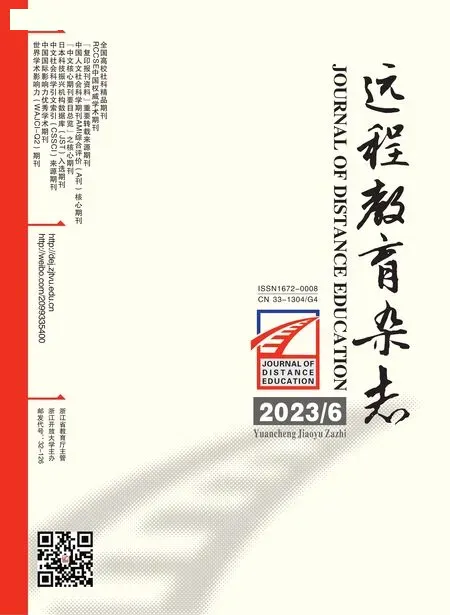从“失序”到“有序”: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转向及其生成机制
2023-12-27吴南中陈咸彰
□吴南中 陈咸彰 冯 永
一、引言
2022年11月30日,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OpenAI 上线了基于GPT3.5 的大型自然语言模型Chat-GPT,它不仅能完成一般意义的对话,还可以在不同领域显示其高超的通用问题解决能力,将人工智能中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与实践提升到了新高度,也掀起了各界围绕人工智能开展创新的实践。在教育领域,众多学者对其应用模式和使用策略进行了基于不同视角的探讨(吴砥,等,2023;卢宇,等,2023;焦建利,2023;郑燕林,等,2023)。从科技与人的关系视角审视教育中ChatGPT 及其类似模型的教育应用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创造的工具,是实现人类特定目的和满足特定需求的产物。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将事务发展为一种不确立的状态,当个体对技术理解不深的时候,容易根据个体的局域性理解或者片面性理解,自觉采取公开或隐蔽抵制的状态,容易形成一种基于自我选择和自我强化的新的不平等。“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Mesthene,1970)尽管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改变了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现代人无法改变的历史方向,成为具有双重功能的“座架”(Heidegger,1977),但技术本身并不是“异化”为导向的特异性工具,而是可以利用的时代智慧结晶。ChatGPT 一经发布,就快速嵌入到教育的各个领域,成为教育中的技术新势力,造成了“技术悲观主义”的紧张与焦虑,也支持了“技术乐观主义”的狂欢,给广大民众造成了认知冲突和行动迟疑。本研究旨在分析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到教育领域的利弊,以“技术善用”“器以成道”的实践诉求,有意识地进行教育的结构、功能和关系等机制的调整,使ChatGPT 服务于智能化时代“整全的人”的培养(刘铁芳,2017),落实新时代教育所呼吁的“大规模个性化教育”形态,提高教育的整体效率。
二、“剑之两刃”: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立场
ChatGPT 是基于“Transformer 结构”和“回归+Prompting”训练模式的人工智能模型,其核心是通过回归算法、预训练和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等多举措,实现多类任务生成,具备极高自主学习能力、现实推理能力、人类理解力,呈现了易用、仿真、通用等品性,是近年来深度神经网络、大型语言模型共同作用下,算法、算力、存储的多维支持下的重大人工智能阶段性成果(Wodecki,2023;Hirosawa,et al.,2023;朱光辉,等,2023)。ChatGPT 一经发布,就在教育领域引起了轰动,高等教育体系更是迅速跟进,不仅学者们开展研究与实践,大量学生也应用ChatGPT 做设计,甚至毕业设计,这对传统教育体系至少在目标定位、教学资源生产和教学过程重塑上产生了较大冲击。然而也有个体基于抵抗的战术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进行抵制,比如害怕学生作弊而禁止学生使用ChatGPT。ChatGPT 作为一种典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具有应用价值,但也的确存在被异化的风险。全面认识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异化风险和应用价值,是其服务教育发展的前提条件。
(一)教育“失序”:技术悲观主义的立场
1.质量失控: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学习内容风险
“教育质量是指教育所提供的过程、方式、内容实现的结果满足所规定的标准的程度。”(金生鈜,2022)ChatGPT 的出现,意味着基于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智能内容全面侵蚀和冲击教育的内容体系,可能导致教育整体性的内容传播失控,给教育带来了质量风险。一是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导致教育的完整传播链条被肢解。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教育中的知识不是传授的结果,而是唤醒学生内在的真知并予以挖掘,教师自己只是“电鳐、助产士、牛虻”(汉娜·阿伦特,2006);约翰·纽曼(2001)也认为教育过程中需要学习者主动进入知识领域,通过思维行动迎接教育事实。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和过频使用,会导致深度思考机会的减少,难以以思维的行动唤醒大脑的运行,容易从整体上降低教育的质量。二是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会改变教育的内容,提升教育内容的不确定性。由于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了基于预训练的“涌现”内容,这些内容缺乏科学的考证,是已有知识片段生成的结果,如不加以约束会影响学习者学习质量。
2.运行失序: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教育责任主体分散
在教育体系中,责任是教与学关系建构中自身需要承担的角色和功能,是一个基于行动体互动衍生出来的关系性产物和一种特殊的主体间行为。比如ChatGPT 的出现,带来教和学的责任分散问题。从教的角度看,由于ChatGPT 的引入,教师的责任从垂直集中变成了分散交叉,这种交叉的一支是教师,另一支是ChatGPT 所产生的教育内容,这种由于内容“交叉”可能产生的“偏差”或者“误导”,其责任后效甚至挑战了国家对教育的控制。从学的角度看,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新的知识渠道,尤其是在学习过程中以“Chat”为核心的陪伴效应,使学生感受到了具有个体独特性的关怀,这种途径对教师主导教学形成了挑战,由于知识传导形成的安全责任体系坍塌。
3.伦理失调: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学生学业伦理风险
技术应用带来的教育伦理问题担忧和现实困扰由来已久,主要集中在“教师职业倦怠”“学风不良”和“学术不端”等领域(杨洁,2016;于英姿,等,2020)。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带来了学业主体缺失、学风向浅、学术不端等伦理问题。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度介入带来了“主体缺失”的伦理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使过往需要不断寻求知识的过程被简化,学习者学习自主性被机器“喂养式”投放所压制,学生参与集体讨论和共同体活动的机会和时间变少,容易出现技术支配下的“空谈主义者”。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度介入导致对问题的分析流于表面,形成“学风向浅”的问题。长期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问题,容易导致学习者对知识的追求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知识本体。三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了严重的学术不端问题。国外有研究发现,有89%的美国大学生尝试使用ChatGPT 完成家庭作业,有53%的学习者使用其撰写论文,有48%的学习者依赖其完成考试(冯雨奂,2023)。
4.认知浅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学生认知结构“薄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容易导致“生成式人工智能沉浸”现象,表现为既有精神层面的工具依赖,也有身体层面的“失身现象”,还容易导致认知结构的变化,产生类似“谷歌效应”的“认知浅化”问题。一是形成学习者学习的浅尝辄止、走马观花。由于“问题比答案重要”,个体不再需要对知识进行深度加工,学习者容易陷入表层学习之中,无法利用批判性、创新性工具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导致认知结构的“薄化”。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了同质化交流,导致无法通过同步相互启发性交互实现认知的深化。由于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的是同样的数据库,当核心问题一致时,容易形成大致相同的内容。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依赖算法输出内容,是具有“套路和模板”的“知识”,这种模式容易形成海德格尔所提及的“技术使一切都化为千篇一律的和无本质的东西,否决事物所享有的等级,并抹杀了任何区别。”(冈特·绍伊博尔德,1993)三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剥离了身体的参与,形成学习中身体的“离场现象”,导致学习者认知结构的“薄化”。在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塑造的环境中,由于结果与学习者提问方式和过往行为特征密切相关,形成了“信息茧房”现象(张刚要,等,2021),以及“假象的知识获得感”。“真实的经历”对学习者而言没有了意义,导致学习者不愿意通过实验、实践来认识知识本身,无法实现伽达默尔(Gadamer)所阐述的“视域融合”所需要的状态,导致深度学习难以形成。
5.创新堕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学习者创新缺失风险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给学习者的创新能力培育带来了影响:一是降低了反复练习的参与。人类创新的基础是较多的重复和反复练习(高奇琦,2023a)。也正是如此,我国先贤提出“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强调了创新中反复练习的作用;吉尔·德勒兹(Deleuze,1994)也有类似阐述重复产生差异的观点。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快速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学习者完成学习任务时无须反复去揣摩其中的深度含义和内部结构,因此无法实现创新所需要的重复状态准备。二是过于寻求快速解决问题的路径依赖。阿兰·巴迪欧(Badiou,2013)将创新描述为“一种事件,即一种形势的溢出,一种未预期的结果。”快速解决问题意味着学习者给大脑“给养”的是“多巴胺”而非“内啡肽”,学习者持续保持敏锐性的能力缺乏,产生意料之外结果的可能性降低。三是内容一致性降低了学习者创新的动力。在学习共同体运行的过程中,内容一致性会造成团队消耗大量的注意力在同质化的内容上,个体成为对同伴无意义的“节点”,从同伴获取创新动力和灵感的机会被消除,创新的难度加剧。
(二)教育的“变革”:生成式人工智能延展了教育的“身心”
作为一种具有暴力美学特征的技术性作品,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对教育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呈现的强情境化、重整合化、个体差异性和批判“体质”的特征角度来思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现实应用,形成了“技术乐观主义”派系,认为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破坏性创新效应”形成“教育变革”,为教育发展创造机会。
1.空间重构: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学习者打造个体化的专属情境
学习空间是指蕴含学习的发生场所、场景,以及背后关于学习者学习的设计与信息技术增强等隐喻的空间(郭绍青,等,2017)。在教育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学习空间将开放获取、自由参与、互动交流等特性纳入其中(吴南中,2017),实现了学习、数据、技术等多种要素的统整,强化了“主动化、社会性和个性化”等隐喻(许亚锋,等,2015),成为学习者学习效率和质量的关键性变量。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背后是基于强大算力和通用算法支撑的“万智聚集”,学习者提问方式不同、提供的参考模板不同、关注的角度不同,都会形成独特的内容及其学习情境,促使学习者形成“自适应”的状态,进而与情境感知技术等配合,为学生创造自适应学习条件,支持学习者自由灵活地开展学习。
2.内容重建: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知识生产瓦解单一知识来源
从技术特征来看,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通过“大规模通用训练+指令微调”的方式进行文本内容生成,其中还嵌入了人类偏好作为奖励信号对生成内容进行以奖励信号为标志的创造,其实质是形成“人机协同”的知识生产模式。这一知识生产模式实现从经验生产转向数据生产,并从生产速度、数量和创新方式上发生了改变(高奇琦,等,2023b)。这种内容生成不是简单的“抄袭”或“剽窃”,而是“非意向性”与“非创造性”结合的知识,是一种根据已有知识的“集成性创新”,类似于“电机技术”“电池技术”与“汽车技术”的结合,产生了技术集成体“新能源汽车”。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涌入课堂,场域中的知识来源在课程、教师、同伴的传统结构中增加了智能技术这一因素,使得为每个学习者生成独特的、契合自身需要的学习内容成为可能,跨领域、跨区域、跨国家的成果被世界化,以重命名、重分类、重组织的方式支持学习者的学习,大规模个性化学习所需要的个性化内容制约有望得到彻底解除。
3.能力重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延展“整全的人”培养意涵
个体成长是遵循身体自然性发展和教育性发展双重秩序的过程,身体自然性发展是自身身体机能自然生成和身体感官能力自发成长的结果;教育性发展指的是通过教育的方式与外部进行联动,包括知识、技能、情感等维度,是身心能力和技术、制度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个体成长受到“身”“心”的双重制约,“身”之核心是学习者自身的体察,“心”之核心是学习者的体验。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延展教师和学习者的“身”“心”,影响了“教”和“学”的能力,最终体现为学习者能力的重构。首先,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拓展了学习者的“身”。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浩瀚的信息来源和强大的整合工具,对知识和信息形成了整合效应,师生所接触的知识及其情境得到极大拓展,提供了师生提升能力所需要的“营养”。其次,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义肢”支持,优化了学习体验。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实时交互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为学习者沉浸式、自助式、自适应式学习创造了条件,在强调“身体在场”的同时,提升“心理聚集”的效果,服务于席勒(1985)强调的“形式与内容丰富、感性与理性融合、温柔与刚毅并举的人”的养成。
4.过程重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重塑教学实践模式
传统教学过程遵循培根、笛卡尔、牛顿等人在工业化背景下提出的分割理论所建构的过程逻辑。按照分割理论的逻辑,世界是决定性的、必然性的和静态性的(杜炜,等,2016),课堂也可以按照“固定化、逻辑化、边界清晰化”来建构(吴南中,等,2020)。比如将课堂分为“三步五环节”(许崇文,2011)“四环节”(林允修,2011)等教学过程模式,知识、情境和学习者之间密切的联系被切割成为相互独立的整体,形成了格式化、封闭的课堂。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通过开放、整合和生成的理念,促进了教学过程的“生成性”变迁。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裹挟的开放理念,瓦解了师生封闭关系,为教学过程重构建立了基础。要打破传统教学过程,需要借助教学空间形成开放的场域,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所生成的知识和使用模式是“众智”的结果,其发展有效架构了开放课堂的“基座”。其次,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内容及时性生成能力,将“线性逻辑”转化为“任务逻辑”,形成了复杂任务教学的整体性立场。在传统教学中,学生获取最终知识需要通过探究或者讲解等“历时性”的过程,ChatGPT 可以不断围绕任务进行问题的回应,传统课堂的“线性逻辑”转化为以“复杂任务”解决为过程的“任务逻辑”,教学不再是“四阶段”“五阶段”的分裂,而是“教师-学生-资源-工具”多层次交互的任务解决式过程。再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生成,促进了关系建构课堂的生成。由于知识不再是“确定性生成”,而是ChatGPT 等根据提问形成的个性化知识,教学关系形成了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真实有效交往关系,即便认知本身先行于“已经寓于世界的存在”(海德格尔,1987)。但学习者参与的方式和过程是未知的,这种未知性使课堂充满多变的灵性。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自身的不确定性是批判的“活目标”,其课堂过程强化了以批判为手段的教学环节。由于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不确定的,教师和学生首先需要理解这种不确定性并进行真伪性思考和判定,这种过程实质是一个判断性思维形成的过程。
5.评价重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打破传统评价的固化逻辑
长期以来,教育评价基于“效率优先”的功能主义立场和“道德至上”的价值立场开展各类行动,“标准至上”“结果至上”成为教育的异己性力量,对教育评价异化的批判呈漫山遍野之势,其中最大的症结在于以“存储数据的能力确定个体的差异”(檀慧玲,等,2018),以“短视化、片面化、简单化和传染性等为特征”的评价模式(崔保师,等,2020)。在数智化的社会形态中,需要更强敏锐性、更娴熟工具技能和更全面资源整合的过程,来驱动教育评价从“内脑”转向“内外脑”联合。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更是需要加速这种评价的形成。首先,推动教育评价走出“知识”的“窠臼”。在ChatGPT 及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范域,“思维比知道重要、问题比答案重要、逻辑比罗列重要”(沈书生,等,2023),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需要在评价体系上的引导和制约。其次,推动教育评价从结果走向过程。在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作用下,知识的地位逐渐下降,解决问题能力评测的关键能力,可以推动评价标准从传统固化的知识目标转向以核心素养为基座的能力标准。再次,推动教育评价从选拔走向理解。传统教育评价主要是服务于选拔的,“既分高下也决生死”。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弱化了任务结果的尺度,将学习者学习和教师教学的全过程进行整体的获取,形成了促进追求教与学内在价值、涵养师生品性和激发教师教学提升动力的评价过程,强化以理解为基础的多元主体关系性和协作性评价网络的建构。
三、从“批判”到“应用”转换: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实践诉求
尽管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潜在功能分析层出不穷,但其实际应用仍停留在浅尝辄止层次,不管是“异化”的预期还是“应用”的图景描绘,仅仅停留在可能性分析上是无意义的。从教育实践智慧角度看,没有实践存在就没有生成,而教学实践的生成性直接根源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实践本身的人为性。换言之,教育探索的意义需要从理论理性转向实践理性,建构智能化时代“何以如此”以及“如何行动”的“应然”(李太平,等,2014),以成就世界和改变世界为指向的“技术向善”逻辑,从“必然的结果”中寻求符合自身利益需求的逻辑与规律,来创造一个融入ChatGPT 等多种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新客体。
(一)转换价值:现实诉求与未来发展的交织需求
1.强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成为教育发展的现实必然
从现实诉求来看,纵观教育的发展史,从“痒序到私塾”,从“官学”到“公学”,教育是一部与技术互动的历史。在现代,教育与技术的持续不断竞争,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产生的主要诱因,这种现象被哈佛学者称之为“教育与技术的赛跑”(克劳迪娅·戈尔丁,等,2015),并指出:“当教育发展超过技术时,会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反之亦然”。当前,以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但教育仍然在犹豫和徘徊中止步不前。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驱动力,对社会已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延伸、渗透至社会的各行各业(顾小清,等,2021)。有学者称“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和创新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驱动力,并正以指数发展的趋势推动社会以超越人类预期的方式发展。”(Seldon,et al.,2020)从教育运行来看,ChatGPT 等工具以无法阻挡之势进入了课堂,成为“改变的力量”。这迫切需要教育研究者思考其成效转化,促使其“应用向善”,实现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增能”。
2.强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实践转换代表教育的发展趋势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其衍生的工具对教育的冲击必然会延伸到教育的围墙之下,同时也延伸到社会之中,这种工具的广泛使用强化了学生大规模个性化学习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同时也会冲击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组织形式、教学过程和教育评价,这需要强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一是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于高阶能力养成的人才培养。未来人才培养必然走向高阶培养,核心是基于深度学习,培养具有批判和创新能力的人。二是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规模个性化教育。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意味着教育领域知识生产和内容生成成为新的“基座”,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大规模个性化教学”成为可能。三是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个体自适应学习。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伴随性的工具,有望实现自定步调的自适应发展。四是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教育系统评价改革,真正地扭转教育的功利化取向导致的人的异化。
(二)转换逻辑:制度与文化规制下的渐进发展
对教育中人工智能的应用“诘难”难以通过一蹴而就的模式实现扭转,在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其科学的应用中,也不能将其作为教育常量来对待,以“元素”“组件”“构件”等形式成为教育变革的“独立支柱”;而是需要在“人工智能+教育”的整体框架下,认识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场景中的应用,探讨它与制度、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互动机制,进而推进以人机交互为基本样态的教育构建性运动,以渐变模式建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生态。
首先,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作为制度与文化规制的起点,探讨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用于教育应用的普遍性逻辑,将普遍性孕育于制度和文化的整体环境中,促进渐进性生成。缺乏制度和文化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制容易导致“不用”或“滥用”等极端情况,通过规则、程序、组织和价值观念的引导,生成一套分散于教育制度的规则体系,形成循序渐进地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环境,是对冲“技术异化”影响、形成具有“实践智慧”价值路径的有效办法。其次,揭示制度、文化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互动机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质是人的主体性让渡于技术,它的应用本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的主体与“技术”的主体之争,是制度与文化和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互动的主要形态,后者的产生才刚刚开展,对教育主体理论建构的影响也是逐步生成的,尤其是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逐渐脱离了封闭知识所规训的“身体”,需要人关注生命、本能、欲望等人的整全性表达,改变了教育的形成过程。通过理解制度、文化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互动机理和渐进式互构方式,既是谨慎将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工具、方法、手段的基础,也是发挥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居间式”存在的现实依据,以满足精准、个性和灵活的教育体系建构的现实要求。再次,要发挥制度、文化与技术的联动、协同和演进机制,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建构。一个技术嵌入到教育本体之中,与教育本体联动,形成满足功能期待的“互构体”,需要长时间的沟通、接纳、协同和共同演进。从技术接受度来讲,庞杂教育体系的整体改进需要逐渐的推进;从制度工作重心而言,需要形成时序逻辑,才能有足够的保障能力,比如对ChatGPT 等人工智能的技术培训和器械支撑。从演进逻辑来看,成熟的应用需要建立在初始的“物化性”“偶发性”尝试经验之上,其完备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三)转换目标:以深度学习服务学习者大规模个性化教学
实践理性的“应该”与“做”是建立在对“是”的欲求、选择、评价基础上的“做”的要求、期待和决断(徐长福,2001),也是如何“做”的基础。在当前情境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作核心是促进深度学习,服务学习者大规模个性化教学,实现完整的人的培养目标。首先,大规模个性化教学契合智能化时代的人才培养目标。从理想社会和人的进化双重视角思考,理想社会是机器释放生产力、服务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而人发展的目标是形成与社会契合的“时代新人”,具体而言就是“人机协同、人机和谐”发展的整体状态,人与社会的交织就是智能时代的新型人机关系和人机文明。这样的人和社会关系建构需要充分发挥人的潜能,核心是通过大规模个性化教学对人潜能发展的释放。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可能效用能够支持大规模个性化教学的整体形成。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本质是教育中“身”和“心”的延展,主要是通过教学逻辑的改变,以技术、制度和文化的互构关系,塑造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环境和目标。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就是需要将这种可能性,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现实的构建,成为“实践力量”。再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实践转换需要契合现实环境的现有基础。尽管民众对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场景描绘了一种可能性,但其实现需要契合现实环境,需要多种要素的培养。为实现大规模个性化教学的理想,需要强化教育的实践应用,根据实际环境情况,产生一个非均衡的教师发展链条,并逐渐随条件的变迁和应用模式的优化,完成均衡化的转变,以此促进大规模个性化教学的形成,最终实现融入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隐序逻辑的新平衡。
(四)转换支撑:以学习的通用设计形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生态
自ChatGPT 提出之后,学术领域对它的探索层出不穷,有教师开始在多类学科教学中进行探讨性应用,比如陶哲轩(2023)在其数学课上利用ChatGPT解决数学问题,并让学生以此为基础进行判断、调整和完善。这种零星的探索不能止步于先觉者的探索,而是需要在把握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教育发展的真实境脉中,学者对其开展的理论逻辑、模型方法和蕴含的内在价值体系中,提炼出一套有意义的通用设计,支撑更多研究者和实践者据此开展有效探索。首先,将服务完整的人的培养和支持学习者大规模个性化学习作为学习通用设计的“基座”,以“人机协同知识创造”和“人机协同文化建构”为目标设计学习的通用模型。无论是为了“知识”而设计还是为了“学习”而设计,不同的出发点会产生不同的设计类型,以知识转化为目标的经典设计模型旨在设计知识的有效传输路径,以学习为目标的教学设计旨在形成情境的建构。人工智能时代凸显人自身价值的是人具有知识创造的能力,核心目标是培养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完整的人”。其次,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逻辑下,完成学习通用设计的理论建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作用预设下,以精准设计学习和智能辅助学习为方法论,结合认知科学的“脑活动模型”等关于人脑的识别网络、策略网络、情感网络等对学习者学习的通用过程的支持(霍尔,等,2019),配合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教学模式和致力于人机协同智能认知结构的认知模型,形成学习的通用设计理论基础。最后,借助模型方法完成通用设计的结构呈现。要实现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整体设计架构,核心是形成具有参考意义的直观性模型,形成基于科学共同体所秉承的“信念、象征意义和评判标准等构成的整体”(李蓉,2018)。为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提供合身、平等、个性、易用、舒适和文化适宜的支撑框架,同时需要借助设计规避异化的风险,帮助学习者更好地适应、创新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习。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实践应用的生成机制:基于动机与联结的分析框架
生成式人工智能实践应用需要从技术、制度和文化的整体范畴来考察,其生成机制的建设既要考虑技术与教育的结构性关系,又要理解技术与教育的本质相异属性,以及在教育应用过程中需要综合个体性、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从整体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的互动可以参考“科学-政治”的结构关系,其生成机制可以理解为“因相互关联而总是规律性地导致某一特定社会结果出现的一系列主体和行为的组合”(赫斯特洛姆·彼得,2010)。实现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及其背后的技术属性和个体社会结构连接关系建构,其本质是个体和组织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动机(与技术、制度和文化相关),以及联结(形成的机会和规则性力量)的互动过程,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技术、制度和文化互动关系作为结构性变量嵌入到教育体系之中,进而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成机制。本研究梳理为“动机-联结”分析框架,支持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协同共生,并在这样的生成机制中,将人的培育根植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塑造的,涵盖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理想生命融合的发展场域中,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摆脱异己性力量和自身异化的可能性,使之成为支持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支撑性力量,进而建构以“诗意栖居”为追寻的教育环境。根据动力变迁与联结类别,可以将机制分为顺应型机制、响应型机制、主动型机制和建构型机制,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动机-联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转向教育应用的生成机制
(一)顺应型机制:强势技术力量下的工具型联结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利用,代表了来自新颖和独特的高科技社会的技术,在ChatGPT 及其相关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下,形成庞杂的社会智能系统和复杂的技术结构,人民在其整体生态面前,只能信任智能系统及其裹挟的制度和文化。在教育领域,教师和学生也需要不断接受技术的强势嵌入,除了少部分的主动者,大部分人其实是不得不参与高特技术的使用,这种状态通常是“强技术”所导致的被动参与,是一种以文化适应为特征的过程扩张。技术本身更多的是作为工具来使用,其机制构建主要是展示技术的功能性作用,创建展示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力的平台,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嵌于教育的整体架构之中,以创造更多的接触机会而形成联结。通过创造联结机会,实现与教师和学生更频繁的互动,使他们能习惯按照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倡导的教育场景及其所改造的教学内容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首先,创造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强势外在环境,具体来说,包括消费端、生产端。从消费端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望通过交流的过程,向用户深度展示产品的意义,提高各类产品的效用、曝光度,从而强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响,形成教育体系的技术认知;从生产端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交互改进产品的质量,拓展产品的类别,生成智慧陪伴、智慧学伴等产品,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强势力量下,带来智能教育及其生活模式,为学习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种强势的外部环境能促使教师和学生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为教育中的实践转换提供外部文化的力量。
其次,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示范功能。按照行动者网络理论,事物初期的转译工作通常由首先掌握行动主旨的核心行动者承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转换机制中,需要核心行动者通过案例、论文、示范、指导、培训等多种形式,展现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情境创造、教学内容生成等方面的价值,促进好奇、模仿、强制等外部驱动力,驱使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发生。
再次,创造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参与机会。当技术与潜在使用者互动日益频繁时,促使潜在使用者变为真正使用者的机会就越高。对此,提高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师和学生的互动频率,建立保障其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稳定规则,为行动者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结构化空间,是顺应外部技术力量在教育内部转化的有效方式,比如在更多的平台嵌入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接口,并通过多种尝试建立联结,使参与者能便捷地参与其中。
(二)响应型机制:强势制度力量下的功能型联结机制
“教育实践并不是一种纯粹理性活动的过程,它有其自身独特的逻辑。”(许杰,2016)这种逻辑许多学者用布迪厄的“实践逻辑”来解释,是“客观结构(社会场的结构)和混合结构(习性结构)之间的双重意义的关系。”(皮埃尔·布迪厄,2007)要改变这种关系,需要从场域(客观环境)、习性(具体行为)的内在一致性出发,这就给教育制度带来发挥空间,并且个体的能动性也是适应、协商和参与社会规范与技术互动的重要因素(张萌,2022)。当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潜力被充分证明,其异化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规则和引导进行有效规制的时候,需要形成具有特别功能目标的响应型机制,促使教育内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为契机,逐步建构相关制度,以具体应用实践、开拓视野等形式,重构教育系统内的人机关系,形成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实践转换机制。
首先,强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理论探索和制度建构。立足于“完整的人”培养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可能性,对其教育应用进行基于理论探索的价值评估和必要的学术规范建设,构建以“兴利除弊”为基础的选择性应用框架,并开展基础制度的建构探索,完成对ChatGPT 实践应用的理想状态的观念预设,和如何开展实践应用的逻辑建构,形成理想客体的“图景创造”。
其次,梳理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制度作用机理和路径。制度是功能的负载物,通过制度负载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所需要的社会场结构和习性结构,培养具有“习性”的教学整体,并设立规则,最大程度促使师生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注意力集中于正向利用、规避偏离异化效能的教育实践,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实践活动在“可见光谱”之内。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制度至少需要关注三个场景:一是秩序系统,核心是创造理性、友好和富有德性的教育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形态,回到服务人的完整性发展的基础上来;二是创新系统,按照制度所期待的“习性”来梳理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逻辑,形成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顶层设计,保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创新的活力;三是赋权系统,核心是建立审慎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则,并确立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与实践的基本原则,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控制在“奇点”之内。特别是对于基础教育的受教育者而言,他们并不具备完整的“抵制”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的权力,更多需要从“教育向善”的启蒙理念中认可,规则就是一种主动系统。
再次,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制度影响效果。技术社会的“可偏离性”意味着实践者并不是完全按照技术占有者所生产技术时的意图进行使用,他们更像是一种基于战略空间的“游牧人”,通过自己的“诡计”形成与技术生产者所期待的“变异的世界”。制度在技术社会中的作用是促进所期待的效果产生,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逻辑建构上旨在形成以人为本、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秩序时,制度对技术的释放便成为一种“正义”的力量,也就具有规制参与的可能,这就要求不断评估教育应有的效果,以“成效”释放制度的力量,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不断深化。
(三)主动型机制:自主动力驱动下的价值型联结机制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之后,除技术变革力和制度生成力之外,自发型动力逐渐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主要驱动力。自发型动力指的是人和组织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会按照“适者生存”的自然逻辑,自动更新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内在动力(夏海鹰,2014)。在自发型动力下,通常需要与学习者参与过程产生价值联结,形成人与技术的良好互动,参与者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权力、能力、使命等方面,不同的互构模式需要不同的“动机”与“联结”的结构。
首先,权力主导的价值型联结需要建立激发权力回应的生成机制。在主动型机制的建构过程中,最先切入教育实践应用体系的通常为高权力期待群体,包括拥有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政治权力等类别的群体。要激发这类人群参与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需要满足其权力期许或使其感知到权力回报,形成“吸纳-嵌入”的参与方式,并生成与权力结合的机制,促使更多人认同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逻辑、规范和边界,从而产生扩散效应。
其次,能力主导的价值型联结需要回应能力提升的生成机制。能力提升的根源在于教育是“使人成为人”和“职业选择”两个维度共同决定的结果,意味着参与教育的过程需要关注质量、职业能力的生成两个维度来建构生成机制。从质量的维度看,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过程中,需要让参与者直接感受到技术提升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体会其中的比较优势,进而促使其积极地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过程中各类别、各环节的应用模式,规避其应用所引发的风险。从职业能力的生成角度看,主要是关注资历的建构,通过标志性事件支持教师和学生的参与。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实现了参与者自我增能,在教学技能大赛中获得标志性成果,完成自身资历提升的标识,进而体会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价值。
再次,使命主导的价值性联结需要从获得感角度建立生成机制。“使命感是一种源于自我并超越自我体验的超然的召唤,其目的是以能够体现或获得一种目的意识或有意义感的方式去践行一种特定的生活角色,且以他人导向的价值观和目标为主要的动机源。”(Dik,et al.,2009)从使命感的角度看,机制建构需要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中的使命感,强调在使用过程中的教育责任传导机制、感知教育的社会理解、引导教师的职业认同等,并通过宣传、示范、体验等多种途径使教育体系感知ChatGPT等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生存状态优化,将参与则涌动的生态动力和积极的文化认同,转换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使命。
(四)建构型机制:自为动力驱动下的创新型联结机制
当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得到广泛推广之后,参与者会在熟练、批判、反思、创新等因素驱动下,产生自为型动力。自为型动力通常会取代自发型动力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主导,形成以创新实现个体与组织的意义建构。自为型动力指的是通过外部制度和环境形成的个体内部自为自主的动力,是基于文化、制度、监管和邀约等产生的内在动力(夏海鹰,2014),表现为参与目标转向自我实现,参与方式主要是创新形态。换言之,在这一阶段,参与者往往不满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简单应用,而是将它作为创新性要素,比如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学进行过程重组、建构特异的智慧化学习支持服务等,这种形态不再是保守的、被动的、修补式的形态,而是形成一种系统的建构性势态,体现为利用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创新性的模式、组织和能力来实现以“诗意栖居”为追寻的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生态。建构型机制主要包括“人与技术”的双向有意义建构的保障机制、创造人的自我实现为目标的引导机制、服务人的发展的制约机制。
首先是“人与技术”双向有意义建构的保障机制。在建构型机制为主的阶段,生成性人工智能的基础性应用场景已经建构,一般性功能已具备,主要是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创新型联结。“有意义”是创新型联结的基础,主要依靠人的主动性和技术的发展力来塑造。要完成建构型实践转换生成机制,需要加快ChatGPT 相伴随的“人的进化”,核心是以ChatGPT 等技术培育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并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性使用纳入新时代素养内容,“武装”具有智能社会特质、能参与人机协同教学、能科学提问、能引导批判等实现人机协同教学的“新型教育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我们不难发现,人并不是一种被固化了的既定存在,而是与技术在互动过程中进化的结果。因此,在建构型机制的设计中,要为人与技术的同步演化提供制度、物质等配置性资源和自为发展的权威性资源,在支持ChatGPT 改进教育的同时,支持人在教育中突破认知的局限,追求人与技术的同步演化,实现约翰·马尔科夫(2015)所期待的“增强人类”,支持“人与技术”的有意义建构。
其次是以人的自我实现为目标的引导机制。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作为最高层次的激励,在建构型机制中扮演主要调节性的力量。体现为,在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共创的教育应用过程中,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参与的教育是什么? 应该做什么? 并不懈地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其理想状态,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人的自我实现。通常来看,教育的价值包括生命发展的价值,培养社会生产能力的价值,实现政治性、效益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社会生活的价值等(杨志成,等,2013)。建构型机制的建设需要将生命性、生产性和社会性融入到教育目标中来,引导教育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元素,支持教育中的个体理解智能时代的“何以为生”和“为何而生”,将个体幸福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转换的应有之义,成就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持教育活动对个体幸福的合理性意义,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个体的自我实现感。
再次是服务人的发展的制约机制。建构型机制本质是一种创新机制,在“无人区”领域耕耘,但并非是不受约束的行动,而是需要在服务人的发展中实现教育资源的统整,进而制约参与其中的行动。因此,制约机制需要将人的培育与ChatGPT 等教育应用互动,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根植于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理想生命融合的发展场域中,以人与机器的共生为生态架构,以追求教育的诗意“居间存在”为目标,不断审视自身的行为。“居间”的意义核心是“在二者之间并 ‘居于其间’的构成境域”(宁虹,等,2019),是两者之间的交织互构,核心是需要将人的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理想生命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整体性创建,在多重复合关联中完成指向生命完整的整全性教育,使以技术为支撑、以制度为规制、以文化为皈依的教育成为可能,支持人在教育中的“诗意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