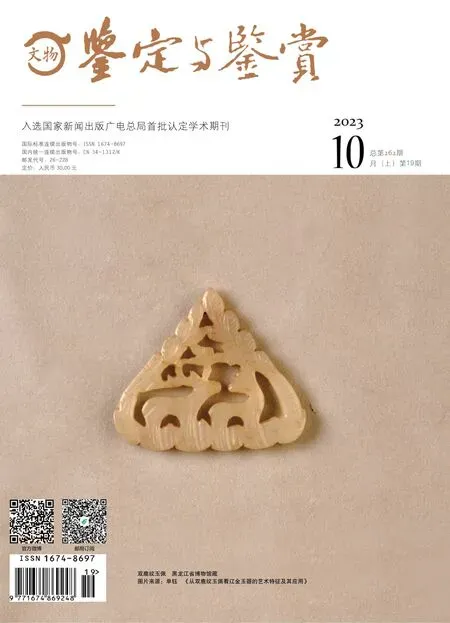文物建筑博物馆化的几点思考
--以七宝寺为例
2023-12-27周南西
周南西
(四川博物院,四川 成都 610000)
近年来,随着基层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全国各地在“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和“正面导向、注重公益、促进保护、服务公众”的原则下,积极挖掘历史文化元素,充分利用文物古建筑,打造出了各类博物馆。
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古建筑的再利用为社会常态,而文物建筑博物馆化实为近代百年来发展的主流。文物建筑①是承载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博物馆是向公众展示一个国家、地区文化的重要窗口,文物建筑和博物馆建筑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功能互补,成了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途径,也能更好地展示本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底蕴。文物建筑博物馆化的趋势似乎让沉寂的文物开始焕发生机,然而在这过程中,也暴露了文物建筑博物馆化所存在的局限性。笔者根据之前工作期间参与过七宝寺南池书院博物馆前期规划的经历,以南充市嘉陵区七宝寺为例,对文物建筑博物馆化提出几点思考和想法。
1 七宝寺基本概况
1.1 建筑格局
七宝寺,旧称龙台院,又名南池书院,位于南充市嘉陵区七宝寺镇藏珠山顶,2019年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宝寺古建筑群坐北朝南,依山势而建,由山门、前殿、大殿、文昌楼、奎星楼、南池书院六处建筑以及周边的厢房组成,占地面积约1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
山门外有四柱三间式木牌坊,面阔8.94米,高7米,坊上嵌“七宝庄严”匾。前殿面阔五间27米,进深三间10米,悬山顶,穿斗式梁架。大殿面阔五间21.8米,进深二间8.8米,高18米,歇山顶,穿斗式梁架。奎星楼于1952年8月改建,面阔七间21米,进深5米,高6米,重檐歇山顶,穿斗式梁架。文昌楼面阔27.75米,进深五间8.8米。南池书院楼位于建筑群最北部,地势最低。
1.2 历史沿革
七宝寺始建年代尚未考证,根据建筑梁架上墨书记载,七宝寺大殿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前修造,明正德十三年(1518)重修。前殿建于明成化年间,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对其进行重建。七宝寺建立之初的用途尚未明确,根据墨书可知,七宝寺后作为佛教寺庙,供奉四大天王、观音菩萨等神像,其香客信徒遍及四川,远至陕西等地。自1742年起,王灏捐资在此修建“南池书院”,寺庙在前,书院在后,寺庙与书院共存。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书院停止办学。1911年,何淦侯在此创办七宝寺高级小学,传播新学。1928年南充西区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中共南充七宝寺小学支部在此建立,成了西区革命的中心。1932年七宝寺高级小学改名为南充县第十一小学校,1938年改为七宝寺中心国民小学校,1950年成立公办南池中学,1981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改为南充市七宝寺中学,1994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为加强对七宝寺文物古建筑的保护,七宝寺中学搬迁至新址,该地停止办学,结束了其长达270年的教学历史②。
2 七宝寺展示利用规划及存在的问题
2019年七宝寺实施全面排危抢险工程,排除文物本体安全隐患。在此之前,七宝寺已历经多次大大小小的维修,但是仅限于局部排危抢险,由于长期无人使用,七宝寺便陷入了“维修-荒置-受损-维修”的古建筑维修定律,不仅伤财费力,文物价值也未能得到很好的利用。2020年七宝寺文物本体修缮工程完成后,政府便着手让七宝寺“活”起来。
2.1 展示利用规划
七宝寺古建筑群保存完整,历史悠久,从佛教寺院到书院,从红色革命中心再到近现代学校的发展,距今已有570余年,其文化底蕴深厚,承载着佛教文化、书院文化、红色文化等多种优秀文化。近现代以来,七宝寺内的教育教学工作不仅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志士,为争取革命的胜利抛头颅洒热血,也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了力量。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在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的指引下,为了让七宝寺古建筑群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以七宝寺文物古建为主体,建立七宝寺南池书院博物院的规划便应运而生。
在该规划中,七宝寺南池书院博物馆将立足于七宝寺的发展脉络,深入挖掘其承载的文化元素,通过展板、沙盘、VR、场景复原等辅助方式,展现七宝寺在不同时期产生的价值和作用,让观众能直观感受七宝寺的魅力。整个展览将最大程度也保留并还原七宝寺各建筑在每个时期的使用功能。其中七宝寺山门将作为展馆的序厅,展示七宝寺的历史发展沿革,展出对七宝寺的保护成果;前殿将利用沙盘及动画等方式,展现七宝寺建筑的修建、重修历程,使观众对七宝寺建筑群的发展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大殿将用于祭奠孔子;两侧厢房将详尽地展示七宝寺所承载的书院文化;奎星楼、文昌楼、南池书院暂定为研学、文创区域;七宝寺文物本体周边建筑将用于展示红色革命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该规划中通过动静分区等方式,既能让观众切身感受七宝寺古建的清幽静谧,又能通过展览、研学教育、非遗体验等活动使观众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凸显嘉陵地区文化地域特色。
2.2 存在的问题
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文物建筑博物馆化最大的优势是可直接利用文物古建筑现有空间,避免古建筑闲置而导致资源浪费。因而建立七宝寺南池书院博物馆的构思以及出发点是利于文物建筑的保护与活化利用,但是古建筑群的群组式布局、柱子及高度、空间形制与现代思维的冲突等这些问题都是硬伤③,也是其他县(市、区)文物建筑博物馆化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
一是主题定位模糊。七宝寺文物古建筑群既是寺庙建筑,又是书院建筑,同时也是革命文物,像这类建筑在特定的时间段具有特定的使用功能,它的文化特性较为明确,所以在博物馆化的过程中也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主题定位的。倘若把握不好该建筑的文化主题和基调,那么在对其博物馆化的定位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现象,或者是文化元素缺乏主次,使博物馆化的方向出现偏差,不能使文物建筑的优势发挥到最大。七宝寺南池书院博物馆在规划之初,对于将其建设成综合性博物馆还是专题性博物馆还是欠缺考虑的。七宝寺发展历程较长,其文化元素较多,作为嘉陵区拟建的第一个国有博物馆,想借此机会和形式将嘉陵区的历史文化也糅合在里面展示出来,这就导致展览内容未进行合理的筛选和提炼,出现了大杂烩的现象,造成展览内容和展览主题不一致。同时没有一条主线支撑,各个板块内容不能有机融合在一起,不能凸显七宝寺南池书院博物馆的主题特色。而后在专家学者的反复研讨下,根据七宝寺“前寺院、后书院”的布局和建筑特征,拟在展览中弱化七宝寺中的“佛教文化”,只通过建筑本身的形式的向大家展示这一文化元素,“红色文化”则利用文物本体之外的现代建筑进行展示,文物本体内主要以“书院文化”为主线,讲叙七宝寺作为教育圣地的重要影响。通过这样的调整,七宝寺南池书院博物馆的主题定位更为清晰,也能更好地起到博物馆展示、教化育人的作用。
二是文物藏品单薄。“博物馆陈列主要是以藏品为基础进行的,如果离开了藏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④对于博物馆来说,文物藏品是博物馆展览的重要元素,也是展示文化的重要途径。嘉陵区因建区时间不长,目前南充市嘉陵区文物保护所可移动文物数量、文物种类相较于其他县(市、区)略逊一筹,其中与七宝寺南池书院主题相关的文物仅有存于七宝寺内的三块碑刻,当前可移动文物现状不能很好地支撑七宝寺南池书院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七宝寺虽然地处嘉陵、西充、蓬溪三地交汇之处,交通便捷,但是仍处于乡镇,距城市中心较远,如若七宝寺南池书院博物馆没有精品文物展出,在某种程度上会缺乏一定的吸引力。根据目前该馆的主题定位,对于书院文化的阐释可以借助场景还原、节目互动等方式营造氛围,实现博物馆展览“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来弥补文物藏品单薄的缺点。如阆中古城内的川北道贡院通过还原科举考试各个环节的场景,以及每日定时场景演出的方式,增强观众对于科考制度的认知,引导观众体验古人科考场景。
三是文化挖掘不够充分,七宝寺在古文献中的记载仅寥寥几句,多为描述七宝寺的地理位置,其中也有一些文人的游文诗赋;在图录资料中,仅《中国文物地图集》中记载了七宝寺为市文物保护单位时的资料;在学术研究中,仅有《七宝寺与近代南充西区革命》一文研究了七宝寺与南充西区革命的关联性,其余未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因年代久远,七宝寺近代之前历史发展信息更多来自附近居民的口述,其内容的真伪还需辨别。此外,七宝寺建筑梁架上有墨书80余处,多数均有明确纪年人名等,是考证七宝寺历史不可多的一手资料。嘉陵区文物部门的文博专业技术人员不足,文物工作任务重,导致七宝寺文化内涵的挖掘不够深入。尽管社会各界很关注七宝寺,但是能够采纳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成果资源均是十分有限的。在七宝寺南池书院博物馆的陈列规划中,囿于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还未形成完整的学术研究体系。在陈列展览的设计中应避开有争议的问题,将达成共识且符合七宝寺发展史实的内容展现出来,以免出现知识性错误。
四是展览空间零碎。在文物建筑的基础上建立博物馆不同于新建现代建筑博物馆。新建博物馆展厅面积大、层高足、展览路线规划合理,布展灵活性较强。文物建筑内的博物馆常受文物建筑格局的限制,文物建筑空间多狭小、零碎,易将展览中统一板块中的内容割裂,导致观展的流畅度和连续性不强,这个问题在文物建筑博物馆化中普遍存在。七宝寺目前有49个面积大小不一的房间,对于陈列展览来说,整体空间较为松散,内容的设置是一个挑战;对于博物馆内展线,是在整体考虑七宝寺及周边文物建筑的参观游线基础上,综合文物内的陈列展览所设计的,由于文物建筑空间布局的特性,部分路线会重合,使展线设置相对于现代建筑博物馆来说略显不合理。
3 对文物建筑博物馆化提出的几点思考
在文物建筑博物馆化的过程中,有的文物建筑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发挥了文物建筑和博物馆之间“1+1>2”的文化效益,但是有的文物建筑博物馆化在前期规划、实施过程或者后期运行维护中偏离了初心,忽视了文物建筑和博物馆最本质的作用,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导致文物建筑博物馆化变味变质。因而在文物建筑博物馆化的大背景下,作为文博工作者,我们该如何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经营真正惠民利民的文化事业,笔者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
3.1 立足文物建筑本体,凸显文化地域特色
文物建筑是该地区文化地域特色的一个缩影,也是该地区文化的重要载体,正是由于这种地域特色,才使文物建筑得以保存至今。对于区县级的博物馆建设,要立足本地区的文物地域特色,挖掘文化资源和内涵,扎根在群众中,在精神层面上服务我们的观众。文物建筑博物馆作为展示地域文化的窗口,首先是要立足于文物建筑本身的文化特色,切莫为了博物馆的展览丢弃了本色,一味迎合现代化发展,打造与原建筑本体不相符合的功能,这样会让观众感觉到突兀。文物主管部门一定要严格把关,在利用文物建筑的时候,要综合考量文物价值、保存现状、社会影响力、敏感度等因素,要根据文物本体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在文物建筑博物馆化的浪潮下,越来越多的文物建筑内都建立了博物馆。对于交通便捷靠近城市中心的文物建筑将其利用为博物馆,可以打造新的文化地标,赋予文物新的文化活力,发挥文物的价值,带动本地区的文化发展,也是对文物活化利用的成功实践。但是将处于偏远乡镇的文物建筑博物馆化,我们就应该分情况讨论了,毕竟不是所有博物馆化的文物建筑都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尤其是七宝寺所处的情况,应立足于本地区文化特色,将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放大,并将其赋予文物本体建筑,放眼未来,打造一个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并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博物馆。
3.2 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通学术“最后一公里”
县(市、区)文物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不足似乎已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博、考古专业类的技术人员被引进到基层文物部门,整体人员架构的学历、专业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在偏远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人才严重不足的情况,许多基层文物管理部门在增编无望的大环境下,只能一人身兼数职,导致工作人员忙于日常业务工作,无法全身心地投入理论研究工作,加之缺少先进、前沿的理论指导,容易在实践的过程中偏离轨道,目前在部分文物建筑博物馆内,我们依旧可以发现许多知识性错误,长此以往,博物馆会丧失在公众心中的权威和信服力,不利于博物馆工作的开展。
在古建筑博物馆化的过程中,离不开先进学术理论的指导,如何在烦琐的工作中、在工作人员紧缺的情况下依旧能够保障学术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这就需要政府、高校、社会团体之间的协作。基层文物部门可以充分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一手文物资料,联合社会各界专家、高校学者等权威人士,建立智囊团,深入透彻且准确地挖掘文物古建筑以及本地区的文化内涵,开展与该文物建筑和博物馆相关的学术研究,力争做到展出内容具有准确性、学术性以及引领性,真正打通学术知识贯彻到实践中的“最后一公里”,使专家学者接触到一线文物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研究,也能让专业技术人员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丰富理论知识,拓宽学术视野,更好地服务于博物馆化的古建筑保护利用。
3.3 合理规划,科学利用,促进文博事业可持续发展
文物建筑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我们精神文化的重要支撑,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对文博工作者的本质要求。将文物建筑博物馆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尊重文物建筑的文化内涵,厘清该文物建筑的功能,明确文物建筑在特定的场合下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该文物建筑是具有社区服务类性质的,那么可以建设乡史村史馆和社区博物馆,并在文物建筑及周边增加社区书屋、公益讲堂、文化站、管理用房等,开展文化活动,发挥服务功能;如具有文化展示作用的,我们可以进行文物建筑现状展示或进行陈列布展,发挥文化传播、科研和教育功能。
文物建筑博物馆化前期的规划必须合理,后期的利用才不会偏离航道。很多文物建筑内建博物馆缺乏合理的规划,缺乏长远的发展目光,在后期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差强人意。不利于博物馆工作的可持续开展。还有一些地区没有考虑经济发展的速度与人类对文化的渴望成正比,在文物建筑内建立的博物馆,其基本陈列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知识的需求,而临时展览又受场地、空间的限制,不能打造精品展览,所以就会考虑重新选址新建博物馆。长此以往,文物建筑被闲置,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文物建筑博物馆化不能仅仅立足于当下,要充分考虑到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寻求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打造能够真正立得住脚的博物馆。
4 结语
文物建筑博物馆化的逐渐成熟,是对文物建筑最大的保护,也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良好契机。在当前这股文物建筑博物馆化的热潮下,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学习优秀的案例,就是为了寻求文物建筑与博物馆合理结合、科学利用的方式,也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注释
①本文中的文物建筑定义是指《四川省文物建筑开放利用指引》中规定的“依法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古建筑、近现代代表性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中的建筑部分和其他建筑”。
②朱华,宋静.七宝寺与近代南充西区革命[J].党史文苑,2022(10):40-43.
③刘礼潜.探析古建筑类博物馆中的展览陈列[J].参花(上),2021(8):79-80
④周晓庆.关于陈列的“内容与形式”几点思考[J].中国博物馆,2004(1):4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