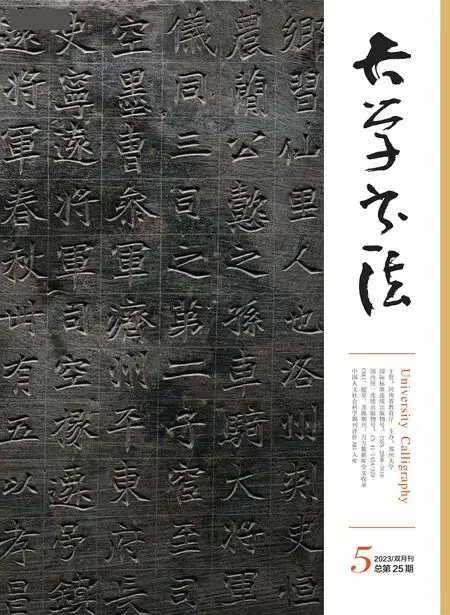无用之用:新学科目录下书法的育人价值与书法人才培养目标构建
2023-12-26杜润东肖寿林
⊙ 杜润东 肖寿林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1]目前国家教育部门正大力倡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书法作为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其中蕴含着中国人的审美核心诉求。但是,书法相对于国家科技的发展、经济水平的进步可谓“无用”,而当下书法成为高等学科教育中的一个门类,那么培养书法人才的目的是什么?书法人才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是什么?本文将从“无用之用”的角度讨论书法学科的育人价值,以及高校书法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指向。
一、“艺”的“无用之用”
(一)“艺”对于“人”的作用
1.“艺”的提出与意义
“艺”字,繁体为“藝”,古字作“秇”“蓺”,指种植,从本义引申出知识、技能等含义。在先秦,“艺”也称“道艺”。《礼记·少仪》:“问道艺,曰:‘子习于某乎?’‘子善于某乎?’”[2]它和德行构成人才素质结构的两大要素系统。《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3]可见在西周时期已经提出“艺”之观念,而“艺”则直接将人类活动提升到精神领域(因为“艺”的存在与否不会影响人类的物质生活,“艺”是为纯粹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六艺”对于生活而言呈现出“非”实用性,但却成为周朝官学中必须学习的一部分。《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在孔子的论述中,将“道”“德”“仁”“艺”并举,可见在春秋时期,“艺”便成为完善人格的法门,亦是衡量“君子”的尺度,更是被赋予了道德层次上的评价标准。
2.“艺”对于“人”心灵的影响
“艺”是人类精神活动引导下的行为,因此“艺”的生产会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艺术会对人的心灵产生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
我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5]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于“艺”的思考,则是将“艺”对“人”心灵的影响与“艺”本身的教化力进行结合。
《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6]当古人将《诗》《书》《乐》并之,谈论其对于“人”品格的温养,即可见《诗》《书》《乐》都会对人的生命精神产生一定的影响,于君子而言《诗》《书》《乐》三者之教都不可少,可见“艺”对人之教化是可行的,且古人也是由此践行的。
无论是孔子或是柏拉图都认为“艺”对人道德的塑造与培养产生着重大的作用。在物质生活已经可以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时候,人类在精神上的追求则将人性中“德”的一面扩大,从而将“人”塑造成“有德之人”,也就是儒家经典中的“君子”。这种塑造品格的教育对于今日仍然有效。
(二)近代“艺”对于美育社会的阐释
“美育”一词,最早由德国诗人、哲学家、美学家席勒在其著作《美育书简》中提出:
除非是达到人的内心不再分裂、人的天性充分发展,从而能使他自身成为艺术家,并保证人的现实成为理性的政治创造物,否则,我们仍然会把这种国家改革的各种尝试看作不合时宜,而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希望看作是幻想。[7]
席勒认为“艺术”可以弥补人类在“利己主义”支配下心灵中人性的缺失。20 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两位学者将“美育”分别从英文和德文中提炼出来,从而将美育对于社会的价值带到了中国。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实质上是把一种抽象的美转变为大众都能接受的一种具有共同性的美,蔡元培认为美感教育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因此,大力发展美育成为其教育思想的一个特色。其曾言:“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8]他强调“崇尚自然”;对于艺术门类,始终倡导发扬个性、追求真美。他认为倘若“把美术家的个性完全去掉,这就是把美术的生命除绝了”[9]。蔡元培将美育看成是实现社会改造和人生美化的途径,在“救国先救人,救人先救心”的理想支撑下,他试图通过倡导美育培养人健全的心灵,这与席勒通过审美与艺术恢复人性完整、实现自由王国的思路是一致的。
可见,不论是西方资本主义产业链分工,致使“利己主义”造成人性的缺失的情况,又或是,在近代中国民智未开,有志之士挽救国家之际,中国的先觉者都选择将看似“无用”的艺术作为拯救人性的一味良药。故艺术的“无用之用”更趋向于对“人”的心灵与精神向度进行弥补。
(三)艺术的“小用”与“大用”
2015 年“第五届世界华人美术教育大会”的主题是“大数据时代的创意美术教育”,创意美术成为美术课的主要内容与课程评价重要的标准。可见,艺术从物质的角度而言,无法直接提供科学与技术,但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开发创造力,从而作用于科学的发展。但此“用”仍为有“利”可图而做,是为“小用”。
艺术之用在于不知所用而做,所谓“不知其情所起而一往情深”大抵如此。在“人”对艺术的探求过程中,完成了对“道德”,对“人性”的自我圆满。因此,艺术是人的艺术,“无用之用”(没有利益之用)才是人进行自我圆满、自我修行之大用。
二、书法的育人功能
在艺术成为使人类精神愉悦的方式时,“人”所选择的诸多艺术形式便都成了精神选择的需要。正如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发于天然,非由述作。”[10]在艺术生产的过程中,“人”的心灵与人性都将逐步趋向于往“德”的一面发展。书法作为诸多艺术形式之一,也承担着这样的教化功能。
(一)书法对“人”道德的砥砺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云:“书者,如也。”[11]而“如”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如,从隨也。”[12]结合来看,笔者认为“如”实际上表达的意思与孔子《论语·为政篇》中“从心所欲不逾矩”所表达的意思相似,其意为内心极度自由而一切的行为都在规范之内。清代刘熙载则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13]因此,书如其人,不仅对人的眼界、才学、涵养要求极高,且对于“人”的内心约束亦有极大的力量。
唐朝时期柳公权提出“心正则笔正”的观点,从书学角度来说,即心与笔、字之间的关系。此论,最早可追溯到西汉萧何,《书苑菁华》中记载萧何论书言:“笔者心也,墨者手也;书者意也。”[14]萧何将毛笔等同于心,用笔书写是“意”的发挥。扬雄提出了“言,心声也;书,心画也”[15]。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16]李世民指出“神”是字的精神魂魄,“心”是字的筋骨,“神”和“心”与书法的精神气质、骨力雄健有很大的关系。张怀瓘认为通过书法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柳公权在前人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心正则笔正”的思想,他将书法美学与人格伦理相关联,将书法作为“心法”“心学”的一部分,从而将书法对“人”心灵的洗涤与对人品的砥砺带入理论层次,亦将学书看作是对道德修养的磨练。
隋唐以后,书法成为科举取“士”的条件之一,吏部选择官吏的条件有四,分别为仪表堂堂、语序井然、书法工整、文笔优美。在书法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一直以一种审美的眼光对其进行审视,唐代盛行楷书,因此“楷书遒美”成为登科的必要因素之一,这对即将走上仕途的科考者来说,考验的不仅仅是书法基本功,更是眼界及审美境界。所谓“唐尚法”,其“法”并非仅指“楷法”,亦是对“人”的约束。在书写楷书时对坐姿、执笔,以及心态的要求无不体现在对人的约束,亦是对“法”的要求。可见楷书之楷,是因其对人之道德要求之高而谓之“楷”。
明代项穆《书法雅言》云:“夫人灵于万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17]由此可见书法家的书法身份外显,来自书法家个人内在的心灵特质和精神修为,不管是个人的道德情操,还是文章和字迹,一丝一毫皆是个体的生命象征。这种生命象征与自我书法风格的追求与形成,书者自身的心性、人格精神诉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在诸多书品即人品的书论中,对“人”的要求不断的叠加,将书法与道德进行绑定,认为道德与书法可以互相完善,在经典儒学的道德约束下,砥砺无数学书者提升对道德的要求,继而学习书写技巧。
(二)书法对“人”感知的提升
崔树强在《书法是中国人美育的基本途径》中提到书法作为中国人美育的基本路径,有两个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在写书法的过程中,对孩子们潜移默化的作用,首先在于秩序感的培养;二是书法可以引导他入静且专注……让孩子在书写当中感受到笔墨活的趣味或者生命的精神。这些潜移默化的训练和陶冶,都是可以在孩子身上扎根和滋养的。”[18]崔先生对于书法美育的两种意义,笔者认为其对应的群体,不仅是“孩子”,而且应该包含是每一个学书者。
秩序感的建立与道德砥砺、逻辑思维构建息息相关,而生命精神的感知却承载着中国古人在做“艺”之时,“艺”与“生命”产生的关联互动。孙过庭《书谱》言:“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性情,形其哀乐。”[19]由《书谱》可见,书法之“用”在于“达其性情,形其哀乐”,而在“达性情”之前是通过凛其风神,温之妍润,和以闲雅等办法,使“人”进入与书法互动的状态之中,由此,“人”通过书法而感知到生命的精神。
朗格从符号论的视角,提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创造。艺术这种独特的表现性符号,它的出现就是为了将人类情感赋予形式,从而实现人类对其内在情感生命的表达与交流。朗格对此说:“艺术就是将人类情感呈现出来供人观赏,把人类情感转变为可见或可听的形式的一种符号手段。”[20]因此,艺术即是情感的形式。艺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呈现,如一幅画、一首诗,书法也在此列,但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
由上可知,在书写的过程中“人”通过对笔墨精神的感受从而感知到生命的精神,艺术的生发与人的生命精神感知息息相关。当通过书法感知到生命精神之时,这是共情的能力的升华,同时通过对情感的认知去观看其他艺术形式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同时修养也得以提升。
(三)书法对“人”审美的提纯
在中国美学的审美体系中常以“气、韵、神、思、阴阳、筋骨”等审美范畴对艺术形式进行品评,如《六砚斋笔记》中说道:“凡状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势;得其势,不若得其韵;得其韵,不若得其性。”[21]
书法中亦有此说,周星莲《临池管见》言:“自伏羲画八卦,而文字兴焉。”[22]《周易》中的“阴”与“阳”是中国美学最早的范畴,“阴”与“阳”是将具有对立统一特征的宇宙万物高度概括的两种基本分类。“阴”与“阳”之后又衍生出“八卦”,其将宇宙万物分为八类,用两种符号排列出来,分别为天、地、火、水、风、雷、山、泽。八卦符号就是在传递信息,汉字便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中国书法美学又将“阴”与“阳”两种范畴发挥到极致。书法中的方圆、虚实、刚柔、疏密、巧拙、雅俗、奇正等对立统一范畴成为书法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另外,书者在书写过程中伴随写字动作产生了“势”,所谓“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南朝梁庾肩吾在《书品》中又根据书法作品所呈现的状态将其分为“神、妙、能,逸”四品。
这些审美范畴是对书法审美的高度概括,亦是书法作品带给人情感上的共鸣。因此,对书法的审美与品评,可以在今人与古人的审美之间架设沟通的渠道,且书写者在面对审美范畴的高度概括时,可以将自身的审美能力通过感知的方式加以提纯,从而使人的审美格调有所提升。
三、书法人才的培养的要求
(一)对“人”内在素质的全面性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教育要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的“五个人”为工作目标,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新要求,提出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人才培养的新思想。梅贻琦说:“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23]而“大师”之责在乎育人,书法学科的建设之责是育人,也是为国育师。因此,书法的育人目标不能仅局限于对书法技法、书法理论的学习,而是应该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完善对道德、修养、审美、技法、知识等全方位的提高,正如刘熙载所言“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
(二)对“知觉”的敏感要求
对于“知觉”一词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记载得尤为贴切:“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24]可见,“心”在王阳明口中变成“知觉”,而“知觉”一词便是“观念”“思维”“情感”等多种因素的统一。
从书法技法中提炼完善人格所需要的道德、修养、审美等内容,则需要通过“知觉”持续深入感受书法,从而进入书法中所蕴含的精神向度。《书谱》言:
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25]
“五乖五合”的观念,将书法的创作环境以及创作动态进行提炼,而这种对工具、心情乃至天气的挑剔,便是通过细腻的感知让书法的创作进入身心合一的状态。
在书法人才培养中,过去很少将感受“知觉”作为培养的一部分,但是书法在成为一级学科之后,对“知觉”(感受力)的培育亦是书法人才培养所需要注重的一个方面。
(三)对视域开阔性的要求
在清代碑学运动兴起之前,人们对于经典的认知仅限于“二王”帖学一脉。清代碑学运动之后,人们对于经典的认知拓宽到金石领域。在信息多元的今日,中外思潮交织碰撞,碑学运动兴起的原因也可以成为当代书法发展开拓的途径。
书法人才的培养,其视野不能仅局限于中国传统经典的视域之中,亦应该将当代世界艺术前沿理论的发展成果纳入教学范围。对于书法的研究不仅仅在书法史上执着发力。对书法的书写思考,对古代几次重要书法思潮变革,我们不能仅依靠对古代文献的定义而得出论断。时代于今日,心理学、逻辑学、现象学、图像学、哲学等学科均有较大的突破。书法学科的发展更应该基于当代学科发展的背景,对“书法”中经典的问题重新思考,从而深化“书法”本体的问题。
四、书法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笔者借鉴云南师范大学书法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结合己见对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构建。
教育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师者应该教什么?怎么去教?怎样培养学生的能力?面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2245”的人才培养模式(即:两大视域、两种能力、四大板块、五维一体),为书法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如图一所示。
(一)两大视域
“视域”一词,结合字义来说就是“目光可视之处”。将其字义在书法领域引申可解释为:“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在哪里?事物发生的背景是什么?”由以上问题可以知道“我可以做什么”。在这些问题的缠绕下,若想厘清头绪则需要培养书法专业学生建立“两大视域”,即当代世界艺术的视域、中国传统文化的视域。两种视域的构建可解决三个问题:对于书法的思考当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深度?对于书法的探究未来应该指向何处?对于书法的思考前人的经验是否可取?书法专业学生在两大视域的构建中形成属于书家自身的定位方式,继而可以在学书之路上厘清思路,构建自身的书学理想与书法审美脉络。
(二)两大能力
在“两大视域”之下,对于学书者而言可以清楚的认知自身对于书法问题的思考在什么层次,可以树立自身的学术理想与学术追求。但是如何将想法转为有效的学习行动,又如何将学习行动转化为研究能力?如何将别人的理论转变为自身研究问题的能力?这种种问题的解决则需要培养两大能力(写作能力、创作能力),简单来说就是所有的学习终将指向书法问题的研究。而写作能力与创作能力的培养则是深入学习书法的一条路径。将深度思想转化为文字,需要写作,在写作中发现新的问题继而产生深入的研究,将研究内容应用于书法生活则视为创作能力的提升,在创作中又发现新的问题继而研究。由此形成“理想(两大视域)—理论(写作能力)—实践(创作能力)—理想(发现新的问题)”的闭合链条。
(三)四大板块
在“两大能力”的基础上,如何将课程设置的更加符合两大能力的培养?由此四大板块对于课程建设的要求,即为“思想、理论、技法、修养”。“没有思想的实践是没有高度的实践,没有实践的思想则为空想。”因此,思想类课程板块的设立是给予学生一个问题:“在艺术领域或文化领域书法人能做什么?”而学生对此问题的不同思考则形成不同的学习状态,从而产生不同的学习路径。理论板块课程的设立则是指向:“如何研究书法?书法究竟应该指向什么?”在发现书法问题之后,解决书法问题的能力则需要通过理论能力与写作能力的培养来支撑;技法板块是书法本体的问题,技法问题则是指向创作能力的问题,不以提高创作能力为目的的技法是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的技法。而创作能力的提高是思想与理论共同的提升。最后,大学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一种教育,学科建设的目的是培养“人”,设立书法专业的目的也在对于“人”的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实际上就是修养问题。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中提到的修养板块,暗含着人即是书,书即为人的思想。
(四)五维一体
书法人才的培养,最终都将回到社会。当面对中小学书法教育、社会书法教育、专业书法教育,都难以避免地会有“五维”问题:其一,知识。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艺术形式,因此学习汉字的过程中也暗含着书法知识问题。在每个人学习和使用汉字的过程中都将面临汉字生成的学理问题、汉字构建的审美问题、汉字准确使用的问题等。可见,书法成为显学,是因为每个中国人都将面临书法的问题;其二,规范。所有的学科都将面临如何去做?如何设定自身的标准?而规范不仅是一个标准的制订问题,也面临书法教育和书法人才培养当中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其三,文化。正如,当下所交流的热点中有美术书法还是文化书法的问题,此类问题则指向书法中所暗含的文化性问题;其四,德育。对人的教育,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价值观的培养问题,即为德育问题。其五,审美。书法给人们带来什么审美观的问题。没有审美的感知力也就不存在书法的其他问题。
借助“两大视域”确立自身定位与学术理想,通过“两大能力”培养实现完成理想的能力,利用学科课程中的“四大板块”完成对书法人才“德、智、美”全面的培养,通过“五维一体”将学生塑造成具有学术理想,又能将学术与未来的工作生活相互结合的书法人才。
结语
书法学科升级后,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书法的二级学科也将被划分出来,届时书法理论、书法技法、书法史、书法批评等人才也越来越多。书法成为一级学科影响深远,所以书法本身所具备的美育价值更需要被重视,这也是书法本体所蕴含的价值。这样的价值不应该在划分二级学科之时进行拆解,而应该将书法美育的价值化成基因,在所有的书法二级学科中都得到传承。在书法本身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之中,重新构建书法学科的培养模式,将书法的学习变成对中国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