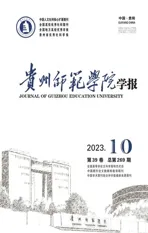论芬利的目的-关系理论及其绝对性问题
2023-12-25张昱顾
张昱顾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自元伦理学的初始发展至今,元伦理与规范性问题之间就呈现出相融贯的特征。规范性语言关心的“并非人类‘是什么’,而是人类‘应当是什么’”[1],并涵盖美学、元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20世纪伊始,元伦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道德属性和道德语言的探讨。例如摩尔[2]提出对“好”这样的道德概念作非自然属性的分析;艾耶尔、史蒂文森等[3]从情感主义的立场将道德属性还原为某种情感态度;布莱克本和吉伯德[4]分别从准实在论和规范表达主义的角度构建理论方案等等。由于人们逐渐发现“规范性”直接囊括了对道德方向的研究,因此在本世纪有关道德论述和道德属性的分析逐渐转为对规范性语言的整体性关注。规范性问题以其包容和更广泛的效益在道德演说和道德语义学的范围内被持续讨论。人们更多地追问“规范性语言表达了什么意义”,探究规范性的概念和各个规范性词项的内涵,并创新提出不同的规范性理论体系在分歧与交流中发展。
史蒂芬·芬利[5]身为当今西方哲学界颇受关注的学者,把规范性研究的语义问题作为自身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试图把语言意义解释为规范性理论的基础。他的目的-关系理论是关于规范性语言的统一意义分析理论,致力于通过“目的”概念的限定作用把关于“应当”的规范性命题转换为关于“是”的自然语言命题,从自然主义还原论的立场为普通模态的“应当”和规范性“应当”提供统一的语义学方案。本文以芬利“目的-关系”理论的具体内容和特征展开,探究其理论在绝对性使用情境下遭遇的重大挑战和芬利“修辞策略”的回应倾向,总结其思维特性,从而揭露理论的可能漏洞并尝试提出合理的优化路径。
一、“目的-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和论证过程
芬利的目的-关系理论从工具主义效用的应当命题出发,这是因为应当的工具性使用在分析过程中存在最少的争议,因此最便于做清晰的阐明。继而芬利将一般性“应当”概念类比“必然”与“可能”概念,采取从普通模态向规范性模态递进的分析策略,在规范性语言中提取关于“目的”的限定关系作为主要特征构成理论雏形。
(一)“目的-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目的-关系理论为规范性语言提供了自然主义还原论(Reductive Naturalism)的分析,把规范性语言理解为以“目的”的限定为主要特征的普通陈述句。也就是每一个“行动者X应当做p行为”的规范语句都等同于“为了目的e,大概率存在行动者X做p行为这一情形”。理论的构建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应当命题(Ought-Proposition)中提取“目的(ends)”内容,利用目的对行为的限定功能解释规范意义。第二,采取比较的方式,对实现概率介于“必然”和“可能”之间的规范行为“应当”进行概率量化。通过量化的概率描述规范性行为的实现可能。第三,结合语境的具体条件将规范性概念“应当”分析为一系列非规范性的术语或概念,并致力于统摄“应当”概念的所有合理用法。
首先,理论搭建了关于“应当”的规范性语言和关于“是”的非规范普通陈述句之间的桥梁。“是(be)”与“应当(ought)”的区分肇始于休谟[6]的认知理论。休谟持相关二元论的立场,考虑“在理论推理层面,从关于事实的规则性的描述,前进到必然法则的表述,如何能够得到合理的辩护”。他认为从“是”的认知判断无法推出“应当”的规范判断,因此我们对规范性问题的裁决无法由理性决定,而必然地指向人类的情感欲望。休谟[7]315关于事实认知和价值评价的划分启发了一些试图利用非规范性、评价性或道义性的术语来分析“应当”概念的尝试。例如理由应当(Reasons-Ought:利用理由的相关概念对应当做出解释,认为X应当作p,即相比其他行为,X拥有更多的理由选择p行为)和价值应当(Value-Ought:利用价值的相关概念对应当做出解释,认为X应当作p,即相比其他行为,X采取p行为是更好/更有价值的)。两者分别对“应当”概念做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利用“理由”或“好”等概念将应当命题描述为实然判断,把规范性语言还原为关于“是”的陈述句。
其次,芬利[7]315发现利用理由或价值比较来解释“应当”实际无法摆脱规范性。例如“我应当尊老爱幼”在“理由应当”中该规范性语言能够被分析为:“相比漠视老人儿童的行为,我拥有更多理由去尊老爱幼,理由包括但不限于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尊老爱幼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等”。但把某种现实理由作为分析的结果显然不够彻底,理由的内容中仍然包含潜在规定性,因此本质上无法将规范性语言完全分解。这样的分析仅仅属于一种半途的尝试和可能。于是芬利在这样的分析思路上加以创新,对理由或关于价值的内容进行再分析和再还原,彻底将其中蕴含的规定性还原为关于“是”的自然语言,并提出“目的-关系理论”。
因此该理论延续了自然还原主义的立场(即同时秉持自然主义和还原论的观点),将重点置于语义学的关注范围,借鉴刘易斯和克拉泽[8]的模态分析理论,尝试对“应当”进行彻底的还原式语义分析。应当语句在工具主义使用下的语言形式指向假言命令,即一种有条件的、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命令手段。假言命令的特点在于语句中同时包含某条件情形和功能性要求,并根据具体条件对行事者的未来行为提出要求。同时,该限定与行为之间存在工具主义的联系,即前者推动后者的实现。根据这样的语句特点,芬利通过假言命令的一种表面为非条件句句型的常用句式“为了(in order that)……,行动者X应当(ought to)……”,将命令中的限定解释为期望达到的目的,凭借行为对目的的促进作用将它们之间的工具主义联系做出了进一步阐明,纳入目的-关系理论的范畴。
(二)“目的-关系”理论的论证过程
理论的具体论证建立在“应当”与“必然”“可能”等相似概念的类比之上。基于“必然”和“可能”概念同时从属于非规范性的普通模态(Ordinary Modal,关注必然性和可能性的模态逻辑)和规范性的概念术语,论证首先从代表非规范性认知的普通模态出发。在这里,芬利[7]319继承了刘易斯关于可能世界的观点,将必然和可能进行了概率量化,如下:
必然模态(Modal Must):必然存在情形p=(定义为)在条件C得以实现的每一个可能世界中都存在p情形。
可能模态(Modal May):可能存在情形p=(定义为)在条件C得以实现的至少一个可能世界中存在p情形。
在对必然和可能进行的概率量化中,分析指向一般性的普通模态,它的功能仅仅在于表达认知和描述,而不包含任何规范性。这对于规范性理论显然是不够的。在工具主义使用的情境中,我们必然地考虑认知情形p的功能效用和实现问题。因此为了在普通模态和规范性术语之间建立起统一的联系,芬利[7]320引入“in order that e”修饰下的语句形式,将普通模态置于规范性情境之中,通过“目的e”实现的概率对相关的可能世界进行规范意义的限制。对此他提出论点:“作工具主义使用的规范性模态术语或概念,仅仅是在“为了……”(的语句形式)修饰下的普通模态术语或概念。”此即为目的-关系理论的雏形,换句话说,工具主义的规范性概念也就是被置入目的-关系情境之中的普通模态概念。由此,芬利展示了其标准表述如下:
Muste(在目的e限定下的规范性必然模态):为了目的e,必然存在p情形=(定义为)在条件C得以实现的每一个可能世界中,都包含了目的e的实现和p情形的存在。
Maye(在目的e限定下的规范性可能模态):为了目的e,可能存在p情形=(定义为)在条件C得以实现的至少一个可能世界中,包含了目的e的实现和p情形的存在。
就这样以普通模态词“必然”和“可能”为例,目的-关系理论首先为工具主义的规范性语言做出了定义的直接分析,即通过目的限定——“in order that”语句形式的修饰,将普通模态的论述和规范性的表征结合起来,提供了关于两组同态术语的统一、单义的语义学解释,并反映了行为与目的之间特殊伴随的概率关系。
再进一步的,基于对同态术语“必然”和“可能”概率量化的理解,芬利[7]322尝试将“应当”概念置入同样的表征方法,并对其进行相似的概率量化。我们在日常规范语言中能够感知,表述“行动者应当工具性地做行为p”,是由于相比其它供选行为,行为p能更好地促进目的e的实现。也就是说,通过行为p实现目的e的概率大于其它供选行为,因此规范性“应当”的概念本质上就是比较性的,又由于在规范性的概念中,“应当”的规范程度弱于“必然”而大于“可能”(出于日常认知的考虑),于是它合理地被纳入介于必然和可能之间的规范概念序列。那么再转向对普通模态词“应当”进行概率量化的考虑,芬利借助比较类R的集合加以解释如下:
应当模态(Modal Ought):应当存在p情形(It ought to be the case that p)=(定义为)在C的条件之下,相比比较类R中任意成员的存在,p情形更有可能存在。
通过与其它可能情形(比较类R中的成员)的比较,芬利[7]323完成了在认知的可能世界中对应当的概率量化。从属普通模态词的“应当”概念和作规范性使用的“应当”概念展现了具备共同语义特征的理由根据,使得建立“应当”和“必然”“可能”之间的类比关系,综合“应当”的语义内容,将其纳入目的-关系理论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根据已有的对必然和可能概念的分析,芬利从条件性概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出发对目的-关系理论统摄下的应当概念进行定义如下:
可以看到,芬利“目的-关系理论”的论证大致拥有如下几点特征。其一,运用比较性质对道义模态词进行解释,为概率量化提供了可能。其二,在应当命题中提取目的概念作为理论的关键特征,对行为p做出事实限定,以代替规范的功能作用。其三,阐述目的e作为潜在事态和行为p的推动力关系,展现演说者的要求命令,集结表达主义和功能主义的主要优势。
二、“目的-关系”理论面临的绝对性挑战
工具主义条件下的应当命题是理论中最典型的使用,但并不囊括全部情形。由于目的-关系理论受到众多关注,一些在规范性领域持实在论或准实在论立场的学者对其在绝对性使用(The Categorical Ought)下的条件提出质疑,认为理论无法囊括绝对命令(形式上无条件的命令手段)的规范情形。芬利[7]323则提出“修辞手法”为理论做出辩护,坚持目的-关系理论能够涵盖“应当”的所有使用范围。
(一)应当命题的绝对性使用
关于应当的命题一般被置于三种不同功能性的使用情境:一是理论的出发点,工具主义使用的应当(The Instrumental Ought);二是绝对性使用的应当(The Categorical Ought);三是预测性使用的应当(The Predictive Ought)。在第一种使用情境下,工具主义应当命题所表述的要求和命令显然地包含某种条件限定,因而承担商谈、驳回、变更的可能。第二种绝对性的应当概念表达某种绝对命令,由于包含绝对性因素而无条件地不可抗拒。第三类预测性的应当概念使用范围则较为狭小,作特殊句式使用,例如预测“明天应该会下雨”的情境。
对工具性应当概念的分析至此已经消除了其原本具有的规范性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关于条件概率的一系列非规范性认知表述。芬利的目的-关系理论关于规范性应当概念的自然主义式还原大致如此,但理论的完整度尚且远远不及,有争议的部分在于绝对性使用和预测性使用的应当概念。在这里可以先对预测性使用的应当做出说明,因为根据芬利在第一部分关于普通模态词应当的解释,当我们进行“明天应当会下雨”“X明天应当会进行p行为”等预测性叙述的时候,表达的依然是关于未来的一种概率性的可能情形,即演说者认为自己预测情形实现的可能性大于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由于这是一种认知层面的表述,往往不被纳入规范性的理解范围,因此在对规范性应当的还原式语义分析进程中可以暂且被搁置。
目光转向绝对性使用的应当命题。绝对性规范语言无法通过假言命令的形式加以解释,这一语言事实构成了芬利目的-关系理论中的一大挑战。该理论的本质意向在于从一个指向应当行为p的规范性要求中提取作为限定条件的目的e,构成目的e与规范行为p之间潜在事态和推动力的必然联系。这在应当的工具主义使用中是显然的,出于功能效用的考虑,每一个工具性的应当行为都服务于某一条件目的。然而,在作绝对命令使用的应当情境下却无法作同等条件的考虑,因为在绝对性应然句最为明显的表面特征——“应当”术语的前后通常都没有“为了……”或类似表达的修饰[7]328。例如,“你应当活着”“不许作弊”等在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行为规范似乎是无条件成立的。这样的规范性语句并不包含任何工具性的目的内容,因此无须任何补充说明或解释陈述,展现出绝对命令的语言形式[9]。
从这一困难的表象出发,我们即可深入应当作绝对性使用的本质作关键问题阐述,由此显化出关于语用学情境的两大困难:“会话难题(Communication Problem)”和“意义难题(Significance Problem)”。[7]331会话难题从会话具体情境的角度出发,关于在相关目的的确没有被引入语境范围的状态下如何合理陈述一个目的-关系命题。这涉及相关目的在语境中的预设和隐藏,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承认语境范围内,一个不随附任何目的索引的绝对命令。而意义难题则从应当命题的功能性本质角度出发,探究应当在具体语境中的实践意义。当我们用绝对命令的语句形式解释绝对性应然句,则必然地意指它包含本质性的规定或建议功能,但从事实情况来说,目的-关系理论下的语言形式却无法体现这一功能。目的-关系理论提供的相对化结构意味着其所包含的规定或建议始终与相关目的联系而缺乏绝对权威的要素。总而言之,这样的情形似乎导致了目的-关系理论的最大困难——无法从中获取一个重要的目的限定,从而使构成该理论的基础性目的关系最终成立。
(二)理论对绝对性使用的容纳
“目的-关系”理论中关于绝对性使用的阐述如下:第一,承认目的-关系理论下应当概念作绝对性使用的事实情形,并明确否认被其它理论涵盖的具有不同本质内容的绝对性应当存在;第二,区别了应当作绝对性使用时的意向特征,提出相关解释;第三,指出理论的又一重要论点:作绝对性使用的应当命题即为根据语境预设了相关修饰的普通应然句[7]328。
芬利[7]328的第一点主张是为了支撑文中的论点“每一个规范性的应当概念都仅仅是‘为了……’修饰下的普通模态词应当”,即申明其目的-关系理论涵盖应当的全部使用范围,能够解释所有语境形式下的规范性应当概念,并以此显露策略——基于目的-关系理论已经为应当概念提供了完整正确的语义分析这一前提,再分述其绝对性使用的本质意义。那么如果最终通过其它论证提供了对绝对性使用的合理解释,就恰好反证了理论系统的成功。再次,他通过第二点主张对应当概念的绝对性使用(亦可称为非工具主义使用)进行解释,认为其特征在于“行事者的行为p对于目的(关于欲望或意图)而言所具备的工具主义价值并不是该命题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应当的绝对性使用情境下,并非完全不存在任何指向功能性效用的特征,更合理的是应当的行为p不再取决于行事者自身的意图,命令背后隐含的目的也与行事者自身的意愿无关,取而代之的是对诸如社会共识、传统习俗等的关注,即芬利称之为“一些显然重要的东西”[7]331。
2)规范机车内通讯线缆的布线,杜绝线缆大幅度弯曲,通讯线缆与高电压(电流)的电缆分隔开,防止线缆有高压(电流)通过时影响通讯信号。
“应当”在工具性和绝对性使用下的区分由此得到阐明。工具性应当命题中包含的目的通常关注的是行事者个人的意图和欲望,因此行为p对于目的e的推动意义在于满足行事者内心的渴求,而绝对性应当命题的目的指向则更倾向于外在制约,例如社会群体间的某种共识或制度,或某种与行事者的个体私欲无关,但对于内心依然“显然重要的东西”,那么无论行事者对该目的认同与否、关注与否,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在的规范而不得不采取行为p以促进目的e的实现。那么依据该区分,命题的绝对性意义通过独立于行事者自身态度的目的得到显化,因此脱离了工具主义性质的范畴,意指外在因素对行事者的规范作用,同时,由于此类目的总是关于一些集体共识(比如促进社会福祉、维持生命)或者其它包含合理原因的承诺,因此无须特别说明。此外,芬利[7]330做出进一步阐述,认为在外在规范力作为主导的情境下,哪怕通过目的-关系理论的加工与分析,依然无法使目的的具体内容得到显化,但也不影响上述解释的指向,因为“无论如何都会存在一个供选目的为某一绝对性应然句提供合理解释。”
从以上两点主张可以看出,芬利[7]333对应当作绝对性使用的理解重点并不在于它表面无条件索引的语句形式,而在于语句背后的真实意图。在具体的语境情形中,目的始终通过多种状态或手法被隐藏或预设,他称之为“修辞性的使用手法(The Rhetorical Device)”。
三、芬利对绝对性挑战的回应和不足
芬利把“修辞手法”当作目的-关系理论面临绝对性挑战时的回应策略,指出理论通过目的内容的隐藏或预设达到对绝对命令的容纳。这一解决方式实际将关注重点放在了规范性语言带有强迫功能的日常效用上。其中展现出的漏洞与不足仍在语言层面,即关于规范性语言和非制度性绝对命令的理解混淆,这些都亟待理论的进一步补充。
(一)“修辞手法”的回应策略
对于“应当”命题在绝对性使用的条件下似乎无法容纳“目的”要素的质疑,芬利[10]指出,尽管呈现出绝对命令的语言形式,但规范性语言的绝对性使用并不是无条件的。更有可能的是,在日常交谈中由于某些行为规范所指向的目的因为过于显而易见而被演说者直觉性地忽略了。“语言表达认知,而认知必定关于世界”,因此语言的表达必然包含演说者内心的思维。正如实用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人类的语言能力(及语言指称功能与真理性)与理性能力 (尤其是信念的形成与基于信念的推理能力)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有力生存工具。”[11]出于实用的考虑,规范性语言呈现出绝对性的特征。例如“我们应当保护环境”这一绝对性命题背后隐含的目的是“我们保护环境是为了人类的未来”,但“为人类未来”似乎是一个公认的、无法反驳的事实目的,因此无须做特别说明而在语言中被省略了。
关于“修辞手法”的回应重点涵盖了两方面内容。第一,修辞手法意味着“应当的绝对性使用是基于目的-关系理论下一种省略性的修辞使用”[7]333,也就是说并非在应当的绝对性使用中就无法容纳目的的因素,而是出于语境和功能需要,利用修辞手法将关于目的的表述加以省略,使其呈现出绝对命令的语句形式。第二,说明绝对命令的语言形式是出于功能性的考虑。其功能性意义即在于利用这样的修辞手法表达演说者的命令要求,指向“意义难题”中提及的建议、规定的本质功能,或者说从某种语境功能而言,应当的意义被用作一种迫使的规范力量。
分析从演说者和听众双方的不同角度展开,具体涉及三种以不同个体认知为出发点的目的定位:来自演说者和听众达成了共识的目的认知、演说者自身的目的认知以及听众识别的目的认知。
首先,最易理解的是演说者和听众达成共识目的时的情境。此时的目的取决于例如社会公认的惯例、规则或制度,由于被普遍接受和认可,而无须做特别说明,因此应当命题具备省略的充分理由条件从而呈现绝对命令的语言形式。由于芬利的应对策略重点关注绝对性表达中的“修辞性使用手法”和演说者对听众的要求,那么从演说者和听众(潜在行动者)的角度出发,考虑该修辞在语境中呈现的具体方法、目的内容在省略条件下对行为规范的效用以及绝对性特征在自然主义还原式分析中的显化结果等等,能够得到不同定位下的策略回应。但从规范理论出发,同样需承认该使用情境的确没有摆脱目的限制的条件。因此,目的的省略和隐藏并不代表“相关目的没有被引入具体语境”,实质仍与绝对性的特征相冲突,该说法亟待进一步消解。
第二,关注演说者自身的目的认知。当演说者自身对应当命题背后隐含的目的具有明确认知时,往往事实地采取修辞性手法表达命令要求,迫使听众服从目的,包括利用其他(更易达到效用的)目的、刻意强调、强制命令等,此时无论听众对目的的辨识程度如何,都在无形中增加了遵从命令的意向。这里有部分理由在于绝对性应当命题的一个重要特征,即 “实践意义(Practical Significance)”。芬利[7]331认为应当作绝对性使用的功能意义在于演说者对待听众是否服从行为p的态度立场,这实际也就是“意义难题”中应当命题应该发挥的那种规定或建议的本质功能。也就是说,通过应当命题的绝对性使用,演说者的目的在于表达一个“要求”,该要求希望听众认同演说者本人对于一些目的(e1)的关注,并最终达到听众采取(能够达到目的e2的)行为p的意图。这里绝对性的使用包含演说者两个层面的目的要求,首先要求听众认同他所关注的某个目的,其次要求听众在达成目的共识的基础之上做出行为p。
第三,在演说者和听众都无法识别语境中相关目的的语境中,尽管演说者无任何目的倾向,但仍然做出了某种绝对命令的规范表达。芬利[7]334在此尝试了几种解释方案,例如虚构主义的路径,演说者假设存在重要的目的共识并进行表达;或使用“同义反复的赘述(tautologies)”手法,将绝对命令的句式“你应当做p(you ought to p)”演变成“为了实现p,你应当实现p(in order to p,you ought to p)”。他声称,“如果绝对性使用的真正会话功能在于达到相关目的的动机要求,而不是传递语义内容,那么它们的意义与同义反复就是兼容(相一致)的。”无论如何,利用同义反复的手法,绝对性应当句能够成功达到会话目的,并展现与目的-关系理论的兼容。继而得到一个可能的结论,即目的与手段本身相同,规范中应当做的事(行为p)等同于应当命题中包含的目的。然而此时仍然存在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是同义反复在语义表述上的必然错误,二是此时目的因为与行为相等同而无法再表达限定功能。
而在从听众对目的的辨认为出发点的思考中,同样存在相似的问题。无论听众的态度和认知变化,演说者都必然表达绝对性论述并对听众施以迫使服从的压力,那么演说者只能够利用与上文提及相类似的手法,例如预设目的、虚构目的以达到预期的语义效果。此时一个矛盾得到突显,即其中工具主义的特征无法被继续掩盖,乃至失去了绝对性使用被赋予的非工具主义内涵。但同时,“修辞”的解释亦间接解决了在会话交流中命题陈述之间互相冲突的可能问题,由于演说双方都意在表达某种态度和要求,则意味着目的-关系理论能够容纳被置于绝对性规范问题中的分歧,也兼容语义矛盾的命题。
(二)回应策略的模糊与不足
对于来自绝对性使用的挑战,芬利[7]333的解决方案似乎能够被总结为:应当的绝对性表达属于一种修辞手法的应用,即“基于目的-关系理论正确的假设,通过绝对性的实践意义表达要求:听众关注某目的并根据它做出行动。”他的解决路径大致彰显了他的以下几点思维特性:
第一,理论体现了他对规范性语言中相对化结构的本质追寻。芬利把包含某种关系属性(Relational Property)的一般相对化结构当作决定规范性论述本质的关键要素。也就是说,有关规范性的判断必然指向一定的标准或目的,建立起判断和判断根据之间的关系构成,如果脱离了根据的具体内容,判断本身则无任何实质意义。他的关注从规范诉诸的来源要素转向语言结构的基本应用条件,这一巧妙转向避免了关于规范背后的指向(例如某种权威)是否完全绝对、不可变更的争论以及最终确定某无条件规范来源的期望,呈现出容纳多种不同质规范内容的理论优势。那么无论规范是否根据主体的欲望意图、是否指向未经证实的权威,无论绝对命令是否完全独立于具体事实,都不影响关系理论的意义与实质。
第二,理论体现了他对规范性语言从属制度性绝对命令的坚持。从芬利对工具性应当和绝对性应当的区分可以看出,绝对性应当的特征在于目的指向与行事者个人欲望和意图无关的要素,规范性来自独立于行事者理性的外在因素。因此芬利所承认的绝对性应当从属制度性绝对命令(Institutional Categorical Imperatives,以下简称ICIs)。但显然,相关目的未被引入语境范围的绝对命令实际可能指向一种非制度性绝对命令(Non-institutional Categorical Imperatives,以下简称NICIs)的规范语言[12]。此处可以通过芬利对规范性语言的一种代表形式——道德判断的相关论述来理解。他反对道德论述在概念上从属NICIs的可能,也就是不承认完全独立于具体事实的判断形式,以及无任何索引的无条件规范,而试图证明道德论述实际仅仅从属ICIs的合理性。在这里,芬利从根本上否认了非制度性绝对命令的存在意义,并依据制度性绝对命令的特征和实质把规范性论述纳入具体制度和规则的关系结构之中。但在关于NICIs不成立的具体论证中,却存在着一个显然的漏洞。我们可以看到,芬利[13]在作关于论证前提“每一应然句都只有在关于行事者S的欲望集和参照标准I以合理方式连接的时候,才对行事者而言拥有规范性权威”这一事实证据的叙述时,声称这是“规范性权威的工具主义观点所公认的事实证据”,也就是说,他的整个论证过程都建立在工具主义对规范性概念的理解之上,将非工具主义的绝对性规范命题排除在了讨论范围之外,这直接导致了论证不完全可靠。
第三,在目的-关系理论中,芬利将“一种修辞手法”列为理论最为关键的解决策略,并主张修辞作用下目的元素在绝对性应当命题中的省略。这实质上是否认了指向彻底绝对主义的规范性论述,即一种独立于具体的语境,包含直觉性绝对权威的事实性论述存在。也就是说,所谓的绝对性应当概念本质上依然属于一种特殊的工具主义使用,即从属制度性绝对命令的范围,而只是为了达到听众服从命令的功能效用,对该命令做了语义上“去目的索引”的修饰,使其表面拥有了无条件索引的表述结构。那么实际上尽管一开始芬利就用“无相关目的引入语境”的说法来描述作绝对性使用的应当,并用“关注点从行动者自身的欲望转向演说者对听众的期望和要求”来解释其与工具主义应当之间的区别,但其实仍然无法摆脱工具主义的影响,而只是将工具主义的服务对象从行动者自身转向了演说者个人。且出于对元伦理情境主义的辩护,芬利认为规范性语言始终无法摆脱具体情境而从孤立的语义层面进行研究,因此必然地将会话情境中演说者与听众的个体思维、个人情感以及相关客观具体条件纳入考虑范围。于是再进一步地,是否能够将工具主义性能的应当命题解释为仅仅指向行动者个人的欲望和意图这一分析,乃至对目的元素的最终定位问题都同样变得值得再商榷和反思,而如果摆脱了工具主义性能,行动p与目的e之间的关联则似乎显得并无充分必要,那么目的-关系理论亦失去了构建的根基。
在这样的论证环境之下,芬利目的-关系理论仍然存在模糊的地方,而对于关键问题的解决,可靠出路似乎再次指向论证非制度性绝对命令的失败,如果在脱离工具主义限制的情形下最终利用可靠证据证明了非制度性绝对命令不具备事实存在可能,也就真正消解了目的-关系理论的最大挑战。
四、结论
本文从史蒂芬·芬利关于规范性语言的“目的-关系理论”出发,简要阐述了理论的论证策略和基本内容。理论站在自然主义还原论的立场上,成功将规范性“应当”还原为关于“是”的命题,并容纳应当的多种使用情境和多种内容意义,构建起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相比传统理论对规范事实的关注和争议,芬利首次将目的内容作为规范性的重要特征,倾向于关注规范的事实功能,无疑具备创新性和前瞻性。但其中的最大弱点在于应当作绝对性使用时,绝对命令“无目的引入相关语境”的形式特征和理论具备的“目的限定”关键要素之间的冲突。尽管芬利采取“修辞性手法”做出解释,但他实际未能对该“修辞”的具体使用表征做出合理解答,而仅仅提供了省略、虚设、强调语气等模糊猜测。这一挑战实际指向芬利对规范性语言必然从属制度性绝对命令的观点坚持,由于非制度性绝对命令是否成立尚无定论,以及关于绝对命令构成本质的理解存在偏差,因而同时容纳非制度性与制度性的规范语言尚无法得到统一完备的分析。但无论如何,目的-关系理论通过对理由主义的再分析不仅摆脱了“理由”概念的模糊和繁复,又同时为“为什么我们应当做这些特定的事,而不是那些”提供了直观合理的解释,以及对表达主义的超越,还合理描述了演说者对听众的要求和命令,而且解释了“规范性语言对听众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促进影响”这一功能性现实要点,展现出现实规范的实用意义,具备较大的理论优势,值得补充和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