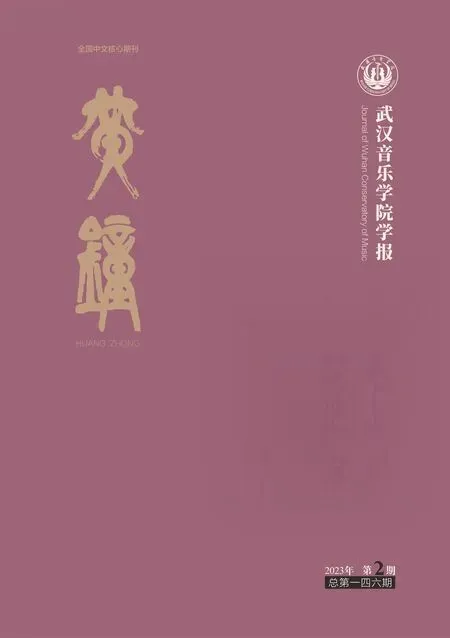天地人神四重维度下的葛洪乐论思想研究
——以《抱朴子》内外篇为例
2023-12-24王维
王 维
绪 论
葛洪(283—363)①有关葛洪的生卒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公元281—341(时年61 岁),一种是公元283—363(时年81 岁)。参见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版,第726—729 页;梅全喜、戴卫波:《关于葛洪生卒寿年及其晚年隐居、逝世地的再探讨》,《亚太传统医药》2018 年第1 期,第10 页。,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东晋著名思想家、炼丹术家、医药学家。葛洪一生著作颇丰,②“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别有目录”。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自叙卷五十”,第698 页。但其大部分已经佚失,留存下来的只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抱朴子外篇》五十卷,《神仙传》十卷,《肘后要急方》四卷。近年来有关葛洪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中医药学、养生学、道教思想、儒学思想、文学、美学等领域,但对葛洪乐论思想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试图以葛洪《抱朴子》内外篇作为切入点,提炼和阐发葛洪乐论的思想内涵及其与儒道思想的内在联系,最终找到葛洪乐论思想的价值意义。
葛洪生活在两晋之交的时代,他亲身经历了家道中落、兵火累身、临危受命、辞官修道等等人生变故,也目睹了永嘉南渡之后种种“背礼叛教”的士人堕落之举,这些都让葛洪开始对纷乱的世事与复杂的人性有了深刻的理解,他将这些思想都倾注在《抱朴子》内外篇的写作当中,据葛洪自述:“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③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自叙卷五十”,第698 页。
葛洪在其“自叙”中提到《抱朴子》内外篇均成书于东晋之后——“至建武中,乃定”④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自叙卷五十”,第697 页。,建武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继位年号(公元317)。这一年葛洪35 岁,正值思想成熟的年纪,葛洪对于“末世”有了这样的见解:“汉之末世,……唯在于新声艳色,轻体妙手,评歌讴之清浊,理管弦之长短……”⑤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崇教卷四”,第162 页。葛洪认为汉之末世的来临,既源于士人们对声色犬马、任情纵欲的沉迷,也来源于人们热衷“品评”“鉴赏”之举。无论是歌舞游艺的鉴赏把玩,还是人物德性的品藻批评,⑥“每见世人有好论人物者,比方伦匹,未必当允,而褒贬与夺,或失准格”。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自叙卷五十”,第678 页。很多的结论在葛洪看来都是“未必当允”“或失准格”的,因为“见誉者自谓己分,未必信德也。见侵者则恨之入骨,剧于血仇”⑦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自叙卷五十”,第678 页。。葛洪看到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标准去评价人事物,带来的结果就是没有了真正的价值标准,人间失序的局面就此产生。⑧“洪以为知人甚未易,上圣之所难,浮杂之交,口合神疕,无益有损”;“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仇,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前鉴不远,可以得师矣”。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自叙卷五十”,第666、680 页。那么,人世间真正的价值标准是什么?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提出了“一”的概念。
葛洪指出:“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⑨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地真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323 页。在葛洪看来“一”是道的起源,具有绝对的价值,道又存在于各处并形成了天地人的形象,所以称之为“三一”。“三一”的“一”就是“道”,“三”是指天地人,“三一”实际上体现出了“道”中所蕴含的三位一体的结构模式。葛洪此处的“三一”延续了《周易·系辞下》中的“三才”概念:“《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笔者按:即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⑩[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义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318 页。葛洪紧接着又指出:“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⑪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地真卷十八”,第323 页。这句话来自《老子》三十九章,原文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为天下贞。”⑫[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06 页。葛洪只保留了其中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省去了道的其他显现方式,又添加了“人得一以生”的陈说,这里显然是在用《周易·系辞下》的三才概念来统摄“道”的存在方式。而《老子》三十九章中的“神得一以灵”则被葛洪单独赋予了超越于天地人之上的人格神的神圣价值,“一有姓字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传其姓名耳”⑬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地真卷十八”,第323 页。。葛洪将此人格神称之为“真一”(“真一有姓字长短服色”⑭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地真卷十八”,第325 页。)。
可见,葛洪在“道”所显现的天地人的三重结构中置入了神性的超验价值,道的构成就变成了天地人神的四重维度,而神性维度在道的现实存在中虽然无法显现,但却是真实在场并有着超验的能力,葛洪认为信守真一之神就能拥有辟邪除魔的超验能力,“鬼不敢近,刃不敢中”⑮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地真卷十八”,第324 页。。葛洪以真一之神置入传统之道的三重结构当中,既超出了儒家在历史时间中的入世理想,也改变了道家在自然时间中的出世目的。由于有了这样一层神圣的超验维度,葛洪的乐论思想也显现出与传统儒道乐论不同的价值意义。
一、《抱朴子》外篇中的乐论思想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的乐论思想涉及到至人、君主、俗士(包括某些君主)这三类人群,葛洪运用这三类人群与音乐的关系描写表达出他对于君臣关系、士人与世人关系的独特看法。这些乐论思想就像是人的内在精神的隐喻,让我们看到了魏晋士人在遭遇到了历史迷乱之后是如何寻求自己的价值旨归的。在这三类人群当中,至人是葛洪为东晋士人树立的理想人格榜样,至人精神不仅继承了老庄思想的精华,更被他赋予了神圣的价值属性。
在《抱朴子》外篇中涉及到的第一类人群是至人。此类人物有着超越常人的能力,所以葛洪将其称之为“至人”。⑯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畅玄卷一”,第3 页。在《抱朴子·尚博卷》中他对至人有着这样的乐论描述:“援琴者至众,而夔、襄专知音之难。”⑰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尚博卷三十二”,第111 页。能够操琴的人很多,唯独舜帝时期的乐官夔和春秋时期孔子的古琴老师师襄专门享有“知音”的难得名声。葛洪写这句话的前提是因为大部分的俗士看问题都是“一概而论”:“俗士唯见能染毫画纸者,便概之一例。”⑱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尚博卷三十二”,第109 页。也就是说,俗士与至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不具备对于事物的深刻感知力和清晰辨识力。事物的复杂性往往体现在高低、疏密、深浅等等对立因素的相互交杂,这就需要有着敏锐辨识力的智者对其进行区分,用葛洪的话说就是“清浊参差,所禀有主”⑲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尚博卷三十二”,第109 页。,智者需要在清澈中发现浑浊、浑浊中发现清澈。那么,夔与师襄超越常人的音乐感知力与辨识能力体现在哪里呢?葛洪并未对此进行详细说明,但在《尚书》《淮南子》等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尚书·舜典》载有一段帝舜与乐官夔之间的著名对话:“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⑳[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舜典第二》,廖名春、陈明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93—95 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帝舜赋予乐官夔教育未来担纲者(胄子)德性教育的责任,这一任务是通过“乐教”的方式达成的,因为良好的音乐不仅能够引导胄子朝着向善的品质发展,同时也能通过音乐内在规律的掌握开启“神人以和”的属天境界。《淮南子·泰族训》中也说道:“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㉑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泰族训》(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673 页。可见,夔通过作乐的方式,能够建立起人与内在性情、人与自然之道、人与神性境界的联系。
孔子的老师师襄也与夔有着同样的超常能力。《淮南子·主术训》载:“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㉒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主术训》(下),第276 页。孔子向襄子学琴,能够将襄子琴曲中的未发之意晓谕出来(“谕文王之志”),说明孔子“见微知明”的能力不仅来自其自身的天然禀赋,也出自其师襄子本身所具有的“见微”能力。正如马融所言“夔、襄比律”㉓马融:《长笛赋》,选自[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327 页。;嵇康亦言“夔、襄荐法”㉔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琴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版,第90 页。,葛洪之所以选择夔与襄两位乐师的例子,都是在说明“至人”的超凡能力体现在他们能够透过外显的事物看到隐而未现的事物本质,他们能够利用音乐来塑造人的良好性情,捕捉音乐内部的规律要素,并将这一内在规律外显为“谕文王之志”等诸如此类的政治行为,孔子所谓的“谕文王之志”即是通过操琴的方式领悟到了文王为灵魂立法的精神意向。
可见,葛洪所说的“援琴者至众,而夔、襄专知音之难”实际上探讨的是一类具有深刻辨识力的至人群体,他们能够区分的不仅是音乐的好坏,更是对人的灵魂层次的认知,因为往往事物的复杂性就体现在雅俗、是非、对错的混淆。因此至士不会像俗士一样对事物的判断“一概而论”,他们不是简单地将好坏断为两截,而是常常能在民间的粗拙歌谣中看到智慧,并把这些智慧言语撰写记录成仅次于典诰的文献。㉕“是以闾陌之拙诗,军旅之鞫誓,或词鄙喻陋,简不盈十,犹见撰录,亚次典诰”。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尚博卷三十二”,第99 页。他们能将各种复杂的灵魂编织成美丽的乐音,“众音杂而《韶》、《濩》和也”㉖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尚博卷三十二”,第103 页。。更为重要的是,至人具备沟通天人的知微禀赋,并能传达上天旨意为万世立法。正如葛洪所言“聪者料兴亡于遗音之绝响”㉗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广譬卷三十九”,第338 页。,至士之所以能够通过音乐感知国家的兴亡,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到音乐中所隐藏的灵魂向度是否“合六律”“调五音”,这些因素关系着“神人以和”的程度,关系着人之性情的良善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都是国家政治兴亡的内在表征。葛洪能够透过至人对音乐的理解看到其背后所具有的神圣价值。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还谈到了第二类人群——君主,葛洪认为君主与臣下的关系是依据上天的法则,尊卑等级是命定的(“往圣取诸两仪,而君臣之道立”㉘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君道卷五”,第174 页。)。既然君臣之间不可以僭越等级,那么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就必须“修诸己以先四海,去偏党以平王道”㉙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君道卷五”,第174 页。君主自身要做到自我修养,自我省思,如此才能为天下做出表率。然而葛洪指出“汉之末世、吴之晚年”的历史实事让人们看到了上层统治者的德行品质并非如此自律,他们“唯在于新声艳色,轻体妙手,评歌讴之清浊,理管弦之长短”㉚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崇教卷四”,第162 页。,也就是说,这些上层阶级对音乐的感知完全停留在自我欲望的满足上。
但葛洪并未把这些过错都统统归咎于君主自身,他没有把由于人性的软弱而产生的腐败问题简单地归于君主的作为与否,因为葛洪曾说“八音九奏,不能无长短之病”㉛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重言卷四十九”,第637 页。,各种乐器持续不断地演奏一定会出现长短节奏错乱的问题,这就等于说在时间当中错谬的产生是必然的(“夫两仪肇辟,万物化生,则邪正存焉尔”㉜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诘鲍卷四十八”,第575 页。),每个人都有可能落入人性的软弱。所以葛洪指出“伯牙谨于操弦,故终无烦手之累”㉝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重言卷四十九”,第638 页。,只有不断葆有一颗谨慎敬畏之心,才能避免声色的诱惑。葛洪在这句话中用了“谨于操琴”的说辞,这就意味着即便像伯牙这般超越常人的至士依然需要谨慎持守自己的心性。这样一来,帝王与至士、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问题就转向了超越历史维度的神人关系问题,两者之间的权利矛盾也被潜移默化地解决了。
葛洪在其乐论中还涉及到了第三类人群——俗人(也包括某些君主)。他指出:“音为知者珍,书为识者传。瞽旷之调钟,未必求解于同世。”㉞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喻蔽卷四十三”,第434 页。师旷所调的音调,未必让同时代的人都理解。为何不向世人表明乐中之意?我们可以查找一下葛洪提到的“瞽旷之调钟,未必求解于同世”的原文之意,该文出自《吕氏春秋·长见》:
晋平公铸为大钟,使工听之,皆以为调矣。师旷曰:“不调。请更铸之。”平公曰:“工皆以为调矣。”师旷曰:“后世有知音者,将知钟之不调也,臣窃为君耻之。”至于师涓,而果知钟之不调也。是师旷欲善调钟,以为后世之知音者也。㉟[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仲冬纪第十一·长见”卷第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611—612 页。《淮南子》与《汉书》中也有类似记载。
师旷之所以能够判断钟声合律与否,是因为他通过乐音听到了音乐背后神圣信息,这里面包括自然之律(六律五音八风),也听到了超越世间的表征着神圣秩序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是为了满足人的耳目,而是为了传达上天的神圣旨意,正如葛洪所言:“薄九成而悦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灵祇而仪翔凤矣。”㊱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博喻卷三十八”,第310 页。大多数世人都无法理解《箫韶》九成之乐背后的神圣旨意和超验秩序,在葛洪看来只有神性意志才是君主与世人都要遵循的绝对法则。之所以不能向世人揭晓这一属天秘密是因为“震雷不能细其音以协金石之和”㊲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广譬卷三十九”,第324 页。,属天之乐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听觉审美需求而产生的,真正的价值标准并不在世间而在上界,但这样的真理并不是俗士所能够领受或者说愿意领受的。
葛洪曾经借助士人“鲍敬言”的话说出了这一属世真相:“古之为乐足以定人情,而今则烦乎淫声,惊魂伤和。”㊳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诘鲍卷四十八”,第549 页。古之乐之所以能够稳定人心,因为其中蕴含着人们可以信靠的神圣价值,而今天的音乐之所以繁杂过度,是因为人们失去了对神圣价值的信仰。“惊魂伤和”就是这种失去神性信靠之下灵魂破碎的表征。那么,东晋士人将如何处理自身与俗士之间的关系呢?葛洪以乐论的方式做出了回答。
葛洪提出当神圣之恩临在的时候(“龟、龙吐藻于河湄,景、老摛耀于天路”㊴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诘鲍卷四十八”,第518 页。),敬奉神灵的礼乐之举自然会带来君臣的安定与百姓的守法,即“礼制则君安,乐作而刑厝也”㊵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诘鲍卷四十八”,第518 页。。也就是说,士人与君主之间如果有着共同的神圣信仰就会和谐相处。在葛洪看来,所有的君臣矛盾都与人性自身的欲望有关,而未必都是君主个人的问题,“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岂必有君便应尔乎?”㊶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诘鲍卷四十八”,第522 页。
当面对有着口舌争竞的俗士时,葛洪给东晋士人提出了这样的忠告:“希声以全大音,约说以俟识者矣。”㊷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重言卷四十九”,第642 页。少发声、少说话,等待未来的知音者,“冀知音之在后也”㊸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应嘲卷四十二”,第414 页。。而这份等待与其说是等待知音不如说是等待神灵的开启,葛洪用了这样一句比喻来说明:“夫玉之坚也,金之刚也,冰之冷也,火之热也,岂须自言,然后明哉?”㊹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重言卷四十九”,第637 页。
对于严守律法、不知变通的君主或俗士,葛洪又以更新礼乐的方式来为士人提供方法,“夫三王不相沿乐,五帝不相袭礼,而其移风易俗,安上治民,一也”㊺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省烦卷三十一”,第96 页。,也就是说“制礼作乐”不能成为历史实事的原样延续。这一思想看似是在重复法家的变革主张,但是葛洪却是站在神圣的超越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人伦虽以有礼为贵,但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让之繁重,拜起俯伏之无已邪?”㊻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省烦卷三十一”,第80 页。在葛洪看来,传统的形式并不能成为礼乐继承的标准,人所要延续的是对神圣秩序的顺服与神圣权威的敬畏。因此葛洪指出每一时代的制礼作乐都有着不同的形式与内容,但这些不同的礼乐又能使人们在持守神圣旨意的时候实现风俗的改变与君民的安定。
由此可见,葛洪的乐论思想当中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特别是至人群体承担了沟通天人的属天使命,而这一群体也是葛洪为东晋士人所树立的精神领袖,至人群体更多关注的是音声背后的隐微象征、审慎品质的塑造养成以及礼乐传统的延续更新。而至人这些优秀品质的建立与他们对雅颂之乐当中神圣意象的追求有关,“苟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鲜知忘味之九成,雅颂之风流也”㊼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辞义卷四十”,第395 页。,在葛洪眼中礼赞神灵的《雅》《颂》之乐带给人的精神满足足以让人忘记世俗欲望带给个人的快乐。
二、《抱朴子》内篇中的乐论思想
葛洪在他的乐论思想当中对至人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至人嘿韶夏而韬藻棁”㊽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畅玄卷一”,第3 页。,其中“嘿”同“默”。韬是隐藏的意思。藻棁是指画有彩饰的短柱,此处喻指天子的庙饰。㊾参见张松辉译注:《抱朴子内篇校释》“畅玄卷一”的注释11,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7 页。这句话的大意是说:至人在《韶》《夏》这样的雅乐面前保持沉默,在侍奉天子之事功方面隐藏自身。葛洪此处所言的至人在《韶》《夏》面前是默然的,而在《抱朴子》外篇中他则言“注清听于《九韶》者,巴人之声不能悦其耳”㊿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守塉卷三十五”,第184 页。,同样面对雅乐,此处的至人又是积极和专注的,可见葛洪的说法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说明一下葛洪乐论思想的价值依据,葛洪认为:“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疏之大宗也。”51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畅玄卷一”,第1 页。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对“玄”做了如下的描述:“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故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5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畅玄卷一”,第1 页。
葛洪所言之“玄”能够孕育元气,铸就天地。吐故纳新,创造万物。在葛洪眼中,“玄”是一种具有创生化育力量的生命本体,这一点继承了王弼等人的玄学理论。然而葛洪在他的《地真篇》中将这一生命本体赋予了神性意志,“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真一同功。……守玄一复易于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长短服色,此玄一但自见之”53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地真卷十八”,第325 页。,葛洪认为掌握玄一之道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辟邪消灾,玄一与真一之神有着一样的能力。守“玄一”比守“真一”更容易些,“真一”之神有姓名、长短、服色(笔者按:不易达到),而“玄一”只需要自己修炼就能成就。
如何让生命的时间性进入到超时间性的玄一之道中?葛洪的办法就是“守一”,持守玄一之道,“杜思音之耳,远乱听之声,涤除玄览,守雌抱一”5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至理卷五”,第111 页。,即隔绝一切外界干扰,回归创生本源的自然状态,安时处顺,在时间中超越时间。具体的方式就是“反听内视”,即以道教的自我修炼方式进入到无形至寂的境界中(“内视于无形之域,反听乎至寂之中”55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释滞卷八”,第152 页。),而要想实现守玄之道,首先要做的就是摆脱世俗音声的牵绊。
那么,葛洪如何既持守玄一,又关注雅乐?一个在《韶》《夏》等雅乐面前保持沉默(“反听乎至寂之中”);一个积极追求“注清听于九韶者”?葛洪曰:“且夫养性者,道之余也;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56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塞难卷七”,第138 页。葛洪认为尊道的目的不是单单为了养生,而是“不言而化行”,即以无言的方式教化大众。也就是说,葛洪眼中的道家与儒家都具有着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只是方式不同,一个制礼作乐,另一个静默不言,但两者都不离教化众生的社会价值,这也是葛洪称自己为“儒者之末”的原因所在。57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自叙卷五十”,第668 页。修身成仙与经世济俗在葛洪处犹如一体的两面,其结合之处就在于价值依据“玄一”,即有着生命本体意义的生生之道。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要想保持静默不言的教化方式,除非让人人都成为至者,否者无法做到对于大众的“化行”。但葛洪也说过:“聋瞽在乎形器,则不信丰隆之与玄象矣”58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论仙卷二”,第13 页。,心耳闭塞之人只在乎有形有声的具象之物,对于自然的丰富与超自然的玄象是不相信的,可见人人成圣是不可能做到的。
二是,葛洪秉承的是道本儒末的思想(“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59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明本卷十”,第184 页。),那么儒家制礼作乐的绝对依据也只能是“玄一”之道,即创生化育的生生之道。就是说儒家的制礼作乐就像是生命本体的生机发展,国家事功也可以视为生命有机体的无限延展。但是葛洪自己也曾指出:“夫两仪肇辟,万物化生,则邪正存焉尔。”邪与正在万物化生的时候就产生了,一旦进入济世救俗的历史时间,恶性也将不可避免的产生。所以,“贵儒者”如果依着“道本儒末”的思想,真正实行起来其实相当危险,因为恶性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葛洪自己也举出过张角、柳根等人的例子,他们“或称千岁,假托小术”60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道意卷九”,第173 页。,以仙道的名义打着济世救民的幌子,利用道术欺骗百姓举兵叛乱。
这样看来,葛洪以“玄一”作为万物之宗,那么道家的“沉默无声而道化流行”就需要人人修炼成圣才能成行;儒家的“制礼作乐移风易俗”要想做到,就需要在万物化生的源头阻止“邪恶”进入历史时间。由于葛洪意识到人的灵魂层次的不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至人”占据“玄一”的位置,修道成仙,一旦“至人”修炼成了“真一”之神,那么他便拥有了沟通天地人神的权柄和能力。
与其说葛洪在避世尊道,不如说葛洪出世的目的是为了入世,其济世救民的政治思想正是其炼丹修仙的信仰方式的内在驱动力,葛洪引其师言“能知一则万事毕者也”61王明:《抱朴子内篇校笺》“地真卷十八”,第324 页。。可见,葛洪思想中的礼乐教化与静默无声在“玄一”之道(生命本体)的基础上达成了一致,之后再以修炼成仙的(永生)方式拥有“真一”之神的神圣权柄,以此实现出世入世、或动或静的绝对自由,最终目的是实现至人对于世人的精神引领(礼乐教化)。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从葛洪《抱朴子》内外篇中的乐论思想中,看到了葛洪作为东晋思想家所具有的深刻辨识力与审慎的德性品质,葛洪看到了魏晋士人任诞谈玄的世风背后带来的是价值标准的混乱,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标准看待事物,“真伪颠倒,玉石混淆,同广乐于桑间,钧龙章于卉服”62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尚博卷三十二”,第105 页。。在葛洪看来没有建立在神性维度上的谈玄论道都是心随己意的一孔之见,因为魏晋士人谈玄任诞、背礼叛教的行为身后无法触及到人世的根本问题。63“无以近人信其喽喽管见荧烛之明,而轻评人物,是皆卖彼上圣大贤乎?”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自叙卷五十”,第682 页。
所以葛洪试图从“玄一”之道这一具有生命本体意义的源头为人们找到绝对的价值标准,同时为了让这一本体视角具有沟通天人的社会价值,葛洪又在“玄一”的基础之上置入真神的神圣意志。由于有了玄一真神的整全视角,葛洪面对复杂的人性与现世时,在其“自叙”中指出:“唐尧、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64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自叙卷五十”,第682 页。即便是唐尧、公旦、仲尼、季札这些圣人也有人性的有限。本着这一审慎态度,葛洪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群,提出了不同的乐论主张,其目的是以至人所具备的超验视角来重新认识士人与君主、士人与俗人的关系。
当神恩临在的时候,葛洪指出“礼制则君安,乐作而刑厝”,因为以共同的神圣目的而制作的礼乐,会自然地带来君臣的和谐与百姓的稳定。当面对相互争竞的俗士时,葛洪言“冀知音之在后也”,即让士人学会等待,不是只等待知音的理解,更是等待神灵对世人的开启。对于固守成规的制礼作乐之人,葛洪提出:“夫三王不相沿乐,五帝不相袭礼,而其移风易俗,安上治民,一也。”礼乐是对神圣秩序的顺从和对神圣权威的敬畏(“但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所以不同时代的礼乐可以是不同样式的,但其移风易俗、安上治民的神圣价值却永远一致。
对于能够听闻天音的少数至人,葛洪还描述出他们的两种看似相反实则相成的行为举动,一边“内视反听”于至寂之中修炼成仙,一边听闻《韶》《夏》施行礼乐教化。因为在葛洪的思想当中儒道思想都是以“玄一”这一生命本体为起点,站在这一起点上,至人可以通过内视反听等道教手段进一步修炼成仙,以此拥有真一之神的神圣权柄与超验能力,最终重返人间实现礼乐教化的精神感召。
不过,葛洪的一生除了集中精力炼丹修仙之外将大部分时间用来研读经典、著书立说。这是因为葛洪终究意识到人的生命与天地相比就像流星与箭矢一样稍纵即逝,所以葛洪在他的“自叙”结尾处强调一个儒者要将有限的思想记录下来供后人去评述,“故因著述之余,而为自叙之篇,虽无补于穷达,亦赖将来之有述焉”65。
葛洪自释以“抱朴子”著书的原因:“洪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书因以自号焉。”66“抱朴”出自《老子》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67“抱朴”就是让人的生命回归到像树木一样的天然状态。葛洪《抱朴子》内篇以道教思想为主,外篇以儒家思想为主,这就如同让自己的本然生命站在儒道思想的中间。在他所构筑的天地人神的四重维度下,葛洪以绝对的神性视角对各类人群进行审慎地观察,他的音乐思想更像是对这些东晋士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在隐喻。当面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价值混乱问题时,葛洪通过他的这些音乐思想做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