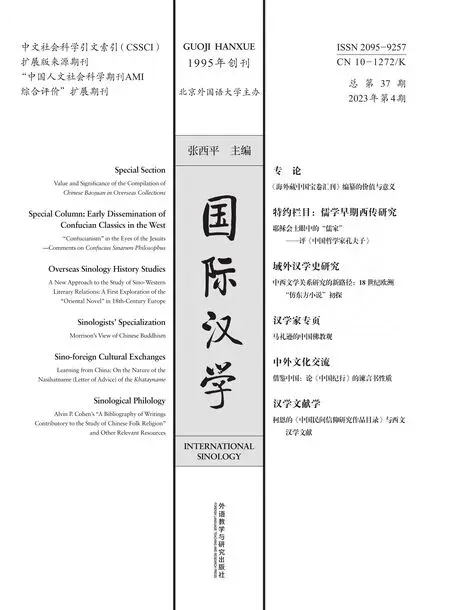借鉴中国:论《中国纪行》的谏言书性质*
2023-12-23王艺涵
□ 王艺涵
《中国纪行》(Khаtаупате)于1516 年成书于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其作者名为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Seid Ali Akbar Khatay),原书以波斯语写成,现有中译本①中译本成书过程见: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张铁伟等译:《中国纪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第14 —21 页。。《中国纪行》以游记为体裁,描写了明代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曾经被进献给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塞利姆一世(1512 —1520 年在位)与其子苏莱曼一世(1520 —1566 年在位)。该书作者声称自己曾于明武宗正德年间到访当时的明朝,以游记为体裁,描写了明代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然而,不难发现,书中的许多内容并不符合明代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是描绘了一个制度完善、法律健全、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化国度。笔者认为,这本书实质上并不仅仅是一本为了要反映明朝真实情况的游记类著作,而是作者借此来为16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现实量身打造的一部政论性质的作品。书中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困境,以“中国”作为参照对象,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一、借鉴中国法律制度
谏言书是一种向统治者提供建议的文体。其内容包罗万象,并在全世界广泛存在。奥斯曼帝国谏言书直接来源于阿拉伯—波斯的谏言书。例如,著名的波斯谏言书《卡布斯教诲录》(Qābūsпāтаh)于15 世纪末被翻译成奥斯曼土耳其语。该书撰成后,广泛传播于波斯和伊斯兰世界,被誉为“伊斯兰哲理和道德箴言集”“伊斯兰文明的百科全书”。类似的作品很多,例如萨迪(1208 —1291)的《蔷薇园》也是属于“教诲类”的作品,尤其在该书的第一章中,明确写出了作为君主所应该有的行为规范。谏言书作为为统治者和官员提供咨询的政论类文本,同时也是一种文学体裁,也在欧洲流行。在西欧语境下称作“君鉴”(拉丁语:sресиlа рriпсiрит,英语:mirrors for рrinces),马基雅维利(1469 —1527)的《君主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一类谏言文学作品为统治者描述了统治国家的基本行为原则,并就某些方面的问题向统治者提供建议。
从15 世纪中叶到16 世纪中后期这段时间,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大片的领土,帝国的疆域横跨欧亚非三洲,是环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塞利姆一世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灭亡了马穆鲁克王朝(1250 —1517),占据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汉志地区,并击败了伊朗的萨法维王朝(1501 —1736)。相较于穆罕默德二世(1444 —1446 年、1451 —1481 年两度在位)时期,领土面积扩展了近一倍。然而,奥斯曼帝国当时的政治体制无力支撑其统治如此庞大的疆域,这就导致了在塞利姆时期,虽然帝国的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然而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在作为本土的安纳托利亚地区都难以实施有效的统治。各地方势力各自为政,不听中央号令乃至于掀起叛乱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如何对国家实行有效统治这一问题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对于如何统治国家这个问题,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们从各种角度出发撰写了一系列的建议类型的作品。此类作品在奥斯曼帝国被称作“nasihatname”,即谏言书。早期的奥斯曼帝国谏言书以翻译和模仿波斯的谏言书为主,其特征为通过无条件地遵守“正义”和“公平”来建立和维护王朝主权的合法性。①Ciрa, Н.E, Тhе Mаkiпg оf Sеliт: Sиссеssiоп, Lеgitiтасу, апd Mетоrу iп thе Еаrlу Mоdеrп Оttотап Wоrld.В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7, р.195.从16 世纪中叶开始,奥斯曼帝国的谏言书由以翻译波斯语作品为主转而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突出特征在于,谏言书的作者们将写作的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不再是单纯的对苏丹或大维齐尔(grand vizier)本身的行为或执政方式提供建议。
《中国纪行》的作者的身份和籍贯目前仍无定论。按照学界一般说法,根据此人的姓氏,他可能是一名来自中亚河中地区的商人,于明武宗正德年间冒充朝贡使者来华。《中国纪行》全书共21 章,其中第六章是该书的核心章节,大部分内容涉及中央政府官僚机构的运作情况,还包括宫廷礼仪及其程序和规则,皇位的继承以及政府结构和官员的职责等。在这一章的最后,作者为本章做了总结:“正是由于忠于法律,他们的国家几千年来没有遭到破坏,相反地,它日益昌盛。”②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张铁伟等译:《中国纪行》,第88 页。对法律的强调可以视为为本书的核心观点,也正是作者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
《中国纪行》的篇章结构与单纯的游记类文本有很大的不同。其并非按照游览的时间顺序或者地理上的空间顺序所书写的,而是每一章都是一个独立的专题,各章之间不存在特定的先后顺序,体现出了其政论性文本的特征。以11 世纪著名波斯语谏言书《卡布斯教诲录》为例。其中,每一章谈论一个不同主题。从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国家行政再到个人生活,包含了对于君主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的建议。③Нemmat, K.L, “Children of Cain in the Land of Error: A Central Asian Merchant’s Treatise o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Сотраrаtivе Stиdiеs оf Sоиth Аsiа, Аfriса апd thе Middlе Еаst 30.3 (2010): 98.同时与《中国纪行》一样,在一些章节的正文之后附有一些故事,来佐证说明正文中作者所提出的观点。④昂苏尔·玛阿里著,张晖译:《卡布斯教诲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译者序第5 页。《中国纪行》中详细记录的并非作者在中国的游览历程,而是描述了作者所认为的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并试图针对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危机提出解决方案。
《中国纪行》的主题虽然是关于中国的,然而它是基于16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国情所写的一部作品,对中国的描述未必符合明朝的实际情况。作者写作的实际目的是给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提供政治上的建议。在16 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的作家们意识到法律概念对帝国政治管理和体制的重要性,“法律”一词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性文本和帝国的公共话语中占有着中心位置。因而与一般游记类作品完全不同的是,《中国纪行》的每一章几乎都在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在波斯语和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原文中“法律”一词写作kanun。该词在16 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更常见的意思是指“习惯做法、习惯程序”。因此,《中国纪行》中频繁提及的“法律”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指代成文法、政策、制度或惯例等。⑤Tezcan, В, “Law in China or Conquest in the Americas: Comрeting constructions of рolitical sрace in the early modern Оttoman Emрire,”Jоиrпаl оf Wоrld Нistоrу 24.1 (2013): 117.该书从君主、大臣和臣民的三个角度阐述了作者想象中的理想政治模式,并与奥斯曼帝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对照。
首先是理想化的称职皇帝与皇位继承。作者在第六章中写道:“如果皇帝到郊外去狩猎,在众人面前掉下马来或让他的马去追踪猎物,这两种情况,都属于犯罪,要被废黜出宫,他的后代也被剥夺继位权。因为他做了违反法律的事,”“如果皇帝因犯罪而被废黜,他的儿子不能继位,或者皇帝死了但无子嗣,则从这些亲王中选出最能干的一个加冕称帝。”在同一段还写道:“中国皇帝如果一个月中有两次未上朝,他可以得到原谅。假如出现第三次,又没有什么理由,他就有罪。他们给皇帝写了罪状。罪状意味着违背了法律。假如皇帝有三次罪状,他将被弹劾交权。他的后代也被株连,不准继承皇位。”①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张铁伟等译:《中国纪行》,第76、81 页。同样在前言的最后部分作者也写道:“他们的国家由于遵守法律而自然地保留下来,在中国不论是哪朝皇帝都不触犯法律的一根毫毛。”②同上,第9 页。这一段关于皇帝犯罪和皇位继承的描写,也许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塞利姆一世继位方式的一种隐晦的批评。塞利姆一世本身并非他的父亲巴耶济德二世(1481 —1512 年在位)最初所指定的继承人。1512 年,巴耶济德二世不愿意再继续统治奥斯曼帝国,因而宣布由塞利姆的哥哥艾哈迈德皇子(Şehzade Sultan Ahmed)继位。然而,塞利姆兴兵夺位,击败他的父亲与兄长成为苏丹,并在即位后为了清除王位潜在的竞争者,杀死自己所有的兄弟与侄子。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的继承制度是极为混乱的。《中国纪行》的作者通过对想象中的中国皇位继承制度进行描写,在对奥斯曼帝国的继承制度进行批评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即使是君主也一定要遵守“法律”,违背“法律”的君主和其后代没有资格继承皇位。这样国家的繁荣和长治久安才能得到保证。可以避免出现像奥斯曼帝国一样,每当世代交替就会发生内战的混乱情况。
其次是理想化的大臣执行法律的原则和行政官僚体系。作者在第十三章“中国的立法人”中写道:“中国有一个立法家,名叫包金星。③指孔子,中文版误译为包金星。Нemmat, ор.сit, р.443.当时国王无法治理国事。这位哲学家和数学家包金星献策于皇帝,请准其治理国家。皇帝答应了他。于是他颁布了法律,治理好了国事。”之后他还写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儿子被迫挖掘其父的坟墓,取出了藏在墓中的法书。而法书上写道要把掘墓取法规的人斩首,于是孔子的儿子就被斩首。之后人们按照孔子的法规办事,中国又一次强盛起来。④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张铁伟等译:《中国纪行》,第115、116 页。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不可能全部都由君主个人完成,因而需要有人来协助君主进行统治,也就是需要一个职业官僚集团。而对这一集团的要求就是如文中所写的,遵守制度与法律,不论亲疏一律按章办事。作者提及此事是因为这与当时奥斯曼帝国混乱的官僚体系有关。在这一时期,帝国的官吏还没能完成官僚的职业化进程,专业化程度低,且人数较少。很多时候苏丹的家庭就等于帝国的中央政府,而政府中的官吏则是服侍苏丹之人,并非职业官员。这个体制已经没有办法统治奥斯曼帝国如此庞大的疆域,因此继续在立法与执法层面进行了改革。之后,苏莱曼时期的官僚化改革正是遵照这一理念进行的。
其三是理想化的臣民遵纪守法的情况。第二十章的内容非常简短,标题为“中国人的守法精神”:“中国人非常守法。如果父母发现儿子或儿子发现父母有一点不守法之处,就立刻去揭发并得到奖赏。他们看着亲属被斩首也不难过。年轻人和老年人都互相尊重,年轻人绝对顺从老年人。……如果一个案子要审两次,按照法律规定就是有罪行,犯人要无条件地受惩处。”⑤同上,第129 页。作者在这一章描写了他所认为的中国人的守法精神,强调守法对于国家秩序的重要性。塞利姆时期地方频繁发生叛乱。各地方势力无视中央的命令各自为政,塞利姆对马穆鲁克的征服和对萨法维王朝的胜利极大地拓展了帝国的疆域。但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极为松散的。针对这一现象,作者给出了人们应当守法的建议。此处的“法律”不仅指法学意义上的法律,也包含了中央政府下达的行政命令。作者认为,只有人人都遵守“法律”才能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从而实现国家的稳定和持久繁荣。作者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中国”从君主到庶民都始终遵从法律。诚然这并不完全符合明代实情。例如孔子的故事很难找到原始出处,亲属间互相举报也违背了“亲亲相隐”原则。①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 年第3 期,第89 页。但与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相比,明朝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确实是十分完备的。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先后颁布《大诰》《诸司职掌》《皇明祖训》《大明律》等法律制度典籍,详细制定了从天子到王公大臣再到普通百姓的行为规范,将全社会的管理纳入法律的框架之内。因此,虽然《中国纪行》中对“中国”法律的描述并不准确,但其中利用法律治理国家这一点同明朝颁布法律制度典籍来管理社会是一致的。
《中国纪行》1516 年成书于伊斯坦布尔,最初是为了献给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的,但塞利姆在1520 年从叙利亚返回伊斯坦布尔的途中突然去世,随即作者将《中国纪行》献给了塞利姆的儿子苏莱曼一世。到了16 世纪晚期,尤其是穆拉德三世(1574 —1595 年在位)即位后,奥斯曼帝国的谏言书在内容上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穆拉德三世时期奥斯曼帝国对外扩张停滞,后宫在朝廷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苏丹的权力缩小。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谏言书中,作者频繁提及奥斯曼帝国处于“衰落”之中。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当权者远离了奥斯曼帝国的既定统治原则。而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一世的时代被视作“黄金时代”,常被用来与穆拉德三世的时代进行比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纪行》一书于1582 年被翻译为奥斯曼土耳其语,这位不知名的译者将书名改为《中国法典》。译者在开头补充了这样一段文字:“这本书是中国国王的法律书的译本。该地区的统治者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法律,哪怕是一丁点。如果他们试图改变他们的法律规定,他们将被废黜,并由一个值得统治他们的苏丹的儿子取代。”②Tezcan, ор.сit., р.115.虽然原著确实强调了中国统治者对其法律的忠诚,但这部奥斯曼土耳其语译本一开始就进行的这一阐述,他还将该书的书名从《中国纪行》(原文可理解为“中国之书”)改为《中国法典》。这种对法律概念的刻意强调,使《中国法典》真正呈现出了其谏言书的本质。《中国法典》的手稿之一与其他谏言书作品被收藏在一起。《中国法典》的不知名译者利用了《中国纪行》独特的写作结构,揭示了这是一部利用遥远的“中国”作为背景,对奥斯曼国内的政治进行变相的评论和建议的政论性著作。③Ibid., р.116.
通过对《中国纪行》上述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是一部基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现实所写的一部政论性质的文本。作者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实际情况,用他所想象的“中国”作为例子,将一部谏言书作品包装成游记来表达其对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隐晦批评和建议。因此,该书可以视作在整个亚欧大陆上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谏言书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通过对所谓的“中国”的描写,打造了一个理想化政治空间,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现实进行对比,为统治者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书中对“法律”的强调令人印象尤为深刻。16 世纪奥斯曼帝国遭遇了种种统治危机,为了解决这些危机,帝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纷纷强调“法律”的重要性。“法律”(kanun)一词在16 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公共政治话语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而这部《中国纪行》则是最早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以及提出应该用“法律”的手段解决统治危机的政论文本之一,在奥斯曼帝国自身政治体制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在奥斯曼帝国乃至早期近代世界政治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借鉴中国政治制度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 —1535)所写的著名作品《乌托邦》(Utорiа)出版于1516年。正是在同一年,阿克巴尔在奥斯曼帝国的都城伊斯坦布尔写作完成了《中国纪行》。两部作品都采用了游记这一形式,虚构了一个理想化的国家样貌,用以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并采用了较为隐晦的手段,对社会和国家提出批评或建议。在这一用意下,《中国纪行》中所描述的中国,如同乌托邦一般寄托了作者对于政治制度的想象。
《中国纪行》第六章,也就是书中最重要的一章的名为“贾姆希德的皇冠和宝座”。贾姆希德,是波斯传说中的俾斯达迪扬王朝的第四个国王,被认为是一位完美的君王,也是后世所有君王的典范。这一章的第一句为“中国皇帝宣称,他的国家和苏莱曼的国家一样,虽然它们之间并无相似之处”。①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张铁伟等译:《中国纪行》,第66 页。其中所说的苏莱曼,指的就是《圣经》中所记载的希伯来国王所罗门,《古兰经》也有对该国王生平事迹的记载,国内伊斯兰教学界将其名字译为“苏莱曼”,以跟基督教相区别。传说中“苏莱曼的国家”是一个美妙无比的完美国度。
在伊朗进入伊斯兰时代之后,原有的前伊斯兰时代的历史和英雄传说开始与伊斯兰教信仰相结合。经过以菲尔多西(Ferdowsi,935 —1020)为代表的众多伊朗文人的创作,贾姆希德开始与《古兰经》中苏莱曼的形象相结合。二者作为君王的典范,常常被一同提及。到了14 世纪,二者的形象已经融合在了一起。至少在文学作品中,贾姆希德和苏莱曼已经是同义词了。②Вrookshaw, Dominic Parviz, “Mytho-Political Remakings of Ferdowsi’s Jamshid in the Lyric Poetry of Injuid and Mozaffarid Shiraz,”Irапiап Stиdiеs 48.3 (2015): 467.《中国纪行》的作者完全将贾姆希德的宝座和苏莱曼的国家视作了可替换的同义词,以此来代指一种理想化的统治秩序。在其之后的叙述中,着重描写了要建立这样一个“苏莱曼的国度”所需要的条件。
在本书前言中作者写道:“万能的真主按天意授给这些人民以管理国家的科学,使它从阿丹③阿丹:《古兰经》中人类始祖的汉译,《圣经》译为亚当。时代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过混乱。中国人甚至说努哈④努哈:《古兰经》汉译名,《圣经》译为诺亚/挪亚。的洪水从未到过他们这里,未发生过瘟疫。饥荒和物价上涨都被克服了。他们的国家由于遵守法律而自然地保留下来,在中国不论是哪朝皇帝都不触犯法律的一根毫毛。”⑤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张铁伟等译:《中国纪行》,第32 页。
在本书的最开头,作者写到,中国是有着管理科学的国家,并描绘了在这种管理科学的指导下,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井然有序。这种乌托邦式的叙述与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实际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从没有过瘟疫的“中国”相比,这一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可谓多灾多难。截至《中国纪行》成书,伊斯坦布尔在之前的几十年里遭受了瘟疫、火灾、激烈的继承权争夺,以及1509 年的一场特大地震。此外,还有30 年的饥荒和战争的间接影响,这些战争摧毁了伊朗西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东部。⑥Нemmat, ор.сit., р.258.此外,穆罕默德二世(1451 —1481 年在位)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后,受困于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已不适合统治庞大的疆域,而试图进行一场财政改革,但因受到了地方势力的重重阻挠而最终破产。前文已经叙述的塞利姆一世征服了庞大的疆域,拥有崇高的威望,但帝国的行政管理混乱,对地方的统治不稳。而《中国纪行》提出的关于“法律”和官僚制度的建议,对这个时候的奥斯曼帝国来说是尤为必要的。
《中国纪行》的作者欲通过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理想化描述来谏言奥斯曼帝国君主应当对奥斯曼国家机构进行相应的改革。首先是在教育体制与行政官员选拔方面历陈中国政治制度的完美。《中国纪行》第十四章讲道:“中国各地都有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学堂。只有皇帝批准才能办学,法律不准私人办学。在学堂里学成后就可成为贵官。他们学习过法律,将是执法者,实际上也是国家的治理人。”⑦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译:《中国纪行》,第118 页。很明显这是对于科举制度的概括性描述。在《中国纪行》写作完成后,苏莱曼一世在位时期,奥斯曼帝国开启了官僚的职业化进程。这一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官吏与学者的主要来源不再依靠从领地上征召有名望之人来担任,而是更倾向于在帝国的教育体系内选拔优秀的人才。从1529 年开始,中央官僚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大,是这些变化的一个标志。⑧Ferguson, Н.L, Тhе Рrореr Оrdеr оf Тhiпgs: Lапgиаgе, Роwеr, апd Lаw iп Оttотап Аdтiпistrаtivе Disсоиrsеs.Redwood C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р.112.同时,奥斯曼帝国将官僚的培养体制分成两个部分。出身于穆斯林家庭的人士会被送入穆斯林学校(Medrese)按照伊斯兰传统对其进行教育。同时,奥斯曼帝国通过血贡(devşirme)征集出身于巴尔干基督徒家庭的男孩,其中的佼佼者被送进恩德伦学校(Enderun)进行包括宗教、科学和军事等方面的严格训练。一部分人将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官员,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大维齐尔也就是帝国的首席大臣就出身于这一教育体制。如同《中国纪行》所写的“他们学习过法律,将是执法者,实际上也是国家的治理人”。穆斯林学校和恩德伦学校中没能成为高级官员的毕业生也会充任政府机构中的中下级人员,或者进入军队。这样严格的教育体制为奥斯曼帝国输送了大量合格的官僚,也为官僚机构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同时,大量的官吏也为在帝国中央和地方贯彻奥斯曼帝国的“法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通过征战、立法和官僚的治理,塞利姆时代奥斯曼帝国对地方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的情形得到了好转。这场由苏莱曼所进行的政治制度改革也为苏莱曼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繁荣与持续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中国在行政官员任用体制方面该书作者也认为十分完善。《中国纪行》第三章“城镇和寨垒”中写道:“官府是根据该城的文武官员人数和等级建造的。每个城市都有人管辖,他们的官邸、厅殿、仆人、俸金和生活所需都由朝廷供给。城市长官为公务而日夜忙碌。一旦失职,要遭朝廷黜免并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①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张铁伟等译:《中国纪行》,第50 页。“中国能保持兴旺昌盛和太平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这种代表皇帝巡视的钦差大臣。皇帝待他们有如自己的子嗣。派到各省的钦差都是在划给他的那部分国土上管理国事。如果另一个钦差被指派接替他,这位前任钦差就带着他的财物,在盛大隆重的队伍中,一站接一站地返回皇宫。”②同上,第28 页。这种描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朝创设的督抚制度。根据《大明会典》记载:“国初,遣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巡抚各处地方。事毕复命,或即停遣。初名巡抚。兼军务者,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管粮饷者,加总督兼理。”③(明)李东阳:《大明会典》,第二百九卷。如同书中所写,明朝的督抚是皇帝派遣到地方的“钦差”,所有督抚均加督查院都御史衔,由中央派出负责管理地方军政事务。对于缺乏职业官僚、中央对地方控制松散的奥斯曼帝国来说,《中国纪行》的作者对明朝官僚制度的描述与想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之后苏莱曼时代奥斯曼帝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推动了帝国官僚职业化与中央集权进程。在苏莱曼统治时期,职业官僚集团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而不再由苏丹的身边人充任。在苏莱曼登基后的几年内,官僚机构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多,从39 人增至81 人,并根据头衔和职能进行细致的等级划分。在苏莱曼长达四十余年的统治过程中,官僚机构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时的奥斯曼帝国政府有意识地建立了一个专业的官僚机构,作为该国行政管理的一个独特的部分。④Нemmat, ор.сit., р.258.
尽管我们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是《中国纪行》这部书直接对奥斯曼帝国的官僚化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中国纪行》确实曾经被奥斯曼帝国高层所阅读过。目前已知的《中国纪行》波斯语和奥斯曼土耳其语手稿共有17 份,其中6份为波斯语,11 份为奥斯曼土耳其语。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被数次翻译与出版。⑤Ibid., р.72.在《中国纪行》被翻译成奥斯曼土耳其语后的1590 年左右,赛义菲·切莱比(Seyfi Çelebi)编撰《中国印度诸 王 纪》(Kitаb-i Теvаrih-i Раdishаhап-i Vilауеt-i Нiпdи vе Нitау)。这是一部介绍中国、印度、中亚和伊朗地区概况的作品。该作品共有九章,其中第一章涉及中国,其中参考了《中国纪行》中的部分内容。就像在《中国纪行》中一样,他主要强调中国的正义、穆斯林、财富和繁荣。⑥Emiralioğlu, P, “Relocating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China and the Оttoman Imрerial Project in the Siхteenth Century,”Оsтапlı Аrаştırтаlаrı, 39.39 (2012): 185.可见《中国纪行》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知识精英中存在受众。在亚欧大陆各国普遍进行了中央集权与官僚职业化努力的大背景下,《中国纪行》反映了这一普遍的趋势。作为直接呈献给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著作,必然多多少少会对统治者的思想产生一些影响。当时,中国作为中央集权与官僚国家的典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各国效仿的对象。而书中对明朝政体的理想化叙述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完美的政治体制的一种想象。它主张实行更加集中的官僚治理,用一种人为的法律和制度来全面规范政体,即从人治转向法治,一方面重塑了帝国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又使社会安定下来,符合了当时人们对完美世界的期待。
《中国纪行》的写作逻辑是,要求君主应有责任创造一个充满“秩序”的完美国度。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公正立法,遵守“法律”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法律”公正和完美地执行则需要由职业官僚群体来完成。因而《中国纪行》中描绘了一个由成熟的官僚群体治理的国度。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而并非完全是虚构的。这一点也正符合了日后奥斯曼帝国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趋势。同时,书中所述“中国”是由一群专业人士,或者说是职业官僚进行治理的国家。在这本书被进献给苏莱曼一世后,奥斯曼帝国也开启了一场中央集权与官僚职业化的改革。不仅是奥斯曼帝国,整个亚欧大陆上的许多国家在这一时期都进行了类似的改革。这些改革的源头并不一定直接是中国,但以《中国纪行》为代表的一批文本至少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世界上官僚制度最为完备的中国的一种想象,也反映出了这一时期的全球交流已经不只局限在物质文化方面,在精神文化乃至政治制度层面也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与参考借鉴。
三、结 论
因此,《中国纪行》不仅在中西交通史中,而且在16 世纪的政治思想史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在亚洲东西两端交流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这部书应运而生。作者曾两次将书进献给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显然其目的并非是将其仅仅作为一个游记性质的文本,单纯地想向苏丹介绍一些异国风情;而更重要的是,他借游记形式来劝诫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所以该书具有谏言书性质,亦可称其为一部游记体的谏言书;是作者想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提供针对帝国当时危机的解决方案。该书作者在文本中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明朝。书中的明朝就像一面镜子,照射出了奥斯曼帝国所存在的问题。作者借此委婉地批评了奥斯曼帝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同时寄希望于帝国统治者能效仿他书中的“中国”,完善奥斯曼帝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而完善整个帝国的统治。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法律”,几乎每一个章节都在不断强调“法律”重要。在16 世纪中叶,面对帝国的政治危机,“法律”成了当时政治话语中的核心词汇。而《中国纪行》则早于半个多世纪前就提出了这一理念。甚至可以说,《中国纪行》可能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强调“法律”重要性的奥斯曼帝国政治文本。以《中国纪行》为代表的一系列政论性质的作品,可能为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提供了参考和灵感,并且见证了奥斯曼帝国的政体由简单走向复杂与专业化的这一历史进程。《中国纪行》中所展现的跨地区政治文化交流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各地的政治结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