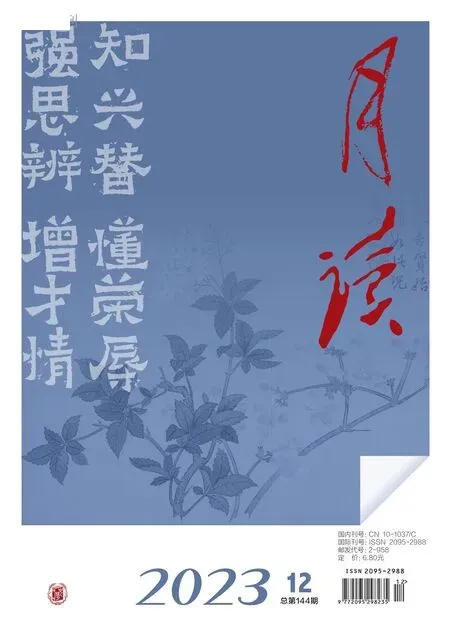现代人仍须“问天”
——《天问》读后
2023-12-22张永军
◎ 张永军

日来闲暇,翻阅朱子的《楚辞集注》,不觉将屈子的《天问》又细细读了一遍。《天问》通篇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皆有问无解。王夫之《楚辞通释》指出:“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下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抑非徒渫愤舒愁已也。”堪称得道之语。
“天道下济而光明”(《周易·谦卦·彖传》),但天道幽远,每无端呈诸福善祸淫。人生天地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问题、设想、说法与关切太多,夹杂在当中的喜怒哀乐、得失兴替更不言而喻。《天问》作于屈子放逐之后,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能无怨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正是藉问天表达自身乃至人类对生存环境与境遇的难以理解、难以接受。设若屈子仍然政躬康泰、日理万机,能否去“问天”,留下这篇“千古万古至奇之作”,还真难说。文章憎命达,果然。
较之于古人,现代人似乎已不再动辄仰问苍天了。在深遭踬踣、濒以绝境际,现在人们深究的多是时运不济、道术不精、人心叵测、丛林黑暗。不遑说,在遭遇不平后,古人问天,而现代人认命。天是道,是规则。对于规则,要敬畏,要遵守。即便“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存亡中不湮没天理、天意,知进守止,大道存焉,“惟数可以推其机”“因数可以明其理”(《留青日札·大明大统历解》)。而命是术,是经营。经营需要营谋,需要取舍,必要时甚或不择手段、罔顾底线。因此,同样是失败,古人虽然抱恨却可以无悔,现代人往往只会遗恨而不想自省。
天道,这个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的核心名词,支撑人生信仰、支配认知取向的理念,是何时被现代人淡忘甚或漠视,更或说现代人何以不再“问天”了的呢?或许,就是从一味求成,对事情本身之外漠不关心,只想更快更便捷获取结果开始的。执着于成败、关注于得失,使人们量事待物日益偏执于有用、无用,“天道”之本渐被“人道”之用所取代。从屈原的问天中,我们或许更得到另外一种启迪: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我们头上的青天、苍穹、日月星、风雨电、白云彩霞,她高大久远存在,就是我们信仰之源、精神之力的昭示和存在。它可以接受祈求赞美皈依敬爱,也可以接受提问质询迷惑抱怨悲情遗憾,但她具备的感召力,永远是我们的人生之本。做任何事情都是始于初心、成于坚守,守得住、行得稳,才能积蓄力量、厚积薄发。道德上真诚的缺失,极易让人流于恍惚,或至狂妄。生如逆旅,方向至关重要,心若偏航,杂念就会纷拥而至。只有光景,没有内在光源,光景炫目,徒乱方向耳。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我们的先人,我们的文化,之所以会问天、观天、敬天、感天、飞天、顺天、承天、冲天、翻天、怨天、倚天、惊天、补天……就因为天道昭昭,一个天,激活了中华文化中思想无上的敬畏和思情感上的无限寄托。没有信仰,哪里会有中华文化、中华故事和中华儿女子孙呢?一个有信仰的人,行为必定与其信仰相符合。有信仰的人才会有所敬畏,认认真真凭藉良知做人做事。梁启超先生曾说:“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即便价值再独特而多元,现代人仍须“问天”—好好做事,营养肉身;好好做人,丰满灵魂。独行快,众行远;心向往之,行必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