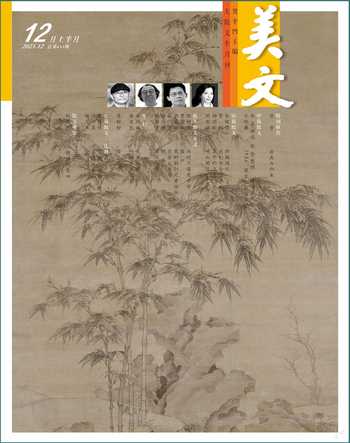哀牢的上空
2023-12-19杨亦頔
杨亦頔
哀牢故地,东山极顶,有一石人端坐,怀中抱有二穴,名金井。在某个不知年岁的孟春,一个不需要细描的脸孔漂浮在水面上,与天空投映在井中的面庞渐渐重叠。脸属于哀牢国中的祭司或典农官,水是神谕,预示着今年雨量的多寡,一口井中足以洞窥天意;此时,他还是抬起了头,放任自己的视线像鸟一样从眼眶中飞走,飞向遥远的天际。
一千多年后,在那个时间确凿的清晨,徐霞客游赏东山金井,在不远处寻到一碑,上书“安乐”,邑人言,不喜哀牢之名,故而改了。霞客说,益无征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瞎扯淡。很显然,对于这种拙劣的教化产品,徐霞客看不上。
1
没有人怀疑,那是一场偶然发生的野合,并且,它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了文字中。
哀牢山下,妇人沙壹捕鱼自给。一日,水中有浮木漂至,她骑在木头上游到了从未探知的幽秘区域。
当雄性主宰一切之前,它只能是浮木,魂体被拘禁在木壳中,拱动挣扎,哪怕它可能是神明。所幸,虫的蛀洞是木身上仅剩的破口,它们充当了它的眼睛、鼻孔、耳洞、嘴。于是,它看到女人柔软的皮肤像白雾一样释放扩散,女人周身的白蒲香气变成蛾蚋的幼虫,钻爬进它的鼻腔,它在猝然而至的异痒中耸动身躯,女人的声音在水中沉没、溶解。只有它的嘴,脱离身体,无限放大,是饲守在水边的山洞,饵诱女人游向传说的深处。
而在父权准时抵达之后,沉木化龙出水,已感孕生十子的沙壹忽听龙语,为我所生之子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幼子不去,背龙而坐,嬉笑如常,龙又用舌尖舔舐小儿。及幼子长成,被共推为王,众子分娶哀牢山下夫妇所生十女,由此世世相继。
无人会注意到荒外溪谷中微小的异动,除非最卑微草木也有了自己的眼睛,它们静不露机,瞵视着这一群骚动不安的动物。直到在一场雷电引发的山火中,它们借助炽烈的火光看清了那些人——他们的手臂和小腿上纹着奇异的图腾,他们的身后拖着长长的,布条装扮的龙尾。
草木是土地上密集分布的触觉器官,它们最先感知到雨的到来,当大火被天上的水浇灭,它们向大地传导着天空的情绪,或者情欲,拖着长尾的人们回到了各自的茅庐。天地交,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似乎一切都在论证着那场人神遇合的真实性。
或许,“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才是历史在哀牢体内留下的真正的受精卵。
传说未完,回到那片山下的水泽,沙壹散开的头发是泼淌在高山深谷间的漆色,顺着石缝淌去了,它是温软的流体,却抱持着汹涌而猛烈的流势,直至与另一个关于水的传说会合。
哀牢故地,不韦,一个真实存在的地名,环绕它的是一条被刀笔精心打磨过的河流——禁水,中原传言,有异事。
那是用无数徒囚的身体饲养的传说,只能借助流放者的眼睛来还原。流经边城的河流,渡客在上船前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有不明的异物疾速坠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辚辚四散,砸进水中。行人以身为船,漂浮在黃雾弥漫的河面上,他被丢弃在流动的荒原中,所有的声音变得异常混沌,只能听到有东西在水中翻腾,像活生生的肉体。人说,水中有瘴母,瘴母,怪物大概是雌性,应是光裸的肌体在水下游摆、堆叠、撕裂。此时,水中有掷物飞出击中了岸边的大树,树应声折断,他却始终没见到河面下那只可能存在的长白的手。将抵对岸,他的后背上突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如果皮肉是一件填了絮的袄袍,现在,厚袍被击穿出一个深深的破洞,白絮轰然膨出,在风中像是微弱却密集的白焰,他在最后看到,河水是缥青色的,叫人想起柔软的蜀锦。几个时辰后,邑民在船上发现了异乡人的尸首,这并不稀奇,色近绀青,软烂如泥。
禁水,人不可近,故郡有罪者,役之禁水畔,不出十日皆死。
禁啊,在任何语境中都是永恒的弃置之地,挤皱的群山间流向不明的河流和慌乱芜杂的水网,像历史腹部的妊娠纹,丑陋而真诚。
传说,生的水泽在扩张,死的水域在收缩。
两个传说在逐退、拉扯,在时间的诱骗下蒸发、积聚、凝结,在哀牢上方形成了虚薄的天空,它应该是第一层。
2
传说的穹隆之下,总有凡人在穿梭。
他们关乎着最通俗而又最复杂的人间法则,他们是传说的现实接口。简单地说,至少曾有三个人试图借助哀牢(或者说与哀牢有关的意象)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人模糊,一人未知,一人未遂。
如果以时间为轴,第一个人约是碎步行走在沙壹传说之后不远的地方。但是,如果用空间来比照的话,任何人都不能确证他是否真正抵达了传说的领地。
在某些特定的夜晚,器物是别有用心的妖灵,在暗中操弄着人、时、事的媾接。青玉五枝灯,铜蟠螭以口衔盘,灯燃,铜兽鳞甲颤动,宫室中像是焕动着无数星辰。空空的漆耳杯扔放在桌案上几近无声,十六岁的汉武帝刘彻还是会忖测,当那个诡异的酒具丢在匈奴人铺着厚毛毯的矮桌上时会发出怎样的声响?他也不止一次想到那些匈奴俘虏的话,匈奴单于擒杀边邻月氏国王,用他的头骨做了酒器,月氏残部遁逃,并与匈奴结下深仇。
寻找月氏旧部,联合共击匈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百余人的使团像未央宫铜灯上瑞兽口衔的一枝灯盏,摇晃、燃照,而在刘彻的眼中,它还不足以照亮整个闳阔的宫室,所以,合兵西域、夹击匈奴只是少年天子军事战略构图中的一个拼块,他拭目以待而又有所保留。也正因如此,张骞的双目是隐秘的移动的窗,它与汉宫宣室殿相通,而当漫天黄沙吹进窗孔,汉武帝会在日光或月华的藻饰下频频见到浮光跃金的奇景。
张骞自陇西出境后被匈奴军臣单于擒获,在单于得知张骞欲往月氏后,他说,月氏在我匈奴的北边,汉朝怎敢派使者前去?就像我们想要遣使去南越国,难道汉朝会让路?
书载这场对话的司马迁没有摹状匈奴单于的表情,戏谑或者玩味,火光和哄笑声也是大帐中一座无形的庞大的灯,向张骞投落在地上的长影发问,是否顺服?张骞的身体和影子始终保持着垂直状态,但他也只能一言不发。
不要低估一个游牧民族首领邃密的思维和清晰的逻辑,在说那句话时,单于蓝色的瞳孔与某一只鹰金色的眼眶发生重合,他(它)们飞临高空,俯瞰大汉的疆域。早在半个世纪前,南越国已向大汉称臣纳贡,以月氏比及南越,是威胁,更是嘲讽。彼时的汉王朝未能完全控御岭南及长江以南的阔大区域,甚至在版图上看,那些晦暗不明地带的形状就像一匹矮小而灵敏的果下马,它被豢养在宫苑中,可以屈身在妇人的胯下,也可以让不可一世的封王坠地折颈而死。
旌节向西,目视四方,汉使的襟怀让一切威胁与讽刺在短时间内失效、风干,尽管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十三年的自由。直到多年后身处大夏,他再次捕捉到“果马”矫捷的身影。集市上,张骞无意中见到了邛都的竹杖和蜀郡的布,而吊诡的是,当时官方绝无蜀地与西域诸国通商的记载。问竹杖、蜀布从何而来,大夏人说,自东南身毒国(今印度)。
在那个寻常的正午,竹杖泛着淡淡的光泽,苎麻布纹理细密,它们是善于伪装的叛徒,它们在向张骞告密,身毒和蜀地之间暗藏着秘密的商道。
或许,汉使張骞永远不会知道,他用错误的要件推理出了一个近乎准确的答案,像天意。
他所看到的布并非是来自蜀地的织物,而是兰干细布,它们产于连司马迁都无法确切描述的西南外域,哀牢国。
回到长安后,张骞向汉武帝呈报了蜀身毒道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对未知地域的推测不会成为政治家决策的动因,早在张骞出使西域的第五年,汉武帝就已派人开辟西南夷道,未果。所以,张骞博广瞻望的凿空之行宿命般地成了大汉继续开拓西南的最好借端。
或可视作一片更复杂的水域,汉朝的疆土像水一样在大地上洇漫,是关乎开疆扩土、鼎定四方的宏构命题,而在西南的边际,水流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它们顺着叶脉状的通道流散开去,车马、商队、奇珍异物、城池驿站,这些分合的“支流”几乎满足了人们对流动的所有想象,当然,在君主的想象中,还有钱粮和赋税。
大汉的西南版图不再浑圆、平滑,在澜沧江西岸的哀牢境内生长出两枚新牙,嶲唐、不韦二县。而不韦县,最初的屯民正是南越国相吕嘉的宗族子弟。打通西域,经略西南,甚至是那个匈奴单于贬刺的南越之喻,就像环状相交的时间和空间,正在沿着未知的轨道缓缓转动。
第一个人不是张骞,不是司马迁,更不是刘彻。他的故事即将结束,而他的脸却始终没有出现。
两千多年后,这条自蜀地通往掸国(今缅甸)、身毒的商道早已残缺不全,甚至在某些路段需要借助文字来连接,但是,稍稍完好的好像就只有这条了: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
这条纸路被卑微的文人视作通道,几乎是唯一的通道,他身属的一切都极其模糊,连同他的名字。
在西南边地,他极有可能是一位底层的文吏,寻求每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是他的终身课题。也许才华和学识不足以支撑他成就一篇子虚、上林那样的大赋,于是,他在这场宏大的国家行动中写下对汉武帝的赞诗,但是,他又无法对从他眼前走过的饱受征役跋涉之苦的行者们视而不见。他无法退避,他在颂扬远不可及的帝王,又在哀怜近在咫尺的黎庶,撕裂的文字恰恰也是他看似打成了死结的人生。
渡兰沧水,直抵哀牢,所有故事必将向前延伸。
那就取一杯江水敬那个注定无法留下名字的凡人,不敬他微末且未竟的梦想,敬他至今存活的文字。
时间总要往前走。
在汉武帝时代结束六十年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已经开始用诗歌来咏叹东方幻境了。一个世纪后,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几乎让所有罗马人相信,当商队穿过积雪皑皑的斯基泰海峡,走过野兽和食人族出没的荒野,会在遥远的东方遇到传说中的赛里斯人。他们的森林里盛产羊毛,他们用水把树叶上的白色绒毛冲刷下来,他们的妻子收集羊毛纺线织布,于是,罗马的贵妇人们穿上了轻薄透明的衣衫出现在宫廷宴会中。当然,也有人怀疑这些绒毛来自某种昆虫的腹中,就像蜘蛛,甚至还给它起了名字,赛儿。
约是在《自然史》动笔的那一年,远距罗马数万里的“赛里斯国”,都城洛阳,汉明帝有一件不大不小的悬心事,虽然不至于社稷攸关,但也颇为棘手,哀牢国即将率部族归汉,明帝每每以哀牢事问朝中官员,无一能答。
当东方与西方发生对视,汉明帝对哀牢的了解并不比古罗马人对赛里斯“羊毛”的了解更多。
殊奇的是,他们的难题会在同一个地方得到破解,蜀。
蜀,桑中蚕,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如果罗马人能见到汉朝人书写在绢帛上的“蜀”字,会对这种幼小生物的印象更加深刻,心中谜团也会像蚕茧在水里的漂絮一样全部散开。
蜀,多才俊,汉明帝不会想到,他的疑题会被一个蜀地的小吏解决。
当哀牢的面遮被扯下,布料丢在地上就是一座绵绵的软山,山上陡直的小路是一个文人的发迹史。杨终,十三岁任郡小吏,此后很长的时间内,他的履历一片空白,甚至怀疑,在一个边郡无名文吏复杂纠结的心境中,对于自身的记忆可能连他自己都觉得多余。
那年秋冬岁尽,洛阳城中益州郡邸,杨终与同僚们在焦炙和不安中等待朝中审核益州郡上计簿的结果,上计,关乎一郡舆图、兵事、农桑、账目,干系地方官吏赏罚升迁,甚而,他们这些上计吏的脖颈上还抵着一柄看不见的铡刀,一旦上计簿被认为欺瞒不实,等候他们的将是郡邸狱幽暗的大牢。可能是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有人讲了汉武帝时名臣朱买臣的轶事,那个生活在两百年的官吏的魂魄被口唇征召,晃悠悠地走进来,嵌套在在场的每一个人体内。也是年末,身为上计吏的朱买臣因献策有功,受到汉武帝赏识,被封会稽太守。朱买臣故意穿上脏破旧衣,怀藏太守印绶回到郡邸,郡中同僚正在宴饮,无人理会他。他闲步到后庭与守邸小吏同席共餐,故意让小吏看到官印绶带。小吏惊骇之下疾报守丞,众官吏如蜂蝶一般推挤在中庭,拜谒朱买臣,朱买臣转身离去,门外只有驷马高车,一骑黄尘。文人在短时间内的情绪切换往往很微妙,彼时可以因为臆想的罪愆而惶惶不安,此时可以为了空幻的功业而暗自欣欣。在这种虚拟的庞杂的心理空间中,一人哂笑说出了上级官署的窘相,今上欲览哀牢事,司徒司空太尉三府所辖官员竟一篇不成。杨终也笑,与众人无二,次日,动身返益州郡。
月余后,杨终抵洛阳,向汉明帝献《哀牢传》。因事务之便,杨终多与哀牢使者接触,他积年记写的“年终总结”即是《哀牢传》的母本。地理通道的雍闭和仕进通道的贯通正如衡器的两端,杨终机巧地沿着横梁走向了想去的位置,汉明帝大悦,杨终被从州郡擢升到兰台做校书官。
至于哀牢归汉,所有史书中的记载都不及一篇大赋中的文字宏丽、翔实。哀牢臣服,故地置永昌郡,诸侯会同洛京,佳肴千种,美酒万钟,金罍成队,玉杯成行,五声高奏,六律弹尽。明帝欢畅,群臣沉醉,空中降下湿热飘荡的云烟,调和人间元气。
此时,在宫中某个远得听不到钟鼓管弦的角落找到杨终,他的句章还远不足以与这场盛大的宴会伴驾并行,作东都之赋,自有文胆班固。
还是衡器,当另一端特定的外力消失了,杨终也只能乖乖地站在原地,也有人讪笑,边郡小吏的奇迹,可一而不可再。可是,《哀牢传》中的文字到底还是僭越了它的主人,变成不安分的咒语,伏笔着另一个更加奇瑰的盛宴。
在漢明帝之后相隔几十年的地方,汉安帝不会想到,自己会在靡丽的宴会上看到如此血腥的一幕。
那个掸国王敬献的幻人(魔术师),裸露着身体,双手伸向耳部,将自己的头颅从脖子上举起,他高高的鼻梁上还涂抹着焰光,他深深的眼窝像是注满诡秘之事的银杯。突然,他的双眼睁开,以这种奇怪的姿势与大汉天子发生了对视。
公元二世纪,分处世界东西方的两个最强大帝国的人第一次真正地见面了,幻人和皇帝。
这个擅作幻戏的外邦人来自数万里之外的大秦(罗马帝国),他们循海而南,横截孟加拉湾,在掸国登岸,沿伊洛瓦底江逆流而上,直抵汉永昌郡。尽管平行的时空在汉朝的宫室中发生了短暂的交叠,但是赛里斯华美的丝绸不在低微的幻人的认知范围之内,就像从大秦到大汉的漫漫长路在天子的认知范围之外。
大汉与罗马,东方与西方,尽管双方开始真正洞察世界的种种真相还远在千年之后,但并不妨碍地中海深处的珊瑚树被栩栩如生地植种在汉宫殿庭的转角处,也不会阻扰帕提亚帝国用东方钢铁制成的箭簇在战场上轻易刺穿了罗马骑兵的盾牌和盔甲。
这一切,必然发生。
杨终在《哀牢传》中写下“哀牢国,其国西通大秦,南通交趾”的时候,就注定了,一切必然发生。
现在,当凡人开始对传说的记忆渐渐模糊,传说却以倾倒的形式迎头而下,就像禁水边那些无处不在的瘴母,凡人站在原地,无处遁逃。
禁水,沿哀牢故地东北而流,见孤高三千余丈的泸峰,晋太康年间,巨山崩塌,震动郡邑,史书有载。而永昌郡,它自晋朝这座中央山体的剥离却悄无声息。
只有蛰伏在《搜神记》中的蛛丝马迹,也许,作者干宝只是随手一记,汉永昌郡不韦县有禁水,水有毒气,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正月至十月不可渡。
禁水,不过是一个蜷曲的畸小的符号,连同禁水一起萎缩、弃置的还有晋朝的疆土。皇权孱弱,无暇四顾,至于僻远的边郡永昌,已在持史为逸、深思熟虑的志怪小说中率先完成了一次舆论性死亡。
东晋咸康八年,罢永昌郡,哀牢故地身归域外。
这一年,晋宫中的妖异似乎比去岁多一些,五月,有马色赤如血,直入宫殿,旋即无踪,数日后,凉州兵事征马数十匹,竟全无后尾。七月,白鹭飞集殿宇,谶言,野鸟入庭,宫室将空。在东晋怪诞的空间里,一切神鬼之事只会验证世族的攻伐,权力的更替,或者帝崩。疆壤和郡治的干瘪、萎缩、凋亡,不过是山体上掉落的碎小石块,当然,碎石的叛乱和异动只会发生在山泽彻底崩塌之前。
在永昌废止,哀牢消失之后,有一人自蜀中姗姗来迟。
常璩,随成汉政权降归晋朝的官员,在兵连战结的成都,常璩第一次见到了率军伐蜀的名将桓温。或许,是桓温的一句话给心怀功业之望的常璩造成了错觉,在众人前,桓温说,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
可能一顿酒,桓温就会把随口说的场面话忘得一干二净。而常璩,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那是“心上人”赠答的信物啊,他心甘情愿地让它盘绕在自己的臂肘上,时时抚看。
常璩错了,桓温伐蜀,意在军事之外,他的剑锋所指终究是代晋称帝,在蜀地举贤用人不过是一面在风中卷展的虚飘飘的锦帜,常璩们不过是他累积声望的工具人。而更残酷的真相是,在门阀世家的拘囿下,政治形势也决不允许他去重用世家大族所认为的鄙远偏邦的一众降臣。
常璩的命途在与桓温相见的一刻就被彻底决定了,而他却像一个口不能言的病者在候守或早或晚但必将得到的良药,期期艾艾、满目欣欣。
归晋后,常璩过得当然不好。理想与现实之间落差的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孩童在子夜独自走进黑暗,行走了数十个时辰却始终没有看到曙光。惊觉家人可能会焦急遍寻他的踪迹,他匆忙返家,竟发现从未有人相唤。也许就是在某个寂长的黑夜中,常璩与数百年前的司马迁产生了知遇之感,司马迁说,凡古人鸿篇巨制,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流离困顿,满面清霜,已年近花甲的常璩开始辑录旧作,起笔编修《华阳国志》,华阳,华山之阳,汉水之南,他说,华阳史志是资腐帛于颠墙之下,求余光于灰尘之中。
华阳国志,南中志,又见到久未谋面的,消失的哀牢。
他讲起不知源流的传说,永昌郡,有一妇人,名沙壹。
他记下没有作者的诗歌,汉德广,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
他转录杨终《哀牢传》中哀牢始祖代代相继的名号。
他写巴国,写汉中,写蜀地,写南中,写那些渐次被晋王朝失却的域外之地。
而在与“禁水”同时存在的时代,他的念愿注定与天子的意望相悖,这是从一开始就无法摆脱的宿命的悲剧,也像多年前他与桓温的见面。
结局没有转圜,常璩的命运并未因《华阳国志》而改变,成书七年后,常璩故世,落寂而哀凉地走向了时间的幽地。
凡人,即是哀牢的第二层天空。
3
没有人知道,哀牢的上空,人间和传说之上是什么。
东晋都城建康,常璩已记不清是第几次抬头观望夜空了,反正这几年都是这样。
有人说,魂魄分去则病,尽去则死,垂暮的老者会在黑夜里看到那些残缺或完整的魂灵,与它们说话,与它们对饮,常璩大概就是如此吧。
同侪讥讽,璩著书夸诩华阳,实为抗衡中原,压倒扬越,自旌才华。太多的话,常璩已经听不见了,他现在倾心所向的是那些看不到的地方。
现在,他只能大致分辨益州的方向,华阳,他曾写下的是,唯天有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
华阳之壤,梁岷之域,分野舆鬼,东井。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分野与巴、蜀同占。
禹贡梁州,永昌哀牢,分野井,鬼。
而哀牢,又何止哀牢。
山河残破,战乱不休,大争之世,一个彻底败退到边缘的文人将视线投向了无边的星野,他把此生恐难再见的中原王朝空间投射、对应、放置到此时可见的星象上,用星辰的分野对应着华夏的州、郡,在袤远的天文图像上,所有流失的,剥离的,碎裂的国土在暗夜中重新合归天际。
此时,在哀牢,或者说是在所有疆域的上空,人间之上是传说,传说之上是繁星历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