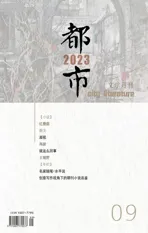桂花巷的呼吸
2023-12-16郭发仔
文 郭发仔
人流,车流,道路,绿地,楼宇,城市的标签千篇一律。我把自己丢进这座都市多年,身处其中却难知其味。而桂花巷,仿佛是夜以继日的呓语,道出了都市生境的温凉。
1
桂花巷,其实并没有桂花。
巷口的道路两侧全是黄葛树,有些霸蛮,枝叶森森,遮天蔽日。不过,低垂的长须透出一身掩饰不住的老气。在炽烈的夏天,阳光漏不下来,清幽的阴气令人身心有些飘忽,精神里有一种恍若隔世的空洞和深远。我曾经问过很多人,桂花巷里缘何没有桂花树,他们要么一脸茫然,要么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在这座都市里,在这个片区,很多人与我无异,是半路挤进来的,对桂花巷纳入城市版图之前的草莽历史,只有零碎的道听途说,唏嘘间只笃定接受眼前匆忙的现实。
其实,没有多少人会刻意深究桂花巷的前世,包括匆匆经过的人群,包括一掠而过的飞鸟,还有长期在此出现的水果摊贩。
摊贩们很准时,他们是桂花巷的时刻表。每天下午,也许是一点过,也许是两点,他们的小货车或者平板车,会第一时间占据桂花巷的喇叭口。苹果、梨子、香蕉、柑橘、李子、桃子、樱桃、草莓、西瓜、杧果、椰子,也不知道哪里贩来的,新鲜得招人驻足。不过,车身横的直的并不一律,车栏板被掀下一面来,水果被认真码过,在车斗里堆成了小山坡。来摆摊的总是那几个人,摊位的顺序略有变化,但从未看见他们为了地盘争吵过,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契约,每个人都服从一种天经地义的铁律,如同小时候玩“老虎棒子鸡”的酒令游戏,耍赖不得。
卖小番茄的摊主,似乎每次都来得晚,只在最里面的位置——一棵主干粗短、枝丫歪斜的黄葛树下,将小斗车一斜,然后从驾驶室里牵出一根电线,用竹竿挑起一盏有喇叭形灯罩的灯泡,照着车上堆满的小番茄。小番茄很水灵,在猩红的灯光下,亮得像一颗颗血红的玛瑙。
这些摊贩一般不聊天,但又好像互相都熟识。没有生意的时候,有人会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几股白烟同时从鼻孔和嘴里喷出,然后咬在嘴角,如同褐色的土豆上兀地长出一支嫩芽。随后,对着隔壁的另一个水果摊主“嘿”一声,丢一支烟过去。那烟在空中翻了好几个筋斗,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伸出来的掌心上。“吧嗒,吧嗒”,两支烟开始隔空对话,冉冉升起的烟圈合在一处,好像也有了共同语言,它们愈来愈亲密,最终互相勾搭着,飘进高处茂密的黄葛树枝叶间。其他几个不吸烟的,则斜倚在水果摊一侧,一只脚笔直立地,另一只脚斜跨过去,脚尖点地,无聊之状让人想起乡下串门子的婶婆子。
其实,他们偶尔也会聊几句,但在这城市的声浪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卖小番茄的男子,高挑干瘦,不抽烟,也不搭话,一人一世界。没有生意的时候,他枯硬的双手显得有些多余,干脆右手抓住左手的腕子,老老实实箍在腹部。有时,他也会在摊位前后走动,但肥大的衣裤似乎跟不上节奏,总感觉有风在里面瞎搅和。
“多少钱一斤?”我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漫不经心问了一句。其实,我很少吃水果,这是一个很难更改的坏习惯。每次经过水果摊时,我都试图快点通过,但黄葛树的阴凉让我背心有些发虚,总感觉有焦灼的目光在背后穷追不舍。但这次不同,我没什么要紧事,凑上去,算是没事找事。高瘦男子从僵硬的姿态中活了过来,粗大的喉结动了动,没有搭话,只将头一扭,撸了撸嘴角,指向驾驶室位置的挡板处:“圣女果,18 元一斤”。字写在硬纸板上,并不端正,每一笔显然都返工过。
我并没有在意男子的不冷不热,装作认真的样子选了半袋,递给他。高瘦男子接过来,麻利地放在电子秤上,有一斤多。“滴滴滴”,不知何时,他手上多了一个计算器。他将计算器抓在手心,朝向我,液晶屏上显示22 元。
“就20 元呗!要得不?”不知哪来的兴致,我居然讨价还价起来。男子一惊,似乎毫无准备,慌得抬起枯瘦的双手一顿乱舞。
“嘿!他是个哑巴——”旁边卖香蕉的矮胖中年男人将烟屁股丢在地上,用脚尖狠狠地碾了几下,对我大喊道,隔着几米距离都能闻着呛人的烟味。
其实,我本没有真正打算还价的,只不过随口这么一说。就像乡间留客,将人送到门口了,还着重补一句“吃了饭再走呗!”刻意的客套里带着真假难辨的随意。
我最终如数付了款。那小番茄味道如何,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
2
桂花巷是有生意的。巷子的两侧门店不少,有做门窗的,有送水的,有修单车的,但现如今都关门了,台阶上淡淡的青苔和门上方颜色泛白的招牌,透出一种无以言说的颓废。
只有一家还在营业,但似乎并不赶时间,一般半晌午才打开卷帘门,哗啦啦的金属片一摩擦,聒噪得令人牙齿一阵松落。店内昏暗,并不开灯——其实是有灯的,不过是深紫色,有时是深蓝色。透过模糊的玻璃门,隐约可见里面有几张白色的床——有时怀疑是放倒靠背的沙发,屋子最里面的墙壁上供着一尊塑像,有几点殷红的灯火,一旁的招财猫不停地摆手,机械而生硬的动作让人觉得有些虚伪。时常,有个妇人会将胖胖的身子挤出来,无论春秋,都穿着花花绿绿的旗袍。头发蓬松地挽起,粉白的大脸上,点缀着一张抹得绯红的厚嘴。走几步,她腰上、腿上的肉开始四处晃动,旗袍的纽扣紧绷起来,总让人疑心随时会绷开。
店子没有招牌,具体是做什么生意的,不太清楚。曾经见过一个高瘦的中年男子,快速经过水果摊的时候,只马马虎虎瞟了一眼,然后猫着腰贴着墙根就闪进了卷帘门。他应该是这家店子的常客。妇人见他一来,脸上瞬间露出笑容,一瓣一瓣的赘肉重新排列组合,僵硬的麻花变成了精雕细琢的挑花。高瘦男人出来的时候,黄葛树下的阴影浓了许多,不过他精神上了头,一副很满足的样子,一直猫着的腰杆竟然挺直了,走路的步子均匀而沉稳,仿佛一头吃饱了归家的水牛,规规矩矩,不慌不忙。目送他的,是挂在虚掩门帘上妇人粉白的脸。
肯定有什么猫腻,我下意识地这么想。好多年前,我曾经在一些偏僻小巷子里见到过类似情形。门店大多以“按摩”“洗头”为名,玻璃门虚掩,屋内亮着或幽绿或暗红的霓虹灯,朦胧如冲洗胶片的暗室。几个妇人蜷缩在布沙发里,脸上厚厚的粉底堆出僵硬的干白。眉毛都是刻意修过的,很粗,很硬,像乡间收割稻子的镰刀。嘴上抹了口红自然不用说了,但过于夸张,无论嘴形如何,都一律涂成血红色。哪怕冬天,这些妇人总是短衣短袖,坐在“小太阳”旁,原本白兮兮的胳膊和大腿,被映出令人遐想的猩红色。我经过这些门店的时候,脚步总想快点离开,因为那些妇人会朝我诡异地使出眼色,像精准抛出来带着诱饵的锋利的钓钩。
这不合时宜。每次经过这个门店时,我都会经验十足地做出判断。一个阴雨天的下午,路上行人稀少,过往车辆心急火燎地驰过,轮胎在焦湿的地面发出极不耐烦的呲呲声。门店里出来一个人,打着花伞,但不是我见过的高瘦男子,而是那个老妇人。她侧身下了台阶,踮起脚尖蹚过积水,径直走向卖耙耙柑的水果摊。
“今天生意如何?”摊贩一边帮着挑选,一边问老妇人,从掐头去尾的问话中,可见他们已经很熟了。
“呃呃,马马虎虎。”老妇人应承着,说话的声音有些尖,正如这身打扮,与她的年龄有些出入,“老头还在工作,突然想吃耙耙柑了。”
过往的汽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对话被巨大的胎噪冲得七零八落。不过,我还是真切地听到了几个关键词:盲人,推背,松骨。
黄葛树上掉下来一串水滴,落在我的脑门上,冰凉的雨水里裹着猝不及防的灼热。
3
正儿八经地说,桂花巷其实是一个菜市场。
黄葛树的阴翳在尽头一曝光,右拐再左转,便是一处两百来米长的棚户菜市场。菜市里有各种新鲜菜蔬,还有鱼肉蛋豆腐类,间或有卖泡菜和炒货的。冬天有人灌香肠和卖腊肉,价格适中,现做现卖,关键是品质好,都靠口碑带货。周围几个小区的人,大多喜欢来这里买菜,有时没事也来逛逛,看看最近菜蔬上的行情变化。这里的小菜都是从附近农家进来的货,活鲜鲜还有农家田园里的气息。不过,我来这里买菜,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商家直道,要多少卖多少,绝不硬生生塞货。有时,还会主动问几个人吃,建议买多少合适。我老家卖肉的老叔就不厚道,说好砍一斤,结果加上搭头零碎,硬是变成了一斤半,然后脸上堆着横七竖八的笑,令人推脱不得,讨嫌。
其实,市场上的蔬菜都新鲜,买哪家的都一样,但买土鸡土鸭我就认一家。老板是个中年男子,干瘦,驼背,还有腿疾。他家的鸡鸭都是正宗散养的,摆在摊位上都有杂草的鲜腥和林木的硬朗。这不是吹嘘,而是经过很多人挑剔的口舌验证出来的。老板人很厚道,总是先问你想怎么吃,不同的吃法需要不同的肉质,否则嚼不烂,或者炒不熟,吃不到正宗的口味。无论是生客还是熟客,老板都要一边忙活一边仔细询问,宽大白皙的额头上总是泛着油光,骨感明显的腮帮子总支起朴素的笑意。买他家的鸡鸭,什么都不操心,清理绒毛、去除杂碎,剁块或者切丁,都在几分钟之内弄好。老板在给顾客交代做菜细节要点的同时,手里的活一点也不耽误,动作麻利得让人想起在课本里认识的那个卖油翁。很多时候,他家的生意忙不过来,而其他卖鸡鸭的摊子却门可罗雀,老板无奈,只好不停地抽烟,烧蚊香似的,还不时拿起棕帚狠狠地驱赶闻讯而来的苍蝇。
给他打下手的是一个中年女子,也是一副干瘦身板,微微驼背,不过没有腿疾。起初我以为二人是夫妻,但从脸型和一致上扬的眉毛来判断应该有血缘关系。老板说,这是他妹妹,在另一个菜市场卖土鸡土鸭,他这边忙不过来的时候,她就过来救急。这妹儿也是一脸津甜的笑,说话声音干脆响亮,像越过田野的南风吹响了一串悬空的铃铛。
我是善于观察的,但管不住嘴。我问过这女子,其他鸡鸭店也说是卖土鸡土鸭的,为什么他们的生意就没那么好。
“呵呵,也有生意的,有的。”女子说这话时,干净的脸上没有过多的情感暗示。她一抬手,将掉在额前的发丝撩向耳后,小指部位,只有一处空荡荡的钝疤。
有时我想,所谓幸运,便是上帝从他们那里拿走一些东西的同时,又慷慨回赠的那部分。
4
爱人总埋怨我不拘小节。其实,从几千里之外的乡下进城,我习惯了我的习惯,日常穿戴依旧一身土气,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人到中年,多了些油腻,那头发似乎有些嫌弃,悄无声息脱落一些。残留在四周的几撮,总是理不顺,稍稍长点,便东西南北乱了分寸,不成形。
我的脑壳是有问题的,小时候在老家,清溪洞的那个李师傅算是老手,无论男女老少,也不分什么头型,他的推剪都能摆弄得服服帖帖。但给我理发的时候,李师傅叼着的烟卷烧完了,都没琢磨明白咋回事。“鬼家伙的,你后脑勺上的反骨太突出了!”李师傅话里带着呛人的烟味,眉心兀地挤出一个“川”字,一笔一画很生硬,像是用钝刀刻出来的。每每想起这情形,我的头皮一紧,本就没有方向的头发更乱成了一团糟。
小区附近的街面上有几家理发店,装修豪华,单是那巨大的黑白条形灯箱,就转得人两眼发花。而且也太贵了,七八十甚至一百多,我这几撮油腻的中年毛发,不值得花高价打理。
去桂花巷,有时是我脑壳上稀疏的头发给出的理由。菜市场过去二十米,右拐,便是一条短短的美食街。其实这算不得是一条街,一边是六七层楼高的民居,一边是低矮的棚户门店。民居的一楼是商铺,烧烤鱿鱼丝、狼牙土豆、酸梅汤、酸辣粉丝、冒菜、铁板烧、臭豆腐、串串香、钵钵鸡,五花八门。生意好得不行,狭窄的过道上都歪歪斜斜摆满了桌椅。来这消受的大多是学生,或者附近商场上班的年轻人,一个个歪着脖子龇牙咧嘴,吃相有些失控,想必那味道是入了神的。我是不敢吃的,怕肠胃受不了。爱人跟我开玩笑说,楼上的住户天天烟熏火燎的,家里的饭菜都吃不出香味了。
街巷的另一边,大多是水果摊、干杂店,还有一家药店,理发店淹没在杂七杂八的招牌中。跨上两级台阶,推开老旧的玻璃门,紧贴在墙面上的长方形镜子里映出街对面一群低头吃食的人,也将自己的身形收纳了一半进去。这里没有浓烈的烧烤味,倒是有馥郁的洗发水味围合而来,给人一种微弱的温暖感。大多时候,理发店里生意断断续续,并不紧张。一个衣着素朴但找不出更多特征的年轻姑娘,有时,她坐在一张残破的沙发上,一台不大的老式电视机嗡嗡嗡地放着节目;有时,她干脆斜靠在门边,看街对面的青年男女你一口我一口亲昵地吃着钵钵鸡。我来的时候,她仿佛被激活了一般,慌忙招呼,清泠的语气从洁白的口齿中吐露出来,如同夏日深山里游离出来的风。
先洗头。小姑娘将一块干燥的旧毛巾塞进我的脖颈,让我平躺下来。水龙头打开,耳边沙沙水响,似秋夜里悄然落下的细雨,又如山涧里只闻其声的溪流。闭目间,十个纤细的手指由轻到重,由点到面,仿佛老家门前大片稻田上拂过的一阵南风。手指揉过头顶的时候,抹在头发上的洗发水开始发酵,一切变得柔和起来,指法有些杂乱但又不失章法。当润滑的指心挪到耳后根的时候,一阵酥麻遍布全身,每根经络都开始跳动,感觉人立马登上泰山之巅,眼前云雾缭绕,转而尽是旭日光辉。
小姑娘理发,轻车熟路,前后左右移动,步履如莲。她用的是电动推剪,嗡嗡嗡,震得耳膜有些发蒙。整个过程倒是很享受,白嫩的胳膊不时在眼前晃过,淡淡的体香洇进呼吸,让人陶醉得有些恹恹然。闲聊中,得知小姑娘老家是乡下的,技校毕业,正儿八经学过理发。不过,这家理发店是别人的,她只是来打工的。
“开一家理发店要十几二十万呢!”我曾经建议她独立门户,她听了惊呼起来,原本干净的声音变得尖锐,如同砸碎了一块玻璃。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从她的那一声惊呼里,我感觉到了一种遥不可及却又不甘放弃的信念。
“先扎实打几年工,等有钱了,再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这样才可以在城里立足。”从墙上立着的镜子里,我清晰地看到姑娘的眼睛里全是光,额头上有几绺青丝垂下,她用衣袖擦了擦,红唇皓齿里又泻出一股和煦的春风。
我喜欢这种笃定和乐观,从不在任何事上无休止地纠结,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在头发这件事上,我无可奈何,因为脱发,脑顶上已经凸显油光的头皮了。待我再次去理发时,理发店还是老样子,不过那位姑娘已经不在了。
我有些纳闷,那位姑娘是否还在筹划自己的城市梦想,抑或改弦易辙找到了新的位置,不得而知。
5
桂花巷的尽头,紧挨着大学路。
大学路四车道,车流匆匆,往来如鲫。而靠桂花巷的一侧,店铺林立,蛋糕店、米粉店、小吃店、干杂店、奶茶店,还有时尚鞋店、包包店,彩球红缨飘舞,似乎每天都有新品,引得过客时常驻足,生意差不到哪里去。不过,人们更多是奔着不远处的超市去的,那里的冬天和夏天有免费的空调,还有养眼的都市男女。对大多数人而言,大学路悠长的过道,不过是顺带的眼底风景。
说实话,我喜欢这座城市的原因之一,是这里的冬天并不难过,不太冷,也很少有风,微寒里透着静心的余暖。我从千里之外来到此地,起初并不习惯这里的阴霾,阳光似乎忘记了这个地方,抑或懒得费劲拨开厚厚的云层,尤其是在冬天。但这里的人很阳光,对谁都一腔热诚,嘘寒问暖无微不至。例如问路,无论大妈、大叔,还是年轻男女,都会停下来认真地细说路线的细节,若还是一脸茫然,他们急促的语气里会带着比当事人还揪心的焦急。
今年初春的一个傍晚,我从桂花巷溜达到大学路口。一拐弯,竟撞上一股莫名的北风。这风虽然不大,但有些力度,连路边光秃秃的白杨树都有些意外,试图控制颤抖的枝丫,终究无力回天,只好硬扛着。路上行人比往日少一点点,还算正常。不过一个个紧裹衣襟,缩着脖子,局促的步子里也夹着北风。
在米粉店的门口,一个黑褐色身影蹲在地上,在川流的人群中,仿佛一块被丢弃的顽石。洁净的水泥地砖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鞋垫,并不齐整。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一身深色葛布衣服,古旧的连襟式,一顶毛线圆帽紧紧箍在小小的脑袋上,有几缕稀疏的头发从严实的帽子里钻出,却是出人意料的青黑。老妇人的穿着有些臃肿,衣服裹了几层,将瘦弱的身子护在最里面,俨然一株冬寒天的包心白菜。微冷的北风里,没有人停下来,老妇人执着地守着自己的小摊,凝固如雕像一般。
“鞋垫怎么买?”我拢了拢衣服,蹲下来。我的光顾似乎激活了一个枯萎的灵魂,这时我才看清了那张模糊的脸,枯瘦,干瘪,褐色,两个眼窝深深陷入岁月的褶皱中。
她似乎没有听清我的话,身子动了动,将两只尖尖的小脚往里一收,倾向前来,凹进去的嘴唇动了动,嘟囔了一声,我也没听清说了什么。于是,我改用当地方言尝试着又问了一遍。
其实,我的鞋垫很多,根本不用买,只是看这老妇人在这微寒的风里,动了恻隐之心。
鞋垫20 元一双,不论大小。简单的信息是老妇人用晦涩的语言和复杂的手势传达出来的。说实在话,着实有些贵,而且这鞋垫做得不很规则,针线扎实,但与那些机器缝制的鞋垫相比,毫无美感可言。
“手工很扎实。”身边突然多了一个中年妇女,有些肥胖,蹲下来时所有的赘肉在腰部挤成厚厚的一圈,隔了几层厚衣都掩饰不住。
老妇人没有继续说话,只平静地盯着我和那个胖女人,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任何内容。北风还在胡乱吹,似乎钻进了我的胸膛里。我疑惑地盯了胖女人两眼,突然决定买两双。
“扫微信吧。”我立马掏出手机。
“没得手机哦,要现金。”老人干瘪的嘴唇咂了咂,拉成了一条尴尬的线。
“现在谁还带现金啊,都是手机支付了。”我像在说给老妇人听,又像在借北风的势,询问旁人。蹲在一旁的胖女人没有走的意思,似乎在等待一个不知怎么收场的故事结局。
“我也没得现金。”胖女人站立起来,轻声说了一句,肥厚的双层下巴跟着微微颤动。不知什么缘故,我竟认真起来,于是决定到旁边的米粉店去兑换现金。
“都是在线支付,一点点现金都拿走了,店子都快打烊了。”我才发现,外面天色暗了下来,街边的路灯早已亮起,将城市昼夜的界限抹得分不清彼此。
路上行人寥寥,我打算往回走。身后的北风愈发无聊,围着老妇人轻描淡写转了一圈,又溜走了。
第二天,我备了些零钱,晚些时候专程去那里,老妇人却没有来。她昨日蹲过的地方,依旧是洁净的水泥方砖,不过当天并没有北风。
后来,身上备点零钱竟然成了我的习惯。其实,我早已不知不觉中丢掉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渐渐熟悉了这座城市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