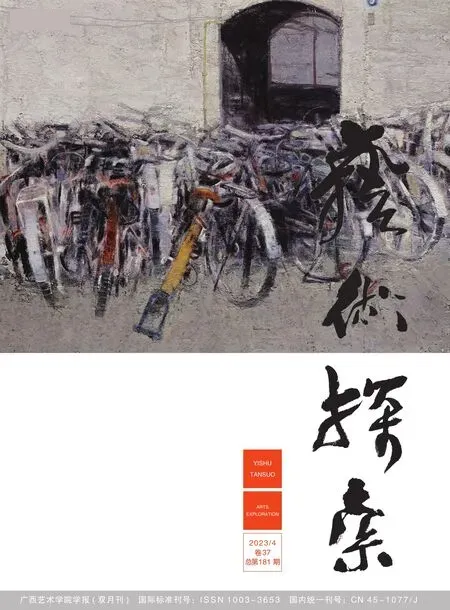论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馆”概念的生成
2023-12-16徐丹丹
徐丹丹
(湖北美术学院 艺术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在欧美学界的认知与实践中,博物馆(museum)起源于缪斯神庙,在藏品研究的基础上发挥教育等各种功能,美术馆(art museum)则是博物馆的类型之一。纵观我国,在学术研究层面,美术馆也多被纳入博物馆的理论体系中,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美术馆与博物馆却隶属于不同的管理系统,具有不同的功能与定位,在公众视野中面貌迥异。这种现状的历史成因是什么?与博物馆相比,我国的美术馆为何被普遍认为社会基础薄弱?当下的美术馆又如何知往鉴今?
一、“美术馆”两种不同维度的认知与实践
(一)对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的初步认知
19 世纪中晚期,在晚清知识分子的游记中,欧美各国博物馆的形象多以猎奇的口吻被勾勒出来。此时汉语词汇系统中并未出现“艺术品”“美术”这些词,于是收藏“今人认知中艺术品”的博物馆,在当时被置于中国传统博物学的框架下,意译为时人更易理解的“博古院”①林鍼《西海纪游草》:“博古院明灯幻影,彩焕云霄”,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 年,第36 页;郭连城《西游笔略》:“午前游天台院侧之博古院。院中多有奇怪邪神像之上古名人之宝石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第92 页。、“古玩库”②徐继畲《瀛寰志略》:“内有学署、医院、观星台、军工厂、古玩库”,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第217 页。、“博览院”③郭连城《西游笔略》:“博览院乃本国国王所建,宽大不知几何,院内满列古奇之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第68 页。等。1841 年林则徐的《四洲志》,较早开始出现“博物馆”的称谓。可见,中国人是在博物馆的范畴中初识美术馆(art museum)的。在时人的描述中,博物馆凸显出两点特征:其一,收藏品种类繁多(包括古玩);其二,对公众开放。
因此,在19 世纪下半叶,西方近代文明的重要产物博物馆,在中国仅是极少数知识分子初识的对象,和民众基本不发生关联,其因物品丰富、对公众开放、辅助于教学等特征,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视野中开启民智的重要途径,教育也就成为中国人随后自主兴建博物馆的首要目的。作为收藏各类艺术作品并发挥社会美育功能的美术馆(art museum),因无对应词语,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中并无独立性,而被笼统地纳入博物馆的范畴中。
这一时期,艺术博物馆不是经世致用的首选,也无相应的公共藏品等基础,因此绝非中国社会创立博物馆的首选类别,但是古玩古物成为博物馆收藏的一部分,却在时人对博物馆认知的过程中成为理所应当之事。这种认知伴随博物馆的发展不断延续下来,形成了考古发掘与博物馆建设的密切关联。包括美术文物、书画在内的古玩古物已多进入博物馆系统的现实,也成为较晚起步的美术馆(art museum)只能从零开始进行同时代作品的积累,藏品体系普遍薄弱的历史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西方获取了在中国传教的特权。从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各国教会出于各种目的,在中国境内创办或与国人合办了中国历史上首批博物馆。但是这些教会性质突出的博物馆多依附于教会学校,其成立目标主要包括:一,搜集自然资料及信息开展研究,作为传教的工具;二,辅助教会学校的教学。因此这些博物馆多为自然科学类,以及少数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文物类、医学类等,没有专门的美术类别,且基本不对中国民众开放。
(二) “美术馆”概念的引入与认同
晚清知识分子在初识西方博物馆的同时,也首次见到了现代文明的产物博览会。王韬在《漫游随录》(1867—1868 年)中称悬挂画作的展览会为“画会”,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称1876 年美国费城博览会中陈列各类绘画雕塑作品的展馆为“绘画石刻院”,黎庶昌1878 年在《西洋杂志》中记载源自1867 年巴黎世博会的美术展馆为“巴黎油画院”,这些不同称谓初步奠定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认知中美术与展览的紧密关联性。但是汉语词汇中始终没有自发演化出“美术”“美术馆”等词,这些概念在中国出现并呈现出本土化的解读,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的“博览会计划”有着直接的关系。
自1877 年日本政府主办第一届“内国劝业博览会”开始,以展示美术品为主的建筑物美术馆就出现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美术馆的定位——其中的展品并不是古代作品,而是当时新近创作的美术作品。[1]75随后至1903 年,日本又陆续举办了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每次都会搭建一个临时建筑作为美术馆。美术馆在这一时期的日本并非博物馆设施,而是博览会上展示公开招募到的同时代作品的临时建筑,并无收藏品与仓库。[2]53-55这一时期是中国对于日本考察的高峰期,由于汉字文化圈词汇的相通性,至20 世纪初,“美术”“美术馆”这些“和制汉词”在时人对日本博览会的报道与描述中已较为常见。④其中较早如日本大阪“第五回内国劝业博览会”的《美术馆观览章程》,《杭州白话报》1903 年第2 卷第12 期,第2 页。因此,中国人初识“美术馆”这个词语是直接经由日本的商业博览会,这也就奠定了时人对美术馆即为博览会上展示美术品的临时展馆的直观认知。
(三)美术馆成为展览馆的时代需求与实践
20 世纪初,出于振兴实业、开通民智的目的,成都、天津、武汉等地率先举办了一些博览会,并效仿日本称之为“劝业会”。因美术与实业的密切关联,其中多设置美术展区。在此基础上,中国第一所美术馆于1910 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出现。这所美术馆“建筑仿罗马式,架铁梁为二层楼,馆内陈列分五门,曰绘画,曰雕塑,曰铸塑,曰工艺,曰手工,后增一门曰古美术,共计物品二千五百一十七件”[3]73。从形式上来看,这是对于欧美及日本博览会制度的仿效,从内容上来讲,美术在当时中国因包含设计、工艺等各门类,被视作与科学一样的新学,对社会生产起到推动作用,所以也被纳入以振兴实业为目标的劝业会。
20 世纪初,在少数知识分子的认知中,博览会、博物馆和实业之间已经形成牢不可破的纽带,博物馆即为“常设博览会”,成为鼓吹工业文明的重要社会文化机构。[4]51同理,美术馆即为常设美术展览会。这种观念伴随之后的博览会实践,在公众的认知中得到了普及。
周波(1984-),男,硕士,高级咨询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教育的法律问题及适用、企业思维下的学生管理方法研究。E-mail:48605299@qq.com
1912 年后,国民政府在此前的基础上更为积极地参与及筹备各类博览会,如农商部针对1914 年“日本东京大正博览会”成立了调查团,并专门出版了《东京大正博览会调查书》;1915 年参加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些博览会都专设有美术馆,即展示并出售美术作品的临时场馆,为美术馆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至1937 年,中国共举办了250 余次国货展览会。[5]69-83基于美术与工艺的密切关联,美术部门或者独立的美术馆也多成为这些国货展览会上的必然构成。如1928 年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国货展“中华国货展览会”中设“艺术与欣赏品”类别;[6]83-881929 年“无锡国货展览会”中设有“艺术陈列馆”“博物馆”。[7]90-97从1910 年至1937 年,由于劝业会、国货展览会在民众中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在当时中国社会的认知中,美术馆必然会和“临时展览”“商业性”“实用性”这些概念联系到一起,这也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美术馆建设带来一系列后续影响。
“美术馆”一词的引入,虽是用来描述商业博览会上的临时展馆,但其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一直伴随着“美术”概念的生成、新式教育的推广与博物馆的发展。相关知识分子对于美术展览的需求愈加迫切,但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将书画等作品公开展示的需求,并无美术展览的适宜场所,因此在东西方文明碰撞交融的背景下,源自博览会的美术馆在实践中逐步成为美术展览馆。
至此,起源于缪斯神庙、作为艺术博物馆的美术馆(art museum),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在“美术馆”概念在中国普及的过程中,多与博览会上的临时美术展馆杂糅在一起,共享了“美术馆”这个称谓。虽然两者性质完全不同,但对于当时急于学习借鉴西方文明成果的中国社会而言,更重要的是怎样将这些看起来功能相似的对象为我所用,而非研究其差异性。“美术馆”在汉语词汇系统中逐步出现并被含混使用,其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收藏展示各类美术作品的艺术博物馆;二,博览会上展示新近创作美术作品的展馆,“美术”也由此带上了新近创作作品的含义,与古玩拉开了距离。而在实践层面,相比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建设而言,美术展览馆明显更易建设,因此也更易在认知中得到强化。这种概念的含混与认知的偏差也为后期中国美术馆独立于博物馆埋下了伏笔。
二、美术馆成为美术教育展览馆的社会现实
(一)美术馆分离于博物馆的行政面貌
虽然中国美术馆最早出现于商业性质的博览会,在20 世纪初期更凸显出经世致用的展览馆功能,但在同时期知识分子对欧美博物馆认知深化的推动下,美术馆作为文化机构在官方行政上已经成为社会教育事业的构成部分。1912 年,在蔡元培等人的力推下,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美术馆与博物馆同属社会教育司的执掌范围。可以看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社会文化机构的博物馆与美术馆在中国诞生之初直接指向了教育功能,这与欧美近代博物馆作为国家文化象征的生长语境完全不同。此时的中国社会,美术馆作为博览会的展览馆刚刚出现,并无作为独立社会教育机构的美术馆建设,而中国自主筹建的博物馆也仅有南通博物苑、国立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等寥寥几个。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关条令中美术馆与美术展览会被归为一类,而博物馆则与图书馆并置为一类。[8]450这种分离反映了官方对于现实情况的认识:美术馆脱胎于商业博览会,与美展关系密切,而博物馆的核心是蕴含知识的藏品,类似于图书馆和图书——如此分类便于管理。1931 年《教育部关于全国社会教育设施概况报告》中将博物馆列为“偏于知的社会教育事业”,将美术馆列为“偏于情及德的社会教育事业”。[9]71520 世纪30 年代社会教育司涉及美术馆与博物馆的条令中,均将二者分别列出。⑤如《教育部修正各司分科规程》,《教育部公报》1932 年第4 卷第5 期 ,第15-21 页;1933 年《修正教育部组织法》,《大公报(天津)》1933 年4 月15 日第3 版。虽然这一时期不论博物馆还是美术馆的发展都举步维艰,许多计划只能停留在设想中而无法实施,但是这些文件一方面显示出同时期美术馆的藏品匮乏以及与展览的共生关系,另一方面从官方管理的角度反映并深化了实际操作维度上美术馆与博物馆的不同功能,明确了二者不同的发展方向。
基于此,经历了20 世纪30 年代近代博物馆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后,在30 年代末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于各类社会教育机构的统计中,“古物保存所”“博物馆”与“美术馆”分列为三种类别:古物保存所包括古物保管委员会、支分会等;博物馆包括革命纪念馆、历史博物馆及卫生陈列所等;美术馆包括各种书画会等。⑥《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度(1933 年)全国社会教育统计》,教育部统计室编,商务印书馆,1936 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度(1934 年)全国社会教育统计》,教育部统计室编,商务印书馆,1939 年。这种分类也是美术馆展览性质及与博物馆差异的现实写照。从现存资料来看,1933 至1934 年,全国范围内美术馆、博物馆与古物保存所,数量在“社教机构”类别中都排名最末,总占比不足0.3%。在年度支出经费中,三者的经费额度总占比不足1%,也远低于数量最大的“娱乐场剧场及电影院”。⑦1933 年,全国范围内美术馆53 所,在社会教育机关中占比0.05%,岁出经费17 937 元,占比0.1%;博物馆68 所,占比0.07%,岁出经费120 175 元,占比0.59%;古物保存所118 所,占比0.12%,岁出经费11 537 元,占比0.07%;娱乐场、剧场及电影院岁出经费5 438 731 元。1934 年,全国范围内美术馆55 所,在社会教育机关中占比0.06%,岁出经费6 051 元;占比0.04%;博物馆74 所,占比0.08%,岁出经费139 615 元,占比0.89%;古物保存所121 所,占比0.12%,岁出经费9 700 元,占比0.06%;娱乐场剧场及电影院岁出经费3 978 504 元。《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度(1933 年)全国社会教育统计》《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度(1934 年)全国社会教育统计》。从1928 年中国第一所美术馆建立至1946 年,中国的博物馆与美术馆基本呈现出并进的发展势头,甚至在某些年份,美术馆的发展一度超越了博物馆。但是从统计数据来看,二者在这个时间段内都并非良性发展,无论机构数量、职员人数还是经费规模,都没有呈现连贯一致性,相关数据在常相邻的年份间大起大落,变化突然。[10]236-240可以看出,虽然博物馆起步更早,但无论是美术馆、博物馆,还是后期被纳入博物馆系统中的古物保存所,彼时都是筚路蓝缕,在民众生活和官方规划中占比很小。因此在相关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认知中,“美术馆”等概念并无清晰的界定与解读——这也就成为美术展览会、美术馆、博物馆等在这一时期发生功能重叠的背景。
(二)美术馆展览及教育属性的强化
20 世纪上半叶,在深受西方艺术沙龙和画展影响的留学生的引领下,中国社会也开始自主发展出独立的专业美术展览,一些在全国美术界具有相对影响力的专业美展形成了兼具商业、教育、文化、娱乐等性质的独特面貌,与作为艺术博物馆的美术馆出现了部分功能的重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29 年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以下简称“全国美展”)。刘海粟等人自20 年代初就倡议举办全国美术展览会,认为“此审美教育上大障碍,是以救药此种弊病者,厥有待于展览会”[11]185-187。在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缺席的年代,刘海粟等人认为美术博览会与之拥有相似的教育功能,那么全国美术展览会兼具美术馆的教育功能、作为国家美术文化的象征也就顺理成章了。
此次全国美展除了陈列当代名品外,还展示江浙沪地区私人收藏家的古代藏品,并逐日更换。组织专题展览如“扇面大展”“最精品联合大展览”,并安排了国乐等演出活动。展览第八日免收门票,并基于“提倡美术宣传”的目的,将刊物《美展》按成本出售。这种临时展览的更换、公共教育活动的举办、娱乐休闲设施的提供,与后世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同时,此次美展又沿袭了博览会的商业销售或经济推广性质——博览会与美术馆的功能重叠。[12]625-683美展结束后,杭州西湖博览会筹办方直接面向全国美展征集参赛作品,用以在同年筹办的“西湖博览会”的艺术馆中展示。画家、教育家王济远甚至指出:“全国美术展览会,是中华民国的西湖博览会的艺术馆,也是中华民国的两个盛会,是二而一,一而二的。”[13]5-6
至20 世纪30 年代,在社会教育司的引导下,伴随着美术认知上从技至艺的转变,从博览会发展而来的美术馆在功能上也从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逐渐和教育普及、民族发展等国家身份的塑造联系到一起。但这些功能在这一时期更多是通过美术展览的方式呈现,如1927 年北京艺术大会、1929 年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1933 年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1934 年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1935 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等。这些虽是美术展览,并且由于时代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兼具商业性,但是从展览的筹备、执行到影响方面,都具备了博物馆的教育性、公益性等特征。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实践中,美术馆与展览的关系非常紧密,美术馆被等同于美术展览馆或美术陈列馆,这直接影响了同时期美术馆概念的生成。如1929 年俞剑华对于全国美展转化为“美展馆”的期待:“开幕以后如能即行筹备改为永久机关,以备每年开会一次,则凡此次所筹备不到,及一切计划不周之处,皆可逐渐详密”[14]3。1936 年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座国家美术馆即名为“国立美术陈列馆”,展览功能尤其凸显。
三、“美术馆属于博物馆”的学术观念与窘迫的现实
(一)“美术馆属于博物馆”观念的形成
在美术馆的“美术教育展览馆”现实面貌愈加凸显之际,从20 世纪初至30 年代,学术界却逐步形成了“美术馆是艺术博物馆”的主流观念。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相关学者筹建艺术博物馆的理想。自19 世纪下半叶,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了起源于缪斯神庙的博物馆及作为其重要类别的美术馆(Art museum)。彼时,虽没有对应的汉语词语对其进行描述,但是中国社会对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的探索从未停止,即便最早的美术馆受日本直接影响脱胎于商业博览会,并形成了美术展览馆的现实面貌。伴随着20 世纪相关学者对欧美博物馆理解的不断深化,美术馆不仅是筹备临时展览的场所,更应该是拥有丰富藏品的艺术博物馆这种观点开始明晰。中国近代的美术家、教育家都已经在美术与实业紧密联系的表象之下,更深层次地认识到美术馆在保存民粹、启蒙民智、怡悦性情乃至树立民族形象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满足于美术馆仅承担临时展览场馆的功能,而在其功能性质、藏品积累、制度建设及场馆硬件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如鲁迅⑧鲁迅认为:“美术馆当就政府所在地,立中央美术馆,为光复纪念,次更及诸地方……所列物品,为中国旧时国有之美术品”,同时指出:“美术展览会陈列私人收藏,或美术家新造之品”。《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 卷第1 期,教育部编纂处编辑并发行,1913,第1-5 页。、蔡元培⑨蔡元培1922 年写道:“美术馆,搜罗各种美术品,分类陈列。于一类中,又可依时代为次……每日定时开馆。能不收入门券费最善,必不得已,每星期日或节日必须免费”,但同时也提出:“历史博物馆,所收藏大半是美术品,可以看出美术进化的痕迹;古物学陈列所,所收藏的大半是古代的美术品,可以考见美术的起源”。《美育实施的方法》,首次发表于《教育杂志》1922 第14 卷第6 号, 载《蔡元培选集》(第四卷),中华书局, 1984 年,第211-216 页。、徐悲鸿⑩徐悲鸿1918 年从开启民智的角度提出“设博物美术等院于通都大邑”,《评文华殿所藏书画》,载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 年, 第1 页。1932 年他又提出“国家唯一奖励美术之道,乃设立美术馆”,并提出具体做法:“每一国立大学或图书馆,至少每年应以五百金购买国中诗家、画家、书家作品或手迹;视为重要文献,而先后陈列之”。《中国今日急需提倡之美术》,《徐悲鸿文集》,第53 页。、刘海粟[15]187-188、李毅士⑪李毅士1928 年提出:“政府应建设国家美术馆”;“各省各大都市,应酌量筹建地方美术馆”;“征求国内私人收藏之美术品,借以陈列于美术馆中,供众观摩”。《为供给艺术教育上重要之参考资料起见应请各地当局速在各大都市中建立美术馆之基础案》,《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年,第573-574 页。、颜文樑[16]14-18、林风眠⑫林风眠1932 年指出美术馆“以保存历代美术品为职志”,具有“直接影响于良善的品性的教育方法”。《美术馆之功用》,原载天津美术馆馆刊《美术丛刊》1932 年第2 期,见《美术观察》2000 年第4 期,第6 页。、傅抱石⑬1935 年傅抱石思考当时的美术危机,认为:“国家所有的古美术品,由美术馆统一收藏起来……分令各省市速筹设省市立美术馆,把各省的古美术品加以搜集、保存,平日开放人人阅览。”《中华民族美术之展望与建设》,叶宗镐、万新华选编《傅抱石论艺》,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 年,第13 页。等,这些学者在美术馆作为常驻机构、保存国家美术古物、对公众开放等方面观点基本一致。
其二,博物馆早于美术馆建设、行使美术馆职能的现实。20 世纪30 年代初,中国多地都建设了博物馆。1935 年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次年全国博物馆数量共计62 所,其中包含美术馆三所,分别是苏州美术馆、天津市立美术馆、国立美术陈列馆。自19 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初识欧美博物馆,博物馆保存并展示古玩、书画等美术品的做法已经被相关学者接受并认同。因此在美术馆(art museum)缺席的年代,从1905 年张謇建设南通博物苑伊始,率先出现的博物馆已经将中国留存的古美术品收纳入自己的美术部门,行使了美术馆的职能。再加上同时期苏联和日本博物馆研究的影响,中国20 世纪30 年代相关博物馆学术研究和统计都将美术馆纳入博物馆系统中,美术馆成为博物馆的子系统。⑭相关研究与统计如马宗荣《现代社会教育泛论》,世界书局,1934 年;中国博物馆协会汇编《中国博物馆一览》,中国博物馆协会刊行,1936 年;陈端志《博物馆学通论》,上海市博物馆刊行,1936 年;费畊雨、费鸿年《博物馆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
基于学者们的美术馆理想及中国博物馆建设的实际情况,至20 世纪30 年代,“美术馆属于博物馆”的学术观念逐步形成。这种观念的明确性与美术教育展览馆的现实面貌形成鲜明对比:如蔡元培、鲁迅担任社会教育部门管理者之际,明确指出美术馆的博物馆性质,但是面对的却是社会教育司掌管下博物馆与美术馆分类管理、美术馆与美术展览会并置的现实。
(二)现实层面难以实现的“艺术博物馆”理想
虽然在学术层面,美术馆从属于博物馆系统的观念已经非常明确,但是学者们从零开始进行艺术博物馆的建设却非常艰难。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对于艺术博物馆理想的实践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辅助新式美术教学,依附于学校,在小范围内展开学校美术馆的探索。1917 年周湘创办中华美术专门学校,次年在其中设立古物保存馆⑮学校制定《中华美术学校古物保存馆简章》,并在《古物保存馆试办缘起》中阐述:“一般任人参观,一般永不变卖,又拟简章数条,以为扩张之备”。从中可以看出,古物保存馆力图形成相对固定的美术陈列,可以看作美术学校下设美术馆的先行者。《古物保存馆试办缘起》,原载《中华美术报》1918 年10 月20 日第8 号,今见李万万《美术馆的历史》,江西美术出版社,2016 年,第137-138 页。,已经萌生出艺术博物馆的意识,但馆内古物的珍稀程度与数量有限,且伴随办学的结束很快散佚,影响有限。刘海粟等人成立的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 年改名为上海美专)于1933 年筹建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⑯“筹建新校舍及美术馆,成立筹建委员会,学校整饬刷新校务获当时教育部的嘉许,自始每年拨给补助费,用以充实设备等项。”陈瑞林《20 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86 页。同样未能如愿。这类探索中仅有依附于苏州美专的苏州美术馆具备博物馆性质,并最终落成。第二个层面,在社会范围内进行公立美术馆的筹建。虽然伴随学界对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认知的深化,1928 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在各大都市中建立美术馆之基础案》,湖南、广东、河南等地都进行了公立美术馆的筹建,但多止步于纸本层面。1936 年国立美术陈列馆落成,是为专业美术展览机构。但其在举办过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1937 年)之后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并未留下藏品记录。仅有1930 年成立的天津市立美术馆具备博物馆性质且成功落成。
1928 年,颜文樑等人在苏州画赛会的基础上,依托于苏州美专筹建苏州美术馆。苏州美术馆既与苏州美专的教学相结合,也与各美术社团合作举办展览。苏州美术馆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固定的馆舍和较为稳定的资金投入,有不断充实的藏品及图书,已经是按照博物馆的标准进行筹建。⑰美术馆自馆长之下设有秘书室,下分事务、编选和印售三个部分,经费来自其发售的印刷品、各种美术品及私人捐助等,年收入约17 000 元。至1936 年,苏州美术馆有模型陈列室三间(模型537 件),中西画件及印刷品陈列室六间(画件及印刷品1 438 件),图书室藏书17 628 册。出版刊物《沧浪美》《三日画报》《艺浪》三本。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博物馆一览》,中国博物馆协会发行,1936 年,第73-74 页。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虽无法与后期的公立美术馆相提并论,但已经是同时期私立学校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但苏州美术馆很快在1937 年后因战事失去了美术馆的功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从20 世纪初至30 年代末,伴随各类美术学校发展起来的保存馆、陈列馆等,只有苏州美专苏州美术馆成功建设并具有博物馆性质,其余美术院校(包括综合性院校中的美术系)只是配备有为辅助教学而积累教具与藏品的美术陈列馆,重在对美术品或复制品的临摹。
天津市立美术馆作为公立美术馆,拥有新建馆舍和完整的组织架构,由天津市政府按月拨付专项经费,设置有建筑、石刻、图画、雕塑、西画陈列室,并有专门出版物《美术丛刊》。[17]53-54天津市立美术馆于1930 年成立“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天津支会”,聘请专业学者持续进行古物及艺术品的搜集。1930 至1932 年,美术馆藏品达几千件,除政府专项经费购买外,多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为进一步征集藏品,天津市立美术馆于1931 年成立“驻北平办事处”。在固定陈列之外,天津美术馆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美术展览会,开设短期美术研究班,并在《美术丛刊》之外筹备《美术》《民教月刊》等。美术展览会、研究班、期刊等活动在30 年代初期较为活跃,随后因资金短缺锐减。即使如此,在艰难的条件下美术馆依旧于1940 年出版《天津特别市立美术馆概况》,对建馆十年的工作进行系统总结,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1]302-313
结合各地未果的美术馆规划及仅有的苏州美术馆、天津市立美术馆的成功案例,可以总结出这两所美术馆成功筹建的原因。
首先,官方的大力支持。苏州美术馆虽为私立,但其建设得到了吴县国民政府的支持,地方各行政机构均有代表出席1928 年美术馆开幕典礼。天津市立美术馆更是得到了天津市市长的大力支持,美术馆直属天津市教育局,开办费和每月经费由市政府专款拨付。这与1931 年中国画会参照天津市立美术馆呈请北平市政府设立北平市立美术馆,但遭遇政府各部门因经费等问题含糊批复而最终未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326-328
其次,丰富的社会资源。苏州美术馆在苏州美术会的基础上依托于苏州美专筹建,苏州美术会由绘画、雕刻、音乐、诗歌、刺绣和演讲部门构成,拥有数百名会员,具备例会制度,出版美术期刊,而苏州美专也具备同时期出色的美术家和教育者。苏州美术会和苏州美专为苏州美术馆设置相对完整的组织机构、丰富自筹经费的渠道、筹办美术出版物、举办美术展览等奠定了资源基础。苏州美术馆这种将美术会、学校与美术馆紧密融合的独特办馆方式,在同时期很难被成功复制。天津市立美术馆的筹建者严智开出身望族,其父严范孙为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其兄严智怡曾创办天津博物馆并担任馆长。严智开任职天津市立美术馆同时,曾被教育部任命为北平艺专校长,同时身为中国博物馆协会执行委员。开创者的社会资源是天津市立美术馆获取官方支持、设立办事处、聚集专业人才、争取藏品捐赠、举办各类美术展览会等必不可少的前提。
第三,专业的学识与广阔的视野。苏州美术馆馆长颜文樑在我国最早举办全国性定期美术展览会(苏州画赛会),后创立苏州美专并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天津市立美术馆创建者严智开则先后就读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法国巴黎美术学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于美术的深厚积淀、对于西方美术馆制度的学习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使得他们具备广阔的视野和开拓创新的实务能力。
这三点同时也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筹建美术馆(art museum)的必需条件。但是在各类美术古物多进入博物馆美术部门或古物陈列所进行保存,美术馆和博物馆在社教机构中占比极小的背景下,建设美术馆的难度可想而知。对此部分学者也有清醒的认识,刘海粟论及此前美术馆建设未能实现的原因,指出宏观环境是“政府未及注意,民间力有不逮”,具体建设方面则是“或因经费欠缺,或因涉及范围广泛,莫由统一”。[15]187-188缦郎论及湖南美术馆建设之难处,也谈到经费、藏品、隶属部门的支持等各项基本保障的欠缺。[18]1-14
这一时期学界在博物馆学的研究框架下对美术馆进行理论建构,与实践层面的展览美术馆的现实情况有着极大的区别。在1934 年的统计中,全国范围内美术馆数量55 所,但据目前资料来看,仅有苏州美术馆和天津市立美术馆通过机构制定的收藏制度明确了其博物馆而并非展览馆的属性,其余的美术馆并未激起水花,社会影响力较小,故应是作为美术展览馆的短暂存在。1936 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的统计已将美术馆纳入博物馆的范畴,但62 所博物馆机构中,冠以“美术馆”名称的仅有苏州美术馆、天津市立美术馆及刚刚成立的国立美术陈列馆3 所。
结语
自19 世纪下半叶至20 世纪初,在“美术馆”这个词舶来之前,中国社会就已经接触到了源自缪斯神庙的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也同步认识了商业博览会的临时展馆美术馆。这使得我国的美术馆自词语引入伊始就兼具了以上双重含义,相关学者从这两个认知维度进行的实践探索,交织勾勒出了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馆的现实面貌与概念的生成过程。
在经世致用的社会浪潮下,受日本商品博览会的直接影响,中国早期美术馆逐步强化了其作为展览馆的概念,并由于现实需求进一步凸显了展览的功能,在20 世纪30 年代的官方条令中与美术展览会归于一类,明确了其“偏于情及德的社会教育事业”的属性,于实践层面走上了与博物馆不同的发展道路,成为美术教育展览馆。与此同时,20 世纪初至30 年代,由于相关学者对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建设的期待,以及中国博物馆早于美术馆建设、行使美术馆职能的现实,学术界逐步形成了美术馆属于博物馆的主流观念,美术馆自然也被纳入博物馆学的研究框架之中。但时局动荡,虽然美术馆(art museum)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被反复提及,但建设成功的案例仅有苏州美术馆和天津市立美术馆两所。相关学者对美术馆收藏美术古物、发挥教育功能进行了诸多规划,但很难实现。美术馆与展览的密切关联及其作为展览馆的身份,在现实层面反而更加凸显。
20 世纪上半叶对美术馆概念的双重认知——艺术博物馆与美术教育展览馆,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美术馆建设。与20 世纪上半叶相似,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美术馆与展览关联密切,被纳入文化宣传部门,与博物馆分属两套管理体系,二者拥有不同的功能与定位,直至20 世纪80 年代的《关于美术馆工作暂行条例》才明确了美术馆的艺术博物馆属性。但此时我国的美术馆已经失去了筹建蔡元培等学者所设想的涵盖古今的艺术博物馆的机会,与博物馆相比,美术馆自然被学者们总结为“社会基础薄弱”。[19]121-123美术馆即为美术展览馆这种认知依旧如影随形:少数美术馆拥有相对丰厚的20 世纪美术藏品根基,在此基础上开展学术研究、自主筹划展览和相关活动,是为艺术博物馆;但是大部分成立于20 世纪后期或21 世纪的美术馆,仅发挥展览馆功能。[20]76-81中国公众更多地将国内保存美术古物的综合性博物馆与学术、知识、教育联系在一起,将之塑造成权威的知识宝库;而将国内的美术馆更多与展览宣传、美感体验画等号——这与1931 年《教育部关于全国社会教育设施概况报告》将博物馆列为“偏于知的社会教育事业”,将美术馆列为“偏于情及德的社会教育事业”遥相呼应。
故此,中国的美术馆具有独特的历史进程,不同于欧美视野中的艺术博物馆,不能笼统置于博物馆学的理论框架下。面对当下美术馆的建设热潮,打造符合中国现实语境的美术馆学必要且迫切,而对于“美术馆”概念生成的辨析,有助于明确当下中国美术馆所处历史发展阶段与定位,从而更好地建立美术馆话语体系,促进其社会功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