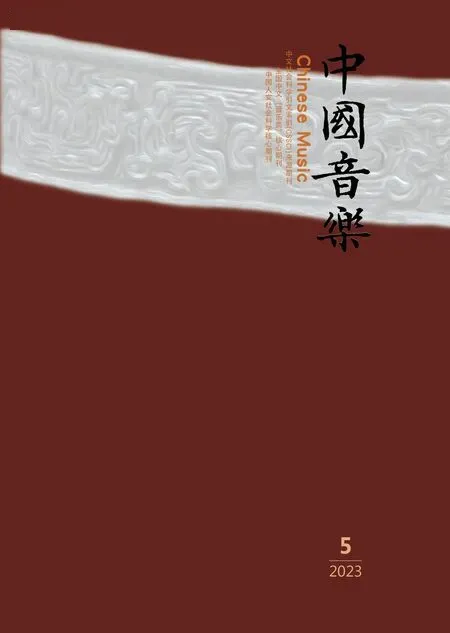论民族音乐学的“再研究”
2023-12-13赵书峰
○ 赵书峰
导言
民族音乐学“再研究”主要受到文化人类学研究观念的影响。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再研究”(re-studies)经典个案较多。国外代表性研究当数米德与弗里曼两位人类学家关于萨摩亚人的“重新研究”。1928年,玛格丽特·米德出版民族志专著《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1983年,德里克·弗里曼继米德之后出版《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引发了人类学界关于田野民族志真实性与客观性等议题的“米—弗”之争①张丽梅、胡鸿保:《米德·弗里曼·萨摩亚——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76页。。对于人类学的“再研究”,有学者认为是“重访与再研究”,即重访(revisit),就是田野工作者对自身考察点的再次访问,即对自己田野工作点的回访。人们平常所谓的追踪调查大多属于此类。这类重访强调对社会文化变迁的考察,如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等,都曾对自身的田野工作点进行过重访,属于经典的人类学“再研究”个案。当下,中国人类学界的“再研究”个案较多,比如:2003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的三位博士生张宏明、梁永佳、褚建芳分别针对60年前费孝通主持的“云南三村”调查、许烺光在大理“西镇”(喜洲)展开的祖先崇拜研究、田汝康对“摆夷”(傣族)村寨的研究。②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2-135;135页。然而,民族音乐学界“再研究”个案不多,且存在一个学理误区,即多数学者认为,在学术研究选题(如研究生学位论文)过程中,如果针对同一种音乐事象或相同田野点展开的“重新研究”很难产生真正的学术突破点或创新点,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炒剩饭”的窘地。为纠正学界这一错误认知,笔者结合人类学界的研究成果与当下民族音乐学界的研究现状展开分析思考,针对“再研究”的概念、研究维度、学理意义与价值、聚焦的学术问题等展开论述。
一、何谓民族音乐学“再研究”
民族音乐学“再研究”主要指研究者针对自己的田野点展开长时间的回访或追踪调查,同时还指针对其他学者的田野点进行的重新调查研究。前者是同一个研究者针对相同音乐事象展开的长时段、持续性的“重新研究”,后者指不同研究者面对同一个田野点开展的音乐民族志的比较研究。王铭铭提及,国内称对旧田野工作地点的再次研究为“跟踪调查”,而海外人类学则称之为“再研究”。③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2-135;135页。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内特尔认为:民族音乐学中的重新研究至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田野工作者不断回到同一地方去,这可看作是重新研究,那不仅揭示了该文化的变化,也显示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变化。……另一种更有特色的“重新研究”概念是,田野工作者考察另一个人(也许是多年前)调查过的一种文化。④〔美〕布鲁诺·内特尔:《民族音乐学最近二十年的方向》,汤亚汀编译,《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52页。人类学界有学者关于“再研究”的界定,通常是对他人的调研点进行重新调查研究,也就是在他人的调研点做田野工作,以期与先行研究进行学术对话。尽管有时也把人类学者对自身田野工作点所做的重新调查称为“再研究”,但相对来说,人类学“再研究”更多的是指对他人田野工作点所开展的“重新研究”。简单而言,所谓人类学“再研究”就是一位人类学者对另一位人类学者先前田野工作点展开的重新研究。⑤兰林友:《人类学再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第36页。可以看出,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关注的“再研究”问题有较大差异,民族音乐学界主要针对自己的田野点展开的长期的历时性的重访或跟踪调查研究,借以关注研究对象的文化变迁与学者个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调整,而国内外人类学界的“再研究”更多是“重新研究”,大多是基于其他学者的田野点展开跨越时空性质的比较研究,借以论证前人学者田野民族志书写的合理性与真实性问题。
二、民族音乐学“再研究”的两个维度
(一)同一个学者针对相同音乐事象展开的跨越时空性质的历时性或持续性研究
即田野点的重访、田野考察对象的追踪研究,目的是观察不同时空维度中音乐文化的变迁轨迹。该类研究聚焦同一学者研究观念、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问题等在前后不同时段的变化与调整。笔者多年在湘南蓝山进行瑶族音乐考察、研究,分别于2008年至2011年博士论文写作阶段、2015年至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项目研究阶段、2020年至今国家社科冷门绝学项目研究这三个阶段将同一个田野点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不同历时性阶段的拓展性研究。这里面既有对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扩展,也有对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明显调整。即以湘南蓝山县过山瑶“还家愿”仪式音乐作为研究支点,逐渐辐射到中国(湘粤桂)与老挝、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老挝、泰国、越南)瑶族《盘王大歌》音乐的比较研究,下一步还会辐射到中国与欧美瑶族音乐的比较研究。笔者博士论文主要针对瑶族《盘王大歌》仪式的民族志书写与音乐形态的分析研究,但缺少了历时性维度的田野考察。随后,在湘南蓝山瑶族音乐的历时性跟踪研究或“再研究”过程中⑥欧阳平方、赵书峰:《民族音乐学研究之路——赵书峰教授访谈》,《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2年,第5期,第3页。,笔者的第一个国家社科项目加入了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维度。第二个国家社科项目由于受到跨学科研究的影响,聚焦于瑶族《盘王大歌》的语言音乐学分析与研究,针对湘粤桂瑶族“还家愿”仪式中《盘王大歌》进行搜集、整理与研究,并将其歌唱进行国际音标、旋律记谱、田野考察报告等方面的资料性与学术性的整理与研究。从亚洲文化圈的角度重新审视笔者三个阶段的中国瑶族音乐研究,可以看出,是一个微观、中观、宏观维度的“再研究”。2008年开始撰写的博士论文是以湘南瑶族“还家愿”仪式音乐为切入点,这看似一个区域性研究,但从亚洲文化圈维度审视只是一个微观研究;2015年以来从事第二阶段的中国湘粤桂与老挝瑶族婚俗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⑦赵书峰:《瑶族婚俗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以中、老瑶族为考察个案》,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课题编号:15BD044)。,是一个中观研究;2020年以来笔者从事的中国与东南瑶族《盘王大歌》的搜集、整理与研究⑧赵书峰:《中国与东南亚瑶族〈盘王大歌〉系列传世唱本整理与研究》,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课题编号:20VJXG022)。,是一个宏观的比较研究。从三个时期针对瑶族音乐跨越时空展开的微观、中观、宏观性质的历时性比较研究,不但折射出瑶族音乐15年的历时性变迁轨迹与研究问题的不断拓展,而且也看出作为研究者本人,由于知识结构的不断丰富、田野工作广度与深度的不断加强,以及田野新材料的不断发现等等因素导致在研究观念、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问题等方面的不断调整。
再如杨民康、符美霞合著的《海南传统仪式音乐文化志》,是对世纪之初两位学者的成果《海南道公祭仪“做斋”的音乐民族志考察研究》⑨杨民康,符美霞:《海南道公祭仪“做斋”的音乐民族志考察研究》,载曹本冶主编《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南卷(下)》,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69-162页。进一步的田野回访与时隔数年之久的“再研究”。前者是作者对海南汉族、黎族传统仪式音乐进行的田野考察研究,后者是对海南黎族“做斋”仪式的田野民族志微观个案考察,上述两个成果实际就是民族音乐学“再研究”或拓展研究。
还有一些民族音乐学学者的博士论文选题也是对同一研究对象的“重新研究”。比如,魏琳琳博士从硕士、博士、博士后三个阶段的研究是对内蒙古“二人台”音乐的“再研究”。其硕士论文《二人台音乐形态初探》,运用赵宋光先生“12维剖析法”对二人台音乐形态特征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其博士论文《城市化语境下内蒙古二人台音乐文化研究》,结合音乐民族志研究个案,从历时和共时角度关注“走西口”音乐文化迁移史及相关文化主题的内在联系与对比观照。其博士后出站报告《传统音乐与文化认同——蒙汉杂居区日常音乐实践的民族志研究》,是以蒙汉杂居区日常音乐实践场域——文化大院为主线所进行的一项民族志研究。可以看出,魏琳琳博士的三个学术研究阶段是对内蒙古“二人台”音乐在不同时间段,在问题意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问题等方面的“重新研究”,从硕士论文注重“二人台”音乐的形态分析,到博士论文扩展到历时与共时维度的音乐民族志比较研究,再到博士后出站报告关注“二人台”音乐实践与其文化多重认同的民族志考察。
(二)不同或多个学者在不同时段针对同一个音乐事象展开的民族志比较研究
不同学者由于教育背景、研究观念、田野工作深度、问题意识聚焦点的差别导致产生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民族志观察与书写(表述)的差异性问题。民族音乐学“再研究”就是考察研究对象的文化变迁与研究者跨越时空的研究观念与问题意识的变化。如:三个不同时代的三位学者关于泰北勉瑶经济与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与礼仪等方面的田野考察就是典型的“再研究”。其一,20世纪60年代以日本民俗学家白鸟芳郎《东南亚山地民族志》⑩〔日〕白鸟芳郎编著:《东南亚山地民族志》,黄来钧译,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1980年刊印。为代表,主要针对泰北勉瑶的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社会结构、民俗仪式信仰等问题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田野考察;其二,以日本民俗学者吉野晃的博士论文《泰国北部优勉(瑶)亲属组织与祖先祭祀的社会人类学研究》⑪〔日〕吉野晃:《泰国北部优勉(瑶)亲属组织与祖先祭祀的社会人类学研究》,2007年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为代表,针对泰北勉瑶民间仪礼中的“家先单”“祭祀制度”“婚俗仪式”等民俗事象给予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三,笔者在2018年对泰北清莱勉瑶婚俗仪式音乐的初步考察研究⑫赵书峰:《中国与东南亚瑶族婚俗音乐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研究——以中国湘粤桂、老挝琅南塔、博胶、万象与泰国清莱瑶族考察为例》,《中国音乐》,2022年,第6期,第120-132页。。如:不同的学术团队与学者个人对冀中音乐会的考察研究也是典型的民族音乐学“再研究”。如: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齐易教授的团队⑬齐易:《一个在城市化背景下复兴的民间乐社——对霸州市南头村“音乐会”的考察与思考》,《中国音乐》,2016年,第3期,第93-99页。,针对20世纪80至90年代期间以曹本冶⑭曹本冶,薛艺兵:《河北易县、涞水两地的后土崇拜与民间乐社》,《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1期,第79-98页。、张振涛⑮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薛艺兵⑯薛艺兵:《屈家营“音乐会”的调查与研究》,《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2期,第81-96页。等代表的学者,对冀中音乐会研究展开的一次大规模性质的田野重新考察。他们针对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如雄安新区建设)冀中区域内音乐会的分布情况、乐班人员构成、传承人情况、音乐会曲牌构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重新调查研究。田野考察成果分别获得了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如:荣英涛博士的论文《京津冀音乐会变迁研究》,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前辈学者成果的一种“再研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问题切入,这实际上也是民族音乐学倡导的“再研究”或者称“重新研究”。再如:1981年,包括杨沐在内的10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研究生在对海南民间音乐展开田野考察后,撰写了《海南民间音乐采访录》。后期,杨沐先生对海南民间音乐进行重新研究,出版专著《寻访与见证——海南民俗音乐60年》(2016),在研究视角、田野工作深度与广度、研究方法、研究问题等方面均与前次有较大差异。此后,杨沐针对前后两个不同时段田野考察的得与失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采访录》跟《60年》二者的内容并不重复。前者是海南音乐和相关民俗在1981年那一节点上的情况报告和记录,而后者是我在那基础之上于其后持续34年的后继考察和研究结果。仅就记谱而言,前者是当年整个小组成员分头记录的那时采集的民歌演唱,而后者仅有一小部分取自我本人在当年的记谱,大部分则是我个人在此后的考察中采集到的民歌记录,其中即使有些跟前者记谱中同名甚至演唱者也相同的民歌,也是这些民歌或演唱者在1981年之后的不同的时间段内不同演唱的记录。《采访录》在不少地方说明了由于当时的时间与条件不允许,更深入的情况与资讯只能留待日后调查补足,而《60年》则部分地完成了这样的补足工作。从两书的性质来说,前者基本上是田野考察报告,而后者则是包含着阐释、分析、研究及其结论的文化志。⑰〔澳〕杨沐:《一份极难复得的音乐学考察报告——〈海南民间音乐采访录〉2018年版前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64-65页。
可以看出,民族音乐学界不管是同一学者还是不同学者进行的“再研究”,多是对自己前期研究成果的丰富与弥补,以及基于比较民族志视野下的针对其他学者研究成果进行的“重新研究”。
三、民族音乐学“再研究”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民族音乐学“再研究”不但是基于比较民族志视野下的重新研究,而且是对研究论域、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问题等不断调整的过程。
1.民族音乐学“再研究”折射出学者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的变迁
每位学者在不同时期由于“知识树”结构的不断调整导致其研究理念、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发生深刻变化,在面对自己或他人田野点进行“重访”、对研究对象进行“追踪考察”时会在问题意识、研究视角、研究论域等方面与之前的研究有较大差异。通过对同一学者或不同学者在不同时段的田野民族志考察个案之间的比较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出某一音乐事象真实的艺术样态以及民间艺人日常的生活画面。正如笔者在谈及少数民族音乐“再研究”时:“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考察研究不应是孤立的、静态的,要时刻关注研究对象的变化、发展的现代结局,而且要在他人研究基础之上进行多角度、动态的综合考察,这样的研究才能被认为是相对完整、合理地诠释少数民族音乐所隐含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内涵。”⑱赵书峰:《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现状评析——以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为例》,《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3期,第99-100页。因为“任何个人都无法全面诠释某种音乐文化,只有来自许多观点的多种声音才可以编织出有关一个民族的音乐上比较清楚的画面⑲汤亚汀著译:《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
2.民族音乐学“再研究”透视出音乐事象在不同时空维度中的文化变迁轨迹
民族音乐学“再研究”,是对相同的传统音乐事象在表演语境、乐舞形态、社会文化功能、传承谱系等方面展开的跨越时空的持续性跟踪调查研究。面对不同时间维度中的不同学者展开的对同一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研究,可以折射出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与合理性、研究者田野互动与反思过程等维度的深度思考。当今全球化、城镇化进程中给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带来诸多严峻挑战,乡愁记忆中的原生性传统音乐的表演语境已经被全球化、城镇化进程遮蔽掉。传统音乐从表演语境、表演形态、社会文化功能等方面发生了诸多显著的身份变迁。以笔者长期关注的湘南蓝山瑶族“还家愿”仪式为例,当下由于瑶族经济生活的不断提升,仪式中还加入了唢呐乐班。这种仪式用乐的变化折射出不同时空语境中瑶族传统民俗仪式音乐的重建现象。如果我们不建立一种持续跟踪性质的田野回访或者“重新研究”,就很难发现由于现代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瑶族传统民俗仪式音乐的变迁带来的重要影响。
3.民族音乐学“再研究”是“重新研究”不是“炒剩饭”般的“重复研究”
民族音乐学的“再研究”虽然是对相同的田野点展开的重新调查或者追踪考察研究,但绝不是所谓“炒剩饭”般的“重复研究”。目前在民族音乐学界存在这样一个误区,有些师生认为,在研究生论文选题过程中,一旦某个拟定的研究对象有过别人(前人)的成果,我再介入,就有重复研究的味道了,很难有突破。笔者以为不然。虽然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但我们选择的研究论域、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研究问题不同,或者民族志考察维度不同,这正是对前人或他人研究展开的比较研究或补充研究,甚至是对某一研究对象更加全面的民族志书写过程。正如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笔者的博士生肖志丹的博士论文选题《湘粤桂区域瑶族〈盘王大歌〉仪式音乐的比较研究》,就是结合前人学者在瑶族“还盘王愿”仪式音乐研究中未关注到的维度进行的重新研究。其论文将针对湘粤桂区域内过山瑶“还家愿”仪式及其音乐本体展开跨区域性质比较研究,尤其将仪式中的《盘王大歌》置于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三个维度对其音乐本体结构(“族性腔词”)的生成逻辑结合语言音乐学理论展开分析研究。可以看出,针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不同学者在不同时期展开的研究,既是研究视域的拓展,又是研究方法或研究理念的补充或重构,这体现出民族音乐学“再研究”的学术魅力与学理的创新之处。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的学术选题不应该回避“再研究”,它不是一种“炒剩饭”的“重复研究”,而是基于自己或前人研究继承与反思基础上的“重新研究”。
四、中国民族音乐学“再研究”应关注的学术焦点
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界的“再研究”应聚焦以下问题展开田野考察:
1.关注“三后”(“后集成”“后非遗”“后疫情”)时代的“再研究”
当下,我们应该针对“后集成”“后非遗”“后疫情”时代开展民族音乐学“再研究”,针对其“前后”两个时代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研究范式、田野工作方法等展开继承与反思研究。
其一,“后集成”时代的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应针对中国各省民间音乐舞蹈集成编撰过程中的田野工作规范、文本书写规范、研究理念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以此揭示出“集成”撰写时代前辈们的田野工作经验及存在的问题与反思。民间音乐集成中,关于部分民歌的记录就存在不少问题:部分只记录音乐和唱词的大意(汉语记录唱词),不能真正还原其歌唱艺术形态与风格的“原真性”特征;同时对于“语言—音乐”的互动关系,尤其在少数民族语言音乐学研究方面的力度稍显薄弱,学者大多关注的是汉族传统歌唱语言与音乐的关系思考,甚少将少数民族歌唱置于语言学(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维度中,结合田野考察搜集的语料库资源,运用语言音乐学思维展开互动研究。由此,如何在“后集成”时代对传统音乐的歌唱(如民歌音乐的搜集与整理)做“原真性”搜集,从音乐(旋律)、语言(语音)、语义(唱词)三方面进行再研究,值得被重视。同时,诸多地方民歌集成搜集与整理者用汉语的形式书写少数民族音乐唱词内容,这或是受到了潜在的“汉族文化中心论”表述思维的影响。“后集成”时代对于诸多民间歌唱搜集、整理的“再研究”亟待开展。
其二,针对“后非遗”时代,传统乐舞在表演形态、表演方式、文化功能等方面存在的文化变迁问题展开比较研究。“非遗”申报自2006年以来,诸多传统乐舞项目为了成功申请“非遗”,就要针对评审规则进行系列性的建构,为此成功申请“非遗”后的传统乐舞项目与其原生性表演形态、文化象征等方面出现诸多重构现象。尤其经历了全球化、城镇化、现代化等多重文化语境的作用,诸多“非遗”项目的音乐形态、表演方式、文化功能出现显著的身份重建现象。因此,亟待加强“后非遗”时代传统乐舞的艺术本体形态、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应用民族音乐学等问题的考察研究。“后非遗”时代学者们应聚焦于对同一个田野点展开不同视角、不同研究方法的“再研究”。因为,随着城市与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致使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生态环境遭受到很多人为性质的破坏。同时,随着经济、社会、文化交往范围的逐步扩大,也导致族群音乐文化之间的“涵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亟待研究者对现代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变化、变异情况、身份属性、文化象征功能等问题给予持续性的跟踪与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音乐在现代化、商业化、流行文化、传媒体系的多元渠道(传播方式的改变)的影响下,其生存发展环境、表演形式、演出目的、民俗信仰依托等等出现较大变化,因此,如何结合多学科理论对其进行再研究(或重新研究)尤其必要。⑳同注⑱,第99-100页。
其三,针对“后疫情”时代,传统乐舞在表演方式、传播渠道等方面存在的多元特点展开比较分析研究。“新冠疫情”时代不但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且也为传统音乐的表演与音乐传播带来了显著变化。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某些大型的民俗节庆仪式音乐表演被人为取消,或改在线上“自媒体”直播平台表演。民俗节庆仪式音乐活动的取消与表演方式的人为改变,严重影响了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同时导致其表演语境、表演形态、表演方式、传播方式的显著变化。㉑赵书峰:《非遗·自媒体·语境:传统音乐表演的建构与生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90-91页。因此,关注“后疫情”时代传统音乐的表演语境、表演方式、表演形态、社会文化功能等诸多因素的重建研究,不但可以探究传统音乐文化在不同的社会时空维度中的发展与变迁轨迹,而且为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策略研究提供诸多智力支持。
2.聚焦于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传统音乐变迁研究
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不但显著改变了传统音乐的表演语境,而且也重建了传统音乐的表演形态、表演方式、社会文化功能。传统音乐与其传承人从原生性乡愁记忆的文化空间中走向由政府、文化旅游部门打造的专业性舞台表演语境。传统音乐的原生性表演语境被急剧的现代化、城镇化进程尘封在历史记忆中,导致传统音乐的表演成为了被现代性解构的一种被观看的文化展演。传统音乐的民俗性、象征性功能被现代性的审美文化解构。因此,传统音乐的“再研究”应聚焦多重社会文化语境的显著变化导致传统音乐的艺术本体结构、社会文化功能变迁问题,关注传承人由于生活环境、经济状况、教育背景、传承谱系、审美价值观念的变化给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带来的影响。比如,在对15年持续性跟踪的同一个研究对象(湘南蓝山过山瑶赵金付师公)瑶族音乐研究中,笔者发现研究对象的居住环境发生改变(从山上简陋的土房子搬到镇上新建的二层小楼);近些年,其从事的瑶族“还家愿”仪式音乐中加入了唢呐乐班。这不但说明瑶族民间传承人生活语境的变化,也折射出其仪式用乐由于瑶族社会经济生活的改善而发生显著变迁。
3.聚焦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制度变迁后的“再研究”
任何时代,国家文化制度都是决定传统保护与传承、发展与创新的根本所在。研究者可聚焦21世纪以来国家关于传统文化保护制度的系列变迁给传统音乐事象的发展与传承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如“文化融合”“乡村振兴”“非遗保护”等国家政策的制定给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带来哪些深刻影响——音乐本体形态的变迁、表演方式的改变,社会文化功能的重建,以及音乐传承方式的变革等。特别要关注遗产化背景中传统音乐的应用性研究,传统音乐的传承与表演与其地方民俗旅游文化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思考。
4.针对自己或前人学者的研究展开“重新研究”
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再研究”,首先要在学者个人前期研究基础上进行长期不间断的重访或追踪调查研究,比如结合学者个人的硕士、博士论文研究开展“重新研究”。这既是学者个人针对同一研究对象的拓展研究,而且更是学者本人的“再研究”。其次要针对其他学者或学术团队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研究”,这不但是对前人学者研究的丰富与补充,也是基于他人或学术团队研究基础上的一种田野民族志的比较研究。比如可针对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香港中文大学民族音乐学博士选题个案进行“再研究”,以及对曹本冶教授团队按照区域划分主编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信仰音乐》(西北卷、华南卷、西南卷、华东卷等)中的研究个案展开“重新研究”。通过这种音乐民族志考察的比较研究,可关注到中国民族音乐学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等方面出现的比较重要的学术转型,以及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等进程给中国传统音乐发展与变迁带来的深刻影响。
结语
民族音乐学“再研究”是基于个人或其他学者研究基础上,对相同田野点的重访或追踪考察研究,是一种研究论域、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调整下的“重新研究”,也是在不同历史时段观察同一音乐事象文化变迁性质的比较研究。“重新研究”不是“重复研究”,而是建立在与本人或其他学者研究基础上民族志考察的比较研究。只有做到从研究论域、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等方面,与先前的研究有丰富与拓展之处,才能真正实现“重新研究”的学术意义。因为只有研究手段丰富、研究视角全面,才能捕捉到同一音乐事象在不同历史时空维度所经历的文化变迁轨迹,同时也折射出研究者研究方法、研究观念的细微调整,这样才真正实现民族音乐学的“再研究”的目的,否则就是一种“炒剩饭”式的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重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