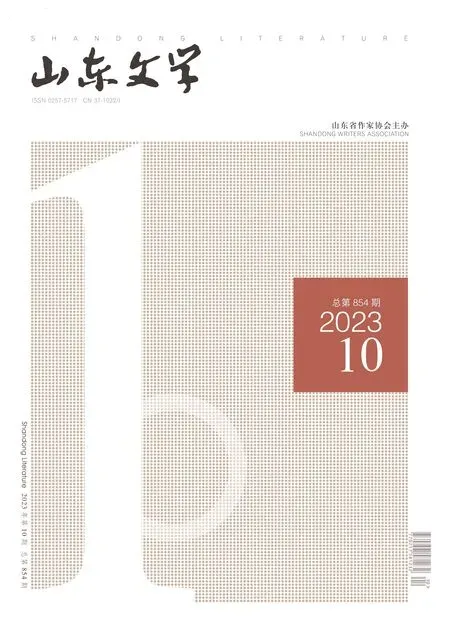孕 育
2023-12-11武俊岭
武俊岭
烧饼的芳香穿透薄薄春寒,像一条绳子飞到章有礼一家人的身边。有礼一家四口,自北县逃荒来到寿张城北的一个村子边上。有礼的妻子名荷花,像是一枝秋天里的败荷,枯枝残叶,了无青翠之色。有礼背着被子,手牵三岁的大儿子守成。荷花怀里,抱着小儿子守功。守功出生刚刚一百天,已是两天没喝一点东西。才会说几天的嗯啊,说不出来了。荷花的双奶,没有了一点汁水。守功,眼睛闭着,小嘴微张,脸皮起皱。
那条有力的绳子牵系着,有礼一家极快地找到打烧饼的人家。虽然时已薄暮,但仍可看出院落的整齐,堂屋的高大。
烧饼炉子在院子的中央。炉内的木炭红红的。
大哥,您行行好,给俺几个烧饼吧。我们一家两天没吃东西了。小儿子快饿死了。
打烧饼的汉子,名孙五,看准炉内一个空处,贴上去一个烧饼后,把头扭向有礼,说,行,给你们一人两个。对了,我让我媳妇给你们倒水。
孙五冲着屋子大喊,媳妇,媳妇,把热水提出来。
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媳妇,闻声从屋里提出一把热水壶,三个瓷碗。刚刚把壶里的水倒进碗里,有礼、荷花,已是吃下一个烧饼。守成吃下去半个。
孙五的媳妇姓王名云,看到有礼夫妇眼睛盯着炉边笸箩里的烧饼,便拿过两个,递给二人。
恩人,恩人!有礼一边大口吞吃烧饼,一边感谢。
有礼夫妇一人吃了三个烧饼,喝了两碗水,才算是饱了。大儿子守成,吃了两个烧饼,喝了一碗水。
王云接过荷花怀里的孩子。孩子的脸面,让王云想到一颗皱缩的黄梨。王云心里一疼,把孩子交给荷花,说,你们稍等。
不一会儿,东屋里冒出让人欣慰的炊烟。淡淡的呛人气息里,有了玉米糊糊的香味。
金黄的玉米糊糊,盛在一只小碗里。王云用一把小勺,一圈一圈地轻轻搅拌。糊糊的热气散发出来。
好了。王云说完,坐在小蒲墩上,喂守功喝粥。
守功的小嘴张了几张,终于张开。于是,王云一勺一勺,送粥至守功嘴里。
喝了七八勺,守功的眼睛睁开了,眼珠黑黑如成熟的龙葵。
王云说,这孩子真喜人!
荷花听了,轻叹一声,说,可惜,孩子命不好,没赶上好年景。
时间不长,守功把粥喝完。这段时间里,孙五已是打完烧饼。乡亲们,陆续买走一些。此刻,有四个烧饼影绰于暮色里。炉子里的木炭,一星红火闪耀之后,黑了。
孙五说,院子里冷了,进屋吧。
有礼说,不了大哥,你让我们一家吃了一顿饱饭,我非常感激。我们,我们一家得走了。
王云说,你们两口子、你们的大儿子,还能走一走。这个小的,一百天的奶孩,太受颠掀了。
荷花抱着孩子,走到有礼面前,窃窃相商一会。
有礼挪到孙五身边,嘴张了几张,吭哧一阵,说,大哥,俺媳妇与我商量,想把小儿子守功送给您,不知您要不?
孙五听了,立即想起十几年求子的艰难。
妻子王云身材高挑,胖乎乎的,但就是不生孩子。有名中医杜远心开的药吃下去一堆,就是不管用。自己的爹娘,在对孙子的渴盼里先后死去。二老临死,拉着自己的手,说出差不多的话,孩子,怎么着也得想法儿给咱老孙家留个后。三辈了,三辈独传。
自己听了,只能含泪点头,想说一句什么,却是说不出来。
孙五快步走到妻子王云身边,把有礼两口子的想法,说了出来。
王云一喜,说,这敢情好。这样,把剩下的四个烧饼给人家。
荷花抱住孩子,泪水哗哗。荷花用衣襟擦擦泪水,用嘴去亲儿子的脸蛋。儿子发出两个字,嗯啊。
荷花双手托着儿子,递给王云。待双手一轻,荷花猛然转身,向院门外快跑。荷花跑出院门一百多米,突然爆发出悲痛的哭泣。守成手拿四个烧饼飞跑,追赶母亲。有礼摇摇头,走近王云,对着儿子盯视有顷,说,孩子给你们,与你们争食了。
王云说,你放心去吧,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孩子的。饿死我们,也不能饿死他。
就是!孙五随声附和。
第二天起,孙五只打三十个烧饼。以往,是四十个。少打十个,是为了把白面留下来,好喂养儿子。
王云问丈夫,儿子,还叫守功?
守功,孙守功。这名字还行,不改了。
好,功儿,功儿。王云欣喜着,抱着儿子,身子转了个半圆。儿子小眼瞪着王云,小手扬着,嗯啊一声。
这一声嗯啊,把王云喜坏了,说,这孩子真喜人,真是好孩子。
王云一天到晚,把心思全都用在孩子身上。王云让孙五往村西金堤河滩地里,用独轮车推回来两大布袋细沙。趁孩子睡觉的工夫,王云把细沙用细罗筛了一遍。筛出的沙子,细细的,颜色微黄。随后,王云用一口铁锅,把沙子炒了半个时辰。沙子在热锅里,散发出淡淡的鱼腥味,这让王云更加喜悦。虽然不是从自己肚子里生出来的,但自小抚养他,长大了,也会把我当成亲娘的。村子里,已有两家这样的例子。
王云用细布缝制了三条沙土布袋。布袋于侧面开缝,缝上密密的布扣。王云把炒好的细沙,装进布袋里一斤。王云让刚睡着的儿子,躺在布袋里,系上布扣。儿子的屁股下面,是微热的沙子。儿子仅剩下小脑袋,在沙土布袋外面。
儿子睡了一个多小时,啊啊哭了起来。王云走近去,用手一摸儿子腚下,有了一个稍硬的圆饼。王云笑着解开布扣,把圆饼拿出,丢在炕下。这圆饼,是儿子尿成的。王云侧过儿子的身子,把干爽的沙土放进布袋。随后,王云轻轻地把儿子的身子正过来。
王云侧身躺在儿子身边,拍着软软的腹部。王云嘴里念叨着,噢噢睡倒倒,老猫来了咬耳朵。噢噢睡倒倒,老猫来了咬耳朵……
温柔的眠歌里,儿子又睡着了。
米汤、面汤、玉米糊,三样交替着,王云喂儿子喝。米汤,是小米汤。王云用一口小铁锅,锅下烧着芝麻秆,熬小米汤。王云大火烧开锅里的水米后,立即换成小火。等锅里米香味儿出来后,就由几根芝麻秆自燃着。芝麻秆烧尽,灰烬完全变灰时,就可以打开锅盖了。王云用一把稍大一点的勺子,先把米汤上面的那一层黏稠的皮儿,珍惜地盛入碗中,再盛余下的汤汁。那一层皮儿,是米油,小米的精华。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育儿方法。王云自记事起,就听母亲说过。
王云坐在一个高点的蒲墩上,左臂揽住儿子,右手用小勺盛上米汤,送到儿子嘴边。儿子小嘴一张,米汤入口,咽下。儿子胃口很好,一碗米汤,一会儿喝了下去。
王云站起来,抱着儿子在屋里来回走动。王云哼唱这样那样的歌谣,声调滋润。
一会儿哼,小巴狗,戴铃铛,晃啷晃啷到集上。要吃桃,桃有毛,要吃杏,杏又酸,要吃果子面丹丹。
一会儿唱,小板凳,打歪歪,我给奶奶下挂面,奶奶嫌我下的稠,我给奶奶放香油。奶奶嫌我下的香,我给奶奶切块姜。
一会儿说,小麻妮,拾棉花,一拾拾个大甜瓜。爹一口,娘一口,一咬咬了麻妮的手。麻妮麻妮你别哭,我给你买个货郎鼓。白天拿着玩,黑了吓麻虎。
面汤,是白面做的。灶下的柴火自燃着,烧着锅里的水,王云把一两面下到碗里,加上清水,用筷子划圈搅动。水开了,王云把搅匀的面汤倒进锅里。随即,王云一边用勺子贴住锅底不停地搅、搅、搅,等麦面的香味出来后,撤火。面汤盛到碗里。这样,一直到面汤不再烫嘴,也不会变稠。
熬玉米糊,与熬小米汤差不多。
王云,累着、乐着,日子便嗖嗖地往前跑,像一支欢快的羊羔。时序,到了秋天。
只是,欢乐的背后,忧虑悄悄来临。孙五最先觉察到,对王云说,阳谷集市上买不到白面了。烧饼,没法再打了。
王云心里一吓,说,咱这里,这两年不是没有天旱吗?
粮食,都让日本鬼子抢走,运到北县去了。
王云说,那以后,孩子还能喝到面汤吗?只剩下十几斤了。
我想想办法!
孙五想出的办法,就是花了两块银元,从村子里收了几百斤干草。孙五把干草垛在前几年盖的牛棚里。
之后,孙五到了寿张集市上,买回来一只母山羊。
一天,孙五挤两次羊奶。趁着羊奶热乎着,让儿子喝下。喝不了的,孙五装进一个瓶子里,把口封严,放进水缸里。这样,羊奶不会变味。儿子喝前,在热水里温一温。
一天三次,王云喂山羊汤水。王云抚摸着山羊的头,柔声说,羊啊羊,你吃好点、喝好点,多产奶,好把我的娇儿喂大。几年后我也不卖你,一直养你到老。
山羊听了,咩咩而鸣,用嘴巴去拱王云的手面。王云心里一热,眼睛一潮,心说,这羊儿通人性。
一个月,儿子长了近二斤,变得白白胖胖的,手腕那儿,胖出一个圆圈。腮帮,也胖出来很多肉。
王云说,羊奶,就是养人,你怎么没有早点想到呢?
孙五说,这不是被逼得吗?要是有几百斤白面放在家里,我也不会想到这个办法。
王云高兴得打了一下孙五的肩膀,说,嘻嘻,你这人看着蔫,但不迂。
受了表扬的孙五,哈哈一笑,说,那是。
一家人正和和美美地往前过着日子呢,一个姓孙名兵的人来到孙五家里。孙兵的大脚走过,院子的白色薄霜上,出现一串又斜又大的脚印。
两个皇协军士兵,在孙五的大门口站着。
孙五正好在家,坐在八仙桌前,脸阴着、长着,不理孙兵。
孙兵不把自己当外人,一腚坐在桌子左边的一把椅子上,高声大气地说,大哥,一笔写不出两个孙字,咱俩是一个爷爷的孙子,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放着我家里的三个儿子,你不过继,养一个北县的杂种,什么意思?
孙五听了,气得双手、嘴巴打起哆嗦,说,没什么意思,就是不愿意与汉奸来往!
孙兵一拍桌子,说,你放明白一些,我若不在皇协军任职,村子不知被抢几回了。
孙兵说完,站起走近王云,伸手在守功的脚脖上掐了一下。立即,守功吭吭地哭起来,声似铜号吹响。
王云把孩子放在炕上,像一头暴怒的狮子,双手齐向孙兵脸面挖去。孙兵极快地躲过。
孙五站起来,顺手操起一把镰刀,大声说,滚,快滚,要不我就不客气了。
孙兵见夫妻二人眼睛红了,一时气馁,只好迈步出门。孙兵走到院子中间,回头,恨恨地说,你们不念堂兄弟的情谊,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孙五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堂兄弟。
愤怒里,孙五想到孙兵五岁时,把屎拉在吃饭的锅里,让叔叔一顿暴打。从小看到大,孙兵这人就是一个土匪坯子。
不一会儿,街坊四邻来到孙五家里。大家好言劝慰:好鞋不踩狗屎,就当没有这回事吧。孙五把烟袋嘴在门镇石上磕得当当乱响,说,他别逼我,逼急了我,我与他拼命。
听了孙五的话,一个老人说,你不能这样想,你现在有了儿子,遇到这类强梁,还是避一避为好。他强梁,就让他强梁吧,早晚有完蛋的一天。
第二天,孙五找人帮忙,把院墙加高。没事,孙五就把大门关上,干点家务,帮着妻子照看守功。偶尔出门,就在外面把大门锁上。
三天两头地刮开北风,天越来越冷了。王云用去年剩下的白纸,把南北窗户糊上。窗框与墙之间的缝隙,用棉花套子塞住。王云知道,最怕冬天窗户缝,一丝小缝要人命。
王云缝制了一件棉套,让母山羊宽宽松松穿上。牛棚里,放上厚厚的麦秸。
王云知道,一冬天,儿子就全指望山羊了。
可是,糊窗户纸后半个月,孙五一大早起来,抱干草喂羊时发现,母山羊不见了。
王云听了,委屈立即如洪水一样淹没了她。她大放悲声,痛骂偷走山羊的恶贼。
儿子被王云的哭声惊醒,啊啊啼哭起来。王云只好止住哭泣,去哄儿子。
孙五一口一口地猛吸旱烟。
照例,街坊四邻又都走来,十几口子人围住孙五、王云,叹息、咒骂。
孙五站起来,走到牛棚里,把一把砌墙的瓦刀掖在腰里,往阳谷县城走去。
孙五走到皇协军驻地。门口站岗的问孙五找谁。孙五说找孙兵。站岗的说,孙队长不在队部,在紫石胡同胡家呢。
紫石胡同,孙五知道,就是狮子楼南边那条街。于是,孙五便大步走向狮子楼。到了狮子楼下,孙五想起西门庆就是在这个楼上摔下来,摔个半死,又让武松补上一刀,才气绝身亡的。西门庆如果不对武大下药,把事做绝,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
你孙兵不就是眼红我那四间祖上传下来的堂屋吗?想当初,爷爷就是看着你不是顺民,才把祖屋分给我爹的。你要我过继你的儿子,我就听你的?你这当爹的一脸匪相,你的儿子,还能好到哪里去?
孙五思忖着,走到紫石胡同。一家大门前,有两个皇协军士兵站岗。莫非,这里就是胡家?
孙五向两个士兵点头,问,这是胡家?
两个士兵笑笑,说,是,你想怎么着?
我是孙兵的哥哥,找他有事。
两个士兵听了,头碰头嘁喳几句。然后,一个士兵挤挤眼睛,说,进去吧。
孙五走进院子,在堂屋门口站住。屋子里面,有女人的笑声传出,有热哄哄的脂粉味传出。孙五一推屋门,闯了进去。
女人发出啊的一声。
孙五定睛,看到一个娇艳的女人从孙兵怀里站起来,对自己怔怔而视。
孙兵脸色一变,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孙五嘿嘿一笑,说,你好到这里来,我自然到这里找你了。
孙兵手一摆,女人立即走进里间屋子。
找我,啥事?
我想告诉你,做事别太绝了,不然对自己没好处。
你吓唬我?
我的山羊被偷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山羊,我堂堂皇协军中队长,会偷你的山羊。哈哈,哈哈。
堂堂,我看你一点也不堂堂。你的心眼,比针眼还小。
别废话了,你快走吧,不然我要发火了。
孙五此时,气愤渐渐上升。
卫兵,卫兵,死哪去了?
两个卫兵跑了进来。
妈的,谁让你们把这人放进来的?快快拖走!
两个卫兵一边一个,把孙五架了出去。
姓孙的,你好好想想,想想西门庆是怎么死的?
孙兵听了,嘿嘿笑了起来。
家里,只剩下不到十斤白面了。三天,王云才让儿子喝一次面汤。两口子看着吃下去不到一半的草垛,心说再买一只山羊吧,家里却没有了那么多钱。借,这年头,人人没钱,往哪去借呢?
好在,家里的玉米面还多,打烧饼换来的。小米,还有三十多斤。这样,靠米汤、玉米糊糊,儿子一天一天地成长着。
只要一抱起儿子,只要一侧身躺在儿子身边,王云就把一切烦恼、一切悲苦忘在了脑后。天天,王云与儿子语言互动。四个月时,儿子的嗯啊已是有了抑扬顿挫。五个月,儿子嗯啊起来已是长长的一串。六个月,儿子偶尔会说出一个含混不清的字……十个月,儿子能说出两个字。这两个字,王云听来,是奶奶。
奶奶。奶奶。王云纳闷了,听人说,孩子说话,都是先会说爹、娘,儿子怎么说起奶奶了呢?
思来想去,王云终于知道了:丈夫一生气,好说,他奶奶的!他奶奶的!儿子听了,就会瞪起小眼,盯住丈夫好一会儿。
原来是这样,王云笑出声来。孙五回到家里,王云用手指指儿子,说,你听听,听听。
儿子小眼看看孙五,停住不转,然后,小嘴一张蹦出奶奶二字。
孙五高兴地一拍大腿,一转身子,大声感叹,他奶奶的,咱没有白疼这儿子。
你又来了。王云白他一眼,说,你以后见了儿子,就说爹吧!
行,不,这哪成啊,不能把儿子当成爹吧。
哈哈哈,哈哈哈,两口子笑成一团。儿子受到感染,也呵呵地笑出声来。
十一个月时,当儿子喊出爹、娘时,孙五、王云两口子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转眼之间,春节将至。
这天,一队皇协军闯进村子,把青壮年连推带搡集合起来,赶到寿张据点挖濠沟。孙五没能幸免,与三十多口人一起到了寿张。孙五看到前后村的人都来了,就没有多想,开始挖了起来。
天黑了,不让回家。鬼子、皇协军运来一些树木、帆布,搭起棚子。众人合身钻进,胡乱睡去。
孙五怎么也睡不着,他担心妻子与儿子。到半夜了,还是睡不着。于是,他悄悄起身,向家摸去。为了壮胆,孙五手里提了一根一米多长的白蜡棍子。
在嗡嗡的纺线声里,儿子睡着了。王云幸福地纺着线,不时地扭头看一眼儿子。油灯灯心冒出一个灯花,王云用针剔去,往油瓶里加了点油。
纺纺纺,一直到腰有点酸、背有点疼的时候,王云停了下来。她看看屋门,门闩早已插好。于是,她走近火炕,脱去棉袄棉裤,钻进被窝,挨着儿子睡下。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王云忽地醒来,感觉有一只手想把被子掀开。恐惧,让王云的四肢不能动弹,嘴巴不能张开。但是,当这人的另一只手也伸过来,想把儿子抱起时,王云陡然有了力量。王云悄悄伸手摸到一块半头砖。王云上身迅速挺起,手里的那块半头砖,朝这人的头上砸去。
这人头一闪,躲开王云的砖头。没有抱着孩子的双手,用力地扳住王云的肩膀。这人嘿嘿笑着,说,孙五的种子太瘪,那就让我好好种种吧。你这块肥地,让我流了十几年的口水。
这人的左手抓住王云的两只手腕,右手撕扯王云的内裤。就在这人快要把内裤扯掉时,左手让王云一口咬住。这人怪叫一声,右手握成拳头,想把王云一拳打昏。危急时刻,孙五跳进屋里,手里的棍子,一下击打在这人的后背上。
这人慌忙跳下炕来,推开孙五,逃了出去。孙五追到院中,追出院外,大骂两声,返回屋中。此时,儿子已被惊醒,大哭起来。接近一岁的孩子的哭声里,已是有了愤怒。
孙五问,听清是谁了吧?
王云说,狗日的捏着嗓子说话,但我听着,十有八九是孙兵。
孙五提棍欲走,但忽然想起村里老人的话。于是,他坐在椅子上,发出一声接着一声的悲叹。
要不,躲到我娘家去?
孙五摇摇头,说,你娘家离阳谷更近。孙兵这个王八儿想找咱们的事,更方便。
春节到了。
这个春节,不只孙五一家,其他人家也过得没滋没味。他们知道,过了春节,就是漫长的三四个月的春天,而家里的粮食,却是越吃越少。人啊,不能用绳子扎着脖子过日子。
但是,对联还是要贴的。于玉米浆糊的香味里,新对联散发出红纸的味道、墨水的味道。王云抱着一身新衣的儿子,观看对联。儿子的脚上,穿着崭新的棉脚包子。棉脚包子上,绣着一只老虎,形神毕肖。
孙五总能凡事抢先,在榆叶半吐、榆钱满枝时,悄悄地上树采摘。他让王云把榆叶、榆钱蒸成窝头,两口子吃。为儿子熬玉米糊糊时,也放进去一些榆叶,切得碎碎的。吃剩下的榆叶、榆钱,晒干存放在粮囤里。
这时,从北县往阳谷、寿张地面逃荒的人,像赶集似的,轰轰地往南走。一天,有几十起人来到大门前,当当地晃动门鼻,苦声哀求,行行好吧,大娘婶子、大爷叔叔,给口吃的吧!
听到这样的声音,王云的脸吓得蜡渣似的。王云怯怯地问孙五,你说,咱家的粮食能撑到收麦子吗?
差不多吧。孙五指指牛棚,说,囤里的榆叶、榆钱,有六十多斤。把榆叶、榆钱弄成粉,就能吃。
王云心里踏实了一些,说,这些天,吓死我了。
孙五手抚妻子后背,说,别怕,别怕!
村上,不只孙五一人知道树叶能吃。榆树上的叶子,很快就没有了,人们开始爬到槐树上,不怕硬刺扎手,一把一把地从细枝上捋下叶子。
在槐树叶子即将捋完的时候,孙五心里突然烦烦的。他对王云说,我在外面锁好大门,你插上里面的门闩。我去邢庄,找邢远路聊聊,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度过春荒。
王云说,去吧,儿子手腕上的胖圈,没有了。喝粥像喝水一样快。儿子,到了吃点硬东西的时候了。
孙五走后半个时辰,一小队鬼子、一个中队的皇协军开进村子,一家一户地搜查粮食。这天也是奇怪,王云十分困倦,在儿子守功睡着后,歪在身边也睡着了。等大门被撞开,王云抱着儿子想躲藏时,已是来不及了。王云惧怕的,一是鬼子侵犯她的身体,二是家里的粮食被搜走。两样都是宝贵的,都应该拼命保护。
两个鬼子瞪着眼睛,端着长枪站在屋门外三两米的地方,三个皇协军走进堂屋、灶屋,搜查起来。
不一会儿,三条盛白面、小米、玉米面的布袋,让三个皇协军提溜出屋。
王云把儿子放在门槛里边地上。王云冲出屋门,朝一个皇协军士兵跪下,说,老总,行行好吧,给俺留下一袋!俺这孩子,才一岁多点。
士兵说,不行,大东亚圣战需要粮食。
王云站了起来,伸手抓住士兵手里的粮袋,奋力夺了起来。一个鬼子骂了一句,对着王云的手就是一枪托子。
剧烈的疼痛,使王云冒出一头撞向鬼子的念头。就在将要变成行动的工夫,儿子的哭声让她回转身子。王云脚步不稳地走向儿子。在王云快要走到门槛的时候,另一个鬼子端枪朝后心猛然一刺。王云惨叫一声,扑倒在地。王云的右手伸向儿子。儿子双手用力,向母亲身边爬行。王云的右手,快要触到儿子时,猝然停住。儿子的哭声,大了起来。
孙五到了邢庄,找到邢远路,说了家里的情况。邢远路叹息数声,说,老弟,离开村子吧,离孙兵这个败类远远的。
他孙兵还不敢占了我的堂屋?
命,比什么都重要!
回村路上,孙五一遍一遍地寻思邢远路的话,渐渐认可。那就也往南走吧,黄河北边的孙口村有一个本家,心眼很好。
孙五走近村子时,听到哭声一片。到家,看到妻子王云倒在血泊里,双目圆睁,含着无尽的悲愤、冤屈。儿子守功趴在门槛上,抓住母亲的右手,哭得嗓子已是嘶哑,不时地呼喊,娘,娘……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一席苇箔圈住王云,埋葬在祖坟上。
乡亲散尽之后,孙五抱着哭睡的儿子,坐在坟前,发呆发愣。孙五的思绪,如大海的波涛一样翻滚。最后,他想到的是,儿子的母亲没有了,那就让我既当父亲又当母亲吧。妻子没有了,还去不去黄河边呢?
回到家里,孙五把儿子放在炕上,盖上薄被。然后,他走到牛棚里,把囤盖拿开,盛一些榆叶、榆钱到簸箕里。孙五把里面的枝梗、土块挑出,又把尘土簸出。
随后,他走到大门外面的碓臼窑子旁边,把焦干的榆叶、榆钱放进去,然后用木槌一下一下地捣起来。待榆叶、榆钱碎得不能再碎时,取出。
孙五用一个细箩,把碎的榆叶、榆钱筛了一遍。这样,就有了一种特殊的面粉。
孙五在小铁锅里,刚刚把面汤熬好,儿子醒了,哭喊娘、娘。孙五心疼着,像妻子那样坐在一个高蒲墩上,左手揽住儿子,右手盛汤让儿子吃。不一会儿,儿子喝下去一碗。
儿子喝完,盯着孙五,喊,爹。
孙五心里一酸,说,儿子,爹爹抱你往村后麦子地里看看,好吗?
娘,娘。儿子又哭了起来。
孙五抱起儿子,缓缓地向村北走去。此时的春风已是没有了凉意。孙五忽然想到,儿子来到家里,已是一年多了。这一年多……
春风里,一尺多高的麦子轻轻倒向北方,绿油油的很有生机。孙五脑子里对儿子说,再有两个多月,孩子,你就能喝上白面疙瘩了。只是,我要是带着你去黄河边,让谁帮着收割麦子呢?
先按不去黄河边盘算:打下麦子后,我先藏起来一些,让该死的小鬼子找不到。
这时,孙五说出声来,把麦子藏起来,好不好?儿子,你说好!
好!儿子的声音稚嫩、清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