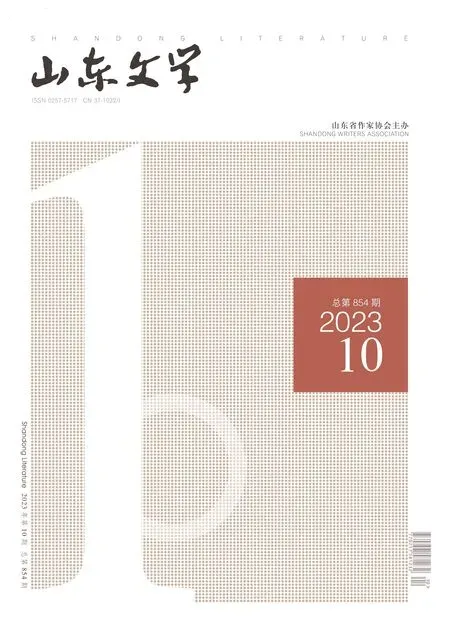七彩水晶
2023-12-11徐源
徐 源
在我九岁时,我们家生活在大山里,家里驯养着野鹿、锦鸡、松鼠,我与父亲到菜园锄草,它们就会趴在栅栏上围观,喇叭花一朵一朵顺着荆竹条爬行,爬到它们身上,就盛开了。那时,我的小动物们,都是父亲从森林里捡回的,父亲不是猎人,但他经常到黑漆漆的森林里去,回来时身上总湿漉漉的,还散发着一股木叶般腐蚀的清晰味儿,我知道,这就是森林的味道。我的小动物们说,这片无尽的森林,是蘑菇仙子的,每当月光皎洁之时,森林里的动物们、植物们,就会换上银色的衣裳,参加蘑菇仙子举办的音乐舞会。
父亲会不会是去参加音乐舞会?
父亲身体不好,经常咳嗽,三十八岁的他,面容枯瘦,人们预测,他活不了多久。我们家曾卖掉一头母牛,把他送出山外就医,他从山外回来后,咳得更加厉害,有几次还咳出了血。我的母亲是一位裁缝,她在另一块土里,种了许多麻,根据不同的季节,为我们织麻缝衣,有时,她也把山里的花草和云朵采来,在衣裳上染成精致的图案,被时间磨得破损的田园,在母亲纯熟的手艺下,也会用炊烟把它缝补得贴贴实实。
有一天,父亲与母亲商量,决定带我到森林里走走。这是我多年的愿望,一想到要见到蘑菇仙子了,我的心就激动得怦怦跳。
那天,父亲刮掉了他蓄留已久的胡茬儿,在梳子上沾了些清水,把头发梳得整洁、光亮,他穿着一件青色的中山装、一双反光皮鞋,从母亲手里接过沉甸甸的行李,与母亲对视三秒后,牵着我的手,对母亲说:
“我走了。”
母亲咬着嘴皮,眼里闪着泪花。我不知道,那天母亲为什么悲伤,父亲要领着他的儿子到森林里参观,这是一件多荣耀的事,我不知道,那天母亲为什么会穿一件白色的衣服,白得像午后的云一样,刺着我的眼睛。可现在是黎明,薄雾笼罩着我们,我们拨开它,走了十几米,母亲在后面唤我的名字,我回过头,看见她微笑着向我挥了挥手,薄雾像蚕丝一样把她束住,她像一只白色的蝴蝶,欲挣扎着飞舞起来,她努力了那么几次,始终站在原地,我看见,她伸手抹了抹眼泪,可她还是微笑着向我挥了挥手。父亲呢?父亲没有回头,他牵着我的手,义无反顾地向前走。
我和父亲踩着曙光走了一里路,太阳才从森林里升起来,我们的裤腿已被露水打湿,沿路上生长着比人还高的苞谷秆,修长、宽大的叶片伸到路上,割着我们的脸。这一片庄稼地是爷爷交给父亲的,父亲已耕种了二十年,这些苞谷是父亲亲手种下的,它们生长得茂盛,到了秋天,准会有一个好收成。但是,现在,父亲却没心情关心它们,他正牵着他的儿子,一心往森林里走,金色的阳光洒在大地上,他也无心拾起一缕,他正牵着他的儿子,去会见蘑菇仙子。他儿子的心,正激动得怦怦跳,这是一个多美好的清晨啊!
我和父亲来到森林边缘,黑乎乎的森林透出一股阴冷的风,它像一头心无旁骛的野兽,在阳光的抚摸下温和地喘着气。父亲上前向它问好,它动了一下身子,风从远处滑来,吹动了我们的衣衫,它竖起耷拉着的耳朵,就这样,我和父亲钻进它的耳朵里,沿着它陡峭的耳壁,我走进向往已久的黑森林。
我们踩着一条铺满落叶的小径往前走,丛林深处突然跳出一只狸子,皮毛黑白相间,眼睛圆得像两颗珠子,它挡在我们面前,我以为它会攻击我们,它站立起来,向我们敬了一个礼,父亲给它招了招手,它兴奋地跑到父亲跟前,不断用前爪子挠着脖子,父亲蹲下身子,从行李里取出一些食物,它捧着我们的食物,一溜烟就消失了。
这条小径很长很长,也不知走了多久,我走累了,父亲就把我扛在肩上。我骑着父亲的脖子,像骑着一匹青色的马驹在森林里畅行,阳光透进森林,小径两旁的草木伸展着身子,抖落一些鸟语,我闻到一股草莓的香味,持久而诱人,父亲说:“这就是鸟语的味道。在这片森林之外,是没有人能闻到它的。”父亲让我用心去感受,我微闭上眼睛,任草莓的香味浸湿我的脸庞,这草莓的香味,有偏向于巧克力味的、有偏向于牛奶味的,有偏向于柠檬味的、还有偏向于樱桃味的,想不到,森林里的鸟语是如此的诱人。
我们正说着话,一只蓝色的鸟飞停在我的手臂上,它向我点了点头,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它的羽毛蓝得发亮,好像无数蓝色的天空叠加在一起,才能调出这种充满魔力的蓝。我屏住呼吸,生怕打扰它,父亲察觉到了我的心思,从口中吹出一声明亮的口哨,蓝色的鸟并没有飞走,相反,它跟着父亲的口哨,唱起了歌。
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一座小木屋前,父亲把我从肩上放下,他熟悉地推开了门,我以为里面会有一些让我惊奇的东西,比如会住着一位老婆婆或者小鹿,也比如会堆满闪闪发光的果实,但除了几张凳子,什么也没有,我与父亲坐下来休息,我问父亲: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蘑菇仙子?”
父亲说:“快了。”
这时,我发现,自从我们进入森林后,父亲没有咳嗽过一声,他的脸色也有了红光,整个人看上去无比精神。我们在小木屋里简单吃过一些干粮后,父亲对我说:
“路还很长,我们需要在小木屋睡一个午觉再启程。”
我急于会见蘑菇仙子,对父亲的安排表示不满,我噘起嘴,坐在一旁默默生气。父亲走进丛林,没几分钟,摘来了一张宽大的树叶,这树叶足有一米多宽,上面铺满绒绒的毛,摸上去很柔和,父亲把它盖在我身上,抚摸着我的头,说:
“睡吧!睡吧!我会守护在你身边的。”
下午,我们在森林里遇见了母亲,她依旧穿着那件白色的衣服,手腕上挎着一个篮子。她扇动着翅膀,飞舞到我身边,她真的变成了一只蝴蝶,优雅美丽。我非常惊讶,母亲为什么会在这儿,我问母亲:
“妈妈!你不是在家里吗?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母亲笑了笑,说:“傻孩子!我来森林里采点野果,给你们准备晚餐啊。”
母亲给父亲理了理散乱的衣领,与父亲对视了三秒后,对他说:“放心去吧!去吧!”
父亲紧握着母亲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母亲解开他干枯的手指,突然变得忧伤起来:
“去吧!别让孩子失望。”
母亲篮子里的野果,正在发光,它那件白色的衣服,在黑森林里显得耀眼。三十八岁的父亲再次牵着我,告别母亲,向着森林更深处走去。我们走了十多米,我回过头看母亲,发现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衰老。父亲呢?父亲依然没有回头,他牵着我的手,义无反顾地向前走。
我们经过一个湖泊,湖泊周边开满鲜花,湖水绿绿的,散发着乳香。我想在这儿玩一会儿,父亲便停了下来,他坐在一块岩石上,看着我跑进了花丛中。这些花,与我在森林外见到的不一样,没有根,没有叶,悬在空中,花瓣呈不同的几何图形,有三角形、长方形、扇形、圆形,五光十色,花瓣硕大,花瓣中心不是花蕊,而是糖果。
我捧着一朵花的脸庞,问它:“您好!您叫什么名字呀?”
它摇晃着脑袋,从花瓣间发出了细微的声音。我兴奋地向父亲招了招手,此时,我看见,父亲已脱光衣服,一头扎进湖里,他像一条鱼,在湖里自如地游着,我也脱掉衣服,跳进湖里,跟在父亲的后面游了起来。我们游累了,就坐回湖边休息,我看见,父亲的身子瘦得皮包骨,没有一点肌肉,我伸手去抚摸他的背脊,冰凉凉的,没有一点温度。我的鼻子酸酸的,忍不住抽泣起来,父亲一把把我搂在怀里,阳光从树枝间透下来,照射在我们赤裸的身上。
黄昏,我们终于在一个宽大的树洞里见到了蘑菇仙子,她穿着一件彩色花斑的裙子、一双水晶鞋,头上戴着一顶花冠,说话带着回音。蘑菇仙子招呼我们坐下,几朵小蘑菇随即给我们端来牛奶和点心。蘑菇仙子说:
“吃吧,吃吧!你们父子俩是森林尊贵的客人,只有你们才能走进它,也只有你们才能见到我。”
蘑菇仙子轻轻挥了一下手,灰暗的树洞立刻变得富丽堂皇,此刻,月光也从窗外透了进来,蘑菇仙子领着我们走出树洞,先让我们参观森林里的月光,然后再回洞里参加音乐舞会。
森林里四处闪着银光,仿佛黎明的雪景。月光在空中飞旋,一片一片,轻盈、柔和,月光堆积在树枝上,又从树枝上悄无声息滑下,月光包裹着我和父亲,我看见父亲笑了,笑得那么幸福。森林里的石头像一颗颗星辰,不断眨着眼睛,鸟儿们唱出的歌声,也是银色的,野兽们的脚步声,也是银色的。动物、植物,从四面八方起来,蘑菇仙子举办的每一场音乐舞会,它们都不会缺席。
音乐舞会上,蘑菇仙子作了简短的致辞,并向所有动物、植物们介绍了我和父亲,它们纷纷给我们分享了自己的礼物,我和父亲被一群小蘑菇拉着到了舞池中央,大家围着我们唱起了歌,跳起了舞:
尊贵的人类朋友,欢迎您来到黑森林
黑森林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你们的家园
如果哪天您丢失了它
请在月光中呼唤它的名字,它就会归来
歌声好像不是从它们口中发出,而是从树洞的每一个细胞里发出,立体、悦耳。它们跳着跳着,就在空中飞舞起来,我和父亲也跟着失去重心飘到了空中,这么奇妙啊,任凭我怎样蹲脚,身子都不会往下坠。我们在空中飞舞了一会儿,蘑菇仙子就站在舞台上唱起了歌,一时间,她的歌唱把所有事物凝固住了,时间仿佛停了下来,只有那声音,悠扬、缥缈,好像来自遥远的未知地,干净而透彻,我和父亲,动物、植物们的心灵受到了一场洗礼。
舞会结束后,动物、植物们纷纷散去,但月光仍旧洒在森林里,它会为它们照亮每一条晚归的路。我和父亲向蘑菇仙子告别,她拦住了我们,盛情地说:
“树洞的深处,就是这片森林的心脏,我想邀请你们前去参观。”
我和父亲欣然点了点头,蘑菇仙子领着我们,在树洞里打开一扇隐蔽的门,沿着一条窄小的、幽深的小道往里走,我们走着走着,看见前面闪着光亮,再往前走,才发现这条小道由白色的水晶铺就,小道两旁,生长着的是粉色的、蓝色的、紫色的水晶,我伸手抚摸着它们,它们冰凉中带着湿润,沁人心脾,蘑菇仙子告诉我们:“这些水晶,都是森林的精气。”
小道尽头,是一个宽敞的大厅,大厅里也全是水晶,比小道两旁生长的水晶更巨大、通透,我们仿佛来到了一个透明的世界,感觉身子也如水晶一样,是那样透明、干净。透明的父亲牵着透明的我,在蘑菇仙子的指引下,沿着几级水晶台阶,走向大厅中央的平台上,那里矗立着一块白色的水晶,光照进它里面,立刻变成了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迷幻动人,蘑菇仙子介绍说:“这块水晶,是众晶之首,森林之魂。你们可走进它里面,也可从它里面走出来。”
我看了一下父亲,他对我点了点头,默许我的冲动,我走进那块水晶,一开始,一股冰凉之气透进我身子里,让我难受,我往里走,逐渐适应它的气息,心境变得平静、辽阔,后来,我感觉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里,都闪耀着水晶之光。这无疑是一次愉悦的旅行,我从水晶里走出来后,把这微妙的感觉告诉父亲,在蘑菇仙子的鼓励下,父亲也决定试一试。我站在水晶前,看见三十八岁的父亲走进水晶,他走进水晶后,立刻变成了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一分钟时间,色谱消失,父亲仿佛被水晶融化了一样,我只看到无边的透明,看不见父亲的身影。
我在水晶前,等了许久,也没有等到父亲归来,我无比悲伤,蘑菇仙子告诉我,父亲去了他想去的世界,她抚摸着我的头,慈祥地说:“孩子!你该回去了。”
我在小木屋里醒来后,身边空无一人,月光给森林镀上了一层轻缈的银,我喊了几声“爸爸”,没有应答,方知是梦一场。我的悲伤,像树叶腐蚀的气息一样,在森林里漂浮着。我准备沿父亲领我走过的路返回家里,我走啊走啊,也不知这条路有多长,我的脚掌磨起了血泡,我的衣衫被荆棘扯得褴褛,我的下巴被风吹出了胡须,我带着孤独勇敢地走着,当我走出森林,映入我眼帘的不再是那个偏僻、寂寥的深山,也不再是那个炊烟袅袅、牛欢狗吠的人间。
这是一个民房杂乱、街道堆满垃圾的小镇,窗口里透出的灯火,想努力把它擦亮,可它却陷进了废墟一样黑夜,无法自拔。这一条回家之路,我走了二十九年,现在,三十八岁的我,弄丢了三十八岁的父亲,我不知该以怎样的身份,去面对这个居心叵测的世界。
这些年,我没找到一条与世界对话的途径。
人往往就是这样,如果这世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样子,我们宁愿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与它交流、融合。显然,我的这种推理,是不适合用在孩子身上的。我的孩子叫小宝,六岁了,他在三岁的时候,某一天突然变得沉默起来,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不愿与人交流,语言表达能力出现退化现象,后来,他干脆不说话了。三年来,他没喊过我一声爸爸,偶尔从他的嘴里冒出几句含混不清的词,很难猜测出他想表达什么,他的性格越来越孤僻,拒绝与小朋友们玩,见到陌生人瞳孔放大、表情恐慌,他总一个人呆呆地躲在角落里,一待就是大半天。医生说,他患上了自闭症。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或孤独性障碍,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代表性疾病。全国有近一千万自闭症患者,他们仅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人发着暗淡的光,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
我不知道小宝来自哪一颗星辰。
现在,小宝就躺在我怀里,他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我伸手关掉空调,拉上车窗帘子,以免阳光照射着他,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它有着节制的时速和清晰的目标,而我身心疲惫、目光漂浮,车厢里陌生的人们,微闭着眼,佯装小睡,他们各怀心事,难以与外人诉说心中悲喜,而那些一闪而过的青山或白云,与车窗对立,不知与我们多少逝去的日子有关。
这是我第五次带小宝来重庆,从我居住的小镇到重庆,要坐六个小时的大巴车,车到沙坪坝长途汽车站,已是下午两点,我摇醒了小宝,他面无表情地睁开眼睛,不哭不闹,表现得顺从,我背上行李,牵着他的手,走下了车。夏日的重庆,闷热得像一个大蒸笼,没有一丝凉风。我牵着小宝,沿一条宽阔的大街向前行走,流水般的车辆在热气里穿梭,流水般的车辆,更像一群蚂蚁在热锅上爬行,忙碌而急躁,根本不理会路边一位三十八岁父亲的酸甜苦辣,也不理会一位六岁孩童的孤独。我买了一瓶冰冻的矿泉水,给小宝喝了一点,我们走到了一家小旅馆——宾归旅社,前四次,就住在这里,老板还记得我,简单问候了一声,付了八十元,办理了入住手续。
房间窄小而潮湿,散发着一股霉味,小宝坐在床上,呆呆地望着泛黄的天花板,我打了一盆清水,从行李包里取出毛巾,给他擦拭身子,我说:
“小宝好乖,左洗洗,右洗洗,上洗洗,下洗洗,凉快好休息。”
小宝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他还在看天花板,对我来说,那块天花板枯燥无奇,也许,小宝从中看到了一个五彩纷呈的世界,所以,他看得那样入迷。我试图从小宝的视觉,去观察那块陈旧的天花板,那些泛黄的斑痕,是岁月留下的印迹,有几处,由于受潮,瓷粉已剥落了些许。这块天花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悬浮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它忍受了繁华,更忍受了孤寂,难道,它不厌倦自己的使命吗,也许,它本身就没有使命,只有状态,那就是悬浮。
我艰难地从这块天花板幻生的景象,进入小宝的心境。小宝啊,你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洗漱完毕,我掏出手机,打开APP,再次检查所挂的西南医院儿童精神科陈医生的专家号,这是明天上午的号,一个星期前预约的,自从三年前采用陈医生的治疗方案后,每半年,小宝都要来复查一次。这三年,为了小宝,我拒绝了所有饭局,放弃了热爱的写作,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他身上,作为父亲,哪怕前方荆棘遍布,如果没有工具,我也要用身子为他开辟一条行走的小路,我希望我的孩子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抵达的不是悬崖,而是花园。
我希望小宝内心里的那颗星辰,是有温度的。
晚餐时,我带小宝到旅馆隔壁的餐馆里吃小笼包,他对食物从不挑剔,给什么他就吃什么,他对我表达意见时,会用手作简单的比画,三年时间,我已适应了他自创的手语,这是父亲与儿子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晚上睡觉,小宝有自己专用的小毛毯,这条小毛毯用了多年,已经很陈旧了,但他只需要它,没有它,晚上他就拒绝睡觉,一个人站到墙壁前赌气,重新换一条一模一样的也不行,好像这条小毛毯会散发出独特的气息,这气息让他无比信任。
第二天早晨,我带着小宝到医院排队,在上卫生间时,我让他站在门边,不准乱动,当然,不用叮嘱,在陌生的环境中,他也不会乱跑,我以为只要他在我的视线内就没有问题,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当我推开卫生间的门时,已看不到他,我急得四处寻找,呼喊着他的名字。我大脑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他被人贩子抱走了,我寻求到医院保安的帮助,他们热心地参与了搜寻。最后,还是保洁阿姨在打扫卫生间时,在卫生间的另一个隔间里,发现了呆呆站着的小宝,这一场虚惊差点夺走了我的魂,我紧紧搂着他,五味杂陈,眼眶里溢出了一个三十八岁男人坚强的泪水。
陈医生对小宝的状态很乐观,对自闭症的治疗,除按疗程进行药物治疗外,行为心理治疗及特殊教育也很重要,陈医生建议我加入了语言训练、游戏训练及增强物的使用。行为心理治疗及特殊教育主要靠父母平时潜移默化的植入,对于自闭症,一百个好医生不如一个好家长,陈医生说:
“再坚持三年,我相信他会有很大的改观,继续努力。”
我说:“只要孩子有希望,别说三年,三十年我也坚持。”
陈医生给小宝开了处方单,我接过单子后,向他深深鞠了一个躬,他站了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投出信任的目光。
医院里,人潮涌动,人们进进出出,悲欣交集,人间太苦,但从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这种苦而放弃它,他们还是那样热爱它。就像我爱着我的小宝,这种爱来源于生命——卑微而坚定。
小镇后面的林场,是我们县最大的国有林场,栽种的多是杉树。十年前,林场发生了一次特大火灾,连烧了七天七夜,几乎烧掉了它的三分之二,在这场火灾中,牺牲了三名消防人员和两名当地群众。林场边上有一片坟地,父亲就葬在那儿,火灾原因是那年清明,一户人家在坟地里放火炮引发了山火,那次火灾,彻底烧毁了我童年时漫长而温馨的梦。
火灾过后,山坡一片漆黑,东倒西歪的树干,像一截截未完全火化的骨头,它们卑微地呈现在风雨下,任人们说三道四。我所梦到过的蘑菇仙子,我所梦到过的音乐舞会,我所梦到过的七彩水晶,我所梦到过的父亲,是时间与意念所生出的幻境吗?当森林被掳走后,剩下的只是一片残酷的废墟及平凡的现实。那是一片可通往过去的森林,当它被烧毁后,我的记忆开始变得混乱,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我美好的童年,我消失在水晶里的父亲的爱。
当我向往的美好的世界,如森林一样灰飞烟灭,我们——也许会关掉身上的每一个窗口,拒绝世界这突如其来的另一张面孔。我们也会变得孤独,变得自闭,并以旷日持久的姿势,去对峙、对抗无所适从的一切。只有感同身受,才能与小宝站在同一条线上,让他放弃戒备,带领着他,沿一条铺满落叶的小径,走向我所憧憬的黑森林,寻找那遗失的快乐和透明的水晶。
从重庆回来后,我给小宝拟订了训练计划,每天晚上进行十分钟声音训练、半个小时游戏训练、十分钟增强物训练,每个星期,带他去一次儿童乐园。
为培养小宝的注意力,我以他喜爱的玩具木槌作为增强物,不同方向、不同速度移动木槌,吸引他的目光,然后,让他对视我的眼睛,我才把木槌给他玩。接下来进行单音和单词的训练,为了让他注意我的发音特征,我每发一个音,都尽量做到表情丰富,嘴型夸张,我们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会跟着我正确发出“a”“o”两个单音了。每一段时间的游戏训练,我变化着花样与他一起玩,我们玩挑豆子游戏时,我在盘中倒满黄豆,加入少许花豆,我和小宝从黄豆里把花豆一粒一粒找出来;我们玩五官游戏时,我面对小宝,一边说“眼睛”“鼻子”“嘴巴”“耳朵”,一边触摸自己五官相应部位,让小宝模仿着做,比一比谁正确、速度快。有时,我还给小宝读故事书,虽然他不感兴趣,但我也坚持读,一个故事,读十遍,读一百遍,读得多了,这个故事就潜意识地成了他内心世界所知晓的一部分。
每个星期去一次儿童乐园,主要是想让他多与同龄小朋友接触,学习与人交往。有一次,在儿童乐园,他正在玩皮球,一位调皮的小朋友跑过来抢了他的皮球,还打了他一巴掌,他呆呆站着,我看到了他的无助与麻木,心里很痛。小孩子间打闹,本是寻常之事,但对我来说,事态非常严重,他自我的保护意识,会因为这次经历让他把刚打开一个缝的心扉重新关闭。我只得找到那位小朋友的母亲,苦口婆心向她说明情况,并请求她帮忙,让小朋友给小宝道歉。
每一步,我都走得很小心;每一步,我都走得很辛苦。
我对父亲的记忆其实很少,只记得他是林场里的工人,常拿着一只烟斗,吧嗒吧嗒地抽个不停。我九岁的时候,发了一次高烧,烧到四十度,持续不退,他背着我穿过那片林场,走了两小时山路,到县城去看病。我患的是脑膜炎,医生说,要是再晚半天,我连小命也保不住,医好了,也会留下后遗症。
那时,我的父亲背着我,走一步咳三声,他的肺痨已到了晚期,医生劝他住院,他自感时日不多,背着病愈的我悄悄溜了。父亲以为我长大后会变成一个傻子,但他没有机会看到我长大,就在那年冬天,当他从喉头里咳出最后一口血时,他的生命定格在了三十八岁。
我想,我应该带着小宝,去拜访一下父亲。
秋阳高照,我牵着小宝的手,走过金黄的田野,向着那片黑漆漆的废墟走去。年迈的母亲拄着一根木棍子,跟在我们身后,我时常回头看看她,怕她跌倒,她总微笑着向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先走,她会慢慢赶上。
十年时间,林场也没把烧焦的山野复绿,每年都补种树苗,种一年死一年,种得人绝望。我们走到废墟边缘,远远就看见了父亲的坟头,上面生长的茅草在风中摇曳着,好像在向我们招手。
我和小宝给父亲打理了杂草,摆上供品,磕了三个头,我不知道父亲看见了吗,他曾经九岁的儿子和他儿子六岁的儿子。
“爸爸!爸爸!爸爸!”我对着坟头喊了三声,我的声音空荡荡的,心也空荡荡的。
母亲坐在坟场边的石头上,举起木棍子,敲了敲父亲坟头上的泥土,喘着气,说:
“出来晒太阳啰!”
我又想起了黑森林里的母亲,她是有机会变成蝴蝶的,但她选择了放弃。这么多年,她一直陪在我身边,以惊人的速度衰老。
哦!我失去的美丽的黑森林。在我九岁时,父亲常摸着我的头,一言不发,阳光噙在他的眼眶里,他抱紧一团团野草,若有所思、行动缓慢,这无尽的野草啊,多像他的愁绪,年复一年生长。父亲是一片黑森林吗?父爱是那一股木叶般腐蚀的清晰味儿吗?
阳光涂抹在废墟上,阳光也想把它还原成昔日繁茂的模样,阳光的努力是徒劳的,它越涂抹,废墟越苍凉。我多想牵着小宝,走进这片废墟,一直走啊走啊,走进童年的梦里,走到这片大地的心脏,那里有一块七彩水晶,人们可以自由地走进去、走出来,人们可以像水晶一样,唱着透明的歌。
一只松鼠从草丛中跑出来,跃到一块高耸的石头上,它回头调皮地看着我们,用前爪挠着自己的脸,得意洋洋的样子。小宝最先看见了它,他用手指向松鼠,嘴里发出了一句含混不清的话:
“爸爸!那——那——”
松鼠受惊,一溜烟逃走了。我紧紧搂着小宝,一粒泪水滴在了手背上,秋日的阳光走进泪水里,折射出红、橙、黄、绿、蓝、靛、紫,我的心突然被这久违的温暖触着,啊!水晶,七彩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