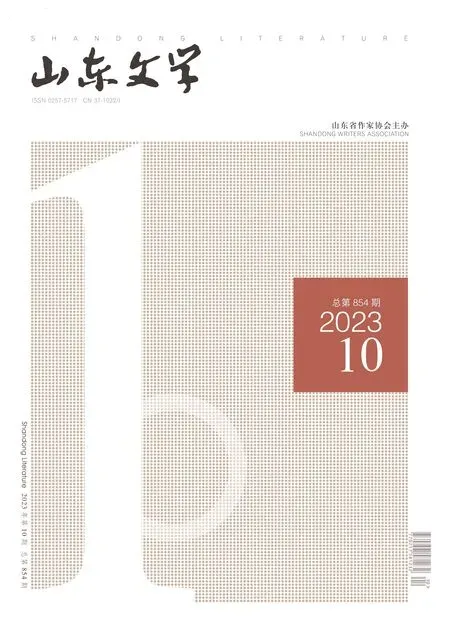你的村庄
2023-12-11陈华
陈 华
一
大黑披着第一缕光亮钻进屋子时,你已经醒了。你不睁开眼,不挪动身体,闭着眼使劲想,是董湘书还是王老四?陪你在南山坡上割了一夜麦?你想不起来,大黑却急了,潮湿的舌头小蛇般划过你干枯的面颊。你笑笑推它:去去去,跟如莲似的,见不得人多睡一会。说完这句话你瞬间愣住,不自觉朝窗外南山坡看了看。
南山坡上,睡着如莲。
是天不够亮还是眼花得更重了?你将线衣穿上又脱下来。领口紧,经验告诉你,领口紧就是穿反了。你脱下来,翻了个儿又穿上。这次不紧了。你满意地笑笑。其实,你还是穿反了,本该贴身的衣缝裸在外面。这也没什么关系,你还要穿一件外套。就是不穿外套又有什么关系呢?没人看。
你穿好衣服推开门,一边将几根木头绊子塞进怀里一边扭头朝东边院子叫:湘书,起了,该割麦了。抱着柴又扭头朝西院叫:老四,起了,割麦去。走到门口你不放心似的顿住脚,仰起头又叫:今天谁帮我割麦,杀只牡丹红!这句话用了力,震得外套几乎在肩头挂不住,你耸耸肩朝里抗了抗。大公鸡似乎听懂了你的话,探头探脑看了两眼你的背影,喉间发出几声咕哝,顶着肥硕的红冠子跑开了。
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雪。萧条枝影月牙照人眠,小伙赶马车,手里攥长鞭。西北风吹过他通红的脸……你唱着歌,将一缕炊烟送进烟囱,合着你的旋律,烟囱将炊烟送进村庄。
村庄醒了。
大黑一直不错眼珠地盯着你,你将一块咸肉切碎扔进铁锅时,大黑的涎水亮晶晶地拖到地上。该弄些豆浆。你这样想。你打开橱柜取出九阳豆浆机。你将珍珠般的豆子洗了又洗,将它们一粒一粒地揉搓,让它们从你的指缝间滑进水里,又将那几粒跳出去的捉回来,都放进豆浆机。你拿电插头的手却定格在插座边。你忘记了一件事,电早就断了。不光是豆浆机,电饭锅、冰箱、洗衣机、头顶的电灯……都变成了聋子的耳朵了。
最近你总爱忘事。
今春女儿拉着你的胳膊苦苦哀求:爸,别回去了,好好地在我和哥身边安享晚年不好么?女儿贴心贴肺,不像粗枝大叶的儿子,说话像冲天炮:爸,不许回去,从前你说回去陪四爹,现在四爹也走了,就剩你一个人,还回去干嘛?你浑浊的眼神凛冽地掠过儿子。儿子不看你,又说:我就搞不明白,那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哪儿勾了你的魂?儿媳推了一把儿子:咋跟爸说话!故土难离嘛!儿子倔强地一仰头,将眼角的晶莹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坐上车,女儿往你口袋里塞钱。开车的儿子虎着脸回头叫:你塞钱干啥?当手纸么?女儿缩回了拿钱的手。可不,赶花村空了,拿钱去哪买东西?步行三十里去镇上?
那天一路上儿子都虎着脸不和你说话,进了村,把后备箱里的东西扛进屋子,儿子还是没说话。他屋前屋后地砖,他看了菜园,看了高高的柴垛,又看了老压井,接着他开始压水,直到水缸满了才停住。他拿起水瓢,舀了一瓢凉水,仰起头,咕咚咕咚地灌下去。一瓢水灌完了,他的头还仰着,眼睛微闭,一脸惬意。似乎想留住那些水划过喉咙的味道,或者是感觉。谁知道呢。
真老了?你摸摸脸问自己,脸上的皮肉随着你的抚摸蠕动着,你似乎看见那些褶皱,像河水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你摇摇头,用指甲抠出没嚼烂的咸肉丢给大黑,又将盘子里的咸肉夹给大黑。大黑一块一块吞下去,你掰一块馒头送到大黑嘴边:吃口馒头,别齁着!大黑叼起馒头,象征性地嚼了两下,吐在脚下,又叼起一块咸肉。你将馒头拾起来,掰碎,倒些开水和咸肉拌在一起。一顿饭,你吃了一个馒头的四分之一,大黑吃了四分之三,还有那盘咸肉。
肋骨间的疼痛又隐隐地漫上来,你皱皱眉毛。挣扎着站起来去喂鸡,又去看空空的兔窝。小灰还没回来,跑了很多天了。你骂了句:养不熟的东西!再不回来,你就见不到我了!眼角却骂出两点晶莹,小灰调皮的身影在里面跳来跳去。
疼痛轻了些,肿胀感又强了些。
这时东方泛红。你开始磨镰刀。得趁着露珠还没被太阳晒干割麦,你这样想,拿了绳子,牵上老山羊,院门不用落锁,甚至不用关,你用脚拨了一下,院门不情愿地“嘎吱”一声,朝回弹了弹。你大声叫:湘书、老四,我先走,你们快着点!没有回应,只有矮墙那边探过头来的蒿草冲你点了点头。
你朝南山坡走去。
二
你走过荒草连天的菜园;走过你栽下的杨树林;走过二巩家;路过高老三家时你停了脚,高老三的半个老屋塌了,想是昨夜那场大风刮的。你站在那看了看,木头窗棂碎成几根木棍横在地上,上面还斑驳着些蓝油漆。房顶几棵蒿草、灰菜顶着饱满的籽,在微风里不堪重负地点着头。一只肥硕的老鼠从塌陷的老屋窜出来,朝你身后跑去。你跺跺脚:高老三,当年这个地方该是我的,你抢了去。你,就是个胡子!抢去又撂了。你看看,全村的屋都没塌,偏你的,风一吹就塌了!
你气哼哼地走了两步又回头。
高老三前几年就死了,死在城里,他也是被孝顺的儿子媳妇接走的。进了城吃好的、穿好的,就是不能乱跑。他不听话,也许是太闷了,就趁着儿子媳妇上班跑到街上,他不会看红绿灯,不知道行人该走斑马线,更不会躲避飞驰而来的汽车。
两行泪溢出你的眼眶。
一九七四年,建点设村。你赶着毛驴车,车上有一口十二印的铁锅,铁锅里装着盆盆罐罐,如莲怀里揣着你儿子坐在铁锅边,铁锅边,是两床被褥,那是你们全部家当。三十几里山路坎坷不平,从日出走到日落。
很多年后如莲对一双儿女说:越走草越深,越走林子越密,越走人烟越稀少,越走越心慌……
你从口袋里掏出老汉烟卷了一支,点上。缭绕的烟雾似乎又把你送回到遥远的岁月。你是在王老四家借住了半个月才搭好自家地窨的。
一截炕连着铁锅,睡着王老四,再加上你们俩,就只能侧着身了。
是条重情重义的好汉!你吐出一口烟,朝着北山坡望望。那里葬着王老四。
清一色山东人,只有你是镇上来的。欺生是一定的,尤其是王老四和董湘书,撇着嘴骂你:臭糜子!你当然不肯示弱,清一色穷光蛋,清一色地窨子住着,就凭口音欺负人?你吐口唾沫骂回去:山东棒子赶大车,臭糜子是你爹!董湘书就冲上来了。
那是一顿好打,谁也没占到便宜,闻声而来的如莲尖叫声唤醒了看热闹的人,也唤醒了呆若木鸡的王老四,他冲过来,提起了董湘书,扔在一边。董湘书眼睛都红了,他抹了一把嘴角的血骂道:你他妈的瞎了,帮臭糜子忙?又有新的血流出来,他骂人的时候,冒起了血泡儿,骂完了,血泡儿也“啪”地一声破了,变成一条红线,顺着董湘书的脖子流淌着。王老四不说话,瞥了一眼抽泣的如莲,头一低,走了。
那次要不是王老四拉开,你怕是要吃大亏了,你的体力,说到底还是不如山东大汉董湘书。
你们来的时候是早春,秋天到了的时候,小村就有六七十户人家了。
名字是董湘书想出来的。他说:是养蜂人的双脚先踏上这块土地的,叫赶花村吧。董湘书是养蜂人,王老四也是,高老三也是。大部分山东人都是养蜂人。你撇嘴:山东棒子向着山东棒子,取个名字都忘不了自己!这句话掉在地上,没人捡。被一阵风刮跑了。都忙着建家立业呢。
赶花村,你念了一遍这个名字,觉得还挺好听。
有了名字就该落户了,董湘书做了村长。
占地风波就是那时候开始的,当上村长的董湘书说:自己去占地方,看好了哪块就占哪块,脱坯、盖房。
你没抢过高老三,那大脚片子跑得可真快,等你到的时候他已经拿根树枝圈地了。他举着树枝对你说:冯志刚,这里是屋,三间。这里是牛棚、羊圈。这里是菜园子,对了,这里还应该有个鸡窝,狗也应该有个狗窝,挨着鸡窝。夜里黄鼠狼来偷鸡狗会叫醒我……你站在那里,随着高老三的憧憬,一个像模像样的家园立在你眼前。你头一低,另择去处了。张连友却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和高老三在你忙碌的背影里抱了个子,抱了个子也没用,高老三擦干净嘴角的血沫子,得意地占领了那块干净、朝阳、平整的地儿。
你和董湘书、王老四选了后山根儿,也不错。屋后一条河,清亮亮地耍着鱼儿。半截腐朽的老榆树插在河边,年年有吃不完的榆黄蘑。榆黄蘑的滋味儿可真鲜啊,鸡窝里掏几个鸡蛋,炒成碎儿,榆黄蘑切丁,一起炒,添汤,浇在如莲的手擀面上。那滋味!
如莲常在河边洗衣,洗完了就晒在河边的蒿草上,脸盆沉进河底,衣服干了,把手巾蒙在脸盆上,滤掉河水,盆里的鱼大的煎着吃,小的做鱼酱。
房子一栋一栋地盖起来,拳头粗的原木围个篱笆,院子里鸡鸣犬吠,热炕头上传来儿子大栓嘹亮的哭声,日子就过起来了。男人女人白天一起开荒种地,大一些的娃娃耐不住寂寞,挎着柳条筐出了门,大山总不吝啬,紫莹莹的山葡萄、红艳艳的马琳果、绿莹莹的灯笼果、山核桃、各种菌类、野菜,滋养得婆娘珠圆玉润;滋养得汉子虎背熊腰;也滋养得娃娃生龙活虎。
夜里煤油灯下女人们哄睡了娃娃就缝缝补补,你们蹲在大门外叼着旱烟说闲话,说谁和谁又抱了个子,说谁家的庄稼好,谁家的娃娃俊。当然,也说谁家婆娘夜里叫得响,谁钻了寡妇的被窝……
那是一段好日子。
你看看破败的院子,说:老三,王老四去陪你了,董湘书也去陪你了。咱们这茬人,去了很多了,你见着他们了吧?
你们可是不孤单喽!你把一声叹息扔进风里,又朝着南山坡走去。走几步,你回头,看见高老三站在那里,手里拿着树枝,说:这里是屋,三间。这里是牛棚、羊圈。这里是菜园子,对了,这里还应该有个鸡窝,狗也应该有个狗窝,挨着鸡窝。夜里黄鼠狼来偷鸡狗会叫醒我……
三
南山坡朝阳,地肥。撒啥种子就把啥长得像模像样,啥年景都丰收。现在,连天的荒草也长得肆无忌惮。只有睡着如莲的一块地还种着些麦,那是今年春天你回来撒下的种。麦挤在连天的黄草里,像浩瀚夜空里几颗寥落的星星。
哎!你又把一声长叹扔进漫山遍野的荒芜里。
你开始动手割麦。边割边跟如莲说话:大栓和可心说割完麦就接我走,不让我回来了。可心说我老了,大栓没说。如莲,城里可繁华,路灯彻夜地亮,房间里都不用点灯。街上全是汽车,大栓开上汽车了,可心也开上了。日子好了,娃娃都不种地了,都过上好日子了。
你直起腰擦把汗,将浑浊茫然的眼神扔向远方。像是问如莲,又像问自己:都不种地了,以后吃啥呢?
一阵微风吹来,麦翻起了浪花,远处的荒草也翻起了浪花。你似乎听见风中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如莲坐在孩子中间,引着孩子念: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赶花村小学是在你那三间土屋里成立的。开始你不愿意,你说:凭啥在我家?要是用,也该用你的屋,你是队长。董湘书把肩头的袄往里抗了抗,往你家门框上一靠:我家?我老爹老娘送你家来?你又说:如莲还要出工挣工分呢。董湘书身子矮了下去,坐在门槛上。他掏出纸烟卷起来:娃娃都这么大了,有几个都过了入学的年纪。村里就两个初中毕业生,我还得当队长。如莲不干谁干?
三间土屋腾出一间,树墩子上面横一块白木板,就成了。如莲认了真,她是个干啥都认真的人。隔日就从镇上背回来一捆书,贴着大门立一块窄木板,上面用墨汁写着:赶花村小学。
娃娃们都来了,读书声响起来了。屋子里黑压压一片小脑袋,门也被堵死了,挤得如莲没处下脚。下课了,如莲就从窗子里跳出来,敲响挂在大门口的瓦片。敲完了就跑回去,一个一个把娃娃抱出来。上课了,她又去敲瓦片,再把娃娃一个一个地送进窗子,自己再跳进去。
一年后,赶花村小学盖好了。六间房,一个大操场。操场中间有根杨木杆,杆上挑着如莲做的五星红旗。娃娃仰着头看着五星红旗行队礼,五星红旗哗啦啦地飘扬,娃娃胸前的红领巾哗啦啦地飘扬。真美。
那时候娃娃苦,一个本,正面写满了写反面,铅笔写过了钢笔再写。把本都写烂了。如莲教得认真,娃娃学得也认真。年年统考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一拨一拨的娃娃走出大山考上了镇上的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有了知识的娃娃眼界宽了,能耐大了。
可是赶花村还那么小。
哎!如莲,你要是不当老师就好了。不让娃娃学那么多文化,说不定赶花村还有人愿意留下来。你说。
弯下腰割麦,你将绳子铺在一块大石头上,割好的麦码在上面,用绳子捆好,扛在肩头。你趔趄着朝村里走去,这一刻你仿佛回到了从前,那时候啥也没有,也是这样肩扛手提,日子却沸腾着。
这些麦你扛回去,用石磙子碾出来。碾出来有啥用呢,没有磨坊了。去年的麦还在仓房里呢,一部分喂了鸡,还有一部分喂了老鼠。你还是佝偻着腰身背起了麦,步履蹒跚地朝家里走去。春种秋收,庄户人的本分,庄稼熟了哪有不收回家的道理?
上午背了两趟麦,中午你煮了一包方便面,那是可心来看你时买的,一箱子。还有很多吃食,袋装面片、挂面,以及各种真空包装的食品,你没打开,也不爱吃。你还是愿意自己和面蒸馒头吃,大黑也爱吃。挑起一筷子面你才想起来:咋没卧个鸡蛋呢。橱柜里鸡蛋都攒了一筐了。等大栓来拉回去给孙孙吃。你这样想。嘴角泛起一丝笑意。你呼啦呼啦吃着面,大黑趴在你对面,眼巴巴地看,它边儿上,半盆咸肉拌馒头冷在那里。你边吃面边训斥大黑:你别盯着我,吃你自己的,我这里没肉。
四
吃完面,你把背回来的麦铺在院子里。忽然觉得有些疲惫,就歇在门槛上。你似乎又看见了王老四年轻的时候,那时他叫王四。他是个光棍。谁也不知道他为啥打了一辈子光棍。可你知道。你见过王四偷眼看如莲时的眼神,痴痴的。王四变成王老四躺在北山坡后,夜里入了你的梦。他说:你呀,亏咱俩是一世的好兄弟。一辈子小心眼,都到了这边了,还让如莲离我那么远。你在他健壮的胸前捶了一拳:兄弟是兄弟。如莲是我的女人,哪一世你都得离她远远的!
你给王四介绍过好几个女人,介绍得有些迫不及待,王四却像个被雨水泡湿了的榆木疙瘩,燃不起一丝光亮。那次喝醉酒,你僵着舌头说:四儿,你找一个结婚吧,生个一儿半女,就是一家人。王四那天喝多了,第一次和你瞪了眼:我就是不想娶,咋了?不是心坎上的,不是看得下的就不娶!你个死榆木疙瘩!你给了他一拳,他薅着脖领子把你撂倒,四角炕桌被你们压在身下。
这一辈子,你们抱了多少回个子?谁记得清呢。
别人家的女人再好也是别人家的!你揉着乌青的眼眶吼道!王四喘着粗气压低了声音吼:那我就看着,看一辈子!
王四把自己看成了王老四,在赶花村无亲无故。他的后事,是你料理的。你把他葬在北山坡,和如莲隔着赶花村,和村中间那条街。
一丝疼痛唤醒了你。这一歇,就把太阳歇进西山了,你睁开眼,用手遮着傍晚的霞光,眯缝着眼看了看。又该做饭了。一日三餐,哪一餐你也吃不了几口,但是每一餐都做。房子里得有烟火气,就像村子不能没有炊烟。
你从高高的柴垛上抽出几根绊子夹在腋下,一会儿,红砖瓦房上缭绕起炊烟,那是一股灰白色的炊烟,从高高的红砖烟囱里挤出来。缭绕在赶花村上空。
你烧了些开水,趁着烧开水的当儿,你在院角随手摘了一把豆角。你将豆角择好、洗净,扔进铁锅,香味飘出来。大黑摆着尾巴在你脚下蹭来蹭去。你将最后一个馒头扔在箅帘子上。想:明早发面,又该蒸馒头了。
你擦了一把手,太阳就暗下去了。你打开抽屉去摸蜡烛,蜡烛没摸到,却摸到了几个冰凉的充电宝,你一惊,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又把手伸进抽屉。
一个人的日子过得糊涂。墙上的日历很久撕一次,戴上老花镜,对照着手机屏幕上的日期,一次撕下很多页。女儿半个月开着车从城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把几个充满电的充电宝带回来,再把你空了的充电宝带走。
那是一款老年机,大屏幕。你按了按,黑屏。你赶紧抓起一个充电宝插上,开了机。星期天,这三个字直接闯进你眼帘。你“哎呦”一声转头就朝外跑。你得跑过烟地、穿过荒芜的菜园,走过后山根小桥,爬上后山坡,那里有信号。
每个星期天中午十二点,这是和儿子女儿约好的。
你往外跑的时候被门框绊了一下,跑到院子里被晒着的麦稞又拌了一下。你踉跄着跑,大黑跟着你跑起来,它比你跑得快,跑远了看看你又转回头来迎你,你差点又被大黑撞倒。过桥时你喘不过来气了,你站在桥边深深地喘过几口粗气,揉揉眼睛看了看小桥,揣着突突乱跳的心脏走过去。
山爬不动了,你吃力地拽着树枝和蒿草一步一步挪上去。
到了平时坐着打电话的那块石头了,你认得它,从前想坐在上面打电话得排队,现在不用了,你一只手拄着旁边的小树,重重地坐下去。你的手朝衣袋掏去。
是的,你没拿电话。匆忙中你“哎呦”了一声,你拍了一下后脑勺,就是因为拍后脑勺,你把正充电的手机放在了桌子上。你的另一只手拄着桌角。你越来越依附什么东西站立,这一点,你自己没有察觉。
天色暗下来了。你想过跑回去拿手机,可是你跳得喘不过气的心脏不允许了,你发抖的身体也不允许了。按照惯例,他们接不到你的电话会开车跑回来,这种事发生过。明天,他们就该来了,这一次他们一定要把你接回去了。你索性坐着,掏出用了几十年的烟荷包卷起纸烟来。
大黑歪着头看你,它在想:今天你为啥没有像以往那样托着手机说话。你舔了舔烟纸,完成了卷纸烟的最后一个程序。你摸了一下狗头,顺势将大黑揽在怀里:大黑,明天我可能就走了。孩子们对我挺宽容,让我回来再收下这一季麦。如果他们坚持,我没机会回来了。医院的检查结果我偷偷看过了,也打听过了,癌症晚期,没有多少时日了。你说到这里哽咽了,你似乎看见你离开后,变成野狗的大黑,夹着瘪瘪的肚子,在没有炊烟的村里到处乱窜。
五
你把卷好的烟叼在嘴上,打火机点着了烟,也点亮了你枯树皮般的面颊。你松开手,打火机灭了,赶花村沉进暗影里。
哪一年通上电的呢?你伸出骨节粗大的手指一节一节地数,数了半天摇摇头,又叹气。
那年高压线刚牵到赶花村口,村长董湘书就带着几个年轻后生去镇上,拉回来几捆电线和几箱子电灯泡,回村的时候是黄昏了,饭都没吃就指挥着在大队部接电灯。一村人都在煤油灯下吃饭的时候,大队部院子里像是升起了一轮满月,瞬间照亮了村子。平日里虎着脸的董湘书也不淡定了,他张开黑黢黢的大手掌夸张地遮住眼:娘咧,这么亮光以后晃坏眼可咋弄!
小村沸腾了,也不知是娃娃们尖叫的,还是婆娘们尖叫的,也许是平日里虎着脸的汉子们尖叫的。赶花村被尖叫声撑破了。
没吃完饭的端着饭碗,吃完的嘴角叼着旱烟,女人拉着孩子,老人拄着拐棍,狗顾不得吠叫,也挤在人脚下拌来拌去,都朝大队部跑来。跑近了又都被突如其来的亮光晃得眯缝着眼,不敢靠得太近,举起一只手遮住仔细地看,又不甘心,放下手,又晃得眯缝了眼。孩子跳着闹着,去追逐灯光里成群结队的飞蛾。
董湘书大手一挥:排队!都来了就发下去,不等明天了。出纳小梁负责发电灯泡,边发边问:几间屋?三个。算不算牛棚?牛棚点灯做什么?牛也照着亮吃草啊?嘚瑟的你!每个人都喜滋滋地捧着几个电灯泡转身。有人把电灯泡举起来,对着大队部的电灯仔细地看。终于看出了些倪端,就叫:队长,我这个咋和你点亮的那个不一样?咋不一样?董湘书皱着眉毛,用叼着旱烟的半张嘴问。你那个大,俺这个小。所有人都举起了电灯泡:是咧,咋小了一圈?
董湘书将手上满满一箱灯泡放在地上,从嘴角拔出烟蒂,烟蒂又将一根长长的涎水拖出来。人群里有人忍不住笑了:电灯真亮,口水都看得这么清楚。
董湘书有点不好意思,伸出大手掌将甩在下巴上的涎水擦去:不一样就对了!这可是二百瓦!你家里点上这个,收电费的时候你不哭才怪!
几天的工夫,整个小村都亮了。
录音机来了。年轻人在灯影里扭起了屁股。老人撇着嘴说:张狂!
电视机也来了,人们不再对田埂上那块白布上的人影欣喜若狂,嘴角闪一丝不屑:有啥好看的,今晚有《篱笆女人和狗》,我一集都没落下。刚结婚的出纳小梁搬回来第一台电视,董湘书家第二台。为了一双儿女去董湘书家看电视,你还请董湘书喝了一次酒。那次,可是杀了一只下蛋的母鸡呢,再去看电视,全家都有了底气。理所当然地挤过人群在炕沿上落座。
通了电,有了孩子们琅琅读书声,每逢星期天大集还有镇上开来的大巴车,女人们早上提着一筐山货挤上大巴,晚上提回来几尺花布、几块肥皂、酱油、盐、醋,还有孩子眼巴巴望着的芝麻糖烧饼、甜麻花……
烟头烫疼了你的手,你手一抖将烟蒂扔出去,那点火光落尽草丛就不见了。赶花村又黑了。你吃力地站起来朝家里走去。
锅里的豆角烧焦了,箅帘子上的馒头也烤出一层硬壳。你叹了口气,拿起馒头看了看,随手一丢,大黑不嫌,叼上就跑。
疲惫感涌上来,疼痛越来越强烈,身上的力气却在减少。有时候觉得呼吸都累。你想再做点什么吃,胃里却满了。
蜡烛在夜色中摇曳着。落满灰尘的电视机暗影随着烛光摇曳,你戴上老花镜,把墙上的日历牌拿下来,对照着手机上的日期一页一页地撕。撕掉的日历有一沓,你折好,又撕成卷烟纸的样子,整齐地叠好,大黑盯着你的手,尾巴不时地摇摆着,你对大黑晃一下,说:馋狗!揣进口袋。你给自己沏了一壶浓浓的茉莉花茶。电视机是平面直角彩色的,哪一年买的呢?记不得了。断电后,你让孩子搬进城,孩子不搬。撇着嘴说:爸,你这些早该淘汰的老古董我们用不上。现在的电视薄得像纸片,贴在墙上。不仅是电视、洗衣机,冰柜、电饭锅……孩子们都不要。
你又卷上一根烟。
六
太阳循规蹈矩地跳出东山,你在晨曦中醒来。你和每天一样,抓起线衣穿起来,这一次,穿对了。
你照常去院子拿几块绊子,你又用一缕炊烟唤醒赶花村。馒头吃没了,你和了一块面,开始烙葱油饼。如莲葱油饼烙得好,你一辈子都没吃够,不仅是葱油饼,如莲的手擀面、饺子,甚至炒菜,都是出了名的好。你是在如莲去世后学着做这些的。
这一算,如莲走了十多年了。
烙完饼,你又做了西红柿蛋花汤。你还是了解自己的,那香酥的葱油饼,你嚼不动也咽不下。你将香喷喷的饼掰碎,扔进蛋花汤,泡软了,你端起碗喝起来。
你拿上镰刀、绳子,又朝怀里塞进两张包好的葱油饼,出了房门你朝东院喊:湘书,割麦了。然后又朝西院喊:老四,割麦了。说完你踩着铺了一院子的麦走出大门。你没有理会叽叽喳喳来偷嘴的麻雀。
你没急着朝南山坡走,你走上村中间的路,朝东走去。你路过很多人家,很多人家院里、屋里的人和事儿都在你脑海中热闹着。你路过刘金宝家时停住了脚步,你似乎闻到了豆腐的香味儿。刘金宝的豆腐做得好,远近闻名。邻村做豆腐的来学过,学完了回去做,还不是这个味道。后来才知道,学问出在人家院子里的压井上,人家那井,花了大力气,一百五十米深呢。
你多爱吃刘金宝做的豆腐啊,你把热腾腾颤巍巍的豆腐装进盘子,从菜园子里摘两个辣椒,和蒜瓣一起用蒜臼子捣烂,加一点碎盐,浇在豆腐上,那鲜嫩的滋味,让你的胃一整天都满满的,干活有使不完的力气。
刘金宝做的豆腐脑也好吃,尤其浇上如莲的榆黄蘑卤,含在嘴里都舍不得咽下去。刘金宝做的干豆腐也好吃,纸一般薄的干豆腐切成丝,也用辣椒炒,唇齿间的豆香千回百转。
一条浅浅的溪流挡住了你,到村口了。从前王云香总站在这里朝村外望,她男人在镇上蹲市场,卖烟叶很久不回来一次。家里没男人,女人的心就在路上了,后来村里几个光棍汉经常帮着王云香担水、劈柴,甚至春种秋收。就连董湘书也在自家婆娘看不见的地方照顾王云香孤儿寡母。有了大家的照顾,王云香就不去村口张望了。她变得开朗、漂亮起来。
只是茶余饭后村人再提起王云香,就撇嘴了。
你折回头又朝村西走去,你路过了自己家、王老四家,一直朝西走。你边走边打量路边的人家,像是一个老眼昏花的母亲打量自己的孩子。路窄了。路怎么会窄了?你疑惑着。你仔细看了看,笑了。不是路窄了,是路边的蒿草太多了,多得挤到路上了。明年,会不会都长满蒿草?你这样问自己。会。有句话说:世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如今没人走了,路也就没有了。
走到西头你又折回来,这一次,你朝南山坡走去。
你径直走到如莲坟前,将怀里的葱油饼掏出来,放在坟前的石桌上。你说:如莲,我不能来陪你了。估计今天儿子闺女就来接我了。你也别难过,用不了多久,我就去那边找你了。你边说话边用镰刀将坟墓周围的荒草又细细地割了一遍。你吓跑了一只松鼠,还有一条蛇盘在那里,挑衅般与你对峙,你绕开了它。
你站在那里,看着眼前那仅剩的一点黄色。此刻手里的镰刀仿佛一个刽子手,你抬起又慢慢放下。
那撮麦,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那条不肯逃跑的蛇一般与你对峙着,阳光插进麦秆缝儿,像是一把刀插进了你的心脏,疼得气都喘不匀了。你蹲下身子,抱住头,孩子般地呜呜哭了。
有一些声音掺和进你的哭声里,学生的读书声、一双儿女绕膝嬉笑声、如莲的歌声、刘金宝卖豆腐的吆喝声、一家家上房梁男人的号子声、雪亮的灯影里人们的尖叫声……
你在这些声音里止住了哭泣,你伸出镰刀割下那撮麦,你生命中的最后一撮麦。然后你扬起手,镰刀闪着寒光,像是一只飞倦了的老鸟,一头栽进遮天蔽日的荒芜。
村口传来汽车马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