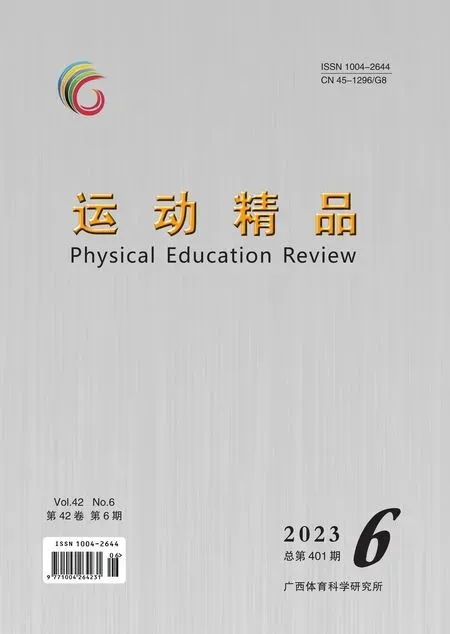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概念、影响因素及展望*
2023-12-10陈梦一祝大鹏
陈梦一 祝大鹏
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概念、影响因素及展望*
陈梦一1祝大鹏2
(1.长江大学 文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0;2.武汉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认知会受到来自内外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的概念、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指出未来可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1)促进本土化测量工具的研发,促进研究方法的综合化;(2)厘清体育道德认知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3)重视体育道德认知与不同指向的体育道德行为的关系研究;(4)重视对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的干预研究。
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行为
由于情境的特殊性,相比一般情境,运动员对于体育运动中出现的身体碰撞、故意违规等行为的容忍度更高。作为榜样人物,运动员的行为表现对于观众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会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因此,有必要厘清体育道德认知的相关研究,探讨体育道德认知的影响机制,对体育道德认知有一个更深刻透彻的认识,积极引导和规范运动员在体育运动背景下的道德认知,发挥其对个体的体育道德失范行为的约束作用,促进运动员体育道德的积极发展和个人综合素养的提升。研究对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的概念、影响因素和作用进行梳理,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促进运动员体育道德的积极发展。
1 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的概念界定
道德认知是指对道德行为的正确、善恶与否作出判断的过程,是对道德事件的认识过程。是个体进行道德判断时对依据的行为准则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1]。道德判断则是指个体运用掌握的道德概念对他人的行为结果进行判断和评价的过程[2]。关于道德认知的发展过程究竟是情绪主导还是认知推理的,主流观点是Greene[3]基于实证研究提出的道德双加工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拥有情绪与认知推理两套加工系统,当个体作出道德判断时,两套加工系统会相互竞争,不同情境下两种成分优势不一,占优势的一方将决定个体道德判断的结果。
综合以往学者的观点,可以将道德认知定义为:个体依据内在道德观念和原则,对道德事件中行为主体的关系以及处理结果时遵循的准则和规范的认识,并集中表现在道德判断上。体育道德认知是指对个体在体育背景下的行为规范和意义的认识,对体育参与主体的行为起规范作用[4]。由于体育竞赛的特殊性,运动员在体育活动中会依据适用于运动背景的行为准则对比赛中涉及的行为事件作出道德判断。基于此,研究将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定义为:运动员在参加体育活动或身处体育比赛背景下时,对处理行为事件涉及到的道德准则的认识,是一种情绪和认知驱动相互竞争的认知过程。
2 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的影响因素
通过分析以往相关研究发现,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认知往往会受到环境因素、心理机制、情境变量等因素的影响。作为体育情境下的主体,运动员在体育活动中会与不同的群体产生交互作用。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运动员的父母、教练、同伴等重要他人以及个体所处环境背景下的氛围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运动员对比赛的看法及对体育活动中的道德事件的认知过程,运动员的个体特征、人格特质的不同也会导致不同个体对体育情境下涉及的道德事件产生不同的认知,进而采取不同的行动。
2.1 环境因素
2.1.1 社会环境
第一,社会文化的变迁对运动员道德判断标准的影响。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群体可能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导致其在评价体育道德现象时有不同的观点。不同运动背景下的运动员由于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对体育道德会有不同的理解,对体育参与和自身发展之间关系的道德认识与判断也会有所区别。
第二,体育体制的变革导致运动员对道德事件的认知改变。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体育赛事的关注热度高涨,体育运动的参与规模也迅速扩张,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使得体育运动的发展模式偏向职业化和商业化。一些运动员受到高额利益的诱惑,通过使用兴奋剂或高科技仪器作弊等不正当手段来赢得比赛和荣誉,这显然违背了体育运动的初衷。体育运动背景下的道德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第三,大众传媒的推广也对运动员的道德认知有所影响。科技发展的迅猛让我们步入了“互联网+”的时代,青少年通过数字媒体能够获得大量信息,在浏览网络信息的时候了解了相关知识并形成自己的价值观。通过观看体育直播、转播中的暴力画面,个体在观察中学会了这种攻击性行为。当运动员在体育赛场中遇到类似的情境和事件时会不自觉的进行模仿,表现出攻击性行为。
2.1.2 情境变量
除了社会环境因素,重要他人和团队的氛围等社会情境变量对个体的体育道德认知会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毋庸置疑,父母对孩子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研究发现当父母采取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时,青少年的体育道德认知发展水平更高[5]。而不良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相关,不利于青少年的道德发展[6]。当父母对于孩子的期望过高时,感知到来自父母的压力可能会驱使运动员通过使用兴奋剂的方式来追求胜利[7]。
教练和队友表现出的认知及行为也会对运动员产生影响。以往研究发现不同的教练风格与运动员在体育运动背景下采取的社会性行为关系密切[8]。如果运动员感觉教练会支持他们的攻击行为时,其会做出更多的攻击行为[9]。另外当感知到队友对他人有更多欺骗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时,运动员也更可能会在体育情境下做出更多的反社会行为判断[10]。
以往研究也表明,运动员所属团队的道德气氛与其在体育情境下的道德判断、道德意图和道德行为等均存在紧密联系。感知到团队气氛较为和谐公正的运动员,在进行道德判断时也倾向于表露更多亲社会认知[11]。Steinfeldt等[12]人的研究也表明,运动员感知团队的道德氛围以及其表现出的动机氛围水平,对其在体育背景下的道德判断都有显著预测作用。
2.2 运动员自身因素
2.2.1 人口统计学变量
个体自身的特征、受教育程度、运动经验等都与其道德发展联系密切。祝大鹏等[13]的研究发现,体育专业大学生在体育情境下的道德水平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和运动项目差异。Mouratidou等[14]也发现,运动员的年龄及运动经验对其在体育情境下的道德判断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相比非职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在体育情境下的道德水平更低。邓章岩等[15]通过运用fNIRS技术探讨了篮球运动员和非运动员在完成道德两难任务时的脑区加工机制,发现大学生篮球运动员在对道德情境中的行为进行判断时,右侧DLPFC激活更强。相比非运动员,运动员在进行道德判断时会抑制情绪反应,更多采取基于功利性判断的思维方式。
2.2.2 个体特征变量
除一些基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更多研究关注运动员的个体特征变量对体育道德认知的影响。人格是指个体独有的稳定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统合模式。不同人格特质的运动员对相同的道德事件的认知和观点可能不同。在做出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之后,不同人格特质的运动员可能会有不同的心理活动及行为反应,胆汁质的运动员可能会立即道歉并接受判罚,而多血质的运动员则可能有较高的道德推脱行为,以免受到惩罚。研究表明,具有积极体育人格取向(即对体育实践高度尊重)的运动员比消极取向的运动员表现出更少的攻击性和暴力行为[16]。此外,具有不同运动动机的运动员在体育参与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任务定向动机较高的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较少表现出反社会行为。而自我定向动机较高的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表现更多的反社会行为和更少的亲社会行为[17]。
3 问题与展望
体育运动中时常发生的假摔、服用兴奋剂等不良体育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担忧,国外学者从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的视角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国内相关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完善和解决,这也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3.1 测量工具的本土化及研究方法综合化
现有关于体育道德认知的测量工具主要以国外运动员为常模编制,国内学者则经过翻译或修订后直接使用国外量表,少有针对我国运动员编制的本土化量表。祝大鹏等[13]编制的道德意向、判断和行为测量问卷通过使用体育和一般情境下的故事来分别测量个体的体育道德和一般道德,问卷施测于体育专业大学生后信效度良好,能够有效测量大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陈梦一等[5]使用该问卷的道德意向、判断部分用于测量青少年的道德认知水平,结果表明该问卷也同样可以应用于中学生。不过该问卷在运动员群体身上的信效度如何还未可知。王栋等[18]基于对高水平运动员的访谈,及对新闻媒体关于运动员道德失范行为的报道的分析,进行了质性研究并研制了运动判断材料,材料施测于运动员后信效度较好。影响体育道德认知的因素有很多,未来应加强体育道德认知测量工具的本土化研制,从前因方面对体育道德认知进行测量。
另外,目前关于体育道德认知的测量主要是心理测量的形式,这种自陈量表具有一定社会称许性,无法了解个体在进行体育道德认知判断时的脑内加工机制。关于体育道德认知方面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还较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fMRI、fNIRS、超扫描等技术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了解个体进行判断、做出决策时的脑内活动特点。未来研究应当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结合行为测量与认知神经技术,使得体育道德认知的测量更加准确和精确。
3.2 明确体育道德认知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探讨体育道德认知的前因变量,然而,不同学者研究方法不同,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差别。现有关于体育道德认知的研究主要是一些两两变量间的相关研究,实证研究和纵向研究较少。因此,未来应该多通过实证研究明确已有的前因变量对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认知的预测效应。个体成熟发展过程中道德认知发展的纵向研究也需要引起重视。有关父母教养方式、裁判员判罚等他人方面的因素以及运动员的移情、道德推脱等个体特征变量对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都会产生影响,但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此外,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多种影响因素对体育道德认知的综合影响效应,未来应该采用更复杂的模型探讨多个前因变量与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认知间的关系研究,深入探讨多个变量间的关系,促进研究的深度。除了探索体育道德认知的前因变量及作用机制,未来研究也应关注情境变量与运动员的个体特征变量间对体育道德认知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明确多方面可能影响体育道德认知的的因素,为提升我国运动员的职业道德素养提供完备的理论指导及切实的实践方针。
3.3 关注体育道德认知与不同指向的体育道德行为的关系研究
除考察前因变量外,揭示运动员在体育情境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关系研究同样重要。运动员的体育道德失范行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运动员的体育行为无法跟上其道德认知的步伐,而这对运动员体育道德水平的健康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利影响。由于新闻媒体的报道,早期研究十分重视对运动员的攻击性行为的探讨,相关研究也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研究表明,运动员体育道德判断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和更少的反社会行为[19]。Al-Yaaribi等[20]的研究则进一步区分了行为指向,研究发现运动员对队友的亲社会行为在体育情境中显著多于一般情境,而对对手的亲社会行为则在一般情境下更多,这种差异不受年龄或性别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探讨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认知对体育道德行为的影响,是否会因行为指向对象、情境变量和个体变量的不同而不同。后续研究可探讨体育道德认知与体育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通过开展广泛研究促进对体育道德认知的理解,促进运动员的知行合一,为制定相应的干预计划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3.4 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干预
研究表明,在体育运动中对对手有更多反社会行为的大学生运动员,在学校对其他学生也有更多的反社会行为,这表明个体的道德行为在不同情境下存在一致性[21]。运动员在体育情境下的道德水平引起了公众的忧虑,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体育情境下的道德认知可能会影响到运动员在一般情境下的道德认知。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干预机制,促进运动员在不同情境下道德认知的正向协同发展。
明确道德准则对运动员有警示作用。研究表明,“俱乐部有一个道德准则,规定公平竞争”,简单的一句规则也会使运动员更有可能采用更严格的准则行事,进行公平竞争,拒绝有问题的行为,这对俱乐部和比赛中的公平竞争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22]。道德价值评价较高的个体,采取的反社会行为更少[23]。重要他人的榜样作用也会影响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认知。研究发现,父母对运动员在参加比赛过程中使用兴奋剂的态度有很大的影响[24]。父母和教练对运动员自主学习的支持都有助于动机体验,而动机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运动员的道德态度[25]。未来研究在充分探讨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的影响因素,及对后续道德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之余,可进行一些干预研究,为国家运动队、省队、俱乐部等的运动员的道德认知发展提供实际的干预方案,促进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认知以及一般道德认知的正向发展。
4 结语
体育道德认知作为体育道德的重要部分,对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行为有重要影响。运动员对体育情境中的道德事件的道德认知及表现出的道德行为受到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现阶段国外关于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的研究较为广泛,国内还鲜有关于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的研究。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体育道德认知的概念内涵,制定本土化的测量工具,重视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加强综合性实证研究和纵向研究,厘清体育道德认知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探讨体育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关系,开展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干预研究,为促进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健康发展提供指导方针。
[1]Kohlberg L. Moral stages and moralization: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approach[J]. Infancia Y Aprendizaje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 Development, 1982, 5(18):33-51.
[2]曾钊新,李建华.道德心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60.
[3]Greene J.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J].Science,2001,293(5537):2105-2108.
[4]徐红萍,李江.运动员体育道德认知与体育道德行为脱节的省思[J].体育科技,2011,32(1):12-14.
[5]陈梦一,祝大鹏.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道德认知:道德完美主义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29(9):1399-1407.
[6]Morenoruiz D, Estevez E, Jimenez T I, et al. Parenting Style and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dolescent Violence: Evidence from Spai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8, 15(12): 2634-2646.
[7]Chan D K C, Hardcastle S J, Lentillon-Kaestner V, et al. Athletes' beliefs about and attitudes towards taking banned performance-enhancing substances: a qualitative study[J]. Sport Exercise & Performance Psychology, 2014, 3(4): 241-257.
[8]Hodge k, Lonsdale C.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sport: the role of coaching style, autonomous vs.controlled motivation, and moral disengagement[J].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011, 33(4):527-547.
[9]Guivernau M, Duda J D. Moral Atmosphere and Athletic Aggressive Tendencies in Young Soccer Players[J].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002, 31(1): 67-85.
[10]Malete L, Chow G M, Feltz D L. Influence of coaching efficacy and coaching competency on athlete-level moral variables in Botswana youth soccer[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3, 43(10): 2107-2119.
[11]Kavussanu M, Spray C M.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moral functioning of male youth footballers[J]. Sport Psychologist, 2006, 20(1): 1-23.
[12]Steinfeldt J A, Rutkowski L A, Vaughan E L, et al. Masculinity,moral atmosphere,and moral functioning of high school football players[J].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011, 33(2): 215-234.
[13]祝大鹏,陈明辉,叶娜.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道德与一般道德的关系研究[J].体育学刊,2019,26(5):1-6.
[14]Mouratidou K, Barkoukis V, RIZOS S. Achievement goals and moral competence in sport[J]. European Psychologist, 2012, 17(1): 34-43.
[15]邓章岩,王栋,蔡季伦,等.基于双加工理论的大学生篮球运动员道德判断:抽象推理还是情绪控制[J].科学通报,2020,65(19):2010-2020.
[16]Chantal Y, Robin P, Vernat J P, el at. Motivation, sportspersonship, and athletic aggression: A mediational analysis[J].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2005, 6(2): 233-249.
[17]Hodge K, Gucciardi D F.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Sport: The Role of Motivational Climat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Moral Disengagement[J].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015, 37(3): 257-273.
[18]王栋,陈作松.我国运动员运动道德判断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基于ERPs证据[J].中国体育科技,2020,56(11):3-12.
[19]Shields D L, Funk C D, Bredemeier B L. Relationships among moral and contesting variables and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sport[J].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018,47(1):17-33.
[20]Al-Yaaribi A, Kavussanu M. Teammate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s Predict Task Cohesion and Burnout: The Mediating Role of Affect[J].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017, 39(3):1-10.
[21]Kavussanu M, Stanger N. Moral behavior in sport[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17(16): 185-192.
[22]Al-Yaaribi A, Kavussanu M, Ring C. Consequences of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for the recipient[J].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2016(26): 102-112.
[23]Kavussanu M, Boardley I D, Sagar S S, et al. Bracketed morality revisited: how do athletes behave in two contexts?[J].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013, 35(5): 449-463.
[24]De Waegeneer E, Willem A. Conceptualizations of Fair Play: A Factorial Survey Study of Moral Judgments by Badminton Players[J]. Ethics & Behavior, 2015,26(4): 312-329.
[25]Beerthuizen M J, Brugman D. The relationship of moral value evaluation with externalizing behaviour across value areas in adolescents[J].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5, 13(1): 84-98.
Athletes’ Sports Moral Cognition:Concept,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Prospect
CHEN Mengyi, etal.
(Yangtze University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Jingzhou 434020, Hubei, China)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19年研究项目:基于青少年一般道德认知与体育道德认知协同发展的体育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9YJA890044);武汉体育学院院级科研团队项目(项目编号:21KT01)。
陈梦一(1997—),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运动心理学。
祝大鹏(1976—),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运动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