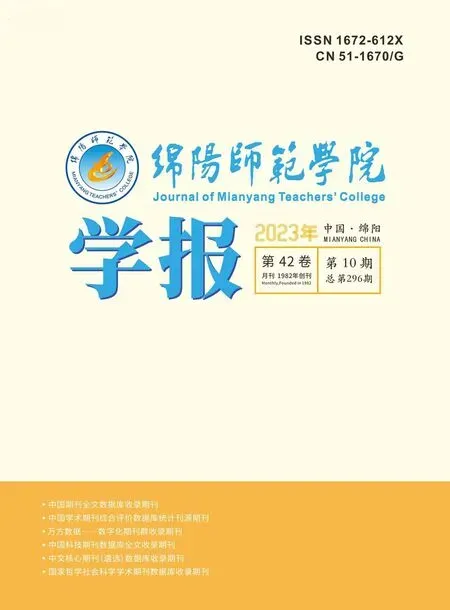他者与自我的权力博弈
——论《为奴十二年》
2023-12-09杨月妮张大为
杨月妮,张大为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第8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为奴十二年》根据所罗门·诺瑟普在1853年所著同名传记小说改编,讲述了黑人小提琴家所罗门·诺瑟普被拐骗至南方种植园十二年的经历。尽管该片有“政治正确”和男性凝视之嫌,但它体现了奴隶制的不合理性,还表达了黑人奴隶对自由的渴望,更深层的则是对“人”的他者化。电影中,在奴隶主的凝视中,黑人的身体不由自己支配,其中女性的身体成了他们欲望的载体,男性的身体则成为彰显、强化、实施白人至上主义权力的场所[1]。一方面,黑人女性是“非人”的劳动工具,另一方面,她们是欲望的符号,也承载着种植园的繁衍生息,三重身份使之难以对抗身份带来的剥削[2]。不仅如此,作为“人”的尊严随着剥夺名字、丧失隐私权和商品化逐步失去,随意买卖和家庭单位的瓦解导致黑人群体产生了文化认同困惑,在白人主流文化体系下失去话语权,逐步形成黑人文化失语[3]。在内化白人奴隶制、宗教、艺术体系后,黑人群体产生了奴性思维,部分成为了主流话语体系的守门员,对他者的处境麻木不仁[4]。
影片中黑人的“他者”处境无处不在,但成体系的“他者化”研究较少,集中体现为性别、种族和宗教他者化与身份研究,尚无地域他者化的研究。那么,《为奴十二年》中的“他者”是如何体现的呢?本文提出,南方白人男性对黑人男性的规训以及南方白人男女对黑人女性的控制,暗含北方对南方的东方主义凝视,以及南方出于地域保护主义引申出的反凝视。
一、他者和东方主义
(一)他者和东方主义
爱德华·赛伊德将“东方主义”视为西方视角下的“现实”,在这一话语下,西方人将自身的价值观和信仰、基于西方政治经济利益的问题和答案强加诸于东方人民[5]。东方主义的准则包括:东西方之间绝对和系统性的差别;比起现代东方,概念中的东方更为话语所好;东方永远无法自我定义;东方要么被惧畏要么被统治[5]。“东方主义”将东方和西方间的边界模糊,并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权威性提出挑战,激发了学界从他者的角度解读现代西方,这一角度试图消解西方—东方、学者的客观性—世俗的动机、表征(representation)—现实的二元对立。赛伊德从福柯的视角看待东方主义,视其为一种生产、编码和流通东方主义体系的话语[6]。在东方主义话语下,作为他者的东方成为了被凝视的客体,话语不仅成了西方传播对东方的偏见和错位表征的集合体,还通过学术作品、游记、文学作品等传播故步自封的、自以为是的一套东方主义话语体系[6],而这套话语下的东方表征与现实相差甚远。
东方主义不仅与主流话语相关,还体现出西方对他者的欲望(desire),既是一种潜在的话语,还以历史和叙事的方式体现出来[7]。在《为奴十二年》中,东方主义体现为南方白人对黑人群体的规训和掌控、南方白人对黑人女性身体的凝视和控制、北方对南方奴隶制的凝视。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以东方主义体现“被动的”东方的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扭曲西方的自身表征[8],这些影片中主导者在规训、调教和加强权力的过程中也在形成与理想不符的自我形象,逐步变成扭曲的“自我”。
(二)黑人和女性他者
“东方主义”作为一套统治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信条,服务一个群体统治另一个群体。东方主义将“一个群体统治另外一个群体”和“群体间有不同”转变为被统治群体的方方面面均低劣于统治阶级[5]。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非裔美国人成为美国主流话语体系中的“他者”,而话语掌权者白人群体则通过压制黑人民权家、政治领袖和学者对反帝反殖民运动的书写实现话语的主导权[5]。非裔美国人受到东方主义话语的影响并非单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某个方面,而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在东方主义话语的引导下,非裔美国人文化的生产、传播、再生产和评估都遵循着以白人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准则,被迫舍弃掉原有的话语体系[5]。
不仅如此,东方主义还通过性别意象兜售话语,通过将东方的女性刻画为勾人的、神秘的、生殖力强的和易得手的客体渗透到东方的文化中,从而与东方女性形成主仆关系,以征服东方女性为手段征服东方,形成政治压迫[6]。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女性,常常遭到统治群体的男性的凝视、幻想和征服,她们的女性气质被强调和异域化的同时,统治群体的男性也在向她们兜售东方男性的女性气质突出的观念。
在《为奴十二年》中,白人奴隶主对黑人男性进行身体规训和男性气质阉割,而对黑人女性进行劳动压迫的同时视其为性欲对象,将黑人群体分而治之(divide and conquer)。对黑人群体的压迫不仅体现在个体上,拆散黑人家庭等手段也在内部分裂黑人群体,使之难以形成反抗的力量以巩固统治。
(三)地域东方主义
“地域东方主义”(或称内部东方主义,internal orientalism)最早用来指代歧视非裔美国人的意识形态[5],后被发展成为对一个国家的部分地区的系统性歧视,即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和种族化的美国南方地区[9]。至今北方仍与“国家”划等号,而南方则被排除在这一定义外。地域东方主义的逻辑是以话语设立一个污名化的地区身份(他者),以及一个平行的地区身份(自我),通过赋予话语下的“自我”更多权力和话语,加强这一部分地区人民的共同体认同感,从而形成一种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9]。
地域东方主义符合东方主义的准则,即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绝对且系统的区别,西方是理性的、发达的、高等的;东方是反常的、落后的和劣等的[5]。在地域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下,国家形象是开明的、进步的、包容的、繁荣的和都市化的;南方则充斥着种族主义、不包容、贫穷和恶意[9]。在美国地域东方主义的话语下,南方的身份和历史都建立在挫败和战败之上,国家身份则保留无辜、美德、成功与胜利[9],通过将南方的身份和历史排除在国家之外,国家身份与历史记忆保留了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一面,即种族平等、经济发达、社会包容和思想进步。
《为奴十二年》中的南方和北方被分割成一个国家内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区,种族主义行径和奴隶制成为仅限于南方而存在的历史伤疤,美国北方和加拿大则成为进步、平等和公正的象征。
二、《为奴十二年》中的他者
在《为奴十二年》中,黑人群体和白人群体并不总是对立的“自我”和“他者”关系,例如所罗门在北方的白人邻里,以及最后帮助他摆脱奴隶身份的北方白人朋友,都和黑人群体是平等关系。然而南方白人和黑人群体却总是处于敌对的状态,无论是拐骗所罗门的骗子、将黑人带到奴隶市场转卖的中介、在福特庄园里轻视和威胁所罗门的白人木工工头约翰·迪比茨、看似善良的奴隶主福特还是“黑奴杀手”埃德温,都对黑人充斥着轻蔑、冷漠和敌对的感情。因此,本文从南方白人的视角出发,探讨白人男性对黑人男性的规训、白人对黑人女性的控制和南方地区在北方的凝视下的反抗,并从电影中着墨较多的人物关系中分析“自我”对“他者”的驯化和操控,以及部分“他者”在凝视下的反抗。
(一)显性的“他者化”——南方白人男性对黑人男性的规训
不同的白人对黑人的“他者化”程度不同,同一个白人在不同时期对黑人的“他者化”也略有差异。因此,本文将随着电影叙事的展开,从不同的白人男性对不同黑人男性的规训,以及同一个白人男性不同时期对不同黑人男性的控制进行分析。本节将时间划分为:被骗时、被人贩子运输时、在福特家和在埃德温家四个时期,分别论述白人男性如何他者化黑人男性。
首先,在所罗门被骗时,白人骗子布朗和汉密尔顿以高价薪酬为诱饵,将之带到华盛顿灌醉并拐卖,此时他者化没有显现。尽管口头上赞许所罗门作为小提琴家的才华,他们却将之卖给视黑人为牲畜和私有财产的中介和奴隶主,不仅不认可黑人的艺术才能,还秉持着黑人只能作为苦力的那一套固有思维方式。因此,他们不仅不认同黑人获取教育和运用才能的能力,还将黑人降格为动物和劳动工具,摧毁黑人尊严的同时,还试图以此加强白人对教育、知识和技能的掌控。白人骗子不仅将黑人他者视为动物,还假定他们没有能力学习、掌握、运用白人主导的知识,已经掌握的则通过售卖为奴的方式收回他者的知识,以巩固白人对知识的主导地位。
其次,人贩子对所罗门和其他奴隶的不同行为的反应开始了他者化链条的第一环。宿醉后的所罗门想要自由和身份,而人贩子则强调他的奴隶身份,通过鞭打让其自证奴隶身份,并没收他之前的服装。如果说售卖黑人的行为是从外部他者化黑人,那么擦除原本的身份、抹除过去的痕迹以及续写新的奴隶身份就是在内部改变黑人的自我认知。通过强调改名、奴隶身份、要求黑人自己承认新身份以及没收原本的服装,中介切断黑人与过去的联系,并让其适应新的话语体系。粗暴的鞭打将“过去的经历”与“疼痛”关联起来,在黑人的头脑中构建出一个反应机制,通过反复鞭打到皮开肉绽,使得疼痛机制烙印在脑海之中,从而形成隐瞒过去和认同现在的应激反应。没收私有财产、更换地方和赋予新身份都是通过让黑人对原有环境陌生化,从而迫使他们接受黑奴和劳工的他者身份。同时,白人让黑人不分男女在公共区域洗澡则是强迫黑人舍弃自尊心和隐私感,强行将他们变成没有男女老少之别的牲畜。通过剥夺黑人的隐私权、尊严和道德感,白人中介彻底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划分了文明—野蛮、人类—动物的界限。此外,为黑人女性出头的黑人男性被随意杀害,随后被同胞抛尸,也为白人在他者间立威奠基。在白人决定生死的船上,被拐骗或欲反抗的黑人都在无形中接受了白人可以随意占用女性“资源”和“反抗即死亡”的规则,也为后来黑人在南方蓄奴州接受奴隶制铺垫。
再次,作为他者化链条的第二环,福特以温和的方式从精神层面让黑人对自己的他者身份产生认同感;白人木工则以威胁的方式暴力强迫黑人接受自己的他者身份。福特通过布道的方式麻痹黑人对苦难的感知,使其更勤勉地工作;他还不顾主仆关系,邀请所罗门加入解决河运问题;问题解决后,福特还奖励了所罗门一把小提琴。较之于威逼黑人的人贩子,福特显得和蔼可亲,使得所罗门在黑人妇女伊莱莎面前为他辩护,忘记了福特是奴隶制的既得利益者。福特看似将黑人当成可感化的、可以思考的同类,实质上仍将黑人当作私有财产,一旦遇到生命威胁和债务问题,依旧毫不犹豫地转卖所罗门。不同的是,福特使所罗门接受了被奴役的现实,甚至站在主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在遇到威胁时也找主人寻求庇护,无意中加深了奴性和他者化程度。正因为福特要求黑人服从白人和满足现状的布道,黑人才不敢忤逆白人的行为,所罗门被吊起时才会无人帮助,最多讨得一口水。福特庄园的黑人在温和的奴隶主、宗教信仰的制约、适时的奖赏下内化了奴隶制,成为听话的奴仆,对自身和同胞的苦难丧失感知力。不同于福特,白人木工约翰·迪比茨强迫黑人为自己的发言鼓掌、唱恐吓黑奴的歌曲、反感黑人比自己能干、禁止黑人指出自己的问题以及对所罗门处以私刑。尽管约翰的行径对天生的黑奴有管制作用,但这种外显的、粗糙的和暴力的种族主义行径在天生的自由人身上碰了壁。尽管约翰没有加深所罗门的他者化程度,但他的种族主义言语和私刑行为深刻体现了南方白人至上主义,也体现了所罗门等人被压迫的他者地位。
最后,埃德温·艾普斯以严刑峻法树立“自我”的威信,成为所罗门他者化过程中的最后一环。在福特思想上同化了所罗门后,艾普斯苛刻的种植园管理使所罗门接受了南方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强奸、鞭打和辱骂。不仅如此,反抗思想被福特和约翰麻痹后,所罗门开始接受奴隶生存守则——藏拙,隐藏了知识、喜怒哀乐和身份,加入到黑人他者群体中。黑人他者们接受埃德温的鞭打,对帕茨的遭遇视而不见,以沉默和谎言对抗“自我”的统治。他者的反抗也加强了白人话语下自我和他者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诚实—撒谎、智慧—无知、力量与统治—弱小与被统治,强化了白人对他者的刻板印象。不仅如此,艾普斯在精神上给黑人施压,布道时通过上帝将不顺从主人和惩罚联系起来、夜深人静时将黑人从睡梦中拉醒跳舞、将虫灾归咎于黑人渎神,都是在通过宗教信仰等方式训练他者的服从。比起麻痹黑人精神意志的布道,艾普斯威胁加恐吓的布道配合严刑峻法,像达摩克里斯之剑,迫使黑人无力反抗,沦为麻木且无力反抗的他者。由信仰和上帝授意的主仆关系从文化信仰上束缚黑人的言行,促使他者畏惧反抗带来的后果,从精神上瓦解黑人联合反抗的力量。
(二)显性的“他者化”——南方白人男女对黑人女性的控制
在《为奴十二年》中,黑人女性一方面遭到白人男性的劳动剥削和性别压迫;另一方面受到白人女性的轻视、嫉妒和报复。较之黑人男性,黑人女性的处境更加艰难,处于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权力斗争的旋涡中,成为二者间的牺牲品。两个孩子的母亲伊莱莎和年轻的帕茨都是白人性别斗争的受害者。本节从黑人女性伊莱莎和帕茨的视角展开,论述她们如何遭到白人男女的他者化,成为白人男女性别斗争的牺牲品。
首先,伊莱莎为白人男性主人生下两个混血孩子,却被主人的白人女儿拐骗到南方,再度沦为奴仆。一方面,伊莱莎的身体受到男性凝视,成为欲望的载体和生殖繁衍的工具,作为无力反抗的女性他者,她寄希望于白人男性;另一方面,掌握大权的白人女性对黑人继母和姐妹充满轻视和不满,因此将她们当成私有财产随意处置。在这对白人父女的权力斗争中,父亲因身体每况愈下而处于下风,女儿占上风却不顾血缘亲情处置了父亲的私有财产——黑人他者。在这个家庭结构中,伊莱莎是女性和黑人双重他者,致使她在两方面前都身处被动和无力抵抗的处境中。随后,在人贩子手中,伊莱莎和黑人男性混浴,又遭到白人男性强暴,维护她的男性也惨遭杀害。在白人人贩子眼中,黑人他者和自我有着动物—人之分,没有隐私和尊严。然而矛盾的是,被当成牲畜的黑人女性又是白人男性泄欲的工具。在身体的控制和尊严的打压下,伊莱莎放弃尊严,屈于人下,沦为了被动的他者。最后,失去孩子和没有同理心的白人促使伊莱莎的他者意识觉醒,以哭泣和沉默对抗白人的控制,招来杀身之祸。伊莱莎的他者反抗意识觉醒得比所罗门早,因为前一段经历让她意识到奴隶制白黑主仆关系的本质以及依附白人的可怕后果,母性又加剧了她对奴隶制度的不满,因此她以哭声反抗不公,也将自己引向毁灭。伊莱莎没有被福特夫人视为女人,而是可以遗忘亲生儿女的雌性动物,思念孩子的哭声在她眼中也只是动物的叫声,没有人的复杂情感。伊莱莎的他者身份让福特夫人忽视了女性的共同身份,而是站在白人奴隶主的角度随意处置私有财产,促使她伤害更弱势的黑人女性。
其次,帕茨因采摘天赋受艾普斯觊觎,又因种族和性别遭到女主人的鄙视、愤怒和嫉妒。帕茨惊人的采摘天赋给艾普斯带来了经济效益,却没有受到奖励,反而因艾普斯畸形的爱意被强暴和控制。一方面,艾普斯对帕茨心怀爱意,为了她不惜与白人妻子翻脸,以此表达自己畸形的爱情;另一方面,“黑人杀手”艾普斯对所有黑人管理严苛,将黑人当成私有财产而非人,只能通过强暴帕茨来抹杀她的人性和尊严,以弥补自己恋上“他者”的心虚感。种族歧视、奴隶制和主仆关系迫使艾普斯将帕茨当成牲畜和非人的他者,但爱意又使他奔向帕茨,遭到妻子鄙视和非议的他转而通过鞭打帕茨来挽回尊严。肤色带来的劳动压迫和女性身份带来的弱势地位让帕茨崩溃,她想摆脱双重他者身份,但宗教信仰禁锢了她的勇气,使她不敢自杀,求他人谋杀,在生死抉择上依旧处于仰仗他人的他者境地。此外,帕茨因艾普斯畸形的爱遭到艾普斯夫人的嫉妒,遭到她的砸、刺、打和间接攻击(剥夺香皂)。肤色让艾普斯夫人歧视黑人群体,然而丈夫对黑奴女性的爱又否定了她的女性气质和性魅力。这种打击使她同时咒骂丈夫和帕茨,然而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的她又对丈夫无可奈何,只好转而攻击更弱势的黑奴。如果说第一次当众砸帕茨是她在尝试剥夺帕茨在公共场域的尊严,那么第二次刺伤脸颊和剥夺香皂就是在剥夺她的女性气质和性魅力,而在众人面前鞭打一丝不挂的帕茨是她在去人化、动物化帕茨,使她丧失女性气质、性魅力和人性,彻底沦为白人话语中的动物他者。
(三)隐性的“他者化”——北方对南方的凝视
《为奴十二年》发生在美国内战前,南方和北方处于蓄奴—自由的二元对立局面,较之于奴隶制根深蒂固的南方,北方接纳自由黑人和黑奴。本节将从三个层面阐述北方对南方的凝视,以及南方对北方的反凝视:电影开头、结尾和叙事角度。
首先,电影开头的所罗门和白人平等相处,以小提琴家的体面身份谋生,在被拐卖后,他被同行者告知目的地是蓄奴合法的南方。电影开头所罗门快乐地为白人演奏小提琴与后来他恐惧麻木地给埃德温伴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北方,黑人可以合法地通过艺术和技艺获得私有财产;在南方,黑奴作为私有财产为奴隶主免费伴奏,且随时面临会被打断和打骂的威胁。在北方,黑人自由人与白人就业机会平等,且能够通过学习、练习和运用符合白人文化的技艺挣得个人财产,尽管黑人需要遵循白人文化主导的文化体系,但人身自由、尊严、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都能得到保障。而在南方,黑人处在白人至上主义体系下,所有人性均被剥夺,成为附属于白人男性的私有财产。这一对比展现了北方和南方的种族平等—种族歧视、自由—奴役、合法个人财产—个人沦为私有财产的二元对立,其中南方被视为不符合北方价值观的他者。
其次,与所罗门第一次求助的南方白人安比斯相比,第二次的求助对象——加拿大人巴斯——追求自由平等,敢于指责奴隶制的不合理和不人道,当面驳斥埃德温的种族主义说辞。而电影对南方白人的刻画皆充斥着种族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表面善良的福特假装同情黑人的他者处境,实则利诱黑人为自己的经济效益服务,一旦面临危险便暗自抽身;南方女性福特夫人将黑人女性视为动物和财产,缺乏同理心,谋杀不服从布道和管教的黑人母亲;白人主义至上者埃德温对黑人施以严刑峻法,将黑人视为私有财产,并通过布道麻痹黑人的反抗精神;埃德温妻子将丈夫畸形的爱归咎于黑人女性,却不敢反抗病态的丈夫,而是对更弱势的黑人处以极刑;看似关心黑人苦难的安比斯酗酒如命,既收取黑人利益,又背刺黑人,贯彻主仆分明的奴隶制。与之相比,反对奴隶制的巴斯和坚持不懈找回朋友的北方白人帕克与黑人和平相处,对落难的人伸以援手,反映出美国的主流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尊重。在电影中,南方白人有各式各样的种族主义思想,并生活在落后的种植园中,而北方白人平等待人,与黑人泰然共事,一起在工业发达的城市中生活。实质上形成了南方—北方、农村—城市、农业—工业、主仆—平等和奴役—自由的二元对立。然而,北方白人身上的种族平等观念挑战了南方白人固有的种族主义思想,并被视为文化入侵。因此,平等自由的北方思想遭到了南方白人的强烈抵制,激起了地域保护主义。例如,巴斯反对埃德温强迫黑人劳动并视其为个人财产,却被嘲笑其加拿大国籍。此外,帕克将所罗门视为“先生”和自由人,要将之带走,却被埃德温阻拦,称其为合法购买的黑奴,在法院有合法的文件。北方对南方的质疑实质上不会纠正奴隶制,短期内只会如电影那样使南方激发更强的地域保护主义,以反抗北方的文化入侵。
最后,电影以北方人所罗门的视角觉察到了诸多北方闻所未闻的种族主义行径,通过北方和南方的文化冲突,展现出以所罗门为代表的北方人对南方奴隶制的价值判断。刚被拐卖的所罗门以为自报家门就能重获自由,预设了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和信任,以及由于北方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以致于他对所有白人卸下防备心,被拐卖后急于自证身份。在船上邀请黑人同胞反抗的黑人也预设了同胞的团结和反抗精神,而忽视了北方也存在麻木不仁的天生奴隶的事实。不仅侧面印证了北方社会中自由黑人的普遍性,也印证了北方的自由、独立、勇敢和民主精神。所罗门敢于驳斥白人木工约翰,甚至夺过鞭子殴打他,也印证了北方社会文化中的尊严、平等、勇敢和反抗思想。总之,所罗门和北方黑人面对南方种族主义行为反映了北方文化对南方奴隶制文化的冲击,也侧面印证了北方的种族平等思想,批判了南方异化、非人化和机器化黑人的强迫劳动体系。
三、他者与自我的权力博弈
《为奴十二年》审视了六个群体:南方白人男性和女性、北方白人、南方黑人男性、南方黑人女性和北方黑人,尽管叙述者是北方黑人,但权力的主导者仍为白人群体。在六个群体中,北方白人对所有黑人群体怀有同情和尊敬之心,将之视为“自我”群体的一部分,敌视违背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南方白人群体;而南方白人轻视黑人群体的同时,也反对北方白人对自己的他者化,并以更强大的种族主义行径抵抗北方主流话语,以维护南方地域主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同为主流话语体系中的“自我”,北方黑人也无法完全与北方白人平起平坐,例如电影中一闪而过的求救的纽约州黑奴依然是低人一等的存在,北方白人也将之视为奴隶而非“人”。不仅如此,南方白人男性和女性也处于“自我”间的斗争当中。南方白人女性经济和文化上依附于男性,却囿于他者文化对黑人女性的性化及其带来的性吸引力,被南方白人男性当作与黑人女性平等的性欲对象,遭受了种族和女性气质羞辱。为摆脱南方白人男性带来的经济、精神和肉体羞辱,白人女性一方面试图摆脱白人男性眼中的“他者”身份,另一方面打压更弱势的黑人女性,以削弱其女性气质和摧毁他者尊严的方式向白人男性反击。将黑人女性视为性对象和私有财产的南方白人男性,不仅对东方主义驯化下诱人的黑人女性产生更多占有欲,还因种族歧视感到羞耻,在精神博弈的侧面劣逊于“他者”白人女性。最后,同样是南方白人眼中的黑人“他者”,黑人男性因性别优势免遭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但受到白人男性的劳动压迫和男性气质阉割。在黑人反抗后,南方白人以私刑处置,以警示其他黑人群体。而黑人女性不仅需要在南方白人男性和女性的权力斗争中表现得乖巧沉默,还需要承受白人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凝视。总之,北方白人和黑人同属于“自我”,却通过将后者分类,选择性地他者化没有自由人身份的黑人。北方白人又因其文化和话语将南方白人视为种族主义的“他者”,而南方白人在其凝视下以加强种族主义行径的方式进行反凝视抗争,这一过程中,奴隶制是他者化的催化剂。同为北方白人眼中的“他者”,南方白人男性和女性处于权力抗争中,以性别为界“他者化”彼此和黑人。
此外,南北方的二元对立也体现出自我和他者的权力博弈。南方和北方两个建构的地理概念被塑造成了一组消极—积极、落后—先进、种族歧视—种族平等、贫穷—繁荣、不容忍—包容的二元对立,其中南方在主流话语中处于他者地位。地域东方主义将南方他者和北方自我身份建造成话语的一部分,并通过话语生产、再生产和传播这一“事实”。遭到他者化的南方因不满他者身份而反抗地域东方主义,但因难以撼动话语中的认知体系和存在性而促进了地域东方主义的再生产[10]iii。在《为奴十二年》中,南方白人为反对北方白人的批判、捍卫南方种植园传统和促进经济发展,加强了奴隶制,并为之背书。他们不仅反抗北方白人赋予的他者地位,也不满北方占据的道德高地。
四、结语
《为奴十二年》反映了南方白人男性、南方白人女性、北方白人、南方黑人男性、南方黑人女性和北方黑人群体间的“自我”和“他者”的身份博弈,以及北方对南方的他者化和南方在北方凝视下的反抗。由此可见,种族主义奴役黑人的同时,也在反噬白人自身,使其受到主流话语的批判。
《为奴十二年》中没有赢家,只有奴隶制留下的伤疤和因此永久蒙尘的美国南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北方并非没有奴隶和种族主义,只是在主流话语的书写中将黑暗的种族主义历史凝练在南方的记忆和想象中,而保持了北方完美的“自我”形象。笔者认为,美国社会在反思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基础上,也应避免对北方的过分美化,正视南北方潜存的种族主义。另外,南方不仅是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思想的祸乱之地,同时也是美国黑人的故乡,凝聚了美国黑人祖辈生存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10]iii。持续他者化美国南方也是在持续受害者化美国黑人,将其放在弱势的他者地位。最后,美国社会应当给予黑人女性更多自我表征的机会,避免他者化。